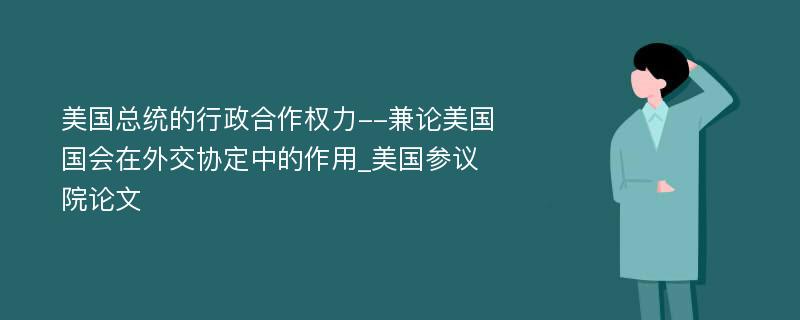
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兼论美国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国会论文,协定论文,美国总统论文,外交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外交协议从缔约主体而言,可以分为条约、纯粹的行政协定、国会—行政协定三种。透视总统行政协定权的发展规律,似乎可以看到总统权力呈不断扩张的趋势,然而,这并不是说国会在缔结外交协议过程中无所作为。
一、行政协定权的起源与发展
从宪法文本而言,与美国总统的行政协定权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内容主要有:(1)宪法第1条第10款同时提到了条约(treaty)、公约(compact)和协定(agreement)。“任何州不得缔结条约、结盟或加入联盟”。“未经国会同意,无论何州均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公约或协定”。(2)宪法第2条第2款,“总统根据或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有权缔结条约,惟需有该院出席议员三分之二之赞同”。(3)宪法第6条“本宪法,依照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及经合众国授权已经缔结或将来缔结之条约均为本国之最高法”。
宪法第2条第2款的“缔约权条款”中包含着许多内容:如提出和谈判条约的权力属于总统,总统本人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谈判,但是,至少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总统缔结的条约必须得到参议院出席参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票的同意。在美国宪法中,涉及“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的条款只有4条,除上述条款外,其他几条涉及的内容包括:被总统否决的议案、命令、决议或表决需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的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重新通过;国会开除议员得经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认为必要时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这几个条款之所以采用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而不是过半数,应该说是着重强调了条款内容的极端重要性。1787年立宪时的“大妥协”协调了大小州的利益,众议院以人口比例分配议席,大州占优势,参议院每州拥有两个席位,小州占优势。“缔约权条款”只给予了参议院建议与同意的权力,而把众议院排除在缔约程序之外,可见,立宪之父们把缔结条约视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政府行为,缔约权由谁行使涉及的是权力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程序问题。缔结条约过程中设置一个“三分之二”的“门槛”,可以避免签订一些损害少数州的经济利益的条约。
不过,美国参议院素有“条约的坟墓”之恶名,(注: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2页。)原因在于总统缔结的一些条约,在参议院遭到了扼杀。参议院拒绝批准总统及其代表谈判和签字的条约,虽然大约只占1%,然而其中不乏重要条约。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倡议成立国联,并缔结了《凡尔赛和约》。然而,参议院与威尔逊不和,许多议员发表演说反对该条约的通过,当时参议院的投票中,49人赞成,35人反对。威尔逊为此十分生气。于是,他启动专列到各州演说,努力说服参议院批准该项条约,他演说22天,行程8000英里,发表演说40次,然而,参议院在1919年、1920年的两次投票中,都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拖延两年后,仍未获参议院批准。1979年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签署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也遭此厄运。(注: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最有名的例子,当数《种族灭绝罪行公约》,被冷落在参议院的档案架上达37年之久。在条约草案拟订40年后,才得到国会的支持并通过。这使美国总统们在国际舞台上大丢面子,也使许多国家对美国出尔反尔的行径大为不满。(注: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4-85页。)
为了规避参议院的“建议”与“同意”,总统以及行政当局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会签订一些不需经国会任何一院建议与同意的行政协定。或者,行政机关也会依据国会的授权制定一些行政协定。也许,国会这方面的最初正式授权可以追溯到1792年的一个法令,允许美国的邮政部长“可以与任何国家的邮政部长签订通过邮局来互相接收和邮递信件、包裹的协定”,不需要经过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此后,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夏威夷,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关于保护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协议,行政机构在处理领土争端、疆域界分的问题时,都采用了行政协定。
这些行政协定在国际法、国内法上的效力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与此相关的案例有1937年的“美国诉贝尔蒙特案”与1942年的“美国诉平克案”。这两个案例都涉及1933年罗斯福与苏联政府代表李特维诺夫签订的承认苏联的《李特维诺夫协定(the Litvinov agreement)》。1918年,苏联政府成立后,宣布没收俄罗斯私营公司。在“美国诉贝尔蒙特案”中,美国政府接受了苏联转让的一笔资金,这笔资金是苏联政府没收的一个俄罗斯钢铁公司在纽约的存款,美国的地区法院依据州法判决美国政府的行为不合法。最高法院裁定地区法院是错误的。法官提出,总统承认苏联政府的行为以及它签订的行政协定构成了一个国际公约,而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总统可以成为签订国际公约一个独立主体,不需要咨询参议院的意见,当然,也就不需要考虑州法和普通政策。因为,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了条约的最高性,但是宪法也规定了,“无论何州均不得……与他州或外国缔结公约或协定。”缔结公约与协定的权力属于联邦政府。“美国诉贝尔蒙特案”确立了这一原则:条约和行政协定都享有宪法第6条所规定的最高法律的地位,凡与之抵触的州法均受之约束。同国外缔结行政协定,是总统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无需参议院批准。(注:http://caselaw.lp.findlaw.com/data/constitution/article 2002/12.)1942年的“美国诉平克案”争论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依据1933年的the Litvinov agreement恢复一家俄罗斯保险公司在纽约的分支机构的资产。公司提出,苏联政府没收财产的法令并不适用于它在纽约的财产,此外,这与美国及纽约州的宪法都不相符合。(注:http://caselaw.lp.findlaw.com/data/constitution/article 2002/12.)但是,法官认为,联邦政府承认苏联政府的官方声明对州有约束力。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再次肯定了1937年的裁决。
此后,总统便尽可能地多同外国签订行政协定,少缔结条约,以摆脱参议院的制约。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确切地说,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行政协定迅猛增长,不管是其数量,还是涉及政策的重要性都远远超过了条约。在美国立国后的前50年中,条约是行政协定的2倍;在1839-1889年间,行政协定的数量开始超过条约;在1889-1939年间,行政协定的数量是条约的2倍;自从1939年到现在,行政协定占了美国国际协议的90%多。一些重要的外交问题,例如使美国介入欧洲战争的1940年美英《驱逐舰换基地》的协定(罗斯福与英国签订协定,以超龄驱逐舰交换海军基地,帮助了载运军用物资穿越北大西洋的英国船队),《德黑兰协定》,对战后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1945年《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结束越南战争的1973年《巴黎协定》,都采用了行政协定的方式。此外,行政协定还用于实施马歇尔计划,同许多国家达成秘密军事协议,作出军事承诺,提供援助等。(注: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5页。)特别要注意的是,许多行政协定都是总统暗中签订的,典型的如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
总统行政协定权的发展,使美国出现了一个不受到任何制约的权力,三权分立原则失去了平衡,出现了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等“帝王总统”,就像有人慨叹说,“今天,美国仍然拥有一位国王,而英国仅仅保有一顶王冠”。(注:分析的数据来源: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January 2001),p.31.)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监督与制约总统权力的起因。国会于1972年通过了《凯斯—赞博洛克法案》,国务卿必须把所有行政协定的副本在生效后60天之内递交给国会。如果总统认为行政协定的公开会威胁到国家安全,行政协定就交由参议院的对外关系委员会或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进行保密分类。事实上,大多数的行政协定都没有向国会汇报。不过,国会制约总统权力的企图失败了,最终引发出70年代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政治危机,国会才逐步地收复失地。可见,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一直在平衡—失衡—平衡中寻求一种动态的稳定。
表一:1789-1989年美国的条约与行政协定(注: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行政 行政协定占全部对外协定的
年份
条约
协定 百分比
1789-1839 60 27
31.0%
1839-1889
215 238
52.5%
1889-1939
524 917
63.6%
1939-1989
702 11698 94.3%
二、行政协定的规律
在实践中,美国总统可以选择三种缔约国际协议的方式:
1.条约。条约的名称可以有许多种,如国际公约、宪章、协议、声明、议定书、备忘录等,它是国际上多方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既有双边条约,又有三方条约。总统提出、谈判并缔结条约,参议院提出咨询意见、表示同意。宪法文本隐而未述的意思是:总统是外交事务的执行者,而外交政策之形成则在于参议院,参议院就像是总统在执行外交事务中的一个咨询委员会。以美国参加联合国和北约为例,《联合国宪章》或《北大西洋公约》的每一条都需要参议院三分之二的批准。然而,“政策执行”与“政策形成”之间的界限在实践中实在非常模糊,难以把握。为了贯彻条约的国内义务,行政机构可以依据条约制定行政协定,这是条约授权的行政协定。
2.纯粹的行政协定(sole executive agreement)。美国的行政机构与外国政府签订的、无需参议院批准的协定。行政协定的签订主体并不局限于总统,而是包括总统在内的行政机构,比如说政府各部门的部长。然而,行政协定真正实施时,一般都需要国会制定一些法规来配套。国会如果持反对意见,通常就会在此过程中设置一些障碍。
3.国会—行政协定(the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agreement,简称CEA),也有的称之为立法性协定(the statutory executive agreement)。(注:三种协议的定义参见:Louis Henkin,Foreign Affairs and the U.S.Constitution,(New York:The Foundation Press,2d ed 1996)pp.175-230.)由于美国总统经常运用行政协定来处理重大外交问题,规避了参议院的建议与同意,这一方法引起了参议院的不满,而众议院早就对自己被排除在缔约程序之外不满了,在两院的要求下,美国又出现了另一种协定——国会—行政协定。与条约不同的是,国会—行政协定不超越于现行法律之上,也不需要三分之二的参议院同意,它只是要求总统缔结某些行政协定时,也像国会制定普通法律一样,在国会上、下两院以简单多数通过。国会—行政协定给予参众两院同样的建议和同意的权力,从而也给予了参众两院同样的否决或修正的权力。
在这三者中,条约由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同意才能生效,国会—行政协定由两院的过半数同意,纯粹的行政协定不需国会的同意,纯粹依据宪法授予总统的权力。如果说美国总统凭空创造了这一“行政协定”权,这也是言过其实。宪法第1条第10款对条约、公约、协定作了界分,明确规定各州不能作为缔结条约的主体,不过可以成为公约与协定的缔结主体,前提是得到国会的同意。这其中隐含着的意思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一些条约之外的“公约”或“协定”,既然州可以成为缔结公约、协定的主体,那么总统及行政机构也可以成为缔约主体。(注: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第83页。)而且,依据宪法的授权,“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总统得提名并根据或征得参议院之意见并取得其同意任命大使、其他使节、领事”,总统在外交事务中享有一定的缔约权。问题在于,尽管宪法中对条约、协定和公约做出了区别,然而,其中的差别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宪法却并没有明确。什么情况下选择条约?什么情况下选择行政协定?宪法没有提供一般的、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哪些是总统可以、应该、必须缔结的协定?
条约、国会—行政协定、纯粹的行政协定数量的消长,体现出美国行政权、立法权的消长,从行政协定数量的增长,清晰地勾勒出总统权力不断膨胀的脉络。纵观美国历史,可以总结出行政协定的一些规律:
1.内容:以20世纪40年代为界,以前,条约多用于解决与重大、长期利益相关的问题,行政协定通常用于解决短期的、技术性的问题,如疆域的界定、捕鱼权等。之后,行政协定往往用来解决重大的政策问题,而条约反而用来解决一些细节问题。
2.形式:总统之所以选择行政协定而不选择条约,主要考虑是行政协定的程序比较简单。因此,选择行政协定还是条约受到总统和国会关系,尤其是总统与参议院关系的影响。两者关系融洽,总统可能就选择条约,两者关系不融洽,则可能选择行政协定。
表二:美国1930-1999年期间行政协定权的数量增长(注:作者依据下列数据统计而成: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p.31.)
年份
条约
行政协定
行政协定所占百分比
1930-1939 132 154 53.8%
1940-1949 116 919 88.8%
1950-1959 138
2229
94.2%
1960-1969 108
2162
95.2%
1970-1979 173
3039
94.6%
1980-1989 160
3524
95.7%
1990-1999 249
2857
92.2%
3.数量:行政协定的数量总体上呈逐渐增长的趋势(见表二)。具体到每届政府,如果总统与国会中的多数党不是同一政党,尤其与参议院的多数党不属于同一政党,条约的缔结难度增大,那么该届政府行政协定的数量就会增多。即使总统与国会的多数党是同一政党,如果参议院中多数党所占席位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总统仍然没有绝对的把握获得参议院的三分之二同意,那么,总统在签订国际协议时也会非常谨慎,这一时期的行政协定也会增多。1930-1999年间,只有1976年、1977年、1978年、1986年、1987年五年每年的行政协定超过了400个。1976年、1977年共和党人福特主政,参议院中民主党占据了60个议席,1986年、1987年共和党人里根当总统,民主党人占据了参议院的55个议席。(注:分析的数据来源: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p.31.)
在同一总统的任期内,行政协定的比例通常随着任期逐渐提高(如表三、表四所示)。原因在于,总统就任的第一年是总统与国会的“蜜月”期,总统往往能如愿以偿,但遗憾的是,总统们对自己所应达成的目标还缺乏经验。因而,他们总是小心翼翼,签订的行政协定也比较少。随着经验逐渐积累,他们对如何能达到目标有了更好的设想,但偏偏这个时候国会中能投票赞成他们方案的支持者比过去减少。尤其是当国会控制在反对党手中,或者执政党内部有不同的派别,总统会发现,他的许多设想往往会被国会扼杀。因此,随着在职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国会的成功率越来越低。总统就会绕开国会,另辟蹊径,通过增加行政协定来解决外交问题。这就导致了行政协定比例的增加。
表三:总统任职期间每年签订的行政协定的百分比——杜鲁门到卡特(注:Lawrence Margolis,Executive Agreements and Presidential Power in Foreign Policy,(New York:Praeger,1986)Special Studies,转引自Victoria A.Farrar-Myers提交美国政治学协会2002年年会的论文:Presidential Use of Executive A greement in the Post-case world.)
艾森豪
杜鲁门
肯尼迪
约翰逊
尼克松
福特
卡特
威尔
5.8%
8.8% 32.8%
2.7%
12.9%13.3%
55.4%
9.8% 11.1% 42.2% 20.2% 17.1%38.6%
44.6%
11.9%
17.2% 25.0% 19.5% 17.7% 48.1
13.8% 13.0%
20.7% 22.4%
13.6%
11.5%
20.5% 18.2%
10.6%
10.7%
16.5% 11.8%
16.8%
13.0%
17.7%
14.6%
总数: 1466
1824
759
1089
1234
754
670
表四:总统任职期间每年签订的行政协定的百分比——卡特到克林顿(注:
作者依据下列数据统计而成: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p.31.)
卡特
里根
布什 克林顿
27.7% 11.3% 26.9% 13.7%
23.5% 12.1% 29.5% 18.1%
23.6% 9.9% 21.2% 16.0%
25.1% 11.8% 22.4% 13.9%
13.7%
11.8%
13.9%
14.1%
10.6%
15.3%
13.6%
总数: 1364
2840
1350
1870
三、国会在外交协议中的地位与作用
尽管宪法文本规定的“缔约权条款”在现实中发生了变化,总统通过行政协定权扩大了行政机构在外交事务中的权力范围,然而,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国会在外交事务中无足轻重,那就大错特错了。国会对缔约权的影。向仍然不容忽视。原因在于:
1.尽管行政协定在外交协议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是,纯粹的行政协定只是占了行政协定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是国会—行政协定。依据约翰逊与麦考米克的调查,在1946-1972年间,87%的协定属于国会—行政协定,其余的7%属于行政协定,6%属于条约。他们考察了五位总统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发现他们的外交协议所采取的形式差别不大,即使杜鲁门执政期间签订行政协定最多,80%也属于国会—行政协定。(注:Loch Johnson and James M.McCOrmick,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a Reappraisal of Congressional Involvement,Journal of Politics Vol.40:468-478.)可以说,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条约与国会行政协定之间,而不是一条约与行政协定之间。条约为美国最高法律,缔结者必然有立法权。从法律角度而言,国会—行政协定可以把批准外交协议与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这两者合为一体,使外交协议在国内产生法律效力。因此,“现在人们承认,国会—行政协议是在宪法上可接受的另一种条约缔结方法”。(注: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第87页。)可见,行政协定数量的增多并没有削弱国会在缔结外交协议中的地位。
2.美国不存在欧洲宪法中的“国际法至上”、“条约至上”的理念,条约、行政协定在国内法的地位是不确定的。
条约是国际法的一个主要渊源,对国家产生外部约束力。但是,国际上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超国家的组织可以强制执行国际法,国际法只是通过国际舆论的压力、国际法的“软约束”和国际干预等限制国家行为。国际法不关心各国国内如何对待条约,因此,条约在国内法的问题是一个宪法问题。欧洲许多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际法至上”、“条约至上”的原则。尽管国际法也是美国法律制度的一部分,但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却是不明确的。一些人认为国际法只是联邦法律的一部分,并不存在“国际法至上”、“条约至上”的观念。他们的理解是,对“国家”产生约束力的条约并不必然对“国民”产生约束力。前者是个政治问题,而后者才是法律问题。(注:Frances Fitzgerald,Politics as law?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Treaty,n California Law Review,Vol.89:851-916.)就像汉密尔顿所说,“缔约工作的目的是与外国订立契约。此种契约虽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其约束力出于国家信誉所负义务。条约并非统治者对国民制定的法规,而是主权国对主权国订立的协定。……并不真正属于立法或行政范围”。(注:[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9页。)
在美国,条约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自动执行的条约(self-executiving treaty),即条约能够自动转成法律,由总统和法院自动履行。第二,非自动执行的条约,这种条约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要求缔约双方制定必要的法律使其生效,如《种族灭绝罪行公约》;第二种是要求制定相关的协定来加以执行,如调拨经费、宣战等等。条约连同“必要而适当条款”,可以为立法作依据。麻烦的是,在实践中,参议院和法院越来越倾向于将条约视为或解释为需经国会颁布实施法规的非自动执行条约。(注: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第92页。)如果这样,就可能出现条约与立法不一致的情况。也就是说,条约对国家的约束力并不必然转化成对国民的约束力。
依据美国宪法第6条的规定“本宪法,依照本宪法制定之合众国法律及经合众国授权已经缔结或将来缔结之条约均为本国之最高法”,条约在国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是,人们还把第6条解释为,条约与宪法性法规的地位相同,当条约与宪法性法规相冲突时,采用“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即以制定时间较后者为优先。而且,宪法并没有明确禁止国会制定与美国的国际义务相违背的法律或采取与之相悖的行动。这样,在现实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条约与法律相冲突的情况。而依据条约与法律同样地位且以后来制定者为准,引起的后果就是:即使条约批准生效,美国也不必然承担条约中规定的国际义务。美国的“国内法高于国际法”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
条约的遭遇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身份”本来就暧昧不明的行政协定了。纯粹的行政协定所依据的是总统的宪法性权力,然而,由于没有国会的介入,在美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尚处于争议之中。这里面涉及几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国会立法。行政协定与国会立法相矛盾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最高法院尚未作出裁决。法院似乎不愿意受理涉及国会与总统权力冲突的案件,一般都把类似案件界定为政治问题而加以回避。从美国的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行政协定与国会立法产生冲突,行政协定能否占上风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其二,州议会立法。1937年的“美国诉贝尔蒙特案”与1942年的“美国诉平克案”确立了行政协定无需参议院的介入,对州法有约束力。但是,在学术界,这并没有成为定论。倾向联邦主义的学者认为,这侵犯了州的自治权,仅仅是国家主义者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法律上缺乏依据。(注:David Sloss,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the Political Safeguards of Federalism,Stanford law review,Vol.55:1963-1997.)其三,州的普通法律。行政协定对与其冲突的州的普通法律具有约束力,这是大家惟一可以取得共识的问题。
3.至为重要的是,条约或行政协定的执行权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美国总统缔结行政协定,通常用来缔结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关于其他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同意。比如,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揽子协议,就属于克林顿行政当局与外国签订的“行政协定”而不是“条约”。也就是说,没有国会的批准中国照样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即使在签订行政协定以后,也存在着行政协定的国内效力问题、与之相关的法规能否得到国会的支持的问题。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行政协定”与国会要严格审批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密切相关。国会不仅要讨论,而且有权通过或者否决这一法律程序。把中国带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总统克林顿以及行政当局在1999年的一个重要外交成果,但是,如何游说国会并使国会通过给予中国PNTR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只有参、众两院通过了必要的实施法规,才能使中、美协议付诸实施。
尤其当条约或行政协定涉及拨款等事项,总统就无法排除国会的影响。因为宪法第1条第9款规定:除根据法律规定的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提取款项。有关对外军援和对外经援的行政协定涉及拨款,掌握“钱袋子”的国会经常会削减款项。早在1975年,国会就要求行政部门汇报一次成交额超过2500万美元的军售,而且国会可以在20天内否决该案。1976年,国会又通过了《武器出口管制法》,此法最初曾遭福特总统否决,国会经过修改妥协后始获通过。向外出售武器,一次成交额若超过700万美元,须通知国会,国会可在30天内以共同决议予以否决。在此过程中,国会可以利用拨款程序与总统讨价还价,影响其对外政策。
可见,尽管行政协定权的增长意味着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权力的增长,然而,国会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来影响条约、行政协定等国际协议的国内效力,在20世纪80年代,民主党占主导的国会给共和党的总统对中美洲实施军事干预增加了难度;在90年代,共和党占主导的国会通过扣压对一些多边机构以及联合国的会费,让民主党的总统受到掣肘。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四、对我国制定外交政策的意义
外交协议在美国国内法中的特殊地位揭示了美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一大特点。正如一位美国外交百所说:“我们有一个行政机关来作出承诺,同时有一个国会来否决这一承诺。”(注:Nancy Bernkopf Tucker,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373.)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了解美国外交事务中不同名称的国际协议的意义。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可以选择条约、国会—行政协定、纯粹的行政协定这三种方式与其他国家缔约。选择哪一种方式缔结协议,是美国的一个战术性问题。尽管对美国自身而言,缔结条约需要征求参议院的意见,并得到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的同意,这一缔约方式增加了缔约的成本,而且可能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然而,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看,如果参与缔约的另一个国家急于签订这一条约,那么,美国总统在谈判时,就可以以参议院提出的意见、参议院通过时可能提出的条件相威胁,从而增加了谈判时的砝码。而运用纯粹的行政协定方式又可使美国迅速地和悄悄地在外交领域中采取行动,无需国会的任何卷入。这就使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处于一种比较灵活、有利的地位,从而确立了美国对外事务中的优势。
2.我们要区分并了解条约、行政协定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效力,选择合理的缔约方式。依照国际判例说明,不同名称的条约并不意味着条约法律效力的不同。然而,依照美国的逻辑,不同主体缔结的外交协议效力不同。比如,中美关系是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communiqué)的基础之上的,联合公报是由行政机关制定的,但国会在1979年就通过了《对台湾关系法》。美国一部分人认为联合公报只表明一种外交宣誓,属于所谓的“无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政治需要,美国会在一段时间内承诺遵守联合公报,而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就会通过国会立法进行一系列反华活动。然而,按照国际惯例,中美联合公报明确了双方权利和义务,在国际法上是有约束力的。因此,在处理中美外交事务过程中,我国需要选择能够最大程度保护我国利益的缔约方式。
3.研究美国国会的院外游说活动,促进中美两国的民间交往,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影响。不管是条约、纯粹的行政协定还是国会—行政协定都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这就是外交协议的国内效力问题。我国在开展外交活动时,就得努力寻求对国会议员的影响。当前美国注册的游说集团共有2万多。1999年,游说集团平均花费在每个国会议员上270万美元,总计共1.42亿美元。以色列、中国台湾、希腊是三大院外游说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被称为“美国的第五十一州”。(注:Eugene R.Wittkopf,Charles W.kegley,James M.scott,American Foreign Policy:Pattern and Process,Belmont,CA:Thomson/Wadsworth,2003.)中国台湾一度花费了四百万美元雇用了一个名为卡西迪的公关公司(Cassidy and Associates)进行游说。(注:Nancy Bernkopf Tucker,China confidential: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945-1996,p.478.)前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汉密尔顿在与复旦大学师生的电视座谈会上说,“国会议员们不能用战略眼光来看待美中关系……他们往往只注意一时一事”。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美国政界人士更注重国内事务而不是对外政策,并且认可把对外政策与党派政治掺和在一起的做法。(注:《前众议员汉密尔顿谈中国与美国国会》,《美国参考》。)白宫、国务院、国会之间的冲突,国会两党之间的冲突使中美关系往往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国会往往以人权、贸易等借口阻碍中美协议的配套法规。因此,我国要深入研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与地区是如何努力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同时,利用一切民间组织如环境保护、商业贸易、文化交流等,加强中美两国的民间交流,从而真正影响美国国会,在外交事务中占据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