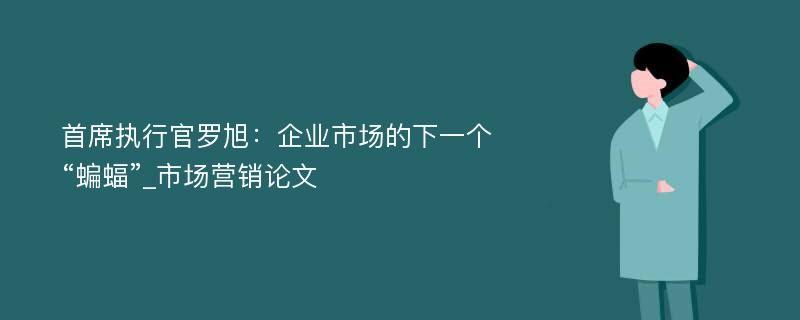
纷享销客CEO罗旭:做企业级市场里的下一个“BAT”,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级论文,市场论文,CEO论文,纷享销客论文,BA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一年内完成三轮融资的公司其实并不多,你会怎么解读纷享的融资节奏? 罗旭:过去一年,企业级市场在快速催化和成熟,就像当初智能手机快速地主流化一样,我们判断未来一到两年内,整个企业级市场也将完成“移动化”转型。市场在快速成熟,我们要跑得足够快,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融资去扩大研发团队,获得足够的技术能力。现在北京只是我们一半的团队,另外一个研发团队在深圳。 在庞大的研发团队之外,还需要强大的销售能力,企业级市场产品是需要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需要为此建立庞大的“最后一公里”销售体系。另外,塑造品牌、教育用户也需要很高的成本。 当然,融资最重要的用途是配合整个公司的战略升级。战略升级是指之前我们要做工具,但是未来我们想做平台。 用户从前端看到我们是一个企业级的工具,但其后端是构思着非常庞大的企业级平台。这部分的投入是巨大的,未来我们判断,至少要投入两到三亿元去做这个平台。 现在我们产品在销售领域的专业能力更强了,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另外工具本身体系能力也在不断精进,就像微信,你会发现这么多年它的形态没怎么变,但是功能增强了。 记者:纷享从2011年成立到现在,公司有过哪几次大的转型?可否为我们还原一下。 罗旭:当年我在《新京报》做总经理,出去见客户常常一天都在外面,回到公司最头疼的是好多事情不知道。很多人在等你签字,但我很多时候在外面开会。所以我本身就是企业服务痛点的诉求者。我觉得日常工作不能靠口口相传,需要一个平台沉淀下来。 我们第一个关键节点在2013年6月,是整个公司的定位转变。当时我觉得移动办公有一定诉求,是个产品方向,但具体怎么承载呢?是要把整个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系统做到手机上吗?其实不是。我还是觉得,做一个社会化的东西更有意思,那时候企业级社会化最好的表现形式不是微信,是微博,也就是美国的Yammer那种模式,选择用社会化的模式来做企业的移动办公。那时候有个名词叫企业社会化。 但是我们做了一年多之后,发现教育企业去做移动办公还是痒点,不是痛点。慢慢我们发现移动办公对那些跑销售的人最有价值,所以当时我们就把方向转到了移动销售管理。这个转型到今天来看是非常成功的,第一切到用户痛点,第二产品也更聚焦。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我们产品形态的变化。我们从一个微博的模式变成了微信的模式,从企业社会化平台变成了企业通讯平台。这对整个技术交互能力要求很高,但是当时我们顶住了所有压力,把产品彻底掰过来,结果发现用户喜欢,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微信的模式。这个时间点大概在去年三月份。 最后一次重要的转变是在今年。我们决定做开放平台。基于开放的架构,让其他第三方的业务接入到我们产品中来。你可以通过我们平台做很多H5的页面,包括名片、简介、活动通知……然后把制作好的信息转发到微信里,我们帮你统计转发、点赞数。将来还会涉及电商。 记者:调整的过程和预期中一样顺利吗? 罗旭:刚开始“掰”产品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我们是做业务和销售管理的,一旦决定做企业微信的模式就相当于多做一个通讯层,恰恰这部分是最难做的。这个要求太高,就相当于以前我们是造火车的,就够难了,现在还打算修铁路,做底层。 我们相当于在做了企业的通讯之上又做了企业的销售管理体系,产品复杂度、开发投入度非常大,那时候我们的产品团队才30多个人,要干300人的活,所有人压力都非常大。 记者:除了自身发展需要,这中间企业级市场大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促使你下这样的判断? 罗旭:比如说像第一次和第二次,究竟是做整个移动办公协同还是去选择一个更具体的针对销售方向的产品,这个通过市场最终得出结论。包括产品现在这种形态,从SAAS模式转向企业级通讯的方式,这也是实践总结。 谁都曾经梦想过做平台,但是一开始做平台你是不是具备这个条件和能力?到现在,我们感觉时机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可以做大的转型。 但转型是有风险的,你要重新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做未来三到五年长足发展准备,这个时候你做这个的能力和环境是否匹配,做早是死,做晚没机会了。 记者:前几年刚做纷享时经常有人会问你是不是想做中国的Yammer,现在还会有类似的比较吗? 罗旭:Yammer后来被微软收购了,和微软的各个业务线紧密融合。现在我们的定位更清晰了,专注做销售管理,产品形态也从企业社会化的模式,变成一种企业级通讯的模式,现在我们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企业级的通讯服务商了。 Yammer迎合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产品的诉求,那是邮件的时代,但是你想,真正在微信出来之后,Yammer的交互模式就会迅速地被边缘化。有些产品可能有亮点,但真正好的产品还是要有价值创造,并且可持续。 记者:过去三个月,纷享的员工数增加了600多人,网上有一些报道会质疑你们扩张过快。你怎么看? 罗旭:有人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度——你能不能驾驭这件事情,这是大量扩张的前提。去哪儿网当年也仅仅用了一两年时间就做到和携程的体量相当,所以快和慢之间没有对和错,而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个速度,其次要看这个速度跟你公司战略是否匹配。我认为企业在整个竞争过程中的窗口期就是24个月到48个月,为快不破。 记者:在这之前,什么原因促使你决定快速扩充团队? 罗旭:第一产品相对成熟,第二我们整个营销模式体系成熟,第三我们管理思路和体系基本上成熟。这个事,只要是有这三个成熟,我们就OK了。另外市场空间无比的大,用户本身也在快速地成熟,当市场和用户已经成熟,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速度。 记者:所以现阶段,我们追求速度第一? 罗旭:速度和能力都是应该匹配的,有人跑得很快,但是不稳,有人走很稳但是走不快。比如联想这种公司现阶段不需要跑得快而是跑得稳,战略不要出错。 企业分三个阶段:创业期、快速成长期、成熟期。创业期的时候应该快速试错去摸索;快速成长期靠风一般的速度占领市场;成熟期是形成公司战略、文化、体系,通过资本构建你的壁垒,我们正好是在迈向快速成长期。 记者:现在团队已经1000多人,作为CEO,你是怎么渡过“管理”这一关的? 罗旭:我是觉得我们有能量驾驭这样的速度。仔细想一想,2003年我们从南方报业集团派到北京,花1个月的时间招了2000人,再用1个月培训时间,总共用两个月筹备做出《新京报》。你说这个速度快吗?很多报社是筹备半年才筹备起来。所以《新京报》短短一年多扩张到2000多人,怎么做准备,怎么做文化认同,怎么做团队梯队体系,这方面我的逻辑蛮清晰的。 记者:创业四年,这个过程有哪些是你预期外的困难和挑战? 罗旭:这三年中我们遇到很多问题都是做减法的问题。公司要是没有钱,是很苦的事情。如果钱很多,也会面临很多诱惑,这个事可以做,那个事也可以做。开始我认为跟销售有关系的都应该做,跟销售没关系的不应该做。 最近我们有谈合作,打算在应用里面做一个随手笔记,但现在看来都不归我们管。真正心智成熟的企业应该开放,然后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一块来做。中国很多企业在这个问题上心智不成熟。我自己做大佬,什么我都自己做。 记者:听上去在做减法这件事情上,是不是也吃到一些苦头? 罗旭:这部分我们确实是有教训的。举个例子,我们曾经专门组织一个团队做淘宝的项目,因为觉得电商是好大的群体,就做了一个电商版,后来把整个团队都取消了。 记者:现在你们有多少企业用户? 罗旭:接近13万家企业。 记者:用户规模从什么时候出现较大增长?是怎么做到的? 罗旭:去年下半年我们迎来了比较大的增长。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用户自己的需求被激发出来了,而且是口碑传播,放到两三年前,估计谁都不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 关于渠道,一开始我们就想得比较清楚:在北京先用直销模式,看我们的产品卖不卖得动,在我们自己想不明白之前不让别人去卖。一旦确定产品卖得动而且需求还不错,就会立即扩张合作伙伴,由我们做“教练”。现在我们在北上广深和杭州是有自己的直销分公司,此外在全国还有一百家左右的分销商。针对代理渠道,我们建立了商务拓展和培训两个团队来给他们做支持。 记者:之前做企业协同办公大家一直有一个担忧,认为中国企业文化里并不习惯这种开放、透明,你们的客户是否也有这种顾虑? 罗旭:对,我们也背负过“签到”、“打卡”的恶名。但其实我们的初心是希望做人和人的连接,也就是此时此刻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公司的情况,别人也知道你在干嘛。 假设我在外,也能清楚知道公司发什么公告,员工有需要审批的文件我也能马上处理,另外我也能看到一些工作提醒,总之大家线上互动特别有意思,使我不在办公室时效率也高很多。我们下半年宣传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很大的资金,希望塑造一种分享调性——你越分享就越强大,越分享越自信。我把我的想法、把我的一些工作经验、把我的好的思路分享给我的团队,让我领导看到,我的同事也看到,我们整个团队自然而然沟通就有效了。 记者:美国科技媒体曾经统计过2B企业和2C企业的创始人平均年龄,发现2B企业创始人平均年龄在35岁,远大于2C企业创始人的年龄,这其中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吗? 罗旭:2B就是一个商业的事,因为你面对的是企业市场。做2B的产品,第一懂商业,第二懂组织,第三还要懂人性,第四还得懂产品、懂销售。产品是为企业服务,所以是一个强逻辑、强销售的市场,要把东西卖出去,你想一个90后的孩子或者一个95后的孩子20岁要懂这几个东西得多久时间,除非他是天才。 记者:在创业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来自员工和投资人的压力,如何化解? 罗旭:谈不上多大压力,但有些事情上,员工的认知跟你是不一样的,甚至包括投资人,你心中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其实并不清楚。有人会觉得你们挺好的呀,又不缺钱,为什么融资?因为融资意味着要牺牲股权。而且以后即便有了更好的条件,再融资会挣更多的钱吗?对于团队来讲,我需要速度,用速度覆盖整个市场,我一定需要资本的介入。但这些事情上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只有靠自己思考。 记者:经过一年拿三轮融资这样的事,你的心态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 罗旭:有人会觉得,你们融了这么多钱,那你们一定开心啊,花三年都花不完。但其实不是这样。尽管没有对赌,也不会出现很极端的情况,但钱就是一种责任,是希望你在既定的时间跑到位,这对于创始人和团队来讲是更大的压力。 拿了这么多钱创业,我最大的变化是考虑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想得更深更广。因为一个企业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文化的成功、产品的成功、市场的成功,甚至是团队的成功。最开始,从草根状态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元素做出来,快速发展的时候必须从这些维度考虑怎么让公司更健康。 创业到最后,一路走来其实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往往创业者和创业团队,甚至核心团队也很少人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是我追求的东西,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来,最后会发现我更在乎长远的发展,像是下围棋的人,不着眼于每个直角上,而是在于全盘的布局和九维的路径,即便某一个地方丢掉小角,大势还在,你就有办法把这个事做成。 也许到一个合适的时候我也会退休,不用干一辈子。我更希望自己将来做投资人,走到前端去,促进创新,促进创造。 记者:你最近读过哪些与创业有关的不错的书籍吗?它们为你创业提供了哪些借鉴? 罗旭:最近在读《创京东》和《企业的生命周期》。这两本书让我理解组织和生态的一些成长规律,减少自己犯错的风险。 《创京东》里写了京东的历史,这个过程中我能够看到别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思考方式、处理方式,企业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所曾经面临的问题,他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到最后惊奇地发现任何一家公司在固定阶段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创业过程中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一种趋势,关键时刻要做出关键性的决断。什么是关键性的决断? 我记得,这本书中曾经写到,京东做全品类的决定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但刘强东决定既然做一站式那么必须通过全品类来留住用户,购物才是终极目标和成功的标准,所以专注极致不需要贪,这些东西是你要不断拷问自己的。 记者:最近大家好像都在谈论媒体人转型的话题,您对此应该很有发言权。 罗旭:媒体人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当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候,很多的媒体人是没有勇气去改变自己、走出自己世界的。我是已经在创业的了,但身边还有一些媒体老朋友,有的在抱怨,有的得过且过。我总劝他们,既然抱怨为什么不离开呢?你会发现我们做报纸的那十年是媒体业“黄金十年”,从1998年到2008年。 记得当年我去《南方都市报》面试的时候,去了《南方周末》的会议室,他们在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总有一种力量让你不断前行。”我去《南方都市报》也是喜欢看《南方周末》,觉得这才是我内心愿意追随的。现在这些优秀的媒体人几乎走光了,媒体没有了灵魂,所以就会劣币驱逐良币。 记者:从一家传统媒体的创始人、管理者转型为一家纯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罗旭:其实这么多年之后,我的深刻理解是,创业比想象中的还要难。那时候不管《南方都市报》还是《新京报》都有体制的壳,所以当时的难,不是真的难。真的难是你出了这个大门只剩下自己,你没有权力了,以前别人尊重你是因为你有权力。当时我们做《新京报》时还是靠理想,认为在中国通过媒体能推动整个国家和社会进步,今天回想也是一件激动的事情。后来创业,还是和这有一定的关系。 我更喜欢去思考做事情的原动力是什么。当初我们做媒体,需要有热情地去学习,媒体的理想性和热情,才是最大的智慧源泉。做纷享之后,我觉得媒体人创业有共性之处,我们不止是做一个2B的生意,我们看到这个机会,是因为它可能会为中国的企业带来真正的变革。 记者:过去你们已经有了四轮融资,下一步打算做什么呢?你对纷享的预期是什么? 罗旭:我希望在中国做成企业级的BAT的公司。我们促进中国企业组织效率的变革,是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手段。 第二我们会把产品和服务连接起来,使整个商业效率被大幅度提升。 第三点是“企业云化”。以前一套SAAS软件要几十万上百万,放在家里其实没什么用,现在我们把它放在云端,让企业尽可能少花钱,为企业减负,更有竞争力。 第二个是公司形态,也是一种产品战略转型,其实这次融资之后,或者说这次融资前,我们正进行第三次转型,希望从一个工具过渡到平台。 就好像苹果最早出手机时是一个工具,但有了App Store后,它是一个平台。未来我们更多是构建一个企业级的应用平台、数据平台,甚至有可能是一个生态平台,我们现在更像一个企业级的微信。 记者:上市已经在您的规划之中吗? 罗旭: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说,上市都不是目的和诉求,它只是打通资本通道的一个手段。从目前纷享销客的发展状态来讲,上市这件事并不在我们的战略规划之中。 一方面企业级市场量级很大,我们才刚开始而已。另一方面,公司如果上市,那么产品、市场、用户规模还有整个生态体系都要相对到一个成熟度之后才更适合。我们虽然扩张很快,最近三个月,团队新增了几百人,但现在想上市真的还早。 记者:您现在还有推崇的企业家吗? 罗旭:我非常佩服刘强东在京东关键时刻的转型。零售强调一站式购物,一定要做全平台,京东当年这个逻辑是对的。 亚马逊也是这样的,京东学习亚马逊,第一个就是专注,第二个是克制自己,第三个是利他。未来我们也希望像这些优秀的企业一样,最大限度把资源开放出来。 纷事销客CEO罗旭简介: 2011年以前,罗旭一直任职于传媒产业,在南方报业集团、《新京报》负责财务和销售。2011年,罗旭从《新京报》辞职,创立北京易动纷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纷享科技),并很快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先后获得千万元天使投资及IDG资本等多家机构青睐。2015年7月,纷享销客获得1亿美元的D轮融资,在过去12个月内,一口气获得三轮总计近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纷享销客目前服务的中小级别企业级用户已经接近1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