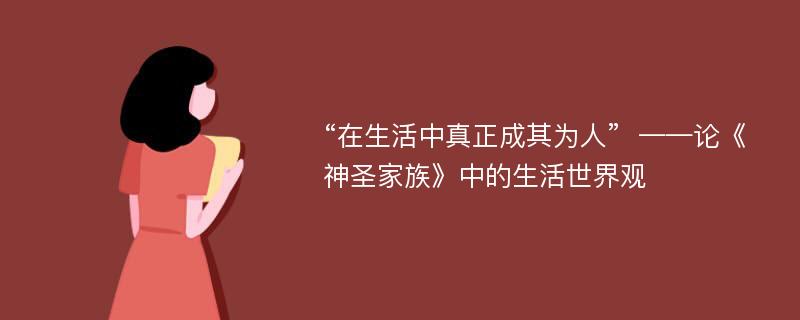
[摘 要] 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出发还是从唯物主义的现实生活出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中介,展开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从感性的对象入手还是从人本身的生活入手,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水岭。面对现实的生活,走向“精神的绝对的社会主义”还是“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决定了人类是否能够找到解放自己的现实道路,即“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的道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生活世界观。
[关键词] 神圣家族;人;生活世界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社会主义
学术界主要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批判的视角来评论《神圣家族》的重要意义,而忽略了他们通过认真审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找到了人类解放自己的现实道路,即“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通过消灭这些生活条件进而消灭自己的对立面,实现自身解放的实践途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个人的生活状况是由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个人生活的目的和他的现实使命就是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现实的生活世界,使其能够满足现实的生活需要。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生活世界观。这正是《神圣家族》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独特理论贡献。
一、从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出发还是从唯物主义的现实生活出发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两种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第一种是从超越于人的永恒不变的存在中来认识世界的本质及其意义,从而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第二种是从人自身及其实践活动中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从而形成了唯物主义的生活世界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青年黑格尔派试图将自我意识作为脱离人而独立存在的永恒实体,从而建立形而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自我意识是脱离现实生活的形而上的抽象。他们认为,实现人的解放的第一步是研究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人的实践活动在时空中的展开就是生活世界的形成过程。人的生活世界是围绕着物质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而建构起来的。这样,生活世界就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往的学术界大都是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解读《神圣家族》,即通过批判唯心主义从而建立唯物主义的意义上来诠释《神圣家族》的重要性,而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本书中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肯定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合理性,又通过指出费尔巴哈脱离人本身而抽象的谈论生活,提出人要在现实生活的实践过程当中不断解放自己,从而建立科学的生活世界观。
北京东方妇女老年大学焦作校区,创建了老年教育全新模式,在创新中办好寄宿制老年大学,为老年朋友创造了一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学习乐园和享老乐园,确立了文化享老的办学理念,创建文化、养生、田园、医疗、旅游“五位一体”的综合办学模式,创新“灵活多样、精品带动、重在参与”的办学方法,营造轻松、快乐、奋发向上的学习环境。
具体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蒲鲁东等人的批判,逐渐突破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的束缚,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探寻哲学的本质,从而建立唯物主义的生活世界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蒲鲁东关于哲学的看法曾有过著名的评论。他们认为:“蒲鲁东竭力反对哲学,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认为,哲学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骑在思辨的高头大马上,因此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我认为,哲学是超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到现在为止无非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被它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的事物现状的前提的束缚。”[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4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蒲鲁东已经意识到“思辨”即自我意识对人的绝对统治地位,不仅使人在自我意识面前显得不值一提,而且使哲学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不够实际。“实际”和“实践”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即practical。从该处的语境来看,这同一个词前后确实是两个意思,即前一个是“不够实际的”,后一个是“超实践的”。因此就能知道,蒲鲁东指责哲学太抽象,因此不够实际或者说不具有实践性。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的抽象性是它的优点,哲学本来就是对现状的抽象反映,因此不能摆脱事物现状的前提的束缚。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面向现实生活来研究哲学才能突破思辨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他们认为,指出哲学的抽象性和脱离生活的特点是费尔巴哈的功劳,但费尔巴哈这样做恰恰是为了让我们回到生活,以便正视生活的缺陷,从而改造生活。青年黑格尔派则借口哲学的抽象性,认为哲学高于生活。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费尔巴哈开启全新世界观的重要意义。他们分析说:“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一看法,最初并不是埃德加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称作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做了证明。可是,埃德加先生却能够使这种看法发生独创的、批判的变化。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曾经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践的。其实情况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不同于世界,它必定会以为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它自己的;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的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旧的思辨在这一点上同批判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4-265页。
每一个基层单位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会各不相同,管理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结合自身特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医院科室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初步探索,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医院科室的精神文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将不断努力,制定和完善科室精神文明建设保障制度和激励机制,加强科室文化内涵建设,建立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使科室长期保持和谐的精神氛围,使职工群众团结一致,爱岗敬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医学事业中去。
这表明,费尔巴哈的生活世界观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而在辩证法和历史观上存在局限性。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反驳思辨唯心主义的谰言,具有极大的思想进步意义。他认为:“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他们。”[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10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8页。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又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生活世界观又分道扬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要求。他们通过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详细研究了事物的“产生情况”,即关注事物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实践形态,把费尔巴哈仅停留在直观层面的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具有辩证法的实践唯物主义。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经过实践中介的事物都不过是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类活动而服务的。历史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形态。所以,《神圣家族》这样来定义历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5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对于破除黑格尔哲学统治,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全新的生活世界观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黑格尔哲学都处于独占的统治地位。黑格尔把哲学中的“人”仅仅当成“哲学人”,即不是当成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而是当成抽象的观念和精神的附庸。人在这里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唯物主义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却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不是宗教神学或观念意识。他们在对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才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他们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实践改造生活,而非仅仅停留在认识的抽象层面。哲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不是对事物现状的抽象反映,而是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实践。哲学不是教人沉浸在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想象当中,以为或假装以为事物的现状以及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自己的,而是教人直面现实生活,通过实践做出实际的判断并通过干预现实而改造生活。这样的哲学并非在实际上与客观的世界有所不同的哲学,也不是未对现实生活做出任何实际判断的哲学,更不是表现不出对现实的生活世界有任何识别力的哲学,而是能够通过实践来干预客观事物进程的哲学,是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的哲学,是能够从自我意识的思辨王国下降到人类现实生活当中的哲学,更是认为现实的人即群众能够通过实践来创造现实生活的哲学。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尤其是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通过彻底否定思辨唯心主义的旧哲学,从而形成了一种生活世界观的新哲学。
二、两种唯物主义:从感性的对象入手还是从人本身的生活入手
为了实现社会医疗资源的跨区域协同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机制,建立重点专科对口扶持机制、绿色通道转诊、远程会诊、业务指导“专全结合”的社区慢病管理等体系与机制,贯彻与落实中央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任务,在河北省某医院成立I期临床试验病房,与某急救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建立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与河北承德市、秦皇岛市、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江西省瑞金市等多家医院协作,开展技术合作、对口支援等,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认可。
“我由此猜想李卫中同志一定是与党有关系的人,便向他提出找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请求。他当即答应帮助我。” 1947年 8月2日,李卫中正式介绍汤甲真加入中共地下党,并嘱咐他如何保守党的秘密等。
然而,“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费尔巴哈认为,人在客观世界面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不是宾语而是主语。“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隐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第102页。他进一步主张,哲学的任务不是构建形而上的天国,而是通过认识自然来为人服务的。通过直观自然来探寻人的本质才是哲学的根本任务。费尔巴哈接着指出:“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认识,就是自我意识。你由对象而认识人;人的本质在对象中显现出来:对象是他的公开本质,是他的真正的客观的‘我’。”[注]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页。从这段话可知,在费尔巴哈的世界里只有纯粹客观的生活和作为对象的人,而没有现实生活的人和人本身的生活,所以马克思才说,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
虽然费尔巴哈开始关注人,但他只是得到了抽象的人。马克思批评他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本身。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犯了埃德加的错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用爱情的例子来论证人本身的重要性。他说:“埃德加先生把爱情变成‘神’,而且是变成‘凶神’,所用的办法是把爱人者、把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把爱情作为特殊的本质和人分割开来,并使它本身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通过谓语到主语的这一转变,就可以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规定和表现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例如,批判的批判把作为谓语和人的活动的批判变成特殊的主体,变成针对自身的批判,因而也就变成批判的批判,即变成一个‘摩洛赫’;对它的崇拜就是使自己成为牺牲品,就是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考能力的自杀。”[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3页。马克思在这里批评埃德加用对象取代了人,即用爱情取代了爱情的人。尤其是当埃德加把爱情变成独立存在的对象即“摩洛赫”时,人就只能成为这一抽象对象的自我异化形式。费尔巴哈在对人的认识过程中,也没有跳出“对象”的层次来理解人本身。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表明他同样迷恋抽象的对象。只不过费尔巴哈比埃德加前进了一步。他没有建立一个唯心主义的对象即“摩洛赫”之“神”来解构人,而是只把人本身当成感性的对象即一种抽象的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出,要在对现实生活的改造中理解社会主义,而且认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超越“精神”与“群众”的对立,从而否定思辨唯心主义所主张的精神的社会主义,实现对社会主义理解的超越。
5)葫芦岭位于惠州博罗老城的东面,形如葫芦,传说是八仙的铁拐李抛葫芦所形成的防洪高地,葫芦还吐九珠在博罗老城形成九块高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评论非常重要。要想超越思辨哲学的迷雾,就不仅要对之进行彻底的批判,还要建立全新的世界观。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对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新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一个是机械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人本学唯物主义。马克思先简略阐述了来自笛卡尔的物理学(也就是自然学)的唯物主义,认为它重视研究物质世界的自然概念和规律,使得人类“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8页。。但是,这些思想家们又把人变成了科学的对象——类似于机器的存在。人在他们眼中只能是没有主体性的机械存在和机械运动。他们看不到人身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创造性和能动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虽然也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但是在他那里不存在唯物主义对人的敌视状态,即不存在仅仅关注人之外的自然状态和科学研究的情况。费尔巴哈认为,人以及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才是哲学要真正研究的对象。自然是人生活的客观的物质存在,“人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注]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84页。来理解自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超越机械唯物主义,让哲学从“思辨的天国”重新返回人类的世界做出了高度评价。马克思还借助于伏尔泰的话指出,18世纪法国人之所以对神学争论不感兴趣,是由于当时的生活世界已经世俗化了,“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9页。。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的实践”是指生活唯物主义,而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在推动哲学从纯粹的思辨到生活面向的转换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经过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又复归于绝对精神,从而建构了庞大的思辨体系,那么费尔巴哈就是从反对抽象思维的东西入手,将在黑格尔哲学中被贬低为注释的东西转化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使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降到人间,使哲学成为关注现实生活的有血有肉的哲学。费尔巴哈认为,哲学应当从现实生活出发,将自然界中的人以及人所存在于其中的自然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他告诉我们,人不是以抽象的精神和意识作为前提而存在的,而是以自然作为生活的前提。客观的自然和感性的人才是认识的出发点。哲学应该深入到人的现实生活当中,研究“具有现实性和总体性的实际事务”[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91页。,这样人类才能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自己的生活。可以说,费尔巴哈所要解决的哲学的任务在于,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对立面建构一种关注人的生活的唯物主义哲学。他所建构的“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学连同生理学当作普遍的科学”[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第491页。。
三、生活世界的归宿:走向“精神的绝对的社会主义”还是“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为中介,展开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批判,进而萌生出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包含着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现实生活中的人,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着眼点都是很具体的、很实际的,而不是绝对的和抽象的。因为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从来不是一种抽象的幻想,也不可能只是对自然的一种抽象的直观,而是处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生产生活的实践,以及受具体物质条件限制下的生活。只有这样的生活世界观才能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才能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
费尔巴哈比机械唯物主义有很大的进步。后者不是把自然当作生活来对待,而是当作纯粹机械的存在来对待。也就是说,以纯粹机械的方式来感性看待自发的自然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机械看待事物运作方式的抽象思想。马克思在论述笛卡尔的物理学之后,紧接着就对法国的伽桑狄和英国的霍布斯展开说明。伽桑狄试图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来冲破中世纪的非理性加在人们身上的禁锢。他用机械运动来展开对原子的描述,通过构建唯物主义原子论来解释大自然的运动状态。霍布斯以彻底的精神建构了系统化的唯物主义。他从感觉经验出发,主张世界统一于客观的物质,不存在脱离物质的无形实体。他批判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认为没有“我”的存在就没有那个“我思”。机械唯物主义既理性地反对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又经验地认为人与自然都统一于物质。这种论证上的理性主义与观察上的经验主义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它经验地观察到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实体都统一于物质,从而通过理性的思维在科学层面上将之进行抽象。但是这样做的同时就抹杀了自然界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否定了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所以马克思这样评论:“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 [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1页。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与精神和群众的对立相应,也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精神的社会主义,一种是“群众”的社会主义。以鲍威尔为代表的思辨唯心主义认为,“精神”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鲍威尔等人把精神绝对化,“从‘精神’的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9页。,而不是从人民群众的信条出发,把“群众”看作是“精神”的对立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认为,“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导致“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3页。。思辨唯心主义之所以“危险”,正是由于把群众排除在创造历史的领域之外,没有认识到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推动者和体现者。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种社会主义的区分。“按照这个原理,人们立即就可以测量出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鸿沟。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7页。这段话告诉我们,“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从来不满足于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或单纯的精神自由、理论自由,它要求对现实生活的改造,要求现实的自由。这就要求“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而“精神的社会主义”却主张单纯的思想范围内的自由。
现实的人以及人本身的生活才是人的本质的基础,这是费尔巴哈没有达到的一个认识水平。他无法看到在客观的生活之外还有人类复杂的联系,以及由这种联系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费尔巴哈也不可能从具体的生活条件入手来观察和研究人的存在方式。他看不到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的、从事具体活动的人,而是一谈到人们之间的关系,马上就停留于抽象的“人”。马克思还指出,费尔巴哈“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费尔巴哈不会从社会关系这一范畴来审视和批判人与人之间的爱和友情的关系。他只把感性世界理解为可以认识的对象,而从来没有把它理解为是构成这一世界的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所以,费尔巴哈只能看到抽象的人,而看不到活生生的人。当他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作为个体的穷苦人时,他看不到这些人的社会属性,而不得不求助于理性的直观,以及抽象的人的本质。也就是说,费尔巴哈在把人理解为是抽象的存在的地方止步不前了。他在人能通过感性活动创造自身及其展开的历史的地方陷入了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才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0页。
精神的社会主义不仅通过“精神”无视了现实生活中的“群众”实践,而且否定了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力量。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肯定工人联合会,明确地告诉我们,群众只有在实践中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及其方式和条件,才能在生活中真正成为人。他们对此做了精彩分析:“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而事实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些联合会中,工人们彼此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此外,在这些联合会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般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粹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作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这种‘精神’既然把现实只看作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注]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73-274页。
(2)现对一箱产品检验了20件,结果恰有2件不合格品,以(1)中确定的作为p的值.已知每件产品的检验费用为2元,若有不合格品进入用户手中,则工厂要对每件不合格品支付25元的赔偿费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谈到三点,第一,就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他们认为,英国和法国的工人联合会已经超越了市民社会,成为未来的人类社会的萌芽形态。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有作为工人的异化的需要即动物般的生存需要,而且有作为人的需要,即对象性的、相互联合的需要。在工人联合会中,他们不再把分割和对立当作社会的正常状态,而是把联合和团结当作现实存在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工人通过联合会既现实地改变自己的存在状态,又使其成为改变生活现状的物质条件。
第二,通过联合会,工人们认识到并不能用革命的理论来代替革命的实践。工人们已经认识到精神与生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他们逐渐意识到了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只有金钱和财产才能满足他们作为人在生活中的各种需要。这些非常具体和实际的东西并非仅作为雇佣劳动的产物而存在,还作为改变工人生活的异化力量而存在。因此,工人们必须在劳动实践中用具体和实际的方法来解除它们所强加的锁链。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已经决定了,他们必须用革命的实践才能消灭导致自己异化的生活,从而开辟出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新生活。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讲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近代认识论问题。它被等同于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因此是生活世界观的基本问题。青年黑格尔派教导工人们用在思维中的自我改变来代替现实生活的改变,这属于生活世界观意义上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拒绝研究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现实关系,而是仅仅停留和满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空谈。因此,青年黑格尔派才这样教导群众,只要工人们在思想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他们就能消除现实资本强加于身上的枷锁,就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感到痛苦。这种希望群众只在精神中改变自己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式的欺骗。青年黑格尔派只把群众当作“抽象的我”,而不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我。他们并不期望在生活中现实地改变工人们的生活处境,反而轻蔑那些通过工人联合会改变物质生活条件的人。他们想当然地引导工人们通过幻想来改变自己,而不是通过现实的实际的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此予以彻底否定。他们从生活世界观的视角入手,认为群众只有通过现实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自己的生活现实地发生改变,并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从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才导致其不能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更无法认识到人的实践是受历史局限性和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然而,人类社会总要在物质生活实践的不断发展中前进。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才走向了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从而对科学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阐述。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却把现实只看作一些范畴,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于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世俗的社会主义也就根本不同。
To Become a Human Being in Life——On the World View of Life in The Holy Family
REN Shuai-jun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Marx and Engels to criticize the young Hegelians from the idealistic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r the materialistic real life in The Holy Family. Marx and Engels, based on Feuerbach’s materialism, launched a critique of the idealistic speculative philosoph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uerbach’s materialism and practical materialism o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whether to start with perceptual object or human life. Facing the reality of life, moving toward “absolute socialism of the spirit” or “secular socialism of the masses” determines whether human beings can find a realistic way to liberate themselves, that is, the path of “to become a human being”.
Key words: The Holy Family; human being; the world view of life; materialism; idealism; socialism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19)04-0009-08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 10.13951/j.cnki.issn1002-3194.2019.04.002
[收稿日期] 2018-12-03
[作者简介] 任帅军(1984- ),男,山西河津人,法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权价值等。
[基金项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人权价值的生活实现问题研究”(2016EKS006);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建设项目。
[责任编辑:刘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