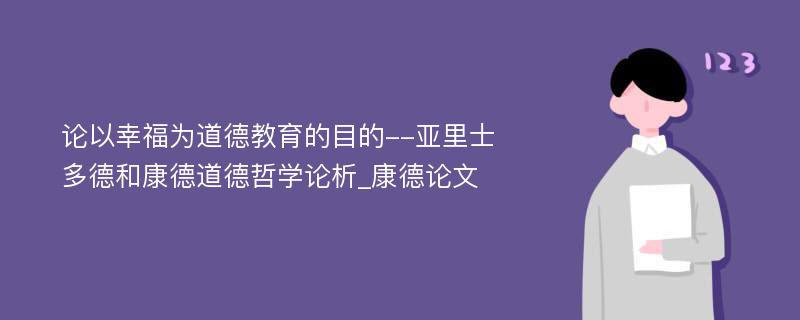
论幸福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关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道德哲学的争论与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康德论文,目的论文,道德教育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3)05-0095-07
道德教育不仅应当是高尚的,而且同时也应当是快乐的。道德教育最终给予我们的不仅应当是生活的目的和规范,而且也同时应当给予我们对道德生活的快乐体验和幸福感受。
一、古典德育哲学的争论与质疑
对于道德与幸福的关联,是学者们长期争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幸福和道德的理论,是留给我们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资源。这些理论和观点被学者们一再引用和论辩,而一次又一次地被悬置。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把道德与幸福拉到一起,提出所谓德福统一论的观点。认为幸福是生活的最高目的,自然也是道德的最高目的。然而,亚里士多德始终没有明确承认幸福可以成为道德的目的。他在《尼可马罗伦理学》中说:“幸福是完满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①在这里,他只是说,幸福应当是一切行为的目的,而没有说也应当是道德或道德教育的目的。相反,他坚决反对离开道德约束的幸福,却一再强调道德作为幸福的条件这一无可争议的前提。在他看来,道德是幸福的条件,如果没有道德,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他最终断定“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②,认为只有道德的幸福才是永恒的幸福。在他的论述中,幸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幸福是否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终点,却似乎显得模糊而不清。可以得出结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虽然可以让人幸福,但它并不一定以幸福为目的。
而至罗马时代的斯多噶学者,也与亚里士多德有同样的思考和态度。他们表达了对把幸福作为生活目的的怀疑。在他们看来,宁静才是最美好的生活。直至康德,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被另一种立场所诠释。在康德看来,道德是一种律令,一种义务和责任,绝不允许受快乐的牵引和支配。在康德这里,亚氏的犹豫已经消失,道德就是道德,道德与幸福毫无联系和瓜葛。道德不是为幸福而存在。相反,道德只以它自己为目的,道德只为道德而存在。换句话说,道德只是为了使人更善,而不是为了使人更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或是康德都尚未完成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这也是目前诸多学者的观点。比如,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也持这一观点。杨泽波认为,牟宗三写《圆善论》就是为了专门解决这一亚里士多德难题。康德与亚里士多德讨论问题的立场不同,康德没有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立场,因而康德不承认幸福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康德幸福论只是论证了什么是幸福,并得出与亚里士多德相同的结论,即幸福必须以道德为前提。但康德没有论证幸福是否有必要成为道德的目的这一目的论的话题。在他看来,幸福是对一切爱好的满足,而不一定是一切行为的目的。杨泽波认为,康德的幸福观是反经验主义的幸福观,幸福不是直观体验的快乐,因而任何幸福都只能是一种“道德的幸福”及理性的体验,而不是直观的快乐。由此他认为,康德的道德幸福比较难于理解,需要理性和智慧的帮助,同时也需要改变对幸福的定义才可能获得,因而是“玄妙而转折”的。③
在两千年的历史和争议中,唯独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是个例外。他们没有亚里士多德的犹豫,也没有康德的坚定和意志。康德的义务论哲学被他们彻底抛弃,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模棱两可中选择了快乐。在边沁和密尔看来,快乐是评价道德的重要元素和标准,而道德也应当是可以用快乐和痛苦来计算和比较的。认为道德的重要价值在于给人带来光荣、名誉和幸福等精神的快乐。密尔将这种包含快乐的道德称之为人类的“高贵情感”,一种具有“终极约束力”的“幸福道德”④。然而,无论是边沁还是密尔都未能真正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悖论中摆脱出来,他们仍然停留于对道德所具有的幸福功能的讨论上。在他们那里,只是随意地对康德作了抛弃,并在亚里士多德的犹豫中作出简单的选择,再没有更多的理性想象和思考。尽管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边沁和密尔是一个里程碑,但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深邃想象及解决其哲学悖论的复杂性来说,他们的理论显得过于简单和幼稚了。不过,他们对人类道德的快乐功能所作的讨论仍然为我们思考德育问题提供了启示。比如,鲁洁在上世纪末探讨德育的“享用功能”,亦可看到受功利主义哲学的重要影响。在她看来,所谓享用功能,即“可使每个个体实现其某种需要、愿望,从中体验到满足、快乐、幸福,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⑤。从这一点看,功利主义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批判康德哲学的偏激和无情,但除此之外,如果试图真正解决道德与幸福的悖论问题,仅仅依靠功利主义似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看来,古典学者的观点是大体一致的。道德是幸福的前提,道德只有作为幸福的条件时才与幸福关联。在两者的关系中,道德优先于快乐。古典学者的立场,尤其是康德的观点,为道德教育确立了永恒法则——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意志而不是寻找幸福和快乐。只有把快乐排除在道德之外,道德教育才是一种“道德的教育”。按照这样的观点,只能得出的结论是,道德或道德教育应当是高尚的,但不一定同时也是幸福和快乐的。
然而,对古典学者的如此诠释亦没有获得所有学者的一致认同。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论出发,似乎应当推论出幸福作为道德目的的结论,虽然在仔细推证后最终难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却给我们留下了推论的想象和希望,令后世的学者们不能轻易放弃。比如,加拿大学者克里夫·贝克曾严厉批评将道德与幸福完全对立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对道德的理解过于“夸张”了,人的许多道德行为常常具有“强烈的助人欲望”,助人本身就是人的一种欲望,而满足这种欲望会给人带来巨大的幸福感,即在人的天性中包含着道德的欲望及由此而获得的快乐体验。⑥按照他的观点可以认为,不是古典学者的观点不正确,而是我们的诠释有问题。在这些诠释中,包含着对人性的不信任,而用这样的立场设计道德教育,尤其是为道德教育确立基本的价值立场是不适当的。道德教育必须建立在对人生目的及人性的完整理解之上,那种没有人生目的和人性基础支撑的道德教育是有缺陷的道德教育。
学者叶飞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给予我们一个值得思考的路径。他从西方伦理学两大理论范型出发,即义务论伦理学和目的论伦理学。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正是义务论的重要代表,而亚里士多德正是目的论的重要代表。叶飞认为,义务论与幸福无涉,因为义务论强调道德义务而不是人生幸福,没有把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的,作为伦理学的前提。在义务论看来,幸福不应该出现在伦理学中。义务论强调的是道德的义务和责任,因而很难想象把道德行为与追求个人幸福联系起来,也不大可能把道德与全部人性结合在一起。义务论的立场是就道德谈道德,因而不可能推论出道德的人生目的,相反,更容易接受对道德本身目的的追求。但目的论伦理学则完全不同,它以全部人性及人生目的为前提,因而自然更容易接受把道德问题纳入人生问题的范畴去讨论的立场,进而也更容易把幸福视为道德及道德教育目标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之所以比康德更倾向于认可幸福论的道德理论,是因为他从目的论出发,视幸福为一切行为的目的,所以才比康德更容易推论出道德也是幸福的终点这一结论。⑦
亚里士多德虽然比康德早两千年,但却比康德更为包容和博厚。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就是最高的善,是一生中那种最好、最完善的德性。因为幸福被置于生活的最高目的,因而比康德有更容易接受的推导逻辑和前提,而这样的结论应当说比康德更具有伦理学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也更容易为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者所接受,同样也使他的理论更具有人性的魅力和光辉。相反,康德的理论虽然更容易为常识所接受,或的确更好地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我们对道德的看法和理解,但是,康德的立场却过于缺少人性和想象。从另一方面看,道德的生活也是幸福的生活,这同样是可以成为一种合法并符合逻辑的立场,虽然反过来推论仍然面临逻辑的困难,但要比康德的理论更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在康德这里,是没有任何逻辑方法和途径获得这一结论的。
二、人性主义立场的确立和思考
由此看来,用幸福诠释道德及道德教育,并不仅仅在于为道德教育确立终点与目标,而在于为道德教育奠定坚实的人性基础和正确的道德立场。从这一点出发,那就必须让我们首先去探讨完整人性视角下的道德概念,从而进一步去探讨古典德育哲学留给我们的道德与教育的难题,即道德是否应当有人生的目的,以及是否应当超出道德本身的范畴去认识道德的目的。学者杨豹认为,讨论道德与幸福的关联这一问题涉及人性问题。他说,人性在于理性,理性是人性的本质,一切符合人性的东西就是幸福。而道德是人类理性最重要的元素,因此,顺应道德的也是顺应人性的,因而必然也是幸福的。杨豹认为,这也是理解亚里士多德德福理论的关键。在他看来,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理论,就完全可以推导出幸福论的德育哲学。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善德的实现,也就是善德的极致。⑨按照这样的逻辑与哲学,道德教育以幸福为目的就成为非常合乎理性与逻辑的,具有了哲学与逻辑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如果我们仍然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推论,那么,就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在矛盾心理的背后,仍然流露出比较清楚的立场与倾向。比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切行为的目的,那么自然可以推论,幸福也应当是道德的目的,因为道德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道德只是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道德是被用来应对人性缺陷的手段,因而道德永远只能用来表达对人性的规范,而不能用来表达人性美善的光辉。那些最令我们陶醉和迷恋的人类榜样只能用人性力量而不是道德精神来概括,因为其他任何词汇都难以完美表达人类本能中那些美好的精神和德性。在所有伟大榜样和完美德性中,都包含着助人的快乐和给予的幸福。
从完整人性看,那种为道德而道德的片面立场,可能又犯下了另一个错误。即我们常常只用道德来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但却忽视了同样应当反过来,幸福同样可以甚至也应当成为衡量道德的标准,因为幸福占据了对人性的认识和理解。亚里士多德早就这样尝试过,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这样的推论中,幸福自然获得了为道德教育立法的可能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仅道德是幸福的标准,而且“幸福在于善行”。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中论述城市的道德性时写道:“社会幸福的由来固然应该类似个人幸福的由来,那么,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⑩从这里可以看到,道德是不能自立的,它同样需要以幸福为条件,只有能给人带来幸福的道德,才是真正“道德的道德”。这一观点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亚里士多德德育哲学对幸福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似乎显得有点隐晦与含糊。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推论方式说,亚里士多德道德幸福论为幸福作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提供了某种正当性的辩护。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教育不能用道德的规范去控制人性的美善,而只能用人性的标准去建设道德的规范。同样,道德不能离开幸福的支撑,相反,只有在幸福召唤下的道德,以及用幸福建构的道德教育才会充满人性的魅力,才能真正唤起人内心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种向往和追求中,才可能在获得一种道德的标准时,同时获得道德的快乐和幸福。这样的道德和规范才有可能最终成为完整人性及人类德性的一部分,一个拒绝人性而以道德本身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最终不能达到道德的目的。
这样的推证逻辑在后世的哲学家那里也一再出现过。尼采在论述古希腊道德哲学时,也曾同样表达对幸福的信仰,尽管在这种信仰中包含着反道德的倾向,但其中所显示的对人性的另类诠释则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尼采认为,包含着同情和给予的基督教道德是一种弱者的道德,而“希腊宗教尊奉的诸神不是非人性的或反人性的本质,而是理想化了的人,所以应该以希腊宗教来取代基督教道德”(11)。在希腊人这种“理想化了的人”的哲学中,同情、理解和给予都不是道德,而给予也不是因为同情和理解而是因为慷慨和卓越。在这种慷慨中体验到的是成就、卓越和幸福,而不是损失,只有从慷慨、卓越与成就中体验到的快乐和幸福才是一种完美的德性。
三、幸福优先论的依据与阐释
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争论中作出选择,即人性优先于道德,或是道德优先于人性。到底应当强调伦理对人性的支配,还是人性对道德的把握,这是道德教育必须首先作出的选择。现代哲学对人性的推崇,不仅意味着要重新审视道德与人性的关系,而且折射出哲学家们对现代人性危机的关注——即道德对人性的控制及其对幸福的拒绝。存在主义从存在出发探讨人性危机,首先挑起存在与道德的争论。海德格尔视“存在”具有伦理上的优先位置,所谓存在优先即存在大于或高于伦理。而萨特从自由的概念出发探讨同样的问题,认为“人是被判定自由的”,自由是人作为“自为存在”的最大特点,而伦理则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在他看来,自由永远具有比道德更为优先的位置,即自由比道德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国内学者何怀宏则指出,存在问题完全不是伦理问题,但伦理问题绝对是存在问题。(12)他的观点是,存在是伦理的目的,只有从存在的意义上看伦理,伦理才显示出自己的方向,否则伦理只是一种既定生活的规则,而失去为存在守护意义的功能。史怀泽在他的《敬畏生命》一书中,论证了什么样的伦理才具有真正的伦理性问题,他把伦理的根基奠定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他说:“只有人道,即对生存和幸福的关注,才是伦理。”(13)从这些论述中可知,代表人性最高价值的幸福被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之上。这一观点的基本立场是十分明确的,即道德如果不能增进人性,不能促进幸福和美好,那道德也就成为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规范和形式。
幸福是否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或道德教育是否应当追求幸福,在幸福优先论看来已经成为没有争议价值的命题。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应当是人性的增长而不是教授道德的规范,因而以追求幸福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才有可能成为人性增长的教育。用一句极端的话来表达就是:只有拒绝单纯以道德为目的的道德教育,才有可能真正达到追求幸福的教育目的。幸福论的道德立场认为,人性大于道德,幸福高于伦理,因而道德虽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道德一旦脱离人性的指引,就有可能变成压迫人性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便道德教育不能成为增进人性的手段,也无论如何不应当成为压迫人性的工具。道德教育应当是高尚的,但也应当是快乐的。这不仅是对学校德育的一种希望,而且同时也是最符合人性与道德关系法则的一种诠释。道德教育,作为增进人性的一种手段,最终应当是帮助人获得幸福,而不是相反。这就是人性优先论最基本的观点和立场。一切道德的规范都应当在人性的制约之下,而不应当是独立于人性诠释之外的纯粹的道德规范。道德的追求不能局限于道德本身,而应把全部人性的美善纳入自身的目的之中。道德与幸福的关联,是幸福大于道德而不是道德大于幸福,是幸福优先于道德而不是道德优先于幸福。道德教育不能离开对幸福的追求,否则完全有可能将道德教育变成创造人性暴力和道德悲剧的工具。
古典哲学从来没有明确否定或肯定什么。亚里士多德流露出矛盾和犹豫,始终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而是以隐晦的语言在暗示着什么,让后人在这一问题上无休无止地争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方面,他视道德为幸福的条件(同时也包含幸福为道德的条件);但另一方面,他又说这种道德超越于伦理的善,并认为这种善是一种自足的、绝对的和最高的善,是人的一切存在的目的,是一种存在的“好”。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中,已经能够隐约看到,他对幸福的优先性似乎已经表示出一定的偏向与倾斜。正像麦金太尔在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时说:“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中,德性概念从属于内含着人的行为目的的好(善)生活的概念。”(14)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谓善的概念,既包括了伦理的善,也包括了人性的善,而不是单纯的伦理的善。因而,我们应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实际已经表达了对幸福优先于道德这一人性诠释的认可。
国内学者金生鈜认为,应当把教育的理想安置在生活当中,并以所谓“好生活”的观点表达了对幸福优先论的支持。在他看来,教育必须守护好生活,认为这是教育哲学的最高问题,只有守护好生活的教育才能是好教育。他写道:“对教育放弃了价值的追问,就等于放弃了对好的教育的信念,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是放弃了对现实的教育改善的理想和愿望。”(15)在这里,所谓“好生活”的含义除了幸福就再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了。好生活就是幸福,而幸福就是好生活。一个没有幸福的生活不可能是好生活,而一个没有好生活的幸福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幸福。幸福优先不仅可以表现为存在优先(海德格尔)、自由优先(萨特),同时也可以表现为生活优先。生活永远是高于并大于道德的概念,道德只有成为创造好生活,给予人幸福的源泉,才能最终成为生活所接受的一种价值和标准。由此看出,教育的问题在于,不是要不要美好和幸福,而是在哪里寻找美好和幸福。教育没有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目标,教育的根本目的应当与人生的目的相统一。金生鈜认为:“教育哲学要探寻教育发展的方向,要反思现实的教育,就不能不关切这一永恒的存在,就不能不把它作为参照。这正是教育哲学关切终极价值的根据。”(16)寻找美好的生活,这永远应当是教育的理想。期待一个更美好的生活,追求一个更高的善和美满的幸福,这就是教育必须守护的目的。离开这个目的,任何教育都不能算是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也一样。
四、道德悖论的终结与讨论
关注幸福的伦理学,虽然具有哲学的可靠性,但却不能逃避人们对道德常识的矛盾和冲突。德育哲学面临的最大悖论是道德与幸福的对抗。一方面,这反映出幸福论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这也不能就此证明道德论(义务论)已经取得胜利;同样,也不能反过来证明幸福论的谬误与失败,或许这只能证明,道德教育面临无法摆脱的尴尬和困惑。将道德与幸福对立,这既是一种常识态度,同时也是一种易于接受的立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论,道德的确可以换来幸福,但只是一种“道德的幸福”,这种幸福需要改变对幸福的理解,需要用克制来换取,这种幸福与我们的自然体验或常识态度相悖;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并未带来任何值得慰藉的进展,康德的道德义务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困扰,但却让人们重新陷于道德对人性的迷茫之中。
这样的逻辑似乎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既希望获得一种道德的崇高,又企求获得幸福的体验。道德教育应当是高尚的,但也同时应当是快乐的。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目标和追求的理想。道德教育如何摆脱哲学与常识的悖论,让道德教育在增进德性的同时获得幸福,这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解决悖论的前提是必须明确这样的立场,即仅仅为了道德的道德教育肯定是不道德的,但仅仅为了幸福的道德教育同样是不道德的。比如,在奥古斯丁看来,幸福就在于拥有真理,即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因而人们是在认识真理的同时才获得了幸福。(17)这一立场的深刻含义在于告诉人们,道德教育若要真正具有意义就必须具有更高的追求——真理、人性、存在与幸福。由此看来,那种试图让道德教育获得纯粹自然主义的快乐体验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道德。以快乐为快乐的快乐最终不是快乐,以幸福为幸福的幸福最终不是幸福。必须改变对快乐和幸福的自然主义定义,才能真正获得道德与幸福的完美结合。
由此我们可以逐渐清晰起来,即只有同时拥有道德与幸福的目的,道德教育才可能是完美的。既是高尚的也是快乐的,既是道德的也是幸福的,这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同时也应当是一个真理。事实上,无论是为了幸福或为了道德,只要放弃了一方都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幸福论的危险是人性的危险,即离开幸福目的的德育可能是压迫人性的德育;而义务论的危险则是常识态度的危险,即离开道德的德育则可能是放纵人性的德育。两种德育哲学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比如,学者叶飞在文章中专门论述了义务论的危险和问题,在他看来,义务论的后果是将道德教育变成纯粹的知识传授、政治教育和圣人理想。(18)而这一切都将葬送道德教育为增进人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目标。
如果我们具有更高的眼界就会懂得,我们需要康德但更需要亚里士多德。人之所以要过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最终还是为了追求美好生活。也就是说,道德——不是为了道德而道德,而是为了幸福而道德,因为只有道德才有真正的幸福。幸福与给予绝不对抗,道德与快乐也不对立。无论是奉献还是给予,都是为了一个美好的目的和幸福的终点,这是道德教育的最后期待。在这里,常识与理论达成相互谅解和包容,即不仅道德需要幸福,同样幸福也需要道德,独立于道德之外的幸福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道德即幸福”应当成为道德教育的真理。如果有了这样的立场,不仅道德教育没有悖论了,而且也有了目标和方向。这个目标和方向就是,道德教育必须提升对幸福的认识及对快乐的体验。这不仅应当成为道德教育的一种哲学,同时也应当成为一种常识的态度。
拒绝把道德与幸福对立起来的观念和态度,就不会把一切快乐的东西都视为对道德的背叛,同样也不再会否认道德教育中幸福的可能性。道德教育必须进行道德的设计,但也必须有牢固的人性立场,这将为道德教育最终成为道德的教育提供依据和根基。
*收稿日期:2013-07-21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③杨泽波:《“赋予说”还是“满足说”——牟宗三以存有论解说道德幸福质疑》,《河北学刊》2011年第1期。
④[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功利主义》,刘富胜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49-50页。
⑤鲁洁:《试论德育之个体享用性功能》,《教育研究》1994年第6期。
⑥[加拿大]克里夫·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戚万学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155页。
⑦叶飞:《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⑧杨豹:《理性、中道与幸福——探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理论》,《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5期。
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页。
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徐大同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3页。
(11)[德]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上卷),魏育青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12)何怀宏:《生命与自由——法国存在哲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13)[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14)[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36页。
(15)金生鈜:《教育哲学怎样关涉美好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2年第1期。
(16)金生鈜:《教育哲学怎样关涉美好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2年第1期。
(17)孟凡芹:《奥古斯丁的宗教幸福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理论界》2011年第2期。
(18)叶飞:《关注幸福:道德教育的新目的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
标签:康德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教育的目的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生活教育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伦理学论文; 人性论文; 政治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