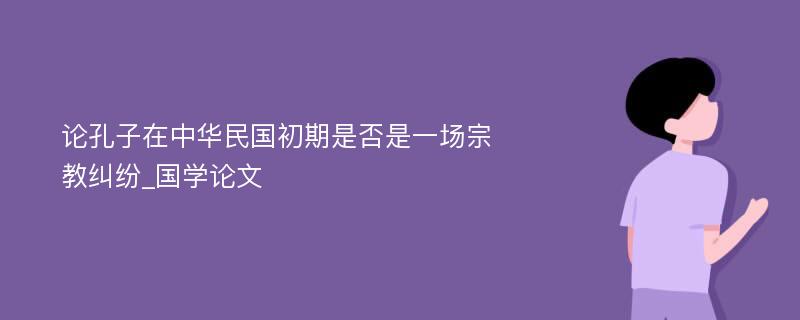
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之争论文,宗教论文,孔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教是否宗教,是聚讼多年、迄未定论之问题。该问题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文化领域里曾成为争论之热点,各界要员卷入其中者甚多。该讨论正值社会嬗变、文化转型时期,无论对当时的舆论、政局,抑或对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对清末民初康有为等人试图创孔教的实践,近年来有不少专著和论文进行了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迄今未有专题研究充分展示论战的全貌,以至对该问题缺乏全面研究。鉴此,笔者试图全面梳理参与论战的双方、言论及论战之结果,将其置于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充分吸收既有的研究成果,揭示隐藏在辩论背后的实质问题——何以该讨论发生在民初?试图解决什么问题?
一
1913年8月15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孔教会陈焕章、梁启超等,上书国会请于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因争论双方均将孔教是否宗教作为孔教能否定为国教的前提,孔教是否宗教也因之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到第二次国教请愿失败终,有关孔教的争论始终存在于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并成为当时主要的思潮之一。
为了有助于认识这场辩论,笔者将双方之言论陈述如下。若以赞成、反对孔教为尺度,可将民初思想文化阵营略分为二,前一阵营大致以孔教会成员为主:
第一,康有为、陈焕章等孔教会主要领导人,建构了兼具人道与神道,且优于基督教的孔教理论。
早在清末,康有为就“致力于将儒学转化为宗教”,随着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康氏着手“将儒学从道德哲学转化为宗教”(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以挽救“国亡教危”的局面。1912年,康氏授命陈焕章创办孔教会,并亲自撰写孔教会序,宣称“中国数千年来奉为国教者,孔子也”,孔教是“人道”教,所谓“太古草昧尚鬼,则神教为尊,近世文明重人,则人道为重,故人道之教,实从神道而更进焉。要无论神道人道,而其为教则一也”(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
作为孔教会的直接领导人,陈焕章秉承其师的孔教主张,撰写了孔教会的纲领性文件《孔教论》。(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在《孔教论》中,陈氏首先指出孔教之精髓是《书经》所谓五伦,《礼记》所谓七教。然“《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是故有神道设教。可见,“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而尤偏重人道”,故“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且“野蛮时代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是故,孔教乃重人道、优于其他宗教之“特别宗教”。其次,陈氏论证“教”之界说,认为“孔教之经传,其确定教之界说者,莫著于《中庸》,《中庸》曰:天命之谓之性,率性之谓之道,修道之谓之教,此教之定义也”。据此“评论孔教,则孔教之为教,铁如山,不可动矣”。最后,陈氏指出孔教具备基督教所具有的宗教要素,诸如教主、上帝、教堂等。(注:陈焕章:《孔教论》,《民国丛书》第四编·2·哲学·宗教类,上海书店,1989年。)要之,孔教就是宗教。
此外,孔教会人士还从征诸宗教的不同定义以论证孔教。如张东荪认为确定“孔教果为宗教否”,“在宗教之定义”,张氏考证康德、斯宾塞、赫胥尼等人对宗教的定义,概括出作为宗教的四要素,而孔教具备此四要素:宗教所谓之神、信仰特质、道德特质、宗教代表之文化特质。(注:张东荪:《余之孔教观》,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36-5038页。)又如,张尔田以信仰者之多寡为衡量标准,认为自民国创建以来,“上自开国巨公,下至贩夫走卒,无一敢以非圣诋孔者,此心同,此理同也”(注:张尔田:《孔教五首》,《甲寅杂志》第1卷第3号。)。因此,孔教是宗教。
第二,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及一些颇有影响的传教士也拥护孔教,如俄人盖沙令,英人麦禅原、庄士敦,德人费西礼、卫西琴,日人有贺长雄及传教士李佳白、李提摩太、花之安、狄考文、卫礼贤等。其中以庄士敦、有贺长雄、李佳白等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庄士敦认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哉!”故孔教于中国,非他教可比,“外教无论如何优美,亦不可与孔教并峙于中国”(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
而有贺长雄则认为孔教“尊祖祀天,不言神秘甚密之义。而于人伦则至纤至悉,郑重周详,是故伦理者乃中国文明之精华,为西汉以来二千年间政教之基础,其浸润于国民意识甚深,其支配国民精神之力极大。居今而言保守,不但须将通国之中所有被服儒术,崇奉孔教者总为一团体,由国家公认而保护之,且于宪法特著明文,以此为国家风教大本”(注:有贺长雄:《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大本》,经世文社《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卷,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094-5098页。)。主张定孔教为国教。
第三,军阀如张勋、阎锡山、吴佩孚、张作霖、冯国璋等地方势力派,也坚决拥护孔教。
1912年,张勋曾向袁世凯呈文(注:张勋:《上大总统请尊崇孔教书》,《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1号。),呼吁尊崇孔教。尔后,张勋利用在徐州召开的13省督军联合会议,请康有为拟致黎元洪及国会的电文,称中国“千年之历史风俗,举动行为,人伦日用,皆受之于孔教,与之化成国魂……”(注:柯璜编:《孔教十年大事记》第8卷,太原宗圣会,1923年。)。而在国教运动中,张勋更是不遗余力、屡次上书请定国教;阎锡山也通电赞成孔教,并拟具体而详尽的尊孔方案致电袁世凯(注:《山西都督呈大总统祀孔典礼文》,《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8号。),也可谓煞费苦心;吴佩孚不但手创孔教会组织,且在其数次公开讲话中均表示孔教是宗教。
此外,当时一些组织也支持孔教,如世界宗教会,其简章就明确指出孔、佛、道、耶、回都是宗教,只因产生在不同的地域,而导致“孔佛操戈,耶教对垒”(注:《世界宗教会小引》,《东方杂志》内外时报栏,第8卷第11号。)。另有一些舆论也支持孔教,反对以有无宗教仪式判断孔教,“举凡足以陶铸一民族之道德,维系一民族之风化,范围一民族人民之精神者,即无不足为一民族之教”,而孔教正具有以上功能,故孔教虽无宗教形式,“亦无害其为教”(注:Cyz生:《宗教论》,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6号。)。
二
孔教是宗教,褒者众,贬之者也不乏其人,此构成了与孔教对峙的另一阵营。该阵营人员构成较前者更为复杂,反对之理由也不尽相同,略为以下几类:
第一,部分主张保存民族文化的人士。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即是非议孔教、颇具影响之代表人物。1897年,当“梁卓如等倡言孔教”时,章氏就“甚非之”(注:章太炎:《章太炎先生自编年谱》,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3页。)。1912年,章氏在国学会的讲学处墙壁上贴通告(注:章太炎:《示国学会诸生》,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97页。),宣称与孔教会划清界限,并明确指出“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反对孔教是宗教。
章氏亦从根本上否认康、陈宣称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观点,认为“《易》称圣人以神道设教,斯即盥而不荐禘之说也,禘之说孔子不知,号曰设教,其实不教也……”驳斥孔教会“创教”的依据。此外,章氏以为从古文经的角度出发,以为六经皆史,“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献、振学术、平阶级而已”,而不是教主(注: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88-692页。)。故有学者以为,民初“儒家是否为宗教的辩论,是清代今古之争的继续发展”(注:董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的争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2期,第206页。),而今古文之争确随着孔教之争又重新燃起(注:艾恺:《梁漱溟——以圣贤自许的儒学殿军》,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43页。)。时从古文经的角度反对孔教者,不在少数,如章士钊就属其中,章认为“孔子夙非教主,其言绝非教质”,“且口说所垂,删订所著,皆已转诸门人……至于岁时致祭,享以太牢,亦不过儒士趋跄,以尊其师,诚犹鲁班轩辕萧何之各得崇拜”,故孔教“本非教也”(注:秋桐:《孔教》,《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陶庸:《孔教与耶教》,《甲寅》第1卷第3号。),显然是站在古文经的立场上,反对孔子是具有神秘思想的教主。
而身份颇有些特殊的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列名孔教会、参与国教请愿,却以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身份非议孔教。因梁认为孔教之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而所谓“创教”,在梁氏看来即是将儒家文化中的信仰功能,通过现代诠释,以在新政体下规范社会秩序。在孔教会举行的国子监丁祭上,梁即表达了此观点,希望通过孔教会成员遵守与践履儒学道德条文,成为真正的“君子”,以作为社会道德的示范。
第二,某些社会团体的反对。孔社是参与争论、与孔教会对峙的一个尊孔组织。孔社认为以宗教尊孔,反使孔教“狭之”、“亵之”,宣称“孔学之发达,自应以本社为权舆”(注:《孔社杂志》第1期。),其社长徐琪曾明确反对“以宗教推孔子”,因孔子之道已深入人心,贩夫走卒“已在孔子范围之中”,何必定要拘泥宗教之仪式(注:徐琪:《孔社杂志弁言》,《孔社杂志》第1期。),如是,则“反以亵之乎”(注:《书后》,《孔社杂志》第1期。)。
孔社对孔教的驳斥,代表了当时部分尊孔者的观点。时《京津时报》即刊文指出:孔子之道,“如布帛菽栗,举世衣被饮食而不知”,而“侪之于神鬼之无门,巫医之小道”为尊之手段,其结果必使“圣道之遭鲁莽而灭裂也”(注:《书后》,《孔社杂志》第1期。)。可见,同是尊孔,但主张却迥异。
第三,袁世凯及部分政界人员。对孔教会之“创教”,袁世凯也不尽认同。(注:关于袁世凯与孔教会的关系,参见拙著《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在袁先后颁布的尊孔令中,强调的是孔教“正人心”,“齐民以德之效”,如袁在1913年的《尊孔祀孔令》中说:“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同年,代表袁出席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丁祭仪式的梁士诒,在会上发言说,孔教“道之于德,齐之于礼,……深望社会上有贤人君子出,而道民以德”,“俾收齐民以德之效”(注:梁鼎芬:《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5辑(743),台湾文海出版社。)。而且,当1914年袁恢复祭天大典时,基督教传教士认为袁此举是以政府行为提倡孔教,但“袁世凯说:‘政府要想着重指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原则乃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孔教没有什么神秘的或神学的色彩……”(注:(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页。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近之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1期,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出版。)
对孔教持异议者,还有其他政界人士。如在1913年孔社举行的庆圣诞典礼上,副总统代表胡瑞霖便明确反对孔教,对“以孔子为宗教”之主张“不以为然”,且“尤望全国人士勿以宗教家狭视孔子”(注:《副总统代表胡瑞霖君演说词》,《孔社杂志》第1期。)。
第四,新文化运动人是最激烈、彻底的反对孔教者。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鲜明指出,“忠君与共和制度相悖,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尔后,蔡氏也驳斥孔教,以为孔教同宗教的本质“相刺谬”(注:蔡元培:《提议以内务部之礼教司移入教育部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且孔子既无神秘思想,也无“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注:蔡元培:《致许崇清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故孔子与宗教,“两不相关”(注: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94页。)。
当第二次国教运动再度喧嚣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其斗争之矛头直指孔教(注:“民国四年以前,打击正统思想的箭头,还没有特别指向孔子。但民国五年春,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进行,反孔运动便正式揭幕。”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3页。),将思想上的反对孔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紧密结合起来。陈独秀以为“夫‘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注: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3页。)。孔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而且,“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因此,“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主张“以科学代宗教”(注: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3页。),宣称与现代生活不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179页。)。
第五,宗教团体。随着民初教会势力的蓬勃发展,教会对孔教也是重拳出击。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天主教、基督教等教徒,或以教会组织、或以教民身份,纷纷撰文、通电反对国教,而孔教非宗教,则成了教会组织及教徒反对国教的普遍理由。
耶教徒艾知命驳斥孔教的理由囊括了嘈杂的反对声中的主要观点,艾氏认为,“我国五族共和,教统庞杂,教体万难统一”,“于群教并行之中,无端而举一非宗教者,立为国教,是何异于续凫断鹤”,且“儒术本非宗教,而乡曲迂儒或有守之太过,基督教之输入,教案由此而兴”(注:艾知命:《上国务院及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142-5144页。),文中暗示若定国教,将有教争与教案发生。同时,在基督教的喉舌刊物《圣教杂志》上,也屡屡刊载非议孔教的文章,否认孔教是宗教。(注:张百禄:《孔子非宗教家》,《圣教杂志》第2年第12期。)
三
剖析以上辩论双方之言论,不难发现,辩论的实质非落实孔教是否宗教,或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而是围绕着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能否在新体制下存在的命题而展开,这亦是该讨论之所以发生在民初的根本原因。对孔教或褒或贬,实则是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政见、学术立场、宗教团体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无论是孔教会、支持孔教的军阀、传教士,还是反对孔教的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甚至包括袁世凯等政界人物、孔社、外教组织等,均是处此政体变更之际对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不同思考。
第一,孔教会人士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模仿基督教进行宗教的内外在建构,借宪法以确定孔教权威,将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挽救道德沦丧与寻找传统文化出路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儒学在新政体下合法权威。
民初,康氏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不仅使政体变更,同时也使“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堕鐸,礼俗变易”,使国人“不知所师从,不知所效法……”(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799页。),在意识到建立共和政体、废除尊孔读经,将必然导致传统失落及普遍意义的信仰危机的基础上,康意识到重塑一套亲和于国情并相配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作为国人的价值目标与精神寄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孔教会藉孔教重建国人信仰体系,然其思路是藉此开启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曾说其师是基于“民俗历史”而建立孔教,而康自己亦说国无论大小,“莫不有教”,“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显然,康氏在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前提下,利用儒学信仰层面的合理内核,将重建信仰与提倡孔教结合起来,以寻找传统存在的庇护所。就此论之,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儒学具有信仰与宗教的功能。对孔教会人士“创教”,当时褒贬有之,以后学者也多有持论。以下征引诸家议论,以论证之。余英时曾说,康氏“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余接着说:“作为一套信仰系统,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儒家毕竟与一般意义下的宗教不同,它基本方向是入世的”(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50页。)。在否认了将儒教变成宗教的可能性后,余氏又肯定了儒家信仰层面所具有的宗教性。
在儒家信仰层面上,钱穆则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主要动力”,就历史形成而论,“儒家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几个古圣昔贤凭空创造出来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注: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学》,《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5-50页。)。钱穆此论,更说明了康氏等人本着历史风俗习惯建立孔教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因为,康氏以孔教布道于中国,是因为孔教形成于“民俗历史”,此与钱穆所谓儒家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之意极其吻合,因而将中国人日日涵濡的这套价值体系打造为教,作为国人的信仰之物,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之处。
而冯友兰虽否认儒家是宗教,然就其相关的论述中,却能找到与康相通之处。冯氏认为:“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而实际上,儒家不是宗教。”但冯氏又说,儒家学说即是哲学,中国人是哲学的,而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成为人”,中国人在中国哲学的涵濡下“成为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
且后来冯又声称“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而冯所谓之哲学,即是儒教(注:钟肇鹏:《以儒学代宗教》,王中江、高秀昌编《冯友兰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8-89页。)。征诸以上各家论述,至少可认为利用儒家宗教信仰层面、以其道德价值去整合国人的意义世界,有其历史根据。
(二)选择孔教作为国人信仰,与佛、耶相较似乎更胜一筹。尽管基督教在民初有长足的发展,然就中华民族的感情与基督教教义本身而论,都注定其与中国社会民众格格不入。蒋梦麟曾说基督教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注: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其在国人眼中的形象跃然纸上。民初,基督教利用“信教自由”约法条款,攻讧孔教,挑起佛、道、回对孔教的仇恨,企图打败并取代孔教。然鉴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的需要,佛、道、回各教审时度势,也不尽然反对孔教。
而且,基督教排斥孔教之根本企图,是实现“中华归主”,“实欲孔教之在中国,失其宰制人心之权籍”而被取代,当时之局,诚如时人所谓:“孔教苟废,则各教必不能独存,试观五年以来,天师则削其封号,僧侣则夺其庙产,惟基督新旧二教,以有通商约章之保护,纵横全国”,“测其势力,不至尽并各教不止,是故孔教亡,则佛教次之,道教又次之,回教又次之”(注:《希社全体公民关于国教之请愿书》,《孔教问题》,《宗圣学报》,第17号第18期增刊。)。显然,如此之格局决定了基督教在民初并非众望所归,故有论者驳斥“今日中国惟一之救济术,惟耶稣教士耳”的论调,认为“耶教”欲想取代数千年之“国教”,而成为中国人之宗教,是不可能之事(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显然,民初基督教对孔教的诋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冲撞的继续与在民初的表象。
(三)国教方案乃是康有为等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而国家因儒家思想的衰败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认知前提下提出的,故国教成了走出困境的“功利主义”(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8-409页。)的选择。萧公权说康氏在戊戌时期就已确信,中国若丧失传统,“民族将无可认同。保全儒教与保全帝国一样重要”(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而在康氏反复强调的“保国、保种、保教”中,“保教”是其强调的核心。民初,康则谓孔教即“国魂”,“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7页。),国魂在,国亡也有复兴之日。而陈焕章也反复强调“孔教之废兴,即吾国吾种之存亡所系也”,孔教亡,“则国家必亡,社会必乱,种族必灭”(注:《经世报》,第1卷第1号、第4号。)。
国性之谓,也在梁启超的关注中。1913年,梁宣称国性凝集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中,国性的衰败,将严重的威胁国家的生存,强调孔教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宝贵的统一体,中国必须在其国民性的基础上,恢复其传统的道德规范,否则中国将灭亡。(注:梁启超:《国性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尔后,梁数次强调国性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并断言“吾就主观方面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注: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第1卷创刊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台湾文海出版社。),而不亡之原因,有孔教在。因为,“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搏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弊,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注: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中国国民者何,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基于上述三点,可以说,尽管作为策略——提倡孔教在当时有阻碍新思想、客观上支持帝制复辟等应被坚决否认之处,但作为策略要实现的目的及策略的部分内涵,却并非绝无意义可言。而且,就当时反对孔教的人中,随后也逐渐意识到孔教会关注宗教、填补信仰真空的必要性,这反证出孔教会建立国人信仰的合理性。如蔡尚思在20世纪初请陈焕章校阅其所著之《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一书,当陈对书中不认同孔教之处向蔡提出异议时,蔡答曰:“孔子之教,并非释耶一类之宗教比也”(注:蔡尚思:《孔子哲学的真面目》后附《师友商谈录》,收入1935年3月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2·,上海书店。),反对孔教是宗教,但后来,蔡尚思一改当初之观点,“才觉得以前说的‘孔子不是宗教’,未免错了。说‘孔子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还是对的”(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
第二,新文化运动人与孔教会争锋相对,表现了民初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注:董士伟:《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评康有为、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既是对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在新政体下是否需要传统问题的不同回答。
孔教会提倡孔教,客观上支持了政治倒退行为,使孔教与帝制脱不了干系,这使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政治革命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乃是因为在共和民主这块招牌下,仍然是君主专制的旧思想、旧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人对传统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倡导科学、民主,讨伐传统文化。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人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民初两大阵营对传统文化迥异的文化价值取向,前者以保守传统求发展,后者以破坏传统求发展。
对孔教会倡导孔教,无论是孔教的宗教形式,还是内容,新文化人是鞭笞不遗余力,但后来对宗教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此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孔教会要实现的目的:整合国人意义世界的必要性。新文化人最初的口号是科学、民主,反对包括孔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方案的偏颇,诚如余英时所言:“民主与科学绝不能穷尽文化的全幅内容。道德、艺术、宗教等等都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但并不能乞灵于民主科学”(注: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变迁》,李泽厚、庞朴主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页。)。事实上,“穆小姐”(moral)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道德领域的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民主,后来相继提出“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以不朽代宗教”(注: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2),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等方案,已说明新文化人意识到排斥宗教的不妥(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有关孔教的讨论,至今仍存在于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而在海外,有关孔教的争论也未间断过,因此,20世纪初关于孔教的讨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标签: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基督教教育论文; 康有为政论集论文; 孔子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东方杂志论文; 民国丛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