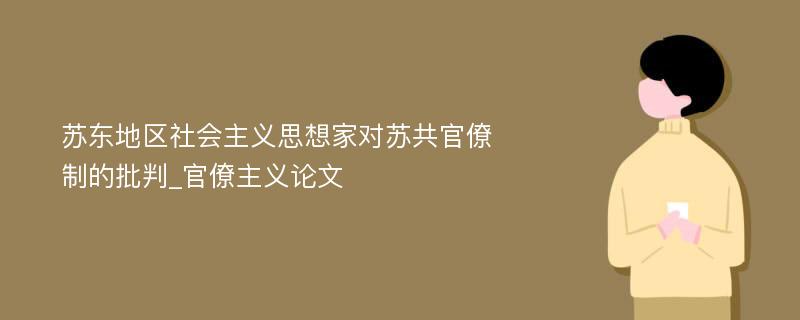
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共官僚化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家论文,官僚论文,苏共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认为,官僚政治是旧制度的产物;旧制度下的官僚机构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把无官僚政治的统治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不成熟以及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如何进行组织和管理认识上的不足,苏联建立起了一种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初的社会主义构想,又不同于旧官僚制的“异化官僚制”——官僚机构不仅未被消除,反而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甚至有人称其为“极权官僚制”“超级官僚制”。对此,苏东国家的一些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官僚主义”论、“官僚阶层”论和“官僚阶级”论三大类别。由于提出者立场不同、切入角度不同,三者对官僚主义者的性质、产生官僚异化的原因、摈弃官僚制的措施给出了不同答案。 一、“官僚主义”论 “官僚主义”论的代表人物是列宁。它的核心观点是虽然承认苏联党和国家机构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异化现象,但是否认苏联政治体制已经异化为一种官僚制,而认为只是存在着个别机构和个别干部作风上的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提出应该按照“巴黎公社原则”①来设计社会主义政权,“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②。然而,革命胜利后,列宁很快意识到在落后的俄国,人民不能直接参加管理,需要启用旧官吏。随之,苏维埃国家出现了官僚异化现象。对此,列宁给予强烈谴责,甚至认为,“党和政府机关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能够把布尔什维克政权毁灭掉的就是共产党员成为官僚主义者。③当时,虽然认识到官僚异化问题的严重性,列宁却将其定性为官僚主义。所谓的官僚主义,列宁的定义是个别机构、个别官员的作风问题。他在《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是“泛泛之谈。空话连篇。大家听厌了的愿望”④;在《进一步,退两步》中提出:“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为增补进行争吵而不进行思想斗争。”⑤ 从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布尔什维克政权仅仅走过了5年多的历程。官僚异化问题虽然在党和国家政权中都有所显现,但发展并不充分。因此,列宁没有也不可能把它作为一种官僚制来看待,而只是把它当作俄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暂时的附生现象,一种旧制度下的官僚主义的“回光返照”。上述认识直接导致了列宁对官僚异化产生原因分析的局限,即认为它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绝对权力后,自身建设跟不上掌权后的形势发展,而是归因为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和旧官吏进入国家机关的影响。 在列宁看来,俄国经济的分散性是官僚主义产生的经济基础。列宁在俄共(布)十大所作的中央政治工作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国家制度中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脓疮,以致我们的党纲也提到了它,这是因为它和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及其涣散性有联系。”⑥分散的经济决定了俄国的基本阶级结构是农民占多数,工人占少数。在旧社会,小生产者缺乏民主习惯和民主意识,而且他们对权贵的崇拜、对金钱的追求是官僚主义产生的肥沃土壤。十月革命后虽然土地收归国有,但是改变农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思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⑦。这些旧的思想正是现在官僚主义的温床。农民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抵制等行为,正是他们落后性的集中体现。 滋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工人阶级不具备直接管理国家的能力,因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起用旧官吏,正是旧官吏把官僚主义带到了国家机关继而传染给了党的机关。长期生活在沙皇统治下的民众不仅文化水平低,而且缺乏政治参与的经验和热情,“即使国家的管理工作被简化为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俄国当时也无法实现人人都参加管理”⑧。因此,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难以实现。布尔什维克党认识到需要起用具有管理经验的旧官吏和专家。但是,这些人曾长期混迹于旧的官僚机构,带有官僚主义的习气。他们进入苏维埃机关后把陋习也带进了新的国家机关。“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便于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结果,把他们赶出门外,他们又从窗口飞进来。”⑨更严重的是,“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这些旧官僚带来的官僚主义也影响到了部分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党的机构也开始官僚化。⑩ 正是出于以上判断,列宁试图找出遏制官僚主义在党政机关蔓延的方法。他的主要设想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提高工农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尽可能多地吸收工农参加管理工作,对党和国家机关进行监督。既然俄国落后的国情造成了工农文化水平不高,造成了“控产党人”(11)重新回到国家机关,那么,要阻止官僚异化的最根本措施就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为此,列宁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指出:“为了革新我国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12)同时,列宁让工农学会自己管理,鼓励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监督,把官僚主义者驱赶出去,因为“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13)。 其次,注重提高党员质量,控制党的规模。列宁有句名言:“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自给,我们也不要。”(14)在实践中,布尔什维克党也试图去贯彻这一原则。具体做法有二。一是严格入党条件,从源头上控制好党员的质量。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针对不同人群设置不同的入党标准。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入党需3个具有3年党龄的党员介绍,经县委或区委批准;农民和手工业者入党条件同上,但需经州委批准;其他人,特别是脱离其他政党的人需有5个具有5年党龄的党员介绍,经州委批准。此外,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的预备期至少是6个月,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一年,其他人是两年。二是厉行清党,清除不合格的党员。列宁指出:“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到执政党里来,这也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15)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部署清党工作。清除主要对象为阶级异己分子、敌对分子、骑墙分子、蜕化分子及官僚主义分子等。 最后,厘清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职权,通过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来防止官僚主义蔓延。在列宁看来,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分工不明确是官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应该是由国家机关承担的工作都交给了党的机关,甚至是集中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去解决,造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懒政”。因此,除了裁撤多余机构,更有必要明确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他提议在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划清职权,解除政治局的琐碎事务,让各人民委员对自己的工作负责。(16)当然,厘清党的机关与国家机关的职权不是为了削弱党的领导,而恰恰是更好地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让国家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更有效率地工作。为强化党的领导,列宁注重把党的干部任命到国家机关,在选拔国家机关人员时必须选取政治过硬的人员。例如,在谈到工农检察院的人员录用时,列宁提出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胜任,而且他还“必须由几个共产党员介绍”(17)。发动普通党员去监督国家机关内和其他组织机构中旧官吏和专家的工作是列宁阻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的另一项举措。在总结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任务时,列宁写道:“要大胆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我们的党纲非常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官僚主义会在某种程度上复活以及怎样防止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要大胆,首先是说要大胆地让那些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其疾苦和要求的新党员对职员、官吏和专家实行监督。”(18) 可以说,列宁晚年对官僚主义进行的斗争是非常有益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其对俄国的落后性估计不足,以及对共产党的先进性估计过于乐观,他提出的通过强化党的权力来遏制官僚主义的方案有很大局限性。事实上,列宁并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绝对权力,没有认识到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会真正遏制官僚主义。他甚至主张把党的机关同苏维埃机关“结合起来”或“合并起来”(19)来遏制官僚主义。被后世认为是列宁创设的监督党的权力的重大举措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与中央委员会平行而且不得由中央委员兼任委员,但设立的初衷却是为了“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苏维埃中的职权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20)。诚然,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但这种“特殊材料”产自于俄国特定的时空。苏联共产党本身并不天然地具有抵御官僚主义侵蚀的免疫力。“先进”的阶级性并没有有效防止贪婪的人性的侵蚀。因此,通过强化党的权力去遏制官僚异化的做法,最终加重了党政机关的“官僚病”。 二、“官僚阶层”论 与“官僚主义”论不同,“官僚阶层”论认为,苏联党政机关中存在的不仅是官僚主义现象,而且形成了一个背叛社会主义信念、以谋取个人权力和特权为主要目的的官僚阶层。其代表人物有苏联的托洛茨基、麦德维杰夫以及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卡德尔等。 托洛茨基最初也曾持“官僚主义”论。在1920年出版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对考茨基的答复》一书中,托洛茨基针对考茨基提出的十月革命后部分布尔什维克成了新统治阶级的说法,还坚持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中存在的只是暂时的官僚主义现象。(21)然而,在同斯大林的权力斗争失败后,托洛茨基开始认识到官僚主义者在背叛革命的过程中已经结成了联盟,成为了一个“官僚阶层”,不过他仍不同意考茨基的“新阶级”论。在托洛茨基看来,官僚主义者只是一个阶层的依据在于它并不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所有权是划分阶级的基础。在苏联,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官僚主义者虽然在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权利,可以通过垄断国家权力来任意管理和分配国有化的财产,却不具有资本家那样的私有财产,“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个观点来看,元帅和女佣之间,托拉斯经理和临时小工之间,人民委员的儿子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之间,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差别”(22);而且,他们还“不得不保卫作为自己的权力和收入源泉的国有财产”(23)。同时,官僚主义者没有股票,没有公债,也不能把官位传给下一代。这些与传统的阶级有着根本不同。所以,官僚主义者只是一个从无产阶级中异化出来的特殊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 托洛茨基的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相关问题的批判者,无论他们是否赞同托洛茨基的结论,但是在讨论苏联官僚主义者的性质时基本上是围绕着他提出的命题——所有权问题、权力继承问题展开的。麦德维杰夫、铁托和卡德尔虽然因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负面形象而否认自己的思想与托洛茨基有任何渊源,却很“巧合”地提出了与托洛茨基相似的看法,认为苏联建立了一个“官僚阶层”的统治。不同的是,他们比托洛茨基更加强调“官僚阶层”的权力之大、腐败之甚。麦德维杰夫指出,官僚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阶级的特征(24),因为官僚主义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压倒一切的作用,并企图利用国家机构作为自己的工具”(25),而且已经具有了类似于阶级意识的观念,有意在维持自己特权地位和权力。(26)卡德尔则指出,苏联的“官僚阶层”比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资产阶级还要专横武断,因为西方国家由于实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多元化,还可以阻止官僚主义演变为极权主义。(27) 托洛茨基等人对“官僚阶层”产生原因的分析也十分近似。首先,他们都相信,落后国情所导致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掌权后不能实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国家“消亡”是官僚异化产生的重要原因。托洛茨基认为,阻止苏维埃国家“消亡”的首要原因是物质条件匮乏、内战和外敌入侵等因素需要保留国家机器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由于工农文化水平低,国家机关需要启用大量旧官吏参与社会管理,在此,托洛茨基得出了与列宁一样的判断——是旧官吏把官僚主义带到了国家机关。不过,托洛茨基并未像列宁那样把官僚异化的出现单纯归结为启用了旧官吏,而是认为,虽然“‘苏维埃热月政变’的队伍主要是从旧执政党的残余和它们的思想意识代表们中间集结来的”(28),但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假社会主义者不容忽视。这些假社会主义者自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之初就存在于党内,等到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他们就伺机而动,直接导致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异化。(29)当国家机关成为客观需要以及国家机关掌握着产品分配权时,无论官吏是来自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不会放弃谋取自身利益的机会,官僚化便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在使少数人得到好处并维护这些好处的时候,它当然把最大的好处留给自己。谁也不会在有财富可分的时候把自己除外”(30)。据此,托洛茨基甚至认为,“目前的苏维埃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也不能——适当地——没有一个官僚阶层”(31)。 麦德维杰夫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捍卫革命成果而强化国家机器的做法无可非议,但是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国家机关里混入了一些不愿意为无产阶级利益工作的“阶级异己分子”,而且他们把旧习气传染给了信念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于是蔓延到了党的机构。由于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许多党的领导干部便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党的机构的某些工作人员开始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去使用自己的权力。党内机构的个别重要环节也出现了腐化因素,完全没有什么理由使一些党的干部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后来又变成目的本身,成为一种拜物教。”(32)铁托和卡德尔同样相信官僚阶层产生的根源是斯大林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国家“消亡”。在苏南论战中,铁托指责斯大林说,斯大林“从未确定党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依旧把它看做是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的领导者,“把党和党的作用归结为官僚机器,归结为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归结为执行各种强制性措施”,并导致党越来越同国家机器融合为一个整体。(33) 其次,革命者的背叛。在托洛茨基看来,自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之时起,党内一直存在着两种人:前者是以列宁为代表的真正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理想;后者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假社会主义者,他们虽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喊得很响,却以夺取和巩固个人权力为最终目的。(34)列宁在世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坚决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并且严防官僚主义蔓延到党的机构。但是,斯大林上台后把党的机构也官僚化了。“斯大林派的历史作用就在于摧毁这种双层关系,而使党屈从于它自己的官僚并把后者融合在国家的官僚当中。目前的极权主义制度就是这样产生的。”(35)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会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不断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并将自己的权力转换成现实的物质好处。麦德维杰夫则提出,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有继承关系,但本质是不同的。是斯大林利用了原有体制的漏洞,依靠官僚主义者的支持,改变了列宁的政策。例如,斯大林拒绝了多党制,而列宁并不是绝对反对除布尔什维克以外的其他党派的存在;斯大林禁止了党内派别活动,而列宁虽然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却不绝对排斥党内反对派;斯大林禁止发表各种不同观点,而列宁是以说服和示范的方法进行有计划的指导。最终,斯大林的上述做法导致党和国家机构的严重蜕变,产生了官僚主义制度。 “官僚阶层”论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解决官僚异化的方案。托洛茨基给出的方案是“不断革命”。他呼吁苏联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第二次革命,推翻官僚阶层的统治,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写道:“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注定要完成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个历史特权,从一切迹象来看,无产阶级还必须再进行第二次补充革命来反对官僚专制。”(36)然而,因为官僚主义者是一个特权阶层而不是阶级,无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绝不是一次阶级革命,“问题并不在于一个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统治集团,而在于改变国家管理经济和指导文化的方法”(37)。因此,第二次革命的目标是恢复列宁时代的传统,建立一个“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党将代替特权阶层成为领导者,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度,以及恢复苏维埃中各党各派的自由”(38)的社会。 麦德维杰夫主张“回归真正的列宁主义”。第一,实行真正的选举制度。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允许立即实现列宁设想的“人人都成为官僚,人人就都不是官僚”的直接民主,因而只能是通过真正的选举制度产生忠于人民的政治家来代表人民治理国家。(39)第二,确立多党制。多党制的存在同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有关,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别,而拥有不同利益的人们在政治上需要不同的政党来代表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差别导致了党内外不同的政治流派。(40)第三,要遵守和发展党内的民主原则,开展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辩论,允许反对派发表不同意见。第四,要扩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结社自由。对于“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实现,麦德维杰夫寄希望于上层官僚阶层中的开明者、知识分子和下层人民之间的结盟。尽管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斗争十分重要,会给执政集团带来政治压力,但是“来自最高党政机关的正确政策和对民主化进程的正确领导,乃是使围绕民主化的许多困难问题进行政治斗争时付出的代价最少,并且将不会超出一定范围的重要保障”(41)。 铁托和卡德尔寄希望于“自治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具体做法是:在经济领域,把国家所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让全体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用“计划化”逐渐取代指令性计划经济。在政治领域,削弱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推进国家“消亡”,把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以及收入分配权逐步由国家转交给直接生产者和社会自治组织;党要逐渐“消亡”(42),从对社会的全面干预和控制中退出来,成为一个“推销员”和“教育者”。(43)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南斯拉夫的政党体制在改革过程中并未真正触动。当改革触及政党体制时,铁托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南共联盟要“消亡”,但“消亡”没有明确的时间表。铁托认为,由于南斯拉夫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党员群众文化水平较低,过早“削弱”南共联盟的领导会导致社会动荡和资产阶级复辟。(44)第二个方案是改良一党制而拒绝多党制。在铁托看来,除了共产党外,其他任何政党都不能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采取多党制就是允许多个政党存在,允许多个社会发展纲领的存在。它不利于国家团结,也不利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45)南斯拉夫后来的政治发展表明,这两个方案实质上都导致了苏联式政党体制的保留,这也成为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失败的主要诱因之一。 可以说,“官僚阶层”论者与“官僚主义者”相比,对于官僚异化的危害认识上更进了一步,已经意识到苏联的问题不再是个别机关、个别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而是在党政机关内形成了由官僚主义者组成的特殊群体,而且官僚异化产生的原因,除了国家落后外,还有党和国家权力过于集中的因素。“官僚阶层”论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摈除官僚异化的措施上。首先,并不是所有人都认识到约束党的权力比提高党的先进性更重要,如托洛茨基;更重要的是,回归列宁主义,何为列宁主义?托洛茨基、麦德维杰夫和铁托等人的看法并不一样。回归列宁主义行得通么?前面提到了列宁对官僚化现象的认识有种种不足,以及列宁主义在党和国家政权设计上的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为日后斯大林建立官僚体制埋下了隐患。因此,即便恢复真正的列宁主义,能保证不再产生出一个斯大林么?同时,人们是否会追随托洛茨基进行二次革命是有疑问的,甚至是否会再次选择社会主义也是有疑问的。苏联的历史也确实没有如托洛茨基和麦德维杰夫的愿。的确,苏联领导层在危机面前产生了分化。一派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他们把民主化和公开性作为了改革内容,以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为目标;一派是顽固派,他们拒绝对苏联官僚体制进行任何改变,认为可以通过暴力来继续维持统治;麦德维杰夫未曾料到的第三派,也是最有实力的一派,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他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而把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作为未来的社会道路,并得到党政军的青壮派的支持,发动了“来自上层的革命”(46),推翻了苏共政权。苏共丧失政权过程中,工人阶级和普通党员并没有站在共产党一边,因为长期存在的官僚异化问题已经耗尽了人民群众对苏共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官僚阶级”论 “官僚阶级”论比“官僚阶层”论更为激进。它指责苏联的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而不仅是一个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意味着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无阶级压迫的自由人联合体。“官僚阶级”论的代表人物有南斯拉夫前副总统吉拉斯、波兰哲学家沙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理希克。 吉拉斯判定苏联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的依据有三。第一,它的所有权。苏联虽然实行的是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财产形式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真正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则是一群官僚”,而在罗马法中“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因此,对生产资料事实上的支配和享用就是所有权。(47)第二,它的阶级意识。“官僚阶级”是一个自觉维护其阶级利益的集团。虽然“官僚阶级”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阶级,但在维持和巩固其阶级利益方面,它的阶级意识比历史上任何阶级都强。“历史上没有任何阶级在保卫自己、控制其手中握有的集体的、垄断性的所有权与行政权时,是如此团结一致。”(48)第三,它的权力。权力垄断是“官僚阶级”之所以为一个阶级的根本因素,而“所有权与阶级意识都是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的垄断权,包括行政大权、经济垄断权和思想控制权)的派生物”(49)。 沙夫和希克在接受了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观点的同时,更侧重苏联官僚制与一般官僚制的区别。在沙夫看来,官僚制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必不可少,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家不复存在,官僚制度的必要性“并不比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必要性小”(50)。苏联官僚制的问题在于超出了官僚制的一般职能,发生了“异化”。“这种官僚体制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像现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可能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这种制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又凌驾于社会之上,往往会转而反对社会。”(51)希克使用的概念是“超级官僚制”。在他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官僚机构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苏联的官僚主义者则由于单独垄断了政治权力,继而垄断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在历史上第一次自己变成了统治阶级,而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其他阶级和阶层都不可能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强加给党政官僚主义者。“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体制并随之而排除了内部和外部反对官僚的重要因素之后,官僚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中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管理机构的官僚化达到荒谬绝伦的程度。”(52) 三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官僚异化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在吉拉斯看来,“官僚阶级”产生的根源在于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客观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俄国若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下,俄国的私人资本力量十分薄弱,不但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反而“事实上在阻挠工业化”——寄生在外国资本和专制王权的篱下并阻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此,能够完成工业化的革命必须既反对本国资本和国外资本,又必须有能力集中一切物质资源。也就是说,“除非革命党能控制国内一切资源,尤其是那些因残酷的剥削和不人道的方法而遭群众痛恨的本国资产阶级的资源,否则,革命党就不能真正地执行工业革命。同时,革命党还得对国外资本家采取同样的对策”(53)。布尔什维克党具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优越条件: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政治上和思想上高度集中,一贯地主张推行工业化政策,自然而然地成了革命的执行者。革命胜利后,还必须有人继续肩负起工业化的责任,在西方国家是由资产阶级来完成的,而“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54)。为了继续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仍必须集所有资源于一身,于是便具备了官僚阶级统治确立的必然性。概言之,官僚阶级统治的建立“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55)。 沙夫认为,官僚异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在革命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发动了革命。当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的时候,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局面虽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掌握政权的可能性,但是不能提供产生社会主义者执政的条件。社会主义者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迫于具体的客观因素来发动不成熟的革命,革命就会发生异化,会朝着与革命发起者的本来意图不同的方向发展。(56)革命胜利后,由于无产阶级的数量少而且文化水平不高,无产阶级政党缺乏雄厚的阶级基础,无法通过正常的选举途径上台和治理国家,于是不得不依靠恐怖手段实行一党统治。(57)同时,“异化”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党的“异化”。在革命胜利后,党的职能从革命变成了建设,承担了大量的管理工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将会由职业革命家的党成为群众性的政党。新党员把他们的社会特征带入党内,而这种特征是由其社会出身及其所出身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心理结构等因素所决定的,带有浓厚的旧社会的特征。“党在向群众党发展的过程中被涌进来的新分子所‘吞噬’,这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非常自然地构成党的群众基础,并占据了党内要津。”(58) 与吉拉斯和沙夫不同,希克强调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官僚异化认识上的不足以及政权设计上的缺陷在官僚制形成中的作用。希克认为,苏联的官僚体制早在列宁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主张取消市场交换,由国家直接分配产品。这种设想在理论上被严重地简单化,忽视了市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客观上不能取消的种种原因,夸大了国家的作用,并把国家对经济的作用提升到绝对地位。这是国家机关滋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但是,当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蔓延时,列宁却相信它是由于旧官僚进入党和国家机构造成的,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造成的,而没有认识到官僚异化现象与高度集中的、垄断化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59)因此,他所采取的反官僚主义的措施主要是提高人民文化程度,加强工农检察院和工农的监督,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这些措施导致党的机构和监察机构的不断扩大,实际上“一面在口头上号召消灭官僚主义,一面又要求人们一切听从于党,这实际上是用鬼驱鬼”(60)。结果党政机构逐渐具有了自身特殊利益,可以决定所有下属国家机构的领导人选,可以任意地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及其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61)。于是,“在一般的官僚体制内部又产生了一个超官僚体制”。据此,希克断言,斯大林就是通过列宁时期已经形成的不民主制度、依靠已经存在的党政官僚主义者的支持上台的。他的作用只是使官僚统治更加稳固,官僚的统治领域更加扩大。(62) “官僚阶级”论者由于认定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他们便否定了苏联官僚主义者通过自身改革来实现民主制度的可能,而是寄希望于人民的抗争。其中,希克的观点尤为详尽。在他看来,面对民众对官僚统治的与日俱增的不满,官僚阶级会分裂为顽固的保守派和希望进行有限改革的自由派。但是,期待他们通过改革来排除官僚统治是一种幻想。“为实现改革体制而努力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们,在较自由的条件下要比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下能较容易地为民主化进行斗争(比如捷克的改革派就曾如此)。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到在为真正的民主化进行斗争时,迟早会遭到整个党的官僚的抵抗。”(63)因此,人民只能通过自己的斗争来解放自己,决不能放弃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只有进行不懈的英勇斗争,“从这个阶级的手中夺取政权,并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体制的民主化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所有决定过程的民主化,才能结束这个特殊阶级的统治,铲除这个官僚体制的统治阶级,这也正是东方集团国家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提”(64)。 此外,“官僚阶级”论者还提出了苏联官僚制的替代方案。多党制是吉拉斯、沙夫和希克都提到的方案。然而,三者对多党制的理解不同,吉拉斯所说的多党制是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允许两个或多个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存在、相互竞争、轮流执政。沙夫和希克并不像吉拉斯那样强调多党必须是多个社会主义政党。他们认为,只有实现多党制,领导人才可能按正常的方式受到社会的监督、批评以致撤换,才会消除政治家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状态。不实行多党制的最终结果就是专制,就是“万人服从一个人,这个人可以借助官僚机构决定一切”(65)。同时,沙夫和希克还分别提出了一些让苏联官僚制回归一般意义上官僚制的设想。例如,沙夫提出,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积极经验,引入多元主义机制,确立权力的制约和平衡原则(66);革新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改变党的组织模式来限制党的机关所具有的绝对权力(67);建立党内不同机构间的权力分立和制约,“各个机关之间的竞争,它们之间的相互监督(在一定情况下可能会滥用职权)”,从而形成有效的制衡;加强对党政机关的社会监督。(68)希克则强调真正的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把一切管理和领导工作交给从最基层到中央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组成的机关,一切关系到人民生活的重要基本方针的决定都由被选举出来的在一定任期内的人民代表来制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69) 与“官僚主义”论、“官僚阶层”论相比,“官僚阶级”论对苏联官僚制度的批判最激进,它彻底否定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正因如此,西方一些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利用它来批判社会主义制度。例如,弗吉尼亚大学的哈蒙德称赞吉拉斯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他通过公开否定共产主义政权,成为了唯一一个主动使自己下台的共产党高层。其他的共产党人虽然享受着共产主义带来的福利,然而,毫无疑问,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早已破灭。这些统治者中却没有一个人具有智识上的诚实和道德的勇气来戳穿谎言和承担后果。”(70)截至20世纪90年代,吉拉斯的《新阶级》已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发行300万册,被《纽约时报》列入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书。 但是,苏联官僚制真是一无是处么?“官僚阶级”论真的科学么?历史的发展给予了“官僚阶级”论最强有力的挑战。如果苏联的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苏联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那么,为何“官僚阶级”在苏联剧变中没有进行激烈反击就交出了政权?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的下台都是要经过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和战争的,英国、法国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不如此。为何官僚阶级的统治只持续了70多年,而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存续时间都要比它长得多?或许把苏联官僚制看做是俄国历史上专制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极端化发展更为合适,现代化的历史使命让其承担起了西方国家专制王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则让其比历史上的专制主义权力范围更广、权力更大。 任何社会意识都是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客观评价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官僚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反思,前提是要准确评判苏联官僚制。苏联官僚制的建立产生于一种社会现实矛盾:从现代化初始条件看,苏联处于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期;而从社会制度看,这些国家要建设的是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因此,执政的共产党需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来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但它可利用的资源只有先进的政党组织、手中的国家权力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了推进现代化建设,共产党不得不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世界革命理念,放弃了国家“消亡”理念,而通过不断强化的国家机器来教条化地推行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念。结果是,党和国家掌握了绝对权力,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并通过行政性指令来计划经济现代化,由此便产生了一个权力巨大的官僚制。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苏联官僚制功过参半。它通过专制的力量积累了现代化的资源,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苏联迅速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建立的工业化体系。然而,苏联官僚制中蕴含的专制力量会逐渐阻碍现代化,并最终为现代化所产生的客观力量推翻,因为现代化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成果分配公平性的合一。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森指出的:“苏联体制动员了数量极为可观的资源,但它却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些资源……苏联型社会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要低于——且越来越低于——处于可比发展水平上的市场经济体。”(71)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苏联官僚制的影响是负面的,它与社会主义的理念相违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写道: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共产党的官僚化现象及苏联模式的失败,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对苏联官僚异化现象的批判集中于其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一面,列宁如此,托洛茨基等人也是如此,鲜有人提及官僚制在苏联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吉拉斯是一个例外。吉拉斯看到了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客观需要是“官僚阶级”产生的客观条件,看到了“官僚阶级”在苏联工业化进程中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他认为,工业化一经完成苏联官僚制就成了完全消极的现象。可是,在吉拉斯那里,工业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72),到底什么标志着工业化的结束?苏联的官僚制度何时变得完全消极了?这些都没有答案。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差异性很大,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苏联非社会主义的一面。列宁的观点自不必说,为何“官僚阶层”论者与“官僚阶级”论者在官僚主义者是一个阶级还是一个阶层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对此,英国学者毕瑟姆给出了答案:“断言官僚制的统治不是构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转折点,而是阶级社会的一种新的形式,在这种阶级社会中,官僚制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结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而且在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态度上,都有着重大的含义。”(73)即便是最为激进的“官僚阶级”论,被许多人认为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它的分析方法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英国外交家巴克尔指出的:“吉拉斯虽然有能力批判马克思和列宁,却仍旧羁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分析方法。”(74)研究方法的差别不仅构成了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异,也构成了他们与西方相关问题的批判者之间的根本差别。极权主义是西方批判者广为使用的一个概念,而苏东社会主义思想家很少有人使用这个术语。极权主义的概念适合苏联的政治体制么?或者更准确地说适合苏联政治体制的全部么?极权主义虽然也是一种全面进行社会控制的状态,但是极权主义的建立必然要打碎原有社会中位于领袖和群氓之间的中间势力,无论其是中间等级、阶级,还是精英、贵族阶层,建立领袖与群氓的直接对话。(75)但是,官僚制度是建立在等级秩序之上的,金字塔形的等级机构是官僚制度的最根本特征,苏联官僚制也不例外。在苏联,除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部分时间外,虽然领袖地位十分突出,但是并不存在上述极权主义的特征,因为官僚机构、庞大的官僚主义者恰恰是横在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力量。这一点也是我们在评析“官僚阶级”论时必须要看到的。 ①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提到后来被人们称为巴黎公社原则的若干做法:公职人员均由普选产生,对于不称职的人员可以随时撤换;实现议行合一,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权是一个实干的机构,而不再是议会清谈馆或者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机构;建立廉价政府,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6页。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0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0页。 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5页。 ⑤《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3页。 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6页。 ⑦《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0页。 ⑧黄宗良:《论苏俄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97页。 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4页。 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 (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人民出版社,第14页。 (12)《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6页。 (13)《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506-507页。 (1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5页。 (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4页。 (16)《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697页。 (17)《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02页。 (1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30页。 (19)《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4卷,第706页。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0页。 (21)考茨基的观点参见《考茨基言论》,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三联书店,1980年,第336-337页;托洛茨基的看法参见Leon Trotsky,Terrorism and Communism:A Reply to Karl Kautsky,Conn.:Greenwood Press,1986,pp.367-373。 (22)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63年,第174页。 (23)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182页。 (24)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赵洵、林英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18页。 (25)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949页。 (26)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928页。 (27)《卡德尔论文选》,李嘉恩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年,第39-40页。 (28)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567页。 (29)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287页。 (30)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81页。 (31)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80页。 (32)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720-721页。 (33)《铁托选集》(1926-1951),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95页。 (34)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85-86页。 (35)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204页。 (36)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211页。 (37)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212页。 (38)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184页。 (39)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162页。 (40)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年,第63页。 (41)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1-362页。 (42)麦克维克:《铁托主义:国际共产主义的榜样》,何璧人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57-258页。 (43)《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任务和作用的决议》,载《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边忆菊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220-229页。 (44)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册,商务印书馆资料室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1页。 (45)《铁托选集》(1926-1951),第43页。 (46)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页。 (47)Milovan 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lnc.,1957,pp.33-47. (48)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p.59. (49)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p.169. (50)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奚戚、齐伍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7-60页。 (51)Adam Schaff,Alienation as a Social Phenomenon,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0,p.252. (52)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蔡慧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53)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p.17. (54)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pp.21-22. (55)Djilas,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pp.10-33. (56)恩格斯也有类似表述:“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萎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无产阶级大众的推动,由于受到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的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透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57)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39页。 (58)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43页。 (59)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8-9页。 (60)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23页。 (61)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16-17页。 (62)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30页。 (63)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185页。 (64)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179页。 (65)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58页。 (66)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69-70页。 (67)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106页。 (68)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第70-72页。 (69)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第150页。 (70)Thomas T.Hammond,"Review,"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73,No.1,1958,p.133. (71)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页。 (72)Henry Mayer,"Djilas on Communism," The Australian Outlook,Vol.12,No.2,1958,p.59. (73)毕瑟姆:《官僚制》,韩志明、张毅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2-83页。 (74)参见Elisabeth Barker,"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Vol.34,No.2,1958,pp.197-198。 (75)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406-423页。标签:官僚主义论文; 斯大林论文; 苏维埃论文; 布尔什维克党论文; 托洛茨基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苏东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