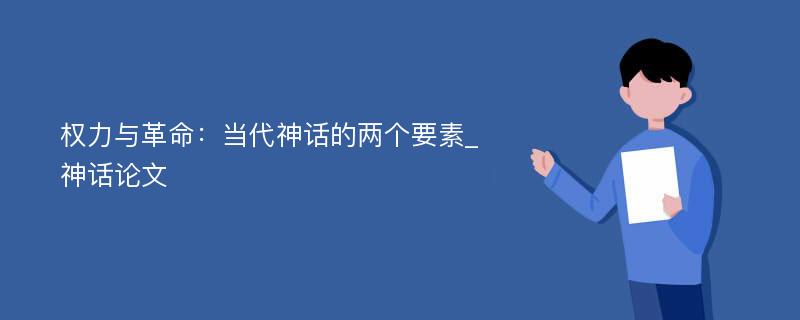
权力与革命:当代神话的两个要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素论文,当代论文,权力论文,神话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神话”理论是指承认神话和神话思维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并对其作出研究的理论。学术界有时候也称为“现代神话”(Modern Myth),其基本内涵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能指不同,其所指具有同一性。为了叙述和表达的一致性,以免引起阐释的歧义,我们统一指称为“当代神话”(Contemporary Myth)。 当代神话理论认为,“神话”在现代社会中甚至在后现代社会中依然不会消亡,只不过它改变了与以往神话不同的存在形式,甚至以现代科技作为神话的构成元素和面具伪装。当代社会必然性地存在着神话,它只不过是当代创造主体精心编造的结果,甚至带有工业社会和文化产业的痕迹。“当代神话”理论是指承认神话和神话思维在现代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并对其作出研究的理论。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的虚假的或理想性的超越,那么,“当代神话”即是指在当代语境中人类精神对现实世界的虚假的或理想性的超越方式。在此,我们将当代神话的基本特性作出简要概括:其一,当代神话是植根于当代社会的历史语境,它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古典神话的具象思维方式,采取了部分理性思维或逻辑思维方式。其二,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普遍渗透到当代神话的表现内容之中,因此,当代神话的思想意识表现出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的相互渗透的复杂特点。其三,古典神话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对神话内容、价值观念持有最大程度的观念信奉和情感认同,而当代神话的制造者在理性观念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神话的虚构性,他们只是借助于这种神话的制造和传播而达到安慰情感和文化娱乐的目的性。其四,如同古典神话采用古典话语方式一样,当代神话运用现代话语方式,而在这种话语运作过程中,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广泛地渗入其中。其五,当代神话除了拥有和古典神话相同的口头传播和印刷传播方式之外,更多运用了现代科技的方式,尤其是利用了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因此,当代神话的传播具有多向度、高密度和迅捷、隐秘和低成本等优势。最后,与古典神话广泛地存在于艺术文本的特性相类似,当代神话也广泛存在和深刻地影响到文艺生产活动,因此,当代神话与艺术生产的关联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当代神话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权力因素对自身的渗透,或者说权力普遍地进入神话疆场。对于权力的崇拜和渴慕成为整个公共空间的集体意识,由此而呈现一个二重性的图景:一方面,大众对于权力的觊觎、渴望和追逐,形成对权力的崇拜情结;另一方面,民众在心理上潜藏着对权力的仇恨和反抗的情绪,在历史提供释放暴力冲动的条件下,最终借助于社会革命获取和占有它。如此而已,合乎逻辑地形成一个权力的转移和循环。在权力循环的过程中,神话传播者支持臆想的“正义”概念,将之偶像化并且赋予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权力的转移和循环的每一个历史尺度,均包含着无穷无尽的阴谋与诡计、冲突与暴力、流血与死亡等必然性因素。显然,神话是鼓动权力循环并应验这一历史法则的有力工具之一。 如果我们对权力进行简略的逻辑划分,存在着两类权力:纯粹权力和潜在权力。纯粹权力是指独立存在的权力形式,主要指政治和法律等行政权力。它由集体权力和个人权力所组成。和纯粹权力的单一性因素不同,潜在权力纠结着多种要素,知识、话语、技术、规则等构成权力的结构,成为权力的复合性整合。 在近现代历史之中,“权力神话”和“革命神话”相互交织,生成了互动性生动景观。“革命”以对“权力”的重新支配为前提,革命的目标从总体上就是发动革命的阶层攫取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力,具体目标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在权力的重新分配中获得个人权力。革命神话一个显明的特性就是革命者向民众许诺美好的未来,把牺牲建立在对乌托邦理想的渴望之上。革命就是建立完美性和理想性的权力模式和社会结构,由此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参与。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借助于“革命神话”唤醒和鼓动民众。其实,“革命”这一话语隐匿着能指和所指的语言游戏。 从词源学考察,“革命”一词,目前所知的最早出处可以追溯到上古典籍《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口头语言应该在时间上要上溯更为久远。据学者考证,清末的王韬在《法国志略》(1890年)中,首次运用现代语义的“革命”一词。尔后,这一词汇经由孙中山等人改造为“国民革命”的话语之后,被赋予新颖的历史内涵,焕发了某种强大的诱惑力。随着历史时间的流逝,“革命”成为公共空间的盛大节日,并且上升为万众统一的语言狂欢,转换为统一国民与党派思想的最有效工具,也成为最富有乌托邦色彩的话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成为红色的话语图腾和最绚丽的文字崇拜,成为红色宗教中的圣词,一个神圣的信仰能指,或者闪耀着乌托邦色彩的巨大和崇高的符号。其实,自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革命这个词汇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被赋予了神话的意义,而且这一神话沾染着强烈耀眼的胸怀色彩。所以,革命神话理所当然地可以被比喻为“红色神话”。法国莫娜·奥祖夫在《革命节日》著述中精湛而细致地探究了革命与节日的逻辑关联: 与革命一样,节日是一个忘乎所以的境界;与革命一样,节日是一次本能的、冲动的创造。最后,与革命一样,普世的节日不会有征服者英雄。如果就像最高主宰节那样有一位的话,节日的感觉就泯灭了,革命也在死去。人民离开了街道和广场,从此各扫自家门前雪。只有当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时,节日和革命才是鲜活的。① 革命与节日的密切关联,表明人类内心深处潜藏巨大的暴力冲动并以宏大叙事方式呈现于现实世界,而宏大叙事的主角不再是平常人物而属于“人民”和卓越的“英雄”。而处于这一时间轴点上的日子就可能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盛大节日。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诸多的节日建立在革命的缘由上。然而,“革命”一词除了它外表上附着的正面意义和有限的历史价值之外,它潜藏着思维暴力和实践暴力的双重含义,隐匿着强大的破坏性冲动和颠覆性势能。“革命”甚至包含着野心家的诡计和政客的谋略,是一个交织理性与非理性冲动的精神旋涡。“革命”扮演着时刻杀戮他者的正义角色,扮演着真理和合法的代言人,随时以公正和正当的充足理由结束他者的生命。显然,“革命”是一个鲜红得流血的字眼,是一个红色的梦魇和阴影。“革命”的意义被不断地转喻和隐喻,甚至有可能流变成为令人战栗和恐怖的词汇。“革命”常常成为悬挂在人们心头的一把利剑,既可以杀戮他者,也可能被他者所杀戮。有时候,“革命”只是一个历史和政治的权力游戏,是暴力与智慧、目标与手段、德性与利益等之间的角逐。或者说,有时候,它就是一个最真实也最虚假的符号,一个飘浮不定的能指活动。也许在将来的历史中,“革命”会一次次被唤醒和复活,它的意义一次次地被重新建构,它的目的和功能被一次次地修改,有可能成为更大悲剧的制造者。但愿它回归原初的意义,不再以杀戮生命为手段,不再成为一个包含阴谋和权力目的的恐怖符号。五四运动缔造出新世界的革命神话,以对集体权力或国家权力为目标,在鼓噪革命神话的同时,裹挟着对国家权力和集体权力的渴望。五四运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话语转换,标志着革命者不仅仅渴望单纯的权力模式,而是追求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角逐扩散到对潜在权力和复合权力的激烈争夺。 和革命神话密切相关的一个要素即是:“人民”(people)。因为人民常常是革命运动的主体,也是革命神话的主角。在迄今为止的历史教科书中,“人民”这个语汇都被赋予了神圣意义和被涂抹上崇高色彩,一方面,几乎在所有的革命运动诸如暴动、起义、反抗、斗争、战争、占领、推翻等一系列相关话语都和它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另一方面,人民关联着正义、公平、伟大、公正、合理、真理、仁道、良知等崇高概念。换言之,人民构成历史和政治的宏大叙事,构成国家与民族的神圣而伟大的乌托邦。然而,倘若我们对“人民”这一话语予以深入分析和辨证理性的运思,不难发现,“人民”在政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它构成一个最空洞和最虚假的神话。首先,人民尽管在历史上占据显赫地位,然而它的结构芜杂和内容凌乱,是一个能指不清而所指虚无的词汇。其次,人民这个概念没有严格的逻辑规定性,内涵与外延都极其混乱,是一个没有经历辩证理性和历史理性细致分析的对象,确切地说,“人民”还不能构成一个确定和明晰的对象。再次,人民这一范畴是任意性缀合的结果,是一个缺席理性沉思的假定性观念。在现实世界,既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与之对应,也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属于它的客观存在。因此,就诞生如此的悖论现象: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是人民的范畴。另一方面,几乎任何人都无法代表人民。于是,合乎逻辑的推论就是:人民是一个自相矛盾或悖谬概念,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和历史的吊诡。人民这一概念实质上是政客、阴谋家和理论家对每一个存在者的虚假的情感慰藉。最后,人民属于意识形态的虚构神话,是一个真正的虚假意识的产品。它看起来是精神文化的奢侈品,本质上却是最廉价的工具。总而言之,人民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神话产品之一,是政治和历史领域最虚假的精神欺骗。与此相关,历史上所建构“人民神话”是一个值得存疑的对象。其实,人民的本质并非是一个伟大、正义、良知、公正、真理等话语的象征品,传统形而上学所假定的“人民”,可能是思想暴力和无理性行为的动因之一,可能是制造过失甚至历史罪过的悲剧角色,可能是听信邪恶鼓动和服从于阴谋诡计的盲动洪流。即使从这一虚假概念自身进行运思,人民自身也携带着诸种的历史局限和理性缺失,也未必是道德良知的完美象征,它们更多关注自身的利益和欲望。因此,“人民神话”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都客观地存在并制造意识形态的悲剧,也许在长久和遥远的未来,这一神话依然存在和发挥自己的强力影响。显然,在后现代社会,“人民神话”依然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客观生活。 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是构成传统神话和当代神话的共同要素的话,那么,在当代神话之中,话语权力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它成为当代神话运作之中的潜在要素。从另一方面运思,权力的生成或获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和话语的运作而得以可能。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园。语言不仅是主体的工具性存在,也不仅仅起到传达意义的功能。其实,语言隐藏着对思想的诱惑功能,它寄寓着绑架情感和宰制心理的强大力量。而由语言转化和被提炼过滤后的话语具有更大的潜力和势能。语言是一种神奇的魔法,与其说每一个人都在使用语言和改造语言,都在改造或创造话语,还不如说,每一个人随时随地都会无意识地跌入语言的陷阱,被它诱拐和欺骗。其实,每一个人所说的语言和话语在本质上都属于他者、公共空间和社会集团,很少属于自己,只有极少数人制造语言和创造话语,也只有极少数人操纵和控制着话语权,而绝大多数人只是语言和话语的接受者、使用者。或者说极少数的人是语言和话语的主人,绝大多数人只是语言和话语的奴隶。语言和话语的生产者用它们控制了语言和话语的使用者的思想与行为,就像奴隶主控制奴隶的身体和行为、自由和权力,两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只有存在方式上的差异。因此,当代神话的建构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语言和话语的功能。换言之,权力拥有者借助语言和话语的作用,从而使神话概念成为民众的意识形态。在政治活动中,诸如口号、标语、纲领、语录、宣传册、社论等话语方式,是制造权力神话、政治神话的常用工具。在任何历史阶段,利用语言和话语的策略达到神话生成的目的都是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革命”这一话语在当前社会常常焕发出神话的色彩,成为被国家、民族和大众广泛认同的“革命神话”。从语言哲学的意义来看,不是存在者运用和支配了语言和话语,而是语言和话语支配和操纵了存在者。绝大多数人会被语言和话语所宰制和淹没。极度夸张的语言和话语,它们有时候,就像爆发的汹涌洪水,彻底地淹没芸芸众生。因此,无论在现代社会还是当代社会,民众经常被“革命”话语所鼓动和迷醉。 在许多的革命运动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口号”的登场。口号在本质上是主体的能力欠缺和内心怯弱而需要借助于情绪宣泄的表现。换言之,口号是形式超越内容的伪装符号,是对难以达到的目标和境界的强力呼唤。从整体上考察,绝大多数口号是空洞的许诺和不切实际的期盼,是人类虚荣心的变相宣泄和意志缺乏的间接表现。显然,口号以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方式掩饰自己的虚弱本质。然而,在社会革命和集体、民族、国家、宗教的重大矛盾冲突中,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均不乏口号的踪迹。口号以强调绝对、永恒、无限、理想、彼岸、公正、真理等乔装内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口号是漂浮的能指和完美的所指的游戏,两者总是存在着鸿沟和差异。从性质意义上说,口号既可能表达强力的意志,也可能陈述虚假的愿望。既可能充斥强烈的思想暴力,也可能包含绝对的理想。换言之,口号是人类的虚伪面具之一,也是人类虚荣心的冰山一角,更是虚假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投影。从功能意义上说,口号具有鼓动盲从的客观作用,使生命个体服从某种阴谋诡计,使个体愿望形成群体意志,从而酝酿群体性暴力运动。口号可以迫使人们放弃深刻安宁的生命状态,随着它的循环和重复,主体逐渐丧失理性的思考和精神的安宁,诱发出非理性冲动和情绪冲动。因此,我们必须对口号保持格外的警惕和冷静的反思。口号是神话思维的果实。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以反讽的态度对待口号。 在后现代社会,对于权力的追逐依然是普遍的潮流,因此,权力神话并没有随着消费社会的演进而减弱,反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逻辑的强化而获得新的生成。福柯尖锐地指出:“如果民主意味着由人民有效地行使权力,并不按等级划分成阶级,那么十分明显,我们离此还差得很远。同样十分明显,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专政的制度里,一个通过暴力树立威望的阶级权力的制度里,即使这个暴力工具已成为制度和符合宪法。就某种程度讲,对我们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②从这个意义看,西方的现代社会还不属于福柯理解的民主社会的形式,至少不是比较理想或合理的形式。然而无论东西方,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崇拜依然是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后现代社会的主体首先表现在对政治权力的崇拜,其次才是对其他权力形式的崇拜。社会民众对政治存在着强烈热情,尽管市场经济在表面上使民众对于政治的热情相对减弱,然而,在集体无意识的心理结构中,政治依然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尤其在集权主义社会,民众对政治权力的崇拜甚至超越对宗教的崇拜。绝大多数人是充满政治权力梦想的主体。乔姆斯基在和福柯的对话中以理想主义的方式说: 在采取正确决策时,如果必需在一个集中的权力或一个绝对自由社团间的自由组合中作选择的话,我情愿选择第二个。因为我想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善良的本性。而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一般来说却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最恶劣的本性——贪得无厌、破坏,目的是为自己牟取权力而消灭别人。这种本性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和运作的。我想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这种恶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类恶性被健康本性取而代之。③ 高度的集权社会不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形式,在这种集权社会,主体很容易滋生权力欲望和权力崇拜,产生乔姆斯基所说的“人类恶性”。革命以权力为目的,权力则以革命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于是,革命与权力之间构成相辅相成的逻辑关系。 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权力与革命的交织构成一幅悲剧的历史图景,这也是人类很难获得自我拯救的缘由之一。如果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拯救的理论资源,庄子思想有助于人们消解这种权力意识和政治渴望及其伴随的功利主义诉求,对当代语境中权力神话和革命神话无疑是一剂良药。 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④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吾始也疑子,今视子之鼻间栩栩然,子之用心独奈何?”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将踌躇,方将四顾,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⑤ 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大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⑥ 古代的许由对政治权力表示淡泊的情绪,甚至对最高的王位也表现出无动于衷的冷静和拒绝。相比之下,后现代的人们对权力产生极大的热忱和欢悦,权力一度成为解救困境的唯一良策,因此造成权力神话的泛滥。显然,庄子这一文本潜藏着对于权力欲望的警戒和讽喻的意义,是对权力神话的价值解构。政治上“得志”者而“轩冕在身”,在庄子看来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本末颠倒的人。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对于权力始终保持平常心态。庄子厌倦权力阶层,不愿作为政治的牺牲品,颜渊自甘贫困,孔子给予高度赞赏。褚伯秀注《让王》篇云:“自尧舜、许由、善卷至于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贵累其心,视天下如弊屣者也。子华、颜阖、曾颜、公子牟之徒,葆真守约,不以利禄易其操,视富贵如浮云者也。”⑦淡泊政治权力是古典主义的精神传统,庄子存在着强烈的逃避政治和淡泊权力的思想,这一思想奠定了后世中国文人的“桃花源情结”。古代文人厌倦政治,希冀逃避政治和权力,追求隐逸山水和躬耕田园的恬淡诗意的生活。尽管这一理念难免存在消极人生和政治惰性的成分,然而它保证不同流合污的道德人格,淡化了社会意识形态的权力情结,促使主体滋生审美情怀和诗性精神。与此相比,现当代民众对权力的沉迷和崇拜远远超越古人,使权力神话和革命神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庄子的上述思想可谓是对当代社会的权力神话的嘲讽和批判。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剧场政治”的概念,指出政治往往成为一个精心营造的表演,无论这种表演是否精彩或拙劣,它们都具有天然的虚假成分和包含明确的功利目的,其根本在于对权力的渴望。这也意味着,权力神话和革命神话乃至于所有的政治神话都包含着表演的成分。当今的文化学者作出进一步分析: 政治总是一个表演,因为无论哪一方声称它代表了多少真理,争论的每个参加者都必须表演一个角色,通过这个角色他们才获得了他们的地位。表演或者表演性的概念在文化政治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它强调特定的政治立场——无论是掌权者的立场还是抵抗者的立场——都不得不持续不断地被形成或重塑的方式。⑧ 在后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政治是一个最大和最显赫的舞台。同时,在各种场合,分布着无数的形形色色的政治表演的舞台。不同地位的政客是不同身份的演员,无论他们的演技如何,其本质上都属于政治表演,是“政治演员”。民众既充当观众,也无意识地参与表演,形成表演与观赏之间的“互动”。后现代的政治表演性达到一个历史性的极致,它借助于现代媒体的信息传播手段令这种表演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强制输入每一个主体的感官。后现代社会的政治表演,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人对于政治及其权力的梦想和渴望,它们共同建构了政治神话,使权力神话、革命神话和政治神话密切形成三位一体的有机结构,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和左右着社会生活与民众心理。庄子和柏拉图的思想启迪我们保持对权力情结与政治表演相互关联的理性警惕,抗衡权力神话和革命神话携手对社会意识的侵袭和渗透,告诫人们必须节制对权力的追逐和认识到当代社会的表演性政治运作。 注释: ①奥祖夫:《革命节日》,刘北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6页。 ②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37-238页。 ③福柯:《福柯集》,第256页。 ④《庄子·让王》。 ⑤《庄子·田子方》。 ⑥《庄子·列御寇》。 ⑦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让王》。 ⑧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