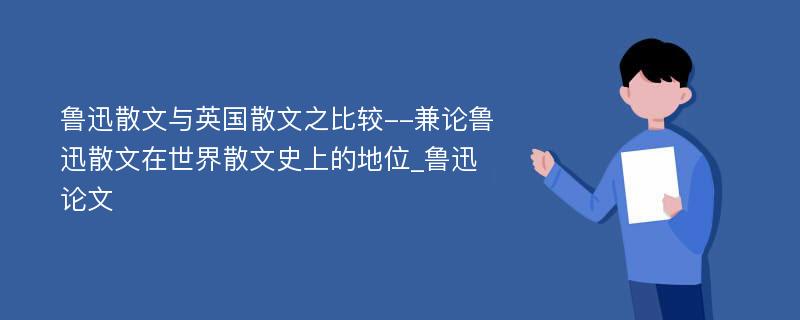
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兼论鲁迅杂文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文论文,英国论文,史上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及其文学地位问题,是鲁迅研究的学术疑难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努力,这个疑难已经有所解决。
但是,考察某种文体的属性与特征时,不能仅限于一个国度或民族的狭窄范围,而应作一次人类学的回归[①],在不同国度的文学比较、文体辨析中寻觅某种文体发生与发展、形成与演变的共性与差异,从文体发生学的人类学根源上阐释、分析某种文体的属性及其文化意味。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疑。
在世界散文史上,中国散文、英国随笔、日本小品堪称三座高峰[②]。特别是英国随笔,世所公认为英国文学的瑰宝,文学殿堂的珍品,文学属性无可置疑。而排除鲁迅杂文文学属性的论者,又多是英国文学造诣颇深、非常推崇英国随笔的人士。如果以英国随笔这一文体出现、发展、形成、演变的历史及其文学属性、艺术特征作为参照系,对鲁迅杂文进行一番比较研究,将会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其论证也会富有无可辨驳的说服力。
当然,鲁迅一再表示过:“英文的随笔小说之流,我是外行,不能知道。”[③]“我不解英文,所以于英文书店,不大知道。”[④]他反对把中国的小品文写成一种英国式的论文体[⑤]。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之间,的确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象梁实秋、林语堂、尤其是梁遇春的散文那样,受到英国随笔的明显影响。因此,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比较研究,应是一种平行比较,不能牵强附会地发掘其中的影响。而这种平行比较,反倒更有益于发现杂文、随笔这一类文体本身所具备的属性、特征及其形成规律。
经过一般性的比较考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和英国随笔,都同样是各自历史时代的文化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由文体,产生的外部条件是政治松动与思想解放的时代环境,报刊等现代传播工具的出现以及广大读者群的需求;内部原因则是随感式的民族思维方式、文体运动的长期积累以及作家个性意识的觉醒。
二
英国随笔引入中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1918年4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谈到国外有不少散文样式值得借鉴,其中包括蒙田和培根开创的随笔。后来,傅斯年在《怎样写白话文》中讨论散文问题时说:“以杂体为限,仅当英文的Essay一流。”最早引进“Essay”这一英文名词,却没有译成相对的中文。1921年6月,周作人首次将“Essay”译为“论文”,在《美文》中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如中国所熟知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时高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也是美文的好手。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周作人这段有名的话很值得琢磨。把“Essay”译为“论文”,对批评的学术性的essay还为合宜,对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就不甚相符了。然而他不仅前边这样说,后边又强调“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意思非常确定。这启悟我们认识到:essay是以“论”为第一特质的,即便是偏重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里面夹杂叙事与抒情,也仍然是以“论”为灵魂的。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突出的是记述的艺术性的essay,把这种文章“称作美文”,而近两年之后,即1923年2月,他在《文艺批评杂话》中又说批评的学术性的论文“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可见周作人不仅开始介绍essay时强调了“论”的特质,而且后来更加扩展了这一观点。以后他在《语丝》上译介的斯威夫特的《婢仆须知》、《育婴刍议》和蔼理斯的《随想录》等,都属于批评的学术性的essay,他本人的文章也大多应划为这一类。
而专攻英国文学的梁遇春、方重、毛如升等人则把“essay”译为“小品文”,并作了长篇大论,概述其发展与演进。胡梦华是将其限定为familiar essay”,译为“絮语散文”,并在1926年3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以此为题的专论。据现任香港翻译中心主任的前伦敦大学教授卜立德先生言,这其实是美国出版的一本《英国随笔》(The English Familiar Essay)引言的节译。不过,胡梦华还是有眼光的,他抄的这篇引言,至今在英国随笔研究论著中仍是第一流的。但是,胡梦华把familiar essay译为“絮语散文”是欠准确的。因为散文在英文中应是prose,是与韵文相对的广义的散文,essay则应是prose当中的一个分支,一个限定更为狭义的散文文体。总之,无论怎样翻译,以上所有研究者在文章中都肯定essay是以论为主的,只是“从来没有根据系统判断事情,总是执着个体来理论”。[⑥]
虽然鲁迅一再表示他对英国随笔是外行,仍然通过日文翻译,对essay作了极为精彩的介绍:“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personalnote)。”这段名言译自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堪称对英国随笔特征作了最为精辟的概括。由于原作本身的精妙,加上鲁迅译笔的生动和他巨大的影响,中国读者简直是通过这段译文了解英国随笔特点的,其印象比其他专门家的长篇大论要深刻得多。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译文中厨川白村对essay译法的见地:“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德川时代的随笔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者炫学家的研究断片那样的东西,不过现今的学徒所谓Arbeit之小者罢了。”因此,鲁迅在后文中把兰姆的《Essays of 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
这里的“杂笔”中的“杂”字极耐人寻味!
这个“杂”字既反映了厨川的日文原意,也渗透了鲁迅对essay的理解。虽然鲁迅自谦“不解英文”,其实还是略知一、二的,从中可以体味出他对essay的理解,认为其中有“杂”的意味。而这个“杂”字,正是英国随笔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之间重要的相通处。
然而“杂笔”一词还是不合历来的习惯。中国古代文体名称中有“随笔”、“杂文”,而无“杂笔”。“随笔”之称始于南宋洪迈,他有《容斋随笔》十卷,清代梁绍壬承其名有《秋雨庵随笔》八卷,俞樾有《春在堂随笔》十五卷,“随笔”之称遂沿用至今,有随笔而录、杂谈琐语的性质,有时也称之为“笔记”。纵然将essay译为“随笔”,有厨川所说的弊端,即往往容易忽略其杂与论的特质,而朝着小机灵、小摆设方面理解,但终归表达了其随意的特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后来大多沿用了“随笔”一说。
无论沿用什么名称,都无法否认essay与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属于相近的文体。仅以英国文坛对英国随笔的界定衡量鲁迅杂文,其文学属性就不言而喻了:鲁迅杂文毫无疑义是符合“以个性化的坦诚态度面对他们的题材和读者”的,是“抱以随便的亲密的态度,关心日常生活的样式和伦理,倾注个人的感情和经验”的,是汲取趣味性、形象性、抒情性等文学性质,主要以理趣体现其文学属性的。这些标准鲁迅杂文不仅完全达到了,而且有很多篇章的文学成分远远超过了这个横竿。以至于使中国学术界在为鲁迅杂文的文学属性作辨解时,制定了一些高难度的标准。
“社会相”类型形象说[⑦]即是其中一例。这一理论确实非常有力地论证了鲁迅一部分杂文的文学成就,并提出了与典型形象有所区别的类型形象概念,对其特征作了详尽的辨析,丰富了文学理论的宝库。但是也留下了理论漏洞,会使人反问道:那些塑造了“社会相”类型形象的鲁迅杂文固然应该进入文学殿堂,而更多的鲁迅杂文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富有趣味地谈论了自己的思想和识见,那么这些篇章是否应该排除在外呢?事实上,倘若以“社会相”类型形象为标准衡量蒙田和英国的随笔,结果就更加不堪了,蒙田随笔朴素自然、耐人寻味,令人感到理趣的魅力,然而并没有什么塑造了“社会相”类型形象的篇章,因为蒙田在“致读者”中就已声明:他所描画的就是他自己。倘若一定要寻找人物形象的话,就是树立了作者的主体形象,作者本人作为一个“人间产物”体现出了人类形态的完整模式。英国随笔中虽然有奥佛伯里的《人物记》和约翰·厄尔的《人物世界》等盛行于17世纪后半叶的人物随笔,兰姆的随笔中也刻画过穷亲戚、扫烟囱的小孩等异常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众生世相作了入木三分的评说,可是以“社会相”类型形象的标准衡量,能达标者也甚寥寥。不仅随笔这一文体如此,其它许多种文体,例如抒情诗、叙事散文等等,也不能以是否塑造了人物形象当作文学属性的检验标准。虽然塑造人物形象、特别是典型形象,是文学创作的重要任务,但是绝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这样做,文学还有其它意义,不能一律化。倘若真以是否塑造了“社会相”类型形象作为能否进入文学殿堂的标准的话,蒙田随笔和大多数英国随笔都要被拒于大门之外了。这当然是其崇拜者们不会答应的。他们会以自己的界定来衡量,以个性化、随意性、趣味性这三把尺子作鉴定,全力维护蒙田和英国随笔的文学属性,绝不会同意将这些引以自豪的世界文学瑰宝拒于门外。不过,这样一来也就自然驳倒了将鲁迅杂文排除在文学殿堂之外的种种说法,因为鲁迅杂文是远远高于西方界定的随笔的文学标准的,当然更不应被排除在外,同样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评说二者的高低,只是力图进行科学的探讨,以共同的标准再次确定这样的观点: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同是一种理论与文学杂交的变体形态与杂糅形式,是人类进入近代、自我意识觉醒时为了自如地表达对自身与世界的理解、自由地互相交流而采取的一种个性化的符号编码方式与随意性的文学写作体例。
三
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的共同性质,决定了二者在文体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共同规律与共同特征。
因为要旨都在于具诚地坦露自己的个性,与读者自由交流,所以必然都反对各种陈套与伪饰,实现语言体式的明白与自然。五四文学革命前期,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鲁迅当然是坚决支持胡适的“八事”的,他的杂文正是最好的实绩之一。有趣的是,在英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反对陈套与伪饰的运动,提出过类似的主张。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们就把18世纪约翰逊、吉朋的风格套式当成了攻击目标。诗人、理论家柯尔律治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这种风格的要素是一种虚假的对仗,即简单声韵的对比,此外则热衷于拟人化,把抽象的变成了有生命的,加上牵强的比喻,奇特的短语,片断的韵文,总之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真正的散文。”[⑧]凡是旨在表达自己真实个性与识见的文学家,无不要求实现语言的纯洁、自然,清除种种的赘疣。鲁迅在总结创作经验时强调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⑨]赫兹里特在《论平易的文体》一文中也这样说:“我从未生造过什么单词,也不曾毫无根据地给哪个单词添加什么新的意义”。“作为一个作家,我竭力使用那些普普通通的字眼和那些家喻户晓的语言结构,正象假如我是一个商贩,我一定使用大家通用的度量衡器具一样。”[⑩]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鲁迅和赫兹里特都是旨在使用世所公认的最平易、自然的符号,以便与他人和社会自如、通畅地交流思想感情。中英两国文学运动中的相同主张之间当然并无任何直接联系,而是人类在以语言文字表达思想感情、进行符号编码活动当中共同的机制和需求所形成的,是文体运动所呈现出的普遍规律。
在这种普遍规律的内在运作之下,鲁迅杂文与英国随笔这两种相近的文体呈现出五点共同特征:闲、随、杂、散、曲。
闲。蒙田和英国随笔家们都爱自称“闲人”,甚至赞美“懒惰”,颂扬“流浪汉”,宛若遗世独立、超然物外的闲云野鹤。蒙田在《自画像》中坦然宣称:“我性爱悠闲,而且十分喜欢无拘无束,我是有心要这样做的。”[11]他的随笔集的宗旨就是“闲话家常,抒写情怀”。[12]而鲁迅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杂文“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特征,又正与此宗旨相通。他们之所以赞美“闲”,实质上是为了挣脱道统和教条的束缚,获得精神的自由与创作的灵气。因为:“人一旦事务缠身,便失其灵性。”(兰姆语)“一个人如果过分用功读书,那就会象老故事里讲的,他就很少有时间思考。”“一走出书斋就跟猫头鹰似的,脸上带一副古板的呆相”,“总显得干巴巴、木呆呆,或者象是害着消化不良症”,没有“闲人”那种智慧,那种幽默和雍容大度的风范。(斯蒂文森语)这一点,与尼采是相通的。尼采就鄙薄学者“愚钝式的勤勉”,靠别人的思想度日,“扼杀一切教养和高尚趣味”,任凭真实的“自我”迷失在刻板而无创造性、“无精神性”的“劳作”中,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他坚决走“自己的路”,宁死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作为真正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向往闲暇,以便自由地从事创造,玩味自己的思想,说出非他不能说出的话,“以谐谈说出真理”,“在十句话中说出旁人在一本书中说出的东西”[13]。人太正经,难于治世。这些大家生性都不太“正经”,因为他们总要冲决种种的奴役和束缚,独创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于事者迷,旁观者清。从俗务琐事的羁绊中超脱出来,拉远距离,从旁观的“闲人”角度冷眼观察周围世态,反倒容易清醒、客观,有利于兑现先祖们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的那句提醒:“认识自我。”中国古代的所谓“懒道人”、“拙叟”、“痴翁”以至老庄禅宗之类,也都与这种“闲人”同源。“闲”,实在是人类智者的共性,写好杂文、随笔的第一要旨。这种“闲人”的素养乃是这种随意性文体的基础和灵魂。
随。既为“闲人”,就必随意。蒙田的随笔,随意挥洒,信马由缰,旁征博引,澎湃无涯。英国随笔家们也是越写越随便,越自如,越得随笔之妙谛。如深谙英国随笔的梁遇春所说:“一个作家抓着头发,皱着眉头,费九牛二虎之力作出来东西,有时倒卖力气不讨好,反不如随随便便懒惰汉的文章之淡妆粗衣那么动人。”[14]因为“随随便便”正是随意性文体的重要特征。鲁迅是非常注意这个特征的。他在《〈自选集〉自序》中自称是“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在《怎么写》中又强调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但是,人们往往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散文这种随意性文体强纳入所谓正轨。中英文学史上都有这种现象。18世纪上半叶,由于艾狄生、斯威夫特等人的努力,英国随笔形成了一种平易、随便的风格。然而到了下半叶,大学问家约翰逊博士却极力把英国散文拉入对仗句、圆周句的套式,追求肃穆,向往堂皇,结果如柯尔律治批评的那样,失去了“真正的散文”。以后浪漫派随笔家们克服了这一弊病,努力发扬随随便便”的风格,按照随意性文体的固有规律写作,使“真正的散文”又回来了。
杂。如前文所述,鲁迅把Essays of Elia译为《伊里亚杂笔》,表现了他对“杂”的钟爱。而这也正与兰姆相合,兰姆极喜爱杂著,视17世纪上半叶的两部奇书——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伯尔顿是一位牧师,他原计划写一部分析治疗忧郁症的医学论著,结果旁征博引、杂收并蓄,写成了一部富有文学趣味、广博知识和深刻哲理的随笔体杂著。布朗是一位医生,有科学知识,又充满诗人的想象,经常冥想死亡与身后的问题,因而也把《一个医生的宗教观》写成了一部奇特的杂著。他的《流俗的谬误》、《瓮葬》、《居鲁士的花园》等其它著作也同样内容驳杂、情调诙谐。这种“杂色”,是随意性自由文体达到很高境界时所呈现出的一种特色。
散。“闲人”随意杂谈的文章,自然会是“散”的。不仅形散,而且神也散。只有神散了,才能自然呈现形态上的散。如果只从形式上求散,神髓却促迫拘谨,放不开,散不来,就只能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钱谷融先生认为散文的“散”字,可以解为散淡的“散”,并以《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作为诠释:“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15]这算是抓住了散文的真义。兰姆佩服的伯尔顿和布朗无意中成了散淡的专家。而兰姆也正发扬了这一优长,于苦涩的微笑中透出别具风味的散淡。由于过去的片面宣传,鲁迅有时给人以横眉立目、剑拔弩张的错觉,其实他的杂文、特别是那些最为优秀的篇章,例如前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等,后期的《病后杂谈》、《我的第一个师父》、《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女吊》等,都透出一种悠远、深沉的散淡美,于不经意中谈出深刻的哲理。与那些离得过近、说得过碎的《华盖集》中的某些篇章相比,要升华多了。徐懋庸在《鲁迅的杂文》中说鲁迅的后期杂文全无“私事”,由“匕首”变为“大炮”,当为中肯之评。散淡,并非不识人间烟火,不问世事,而是站得高远,俯瞰世界,举重若轻,以一当十,有如超脱于云天之上,朝生满荷花的湖面上撒雨,雨点纷纷扬扬滴落于荷池,荷叶上水珠滚滚,漪澜中漩涡点点,构成一种特有的散淡美。
曲。金圣叹有言:“文章之妙,无过曲折。诚得百曲、千曲、万曲,百折、千折、万折之文,我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斯真天天之至乐也。”[16]随意性文体虽然随意、散淡,却绝不可直陋,须在曲折表达方面下刻意的功夫。鲁迅谈自己的写作艰辛时说过:“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17]那么,前面既说随意性文体要随随便便、散淡为之,不要“抓着头发,皱着眉头,费九牛二虎之力”来作,又说要倾以“雕心刻骨的苦心”,此间矛盾该如何解释呢?蒙田早就作过很好的回答,他说他实行的是“人工自然化”,而那些“写得过于微妙,过于做作”的人们“却是搞自然人工化”,“离通常的、自然的用法太远”。[18]这里所说的“人工自然化”与“自然人工化”,揭示了随意性自由文体与矫揉造作文体之间的区别,前者的苦心旨在使文体“自然化”,不留斧凿痕迹;后者却是使原本自然的材料“人工化”,显出造作之气。鲁迅在《汉文学史纲》中论古诗十九首时说:“其词随语成韵,随韵成趣,不假雕琢,而意志自深,风神或近楚《骚》,体式实为独造,诚所谓‘蓄神奇于温厚,寓感怜于和平,意愈浅愈深,词愈近愈远’者也。”这正道出了随意性文体以及所有本色作品“人工自然化”的奥秘,如王安石所言,是“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
四
1931年9月,英国文学专家张若谷先生发表了《鲁迅的〈华盖集〉》一文,第一次从essay、即随笔的文体发展角度评论了鲁迅杂文,用“嬉笑怒骂”概括其风格,“弯弯曲曲”总结其措辞,认为这“代表绍兴师爷派的一种特殊性格”,并分冷嘲、警句、滑稽、感愤这四点赞扬了有些人评价不高的《华盖集》。而全文阐发的核心观点是:“与其当鲁迅先生是小说作家,毋宁说他是随笔作家的更来得恰当。”[19]
该文发表后,反响不大。于是鲁迅逝世近四年以后,即1940年夏季,张若谷先生又在《中美日报》的《集纳》上发表了《写文学随笔》一文,再次重复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结果引起大哗,有人以《活张若谷仍在曲解死鲁迅》为题撰文抨击。巴人在《论鲁迅的杂文》序说中开篇即引录了这两篇文章,认为两文都使他啼笑皆非,都是对鲁迅的曲解。[20]
其实,这是一桩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应予重新评价的公案。张若谷的文章纵然有措辞欠准之处,然而对鲁迅并无恶意,并且从自己具有英国文学素养这一优势地位出发,对鲁迅最突出的成就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当然,鲁迅无疑是一位卓越的小说作家。他是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现代小说从他手中开始又在他手中成熟,他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能列入世界小说名著之林的少数几篇中国现代小说之一,而且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在首位。所塑造的阿Q典型,则可以说是唯一能立于世界文学典型画廊的中国近代文学人物形象。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值得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但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倘若仅以小说作家的身份在世界文坛上排名次,鲁迅自然无法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也不能与巴尔札克比肩,甚至与狄更斯、司汤达、福楼拜、雨果以及短篇小说大家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也都难于相比。一个民族,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伟人,给予恰当的定位,是一件非常艰难而痛苦的事情。人们往往喜欢单纯地从民族感情出发,把本民族的文化伟人定在最高位,使他们在所有领域都坐在首席,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舒心。然而,文学地位是由客观实迹奠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是中国作家,小说又在文学中占有重镇,就把鲁迅列在世界小说大家的一流行列。
实际上,根本不必进行这种比附。鲁迅从最突出的才能特质来看,与其说是小说作家,毋宁说是随笔作家更来得恰当。而且随笔文学对于一个民族的影响并不亚于小说,中华民族文化本来就是以散文为正脉的。
散文作为人类自由表达识见和情感的随意性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股分流:一股是“评他”,即鲁迅所说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触角主要伸向外宇宙,从而延伸为杂文;一股是“述己”,即主要侧重叙说自己的人生体验、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触角主要伸向内宇宙,从而发展为正宗的艺术散文或抒情小品;一股是“诗化”,更多地汲取诗的素质,但又不押韵,保持散文的语言体式,形成为散文诗。当然,这三股分流并不是绝对的,时有相互的交叉与渗透,但是以一股为主。鲁迅不愧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体家,在散文的三股分流中都起到了开创作用,并都创造出了极品:“评他”的杂文,有堪称史诗的十四本杂文集及其补遗在,不必多言;“述己”的艺术散文,有《呐喊·自序》、《朝花夕拾》诸篇和晚年拟题为“夜记”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等焕发着恒久的魅力;“诗化”的散文诗,则一本《野草》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在世界散文史上,有哪一位作家能有鲁迅这样的成就,能对本民族和全人类的灵魂有如此深广的影响呢?
称鲁迅为世界散文史上的第一大家,当是没有疑义的。
注释:
①文体学研究的人类学的回归一说,见于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本文受陶书和童庆炳先生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启发甚大,特此说明并致谢。
②见拙文《季羡林畅谈世界散文》,载《散文世界》1985年第9期。
③《书信·27112致江绍原》。
④《书信·280725致康嗣群》。
⑤增田涉:《忆鲁迅》,见《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第2卷第584页。
⑥《梁遇春散文全编》第56页。
⑦见刘再复:《论鲁迅杂感文学中的“社会相”类型形象》,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⑧转引自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8月版。
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⑩《英国散文选》上册第208页。
[11]《蒙田随笔》第236页,梁宗岱、黄建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
[12]转引自〔英〕P·博克:《蒙田》第20页,孙乃修译,工人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13]见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68、2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
[14]《梁遇春散文全编》第229页。
[15]钱谷融:《真诚自由散淡——〈中国现当代悲情散文精品〉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见《中国古代文论类编》(上)第696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7]转引自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
[18]《蒙田随笔》第298页。
[19] [20]见《汇编》第3卷第268、269页。
标签:鲁迅论文; 随笔论文; 文学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读书论文; 文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