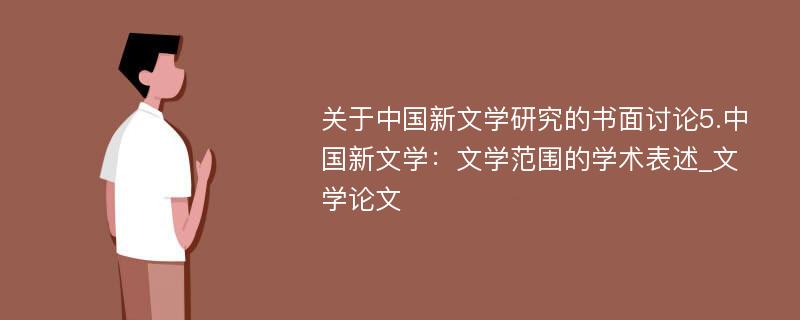
汉语新文学研究笔谈——5.汉语新文学:一种文学范围的学术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汉语论文,笔谈论文,学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次我们讨论的议题有两个,一个是已经提出有年的“汉语新文学”概念,还有一个是新近出版的《汉语新文学通史》。尽管后者是前者的直接衍生物,但我仍然希望讨论的时候将其分开。不过事实上这样很难。参与讨论的各位似乎都不愿花费过多的心思将这两者区别对待,那么我在这里也只能混合起来讨论。
有学者的一个判断我觉得最为准确:“汉语新文学”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设想,我们现在需要编一本书,这本书须考虑将原来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都在新文学传统的意义上统一起来,凝成一体,应该怎样既明确又尽可能简洁地来为之命名?除了“汉语新文学”,我觉得很难有更恰当的题名。也许可以叫作“现代汉语文学”,对此,钱理群先生在2002年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研讨会上提出过,曹万生和黄万华先生都以此题名编撰过有关专书,我自己也曾在2004年撰文肯定过这样的说法[1]。但我觉得这样的指称仍然不及“汉语新文学”。倒不是因为它多出一个字,而是因为,第一,“现代汉语”已经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专用名词和学科名称,我们的学科在人家的稳固名称上黏附一个“文学”的尾巴,好像充任着附庸的角色,感觉不是很顺;第二,如果将其结构解析为“现代”的“汉语文学”,则汉语文学理应包括汉语白话文学和汉语文言文学,这就是说,现代历史时期内产生的文言文作品也须纳入其研究范围,而这样的对象恰恰是“现代汉语文学”所没有准备研究的。显然,“汉语新文学”就避免了这样的歧误和纠结。
“汉语新文学”作为概念的普通性就在于,它不仅不令人费解,而且也不可能导致误解;它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根柢的指称,体现着异乎于传统文学的一脉复杂而清晰的传统;同时它在空间上作了超越各种政治区域、打通其间阻隔的拓展,将新文学的范围扩大到其所能及的最大域限。因此,“汉语新文学”其实就是明确了它最大域限的范围,而不是别出心裁重建文学史的范畴。有朋友对“汉语新文学”质疑: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范畴叫“汉语旧文学”?显然,在五四先驱者那里,“旧文学”固然常常被用来对应“新文学”,但在正式的概念使用上,“中国新文学”对应的乃是“中国文学”,所以,“汉语新文学”对应的其实是“汉语文学”而不是“汉语旧文学”。事实上,“新文学”这个概念经过五四时代和30年代文学家们的琢磨、砥砺、运用、争辩,已经凝结为一种稳固的结构,明确无误地是指用现代语言形态表达现代人思想、经验和感受的文学作品。直至王瑶先生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诞生,文学界一直都更习惯于使用“新文学”这样的固定概念。只是,到了学科体制化以后,出于某种体制化要求,“现代文学”才开始全面取代“新文学”。应当说,在前景仍很漫远的汉语文学发展长途中,用“新文学”标示其独特的传统,标示其与传统文学的质的区别性,可能比“现代文学”更准确,也更趋于稳定(“现代文学”的不稳定性,其实随着“当代文学”概念的出现就已经显露出来,而“当代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具有这样的稳定性)。
“汉语新文学”最大限度地框定了新文学历史形态和现实形态的基本范围,并不是就此选取了一个单一的研究角度。有的学者认为,“汉语新文学”应该从汉语语言发展的节奏和成就方面研究文学史,应该抛却一般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归宿于语言研究。当然,“汉语新文学”可以而且应该——如果有兴趣有能力——从语言学以及其它学术角度迫近其研究,但这样的研究绝对不应视为“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必然要求或应有之义。“汉语新文学”只是从范围上框定了用汉语写的新文学作品以及其组成的文学史现象,至于从什么角度对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那是研究者自己各显神通的选择,也完全可以从最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角度切入,写出的只是在空间范围上比一般文学史更大的文学史而已。诚如讨论中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写一部文学史,那就不是“汉语新文学史”,而是现代文学语言发展史。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目,也是一个很富于挑战性的题目,但不是“汉语新文学”应该承担的学术责任。同样,有学者提出,应该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角度研究汉语新文学,应该提出一个超越于语言的文化的华文文学命题。这样的见解不仅新鲜有力,而且非常尖锐深刻,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学术构想显示出超越于文学研究的胸襟与气派。但是,这种新颖的学术角度与“汉语新文学”同样没有必然的联系,“汉语新文学”的倡导对此恐怕只能作一番兴叹。
之所以强调“汉语新文学”不过是对空间范围的拓展,是因为必须克服那种简单化的思维,以为“汉语新文学”的提倡必然通向对其它既定概念的否定和最终取代。“汉语新文学”仅仅就是一种研究范围的明确,并不是研究规范的重新确立。一个概念最本色的学术责任是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从来就不应该指向“规范”。“汉语新文学”概念与其它已有的相关概念如“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台港澳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现代汉语文学”等等,只是构成比较甚至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构成否定与取代的关系。尽管必须承认自身的某种学术逻辑和语言逻辑上的优越性,但“汉语新文学”没有权利、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建构一种规范性的学术命题,并以此替代任何其它已有的甚至行将出现的相关概念。当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需要有明确的严格的规范意识,“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应该遵守公认的学术规范,同时也不妨针对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调整部分学术规范,但这样的调整仍然在公认合理的学术规范之内,并与其它概念下的规范性学术研究构成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
“汉语新文学”作为概念,不仅并不意味着某种规范,甚至也并不意味着某种标准和性质。有学者建议从普世价值和人的心灵状态的表现研究整个汉语新文学,确实是有价值的建议,但并不能就此确立汉语新文学的标准。汉语新文学不过是一种空间拓展了的范围,它并不意味着任何标准和品质,也就是说,并非只有符合“汉语新文学”范围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不在此范围内的文学都缺少了研究价值。讨论中有学者也曾提出,类似于林语堂等人用英语写作的文学,还有新近一批新移民文学家(如哈金、汤亭亭等)在海外用外文写作的作品问题如何来看。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那里同样存在,没有必要要求“汉语新文学”一定圆满地处理好这些。其实,当这些作家被当作汉语文学家乃至中国文学家进行研究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将他们的外语写作作为研究的必需资料,任何专题性研究都不可能忽略这些文本。目前林语堂的研究成果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一个概念既然其学术功能主要在于明确概念的外延即范围,则范围以外的话题自然就超出了它的学术旨向,“汉语新文学”真正应该负责任的,是被这一概念外延明确包含在内的所有现象,不要受其它如政治、种族等因素的干扰。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外国或别的族裔的作家,他用汉语写作新文学作品而且写得相当有水平,同样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吕进教授较好地处理了对泰国著名华语诗人曾心的学术定位,为汉语新诗的外国群落找到了文学史的相对位置。
《汉语新文学通史》设计了一套不同于任何一部现存文学史的编撰体例,这是我们的亮点,也是我们在“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把握下的一种学术努力与学术自觉。有学者将此纳入“重写文学史”的历史框架,这当然是对我们创新意图的一种充分肯定,但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有些机械。如果说所有有创新意图的文学史专著都在“重写”的框架内,那么这个框架的历史性围墙就被永久地拆除了,以后所有的文学史,要么就是“重写”,不是“重写”的那是什么?难道是“抄写”?有学者认为我们既然有这样的开放条件和思路,大可以打破现有的地域板块,将汉语新文学的历史真正当作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整体。这意见非常精到,学术难度却非常之大,只能作为我们以后努力的目标。就目前而言,我们还不得不就汉语新文学的发展作非常庸常的板块划分,如台湾板块、香港板块、澳门板块、东南亚板块、澳洲板块、美洲板块、欧洲板块等等,一进入文学史的操作立刻就能明白,这样的板块操作虽然不免简单化,但它也实在太管用。尤其是当我们将汉语新文学的发展序列和节奏用“从……到……”加以概括时,离开了板块,我们就会无所适从。尽管我们知道,一部文学史最好能尽量呈现不同板块各个区域不同时段的文学历史的整体,但我们面对的汉语新文学历史,由于不同板块的原因显得是那样地复杂,汉语新文学通史体制又是如此的庞大,以致于我们虽然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有所涉及,可无法做到将各个地区不同板块的文学从头到尾的历史现象全部阐述出来,而只能是选择其中对整个汉语新文学影响最大的现象进行阐述,只能选择该板块在一定时期内对汉语新文学作出最为突出贡献的部分进行分析,而对于其它部分则只能忽略。当然,这样的写法从任何一个板块和区域的文学历史来说,都会余留下以偏概全的缺憾,但如果要避免有闻必录、越写越庞大,也只有发扬这种敢于割舍的精神,尽可能让每个板块最能表现新文学发展显在层面的现象浮出历史的地表,而让其它部分从文学史的阐述中退隐。当然,这样做或许有诸多缺陷,甚至会有一些硬伤。
我非常乐于重申“汉语新文学”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概念,虽然不少学者认为这样的概念和整合的努力反映了当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对于这种趋势的认知,正如我在《“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2]一文中所说,老一辈学者如程千帆先生等早就意识到,程老将他的最后一本文学史著作(与程章灿合著)命名为《程氏汉语文学史》,体现出了对通过国族审视文学史的传统思路和习惯的放弃,这样的放弃是德高望重的学者苦苦思索的结果,也凝结着他进入新的学术思维的痛楚与决绝。老一辈学者的学术经验值得借鉴,汉语新文学的思考和概念把握所体现的学术思索,也许正吻合着老一辈学术反思的路数吧。
同时,“汉语新文学”又是一个带着天然缺陷的概念,这其中一个最为难堪的缺陷,就是它缺乏其它相近似的学术概念所具有的再植能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等都可以再植为不同体裁的延展性概念,如“现代小说”、“当代散文”之类,“汉语新文学”除了在诗歌方面可以延伸为“汉语新诗”外,面对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就失去了这样的概念再植能力。这是因为“新文学”作为概念过于专名化了,以致于很难被拆解开来作为概念再植的材料。不过,这是否也同样说明“新文学”这一核心概念的历史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