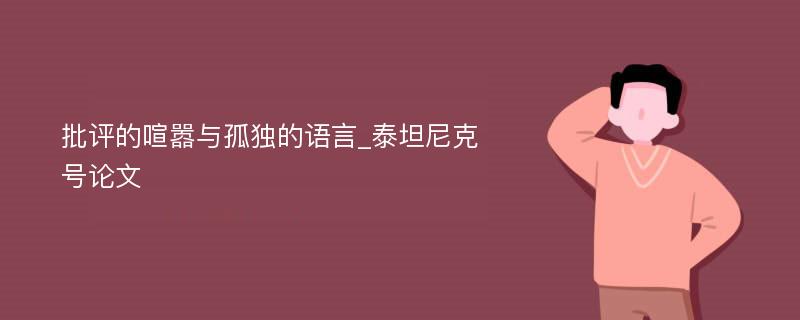
批评的喧哗与独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像罗艺军先生所归纳的,中国电影批评史上有过两个黄金时代,即30年代前期和70年代至80年代末新时期两个时期。出现这两个黄金时代的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出现新的文化思潮;二是电影创作相当繁荣;三是文化环境宽松。
90年代的中国电影批评到底怎么了?98年末,北京电影学院召开了一个有关“电影批评的批评”的研讨会。开这样的会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毕竟很多的批评家已经离开了自己的阵地。尽管如此,首都的电影批评工作者,老中青几代人还是来了不少,批评家,学院教授,报刊编辑,文化学者,影评人,济济一堂,可谓众说纷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整体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更多的是隔靴搔痒,听不见钟老先生那样激越的电影锣鼓声。国片电影市场一片低迷,电影批评几乎成无米之炊,大家在这里发言岂不是自讨无趣。
事实恰恰相反,在今天翻开任何一家娱乐报刊,影评文章比比皆是,众声喧哗,热闹非凡。贺岁片还没有开张,影评就如潮水般涌来。而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更是大小栏目都争着跟电影沾点边。电影专家也走出书斋,开始在大众面前对电影评头论足。有了自由的批评环境,却没有了批评的作品。因为1998年中国故事片产量并不高。专家把电影减产的原因归结为世界性的电影减产和亚洲金融危机。撇开金融危机跟咱们的关系不谈,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电影是否达到跟世界对话的水准,是否具备了国际市场竞争力,都是值得怀疑的。1998年中国电影有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是《泰坦尼克号》驶入中国电影市场,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国营院线几乎是为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创造票房奇迹准备的。当《泰坦尼克号》随风而去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整整三个月,没有美国大片在国内上映。可是也没有出现一部能征服市场的国产片。一度热闹的影院重归冷清。其间,被媒体炒作得有些离谱的电影《红色恋人》倒是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批评、虚假广告和“口碑”的讨论,这样的讨论又连带引发了人们对电影批评的职能和媒体宣传的功能的再认识。至少,在观众眼里,中国电影批评的含金量是大打折扣了。人们把中国电影批评跟注水猪肉联系在了一起。电影批评遭遇的是信任危机。
电影批评的黄金时代的失落,折射的是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失落。很多的年代里,自我封闭的中国电影是在世界之外的。而中国的电影批评则不断地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着自己的面貌,我们很难看清它真实的样子。
尽管如此,由于“电影批评的批评”的批评旨向是电影批评本身,勇敢地对自己开炮,所以它又显示出批评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这样的研讨会是一次面对公众的自我反省,而不是自我辩解,隐隐透出批评所具有的自我完善的诚实天性。
电影批评针对作品,又独立于作品之外。这是起码的共识,又是起码的出发点。
而现在,一切都被颠覆了。或者说被漠视了。
中国电影批评的现状是同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进程紧密联系的。计划经济的强大惯性使中国电影还负载着一定的导向使命。然则,由于整个社会对电影的价值判断越来越趋向一元化,票房和经济效益成了衡量一部影片优劣的绝对杠杆。电影的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被无限扩大,影像自身丰富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家的人文观照由于功利的目的,一概被忽略不计。就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一直没有形成——被视为独立的一个阶层一样,中国的电影批评曾经被动地依附于体制之上,相对缺乏独立判断和基本立场。谁管饭,就给谁干活,强词夺理的背后是随波逐流者的孱弱。电影市场化了,中国的电影批评又迅速地依附于市场。整个国家经济的市场化是历史追逼着我们作出的选择。短视的我们只看到发展带来经济繁荣这有利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的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果我们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丧失,还谈得上持续发展吗?如果电影批评的职能只是刺激观众消费,不让观众有判断力,电影创作的繁荣就永远是雾中的风景。观众像填鸭一样丧失了判断力,意味着电影末日的到来。电影批评将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我们现在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回顾80年代的电影批评高潮时期,虽然多数批评文章集中于专业性较高的理论刊物,还不像今天的电影批评如此密集地散布于整个大众传媒体系之中,但是它曾经和创作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呈现的是互动的关系,而今天,电影批评对创作的影响已经式微了。
尽管电影批评在西方国家甚至决定着一部影片的票房,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简单意义上的促销功能。电影提供的种种感官满足和视听享受,可以让观众“忘了我是谁?”不知不觉认同电影中现存的一切秩序和价值观念。我们看过无数英雄模式的娱乐片,有美国的,香港的,大陆的,在这些影片里,英雄模范人物有着超人的能力,他们鉴照得普通老百姓十分被动和无助。不但使人误以为种种社会问题被化解为少数人的善恶冲突,解决社会问题的秘诀掌握在个人手中,更使人迷信权威和精英的拯救,产生消解社会矛盾的假象。电影批评的功能正是要揭示这些假象,“使人看透这些简单、片面及误导的社会图画,从而提高观众的社会触觉,反省社会的真正关系及追求更加公义平等的价值实现,而不再受蒙骗和支配。”(《电影双周刊》史文达文)当然,电影批评是没有权利阻止公众消费行为的,哪怕他们受到了误导。但是,电影批评完全可以通过对电影中的意识形态的批评,培育公众看电影的能力,促使观众对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有着较为准确的体察和把握。《红西服》里,下岗似乎并不沉重;《非常爱情》跟一个植物人可以爱得感天动地。意识形态的巧妙编码,正是电影的社会功能的展现。道破这两个神话的虚妄,则是电影批评可以办得到的事情。飞越疯人院,不正是我们要做的事吗?总有一些不相信天堂的人。
电影批评应该具有破坏性,刺破所有的虚假;它还应该具有建设性,树立起电影批评的独立品格。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没有自己的理论批评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在研讨会上听见的最让人感动的声音,一家纯学术电影刊物的主编,她尤其提到电影批评应当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因此,今天对电影批评所进行的批评,就显得尤为珍贵和及时了。
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相对主导文化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政治的,商业的)特别浓烈的年代。电影在大众文化里的比重是很小的,可是它在中国仍然是备受重视的。政府推荐八部优秀电影,“五个一工程奖”,都印证了列宁说的“电影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话还有着历史余韵。大众文化的丰富,跟经济发展仍然有着可比的联系,在丰富面前,大众可能无所适从,丧失基本的判断,就像一个自小就面对网络的孩子,他会把那个虚拟的空间误认为现实空间。这就需要职业化的批评家来为社会看守大众文化。批评的现代意义就产生了,它必须拒绝媚俗的喧哗,针对简单丰富选择的表象,揭示其强制性的实质,批评正好给公众提供了多一种选择,有价值的一个人的独语。每个人都可以借此倾听自己说话的语气。每个人的独语汇集在一起,就变成了多个人的独语。于是,尖利的高音喇叭的声音就会减低音量,任何僵死的铁板都会被洞穿。《雍正王朝》轰轰烈烈的上演,解玺璋先生却敢于对该剧是否有着“民间的立场”进行质疑,可惜像解先生这样来自于媒介,却不与媒介合谋的批评家并不多见。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电影批评仍然属于边缘族类。因为这样的声音仍然是比较微弱的。整个传媒体系的批评意识的淡漠,是批评家失去了稳定的接近大众的阵地。
将职业化的批评称之为“媒介批评”,是否科学姑且不论。危险的是某些批评家将媒介批评视为红包批评的保证伞。我掌握着媒体,我是老大,制片商你要卖出去拷贝就得向我行贿;或者我是老板,我有钱,拍了片子,给你红包,你就给我当吹鼓手。他们对电影批评的价值认识就是我通过批评得到好处,至于批评信誉和批评家形象,管它三七二十一,留给历史去评说吧。生命中那无所承受的轻是多么美的事,我才不管电影业景不景气。于是各种各样的新片研讨会议成了红包批评产生的温床。在这个结构重组,经济转型的世纪末,被豢养的批评家们似乎别无选择,要么就饿死,要么就破茧而出,迅速完成角色转换。真是应验了前不久上演的一部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的一段崔健的歌词:“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你要求某些批评家坚持立场是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不符合人性的。
红包批评跟过去唯长官意志是从的喉舌批评并没有质的区别,它们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非此即彼,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生成的“御用”批评家很快就成为市场经济年代的“买办”批评家。我们知道不管是为了制片系统培养的广告运作性批评,还是服务于媒介的娱乐性批评,它们一概都不针对影片的艺术品格和文化意义,前者针对市场回收,后者则几乎都是为了报刊杂志的促销或者电视节目的收视率。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两类批评都不属于真正的电影批评。鉴别了电影批评的真伪,就可以对媒介批评中哪些是属于广告,哪些是属于批评,作出正确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批评被市场和媒介买断的电影批评环境里,你更无法想象从中会诞生法国新浪潮那样推动电影发展的艺术运动。特吕弗、戈达尔、夏布罗尔这些世界级的大导演曾经从事过很长时间的电影批评工作,说起来,大家还不一定相信。中国也有,导演陈国富、陈鲤庭也都是电影批评家出身,这已超出本文议题的范围了。
电影厂、制片商和电影院的宣传体系从电影一诞生起就已存在了,它涉及的是一个大的商业运作系统,这一套宣传体系在讲求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外,怎么运转都无可厚非。因为它不敢轻易冒犯市场。市场是相当无情的,它对商家和经营者的信誉要求极高。它跟一次性的、季节性的跳楼大甩卖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商家失信的市场行为,蒙受伤害的将是整个行业。现在,当整个电影行业在全面向市场转轨的同时,我们除了要强调电影商家的职业信誉以外,更要对电影批评的职能进行一个范围界定。新秩序没建立起来以前,越界的行为是肯定要产生的,大量的批评家加入到宣传的队伍中去,我认为他们不是在做电影批评,而是改了行,重投了主。说批评,道批评,就像郝建先生说的那样,现在最重要的是批评自己批假,不要把广告和批评混在一起。国家不也明文规定政府工作人员禁止经商吗?批评家要转行没关系,可是你千万别当那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托儿”。那样,迟早你会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不仅“托儿”做不了,恐怕连生计都有问题。令人尴尬的是这样的“托儿”已经蠢蠢欲动,四处兴风作浪了。
电影批评需要王海,我们期待的是真批评。真批评需要的是独立的品格,它不容许任何意义上的依附。不管是市场还是权力。真批评的产生需要更多的讲究职业操守的批评家介入媒介,当然还要有一些人留在学院里,他们从事着更接近电影本体和文化学意义上的电影批评。对电影批评的批评进行研讨,其实回归的仍是电影批评。真正的电影批评如何在众声喧哗中坚持自己的独语,是每一个电影批评家面临的难题。
“现实的鞭子终于会打来的,而一个人最要紧的是诚实,就是当无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时候应当从梦里惊醒起来,看清它从哪里来的,并愤怒地勇敢地开始反抗。”半个世纪前,何其芳先生这样说。
喧哗的世纪末,我渴望再度听到你倔强的独语。
标签:泰坦尼克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