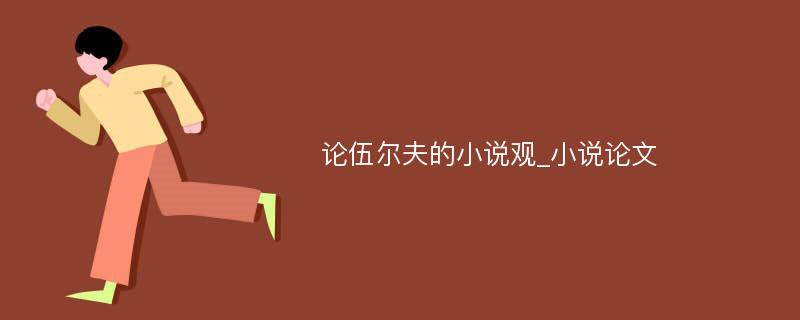
伍尔夫小说观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伍尔夫论文,观补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I56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2146(2000)04—0035—05
说起弗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曾经有过这样一句绝妙的比喻:“她就像一种植物。种植人原来打算让她生长在错落有致的花坛——奥秘的文学花坛——之中,不料她的吸枝长得满地都是,纷纷从花园前车道的碎石缝里冒了出来,甚至还从附近菜园的石板缝里硬钻出来。” [1](P376)这一比喻对伍尔夫的小说理论也适用:她的小说思想散见于 350余篇书评和论文,而且涉及的范围很广,要勾勒其全貌实属不易。我国著名学者瞿世镜先生曾经对伍氏的小说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了系统的概括。他从七个方面归纳了伍氏的理论观点,即时代变迁论、主观真实论、人物中心论、突破传统框子论、论实验主义、论未来小说以及对文学理想的见解。[2](P233-256) 本文拟在瞿先生所作研究的基础上,对伍尔夫小说理论试作更为简明的概括,并对瞿先生的个别定性词提出异议。
一 生活决定论
伍尔夫在《生活与小说家》一文中明确指出,生活是“小说的恰当目的”。[3](P46)这一观点构成了她全部理论的基石。在瞿世镜先生归纳的几大方面中,无论是伍氏的时代变迁论、人物中心论和突破传统框子论,还是她有关真实、实验以及未来小说的论述,其实都取决于她对生活的独到见解。
国内外读者最为熟悉的大概要算伍尔夫的如下论断:“在一九一○年十二月,或者大约在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4](P181) 这一论断也就是瞿世镜先生称作“时代变迁论”的核心。因为人性改变了,或者说时代改变了,所以小说艺术形式也必须随之改变——说穿了也就这么简单。至于伍氏把人性改变的时间定在1910年12月前后的具体原因,瞿先生已经分析得很透彻,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及现代审美观的形成,等等。我们所要补充的是,伍氏的时代变迁论源于她的生活决定论:在她的眼中,生活本来就是变动不居的,而小说体裁的特性又使小说家无法像其他艺术家那样超脱。换言之,小说家比其他艺术家更容易受生活潮流的影响。用伍氏的原话说:“小说家——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危险——必然完全置身于生活之中。其他艺术家至少能部分地引退;他们一连几个星期独自关在屋内,与之陪伴的只有一盘苹果和一套颜料,或是一卷乐谱和一架钢琴。当他们出现在别人面前时,他们往往只是为了暂时忘却自己的艺术,或是为了暂时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然而,小说家永远不会忘却自己的艺术,并且很少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可能会为自己斟满酒、点上烟,也可能会尽情地参与各种餐会和交谈,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感觉,即他的艺术题材无时不刻地刺激着他,作用于他。……他无法停止接受来自周围世界的印象,就像大海中的鱼儿无法阻止水流冲击自己的鳃一样。”[3](P41)由于小说家跟生活的接触最紧密,因此生活对小说家应变能力的要求也就最高。事实上,伍尔夫心目中的时代变迁(包括人性的变迁)并不仅仅发生在1910年,而是发生在所有历史时期,因此小说的不断变革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她在《论现代小说》、 《小说的各个层面》(Phases of Fiction)、 《狭窄的艺术之桥》和《论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等许多文章中都流露了这一观点。仅以她把梅瑞狄斯、奥斯汀和特罗洛普所作的比较为例:她认为奥斯汀和特罗洛普的小说已经达到了完美的状态,而梅瑞狄斯却称不上完美,可是“假如小说一直维持简·奥斯汀和特罗洛普笔下的状况,那么它早就死亡了。因此,作为革新派的梅瑞狄斯值得我们的感激,并能激发我们的兴趣”。[5](P179) 言下之意,小说必须与生活潮流合拍;如果不合拍,即使再完美的形式也会失去生命力,如果合拍了,即使不那么完美的小说也能够唤起我们的敬意。
伍尔夫的突破传统框子论跟她的时代变迁论密切相关。瞿世镜先生已经在这方面作了清楚的梳理。不过,笔者认为,伍氏有关实验主义的论述(瞿先生将其单列为一大方面)可以归入她的突破传统框子论,因为它们毕竟是一回事儿。此外,瞿先生的评述容易使人误以为伍氏的突破传统框子论仅仅适用于乔治时代。事实上,伍氏认为任何时代的“规则只有在不断被打破的情况下才有生命力”。[6](P205) 她在《论现代小说》中确实极力鼓动现代小说家大胆实验,可是她最后得出的结论似乎适用于任何时代:“艺术具有无限可能性……除了虚伪和做作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一种‘方式’,没有一种实验,甚至是最想入非非的实验——是禁忌的。”[7](P13)关于为什么要进行实验,为什么要突破传统,伍氏在《小说的各个层面》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她以司各特为例,指出后者的作品之所以能应运而生,是因为司各特致力于改变当时的一种现象,即不少蹩脚作家打着“叙述真实”的旗号,把敷衍塞责地记录事实等同于小说创作;同时,司各特的浪漫传奇小说本身也隐含着一个危险:“浪漫情调的持续谈何容易……跟普通人的遥远距离以及离奇的成分会变得可笑。”[8] (P110)正是针对这一弱点,狄更斯等人把注意力投向“常人所熟悉的事物的浪漫层面”,[7](P110) 从而实现了新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伍氏主张小说家不断突破旧的传统,但是她同时又强调“变化必须不那么激烈”,[8](P110) 这说明她至少意识到了在继承传统和突破传统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
有关人物的论述构成了伍尔夫小说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瞿世镜先生将其概括为“人物中心论”,这是十分贴切的。除了瞿先生提供的论据之外,[2](P242-245) 至少还有两个例子能说明伍氏把人物放在小说艺术的中心位置。其一,她强调人物是“纷乱的叙述流的支撑点”。[8](P111)其二,她认为“所有小说都保持着一个要素,即人的要素;所有小说都着力刻画人物,这些人物能像真实生活中的人一样,激发我们的情感”。[8](P141)这里,伍氏不仅从小说体裁特性的角度点明了人物的重要性,而且还道出了“人物中心论”的基础——人物的地位和魅力得益于真实生活。这一点可以由伍氏的下列断言得到进一步印证:“小说力图使我们相信它全面、忠实地记录下了真实人物的生活;以此为目标的只有小说这一艺术形式。”[8](P141)
伍尔夫关于未来小说和文学理想的言论其实属于同一个范畴,而且也都以她的生活决定论为依托。鉴于瞿世镜先生已经简明地概括了伍氏对未来小说的预言,即小说将“向综合化、诗化、和戏剧化的方向发展”,[2](P205)笔者仅在此作一小小的补充: 伍氏的理想是小说与诗歌、哲学一起走共同繁荣的道路。在《自己的房间》一书中,伍氏明确提出:“若能跟诗歌和哲学亲密相处,小说的状况将会好得多。”[9]( P164)伍氏的这一主张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她希望小说家能够借鉴诗人和哲学家反映、处理生活的方式。在她看来,传统小说过于偏重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诗人与哲学家却更多地关注与整个人类乃至宇宙之间的关系,然而这两种关系都非常重要。因此,在结合了这两种关系以后,未来的小说将“像一只蜘蛛网,也许只是轻微地粘附着,然而它还是四只脚都粘附于生活之上”。 [2](P255)这样的小说“有能力拔地而起、向上飞升,但它不是一飞冲天、直上霄汉,而是像扫过的旋风一般,螺旋形地上升,同时又和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各种兴趣和癖嗜保持着联系”。[10](P218)可见,伍氏理想中的小说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始终连着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
伍尔夫有关真实的见解可能是她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分。瞿世镜先生曾经把这一部分定性为“主观真实论”,其主要依据包括下面两段话:
“真实”是什么意思?它好像变化无常、捉摸不住;它忽而存在于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忽而存在于路旁的一张报纸上,忽而存在于阳光下的一朵水仙里。它能使屋里的一群人欣然喜悦,又能使人记住很随便的一句话。一个人在星光下步行回家时感到它的压力,它使静默的世界比说话的世界似乎更真实些——可是它又存在于皮卡底里大街人声嘈杂的公共汽车里。有时它又在离我们太远的形体中,使我们不能把握其性质。可是,不论它接触到什么,它都使之固定化、永恒化。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留下的东西。[2](P240)
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因此,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能随心所欲而不是墨守成规,如果他能以个人的感受而不是以因袭的传统作为他工作的依据,那么,就不会有约定俗成的那种情节、喜剧、悲剧、爱情的欢乐或灾难,……[7](P7-8)
诚如瞿先生所说,伍尔夫把人的内心感受和印象放在了十分突出的地位,但是据此推论她鼓吹“主观真实论”却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在伍氏的词典里,主观感受总是和客观经验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在上引第一段论述中,伍氏虽然强调“真实”难以捉摸,但是她毕竟把寻求的目光投向了活生生的客观世界,投向了尘土飞扬的道路、阳光下的水仙以及嘈杂的公共汽车。确实,伍氏之为“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剩下的东西”,可是恐怕先要有那外皮,才能养成“内心火焰的闪光”吧?[11](P89)同样, 上引第二段虽然通篇强调倏忽即逝的印象,但是这些印象实在是客观世界作用于主观世界的结果——用伍氏自己的话说,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通的一天中”生活的结果。不错,伍氏曾经猛烈抨击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三位小说家,指责他们“不关心心灵,只关心身躯”,并贬之为“物质主义者”。[11](P87)然而,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审视一下伍氏的理论,我们会发现她是非常重视客观经验的。《妇女和小说》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有力的凭证:“客观经验对小说起着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是不容争辩的。譬如,假使康拉德当初没当成水手,那么他的小说中的精华部分就会遭到毁坏。托尔斯泰当过兵,亲身经历过战争;他还是富家子弟,受过良好的教育,因而有条件体验各种生活,品尝各种社会经历;假如没有这些经验,《战争与和平》就会大为逊色。”[12](P79)在《自己的房间》一书中, 伍氏也曾下过类似的结论:“假如当初托尔斯泰是生活在修道院里……我想他几乎写不成《战争与和平》。”[9](P106)当然, 伍氏并不主张把实际生活原封不动地搬入小说,而是热衷于实际经验和主观意识的相互作用。不过,以上分析至少已经表明,“主观真实论”这样的定性词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误以为伍氏单纯地把主观和真实等量齐观,而实际上她的真实论深深地扎根于实际生活的土壤。
二 生活决定论的扩展
伍尔夫深得小说艺术三味,并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见解。仔细考察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些表述大都源于她的生活观,或者说是她那生活决定论的扩展和延伸。
小说艺术,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写作的问题。对伍尔夫来说,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解决为何写作以及为谁写作的问题。如前文所示,伍尔夫把生活视为小说的恰当目的,而她所说的“生活”不仅包括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且包括社会的客观存在。更确切地说,伍氏最为关心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和生存状况。她曾经批评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缺乏品位,其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后者“不去尝试解决人类生活的问题”。[13](P156)那么,小说怎样才能有助于解决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呢?伍氏认为小说家至少应该像艾米莉·勃朗特那样,向世人“暗示潜伏于人类本性的幻象之下、并能把这些幻象升华到崇高境界的力量”。[13](P159)夏洛蒂和艾米莉同样面对着一个四分五裂、混乱不堪、充满痛苦的世界,可是前者只知道倾诉“我爱”、“我恨”、“我痛苦”,而后者倾诉的则是“我们,整个人类”——正是这一点使伍氏对艾米莉推崇备至。[13](P158-159)同样受到她推崇的是奥斯汀,因为后者“精微细致地区分了人类的价值观”,[14](P138)并且“以完美无暇的心灵、始终如一的高尚趣味和近乎严峻的道德观为准则,揭露了那些背离仁慈、忠诚和真挚的思想和言行”。[14](P140)由此可见,伍氏所谓的“为生活写作”也就是为人类的教化而写作。
为何写作在很大程度也是一个为谁写作的问题。伍尔夫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懂得为谁写作也就是懂得怎样写作。”[15](P207)她还提出,读者的定位是“作者的试金石之一”。[15](P207)那么,小说家究竟应该为什么样的读者写作呢?伍尔夫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民主立场:应该为普通大众而写作!她认为塞缪尔·巴特勒、乔治·梅瑞狄斯和亨利·詹姆斯的不足之处就在于缺乏对普通读者的正确态度:“他们个个鄙视大众,却又渴望得到大众,结果还是失去了大众;他们个个把一连串生硬、艰涩和做作的文字强加在大众头上,而且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凡是平等对待读者、把他们当作朋友的作者都不会忍心这样折磨大众。”[15](P206)伍氏的这一观点至今仍然有助于解释那些实验作家昙花一现的原因:标新立异者都想吸引读者,可是他们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在心头作怪,到头来只能远离生活,远离普通读者群。把读者当作朋友,跟他们平等相处,这不仅是伍氏对同时代小说家的忠告,而且也是她对所有后世小说家的忠告。
虽然伍尔夫认为懂得为谁写作就是懂得如何写作,但是她就具体的写作方法还是发表了许多见解,其中包括素材的取舍、人物的塑造、场景的安排、情感的处理、作者与人物的距离,等等。限于篇幅,以下讨论围绕其中两个最重要的话题,即素材的取舍和人物的塑造。
前文提到,伍尔夫认为小说家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与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不过,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取材和写作过程,伍尔夫则要求小说家进退平衡,取舍有度,对生活保持既投入、又超脱的态度:小说家“必须投入生活,必须甘冒受她误导或欺骗的危险,必须从她那里夺取宝藏,同时又不为她的糟粕所动。在某个时刻,他还必须抽身隐退”。 [3](P47)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生活的糟粕”一说。 伍氏虽然强调生活是小说的恰当目的,甚至断言小说家“观察到的生活越多,捕捉到的生活越多,他写的书也就越出色”,[3](P46)但是她还看到了另外一面:“生活太不纯洁;她最炫耀的那一面常常对小说家毫无价值。” [3](P46) 为了避免被生活中的一些假象所迷惑,小说家需要有良好的大局观,而大局观的获得又取决于跟生活的距离,所以伍氏主张小说家“站在从生活退后一步的地方写作”。[15](P22)更为重要的是, 生活不仅要求小说家剔除糟粕,而且要求他们舍得割爱。在她的眼里,艺术的桥梁格外狭窄,只有善于割弃的小说家才能通过:“你不可能拎着所有的工具去穿越那座狭窄的艺术之桥。有些东西你必须留下,否则你只能在中途把它们扔入水中,或者情形会更糟:你会失去平衡,掉入水中淹死。”[16](P22)伍氏清楚地看到,丢弃某些艺术手段和工具, 或者说丢弃某些文字,并不意味着丢弃作家想要表达的意思。惜墨如金的原则和洗练的笔法往往会产生以少胜多的效果,所以伍氏明确指出:“作家的任务是汲取某事物,然后让它以一当廿。”[3](P45)她对梅瑞狄斯笔下的茶会有过一段评论,正好被用来说明上述观点:
假如他必须描绘一个茶会,她的第一步会是摧毁——凡是座椅、茶几和杯子等所有容易让人辨认出茶会的东西会被一概摧毁。他会仅仅用手指上的一只戒子和经过窗口的一根羽毛来代表整个场景。就在那只戒子和那根羽毛里面,他注入了强烈的激情和非凡的品格;就在那本来会显得空荡荡的房间里,洒满了他那明察秋毫的想象之光,以致我们仿佛占有了茶会的每一个细节,好像某个不辞辛劳的现实主义作家逐一描述了所有的细节一般。[17](P50)
这段话不仅生动地说明了伍氏“以一当廿”的意思,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她的生活观和真实观的客观基础:尽管她认为小说的想象之光可以取代众多的细节描写,但是这主观的想象毕竟要以客观的事实作铺垫——小说家只有在对大量的生活细节精心观察以后,才能“摧毁”并重组这些细节,然后才能迸发出想象之光。伍氏的下面这句话说得更明白:“(梅瑞狄斯)最出色的词语不仅仅是词语,而是浓缩了不同观察物的复合体;这些观察物被熔于一炉,迸发出一道明亮的闪光。”[17](P50)总之,观察、摧毁和重组,这是伍氏心目中理想作家的必由之路。用她自己的话说:“这将是小说艺术发展的道路。”[17](P50-51)
伍尔夫对人物刻画的关心不亚于她对素材取舍的重视。应该说,素材的取舍和人物的塑造是部分重合的两个话题——从生活汲取的素材也应该包括人物的素材。因此,上文所说的“惜墨如金”这一原则很自然地被伍氏用来衡量人物刻画的成功与否。例如,她对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是这样评价的:“他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产生出来,完全听凭他那只慧眼的召唤——他的目光只要向某个房间投去一瞥,就能把那里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目光只要攫取了某个妇人的钢制发夹、一双眼圈红红的眼睛、一个发白的疮疤,就能使它们揭示某个人物的本质。”[6]( P112)伍氏这里实际上是在敦促小说家们把神韵放在比形似更重要的地位。不过,虽然她提倡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特征,但是她并不提倡把人物简单化——光有一个或几个深刻的特征还远远不够。她在奥斯汀和托尔斯泰的笔下找到了最理想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有着上百万个侧面”。[13](P156)她还认为,这些人物构成“一个可供我们访问的独立世界”。[12](P156)那么,如此复杂的人物又是怎样锻造而成的呢?伍氏曾经给过一个简明的答案:“只有在小说是一座深深的思想库和情感库时,性格微妙而复杂的人物才能被创造出来。”[6](P129) 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伍氏的意思:小说家本人首先必须是一座积蓄了丰富情感和思想的水库,否则就无法孕育出人物性格的大千世界;更重要的是,这座水库的源头只能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中找到。
如上所述,尽管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呈现出五光十色,然而我们一旦抓住了生活决定论这条主要脉络,就能顺藤摸瓜,理出头绪。
收稿日期:2000—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