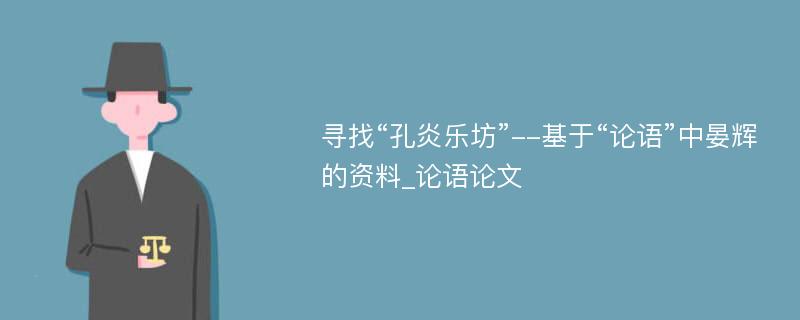
再寻“孔颜乐处”——以《论语》中有关颜回的资料为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背景论文,资料论文,再寻论文,颜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孔门弟子,颜回在《论语》中并不是着墨最多的一个,但他却是《论语》记述中受到孔子称赞最多的一个。《论语》中所记述的颜回受赞赏的品质,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不愚”,二是“好学”,三是“不改其乐”。
首先看“不愚”:
2.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5.9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
11.4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
可以看到,“好学生”的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本身资质的问题。并非说资质不好者不能成其为“好学生”,但是要做到令被尊为圣人的孔子赞赏,没有十二分的聪明绝对不行。颜回之资质,说“不愚”,其实只是最谦虚的说法,而事实上绝不仅仅是“不愚”那么简单,从他的“闻一知十”和“于吾言无所不说”可以看出。表面上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似乎有怪回之意,而其实也从另一方面看出孔子对回之盛赞:能够对他的教导“闻言即解”,并且能够举一知十,实在并非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且“闻一知十”的本领,连孔子也自愧不如(如果我们将孔子的“吾与女弗如也”之“与”字看成是“和”而不理会它可能有其它解释,并且不理会孔子可能在安慰子贡的话)。
其次看“好学”:
6.3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11.7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
9.20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罕》)
“不愚”当然是成为“好学生”最基本的条件,但是,天生的资质并不能代替后天的品质,再聪颖的人,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根本不能有所成就,更何况对于老师来说,对愚而勤奋的学生的爱惜,总会多于对聪明而不努力的学生的欣赏。孔子也不例外,或者说,作为“先师”,这种传统就是由孔子而来的。当被问及“弟子孰为好学”时,孔子总是首推颜回,且认为除回之外,再无一人能称得上“好学”。对“好学”的欣赏,可能源自于孔子对自身的评价:
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资质乃天生,不能选择。好学则是一种品质,可以培养。孔子对“好学”的欣赏,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好学,而是与其学的内容紧密联系的。在孔子心目中,继承、传播传统的礼仪是最重要的使命,而继承与传播首先要靠“学”,学则首先要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所以这里面,所好与所学是有特定内容的。
最后看“不改其乐”:
6.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6.7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雍也》)
11.3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学”之能否坚持,关键在于,个体是否投入,是否能以之为“乐”。颜回的这种“乐”的体验,也正是孔子之“乐”的体验:
7.16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这两处“乐”的提出,都源自于相似的生活环境,都涉及到一般人所关注的生活的贫富问题。于是,孔颜在“陋巷”、在“饭疏食饮水”中所体验的“乐”到底何指?自宋明以来,寻“孔颜乐处”成了解释者孜孜以求的任务,由此可见,在解释者看来,“乐”并不是一个关乎生活质量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般的心理感受那么简单。之所以引后面的两章在“不改其乐”标题之下,是因为有一点可以肯定:“乐”与仁、与德行有着某种联系。所“乐”者何?“乐”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与“礼”与“仁”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上面的论述,在尽量避免引用历代注疏的情况下进行,所以不免失之简单。此部分讨论“孔颜之乐”,首先需要说明本节讨论的主旨。将颜回纳入观察的视野,是因为颜回与孔子独特的关系。孔子称赞颜回,并不仅是因为颜回本身具有的常人难能的品质,更是因为颜回与孔子在品质上的相似与在追求上的一致。历代注者对孔子与颜回的关系多有探讨,往往将孔颜并提。从宋明理学开始寻“孔颜乐处”,再有钱穆称回“最为孔子所深爱”(注: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2002年,第35页。),并提出“志孔颜之志,学孔颜之学”(注:钱穆:《论语新解》,第136页。)。而程度最深的则是康有为,他说到:“孔门多弟子,而孔子所心心相印者惟颜子一人”(注: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又提到:“颜子与圣人契合无间,相视莫逆,合为一体,孔子深喜之……”(注:康有为:《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第160页。)这就已经不仅是相似的问题,而是合而为一了。颜回是《论语》中的一个点,是反映孔子思想,或者说,最能反映孔子的一个点。所以,我们今天不妨从这一点切入,再寻“孔颜乐处”。
二、孔颜之“学”的内容
其所“乐”,必体现在其所“好”之中。孔颜之共同所好,则为“学”也:
6.3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5.28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好学”作为颜子在众多弟子中独有的品质而受到孔子的称赞,而孔子也自称“好学”。颜子之“学”与孔子之“学”的内容是什么呢?贰者是否一致?首先要说的是,从主观猜测上看,作为师徒,弟子之所学应与师长之所传授一致。而具体之分析,则可看历代注者之解释。在6.3章孔子回答哀公的提问而说颜回好学时,提到的是“不迁怒,不贰过”。孔子特举此贰者来说明好学,意图何在?在众多注释中,除皇侃从哀公本身的原因出发,认为“当时哀公滥怒二过,欲因答寄箴者也”,(注: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第367、369页。)其余的,或者将重点放在“不迁怒、不贰过”的原因探讨上,如何晏、程颐;或者直指好学的内容,且皆认为孔子称颜子“好学”是指其“学为人”言,如程树德认为,“问好学而答以不迁怒不贰过,则古人所谓学,凡切身之用皆是也。古人之学,在学为人,今人之学,在求知识”(注: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7年,第367、369页。)。钱穆也认为,“可见孔门之学,主要在何以修心,何以为人,此为学的。”(注:钱穆:《论语新解》,第141页。)而在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一章,朱子注为:“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6页。)由此可见,学者对孔颜之学的内容并无分歧,孔颜之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的学习,而是学而为“人”,且其最终目的,是成为具有至上品德的“圣人”。这也正合了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为己即是为自己的修养德行,为自己成圣的目标。
三、孔颜之“学”之过程
然而,“乐”之体现,必定不在学之“目标”上。因为目标是一定的,是静态的,也是尚未达到的;而“乐”则是动态的,它必定发生、体现于一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因此,寻孔颜“乐”之所在,应该到“学”之过程中寻找:
9.11颜回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博文约礼”一章,是颜回对孔子之教的描述。圣人之道之高深难学,在此可见一斑。也因为此一描述,程子认为“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可见这一章确可体现孔子之教与颜子之学的内容。对“博文约礼”的理解,大部分学者同意“以文章开博我,又以礼节节约我”的解法,如孔安国、钱穆、李泽厚等。朱子引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0页。)这一解法明显异于别人,这就引出了“克己复礼”的解释问题。
“克己复礼为仁”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章节,是讨论“礼”与“仁”不可能绕过的部分。对这一句的解释,成为历代解释者争论的焦点,甚至成为学术史上的公案。问题的引起直接与程朱理学有关,朱子对“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解,几乎成为理学一派之外历代学者的众矢之的。朱子解道:“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盖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55页。)这里所使用的“人欲”、“天理”等最具理学特色的术语,成了后代学者批评的对象(当然也有追随者,如康有为)。程树德认为,朱子解经“先有成见”,“硬将天理与人欲四字塞入其内,便失圣人立言之旨”(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819页。)。赵纪彬更是从其根源上来批评宋儒,认为“唯心主义的‘气质性恶’说,乃程朱‘理学’一派释‘克己’为‘克去私欲’,并进而曲解孔丘关于‘仁’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注:赵纪彬:《论语新探》,第315页。)。李泽厚也在其《论语今读》中多处批评程朱将“七情六欲”与心性修养相对立。(注: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47、150、275页。)“天理”自然是程朱理学一个至高的追求,而人欲,更是理学中要处处克制的方面。但是,将“己”与“己私”、与“人欲”等同,特别将“己私”与“人欲”看成罪大恶极,这也是理学受批评的地方。且如将“己”解为一己私欲,那么“为仁由己”之己字又该作何解?孔子称“古之学者为己”岂不是纵容私欲?事实上,“人欲”是人与生俱来的、在人之所以为人中最自然的部分。在孔子思想中,如果“克己复礼”成了对人欲的克制,对最自然的天性的反叛,那么必然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那么这必然不是人之真正所“好”,也必然不能让人真正从中获得“乐”,除非是有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在里面。然而,对“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怎么理解,对“孔颜之乐”如何理解,在后来的解释中,确实开出了一种援入佛老,追求神秘体验的面向。
语言洗练,问答皆依于特定背景,不离事言理,这是《论语》的言述风格。然而,正是因为其修身的途径过于具体,其使用的概念又过于含混,对于具体之外的一些问题就显得无法解决。如李泽厚所说的,“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克己复礼’(有关行为)为什么是‘仁’(有关心理)?”(注: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47、150、275页。)而自佛学传入之后,援引佛老解《论语》更成了一种趋势。如对“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的解释,皇侃引孙绰云:“8圣人德合于天地,用契于四时,不自昏于圣明,不独曜于幽夜。颜齐其度,故动止无违,所以影附日夜,绝尘于游赐也”。(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450页。)不过是一句“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却能引出这么飘然欲仙的感觉,可见注者受佛学影响之深。又如康有为注“回也不改其乐”一章,“盖神明别有所悦,故体魄不足为累,境遇不能相牵,无入而不自得也。佛氏所谓,地狱天宫皆成佛土,其类此乎?”(注:康有为:《论语注》,第76页。)这里更直接引佛学相对照,且“神明、魂魄”等词在康有为的《论语注》中并不少见。再如李泽厚之解《论语》,也常有诸如“神秘”、“准宗教”等词出现。如对颜回“不违,如愚”,李就认为,“颜回在《论语》中的形象总是这样愚、‘默’、神秘”(注: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对“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中之“仁”的理解,他认为“‘仁’在这里似可指是某种具有神秘性的人生最高心理状态”(注:李泽厚:《论语今读》,第150页。)。可见,无论是否受佛老影响,由于《论语》的语言及其表述的特点,对《论语》中各种概念与己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总是有一部分人会产生神秘化的倾向。但是关键在于,神秘化之后是否就能解决问题?
这种神秘化倾向从一开始就受到批评,批评者试图将其扭转回伦常日用之中。如对“博文约礼”一章的注释,黄斡《论语注义问答通释》讲到:“颜子之见,固非后学所可窥测。然以其不可窥测也,故言之者往往流于恍惚无所据依之地。敢于为言者反借佛老之说以议圣人。其不敢者,则委之于虚无不可测论之域。……夫圣人之道,固高明广大不可几及,然亦不过情性之间,动容之际,饮食起居交际应酬之务,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常,出处去就辞受取舍,以至政事设施之间,无非道之寓。”(注: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97页。)钱穆对此章的理解,几乎照搬以上论述,可见他也应归入“伦常日用”一派。“伦常日用”派最大的特点是,将人的能动性与参与性最大程度地体现出来。学的内容为“礼”,而这种“礼”是关于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的,学的过程又是日常的生活化的过程:这就使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个动态的“礼”与“乐”的过程。如钱穆对于“约礼”与“克己复礼”之理解,“约礼”之“礼”,钱认为指“人生实践”(注:钱穆:《论语新解》,第231页。),而“克己复礼”之“复”,钱则理解为“践行”(注:钱穆:《论语新解》,第302页。),这就比单纯理解“礼”为“礼制”,理解“复”为“归”要生动得多,人的行为、人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值得一提的是,赵纪彬经过仔细训诂,认为“克己复礼”之“克”字应训为“能”(注:赵纪彬:《论语新探》,第304-305页。),“能己复礼”虽然不通,但是如果依照杜维明先生在“什么是经典”研讨会(注:“什么是经典”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2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举行。)
上的说法,改为“己能复礼”,那么人的主体性在其中也可以得到体现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礼”是礼制,更是对礼制的践行。那么“仁”呢?“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礼”与“仁”的关系到底如何?“乐”与“礼仁”的关系又应如何?钱穆认为,“仁存于心,礼见之行,必内外心行合一始成道,故《论语》常仁礼并言。”(注:钱穆:《论语新解》,第232页。)“仁存于心”,一谈到“心”,问题又来了。“克己复礼”为什么会是“仁”,“行为如何是心理”,这是上面提到的李泽厚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说出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确实认为,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的说法是更为合理的,在其《孔子:即凡而圣》一书中,对“礼”与“仁”有详细的论述。
正如书名中的“凡”与“圣”二字所提示的,如果我们套用前面的“神秘派”与“伦常日用”派的分法,应该说,在芬格莱特这里,此二者并不是截然二分的。首先他认为,“孔子恰恰在本质上是反对神秘的(antimagical)”,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引入神秘之说法,“但是我们还是发现《论语》中偶尔有些言论,似乎透显出对那种具有深远意义的神奇魅力的力量(magical powers)的信念。我所谓的‘神奇魅力’(magic),是指一个具体的人通过礼仪(ritual)、姿态(gesture)和咒语(incantation),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自然无为的直接实现他的意志。”(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实际上,从他著作的进一步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导致他产生这一论断的是这样的问题:如何理解“仁”这个在他看来笼罩着吊诡和神秘色彩的概念?如何理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在西方心理学的强势背景下,他花了很大功夫说明“仁”不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最后,他在“仁”与“礼”的关系中找到了理解“仁”的最合适的途径:“‘礼’和‘仁’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各自指向在其担当的独特的人际角色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某一个方面。”(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42-43页。)芬格莱特接下来所论述的一大段关于“礼”和“仁”的关系,可以大致分析如下:首先,“礼”是一种来自于传统的、既有的社会模式,而“仁”则指那些因追循这一社会模式而产生影响的人;其次,“礼”是一种合乎个体身份地位的行为(这与钱穆认为“礼”是“社会实践”是一致的),而“仁”则是个体对这种行为的意向:表明人愿意学习、实施“礼”;最后,“礼”是固定的、有序的行为模式,而“仁”则将学习者、施行者的独特性、个体性带入到“礼”之中,也可以说,因为“仁”,因为人的加入,使“礼”的学习与使用有了与这个人相关的个体特征。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礼”主要与具体的礼制相关,而“仁”则主要与人相关。在“礼”同时作为行为的层面上,“礼”与“仁”开始结合,形成互动。这一结合的成功与否,与主体的决定有关。这一概括可以与芬格莱特后面对于“仁”的其它说法相印证:“‘仁’其实就是一个人决定遵从‘礼’”,“‘仁’就是一种关怀的形式。……‘仁’的关怀就是‘是否你有志于仁’”。(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51、53页。)如果我们撇开关于孔子哲学思想中“礼”与“仁”二者哪个更根本的问题不谈,可以说,这种对“礼”与“仁”之关系的理解,优点在于,将“礼”与“仁”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将个体生活注入到“礼”之学习与践履之中,不离“礼”谈“仁”,也不离“仁”谈“礼”,二者融合无间。而“仁”在这里所获得的意义,不仅是对一种人之状态的描述,而且也是充分体现“人”之为“人”的一个概念。正如芬格莱特在另一处所说的:“美观而有效的礼仪要求行为者个体的‘临在’与所学礼仪技巧的融合无间。”(注: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第8页。)礼仪之美观与有效是与个体之“临在”分不开的,那么,回到我们最初想探讨的问题:乐呢?孔颜之乐又在哪里?
四、孔颜乐处之所在
以前面对“礼”与“仁”的讨论为背景,寻孔颜因何而乐、所乐者何已是水到渠成。
7.16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6.11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
上面的两章,其情境大致相同,都是指粗衣淡饭,生活的贫困不能改变孔颜之乐。为什么呢?朱子认为:“乐亦在其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如气壮之人,遇热不畏,遇寒亦不畏,若气虚者则必为所动矣。”(注:《朱子语类》,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468页。)这里可以确定的是,“乐”绝不是因为生活的贫富,而是存在于其它地方。在什么地方呢?李泽厚曾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认为“乐”在中国哲学中实际具有本体的意义,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成果和表现。(注:详见李泽厚《试谈中国的智慧》,收入《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这里将“乐”提升为本体,实际上是以今人的知识与眼光来看古人的“乐”,而如何以古人的实践、从古人的角度出发来体会“乐”则仍无具体之解释。庞朴先生引入徐复观之“忧患意识”,在为徐复观与李泽厚的“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作圆融之努力时,自然会将“乐”与“忧”合起来讲,所谓“即忧即乐,化忧为乐”。(注:详见庞朴《忧乐圆融》,收入《一分为三》,海天出版社,1995年。)这是从古代儒士的社会责任感来讲“乐”,当然,确实是引发“乐”的原因。但是,如果仅从社会责任心来讲“乐”,那么,“乐”还不是最纯粹的“乐”,不是达到最高层次的“乐”。只有当“乐”成为个体由行动到内心、由强迫到自觉的感受时,才算达到了圣人的最纯粹、最高的境界。
而我们在这里想阐明的,是希望还原回古人的生活情境中,从孔颜的日常生活,从个体最生动而自然的角度,去看“乐”如何实现。
以常识的理解,一个人的“乐”,当然与此人的人生追求相关。而在人生之追求尚未达到时,则与其追求之过程相关。依上文的分析,孔颜之追求,在“学为圣人”,学之过程,则在“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中。钱穆认为,“克己复礼”一章是寻孔颜乐处之需切实下工夫处。(注:钱穆:《论语新解》,第304页。)也就是说,应在“克已复礼为仁”中体会孔颜之乐。而这种体会,依钱穆的理解,是要在切身践行礼的过程中才能体味得到的。虽然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十分难学难能。然而,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将“人”的主动因素加入进去,能将个体生命融合其中,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呢?芬格莱特对“礼”与“仁”的理解提醒我们,在“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人”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静态的人,“仁”也不是一种静止的心理状态。恰恰相反,“仁”使人的主动性得以彰显,并赋予“礼”以个性特征。“礼”与“仁”的这种结合,使圣人之学完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自然而不造作、不扭曲,追求理想的过程也是理想实现的过程,既是学的过程,也是用的过程,融人的生命情趣、价值追求于一体,并可以在其中体验“尽善尽美”的境界:还用寻吗?乐已在其中!
这种“乐”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最为人性化的“乐”,是能在最平常的生活中体验到的“乐”,也是一种最生动的“乐”。其人性化,体现于对种种人伦关系的重视;其平常,则体现于日常生活言行举止;其生动,体现于个体的投入与独特性之彰显。它是在将人情、人性与道德、礼仪实践完美结合之后所产生的体验,而并非程朱抑制人情所能拥有的。儒家追求“天人合一”,所以,并不能因偏重天而废人。相反的是,在“合一”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人”。而“人”就是“己”,“己”就是完全的、丰满的人,而并非“己私”。李泽厚认为,“‘孔颜乐处’固然指‘天人之乐’,……但并不贬低或排斥‘七情之正’的世俗之乐……”所以,孔颜之乐是一种最简单而自然,既善而又美的感受。
而“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是一种准宗教的、神秘性的体验吗?当我们谈论情感体验时,因为这种体验往往不能明确定义、不能传递,所以,在此意义上说,情感体验都是神秘的、准宗教的。这样一来,所有的情感体验岂不是都不能分别?因此,一种体验之神秘与否需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从获得该体验的方式去探讨。从“孔颜之乐”所获得的方式来看,“克己复礼为仁”,正如上面讲到的“伦常日用”派所说,并不离开日常生活、生命个体而另外寻求一种“乐”之体验,更不由冥思默想、虚无飘渺之中去获得。“乐”之产生,是由具体的礼与具体的个人完美结合的结果,在这一意义上,孔颜之“乐”并不神秘。如果你希望得到,只要下决心就行: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标签:论语论文; 儒家论文; 论语新解论文; 四书章句集注论文; 国学论文; 论语今读论文; 论语集释论文; 孔子论文; 钱穆论文; 公冶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