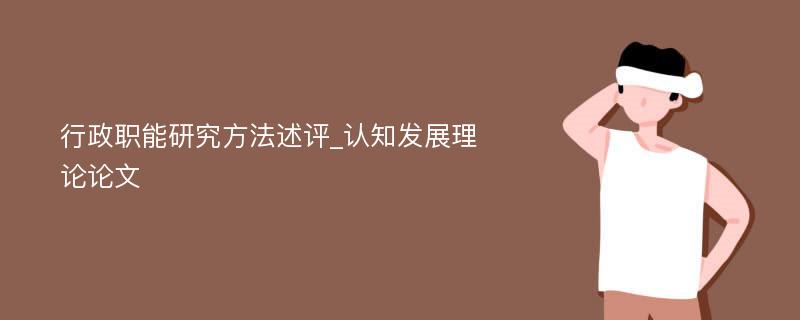
执行功能研究方法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能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简称EF)是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定义混乱的概念。目前,关于执行功能的本质,提出了多种观点,例如,抑制控制理论、工作记忆理论、抑制控制与工作记忆相结合的理论、认知复杂性与控制理论等等,这些观点讨论了执行功能的不同方面,很难用一个确切的定义去限定其内涵和外延。从整体上讲,执行功能指的是涉及对思想和动作进行意识控制的心理过程;它与多种能力的发展有关(如,注意、规则运用、心理理论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意识、思想控制和动作控制。然而,从这三个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看,其内在实质都很难用一个定义去界定明白。
从历史上看,该概念源于对PFC(prefrontal cortex)损伤后果的分析,对执行功能的研究多是从神经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如果执行功能出现障碍,必然引起神经心理方面的明显缺陷,例如:计划、概念形成、抽象思维、决策、认知灵活性、利用反馈、按时间先后对事件排序、流体智力或一般智力、对自己动作的监控等方面的困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心理学领域也出现了大量对执行功能的研究,主要存在几种理论: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理论[1~3]、工作记忆理论[4,5]、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结合的理论[6]、认知复杂性及控制(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Control theory,CCC)理论[7,8]和问题解决模型[9]等。
近年来,Zelazo及其同事在执行功能研究方面非常活跃。Zelazo等[10]将执行功能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眼窝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相联系“热”(hot)执行功能,另一类是与背外侧前额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相联系“冷”(cool)执行功能。前者以高度的情感卷入为特征,需要对刺激的情感意义做出灵活评价;后者则更可能由相对抽象的、去情景化的(decontextualized)问题引发。他认为,长期以来,大多数关于执行功能的发展研究都聚焦在“冷”执行功能上,直到近来,研究者才对“热”执行功能的发展产生了兴趣。相应地,他们将根据是否需要高度的情感卷入,将执行功能的研究任务分为冷执行功能任务和热执行功能任务两种。
由于执行功能概念还不能很清楚地被界定,因此,本文企图以冷执行功能(Cool EF)和热执行功能(Hot EF)为出发点[10],考察散见于各种研究报告中的研究方法,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归类并作比较分析,以期为揭示执行功能的本质问题提供参考。
2 冷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
2.1 搜寻任务
2.1.1 A非B任务(A not B task)和藏与找任务(Hideand-Seek Task)
A非B任务是Hunter[11]采用的延迟反应任务(delayed response)的一种变式。在A非B任务中,大多数时间一个物体被藏于A处,然后被藏于B处。关键要测量的是婴儿在物体首次被藏于B处时的成绩和物体所藏地点转变后到成功地于B处搜寻物体之前儿童犯持续性错误的次数。
Zelazo等改变了这种任务,他们用录像或言语等信息来指导3~4岁的儿童寻找物体[12],称为藏与找任务。研究者将儿童带入房间,在儿童面前把一件玩具藏起来,让儿童了解玩具所藏的地点。然后,将儿童带入休息室,并告诉儿童研究者要再返回刚才的房间更换玩具所藏地点。研究者离开之后回来,向儿童播放显示现在玩具所藏地点的录像带或者告诉儿童现在玩具藏在什么地方。接着,让儿童去寻找玩具。此研究的主要因变量是儿童在得到玩具所藏地点已改变的信息后正确找到玩具藏匿地点的次数,它考察儿童利用新信息(即外部表征)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2.1.2 多地点搜寻任务(Multilocation Search Task)
在A非B这种特殊的多地点搜寻任务的基础上,有些研究者[13,14]采用了多步骤多地点搜寻任务来研究年龄更大的儿童问题解决中的持续错误。这种任务中,研究者首先让儿童注意到物体(如糖果)被藏于多个地点(如3个)中的任意一个,儿童必须经过多个步骤(如4个步骤——拉开挡板、抽出托盘、选择目标、拖动绳子)才能拿到该物体;然后,研究者随意改变物体所藏地点,儿童经过同样的步骤去搜寻。这种研究方法不仅仅测量物体所藏地点变化后儿童持续性错误,同时也探讨了任务难度的增加(搜寻步骤的增加)是否对该持续错误造成影响。
在搜寻任务中,研究者将一个物体藏在一个、两个或多个地点:在一次或多次(一般是多次)试验中,物体被藏在A处,让被试去寻找;接着,物体在被试面前被藏到一个不同的地点B处,要求被试去寻找。此类研究中发现了一种与年龄相关的、反复不止的错误,即当物体被藏在B处时婴儿还继续到A处寻找物体,这种“持续性错误”是执行功能障碍的通常表现,表明婴儿尚不能利用已知道的新信息控制自己的行为。
2.2 规则运用任务
2.2.1 强制性卡片演绎分类(Forced-choice Deductive Card Sorting)
在此任务中,研究者告诉儿童两条规则,然后要求儿童运用这两条规则将卡片上的事物分类。比如,研究者告诉儿童:“如果卡片上是放在屋内的东西,那么把卡片放进这个盒子”;“如果卡片上是放在屋外的东西,那么把卡片放进那个盒子”。接着,研究者向儿童呈现10张卡片(如,雪人、床、卡车、电视机等)。每呈现一张,研究者就询问儿童应该将其放在哪个盒子里,如:“这里有个雪人,应该把它放在哪个盒子里呀?”Zelazo等人[15]在实验中采用了三对规则:(1)如果卡片上是可以飞的动物,那么放进这个盒子;如果是在地上走的或跑的动物,那么放进那个盒子。(2)如果是能骑能乘坐的,放进这个盒子;如果是用来演奏音乐的,放进那个盒子。(3)如果是屋内的东西,放进这个盒子;如果是屋外的东西,放进那个盒子。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测量儿童根据规则正确分类的次数,从而考察儿童灵活利用人为的规则控制自己的行为,实现演绎推理的能力。无论是否进行改进,这类任务都要求具有较好的工作记忆能力,以便记住要运用的规则。
2.2.2 斜面滚球任务(Ramp Causality Task或Two-to-two Ramp Task)
斜坡因果推理任务,也叫做二进二出斜坡任务,是Frye等人[7]在研究3~5岁儿童的心理理论和运用规则进行推理时设计的。在此任务中,研究者采用一个小球斜坡装置(或称二进二出装置),也就是一个木箱,其一面呈矩形斜坡状,上有2个入口,下有2个出口,每个入口有个分路叶片,叶片连接着一盏小灯,叶片打开,小灯亮,小球就交叉滚动(如,小球从左上端入口进入,从右下端出口滚山),相反,叶片关闭,小灯熄灭,小球就竖直滚出(如,小球从左上端入口进入,就从左下端出口滚出)。实验进行时,先告诉儿童规则,即“灯灭,小球竖直滚出;灯亮,小球交叉滚出”,再告诉他们小球入洞的位置和小灯状态,让他们预测小球从哪个出口滚出;或者,在儿童了解规则的前提下,告诉他们小球出洞的位置和小灯状态,让他们逆推小球该从哪个入口放入。这种研究方法关键在于通过测量儿童正确判断小球的出口或入口的次数来考察儿童运用已知的合取规则进行因果和果因推理的能力。这类任务可以变换规则的维度,从而使之复杂程度发生改变,但无论是几个维度的规则,都要求具有较好的工作记忆能力。通过此任务也发现了儿童认知灵活性与年龄有关的增长。
在规则运用任务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告知儿童一个规则,要求儿童按照规则去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规则。所不同的是,有些任务的规则较简单,有些任务的规则较复杂。但就其共同实质而言,所探讨的主要是规则应用的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
2.3 优势规则(反应)抑制任务
2.3.1 手部游戏(Handgame)
手部游戏源于Luria的研究[16]。儿童首先模仿主试的几个手部动作。然后,儿童必须做出与主试相反的手部动作。例如,当主试伸出一根手指时,儿童就伸出拳头;而当主试伸出拳头时,儿童就伸出一根手指。此实验的因变量是儿童在做出与主试相反的手部动作时所犯错误的次数。这种研究方法类似于民间的一种“拍手—踏步游戏”:如果游戏的一方拍两次手,则要求游戏的另一方踏步,如果拍一次手,则要求停止踏步。这种任务要求运用的规则是:“如果我出拳头,你就出手指头;如果我出手指头,你就出拳头”。在实验过程中,主试到底是先出手指头或者是先出拳头,可以是随机的,且以后继续出什么也可以是随机的,因此,在规则之间进行灵活转换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要求儿童在工作记忆中记住这一对规则,并且,由于先让儿童模仿了主试的手部动作,容易使儿童形成继续模仿主试动作的倾向性,因此,要正确进行反应,还需要抑制模仿主试动作的倾向性,否则,将犯一种模仿性的“持续性错误”。因此,在这种任务中,规则运用、工作记忆、规则的灵活转换以及抑制控制都是重要的。
2.3.2 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简称WCST)
Grant和Berg[17]编制了威斯康辛卡片分类测验,当时的目的是为了评定正常成人的抽象思维及其灵活的转换,它是关于抽象和灵活思维的一个经典神经心理测验。发展心理学用WCST来研究儿童的认知灵活性,成了研究冷执行功能的一个典范。测验中,研究者先向儿童呈现多种维度的刺激卡片,接着向儿童呈现与不同刺激卡片在不同维度上相匹配的独立的卡片。儿童必须发现规则并用该规则来分选卡片。每选一张卡片,不管对错,研究者都给予儿童反馈。在连续的正确选择达到一定次数后,研究者改变目标维度,这时,儿童必须找出新的分类规则。此研究的关键因变量是:第一,儿童对刺激卡片和目标卡片的相似性抽取能力;第二,目标卡片的维度改变后,儿童抑制先前规则以发现新规则的能力。通常,在这类研究中,同样发现了儿童不能灵活转换的持续性错误,而不能灵活转换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维度改变前所形成的规则成为抑制新规则的优势规则,同时,这种任务要求儿童在发现规则是要不断猜测主试心目中的目标维度,因此,工作记忆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比规则运用更复杂的假设检验也起到重要的作用。WCST通常用于6岁及其以上年龄的儿童。
2.3.3 灵活选择任务(Flexible Item Selection Task,简称FIST)
FIST是一项归纳性任务。在Feldman和Drasgow[18]的视觉-言语测验(visual-verbal test)的基础上,Jacques和Zelazo[19]改编出了这种方法(FIST)来研究学前儿童的冷执行功能。它和WCST一样,也考察儿童的抽象和灵活思维,但它比WCST任务更简单,它对工作记忆的要求更低,对被试利用反馈的能力的要求也更低,因此结果的分析也更容易。此任务的每次试验中,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三张图片(如一艘大船、一艘小船和一只小兔子),首先要求儿童选出在某一方面相关的两张图片(如形状:大船和小船),然后再让儿童选出在另一方面相关的两张图片(如大小:小船和小兔子)。儿童第二次选择正确的次数就是主要的因变量,这种研究方法就在此基础上测量儿童灵活运用规则、在不同维度间灵活转变的能力,即认知灵活性。在这种任务中,儿童常常在依据一种标准对刺激卡片进行归纳以后,往往难以发现另一个归纳维度,因而同样表现出所谓的“持续性错误”,所以,首先形成的归纳维度所构成的规则就成了所谓的“优势规则”,必须抑制这种优势规则才能进行新的归纳。它通常用于3~5岁的儿童,但也有更加复杂的版本可用于年龄更大的儿童。
2.3.4 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ting,简称DCCS)
DCCS是一种典型的冷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Frye等人[7]用了标准的DCCS任务来研究3~5岁儿童的冷执行功能。此任务中,研究者首先向儿童呈现有着不同颜色和不同形状的图案(如一辆红色的车和一朵蓝色的花)的目标卡片,接着呈现给儿童一系列测试卡片(如几辆蓝色的车和几朵红色的花)并要求儿童在一种维度上(如颜色)进行分类;经过几次(如8次)实验后,又让他们在另一维度上(如形状)再进行相等次数的分类。其关键因变量为维度变化后儿童是否能正确分类,从而检验儿童运用合取规则的能力,即能否在两套不相容的规则之间进行灵活的转换。研究者发现某些年龄段的儿童不能在几对规则之间转换,尽管在每次试验时告诉他们要转换规则并告知新规则,他们还是在规则变换后的实验中系统性地固着在转换前的规则上,即存在所谓的优势规则,必须抑制优势规则才能实现灵活转换。也就是说,儿童的认知灵活性存在与年龄相关的变化。另外,在标准DCCS的基础上,DCCS任务还有许多变式[20]。虽然DCCS的某些版本被用于研究学龄儿童和成年人,但是它主要还是适于3~5岁的儿童。
2.3.5 停止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
Logan(1994)[21]采用停止信号任务来研究了与执行功能密切相关的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他通过计算机向儿童呈现一系列刺激,并告诉他们,如果屏幕上出现某个刺激(如字母“X”或“O”),就按X键和O键中的其中一个,如果听到作为停止信号的声音,就停止按任何一个键。这个研究中的因变量包括选择反应时,而这种选择反应时任务在本质上是一种测量规则使用能力的任务,即:如果出现X,则按X键;如果出现O,则按O键,如果出现停止信号,则不按任何键。因此这种任务所要求的也是一种利用给定规则控制行为的能力,同时还测量对已形成的“按键反应倾向”进行抑制的能力,当然,因为儿童必须记住规则才能灵活地反应,因而工作记忆的作用也不可缺少。
在优势规则抑制任务中,有些任务要求儿童自己归纳出规则(发现规则,如WCST和FIST),有些任务是将规则指直接告知儿童(运用规则,如DCCS),但其共同实质是要求儿童不仅仅能够运用规则实现分类任务,而且更进一步要求儿童在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实现规则间的灵活转换,而实现规则灵活转换的关键则是要儿童抑制先前的优势规则的影响而发现或利用新规则。利用前面提到的斜面滚球任务,适当修改实验程序也能够检测这种要求规则灵活转换的能力。
2.4 矛盾冲突任务
2.4.1 Stroop测验(Stroop Test或Stroop Color-Word Task)
Stroop测验是研究执行功能的典范之一,它是Stroop[22]创造的。在实验条件下,研究者向儿童呈现表示颜色的字(如“绿”字),而这个字是由其它无关颜色的墨水写的(如红色墨水),这时,研究者要求儿童说出墨水的颜色。实验关键要测量的是儿童正确回答的次数。在这种实验中,儿童往往受到字面意义的影响(例如“绿”)而不能正确说出书写该字的墨水的颜色(红色)。其原因可能在与儿童对于字面的意义具有“优势反应倾向”,因而不能抑制其优势反应而错误地以字面的意义代替墨水的颜色。Stroop测验被用于测量学龄儿童的执行功能。
2.4.2 昼与夜Stroop(Day-Night Stroop)
昼夜Stroop来源于Gerstadt、Hong和Diamond[23]的研究。当研究者向儿童呈现画有月亮和星星的图画,要求儿童看见此图画时回答“白天”;当呈现画有太阳的图画时,儿童回答“夜晚”。在此实验条件下儿童正确回答的次数就是该研究的关键因变量。这种任务和Stroop任务具有基本相同的实质。昼夜Stroop这种研究方法既用于学前儿童又用于学龄儿童。
这两种任务一方面具有共同的实质:都要求儿童抑制字面意义和视觉冲突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完全一致,后者同时还是一个规则运用任务,即“如果你看见月亮和星星,那么你说白天;如果你看见太阳,那么你说夜晚”,因此,工作记忆在这种任务中也是不可缺少的;而Stroop任务则几乎没有规则运用的含义,工作记忆在其中并不重要。
2.5 问题解决任务——河内塔和伦敦塔(Tower ofHanoi或Tower of London)
河内塔以流行于19世纪的一道难题为基础。此任务中有一个特殊装置,装置有3个相同大小的底座,n个盘子从大到小、由下直上放置在其中一个底座上,要求儿童必须遵守特定的规则(如每次只能移动一个盘子且移动过程中3个座上都始终保持大盘在下、小盘在上)将n个盘子从起始座借助中间座移到目标座。任务难度随问题解决所需移动盘子的次数而变化。而问题解决所需移动盘子的次数正是此研究的关键因变量。另外,河内塔任务中使用的盘子可以更换,Klahr和Robinson(1981)[24]就用铁罐代替了最初的河内塔任务中的盘子。在河内塔的基础上,Shallice[25]设计了伦敦塔任务。此任务将河内塔任务中的盘子换成了彩球,要求儿童描述他们要怎样改变彩球的最初排列才能将它们按要求移到目标座上。河内塔任务和伦敦塔任务都曾应用于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但近来,更多的研究采用了伦敦塔(如Luciana和Nelson[26]),他们用此方法来研究额叶受损儿童的认知缺陷。
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共同特点是需要被试利用被告知的特定规则,按照一定的计划,有步骤地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规则运用能力是相当重要的,另一方面,根据规则去制定行动计划则显得更加重要,最后,利用规则、按照计划去具体执行也同样重要。显然,这里所研究的执行功能比前面的搜寻任务、优势规则抑制任务、灵活反应任务等所研究的执行功能更加高级,除了研究规则运用以外,还要求更高级的利用规则制定计划以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时,工作记忆依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6 图片工作记忆任务——自定顺序指示(Self-Or-dered Pointing,简称SOP或SOPT)任务
SOP也被认为是研究冷执行功能的典范之一。最初,研究者[27,28]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额叶的功能及其损伤的后果。Archibald和Kerns[29]把它纳入了研究执行功能的重要方法中。在适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一本图册。首先,儿童看到图册的一页上有2张图片并任意选择其中一张。接着,研究者翻到下一页,呈现给儿童与前面看到的完全一样但位置安排却不同的2张图片,这时,要求儿童指出刚才没有选过的那张图片。然后,研究者向儿童呈现新的一页,这一页在原有2张图片的基础上增加一张新图片,且原有的2张图片的位置与前一页的安排又不相同,要求儿童指出哪张图片是没有选过的,以此类推。如果儿童没能正确地从一组图片中找出自己没有选过的一张,研究者就向其呈现重新安排过位置的同样一组图片;如果儿童在两次重新安排图片位置之后还是没能正确指出,那么此任务结束。此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一种图片记忆广度的测量,以此揭示出工作记忆在整个儿童时期内存在的与年龄有关的规律性的增长。完成这种任务需要将记忆中的图片和现实知觉的图片相比较并做出决策,当图片的数量超出儿童的记忆广度时,儿童将不能在头脑中实现这种比较,因而,表现为行动上的失败,即不能利用思维活动正确地支配外部行为。这种研究方法通常用于学前儿童和学龄儿童。
3 热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
3.1 心理理论任务
3.1.1 错误信念任务(False Belief Task)
Wimmer和Perner[30]首创了“错误—信念”(False belief)的研究范式,该范式一直被认为是研究儿童心理理论的标准范式,通常也叫做“意外地点任务”(unexpected location task)。给3~5岁的儿童讲一个用玩偶演示的故事:男孩Maxi有一盒巧克力,他把它放在厨房的一个碗柜里(位置A),然后他走出去玩,当他出去后,他妈妈用一些巧克力做了一块蛋糕,然后把剩下的放进冰箱里(位置B),Maxi因不在现场,因此不知道巧克力已经被转移,进来后,他想要吃巧克力。然后问听故事的儿童,Maxi将到哪里去寻找巧克力?或者问儿童,如果其他小朋友听了这个故事,那么其他小朋友认为Maxi将到哪里去寻找巧克力?研究发现,小于4岁的儿童常常做出错误判断,认为Maxi将到巧克力真正所在的位置(位置B)寻找,或者认为其他小朋友也认为Maxi将到巧克力真正所在的位置(位置B)寻找。以后大多数研究者采用这一范式的研究发现,能否认识到故事人物持有错误信念的儿童的年龄分界线为4岁。这是研究ToM的典型方法之一,探讨儿童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能力。错误信念法主要用于3~5岁的儿童。
3.1.2 表征变化任务(Representational Change Task)
这种任务通常也叫做“意外内容任务”。Gopnik和Astington[31]采用了此任务对3~5岁的儿童进行了研究。国内外还有许多研究者都采用了这种研究方法来研究儿童的心理理论,因此,它存在着许多变式。研究者首先向儿童展示一个儿童十分熟悉的容器(如,蜡笔盒)并询问盒子里装的是什么。接着,研究者将盒子打开,里面出乎意料地装着其它东西(如,糖果)。这时,关上盒子,通过问儿童盒子打开前他们认为盒子里装的什么来让儿童回忆他们对盒子所装内容的最初预料;或者假设现有另外一个人也看到了这个盒子,询问儿童这个人会认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在这种任务中,儿童先根据容器的外表回答容器内所装物品,然后却意外地发现容器内所装物品并非他先前所说的物品,然后,再让儿童回答“盒子打开之前,你认为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以便测量儿童是否能够对自己先前的心理活动进行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理论任务。
最近,一些研究者对表征变化任务进行了改进,如Zelazo和Bosevski[32]在标准表征变化任务的基础上加上了磁带录像来研究心理理论。他们向儿童展示了一个蜡笔盒并询问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儿童回答“蜡笔”,用录像机录下这一过程。接着,研究者打开蜡笔盒,里面装的是糖果。然后,关上蜡笔盒,让儿童观看刚刚拍下的录像带。之后,询问儿童他们刚看到蜡笔盒时,也就是蜡笔盒打开前,他们认为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这样做的目的通过录像来提醒儿童,以排除工作记忆的局限对儿童回答问题的影响。但是,由于这种任务中存在一种意外内容的出现,因而会导致儿童情感上产生惊异,由此,Zelazo等认为它是一种热执行功能任务。
3.1.3 窗口任务(Windows Task)
这种研究方法来源于Russell、Mauthner、Sharpe和Tidswell[33]。研究者向儿童呈现开有窗口的两个盒子,将盒子上的窗口朝向儿童,以便让儿童看到盒子的内容。每一次试验中,主试在其中一个盒子里放上“诱饵”,要求儿童告诉主试(主试看不到盒子的内容)哪个盒子里有东西。接着,主试对儿童指出的地方进行验证。如果儿童示意主试检查空的那个盒子,则儿童能够得到另一个盒子内的东西。相反,如果儿童让主试察看放有“诱饵”的盒子,儿童就得不到该盒子里的东西。这个实验的关键因变量是儿童指导主试察看放有“诱饵”的盒子(因而没能得到“诱饵”)的试验的次数,如果儿童能够学会“欺骗”主试,总是指示主试去空盒子里找东西,那就表明儿童能够主动运用欺骗的策略来获得奖励。其基本假设是儿童具有获得“诱饵”物品的需要,这种需要将推动儿童的认知活动;其要求儿童形成的规则是:如果我要得到奖品,就必须给主试说空盒子里有东西。这种任务主要用于研究3~6岁儿童的心理理论问题。
3.2 延迟满足任务(Delay of Gratification)
延迟满足任务是研究热执行功能的一项经典范例,它采用延迟任务和选择任务来评定满意的延迟(如Mischel,Ebbesen和Zeiss[34])。研究者向儿童呈现一些小礼品(如糖)并让儿童选择是立即得到1颗糖还是过一段时间(如游戏结束时)获得2颗糖(此数量是可以改变的,如:现在1颗,游戏结束时6颗)。研究要测量的是儿童做出延迟选择的次数,并就此来考察儿童是否能够抑制即时的愿望去满足长远的愿望,即能否有着眼于将来。
使用这种方法的早期研究通常未在学前期发现年龄差异,但在学龄期发现了年龄差异。而且,这一研究确定了许多影响儿童选择等待的时间长度的注意和认知因素。例如,对想要的奖赏的抽象的、非唤醒的,而不是具体的、唤醒的特性的考虑积极地影响了儿童延迟满足的能力。这些结果说明了在这个任务上取得成功的一种方法可能是将它从一个“热”执行功能任务转变为一个“冷”执行功能任务,强调了执行功能的两方面之间的密切关系。
近年来,有两个研究[35,36]采用经过修改的选择任务,考察了年龄较小的儿童能否放弃自己当前的机会去满足自己将来的愿望或者能否帮助他人(research assistant)放弃当前的机会去满足将来的愿望。儿童在研究中表现出了审慎和利他行为,并且这种着眼于将来的(future-oriented)审慎和利他行为与年龄有关。Moore还发现审慎和利他行为与心理理论测验中的表现相关。
3.3 儿童博弈任务(Children's Gambling Task)
Kerr和Zelazo[37]简化了Bechara等人[38]研究中的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从而设计了儿童博弈任务来测量热执行功能,它是热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中较复杂的一种。此任务运用了两副纸牌,一副纸牌的正面是竖条花纹,另一副的正面是圆点花纹。将两副纸牌翻过来都能看见它们的反面有开心的脸和悲哀的脸。但不同的是,正面是竖条花纹的纸牌的反面总是有1张开心的脸,偶尔加上1张悲哀的脸;而正面是圆点花纹的纸牌的反面总是有2张开心的脸,但有时会出现好几张(如4,5,6张不等)悲哀的脸。开心的脸代表赢得糖果,其数量也代表赢得糖果的数量;悲哀的脸代表输掉糖果,其数量也同样代表输掉糖果的数量。每次试验只能选取一张纸牌。显然,选竖条花纹的纸牌虽然每次赢的糖果更少,只有1颗,但平均起来,输的糖果也更少;相反,选圆点花纹的纸牌虽然每次赢的糖果更多,有2颗,但平均损失却大得多,一旦输,就会输掉4颗、5颗或是6颗。因此,从长远来看,选竖条花纹的纸牌有利,反之,则不利。实验中,研究者告诉儿童“游戏”结束时要赢得尽量多的糖果(比如50次选牌后,这点儿童事先不知)。开始的25次选择可以看作儿童对两种纸牌的尝试;后面的25次试验将被作为对情感决策的诊断。此实验的关键因变量为儿童在第26~50次试验中做出不利选择的比例。这种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儿童情感决策的诊断,通过这种诊断可以推断出儿童的“热”执行功能发展与年龄有关的规律。它还考察儿童控制受即时愿望支配的动作的能力和预测他们的动作将会产生的后果的能力。它常用于学前儿童,但对学龄儿童也适用。
3.4 反向择物(Object Reversd)
相对于儿童博弈任务来说,反向择物任务是研究热执行功能的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它以Overman等人[39]的研究为基础。每次试验,研究者都向儿童呈现同样两个事物(如事物A或B),并且当儿童选择其中一个事物(如A)时,总是给予儿童奖励。经过一定次数的试验后,研究者又改为当儿童选择另一事物B时给予奖励,即奖励的可能性发生了反向转变。可见,此研究首要的因变量就是儿童要了解到这种转变所需的试验次数。反向择物法测量的是对刺激的强化值(reinforcement value)进行灵活表征的能力,为研究人的消退行为(extinction)提供证据。这种研究方法常用于年龄较小的学前儿童,但也可用于婴儿和学龄儿童。
4 从研究方法看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可谓林林总总,本文所介绍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如关于热执行功能的其中一个方面——道德推理的研究方法就未包括在内),但是透过这些种类繁多的任务,我们发现执行功能的研究还存在许多问题。
首先来看“冷”执行功能任务。在本文所介绍的五种任务中,完成搜寻任务主要需要两种能力:一是当物体被转移到新地点后,幼儿利用新的外部信息表征的能力,二是抑制已形成的习惯性反应从而克服所谓“持续性错误”的能力;完成规则运用任务主要需要两种能力:一是对至少一对规则的工作记忆能力,二是根据刺激物的特点灵活利用规则进行分类的能力;完成优势规则抑制任务一般需要如下几种能力:一是规则运用能力,二是抑制控制能力,三是工作记忆能力,四是规则间的灵活转换能力;完成矛盾冲突任务的主要能力包括:抑制控制能力、规则运用能力和工作记忆能力;问题解决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复杂的种类,除前面提到的能力外,尚需要计划能力、元认知能力等更高级的能力;自定顺序指示任务主要是执行功能的“工作记忆”观点的代表任务,对其他任务中提到的其他能力要求不多,完成这种任务的最主要的能力就是良好的工作记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息表征能力、抑制控制能力、工作记忆能力、规则运用能力、灵活转换能力、计划能力、元认知能力等在不同的冷执行功能任务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能力几乎囊括了广义的“认知”能力的全部。这种观点得到了Zelazo等新近提出的关于执行功能的问题解决模型理论的支持。Zelazo等采用问题解决的四阶段模型来解释执行功能,即问题表征、计划、执行、评价,从问题解决的四个阶段来看,个体要实现正确的问题解决,就必须调用整个认知过程——从最初的感知觉输入到行为输出以及对此过程的监控和评价,这意味着执行功能涵盖了整个认知活动。“执行功能”能否与广义的“认知”划等号,是否可以用“认知”这一老概念取代“执行功能”这一新概念,这正是目前执行功能研究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
再来看“热”执行功能任务,当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单纯地在冷执行功能任务的基础上增加情感摄入,例如在奖品的驱动下灵活使用规则或抑制优势反应(如习惯性反应或即时愿望支配下的反应);二是在冷执行功能任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为复杂的任务(如儿童博弈任务),它们可能不仅涉及到奖品需求和规则使用、抑制控制、工作记忆的结合,而且还需要其它情感和社会性方面的能力;三是心理理论任务,它们涉及到理解和推测他人的信念、欺骗等复杂的因素。
心理理论任务容易引出目前存在的一个较大的争论,即心理理论与执行功能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并列还是包含,如果是包含,是谁包含谁。我们猜测执行功能和心理理论是两种并列的能力,但二者之间可能有部分交叉。从多数心理理论任务不难看出,它们既涉及规则使用、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等因素,又有着高度情景性和社会性及高度的情感(如,吃惊或对自己、他人需求的满足)卷入,应当被纳入热执行功能的研究方法中。但有些心理理论任务,如错误信念任务,似乎并不涉及执行功能通常包括的规则使用、抑制控制和工作记忆等因素,也不符合“对思想和行为的意识控制”的定义。尽管有研究者认为心理理论是热执行功能的一部分[10],我们在前文也暂把错误信念任务作为热执行功能的一种研究方法来介绍,但错误信念任务是否能算作研究执行功能的一种方法仍有待讨论。
总体看来,目前关于执行功能的几种观点都只强调了执行功能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还没有一种观点能够将上述方法所研究的执行功能概括完整。关于执行功能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从执行功能的定义到执行功能与其它心理能力的关系(如与心理理论的关系)等都是十分重要而尚无定论的问题。尽管本文详细评述了散见于各种文章的关于执行功能研究方法,但我们发现,如果要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分析执行功能的本质,这些研究方法所带给我们的是一幅相当混乱的景象,从中难以概括出执行功能的本质。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对这些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鉴别和归类,弄清它们真正适用于研究什么,在此基础上再来概括执行功能的本质;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方法的改进和利用,充实和拓展对执行功能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