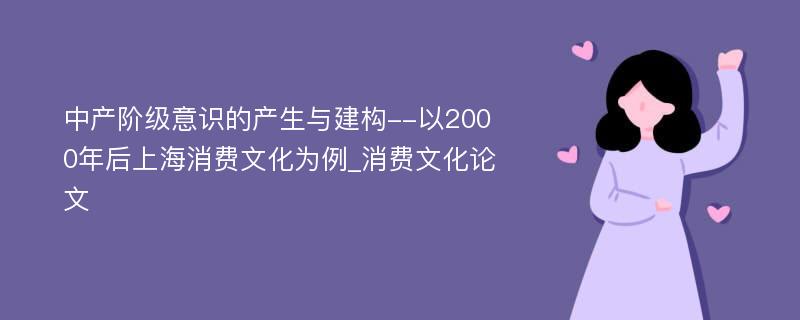
中产阶级意识的生发和建构——对2000年后上海消费文化的个案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个案论文,上海论文,年后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真正摧毁了中国社会传统生存和信仰模式的,不是20世纪中国政治家们的“政治试验”,也不是文人们、政治家们倡导的“文化革命”,而是消费社会的崛起、消费文化的浸润。消费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和思想的中心,也是文化理念的中心,它打破了现代以来,甚至是自古以来我们形成的中国思想、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与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平衡。
上海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消费是由物、服务以及相关的信息交流和财富交换为中介组织起来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合,“物”在消费关系中,首先是“视像”,它首先在电视等视觉媒体中露面,然后是在商场的展示柜台和橱窗中露面,最后作为甲的消费物在乙的眼光中露面,这个过程中,视像的交流和玩味,远远超过了“物”的可用性范畴,甚至是对可用性的回避,这个过程中,“物”的人工化形式被单独提取出来,在作为内容(可用性)的“物”被回避的基础上,作为质料的“物”也被回避,不会有人真的关心欧莱雅化妆品到底使用了什么质地的原材料,消费过程中,消费者更关心的是欧莱雅在别的人的眼光中的视像意味——在别人的眼里,它是高档的吗?有用的吗?现代消费的核心景观是由视像垫造的,真正的奥秘就在视像中。
我们对上海消费文化的分析,可以从视像开始。反过来,我们也认为在所有的视像中,最能担当关键视像角色的是“商业视像”。上海一向被看作是一个商业文化社会,但是,商业消费文化成为社会主导文化是最近才产生的,仅仅是在最近几年,上海市民才渐渐地由产业工人为主导群体,向金融、服务等从业群体转移,日常生活由工厂上班、生产为核心转向办公室上班、休闲、消费兼顾。2000年以后,上海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副中心,如徐家汇、五角场、大宁国际副中心的崛起,这些商业副中心把新的消费意识、身份意识、生活意识带向四面八方,而在2000年之前,上海实际上的消费中心只有淮海路、南京路,那里的消费大多还是针对外地游客的。
过往我们对文化的研究比较重视纸面印刷材料,文字是我们分析的中心。但是,当下的社会是一个视觉中心的社会。法国学者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把当下社会定义为“景观社会”,人们因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对本真生活的要求,资本则依靠制造和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操纵社会生活。德波认为,费尔巴哈判断的他那个时代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事实被这个景观的世纪彻底证实。景观是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景观社会的本质是:少数人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因为对景观的“沉入”,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的观赏中承受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图像,是已被现实化和转化为物质王国的世界观,被转化为客观力量的世界观。在景观生产方式中,意识形态控制通过影像布展得以生成,而分离(异化)则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①中,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成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②。“存在”向“占有”堕入之后,又向“显现”转向。德波认为一种完全倒向景观化的消费文化已经诞生,其作用是使历史在文化中被遗忘掉。在景观社会里,个人被景观弄得目眩神迷,被动地存在于大众消费文化之中。鲍德里亚更为极端,他认为景观社会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拟像时代”,“这是图像历史的最后阶段,它从‘图像掩盖基本事实之缺席’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在其中,‘图像与任何一种现实都没有关系:它只是自身的纯粹的拟像’”③。图像本身就是凶手,它在“谋杀真实”。因为既然我们已经习惯通过图像为媒介来了解事实,那么我们就得服从图像的指示。鲍德里亚说:“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④上述变化的实质在于虚构的东西已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恍若魔术师手中高明的戏法,各种“专门化的媒体”一时间成了主角,视觉被提高到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卓越的地位。费边直言不讳地认为,这个时代文化或社会视觉化的能力几乎可以成为理解的同义词,一个“图”字让新闻的可信力和吸引力同时倍增。
本论文对上海文化的分析立足于视像,而视像的分析又不是立足于传统的文化视像——那些由文化人创造的视像作品,如影视、绘画、摄影作品,而是立足于商业/消费生活中的产生的各种“生活视像”,这是本论文没有把文人创作视像作为解读对象,而把商家和大众通过消费关系合作创作的消费生活视像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关于文化的生产机制,我们有两个路向可以讨论。一种观点是:文化是由大众生产出来的,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不是精英,也不是政治领袖,而是大众自身,他们自我创造,自我造就,即使是精英和领袖的影响也是通过其自身的消化、吸收达到的,大众犹如文化蚂蚁,他们人多势众,匍匐在地面上爬行,看起来不起眼,没速度,没高度,但是,他们恰恰是文化的载体,他们首先是组成了文化,最后,他们组成的那个文化恰恰又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与此对应的是另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把文化看作是由社会精英创造,或者至少是由精英主导的,大众只是文化的载体,他们得有雄鹰引导,雄鹰带路,蚂蚁跟随。前者我们可以看做是蚂蚁文化观,后者我们可以定义为雄鹰文化观。
实际的情形比上述两种观点更复杂。蚂蚁和雄鹰都在同一个空间,他们处于互相影响、相互造就。有的时候,看起来文化大众在反抗文化精英,但是,这种反抗恰恰堕入了精英圈套,走了精英路线;而文化精英常常在进行文化设计和文化建构的时候,又被大众的创造力征服,这里面存在着复杂的权利扭结。本论文试图对此做出解读。本论文用图像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2000年后上海商业文化的建构的新特点,上海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的生成模式。
本论文试图把对上海的商业文化分析建构在案例分析之上,而途径则是视觉分析。我们的研究目的:一、我们研究2000年之后,上海商业文化发展的新特点,尤其关注消费行为中“阶层意识”的建构,而我们的研究是通过“中产阶级消费意愿和消费意识”的建构及扩张展开的,真正的阶级意识,是由消费产生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模式导致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变化,直接产生自我阶层归属感。二、2000年以后,上海出现了众多副中心,五角场、大宁国际副中心等的出现,表示上海商业格局的网络化开始形成,上海的商业生活、消费景观不再局限于市中心一块有限的地方,而是遍地开花,生产不再是这个都市的核心,新的核心是消费,这个消费正被大大小小的副中心的建成从中心城市景观变成全上海的城市景观。
电视出现之后,世界已被造就为“看”的对象,视觉被提高到触觉、听觉、嗅觉等之上王者的地位,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它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地呈现为视觉文化现象,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社会冲突、家庭冲突等等都被媒体视觉化为“图像”,成为被观看的景观。本课题着重分析上海商业视像,把人们的消费行为、日常生活行为“视觉”化,作为“看”的对象来分析,同时也重视对大众“看”的方式(对视像的接受行为)的观察和分析,研究“看”的内容和“看”的方式是被“商业行为”生产出来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我们试图把整个上海看作是“视觉”对象,我们把2000年来上海文化的转型问题转化为“视觉景观”的问题,以解释上海文化的自我生产、自我缔造——“上海,今天的上海文化何以如此”的问题。
二、案例选择
我们选择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建成之前,闸北只有一个不夜城商业中心,但是,2000以后,闸北行政部门承认,以不夜城为中心的闸北发展策略是不成功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夜城对整个闸北没有带动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夜城的“商业定位不精确”,不符合大上海,包括闸北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作为重点建设项目,闸北区政府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项目给予了极大重视和极大支持。
我们时间段上选择2000年之后,空间上选择新型商业中心。
时间的选择是主观的,我们不能掌握时间的开始,也不能掌握时间的结束,对于时间这种不可控之物,任何选择都只能是从主观开始,到主观结束——我们假设2000年可以作为某种研究的时间上的开始点。本论文试图通过实地动态观察以及静态读图分析来达到目的。图像分析首先采用“所见即所得”的直观读图法,整合“符号学”、“解释学”等视像解读方法。不过,本课题不准备采用过分学究化的方式来进行,而是更多地依靠一个学者的直观观察和感受。本课题研究者生活在闸北大宁国际社区已经有10年,亲历大宁国际立项、建设、开张到目前经营状况的这个过程,和大宁国际开发商以及部分商家有过深度交往,本论题不试图回避“主观性”,而是试图发挥这种“主观”观察的价值,使它成为本论题研究的独特之处。
大宁国际社区位于闸北中部地区,内中环线间,地处上海南北高架、一号地铁线上,向南,到达市中心人民广场乘坐地铁一号线为四站距离,向北,到达外环线共富新村站七站距离,是连接上海市中心和宝山的交通要津。2000年后,被列为闸北重点发展区域,相关部门提出“以高品质的规划带动整个地区发展”,“打造现代国际居住社区”,“商业社区”的发展理念,之后这里逐步建设了“大宁绿地”等绿化项目,开发了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向中、高端商业形态倾斜的项目,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商业形态。大宁国际的投入运营,对于区域内的人气集聚、人流量增加、消费氛围的确立起到促进作用。大宁国际的成型发展与大宁国际周边已形成立体的交通网络,交通优势有关。它位于上海的中轴线南北高架与贯穿杨浦、虹口、闸北、普陀四区的横向主干道广中路的交叉处;全国首条集高架道路、轨道交通、地面道路三位一体的南北主干道共和新路在辖区内贯穿而过,是上海城市动脉的交汇点。交通上的优势是构成大宁国际商业中心的硬件。周边情况,北面,广中路“多媒体谷”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这里构成了高新技术人才和商贸的聚集;大宁国际开张之后,南洛川东路、共和新路路口引进了“大宁国际茶城”;向北正在开发的有以“国际企业总部基地”为目标,面向抢滩大上海的国内外大中型企业总部的“东方环球企业中心”、“上海共和国际商务广场”等。
大宁国际以其“多、大、新、齐”的商业形态为消费者带来了现代城市生活的新体验。
多。即品牌多,20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入驻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其中多个为首次登陆上海的品牌。比如,高露洁高档护理牙刷(高露洁360度全面洁净牙刷),整条延长路上所有的店铺,都没有出售,如果你要买,就得去大宁国际;游泳池——在大宁国际富朋喜来登有,附近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没有恒温泳池。大。即规模大,25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高低错落的15幢建筑,11个大小广场和庭院,约2公里步行街道和1300个机动车位使其犹如一艘商业航空母舰。新。即风格新,在建筑外观上,以现代的建筑风格,重塑传统商区的尺度空间。齐。即功能齐,酒店、办公、零售、餐饮、文化、娱乐、教育、现代服务业八大功能有机分布于项目中。
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占地面积约5.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商业面积为9.5万平方米,是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购物中心。商业广场具有商务酒店、办公楼、SOHO式办公楼、零售、餐饮、娱乐、教育文化和城市生活配套设施等八大功能。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引进的120家商户经营的250个左右的时尚品牌中,约有25%的品牌第一次进入上海零售市场,约有75%的品牌第一次跨越苏州河进入苏州河以北地区,约有85%的品牌是第一次跨越内环线进入沪北地区。上海的时尚品牌地区分布结构就此将出现突破性的变化。位于福朋喜来登酒店大楼四楼的“亲子广场”,上海荣臣博士蛙集团在这里开出了“博士蛙365儿童百货”专卖店,由该公司授权生产经营的博士蛙、哈利波特、网球王子等三个品牌的儿童服装系列,以及各种时尚玩具招揽着孩子们。棒·约翰、味千拉面等餐饮店的门前则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德国快速时尚服装连锁巨头C&A中国地区首家旗舰店。按照五星级标准建造的四星级福朋喜来登酒店。
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开业后,上海旅游节的17辆花车巡游、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庆功晚会等市级大型人文活动纷纷跨越苏州河,来到以往很少光顾的沪北地区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上影星汇影城主办的“韩国电影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周周演”活动也都首次在沪北地区举办,为消费者在购物、休闲之余送来国际艺术盛宴,让闸北居民第一次近距离地耳闻这些文化娱乐活动。
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白天阳光灿烂,晚上灯火通明,站在广场上,走在街道上会感到自然轻松,而分布于项目中的人文景观给大家带来消费情趣。看到那些悠闲穿梭于广场步行街的三口之家,或者相约在露天咖啡馆、甜品屋畅谈的二三知己,就不难领会著名艺术家及规划师米丘先生所说的:“LIFE HUB除了便捷性之外,还给人们带来舒适性和享受性。”大宁国际为沪北消费者提供了一个便捷、时尚、舒适的全新消费文化。
按照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开发商介绍:这是一个“原创的汇聚商业与生活元素的LIFE HUB商业新形态”,集购物休闲、体育健身、文化娱乐、办公商住四位一体,占地80公顷、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消费商业中心大宁国际商业广场是闸北有史以来最大的商业项目,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开业将整体提升沪北地区商业形态、消费环境、品牌档次以及消费者的生活素质,将促成闸北区和大宁地区的“大变身”。
那么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到底是怎样将这种所谓的“舒适性”、“享受性”商业文化意识输入沪北的呢?
三、身份意识的塑造与阶层认同
闸北在上海一直被看作是“下只角”,解放前这里是苏北移民、底层劳动者的聚居区,与静安、黄浦、虹口等区形成鲜明对比,解放后,这里的局面并没有很大改观,几乎集中了上海最重要的几个棚户区,长期以来,住户文化水平低、从业档次低,收入低,居住条件差,是沪上的“下只角”。由于居民的这种身份、社会属性,闸北一直没有形成大型的商业中心,唯一的一个商业集中区域是“不夜城区域”,但是,不夜城区域主要是服务往来上海的火车乘客的,与其说它是上海人、闸北人消费的地区,还不如说是往来上海的外地人消费的地方。真正到那里消费的闸北居民并不多。离闸北比较近的消费中心可能是虹口的四川北路,那里被看作是低档消费场所——真正的上海底层市民购买衣物、日用品的地方,2000年以前,闸北人都有到那里消费的习惯。
2000年以后,闸北人的这种消费习惯发生了改变。这个改变的第一个外在标志是南北高架中山北路北段的建成和通车,闸北人的出行变得方便,去四川北路还不如去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路方便。之后是2005年一号地铁北延伸段的通车,闸北人消费可选择的区域扩大,一趟地铁可以到达徐家汇,徐家汇也纳入了闸北人消费的版图。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消费依然是外在于闸北人的,是外面的世界和生活。
不过,出行道路的便捷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可能是双向影响的,出行的方便影响了闸北人的消费意识,使他们的消费中档、高档化,另一方面闸北交通的便畅带来了闸北居民结构的变化。大宁板块的出现是这个的代表——围绕上海最大的公共绿地大宁绿地,这里出现了锦灏佳园、新梅共和城、嘉利明珠城、宝华现代城等一系列中高档楼盘,这些楼盘的建成,为大宁板块引来了至少100万新型居民,他们是一批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在从事比较高端职业的白领阶层,加上这一地区原有的居民,按照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建造方的调查统计,大宁板块及其周边辐射地区(主要指共和新路北延伸段沿线居民),具有中档消费能力的居民增加到了300万人。
温饱型的闸北,把劳动当作生活全部的闸北,社会意识正在发生改变。而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出现,给了这种改变一个契机,一个推动。不是劳动使人的生活有意义,是消费使人的生活有意义——这是一个新的观念,但它的的确确地开始注入闸北人的意识之中。
这个部分我们要研究大宁国际提供的消费结构,但是本文并不想采取统计学的方法,因为本文的一个基本性的观点认为:消费意识的规驯和植入,是通过各种感觉,尤其是视觉,潜移默化进行的,消费者来到这里,不是靠统计数据进行判断,而是靠感官直觉进行判断,而最主要的是视觉。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大宁国际没有奢侈品,比如手表消费,它没有欧米茄,它有一款瑞士中档品牌,叫swatch,请注意这里没有引入中国的罗西尼,而服装品牌,引入的是荷兰的中档品牌,比如C&A。在这里,没有看到所谓的真正的文化消费品,实际上,这里曾有一家明君书店,开了九个月,就关门了,明君书店,除了出售书籍,还出售陶瓷艺术品和咖啡,我们看到,星巴克咖啡在这里热卖,我们可以注意,星巴克也是一款美国中档咖啡,但是咖啡跟图书结合却没人要喝,书店的关门大吉,也许是经营不善的结果,但也可以看出,它在闸北这一块,的确是没有消费市场,或者我们可以说中产阶级还没有真正的文化需要,一本书,还不如一杯牛奶,或者一杯名字叫星巴克的牛奶或者咖啡,这就是消费意识。现在,明君书店已经被一家韩国餐馆取代,当初门可罗雀的书店,现在被人头攒动的餐馆取代,说明什么呢,闸北中产阶级的胃正在被中产阶级化,他们正在追求韩国中高档的牛肉、大酱汤,而他们的头脑,却似乎并不需要一本书来填充,尽管这里的一片牛肉要比当初十本书的价格还要昂贵。
在这个破产书店的幻象之上,是一家中日合资的YOUNG(游歌)KTV,在这里唱一首歌,相当于消费一本书,但是如今这里也是人头攒动,KTV被中产阶级选择消费,而图书却没有,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填饱了肚子的中产阶级们,踏着电梯而上,踏上他们的精神之旅,走向由模仿、噪音、啤酒、拥抱、吼叫、昏暗的灯光,跪式服务组成的KTV,来这里享受精神的放松和所谓的快活,前文已经说过,中产阶级消费不仅仅是实质性的物质,比如食品和服装,更需要由此带来的舒适、舒服和感受,他们可以躺着看电影,享受视觉盛宴,或者闭着眼唱歌,但不可能埋头阅读,如果你在大宁国际看见一个埋头阅读的人,那除了路边的雕塑,是决不可想象的。但是,大宁国际的组织者、安排者、中产阶级消费的总导演,如果他存在的话,却又是绝对不会在这里安置这样一尊雕像的。关于舒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所谓的精神消费场所,电影院。这里的电影院,跟别的地方的电影院有什么区别呢?离它一千米就是沪北电影院,沪北电影院和这里放的电影是一模一样,然而沪北电影院放的29元的电影到这里变成了80元,中产阶级对这里的电影趋之若鹜,沪北电影院的座椅却空空如也,精神的消费,也被分成了档次,仿佛沪北电影院的《蜘蛛侠》就不是《蜘蛛侠》了,只有在这里才是真正的《蜘蛛侠》,中产阶级为此多花掉的几十元的人民币,给他带来的又是什么呢?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内容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他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也非根本无所谓的关系,是好奇心的关系,消费的尺度,不是被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是缺乏了解的尺度,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的大量的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⑤。中产阶层在大宁国际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作为中产阶级的自我身份符号,这个符号是跟无知、不了解、缺乏认识、无根本关系相联系的,从根本上说,他多花的几十元,是支付给自我的,他付钱给大宁国际,向自我购买了中产阶级这个身份证,而这个身份证,就类似于鲍德里亚所说的符号。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大润发,大润发被安排在这个区的西北角上,他的南面靠着大宁福朋喜来登酒店,大润发每天吞吐着数千的人流,步行来大润发购物的人必须从东南角的地铁口下,假设同时一个真实的闸北的原始的消费者,他步行穿过大宁国际的时候,沿途看到的诸种景观,会对他构成怎样的影响呢?橱窗里的模特们,对着他搔首弄姿,使他惊诧莫名,各式店铺门楣上的英文店标,使他羞愧难当(也许他是一个工人,不认识英文字母),头顶上的莺歌燕舞,脚下的斑斓多彩,这一切构成了一座标准的中产阶级大学堂,这是一场严重的心灵锻打,当他真的走到大润发门口,在底楼他看到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物品,而是中产阶级典型意味很浓的东西,中高档化妆品、体育用品、奶油,当他来到真正的生活用品地区,他的手在那些必需品当中,该如何选择呢?他已经不敢伸向他真实需要的洗发水、馒头、青菜,他的手经过一路的锻造,必然离开他头脑的控制,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手。
这就是这些商业符号下面隐含的文化潜规则,它给了你一个商业档次的“定位”,“中产阶级定位”、“中高档”消费区,“白领消费区”等等,都是“符号”,给消费者做身份定位的文化符号,来此消费的人通过这个商家定位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而这个自我暗示和认识,和他来到此处,到底买了什么,用什么价位买,等等,一系列实际消费中发生的问题,毫无联系。“中高档”的认同,在闸北如何可以行得通?难道仅仅是因为闸北原来没有所谓的“中高档”消费区?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到底在闸北消费文化的中高档化过程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呢?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消费水准远没有达到它自己所标榜的所谓“中高档”的地步,大宁国际所引进的大多数品牌并不是国际知名一线品牌,而是二线大众消费品牌,从大宁国际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大宁国际,与其说,它带来了闸北消费水平的真正的中档化、高档化倾向,还不如说:它带来了中高档的消费文化符号,它充当了闸北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代言人、宣教者角色。在闸北的消费者内心植入了“中产阶级”中档、高档消费的自我意识。而这,正是大宁国际商业广场成功的奥秘所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出售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关于中产阶级的身份意识,你来到这里,仿佛就领取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身份证明。
四、休闲与自我呈示
闲逛者,或者叫休闲者,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像中》一文中曾提出这一概念,波德莱尔把“他”看作是一种现代人类型,用他来解释一种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的生活类型。本雅明非常敏锐地抓住了波德莱尔的这一现代发现,用他美妙的语言描述了休闲者的身份及行为特征,“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家乡颂歌,而是这位寓言者凝视巴黎的目光,一位异化者的目光。那是休闲逛街者的凝视,这些人给正在到来的大城市那种令人生厌的生活方式洒上一抹抚慰的光彩。休闲逛街者依然还站在大城市和资产阶级队伍的门槛上。二者都还没有使他真正愿意进入,二者也都还不能让他感到自在,他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避难所。……人群是一层面纱,透过这层面纱,熟悉的城市如同幽灵般向休闲逛街者招手。在这个幽灵的召唤中,城市时而变成一道景观,时而变成了房屋。”⑥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同时都意识到了闲逛者进入人群,进入都市,他是都市生活的体验者,他们凝望着市场;好奇地打量人群、商品;享受着被人群簇拥;陶醉于被都市世相抚慰;震颤于对周遭的观看。是的,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看到了这群没有具体目标的买者,并给了他们命名,但是显然他们直观的、自以为是的披上了都市游离者、远观者、批判者的标签。
与我们在大宁国际看到的景观想匹配的是另外一种景象,这种闲逛者,休闲者,完全是被大宁国际怀胎、孕育生产出来的,大宁国际是一个巨大的孕妇,她的子宫里孕育、诞生着这样的一个中产阶级。其实,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看起来首先不是一个消费场所,也就是不是一个让你购买,让你吃喝的地方,而是一个让你来闲逛,无所事事的地方,他首先给你的,是让你在这里打发时间的这样一种意识,只要你来这里,只要你有时间来这里,有能力把你的时间泡在这里,你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就证明你是她的婴儿,你是她宠爱的人,然后,她才要求你打量她,用你休闲的眼睛,无所事事的头脑和那些搔首弄姿的商品,做一次调情式的交流,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宁国际,没有任何东西是催促你支付钱币,或者背着商品回家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挽留你,款款地邀请着你,无论是舒适的四星级的酒店的大门廊和它的宽阔的大厅,还是那些咖啡店,餐馆,舒适的、闲适的座椅,更不用谈他宽阔的人行步道。步道两边张着的遮阳伞和休闲座椅,仿佛像情人的怀抱,他们都在期待你在其中滞留,成为一个所谓的休闲者。
勤劳的美德,被阻断在街对面。一条高架路割断了上工新村和这里的视线,当你的脚跨过高架大牌的下缘,从高架的阴影中走出,步入大宁国际的时候,你已经被标上了中产阶级悠闲者的身份,他首先问的是,你有时间享受生活吗?大宁国际入口处,父亲、母亲带着孩子在水中栖息的塑像,隐隐约约,展示这里的豪华电影院的一角,高档男性SPA的广告,泰式按摩的招贴,都把休闲跟舒适微妙地结合了起来,这里你消费了你的时间,这是前提,而消费得起时间的人才是富翁,才是现代都市里的合格公民,经过大宁国际不算漫长的子宫,当你离开他的时候,你成了他的中产阶级的儿子。
波德里亚认为休闲已经成为文化符号和被消费的对象。休闲,被彻底地裹挟进大众消费之中,成为中产阶级不可或缺的身份符号,他把作为物质实践的消费,他把大众的生存消费,和中产阶层的身份消费区别了开来,休闲使你高贵,是你身份的象征,为什么大宁国际商业后面要加上“广场”二字,广场,商业广场,多么美妙的字眼!过去我们只会把广场和政治、市民生活相定义,现在大宁国际把商业加在了广场前面,广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宽阔的视野,意味着天空、大地,意味着自由、肆意,大宁国际的自我命名难道是无所指的吗?我们可以分析一系列大宁国际的照片,免费的表演,天天都有,你可以在这里驻足,免费的椅子、凳子处处都有,你可以在这里坐下,请把你免费的时间回馈给大宁国际,这个自称广场的神秘人物,因为他已经把休闲这个消费符号,深深地根植在了闸北,这个劳动者聚居的区域,这里以前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聚居区,整个上海的下只角,这个以上工新村为样板的区域,如今由大宁国际带来了新的生活范式,不是劳动,而是休闲才是美德,不是流汗,而是无所事事的闲逛,不是流汗,而是在商业广场里闲逛,才使你有价值,休闲随着大宁国际来到了闸北的生活的中心,如果说大宁国际的商业广场是闸北的新地标,那么这个地标的名称叫什么呢?休闲。
勤劳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闸北大众,以劳动为美的闸北底层大众,他们的意识逐渐地被重新塑造:不是劳动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而是消费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不是上班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而是休闲使他们的生活有价值。“闲逛者”在本来是作为“现代生活”的批判者、游离者被发现和塑造出来的,但是,在大宁国际,我们发现,这种资本不仅仅生产它所需要的阶层意识和行为,而且还生产自己的“对立面”——它最大的诡异逻辑是:它不仅制造了自己,还制造了自己的“敌人”,它具有把“敌人”转换成自身的促进性因素的能力。
五、“家庭”与“国际”:小和大的直接接轨
消费时代的生活核心由生产向消费转变,由劳动向休闲转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家庭的地位和意义提高了:人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意义也得到了提升。
这种观念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设计与运营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很难想象一个以工作为全部生活内容的人,一个以工厂为家的人,一个丝毫没有挣钱是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愉快、富足的观念的人,他会热衷于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地方。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家庭观念,不喜欢和家人共度周末的人,会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地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它在灌输一种中产阶级家庭幸福生活的理念——一家三口,周末携手,逛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中说道:“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幸福的降临。问题不在于从中看出分析的原则。他只是关系到个人和集体的消费心态罢了。”⑦从中我们看到,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通过其商业行为,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消费观念,还塑造了人们的人生观念。何为“幸福”?拥有休闲的时光,和家人共度周末——这才叫享受人生,才叫幸福人生,这样的人是成功的人,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商业文化不仅仅满足于在自身的范围内起作用,它还试图深入消费者的整个生活,改造消费者的整个生活。表面上看,商业消费是适应人的需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但是,本质上,我们却看到商业消费制造着需求,不仅仅制造了对物(消费品)的直接的需求,还制造了对生活的模式、样式、体式的新的需求,一种全新的对于生活的理解。
如果不深加追究,我们会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中间“国际”这个词怀抱疑问,为什么要加上“国际”这个修饰词呢?它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商业文化”意味的建构中到底承担了什么功能?比如:英文标签的使用,差不多全部商家使用英文(或者日文等外文)标签、广告,或者他们的LOGO、广告等,英文占大幅面,主体地位,而中文仿佛是为英文做注解的,占小幅面、附属地位,何以如此?首先,它是出于消费者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它告诉你,它是为有文化的能识别英文的人服务的,你来到这里就是有文化的人,它的潜意识中恭维着你,进而维护着你“我是中产阶级”、“白领”的身份意识。它和电影、体育、音乐等——文化消费元素被引进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作用是一样的,只是它更为隐蔽。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人来消费,比如,前文说的书店关门的例证就能说明问题,但是,这里的外观,却让你处处觉得,你是有文化的。这里实际是大众的消费,但是,它制造了是文化精英的消费的幻象。其次,大宁国际的命名,为什么其中有“国际”?它符合闸北人新的欲望,一种把自己和世界联系起来的欲望,一种把自我安置在“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在“闸北”的欲望,这种欲望潜在于闸北人的内心,过去通过政治运动、政治话语表达出来的,现在,则通过消费直接实现——每个细节都在呈示这种欲望及其满足,“你所买的是国际品牌!”“你所得到的是国际的服务!”国际品牌的引入、服务方式的“国际”化(英语的使用,外国侍者的使用,侍者服装的国际化等等)。人们内心总是隐含着把自身“小”的生活和某个更“大”的东西联系起来的冲动。占有了某个大的理念,从这个理念获得意义和价值,形成自我肯定。以前这些是通过政治来完成的,现在商业消费行为取而代之。闸北人作为下里巴人的自我意识,作为下只角的自我意识通过这种“国际”化而被洗刷,通过这种“国际化”,他们仿佛进入了国际大家庭,不再是被抛弃的穷人、弃儿,而是国际大家庭中非常了不起的一员。我们可以看到,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中外语教学机构有英芙教学、雅思教学等等,不下五六种,有成人的,更有儿童的,中高低档样样俱全,充分地显示着大宁国际广场对外语的热衷,酒店如喜来登,准五星级具有“国际”品格连锁店的命名,大宁国际着意引入国际品牌:星巴克、A&C、哈根达斯,等等,这些都在塑造着闸北人新的自我意识:来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你就不再是下里巴人,下只角人。
消费行为是政治性的,或者说是过往政治行为的代偿,2000年随着上海许多副中心建成,这种行为被大大加强。人们在不同时代面临不同的历史情境,传统政治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比如:阶级的割裂,国家关系的对峙,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对峙,等等,都在改变,以90年代为分界线,至2000年后,上海形成了商业消费行为对过往政治行为的压倒性代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在生活中的地位衰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代偿性的活动,消费在其中居于主导性的地位。
换而言之,消费是政治活动的延伸。在消费行为当中,某种消费行为完成自我聚集、自我塑性、自我认同、自我维护等等这样的行为,在消费行为中会产生权利关系,个人意愿,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表达,也会受到某种集体性的压制,在消费当中也存在制定策略,执行策略,而这些策略会涉及到社会利益,这种利益也会产生某种权威性的再分配。消费行为也跟传统政治有某种程度上的勾连,比如广场行为,在广场上聚集,通过聚集仪式性的表达需求、意愿。大宁国际商业广场,也是广场,在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消费行为和在人民广场进行的集体政治行为有相似性,可以形成代偿关系。再比如说身份认同,不同的消费场所,不仅是消费对象的不同,更是消费者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何谓中高档呢?首先是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或者是社会高层,中高档的消费场所是中产阶层或者高层自我身份认证的场所,包含某种身份政治的含义,这是不言自明的。再比如欲望的表达和实现方式,政治行为是表达欲望的方式,实现欲望的方式,消费行为实际上也是这种表达和实现,而且这种实现是仪式化的,没有意识就没有展示,政治欲望的实现是通过意识行为展现给其他阶层看,消费行为也是如此,消费行为的结果往往会直接变成展示,比如,购买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以后就会变成展示,身份展示,吃饭的时候不仅味觉、嗅觉在起作用,同时面对服务生的身份感也在产生消费,向服务生,向同桌展示自己的吃、喝,这也是消费的一个部分,这里隐含的逻辑,是政治性的,具有对以往政治关系的代偿作用。星巴克的消费和茶馆里的消费完全是不一样的,对消费区别的理解包含着某种身份上的政治意识。
本文的结论是进入2000年以后,上海人生活的核心行为不再以传统狭义的政治行为为中心,新的代偿物是“消费”,消费对政治起到了代偿作用,政治广场变成了商业广场。以生产为中介,以政治灌输为中心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让位给以生活为中心,以消费为中介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策略。以往政治时代的变成了对消费国际品牌,占有全球高档品牌消费品的欲望。展示政治立场转化成了展示消费观。寻求政治身份的认同(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变成了消费(中产阶层、新贵阶层、底层的自我暗示和向他者的展示)。大宁国际的产生,应该在这个背景当中加以认识。
大宁国际何以是国际的,何以必须是国际的,中国人的国际观一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传统儒家视野当中的蛮夷观,汉族巨大的人口优势、文化优势产生了中央大国,天子为中心,天子统领天下,外及四海,华夏既是种族概念,又是民族概念,蛮夷同样如此,这个观念一直持续到晚清,真正改变这一观念的是晚清社会,西方力量的介入,使我们感受到文化优越感丧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地位,开始丧失。五四时期的西化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上产生的。再次培养优越感的时候,已经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把世界分成东西对峙的两个世界,用阶级关系的转化,用阶级关系来隐喻世界关系。毛泽东把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用阶级关系的隐喻性语言,嫁接到中西关系当中,用暴力斗争的价值观隐喻国际政治,重新塑造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体关系,极大地激发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政治热情,自我意识膨胀,爱国和爱世界被同构起来。
在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人们能通过信仰建立自身和上帝的联系而不需要国家中介,这种过程当中人产生了和上帝勾连的自我意识,上帝是权威、裁判、意义的源泉,价值的基础,通过它人们获得自我认可,人通过上帝和伟大、威权、理念联系了起来,自我的渺小、短暂从上帝的永恒、博大里得到了缓解,渺小变得永恒,虚无得到了意义。但是在无神论国家,人是没有这种心灵慰藉的,找不到这种心灵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人渴望在现实的生活中和“世界”建立联系,个人和世界全体联系起来,从中发掘意义,个人行为通过这种主观关系获得“世界性”、“普遍性”,获得“意义”,这其实是人和上帝关系的一种代偿。80年代以前国家政治还可以提供这种关系慰藉,人们可以从中找到自我认同,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上海社会的崛起,传统政治不能再提供这种慰藉,比如解放全人类的观念,比如制度优越的观念等等,已经不能提供慰藉,代之而来的是另外一种国际观,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使我们产生了我们是全球或者世界的平等一份子的意识,改革开放初期,因为贫穷而产生的国际自卑感逐渐消失,随着中国产品国际热销,中国介入到国际分工当中,出口产品也换来了世界上他国产品的转入,中国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际主义的存在,感到了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这种国际主义的意义,也就是大宁国际事实出现的原因,大宁国际适应了大众通过消费把自己和世界联系的愿望,捕捉了这种愿望,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愿望。
以“休闲”、“舒适”为核心的生活文化取代了以“劳动”、“牺牲”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社会世俗化进一步加剧。随着商业社会的不断建构,消费主导生活而不是政治主导生活的状况带来民众由“人民”向“公民”的转变,过往集体经济模型去魅,国家政治对市民生活的干预度、切入度开始下降,市民更多地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的身份,而是主动地寻求自己的身份,市民不再更多地从政治理念出发寻求、组织自己的生活理想、生活风格、生活模式,而是从经济和消费行为出发,在国家不干预的部分寻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领域,他们变得更加自治,能够自造共同的社会观,具有共同的行为模式,他们更相信“自律”、“自治”,对国家政治的干预抱怀疑的态度,他们开始脱离“国家政治”的领域,组织起了“自己的市民政治”——消费的政治,自主地确定了目标,自主追寻着目标。在中国,非政府组织还不发达,集社、集会还不那么容易,取而代之的是市民的消费行为——在消费中他们完成了自我的政治组织、政治教育、政治行为,一种由人民而公民的文化转型和自我身份的塑造。
中产阶级意识的崛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在沪北的成功带来了中产阶级意识在这一地区的落户、生根、发展。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商业景观造就着休闲、舒适、娱乐、国际、文化等具有中产阶级“身份”意识的特殊文化,在其迷惑的外表之下,“下只角”正逐步甩掉过去的自我意识(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自我意识),而建构起一种“中产阶级”的自我观念。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大宁国际商业广场这样的商业景观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贝斯特曾说,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从我们对大宁国际商业广场的“视觉文化”分析,我们觉得贝斯特的观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注释:
①《景观社会》,[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②《景观社会》,[法]居伊·德波著,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③《让·波德里亚文选》(英文版),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④《消失的技法》,[法]让·鲍德里亚著,选自《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
⑤《消费社会》,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瓦尔特·本雅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80页。
⑦《消费社会》,[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标签:消费文化论文; 中产阶级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大宁国际论文; 上海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商业论文; 大宁影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