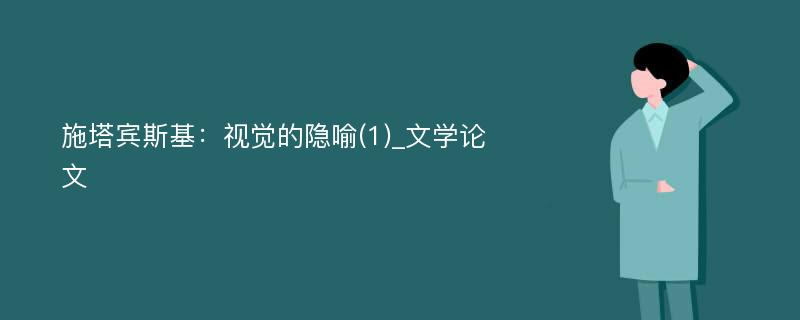
让#183;斯塔罗宾斯基:目光的隐喻(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塔论文,目光论文,罗宾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让·斯塔罗宾斯基“是日内瓦学派中对人文科学态度最为开放的成员”,(注:让—伊夫,塔迪埃《20世纪的文学批评》,贝尔封出版社,1987年,第100页。)同时,“让·斯塔罗宾斯基是我们时代的最具文学性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本身就具有文学性”。(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科学性与文学性的结合,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境界。这在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身上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一
1984年7月,让·斯塔罗宾斯基接受雅克·博奈的采访,针对批评者与作者合一、一个真正的批评家是“作者的二次方”的问题,回答说:“是的,当他放下笔的时候。而诗人,当他写下第一个字的时候,他就是作者了。批评家一上来就把他的言谈诗化了,可能导致完全的失败:他将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批评家。(我这里说的不关乎诗人从做诗的经验出发写的批评文章。)使得帕诺夫斯基的某些研究或者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还有其他例子可以指出——如此之美的,是研究工作都是通过严肃和谦逊来完成的。(批评之)美来源于布置、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论据的丰富与可靠,有时也来源于猜测的大胆,这一切都不排斥手法的轻盈,也不排斥某种个人的口吻,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不应该事先想到这种‘文学效果’:应该仿佛产生于偶然而人们追求的仅仅是具有说服力的明晰……我主张简洁,而非乏味和中立。如果人们反对我,说我在这里确定了一种批评的美学,说我要求批评文章使自己无迹可寻,只通过其表面的遗忘来显示它的诗的性质,那我无话可说。只有意思的追寻使作品走得尽可能远的时候,这种批评的美学才能施其技,非如此我亦无话可说。意思的追寻,服从于意思(尚需寻找)的权威,这是一项工作,说它是道德的并非自命不凡。这是一个先决的要求。在此之后,如果批评工作产生了一部作品,而这部作品被认为是美的,那再好也没有了。”(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
20多年前,乔治·布莱出版了《圆的变形》,让·斯塔罗宾斯基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序的开头这样说:“某些思考或批评的学术性著作在读者的理智上唤起一种精神之美的感觉,这种美使它们与诗的成功相若。它们具有一种唤起的能力,一点儿也不让与最自由的文学语言。它们源于同一种自由,因为追求真理而尤为珍贵。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是最好的例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诗的效果越是不经意追求,则越是动人。它来自所处理的问题的重要性、探索精神的活跃和经由世纪之底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的宽度。它来自写作中的某种震颤和快速的东西、连贯的完全的明晰和一种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的想象力。它从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和新颖上、从其内在的美上、从其所来自的阅读空间的宽广上所获亦多:在乔治·布莱的目光为了写作这本书而问讯的文化景观中,文学、神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语言的分别被忽略了,每一个作者都首先在自己的语言中被阅读。法国(和法语瑞士)、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提供了互相说明的伟大例证,在思想的统一的秩序中遥相呼应。被探索的领域——不存在任何系统和彻底的奢望——几乎是西方的全部文化领域。”(注:让·斯塔罗宾斯基《圆的变化·序》,弗拉玛里庸出版社,1971年版,第7-8页。)
这两段话,相隔20年,一是口头上的,措辞文雅,但不那么严谨,一是文字上的,用语明晰,并显得非常精练。话语不同,然而表达的思想却是那么一致,丝毫没有扦格矛盾之处。把这两段话加起来,我们就有了关于批评之美的完整的论述:明晰,简洁,深刻,精神的自由,问题的重要,丰富的论据,广阔的联想,轻盈的手法,于不经意中达到诗的或文学的效果……
这就是批评之美,这就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一种洋溢着“博学的诗意”(注:斯塔罗宾斯基语,见伊夫·博纳福瓦与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谈话,载《瑞士法语文学》,2005年7月1日。)的批评。
批评或学术性的著作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精神之美的感觉,其来源是精神的“自由”,这种自由“因为追求真理而尤为珍贵”。它不受某种意识形态的指使和束缚,纵横捭阖皆出于求真和求美的动机。一句话,“意思的追寻”控制着批评的道路。斯塔罗宾斯基最为推崇“随笔”——“最自由的文学体裁”,推崇随笔的“宪章”,即蒙田的一句话:“我探询,我无知,”并指出,惟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总而言之,“从一种选择其对象、创造其语言和方法的自由出发,随笔最好是善于把科学和诗结合起来。……它无论何时都不应该背弃对语言的明晰和美的忠诚。”批评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苟如此,我们就可以“给予文学随笔、批评、甚至历史一种独立的创造所具有的音色性和圆满性”。(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
批评家要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批评家能否怀着严肃和谦逊的态度来从事研究工作,决定了他的研究的面貌。“严肃”意味着平等,“谦逊”标志着钦佩。倘若批评家高高在上,或取“臣服”的姿态,必不能与批评对象形成对话的态势。或者,批评家率尔操觚,不能以钦佩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他的研究必然是一纸纵情之作。也就是说,有去无回,有来无往,批评家不能把批评对象当作交流对象。没有交流,则成死水,文章而为死水者,必少洄流九转之形,且乏鼓荡澎湃之象,亦无吹嘘吐纳之气。有对话,有交流,则成活水,文章而为活水者,则澹澹乎,渺渺乎,浩浩乎,无不成佳构。当然,这种“诗的效果”或“文学效果”不可强求,亦不可故意或刻意而为,否则会适得其反:“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批评家”。
批评家要顾及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论据的丰富、新颖与可靠。问题的重要不仅与原作有关,而且与批评展开的远景有关。问题本身可以不重要,但是它可以引发重要的问题,仿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向问题的道路要勾画清楚,勿使如逸马般狂奔,不知所之。论据不但要丰富、新颖与可靠,而且要巧于安排、布置,引人入胜,并能引类连譬,诱发读者的联想,有举一反三之功。所谓“连贯的完全的明晰”指的是论据,论据的安排布置要简明无碍,大路小路,纵横交错,然而都指向一个所在,令读者一眼便能看出,有明晰之乐。批评要说理,提出重要的问题;论据要充分,使问题的阐明达到自足的地步。总之,问题与论据要环环入扣,互相照应。
批评家还要注意探索精神和想像力。探索精神不仅在于对原作意义的寻觅和追问,而且在于对原作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进行开拓,以达到新的深度,给读者以新的启迪。没有探索精神的批评是枯燥乏味、死气沉沉的批评,等而下之,则是原作的干巴巴的重复,这样的批评不做也罢。想象力不仅能“使抽象思想活跃起来”,而且能够使批评所提出的一切观点具有生命力,它像一道光,照亮了它所经过的各种凹凸。它是波德莱尔所说的“洞观者”的能力,或者巴尔扎克所说的“第二视力”,使批评家的著作具有穿透力,即所称极小所指极大的那种能力,超越眼睛之所见或者纸面之所写而看到所言或所写背后的东西,从而具有某种文学意味。
批评家也不可忘记某种“个人的口吻”。个人的口吻来自“手法的轻盈”,来自“写作中某种震颤和快速的东西”,也来自语言,来自他对事物的独特的观察角度。角度不同,语言自然不同。语言不同并不在于选用的语汇不同,更多的在于语言结构的不同,而语言结构的不同则在于词语的搭配不同。词语搭配不同,则语言显示出异样的光彩。有人以为,个人的口吻之独特得力于刻意的追求,这是舍本逐末之辞。口吻的独特并非故意与人不同,而是不同角度的观察决定了表达的选择。有所选择,则出奇焉。口吻既然是个人的,就必然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性是不能刻意寻求的,它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所以斯塔罗宾斯基才说:“这种个人的口吻越是不寻求独特就越是动人。”
批评家更不可忽略“阅读空间的广阔”。阅读空间的广阔或狭小直接影响着批评的肢体之丰腴或瘦弱。肢体丰腴则内容深厚,流转雍容,行动宽松,望之光彩照人,举凡文学、历史、哲学、神学、心理学、甚至医学等学科的材料奔来笔下,任其驱遣,得车轮大战轮番轰炸之效;肢体瘦弱则气血不调,捉襟见肘,展转不灵,望之灰头土脸,行文学批评者文学学科的材料尚不能运用自如,遑论其他诸种学科。所以,阅读空间的广阔,是产生大批评家的必要条件。
批评家要使自己的文章“无迹可寻,只通过其表面的遗忘来显示它的诗意的性质”。批评家阅读作品,经过忘我、研究、思考等一系列过程,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方能组织文字,安排结构,调动知识储备,准确地表达观点,最后形成一篇文章。然而,在高手做起来,一切艰难险阻都被高超的技巧化尽,仿佛云彩在清风的吹动下舒卷自如。否则,满目创痍,凿痕累累,即便体大思精,也说不上好文章。所以,斯塔罗宾斯基谆谆告诫:“应该善于消除用力的痕迹。”(注:见伊夫博纳福瓦和斯塔罗宾斯基的谈话,载《瑞士法语文学》,2005年7月1日。)
当然,批评也不拒绝“猜测的大胆”、“手法的轻盈”、所引证材料的“内在之美”、“勾画清楚的道路、次第展开的远景”,而这种“道路”是“通向我们时代的道路”,等等。
总之,批评之美不是批评的外在的装饰,单纯的词藻不能造就批评之美。批评之美是批评的内在表现,是批评家素质的外化,是其阅读空间的凝聚,是其运用语言的能力的考验,是其洞察世界的眼光的展示。一句话,批评之美是批评家的心灵的再现。然而,这一切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先决的要求”,即“意思的追寻,服从于意思(尚需寻找)的权威”,舍此则批评之美失去了根基。
“意思的追寻”是让·斯塔罗宾斯基所主张的批评活动的根本目的。他的批评是“自由”的,更是“追求真理”的,因而也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他评价帕诺夫斯基、布莱等人的词语,正好说明了他本人的批评:他的批评具有真、善、美的素质,因而具有文学的属性。
二
在日内瓦群体的批评家中,让·斯塔罗宾斯基是最向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甚至医学科学开放的批评家,也是最讲究方法论的批评家,更是一位最灵活、最善于兼收并蓄的批评家。他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集中在《活的眼》和《批评的关系》这两部著作中,后者又名《活的眼二集》,这说明,他始终把文学批评看作一只有生命的眼睛。
让·斯塔罗宾斯基最初在文学批评上的贡献是创立了一种“注视美学”,也就是说,他关于注视的主题学研究最终超越了主题学,使他形成了一整套别具风格与特色的文学批评的理论。
注视是存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文学批评的主题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它集中而强烈地反映出人与人、人与自己、人与世界的关系。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实践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人这个主体,从各方面探索人的意义;同时,注视毕竟隐含着注视的对象,即看什么,看到了什么,其中有注视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存在,因此,他对“注视”这一主题的关注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主题学的兴趣,直接通向一种批评的本体论。也就是说,让·斯塔罗宾斯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观。
斯塔罗宾斯基关于注视的研究是从语文学和语义学开始的。他与当代许多标榜先锋的批评家不同,从未把语文学和语义学在文学批评上的作用视为过时,而是将其作为一切阐释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他指出:“语文学致力于检验文本,根据语境或当时的用法审核词的意义,揭示词的前身,了解文类、通行用法、诗意和修辞的历史,判定特殊的言语和平常的言语之间的差异。无论是语法的理解,还是历史介入的定位,都有一个阅读的不可避免的先决的工作,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根据语言学的、符号学的或者实用主义的描述系统重新表达并焕然一新的工作——这是更加形式化的语法和修辞学。”(注:《时代/斯塔罗宾斯基》,蓬皮杜文化中心出版,1985年,第180、17-18、196、11页。)因此,语文学和语义学的工作乃是任何阅读不可回避的先决的工作,而种种的新方法未尝不是传统语文学的“精细化”的表现。斯塔罗宾斯基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时候,适逢他的同事乔治·布莱和列奥·斯皮策进行激烈的争论。布莱拒绝形式的研究,力主认同批评,而斯皮策则在文本的语言和风格中寻求意义,斯塔罗宾斯基没有偏袒任何一方,却同时为他们的著作写了序言,一本是乔治·布莱的《圆的变形》,一本是列奥·斯皮策的《风格研究》,这种居间的立场很说明问题,它至少告诉我们,在斯塔罗宾斯基的眼中,语言和风格的研究对于文学批评来说是多么重要。
列奥·斯皮策1887年生于维也纳,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在文学批评上提出了文学风格学,或称风格学批评,与卡尔·沃斯勒并称学派的创始人。风格学批评创始于20世纪初,风行欧美,在美国影响最为巨大。从整体上说,风格学批评以研究具体的言语事实为任务,在其全部语境中评论文学作品。列奥·斯皮策在卡尔·沃斯勒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提出了一种建立在作品的风格特征之上的批评,弥合了传统的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分野,深入作品的中心,在作品的语言形式即风格的独特性之中寻求理解作品的钥匙。他的具体做法是:1.批评内在于作品。风格学要以艺术作品而不是以外在于作品的因素为出发点,并提取出它自己的范畴,承认任何作品都是惟一的,与其他的作品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2.任何作品都是一个整体,在作品的中心能够发现创造者的精神。“作者的精神是一种太阳系,一切事物都在它的轨道上,都受到它的吸引。言语、情节等等都是这种整体的卫星,这个整体就是作者的精神。”3.任何细节都能使我们深入作品的中心,因为作品是一个整体,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必要的。一旦进入中心,人们就会看清楚所有的细节。正确地观察到的细节会使我们得到理解作品的钥匙。4.人们通过一种直觉——这种直觉是可以通过观察和推断加以验证的,——通过一种由作品的中心到作品的边缘之间的往返运动来进入作品。这种最初的直觉“是天才、经验和信念的结果”。5.经过这样整理重建的作品融入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作者的精神因此反映了民族的精神。6.这种研究是风格学的研究,它从语言的特征中获得了出发点。7.特征正是作者个人的风格,是一种对于标准的语言用法的偏离,语言范围内的任何偏离都反映了另一个领域内的偏离,例如文学的领域。8.风格学应该是一种同情的批评,作品是一个整体,应该在它的整体上、从其内部来体会理解它,应该对作品和作者抱有完全的同情。(注:以上资料取自彼埃尔·吉罗著《风格学》,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71-75页。)在斯皮策以后,在欧洲,尤其在美国,出现了大量的类似的研究,史称新风格学或风格批评。1970年,斯皮策在法国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他除了博士论文外,没有写过专著,八百多篇论文皆以论文集的形式用德、法、英、意、西等文字出版)《风格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让·斯塔罗宾斯基为之写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说:“列奥·斯皮策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纯粹的语言学。这种纯粹的语言学对他来说具有中心的、战略性的地位,是一种‘源知识’。正是因为这种语言学对他来说具有这样的性质,他才觉得它不应该禁锢在专门的范围内,这种范围是学术性的分类的一种偶然的反映。语言学是一种与意思有关联的形式的科学,具有诠释的功能,在任何有言语需要阅读、有意思需要辨认的地方,它都可以介入。”(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风格论·序言》,第10页,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第10、19、30、38-39页。)这句话的意思是,斯皮策解释文本时是从语文学出发的,他在语言学和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斯塔罗宾斯基指出:“看到相对于通常用法的风格上的差异,衡量这种差异,确定其表达上的含义,把这种发现和作品的口吻、总的精神协调起来,因此更广泛地确立创造天才的特性,通过他,再确立时代的倾向,这就是斯皮策的批评开始时的运动。”(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风格论·序言》,第10页,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第10、19、30、38-39页。)斯塔罗宾斯基勾画出斯皮策的整个认识过程:从对一个文本的整体意思的暂时理解出发,然后研究一个个表面上处于边缘的细节,运用一切科学的和直觉的知识的资源,把阐明的细节与预感到的整体相对照,找出其间的含义,寻找证实逐渐变得明确的意义的把握的新细节,不忽略可能出现的异议和怀疑,始终警惕着不使分析活动服务于偏见。这就是斯皮策所喜欢的诠释活动的全过程:“由整体到局部、由局部到整体的往返,其间确立了一种文本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的明晰,这种明晰任何仔细的阅读都隐约地看到了,但是由解释的功能渐渐地明确起来。”(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风格论·序言》,第10页,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第10、19、30、38-39页。)最后,他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了他的序言:“一个永无止境的行程,通过一系列不可确定的循环,在既是他自己的又是其对象的历史中呼唤批评的注视:这无疑是这种没有尽头的活动的形象,其中投入了理解的愿望。理解,意味着承认永远理解得不够。理解,就是承认一切含义都悬而未决,只要人们还没有完成理解自身。”(注:让·斯塔罗宾斯基著《风格论·序言》,第10页,伽利马出版社,1970年,第10、19、30、38-39页。)斯塔罗宾斯基对斯皮策的批评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正如法国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所说:“他(斯皮策)集直觉与推理、博学与敏感于一身,既是人文主义者,又是结构主义者。这种批评基于一种美学:艺术作品形成一个整体,其形式和内容融为一体,与生活相分离(文学的马不是一匹真实的马,文学中的钱不是生活中的钱),正因为这种分离,它才能影响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斯皮策摈弃了与作品无关的生平阐释、消解作品的观念分析和使一切美学判断不起作用的、扰乱艺术家工作的根源批评。语文学的谦逊的实践的最大教益在于只对作品、只对个人的作品的忠诚之中。”(注:让—伊夫,塔迪埃著《20世纪的文学批评》,彼埃尔·贝尔封出版社,1987年,第68页。)斯塔罗宾斯基正是从斯皮策的批评实践出发,吸取了语文学的谦逊的品格,以自己的博学、推理、直觉与敏感为利器,从语文学入手开始了自己的批评。他对批评的最初的贡献,是建立了一种“注视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