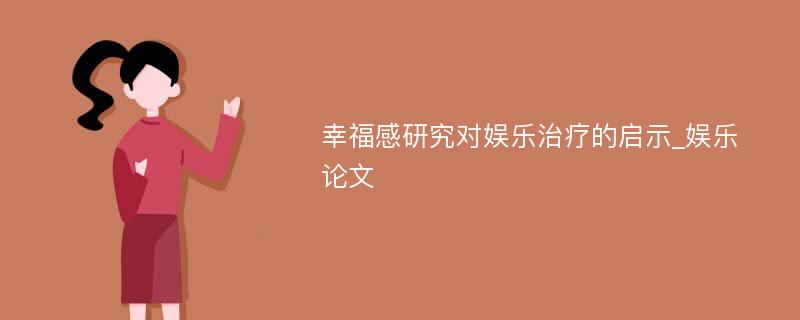
幸福感研究对娱乐治疗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疗法论文,启示论文,幸福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7)05-0123-07
娱乐治疗是指为病人和残疾人提供治疗服务和娱乐服务。治疗服务经常被看做是娱乐治疗,它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患者重建、补救或恢复某种能力,进而提高他们的机能和独立性,同时降低或消除疾病和残疾带给他们的不便。娱乐服务的主要目的则是提供娱乐资源和机会进而提升他们的健康和幸福感[1]。娱乐治疗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四五十年代[2],之后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次革命[3]。第一次革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飞速发展。主要表现为职业组织的飞速发展。1948年第一个职业组织医院娱乐部(Hospital Recreation Section,HRS)成立,成员主要是军医院和退役军人管理医院的工作者,他们认为娱乐就是一切;与此同时,国家精神病院和社区弱智学校的工作者成立了一个与之相对的组织——国家娱乐治疗家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creational Therapists,NART),他们认为娱乐只是治疗的一种干预策略或手段;1952年,一些热衷于体育活动的学者成立了一个规模更小的组织——娱乐治疗部(Recreation Therapy Section);1953年,这三个组织相互联合成立了医院娱乐发展委员会(Council for Advancement of Hospital Recreation)试图探讨三者的共同之处;1966年国家娱乐治疗会(The National Therapeutic Recreation Society,NTRS)成立,它正式将之前不久出现的“娱乐治疗”(therapeutic recreation)这一专业术语确定下来,试图将之前各组织对娱乐治疗概念的争议统一起来。
第二次革命是娱乐治疗职业的专业化发展,它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在60至80年代得到加速发展。它主要体现为:(1)职业结构特征的描述,包括专职工作人员、博学、受过大学训练、合法、成立了职业协会、有明确的职业道德等;(2)态度特征的描述,包括良好的同事关系、乐于奉献、自制(self-regulation)、在本领域具有号召力、能够主动独立作决定等;(3)大学娱乐治疗课程的设置和专业刊物的出版,创立了娱乐治疗杂志(Therapeutic Recreation Journal)和娱乐治疗年鉴(Annual in Therapeutic Recreation)等。另外,这一发展还体现为职业道德的发展、公布了社区和临床的开业标准、在全(美)国成立娱乐治疗的区域交流组织;并且1981年娱乐治疗认证组织全国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n Therapeutic Recreation Certification,NCTRC)建立了娱乐治疗专家认证体系等。
一、娱乐治疗的新动力:幸福感研究
过去,许多娱乐治疗专家受到流行的缺陷模型范式的影响,认为如果能够帮助病人减轻问题、缺陷或疾病,那么他们就应该自认为是成功的,即主要关注如何理解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和缺陷。这一状况持续到一种新的范式的出现,这一范式主张:(1)没有问题并不等同于身心健康;(2)消极缺陷的减少并不会自动导致积极状态的提高;(3)任何患者都拥有自我改进的各种资源和力量。这一范式对原有范式构成了挑战,使娱乐治疗专家不得不修改他们的任务和服务以调整缺陷模型。
与此同时,在积极心理学推动下的幸福感研究获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为娱乐治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进而成为其发展的新的推动力。幸福感研究关注个体的健康、积极情感和生活质量,关注个体积极力量的创造性,强调个体的力量和能力如勇气、未来设想(mindedness)、乐观、情感智力、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真实性(authenticity)、获得快乐的能力(capacity for pleasure)、系列目标等(Seligman & Peterson,2003)[4]。幸福感研究之所以能对娱乐治疗产生推动作用,一方面是因为它关注的这些主题有利于培养患者的各种力量。Seligman(2002b)认为,在治疗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培育患者的各种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同时提供了有效治疗的一些共同原则,如确认和培育患者的力量;向患者慢慢灌输希望和乐观,提升可信任的关系;鼓励自我效能感、自我责任感,以及一些自我控制等[5]。这些主题和原则对娱乐治疗原有的缺陷模型来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拓展和大力的推动。
二、娱乐治疗的新目标:获得幸福感
受幸福感研究的影响,娱乐治疗关注的主题包括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健康的最高水平和心身健康,终身健康和幸福感(Wilhite,Keller,& Caldwell,1999)等[6]。事实上已经将幸福感看作是一个主要的目标(Shank & Coyle,2002)[7]。幸福感带来了一些心理概念如:快乐、自我实现、乐观、活力(vitality)、自我接受、目标驱动生活(purpose-driven life)、至善功能(optimal functioning)、生活满意度等。具体说来,幸福感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既类似于层级关系,又类似于递进关系的三大子领域。一致的,娱乐治疗的目标也是提高患者的三种不同幸福感水平。
1.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主观幸福感大概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指标。在英语中目前主观幸福感的表达有happiness,well-being,subjective well-being等,因此许多研究者也常用快乐、愉快等指代幸福感。但目前对幸福感的表达已经基本形成了用subjective well-being来表达的共识。这个词是指一种主观的好的存在或状态,或者是健康、快乐的状态,与happy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指一种生存状态,而后者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目前研究者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结构达成了较一致的认识,即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个主要维度构成(Diener,1984)[8]:认知维度主要指生活满意度,它是个体对生活的判断和长期评价的反映,目前又有一种观点认为认知维度还包括不同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情感维度则主要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方面。不过也有学者把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维度合并成一个维度——情感平衡度[9]。
Diener(1984)认为主观幸福感有三个特点:1.主观性,指对它的评定主要依赖于行动者本人内定的标准,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准则;2.相对稳定性,指虽在评定主观幸福感时会受到情境和情绪状态的影响,但研究证实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值;3.整体性,指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对情感反应的评估和对认知的判断,即包括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三个维度。
2.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它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60年代临床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发展。这些学科强调个体在面对挑战时有意义生活和自我实现的潜能,强调如何以理想的方式解决基本的生命挑战问题。
相对于主观幸福感来说,心理幸福感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它认为,幸福感的组成不仅仅是快乐,它是充分实现个体的功能而不仅仅是达到各种愿望。换句话说,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符合个人价值的个人成长、发展和自我实现、自我表达和行为等基础上。Ryan和Deci(2001)则认为“真正的快乐是以美德的表达为基础的”,他们将心理幸福感描述成“在幸福感的过程中实现个体潜能,以及在一些自我实现概念的过程中实现个体的潜能,这些概念包括充分实现的个体、意义性(meaningfulness)、自我实现、活力(vitality)等”[10]。
实际上,心理幸福感还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Waterman(1993)用“个人表达”(personal expressiveness)来描述,认为幸福感建立在保持真实自我的生活能力的基础之上[11]。Ryff和Singer(1998)则用“人类繁荣”(human flourishing)来描述心理幸福感,将心理幸福感定义为对完美实现个体真实潜能的追求[12]。
3.社会幸福感(social well-being)。社会幸福感的概念较早时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心理健康和理想健康的定义中。WHO将心理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和社会幸福感,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将理想健康定义为“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幸福感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13]。但是相对于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来说这一概念比较模糊,研究者们并没有达成共识,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1)认为社会幸福感是指个体同社会支持网络联系的程度。例如Pual(1978)等认为,是与物质幸福感、个人幸福感、家庭幸福感相对的一个概念。(2)认为社会幸福感是对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判断,这些事件如婴儿死亡率、青少年自杀、失业、贫困老龄人、虐待儿童、毒品滥用、自杀、学生辍学、酒后车祸等[14];(3)认为社会幸福感是个体对社会生活(如集体自尊)的满意感,或者是指社会方面的幸福感(如孤独)。认为可以用社会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Social Life Scale)对其进行评定[15]。这一观点事实上是将社会幸福感和个人幸福感相对而论。Kenneth(1996)等进而用自尊和社会自我效能感(social self-efficacy)两个概念来评定社会幸福感。这里的社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效能感[16]。(4)Cynthia(2004)等将社会幸福感定义为对生活机能的更公共评价。
不难发现,娱乐治疗在以获取幸福感为目标的努力中,完全涵盖了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两个使命,即帮助人们:(1)有更多的创造性和更满意的生活;(2)达到他们的最大潜能。
三、娱乐治疗的新途径
幸福感既是娱乐治疗追求的目标,同时又是娱乐治疗的有效途径。在娱乐治疗过程中,通过不同的策略和方法的使用可以提高三种幸福感水平,进而顺利达到娱乐治疗的目标。正如Lykken(2000)指出的,个体通过行为和认知努力能够影响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也就是说个体能够通过训练,采取一定的策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水平[17]。
1.主观幸福感的获得途径。目前,研究者们已经采纳了两种主要的途径用以提高积极情感和主观幸福感:一条途径是直接运用一些与娱乐治疗实践有关并且可以直接提高患者体验幸福和感觉愉快的能力的策略;另一条途径则是设计一些策略以帮助个体发展获得积极情感所必需的基础资源。
(1)避免适应。Seligman(2002b)认为“神经细胞对新颖的事件容易兴奋进而作出反应,而不能提供新异信息的事件则不能激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因此,如果一种体验重复产生逐渐地就会导致低的刺激(如更少幸福感)。Watson(2002)指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生活事件,如果它们是由于适应的原因而产生,那么即使它们对情绪和幸福感产生了戏剧性和直接的影响,它们对积极情感的整体水平产生的影响也很少是长期的[18]。因此,幸福感的最大影响不是来自于个体最终适应了的一些主要生活事件,而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对积极情感的频繁体验。因此,理想的日常活动应该包括:变化、新颖、挑战,并且对个体具有一些个人意义。
(2)主动约定(active engagement)。Watson(2002)报告说那些强调行为的变化而不是强调思维的变化最有效。他还进一步指出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是情绪提升的两种最有力的活动形式。很明显,闲暇(leisure)体验能够成为提高积极情感和愉快感的一个重要工具,因为它强调个体自由的选择并且具有个人意义,为个体的主动参与(active involvement)创造了条件。因此娱乐治疗强调使用娱乐干涉和其他行为干涉来影响患者行为的改变(Shank & Coyle,2002)。
(3)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事情的数量。正如Diener(1999)等指出所说,主观幸福感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情感比消极情感更多的基础上。他们也指出,积极情感的出现频率比其强度更重要。因此,尽可能地寻找机会体验愉快是一个重要的策略。这可以通过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体验的次数,或提高活动的多样性或日常活动中愉快的总量等来达到[19]。事实上,提高愉快机会的数量和变化性过去常被当作愉快教育和娱乐治疗的一个重要的部分(Stumbo & Peterson,2004)[20]。
(4)关注体验的愉快方面等。这些关注可以表现为享受这些体验(即有意识地关注愉快)和通过回忆或故事讲述等方式进行积极情感的再体验等。Seligman(2002b)也认为,现代生活的节奏是愉快的另一个阻碍,并且认为为了提高对愉快的检验可以尝试慢化对现实的思考过程和注意过程。娱乐治疗可以教会患者享受和留心的技能,从而提高闲暇和其他愉快体验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
(5)其他有关的策略。包括日常生活中追求有意义的个人目标;对各种情感和正常情感波动的监控(monitoring)、接受(accepting)和适应(accommodating);保持忙碌,花更多时间交际,发展积极的思维,用保持人格健康的方式工作;放松(Fredrickson,2002)等[21]。所有这些策略都有可能使患者获得主观幸福感,并且也是娱乐治疗实践的部分内容。
(6)发展同主观幸福感相连的许多资源。积极的社会关系和乐观是同积极情感明显相关的两种资源。另外,Ryan和Deci(2001)确认能力(competence)、自我效能、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真实性(authenticity)、自主性(autonomy)等是提高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资源。
2.心理幸福感的获得途径。Vaillant(2003)指出:心理幸福感来自于快乐或慷慨的爱(unselfish love),来自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感,或者来自游戏或容易而深入地参与到反映健康的活动中[22]。因此,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达到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些目标有利于个人提升并且能够通向积极机能。在此基础上,幸福感研究也已经确定了一些达到心理幸福感的途径。
(1)注重个人表达。Waterman(1993)认为个人表达是实现心理幸福感的途径。个人表达在活动中产生。这些活动包括:(1)要求热情参与(intense involvement);(2)通过发展个人的技能与才干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3)同自我的生活目标一致;(4)提供和谐(congruence)、满足(fulfillment)、成就(accomplishment)和活泼(aliveness)。事实上,Waterman认为个人热情参与、发展、满足、成就等都是闲暇的确切概念,因此闲暇可能也是个人表达的重要途径(Kleiber,1999)[23]。这样,娱乐治疗领域也可以将闲暇的这种观点融入到闲暇教育程序中,使个人通过参与闲暇表达活动更好地创造自己的心理幸福感。
(2)设计心理幸福感的干预策略。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参照Ryff和Keyes(1995)确认的六个与心理幸福感有关的概念:自主性、个人成长、环境控制、生活目标、积极关系、自我接受。这一观点已经被转化成一个心理治疗模型(Fava & Ruini,2003)[24]。
(3)注重自我决定。Ryan和Deci(2001)认为人类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要,即能力(competence)、自主性(autonomy)和关系,对这三种需要的满足可以导致心理幸福感。他们还指出,这些需要的充分发展对心理成长(如内部动机)、完整性(integrity)(如文化的内化和同化)、幸福感(如生活满意感和心理健康),以及对活力(vitality)和自我和谐(self-congruence)的体验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社会幸福感的获得途径。如果说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关注个体的观点,那么社会幸福感关注的则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个体对生活机能更公共的评价。因此,它要求个体与他人进行整合,表现为利他、同情、为高尚目标作出贡献等。
(1)与社会进行整合。Keyes(1998)认为个体的社会幸福感来自于个体同社会的整合,这种整合可以表现为不同关系,可以分为五个维度[25]:第一维度是社会接受,它意味着积极看待和接受他人;第二维度是社会实现(social actualization),是指对社会的舒适水平(comfort level)和对社会潜在的积极成长的信心;第三个维度是社会贡献(social contribution),是指个体对社会贡献的自我感觉,并且他人认为这种贡献是有价值的;第四个维度是社会一致(social coherence),指对社会充满兴趣并且认为社会是可以理解和预测的;第五个维度是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指个体相信自己属于某一团体并且和其他成员一起分享团体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是指感觉自己是团体的一部分。
(2)进行社会服务和娱乐参与。Seligman(2002b)建议患者也需要拥有机会为他人、社区和社会作出贡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能够发现和体验到社会幸福感。受到这一观点的启发,娱乐治疗工作者认为通过自我决定和享乐(enjoyment)活动,能够为患者提供一些“制造意义”(meaning making)的机会。因此,娱乐治疗很关注培养有意义生活的游戏。而社会服务和娱乐参与提供了发现力量和能力的环境,也提供了个体为他人服务的环境。志愿行为、指导(mentoring)和创造活动都是对社会作出贡献的途径,而且都是娱乐参与的有价值的形式。
四、评价
娱乐治疗以“娱乐”为出发点,对于以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心理治疗来说,无疑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它一出现就受到治疗学家们的广泛关注。同时它在治疗实践中的显著效果又使其更加备受青睐。因此,娱乐治疗从其产生后就获得长足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革命性的发展,一方面扩展了职业组织的队伍和规模,另一方面又深化了职业的专业化水平。但是由于娱乐治疗的理论基础受到当时流行的缺陷模型范式的影响,同时在娱乐治疗队伍内部也存在着“娱乐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争论,致使其发展始终潜伏着一种危机。当一种新的范式出现的时候,娱乐治疗这种理论上的瓶颈缺陷就遏制了它的发展。
幸福感研究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了娱乐治疗家们的视野。它提出了三种不同形式的幸福感,同时又探讨了提高不同幸福感水平的多种途径。为娱乐治疗在个体健康提升中的潜在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支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治疗娱乐的前景和价值,并且可能使其形成一种统一的娱乐治疗理论框架。幸福感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设想这将成为娱乐治疗发展的第三次革命。总之,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幸福感既是娱乐治疗的目标,同时又是娱乐治疗的途径,存在概念自我相依性的嫌疑;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正是因为这一特点,幸福感才很好地整合了过去娱乐治疗中关于“娱乐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的争论,给予娱乐治疗很大的启发,成为娱乐治疗的有力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