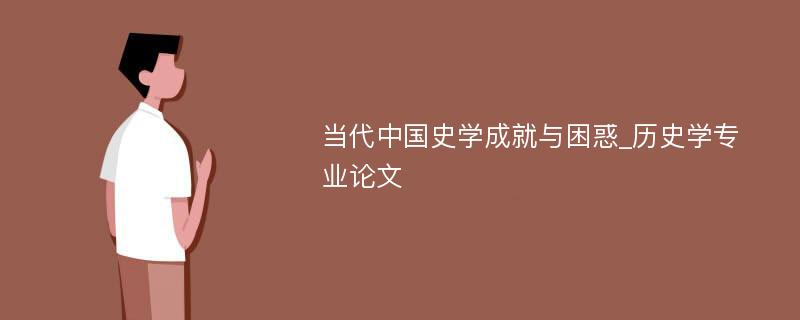
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困惑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3年夏,史学史国际委员会主席夏尔·奥利维埃·卡尔博奈尔(Charles Olivier Carbonell)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家的状况问题。就在那里,我高兴地认识了乔治·G·伊格斯(Georg G.Iggers)。我在1978年曾读到他的《欧洲史学新趋向》一书,从此便知道了伊格斯这个名字。第二年,我开设西方史学史的课程,于是就把他的书,连同E.H.卡尔(Carr)的《历史是什么?》一书,指定为学生的必读书。
蒙彼利埃讨论会结合后,我应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往委员会”(CSCPRC)之邀,去美国作三个月的学术访问。我40年代曾在耶鲁大学读书,以后就再也没去过美国。这次,我可以从许许多多有大学的城市中挑选5个,作为我走访美国同行讨论史学问题的对象。由于认识了伊格斯,纽约大学的布法罗分校便很自然地成为我旅程中的一站。乔治要求我为一个历史班作一次关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的演讲,并参加他的史学讨论班。当时我作了一个什么讲演,我已经忘了,但对于那天夜晚史学讨论班上我们关于历史主义的激烈辩论却记忆犹新。记得威尔玛(伊格斯夫人)在讨论进行中一次次地为我们端上茶点,像是要借此缓和辩论气氛似的。
乔治介绍我认识了他的两位中国学生,一位来自大陆,一位来自台湾。他对两人一视同仁,相待甚善。正巧当时伊格斯受到北京师范学院的邀请,要去中国首都及其他一些城市作一个系列演讲。他们就演讲的主题向我征求过意见。1984年5月底,我在北京大学接待了他们,并为乔治的两次才华横溢的演说作了口译。这两次演说的题目分别是德国史学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引起听众浓厚兴趣。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大学生不大清楚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及其史学著作的缘故吧。
课堂演讲之余,我们有不少神聊的时间。伊格斯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包括二战期间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两位纳粹时期来华避难的犹太孩子才得以同他们在纽约的父母团聚。
乔治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讲课,使人们对西方史学,尤其是它的理论与方法,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入的兴趣。关于这个问题下面我要多谈一些。这里只须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伊格斯的《新趋向》和《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已翻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作者还特地为两本书的中文版写了序。②华东师大的一位年轻助教王晴佳被伊格斯的课深深迷住了,以致决心尽一切可能去美国就学于他的门下。布法罗附近的锡拉丘斯大学历史系主任鲍威尔教授慷慨地接纳了他。经过多次会见之后,王睛佳写了一篇介绍乔治·伊格斯的访问录,刊登在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上。③
我还通过乔冶认识了许多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如威勒(Wehler)、科卡(Kocka)、菲尔豪斯(Vierhaus)、梅迪克(Medick)等。我们一起于1985年夏在斯图加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开幕前,到哥廷根和比勒费尔德走访了他们。后来我们又在1988年7月关于80年代社会史的巴黎讨论会上相遇。那次讨论几乎被来自东西德国的史学家垄断了,连伊格斯都不大插得上嘴。这样便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史学新近动向的“会外”交换意见的机会,而这正是伊格斯一直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探讨的也正是这一问题。
一
“文革”结束13年(1976-1989年)来,中国史学发展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大跃进。出版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成立了众多的历史学会,举行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讨论会,讨论了许多史学问题,开辟了许多新研究领域,并把外国各派史学思想和方法介绍给了国人,其盛况实属空前。④明明是这么一派繁荣景象,可偏偏还有人在那里不停地叫喊“史学危机”。是哪里出了毛病?在繁荣与危机之间难道有什么逻辑的联系吗?抑或二者之间有某种因果关系?如然,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
为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1949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一概述。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的特征,是作为历史研究与教学的指导原则的传播和被采纳。中国革命的胜利加强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也随着对传统史学思想与实践(“封建的”也好,“资产阶级”也好)的批判的深入而逐渐巩固下来。同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实际上被中止了,而对苏联却门户洞开—一当时苏联已成为我们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包括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下,历史学家们开始对诸如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土地制度的演变这样一些问题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世界史方面,欧洲中心论受到批判,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亚非史方面。由于这个时期相当宽松,提倡“百家争鸣”,故而这一新趋向曾产生过一些积极的成就。不过这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左”倾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迹象。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受到了过分的强调,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其他一些方面则被忽略了。学术讨论常常演成政治责难。
第二阶段(1957-1965年)始自反右运动,这场运动使许多杰出历史学家蒙受不白之冤。随后又发生了一场“破除权威”运动,目的是把那些被认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曾经或正在对当代发生重大影响的史学大家搞倒搞臭。这场“拔白旗”运动由于几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干预,才在60年代初被制止。这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组织了一批学者,编写了大量的教科书和史料集,为提高大学的历史教学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④与此同时,一场关于历史和史学问题的严肃辩论也在迅速展开,讨论的问题有历史主义原则与阶级斗争理论之间的关系,对农民“让步政策”的实质,历史上的所谓“清官”现象等等。
中苏论战导致了“东门”的关闭,由此中国陷入政治、经济和学术上的极度孤立状态。反对“苏修”的斗争在史学批评方面也产生了共鸣:那些提倡历史主义原则和对农民“让步”政策,以及赞誉“清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统统被斥为“修正主义者”。“双百”方针的丧钟敲响了。教条主义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研究陷于停顿。
第三阶段(1966-1976年)十年,标志着官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彻底破产。历史在“四人帮”这伙妖言惑众的“理论家”手里,已沦为赤裸裸的整人工具,成为他们用来消灭学术和政治上反对派的一根大棒。其仅有的一项发明创造,便是所谓“影射史学”—一政治冒险主义和最坏的实用主义的一种奇怪的结合。这种庸俗的、简单化的和教条的史学把人类历史描绘成单纯的阶级斗争史,而且唯恐斗争得不激烈。中国古代史只讲农民战争和农民革命,中国近代史也只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共党史则成了两条路线斗争史。世界史中所有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内容都受到谴责,奇怪的是拿破仑倒没有被计入其列,人们重新唱起“拿破仑崇拜”。⑤一句话,史学又变成了“政治的婢女”,只具有论证现行政策正确性的功能—一也不管这些政策究竟正确与否。史学完全丧失了尊严。这时的史学确确实实陷入了可怕的危机!
只有熟悉了这个背景,才能很好地理解和解释最近一个阶段(1976-1989年)中国史学的发展。经过1978-1979年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之后,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参加辩论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不是领袖的言论。利用和滥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评判历史家和历史著作的作法由此被杜绝了。人们还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即任何知识领域都不应是历史学家的“禁区”,而且知识无国界。对外开放的总政策的提出又使我国先后同西方国家和苏联恢复并扩大了学术和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这些意识、政治和心理上的变化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效果。
首先,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历史学家们不再只注意于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而开始研究社会和经济生活、物质文明、文化及思想史、地区史、少数民族史、华侨史、心态史、城市史、宗教史等等。
第二,人们探讨许许多多新的课题,并对一些老课题进行了重新解释与评价。在前一类中,有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中国习俗,上海、天津及其它港口的外国租界,古都,楚、赵、吴越、山东等等地方的古国文化。在后一类中,有洋务运动(19世纪下半叶进行的最初的一些现代化尝试)、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第三国际在中国共运中的作用等,而其中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这一老问题。
第三,人们对史学史、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兴趣。至今已出版十多种中国史学史著作。一部西方史学史正在编写中。人们试图对史学作出更客观、更深刻的重新评价。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了“史学导论”课,五种写法不同的有关教科书在争奇斗艳。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史学思想与实践的主流,但关于史学方法论的讨论已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多元因素,从而开始向唯物主义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各种方法论的综合迈进。第一部讨论历史哲学的著作于1988年问世,关于“人民是否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及“历史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的传统观点受到了挑战。一些多年以前提出并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如今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是荒唐的或假问题了,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的问题就是一个,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这样一个假设,即中国和西方的封建时代本应大致一样长!
第四,一大批西方和苏联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已译成中文,如克罗齐的《历史学:理论与实践》、柯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缩写版),J.汤普森的《史学著作史》、古奇的《19世纪的历史与历史学家》、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卡尔的《历史是什么?》、加尔金的《近现代史学史》、巴尔格的《史学方法论》、波普尔的《历史主义的贫困》、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的《新史学》、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以及伊格斯的那两本书。还出版了好几本有关当代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论文集,辑入了包括雅斯贝斯和伏维尔在内的许多现代历史学家的一些名著。应邀来中国讲学和接受中国学者访问的西方史学家人数之多,实属空前,他们的名字至少可以写满整整一页纸。⑥此外,人们还通过史学刊物向我国读者介绍了大量西方史学流派,尽管被人们认真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西方理论和方法尚不多。也许系统论和控制论是个例外,但人们应用得并不怎么成功。应该说这些理论方法中最有影响的是年鉴学派和马克斯·韦伯。⑦这两派都被认为较接近马克思主义,而且从许多方面补充了马克思主义。
二
最近13年来史学的大发展,显然是对“极左派”文化专制的一种反动。这种文化专制有多种表现:利用和滥用历史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庸俗的、机械的和简单的解释和应用,对本国的和外国的史学进行全面的诋毁,对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一概施以政治压力和迫害等等。若以为所有这些负面特征都已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销声匿迹,那就太天真了。此外,这种反动还采取了“回到考据”的形式。而且老一辈和新一代史学家们对史学的看法似乎也不一致。所以“史学危机”的说法,一时沸沸扬扬。⑧
一般说来,“文革”前表现活跃的那些历史学家,亦即那批在30年代到50年代之间培养起来的、现在都已年逾55岁的历史学家,似乎多少都满意于近十几年来的史学状况。他们喜欢作纵向比较,即同以前发生过的事进行比较,认为他们的环境这些年来颇有改善,比“文革”中甚至“文革前”都好多了。在他们看来,过去的13年是繁荣昌盛的,气氛宽松,国际交流成效显著,虽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在70-80年代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们则看法比较悲观。他们喜欢作横向比较,即同日本和西方国家进行比较,觉得这些国家的历史学是一种更独立、更丰富多彩和更欣欣向荣的学科,相形之下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境况十分不妙。
“史学危机”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同的历史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历史学家们最普遍的抱怨是:历史学科不受重视,它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立志学历史的学生愈来愈少;学历史的学生更难找到好的工作;出版社大多不愿出史学著作;近现代史的研究显得更敏感、更危险了等等。
人们对于“危机”的原因也是意见纷纭。有人说,我们的历史研究的哲学基础—一即历史唯物论—一被简单化,有待改进。例如,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应到处照搬⑨;历史的动力并不只是阶级斗争,而是多种力量的结合。⑩在他们看来,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教条主义的应用,妨碍了对历史的理解。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史学危机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背离,采用从外国舶来的方法与其说开启了人们的心智,不如说造成了思想混乱。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忽视了我们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这种遗产教导我们要着力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注意发挥历史的教育价值,要把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要揭示历史因素的复杂性,要写出优美的故事等。(11)人们爱读历史小说而不爱读历史著作,正是因为前者写得好得多的缘故。
无论人们对史学现状的看法多么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就是我们太脱离社会,我们的史学研究太脱离实际。(12)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为政治目的而滥用历史、搞影射史学的做法的反动,和对于被卷入当代政治问题的实际的惧怕,使历史学家退入了象牙之塔。他们并没有过错,因为这种特殊的心态是政治和社会的动荡所致。甚至在相对宽松的时期,仍然发生过一些秉笔直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事情。(13)此外,历史学家对历史学如何才能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没有把握。
近年来人们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讨论甚多。(14)理论上,谁也不否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在当代社会发挥作用。但这种作用可以从广义或狭义上来理解。广义上看,历史学具有,或应当具有如下诸项功能:1.它可以服务于教育的和道德的目的,因为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有助于人们区分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培养高尚的情操,树立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2.它能提供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使人民和统治者保持警觉和清醒的头脑,避免犯错误;3.它有助于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提供艺术和科学知识,以发展认识和改变社会现实所需的能力和才智;4.它能揭示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世界,其中共存着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不同文化,但它也能指出人类社会将实现平等和公正这一共同的未来,这正是我们当前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狭义的理解,则是说史学应对当前有直接的用处。在中国来说,也就是史学应该能够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所谓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或文化的。正如科学和技术对于农业、工业、运输等等方面的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一样,文科知识,尤其是历史,对于引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全心全意地投入“新长征”,同样是有用的。历史将告诉他们为什么中国必须现代化,为什么中国过去失败了,我们可以从工业化国家汲取哪些经验教训,为什么经济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必须同步进行,我们需要哪一种“新人”以及如何培养他们,怎样才能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较少痛苦等等。有些历史学家走向了一个极端,他们主张研究一些直接同商品经济的发展挂钩的课题,如生产管理史,市场经济史等等。其中有些人甚至设计了一门新学科,叫做“历史工程学”,它将讲授如下一些课程:西方经济史,技术史,政治制度与实践史,法律和政治思想,比较宪法,中国官僚企业史,洋务运动史,海外企业家的发展,港澳史,台湾经济发展等等。
然而,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认为,除了一些非常特别的情况(如某个地区的地震史研究,旨在确定某个建筑工地的选择)之外,历史学的作用只能是间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传授知识和经验,培养历史的眼光和观点,增强对我们自己和对别人的认识能力,—一一句话,提高公民当然也包括统治者的道德文化素质。许多国家的政府,部分地或主要地是由于对本国和他国历史的无知,都犯有一些极为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这一事实足以令我们猛醒。所以,极其有必要大力普及历史知识,特别是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青少年和成年人编写一些好的历史教材和读物。
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结论:或许,并非社会忽视了历史学科,而是我们历史学家没有做好工作。现在,该是我们自我检讨和对历史学科本身进行重新检查的时候了。
三
随着人民共和国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中国的历史学家开始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成就进行评估。(15)从未见过人们就过去自己的经验写过如此之多的重新评价和反思的文章。孔子说“四十而不惑”,而中国历史学家此时却是非喜交集,困惑与自信参半。尽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这一点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学家都不否认,但仍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首先是某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必须解决,但实践也同样不容忽视。
相对容易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这就是扩大研究领域(我已经简单叙述过这方面的情况)。这一情况,是我国史学传统的恢复和西方史学尤其是年鉴派史学的影响联合造成的。中国传统史学,无论是皇朝史还是制度史,都包括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的几乎所有的方面,没有历史不写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个好传统,而等着费尔南·布罗代尔来告诉我们“全面历史”的重要性。此外,在我们这个巨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这一伟大的任务,要求整个社会的转变和参与。人们看到:整个民族在运动中前进,尽管节奏不一;社会各个部分所发挥的作用;经济的不同成分,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国家的作用和它同社会的关系;政治制度的运作;知识分子的地位;我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等。这种观察和经验自然会对历史学家的心智产生影响,使他们认识到历史的巨大复杂性,以及拓宽思想视野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
第二步是采用新的史学方法。这一步比较困难一些,但还不是特别困难,人们正在积极尝试,并已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我国史学的严重缺陷之一是狭隘理解和片面依赖马克思主义方法,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首先,一种生硬的决定论—一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阶级或意识形态决定论,似乎取代和取消了任何其他的解释。其次,阶级分析方法被看成“唯一的”科学方法,不允许有任何偏离。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大概会第一个起来否定这种观点。
从70年代起,史学家们就批判了这种教条主义的立场,但并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们写了许多文章,认为阶级分析方法并非万能的方法,这种方法能用来分析某些而不是所有历史问题,而且还要十分小心谨慎。因为阶级出身和阶级地位并不能决定一切;我们还必须到阶级斗争的后面,去认识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并在政治思想上得到表达的阶级利益。但政治思想一旦形成,就有了一种自主性,可能并不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运用这种方法需要高手,而且必须同历史主义的方法辩证地结合起来。于是60年代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主义之间关系的大辩论在80年代重新掀起,而70年代的武断见解则被否定了。(16)
缺口一旦被打开,其他史学方法也开始被稳步地(尽管有点羞羞答答地)用来“补充”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不足。比较方法,系统分析,心理史学,计量方法,词义学,口述史学,历史社会学,甚至模糊逻辑学,都被引了进来并被运用于实践,而且多少已经取得一些成效(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实践者的素质)。在这些新方法中,人们辩论最激烈的是系统分析的方法。1980年,两位年轻的作者(其中之一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历史的封建社会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作者在文章中,试图从力量的平衡、结构功能网络、多层面的活动和受限制的行为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对于这篇文章,全面否定者有之,怀疑保留者有之,有条件接受者有之,全盘肯定者亦有之。(17)有些历史学家说,鉴于其长期的持续性和显见的停滞性,中国历史更适合采用布罗代尔的分析;另一些人则认为用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来说明中国历史要更贴切一些。看来,中国历史学正处在一个摸索和实验的过程中,这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它是不可逆转的。
历史学家的自我检查,较之扩大研究领域和采用新方法,显得更深入一些、人们谈到了一些更基本的问题,即历史的主体问题,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的自主性的问题,以及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问题。(18)
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作用只是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有效性。史学由此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注解。“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的首创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创造性,人在各种集团中的地位,人的身份和个性,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化的史学(某些年鉴派历史学家也有这个缺陷)。如果“人”的地位不恢复,我们的历史书就很难改变枯燥乏味、虚假不实的面貌,就不会有多少读者,就不能发挥其社会功能。一句话,不成其为历史。
“人”在历史学中的屈从地位,是同作为一个学科的历史的屈从地位相适应的。历史学家们记得,在过去的年代里,历史往往必须臣服于某种外在的东西:某种哲学体系,某种政治教条,甚或某个领袖心血来潮的狂想曲。认为或希望历史可以完全自主和独立于某种特殊的环境,这是天真的幻想。然而,一种外部势力可以专横地给任何一本历史著作、文章或论点贴上标签,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反革命的等等,并把它同作者一起打入冷宫,这对于历史学是最有害的。这也就说明了(至少是部分地)为什么我国在过去的40年里,在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既没有能够产生出很多有独创性的作品,又没有能够产生出一批伟大的历史学家(象在30、40年代成名的那些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一样)。历史的标准究竟在那里?“历史的标准就是它自身;它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外在的什么东西,它是思想的一种自主的形式,拥有自己的原则和方法。”(19)我看,我国十分之九的历史学家都会赞同这一由R.G柯林伍德概括的唯心主义哲学家F.H.布莱德利的观点,尽管他们中百分之九十都不是唯心主义者。他们更赞成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0)
问题是,两代老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对我国历史学过去的这一失误负责?回答是应该,又不应该。言之应该,是因为他们参加了所有那些批判和诋毁被误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品和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运动;而且他们以同样的理由攻击过他们的师长和同事,结果自己又在另一轮运动中受到学生和同事的攻击。他们也写过和教过那些从理论和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历史。另一方面,说他们不应该对此负责,是因为他们自己同样也是那种号称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做法的牺牲品。他们多半只是在违心地遵从上面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存活下来,而不是如何为理想而斗争。
所以在最近关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讨论中,和“客观事实”(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它是独立于研究者而存在的)比较起来,人们更为关注的还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问题。(21)所谓“主观意识”,指的是那些最有助于历史学家履行其天职的素质。我国的史学传统要求史学家必须具备四项美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象南、董、魏、崔这样一些冒着生命危险秉笔直书古代历史学家的故事,无数次地为人们所提及。有人提出,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应该了解他的社会责任,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所应具备的思想品德素质。“历史学家是他自己的权威,他的思想是自主的、自我认可的,拥有他的权威必须遵循的标准,并根据这个标准来评议他的各种权威。”(22)换言之,就是应该坚持你自己的研究成果,直到它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为止,而不要去盲从任何权威,做那种唯唯诺诺的“唯本”、“唯上”的史学家。
在其他方面,最有意义的是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人们提出,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尽管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有密切的关联,但二者终究并不是一回事。(23)它探讨的是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关于这一点,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来专门论述。
就未来的发展而言,中国史学有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史、社会史、心态史、科技史、文化关系史、国际关系史、人物传记等等。人们将继续引进和讨论写历史的新方法,但更需要做的是说明这些新方法应当怎样应用,以及效果如何。人们还将更系统地研究一些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关于史学理论的著作也将纷纷问世并引出更多的争论。最后,在本世纪末,将会出现一批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新的综合著作。(24)
国际史学界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在未来的十年里,它很可能还将继续发挥同样的作用。但我希望,作为回报,中国史学也将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中国史学家可能已经这样做了,或者正在这样做。如然,我期望着能看到更多的实例。
(根据1989年5月英文稿译出)
注释:
①原载《展望2000年历史科学》——祝贺美籍德国历史学家乔治·G·伊格斯65岁诞辰论文集。德国哈根(Hagen)出版,1991年。本文是为外国读者撰写的,原文为英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高毅译出。
②两书均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北京1989年。
③参见《史学理论》1988第3期。
④参见《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周超敏等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1959年,召开了全国大学文科教材编写会议,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被任命为历史组组长。6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大学历史标准教材。
⑥参见张芝联:《对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载张芝联著:《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北京1988年,第148-160页。
⑦就我所能记住的而言,最著名的来华讲过学的历史学家有:GeorgesDuby,Helene Ahrweiler,Jacques Le Goff,Madeleine Reberioux,Francois Furet,Albert Soboul,Michel Vovelle,Maurice Avmard,Francois Bedarrida,Immanuel Wallerstein,Charles and Louis Tilly,Fritz Stern,Georg Iggers,Bill Bouwsma,Bob Forster,John Hope Franklin,E.B.Smith,Michael Kammen,Lynn Hunt,Arthur Schlesinger Jr.,Akire Iriye,Philip Foner,Eric Hobsbawm,E.P.Thompson,Ralph Harrison,Jugen Kuscynsky,Werner Conze,Karl Dieter Erdmann,等等。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来自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学者。
⑧我于1978年发表了第一篇介绍年鉴派的文章,参见张芝联:前引书,第179-191页。布罗代尔逝世之际,我写了另一篇文章《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参见同上书,第232-251页。
⑨参见《读书》,1986年11月号;《光明日报》1986年8月27日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
⑩参见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胡仲达:《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的答疑》,载《文史哲》1988年第5期。
(11)参见1988年4月28日《光明日报》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讨论,《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刘大年:《论合力》,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2)参见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13)《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第465-468页。
(14)参见蒋大椿:《怀念我的老师黎澍》,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黎澍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信条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15)1984年12月在武汉举行了一次史学理论讨论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16)参见《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另参见陈启能:《世界史研究四十年:成就与不足》,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
(17)参见A.杜立克与L.施奈德关于这场辩论的介绍,载伊格斯与帕葛合编《历史研究国际手册》。
(18)《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第482-484页。
(19)参见《史学理论》1989年第2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
(20)R.G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牛津1946年,第140页。
(21)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5-26页。
(22)参见《史学理论》1989年第2期讨论这个题目的两篇文章。并参见李振宏:《论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彭卫:《历史研究主观错误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3)柯林伍德:前引书,第236页。
(24)蒋大椿:《四十年来史学理论研究综述》,载《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
(25)郭圣铭教授正在撰写多卷本的《世界文明史》,吴于廑教授组织编写一部新的世界通史。其他一些个人或集体的写作计划也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