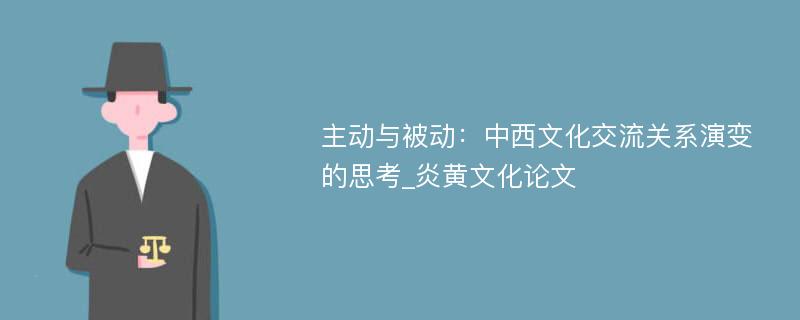
主动与被动:中西文化交流关系嬗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主动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论争,在16世纪以来的几个世纪里热乎了一次又一次,掀起了一次次高潮。笔者无意于对已有的各种争论再作褒贬,只是想通过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来探讨中西文化关系及产生形成这种关系的机制。
文化交流大多是双向的。在交流的双方中,总是由发展层次高些的文化居于优势与主流,处于相对主动的地位,另一方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这是由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就这点而言,结合历史实际,我们认为,中西文化关系曾经历过一个互换位置的嬗变。其段限大致以17世纪为界。此前,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以“东学西被”为主,到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双方的地位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即以“西学东渐”为主。
(一)
翻开卷帙浩繁的历史记载,人们会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文化的各个方面就出现了堪与古代希腊交相辉映的成就,而在公元3世纪到15、16世纪之间, 中国在这些领域仍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为西方各国所望尘莫及。
公元3世纪时,罗马帝国已值晚期,社会动荡不宁, 还不断遭到“蛮族”的入侵和骚扰。公元455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大肆焚掠, 无数文化艺术珍品毁于兵燹。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诚如恩格斯所描述的“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1〕。直到文艺复兴前, 西方为教会势力垄断,哲学成为宗教的婢女,科学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亦无不屈从宗教,文化式微。而其时的中国古代文化,自春秋战国出现繁盛景象以来,中间虽遭始皇焚书坑儒,但经两汉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派张骞出使西域,凿通了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从此,中国凭藉其文化和经济优势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制其先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以丝绸名中西方交通之路,本身就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是以中国为主的。而从东汉到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政权更迭,匈奴又不断南侵,致使丝绸之路时阻时通。但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政权,都十分重视维护中西交通的顺畅,他们继承西汉时期对丝路的管理模式,或在西域设官置守,或屯田驻军,或派员慰抚沿途各地……。这些无不说明中国在其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居主流地位,是为主动的一方。到唐代,中国更是凭藉强大而稳定的政治局势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把自己的先进文化不断地传播到域外各国,也不断地将域外文化吸纳、融会到唐文化中,在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中始终处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唐以后的宋元明三朝,中西文化交流继续保持唐代的格局向前发展,中国文化仍领先一步。直到欧洲大陆文艺复兴运动广泛展开之后,这种文化交流格局才开始逐渐有所改变,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国完全丧失了主动接纳外来文化影响的能力,也不再能主动走出国门去寻求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从此,中国失掉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维持了十多世纪的主动地位与优势。
16世纪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文化不仅一直居于主动与优势地位并对于西方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远比西方文化所带给中国的影响大得多。
从历史事实来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既有物态文化方面(包括科技与工艺成果)的,也有制度和思想意识文化方面的。即以物态文化方面而言,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远不止于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丝绸”、“瓷器”、“漆竹”、“茶叶”等物的文化形态对西人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方面的濡染。闻名遐迩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变革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说纸使欧洲的复兴成为可能也并非过分”〔2〕。 中国其他三大发明对西方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曾断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3〕。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和思想意识文化对西方的影响也很大。《马可波罗游记》风行于14—15世纪的欧洲。学者们一致肯定它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一定影响。从13—18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渐多,他们回国后所作的宣传及在华期间的通信、笔记和译介文献等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向西方社会传播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制度、礼义习俗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等知识。其中金尼阁根据利玛窦札记编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史》、杜赫德主编《中华帝国全志》、冯秉正翻译《通鉴纲目》以及法国耶酥会士编撰《海外传教士书简集》、《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最有影响。
如伏尔泰接触了这些文献后在《风俗论》中说:“欧洲王公及商人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认为中国文化的发现对思想界来说,同达伽马、哥伦布在自然界的发现同等重要。这充分表明了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肯定和赞赏。他还从其抨击和否定法国专制制度的意愿出发,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无论在道德方面或治理方面最好的民族”,主张引进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则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向往〔4〕。 普瓦佛更在言辞语气中透出他对中国制度的赞叹:“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法律的话,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看看中国这幅诱人的图景就可以知道了”〔5〕。显然,法国思想家把中国制度当作了一种幻化的理想, 他们对中国制度的理解和认识是肤浅的、偏颇的,甚至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这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怀有先潜的目的和意愿),也存在客观的壁障。因此才会有戏剧性的事实,即中国封建时代的制度文化对17、18世纪的西方思想界宣传鼓噪资本主义、抨击封建专制统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文化对西方思想学术界的影响还表现在哲学及文学艺术等方面。哲学方面,朱谦之先生撰著《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1983年版),有详尽的专门论述。文学方面,法国的泰·戈蒂耶写的诗篇《中国风》和小说《水上亭》,均以中国为题材,并明显地受到汉学家翻译的《玉娇梨》的影响。德国文学家歌德在求学期间曾读过中国的《四书》,并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谈到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他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倍诺尔》与《赵》剧在主题与素材处理等方面存在许多类似之处。可见歌德受《赵》剧影响之深〔6〕。 至于中国文化对西方艺术的影响,有研究认为,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背景就是一幅中国式山水画,而且中国瓷器及贝壳雕饰艺术在18世纪掀起了一场风靡西欧的“罗柯柯运动”,它一度影响到西方绘画、园林建筑和雕刻等艺术的各个领域,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审美追求。
(二)
如果说,公元3世纪到15、16 世纪之间中国一直保持了一个为西方各国所望尘莫及的文化水平,那么,当历史之页翻到19世纪时,中西方的文化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大颠倒。伴随着西方文化兴盛的是中国文化悲壮的沉沦。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处于被动落后的地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史册记载来看,17世纪以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再也找不出如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东汉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古罗马)、以及明初郑和统庞大的舰队七下西洋的壮举了,更找不出如唐代“万国朝未央”〔7〕的盛况了。中国丧失了主动性。
第二,从16、17世纪开始,纷纷来华的传教士几乎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西方的声光化电,甚至立宪共和的文化思想由他们传进来,中国的经书典籍以至一些戏曲由他们传出去”〔8〕。当然, 这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交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丝毫没有起作用,只是强调指出,曾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已相当被动。尤其是19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倚靠大炮军舰为后盾,对中国进行所谓“文化输出”,如深入内地置产建堂,创办教会学校,主办刊物,成立翻译、出版及一些医疗机构,等等。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被动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中国一些怀抱救国图强宏愿的仁人志士,面对近代深重的国难,放眼世界,向西方探寻强国富民之策。这表面上看似自觉,实则出于无奈,出于被迫。最能说明这种被动性的是,这些有识之士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引进,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内心深处真诚地认为西方文化真的比中国好,而是因为他们看到西方的某些东西可以拿来救亡自强。就拿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能深得中西文化之精要的严复来说,他是走出国门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力主西方文化并曾把西方的进化论、自由民权论等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可是,他却认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只不过是出于急于愈愚、疗贫、起弱这一目的而使用的手段,而决不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制度典章在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性和这种文化输入在哲学和科学上的合理性〔9〕。因此他说过,为了愈愚、疗贫、 起弱,无论西方文化或等而下之的其它什么,“虽出于夷狄禽兽,犹将师之”〔10〕。这种被动接纳西方文化的表现,并不是个别人的某种对西学东渐内在逻辑(即对真善美认识和追求规律〔11〕)的背离,而是有一定普遍性的。因而在严复之后几十年还有人说:“现代的强国……,我们若要和他们并立于天地之间,便非学他们这些不可……就算人家各国的文化都是坏到要不得的,我们也只好去学,因为非如此不能自立”〔12〕。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也载:“文襄(指张之洞——引者注)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的“名教”比“西法”更好。那么有没有坦率承认中国“实不如”西洋的呢?有。冯桂芬就说过中国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如西方: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这数端囊括了中国内政、外交、教育、政制、军事等各方面。可是,当他得出向西方学习的结论时就只剩“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并再三强调“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13〕,他还总括自己的思想理论是“参以杂家,掺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14〕。说到底,西方的政治理论、法律制度、文化思潮等等,还是不如中国的好。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许多人以“体用”、“本末”、“主辅”、“道器”等概念来界定和规范中西文化交融的这种现象才可以得到说明,从而也说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普遍是那样的矛盾和不协调,以致表现出他们文化观几个层面的断裂和脱节。如冯桂芬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薛福成的“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王韬的“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郑观应的“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都同样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和不协调的文化心态,表现了他们的文化观在“道”与“器”、“体”与“用”的层面上的断裂。可见,处在19世纪历史文化转折关头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吸取,看似主动,实则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济世情怀所左右,心灵深处蒙上了一层无奈的惆怅和失落。
第四,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被动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来看,也能说明中国自19世纪以来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不是积极主动的,而是消极被动的。正如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的那样:“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挨了第一鞭子,西人战舰之速、火器之利令人警醒,“四海晏然无堵”的美梦是做不成了。于是表示要学习西方造船造炮,“但只能学这点,其它不能要”〔15〕,在时人看来,西方强于中国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待甲午海战又一鞭子打来,中国才又认识到“西人之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16〕,大声疾呼:“今日之计,莫急于改宪法。必尽取其国律、民律、商律、刑律等书而译之”〔17〕。于是,中国的近代历史在洋务新政后有了戊戌变法。中国近代西学引进不平衡的缺陷(自然科学的引进远远高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从此也大大改观。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确实是被动的落后的一方,但为了摆脱落后,振衰起颓,中西文化交流仍在中国的被动适应中一步步趋向深化。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启动了近现代化的脚步。这便是被动与主动的辩证法。
(三)
通过对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中由主动而至被动这一动态过程的考察,我们知道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曾经有过兼容并蓄不断完善充实自身的辉煌的历史。就拿15、16世纪世界历史大转折时期来说,当欧洲大陆掀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高潮之时,明末清初的中国也涌动着一股并不微弱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的市民意识。这种市民意识与清初普遍的“反清复明兴汉”的意识汇流,更促进了明清之际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思想潮流。李贽、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都是翻滚在这股思潮浪尖上的思想家。此外明末对西学的采纳吸收也形成了一定规模,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李天经、冯应京、王徵等,他们均对西学纳而不拒,强调“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18〕,经世致用学风跃然纸上。中国文化在16世纪末失却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动地位后,仍经历了一个中西双方处于相对平等地位的交流时期。在这种局面下,西方的科技仍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它如果能健康正常地发展下去,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绝不至于沦入被动挨打的窘境。
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资本主义萌芽和随之而来的启蒙思潮产生了不同的结局。西方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后爆发了资产阶级政治和产业的革命,使其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都渐趋兴盛强大,进入了近代发展阶段。而中国在历经早期的思想启蒙后,走出中世纪的契机到17世纪末期转瞬即逝,封建专制主义得到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在18世纪发生逆转,出现了所谓“汉学”复兴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为什么?这些问题均应从中国16、17世纪的历史实际中去探寻其因由。只有探明了因缘,才能明悉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关系中由主动而至被动的机制奥妙。从明清之际的历史事实来看,造成上述中西强烈反差的根本原因首先是明中叶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还很微弱,其次是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和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取明王朝而代之,战乱频仍,中断了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自身生长发育的环境。这两个方面作为原因在学界已属公论,在此不再赘言。只是满清作为一支游牧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个征服民族迅速屈服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并为其同化的历史进程”是怎样深深地妨碍或者说改变了自明末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启蒙思想的潜滋暗长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已经形成的格局的正常发展的,这点值得研究。
先谈第一个方面,即满清作为一个征服民族屈服于被征服的汉民族的文化并为其同化的历史过程,是怎样抑制了明末启蒙思想的潜滋暗长并逆转为“汉学”昌盛的。
首先,清初统治者入关后,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抗清的武装力量,因而竭力拉笼迎合一般汉族知识分子,对他们的讥清、拒清意识也并不过于计较,反而继续明朝的文化政策,以程朱理学为儒家正宗,以科举考试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甚至特开博学鸿词科以招揽更多有才能的汉族学者与清政府合作。可是,由于程朱理学经过几朝几代的发展,到明中叶以后从阐发义理走向了空谈心性,并愈益流于空疏。于是从明清之际起,学术界就呈现出了由宋返汉,通经服古的趋势。而清政府尚不明悉这种趋向,仍以程朱理学为正宗来笼络怀柔汉族知识分子,就使得对满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故意反其道而行之,把程朱理学批得一钱不值,促成了用汉学取代理学的局面。
其次,汉学运动的兴起,也与清初统治者赞赏崇尚中国古典文化有极大的关系。顺治皇帝本来是不通汉文的,但他以极大的毅力攻读汉文,在短短的几年里学会了用汉文读,批阅公文。接其后的康熙皇帝,虽对西方文化表示赞赏,但更崇尚中国文化。在他统治的时代,刊行了《朱子全书》,编纂出版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图书。雍正较其父皇康熙,对中国固有的文明更为崇拜。他即位之初便追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爵”,大力弘扬孔子学说,并且在中国帝王中开向孔子行跪拜礼之先河〔19〕。可见,由于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皇帝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及一再提倡,汉学运动在乾隆朝兴起并达到昌盛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汉学运动”所以能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达到空前昌盛,并由此导致18世纪文化思想对16、17世纪末启蒙思潮的反对,还与康熙末年武装的反清力量基本上被剪灭,清政权日趋稳固,开始钳制言论、专制政治愈演愈烈等因素有关。知识分子动辄得咎,被迫钳口结舌,远离政治与现实,埋头钻故纸堆“铨释古训,究索名物”。可见,汉学的兴盛也是清政府高压文化政策的产物。
16、17世纪启蒙思潮到18世纪逆转为汉学昌盛,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17世纪进步思想家的启蒙思想,多半是以注疏阐发儒家经书的形式表现的,从王夫之《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到戴震《孟子字义疏正》,无一不是披着经学的外衣而表现出新的思想。这种形式,也为汉学在清代的复兴开了先路。
再谈第二方面,即满清作为一个征服民族迅速屈服于被征服的汉民族的文化并为其同化的历史过程,是如何中断了明末以来已形成的中西文化交流格局和规模,以至使一度以“会通求超胜”为旨归的中西文化交流渠道愈来愈窄,西学西器竟至沦为宫墙内的“贡品”、“珍玩”和摆设的。
就中国的知识阶层来说,在明末曾形成了一个对西学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群。仅以与利玛窦一人直接结交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有文献可考的就达100多人,其中大多数即是对西学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群中的成员。他们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认真地翻译西书西学,据中华书局徐宗泽编著的《明清间耶酥会士译著提要》等有关资料可以看出,明末的西学传播,尤其是1629年历局成立以前,西学在中国的译介较为全面完整,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把西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习引进的。因此,其时著译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水利、地质矿冶、医学、宗教等书籍,也翻译了一些哲学、伦理、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心理学等学科的书籍。在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入清以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深怀亡国之恨,在政治上表现出与满清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一种典型的逆反心理。顺治、康熙对传教士优礼有加,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兴趣,这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他们慢慢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冷漠。这正合了清初统治者提倡儒学以抗衡东来之势益猛的西方文化的本意。可见,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格局的改变,是满清政府蓄意在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权量制衡的结果。由此,明末对西学东渐取积极回应态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便无法得到正常的代谢和成长。至反清的武装力量基本清除后,清朝文化专制统治逐渐加强,对西学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群就更不可能存在了。
前面已述,清初统治者对西学还是相当热心的,对传教士也是优礼有加的,按说清代至少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势态不会比明代差,可是,由于明末对西学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群的不复存在,且清初统治者对西学的态度过于以己之喜好为转移,因此使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带有致命的缺陷。拿清初对西学西器最感兴趣的康熙帝统治时期来说,他过于偏好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因而不可能象明末知识分子那样将西学当作整体来把握。而且,他对西学西器的爱好只拘泥于将之作为皇宫贡品和摆设,并把传进来的西学西器乃至东来的西洋传教士都圈禁于皇宫之内,使得它们在社会上几乎没产生什么实际影响。比如机械的研习主要用于宫廷内制造和维修西式钟表及其他一些新奇玩物,生物学知识只用来解释作为贡品的“狮子”和“猎鹰”等,音乐、绘画、建筑等也主要用于宫廷享乐玩赏,医学方面,人体解剖学的编译则只准供御医参考。
康熙为什么对西学西器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欢迎引进,另一方面又将西学西器封锁在高高的宫墙之内,不使之流入社会,传播新知?究其所以,根源仍在于清朝统治者是以一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广大汉民族所致。康熙对西学西器的热衷和对汉文化的崇尚,并不能摈除他内心深处文化思想上的恐慌,他没办法持真正开明的心态,放任西方文化在社会上的流播及汉族知识分子对“各种问题”的“自由研究”的肆无忌惮地说东道西。文化思想上的愚民政策和高压专制政策是他加强防范和统治汉民族人民的主要支柱。梁启超曾批评康熙:“以当时康熙帝之热心于西方文物,为何不开个学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20〕。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失策,而是一个文明程度较落后的征服民族处心积虑、精心设计的思想文化统制政策,它正象征梁启超说的那样是有心要“窒塞民智”!因此,康熙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其说有,从实际影响来说与其后的闭关时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西学西器虽然进了国门,但却被封禁于宫墙之内。康熙之后的历朝满清皇帝对西学就没有什么兴趣了,随后闭关锁国政策也成为了清代的国策。至此可以说,明末西方文化的输入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逐渐光沉响绝,中国在有清统治的二百年里绕了一个大圈子,才在19世纪中叶回到明末已开始的起点。拿明末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来说,徐只译完前六卷,由于明末对西学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群不复存在,因此,继续翻译《几何原本》“续成大业”,竟拖至200 多年后由晚清数学家李善兰和西人伟烈亚合力翻译才告完成。也就是说,到19世纪中叶以前满清统治的200年里, 中西文化交流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与世界潮流隔绝了200年,而在这200年里,西方各国正扬帆急进。因此,当19世纪中叶西方用武力叩开中国大门后重新开始中西文化交流之时,中国的落后决定了它必然的被动地位。
从17世纪到19世纪,正值西方各国继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后又轰轰烈烈地开展第一次工业大革命之时,中国社会却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出现了200年的停滞和徘徊,开始了由先进到落后,由主动到被动的转化, 个中原因复杂纷繁,本文难免浅尝辄止,且只论其文化交流一面,权作抛砖引玉。
注释:
〔1〕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第400页。
〔2〕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09页。
〔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7卷第427页。
〔4〕参见路·马弗里克《中国—欧洲的典范》第二部分, 美国得克萨斯1946年。
〔5〕赫德森《欧洲与中国》,伦敦1931年,第318页。
〔6〕参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115页。
〔7〕《全唐诗》卷1《太宗皇帝》。
〔8〕《人民日报》1982年12月3日。
〔9〕《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50页。
〔10〕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期, 中华书局,1986年,第560页。
〔11〕《文汇报》1994年12月4日第7版。
〔12〕严既澄《〈我们的总答复〉书后》,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22—23日。
〔13〕冯桂芬《制洋器议》,《晚清文献》第106页。
〔14〕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自序》,《晚清文献》第99页。
〔1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译书》。
〔16〕同上。
〔17〕同上。
〔18〕徐光启《辩学章疏》。
〔19〕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2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