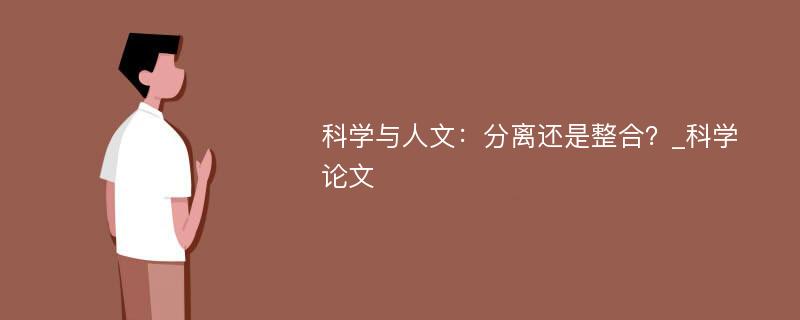
科学与人文:分离还是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1)03-0008-05
一、两种文化的分析
1876年,也就是科学大师达尔文67岁那年,他开始撰写回忆录——《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这是一部相当坦率的作品。其中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之一,是他谈到自己少年时曾对诗歌、戏剧、绘画、音乐等有过热烈的爱好和兴趣,时常一连几小时静坐不动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可是后来:
到现在,很多年来,我竟不能容忍去阅读一行诗句:最近,我尝试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发现它枯燥乏味,使我难以容忍,以致厌恶万分。我几乎也丧失了对绘画和音乐的兴味。(注:毕黎译:《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2页。)
对于这些“高尚的审美的兴趣”竟也消失殆尽,达尔文感到惊奇而悲哀。他忧心忡忡地表示:
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是幸福的丧失,可能会对智力发生损害,而且很可能也会对品德有害,因为这种情形会削弱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注:毕黎译:《达尔文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3页。)
达尔文的悲哀是深刻的。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诗歌、戏剧等的厌恶并非外力压迫的结果,而可以说是发自内心的。长期的自然科学训练和工作,改换了他观看世界的眼光,他固然可以看到许多别人看不出的奥妙,却也同时失去了别人所拥有的某些感受能力。
达尔文的可贵之处则在于,他到底还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些趣味和能力的丧失,并估价其后果。而不少科学家则深陷于这种“异化”之中却不自知,他们充满自信地以自己所知的那一小部分科学知识为满足,以此自傲,也以此骄人。
发生在达尔文身上的这种悲剧,也一直在同时代和此后的千千万万科学家身上反复重演——尽管许多人不相信其后果会严重到“对品德有害”。从那以后,随着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这两种“文化”一直处在日益严重的分离过程中。
昔日亚里士多德那样博学的天才大师,如今已成天方夜谭。这当然并非好事,只是人类为获得现代文明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罢了。有识之士很早就在为此担忧。还在20世纪初,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康奈特(J.B.Conant)建议用“科学与学术”的提法来兼顾两者,就已经受到热烈欢迎。那时,“科学史之父”萨顿博士(George Sarton)正在大声疾呼,要在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建立一座桥梁,他选定的这座桥梁不是别的——当然正是科学史;他认为“建造这座桥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文化需要”。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萨顿博士所呼唤的桥梁不仅没有建成通车,两岸的距离倒变得更加遥远。不过对于这个问题,西方学者毕竟能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我们国内的情况相比)。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当然不是那个去过延安的记者)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以及4年后的演讲《再谈两种文化》,(注:纪树立译:《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深刻讨论了当代社会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日益疏远的状况及其带来的困境,在当时能够激起国际性的热烈反响和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在国内,如果说萨顿博士所呼换的桥梁也已经建造了一小部分的话,那么这一小部分却完全被看作是自然科学那一岸上的附属建筑物,大多数旁的人几乎不理解、许多造桥人自己也没有萨顿博士沟通两岸的一片婆心。
两岸隔绝的结果是相互轻视。一千八百年前曹丕就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堪称千古名言。不仅狭义的文人之间是如此,在广义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之间也是如此。不同类型的文化人相互之间看不起,比如学理工科的看不起学人文的,认为他们“智商很低”、“连正负数也搞不清”、“不懂逻辑”;学文科的却也看不起学理工科的,认为他们是“有知识没文化”、“缺乏鉴赏力”、“根本不会写文章”。这两种观点当然都是偏见,但也都能得到身边很多事实的支持(当然反例也可以找到)。
稍微留心一下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许多科技工作者(或是学科学技术“出身”但后来从事别的职业的人),在适应社会发展、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表现得十分软弱无力,甚至十分低能;他们的思想视野极为狭窄;他们中许多人的藏书之贫乏(更多的人根本谈不到藏书),与他们已经获得的声望完全不相称;……另一方面,文科学者则大多对什么是科学方法茫然无知(即使他们自称对科学“很感兴趣”),一碰到数量关系就头昏脑胀;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对电脑和网络有着莫名的恐惧和厌恶,他们宣称“对着键盘就没有思路”,宁肯在纸上写了文章再请人输入电脑;……。
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必然后果,但在中国表现得特别严重。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强调将人加工成一颗“革命的螺丝钉”,以便被随意拧到“革命需要的地方”去,而心智的开发、人格的培育等等却被抛到一边。我们的许多科学家,少年时就很少有一连几小时静坐不动读莎士比亚的机会——因为那是“毒草”,也因为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成年后却要和达尔文一样承受学科分工造成的伤害。
二、科学的界限
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之后,数百年间,成就无限,支撑起现代物质文明的大厦,自身也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声望。以至于任何企图获得权威地位的理论,无一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也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而实际上,科学显然是有界限的。
能说明科学的界限的例证甚多。下面仅举其最显著者——人生观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激烈论战。当时的北大教授张君励发表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进,(注:张君励:“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不久地质学家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注: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指斥“玄学鬼附在张君励身上”。这场辩论因此得名为“科玄论战”。胡适、梁启超等十几位名人都先后加入战团,最后似乎以“玄学派”居于下风而告结束。
不过,“玄学鬼”提出的问题至少是有启发性的。当时科学派坚决主张人生观问题可以由科学来解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掌握着科学的科学家们自己的人生观似乎更应该由科学来解决了,但实际上远非如此。比如,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要从事科学活动?他又为什么从事这一项科学活动而不从事另一项?这类问题本来很难给出圆满的终极答案,但我们从一些科学家自己的解释中可以窥见他们的人生观,而这种人生观却并不是科学的一统天下——并不能由科学原理和法则来作出解决或加以指导。
正直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活动时,一般来说,当然是遵循科学原理和法则的;但他们在决定是否从事科学活动,以及进行哪一项科学活动时,就难免有许多科学以外的因素起作用了。例如,我们的新闻媒介在介绍杰出科技人物及其成就时,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人目睹中国在某研究领域的空白,深感堂堂中国岂能无人研究此物?于是发愤投身于此项研究。从纯粹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这种动因完全无可指责。然而,“堂堂中国岂能无人研究某某学问”这样一种使命感,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一个科学家是否接受此种价值判断,当然与他的人生观有极大关系,但这却绝不是依靠科学原理和法则可以推出的。比如,一位著名天文学史专家自述,他之所以选择中国天文学史作为毕生研究对象,是由于抗日战争时,日军炸死了他的亲人,他乃发愤挖掘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伟大成就以宣传爱国主义。这里的取舍显然也不能依靠科学原理或法则来作出。
这还只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情形,如果研究领域涉及人文,则科学以外的因素所起作用就更大。即以“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之一胡适来说,他研究《红楼梦》的兴越几十年不衰,晚年自己把这一点归结为“旧恋”。“旧恋”是什么,这里无须深论,但它至少总不会属于科学原理或法则可以解释的范围。又如一位园林专家自述说:“在情难自己时,不免就是写作了,不论学术论文也好,记景文也好,……赏心只有自家知,那种自我陶醉,算是一乐!”写学术论文当然属于科学活动,但其动因却是“情难自己”,目的是“自我陶醉”,这里显然也是科学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
以上所言,都是科学活动中常见的现象,以后也还会继续存在。至于有的人从个人恩怨、政治风向之类的东西出发去考虑科学活动,甚至在科学活动中弄虚作假、欺世盗名,那当然与科学原理和法则更不相容了。但所有上面所谈到的各种情形,都可追溯到人生观上。
到底什么是人生观,梁启超曾在当年的辩论中给出一个定义:
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论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注: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如按这个定义来说,人生观问题确实不是用科学原理和法则所能解决的。迄今也没有任何人能提出一个仅用科学解决了人生观问题的具体例证。事实上,正如梁启超在论战中已经感觉到的,这个问题涉及理性与情感两者各自的有效范畴。
当然,说到底,每个正常的成年人毕竟都是有人生观的。但要弄清一个人人生观的形成机制则极其困难。这里有一片独断的、自由意志的世袭领地,科学和理性难以侵入。由此也就不难推想,试图按一定的模式去“改造”千百万人的人生观,或强迫他们“树立”某种人生观,多半是徒劳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提倡多元和宽容,让人们有更多、更好的选择,而这只有靠人文学术发挥其熏陶、教化之功。
三、重理轻文还是重文轻理?
这里有必要插入一段不算离题的讨论。
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这两者的地位,大多数认为今天的现状是重理轻文。就一般公众的心理而言,这大致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一直是重文轻理的,而且这种传统在今天仍有表现。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教委颁布的学科专业目录的设置:
其中“学科门类”共12种,顺序排列如下:
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
这个名单很值得玩味。我们平时总是“数理化”与“文史哲”并举,分别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代表,然而在上面的名单中,根本就没有“数理化”的位置!原来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等,只是“理科”门类下面的“一级学科”。和“数理化”有同等地位的,可以找到“新闻传播学”、“农林经济管理”、“军队政治工作学”等等。(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1997年。)
还可以举些更鲜活的事例。
1978~1982年间,某著名大学明确规定:文科的学生可以在大礼堂看外国电影,但理科的学生不准看;文科学生可以借阅图书馆所有对外借阅的图书,但有很大一部分人文书籍不准理科学生借阅。这些限制都是通过验看学生证、借书证等来实现的。理由,据说是理科学生对某些人文读物“缺乏分析批判能力”!今天回想起来,这种规定实在是一个大学的耻辱——希望这种荒谬的规定现在早已经废除了。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的天文学史研究人员,曾在上海图书馆遇到类似的、更加令人愤怒的事情:当他们去借阅一些古籍时,遭到粗暴的拒绝和嘲笑:“拿着天文台的介绍信也想来借这些书?”去找有关负责人理论,该负责人则解释说:因为你们天文台是“理科”的,所以不能借。今天我们回忆这些活生生的事例,谁还能说中国是重理轻文?
当然,我们也不难理解,这表面上看起来是旧时士大夫为尊、视工匠为贱役的传统,实际上是被利用来实行愚民政策——尽管它即使按照自身的逻辑也是荒谬可笑的,而且也偏离了本文所打算讨论的问题,但至少在客观效果上,它进一步加深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之间的鸿沟。
四、可能的整合途径
上面插入的讨论,只是想说明,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整合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取消那些明显荒谬的、人为地加深鸿沟的做法。事实上,有些事情已经开始做了。比如上海交通大学规定,文科学生必须修读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课程。也许文科学生深以为苦,其实这对他们来说是极有益处的。当然,可以做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尽管历代的教育制度从来没有使人完全满意过,人们对教育制度的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往往只能“得过且过”。类似的无奈状况还有一些,比如考试制度、官吏选拔制度等等。
人们很自然地将科学和人文的分离归咎于现行教育制度,比如中学里就分文科班理科班,以及大学里课程设置之不合理等等。其实教育制度之设置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是社会的发展和运作使得“术业有专攻”的人容易获利。本来在我国老一代科学家当中,臻于文理兼通之境的大有人在——关于这方面的个案、现象和原因,我们正准备进行专题研究,此处暂不展开。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谁要想步亚里士多德后尘,打算将自己造成一个博学多才,他就要作出远远大于其他人的投入(包括时间和金钱),而回报有多大却难以把握。因此,追求“文理兼通”,在今天还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只有少数有特殊决心、特殊机遇或特殊条件的人士方有可能问津尝试。
这里所谓“特殊决心”、“特殊机遇”和“特殊条件”,值得稍有申论。
特殊决心,是指真的能够淡泊名利,愿意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真要下这种特殊决心是极为困难的。也许少年时曾经信誓旦旦决心甘于清贫,可是真踏入社会之后,即使你本人愿意清贫,你身边的人多半也不能让你清贫——至少在今天是这样。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只有社会足够富裕之后,有足够多的人们不再把钱看得过分重要,而从事“无用的”学问也有不饿肚子的机会,并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时,投入更多金钱和时间完成自身通才教育而不寻求高额回收,才比较容易成为一部分人现实的选择。
所谓特殊机遇,说来话稍长一些。在眼下中年一代人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数很少但潜力很大的‘科学文化人’群体”(刘钝教授语)。该群体中人活跃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交界之处,他们的知识结构颇有异于常人。而这种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文革”时代的特殊环境有关。那时无法正常升学,又很难读到有价值的书。但有些人还是有办法搞到书,他们往往读了很多人文方面的书(因为人文方面的书容易自学)。在这一群人当中,一部分是后来未考上大学的,基本上无法进入学术界;另一方面是考上大学的,则其中绝大部分考的自然都是文科,因为觉得文科基础好一些。这两部分人都无法成为“科学文化人”。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后来考大学时竟考上了理科,这才有机会成长为活跃于两界的“科学文化人”。这应该说是他们的特殊机遇。
但这种“特殊机遇”,原本是一场灾难,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本无心至此”。这种特殊环境,在今天无法重现。也许有人会想:我也故意几年不考大学,就在家里读人文的书,不行吗?恐怕是不行——因为环境和心境都和当年的人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些年青人几乎看不到前途,精神极其苦闷,读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或者说精神支柱,因此他们的读书带有一种“生命体验”(王毅教授语)。今天和当年相比已是太平盛世,年青人无论怎样刻苦砥砺,也不可能有那种体验,读书的效果就会大不相同。
至于特殊条件,含义甚广。比如特殊的家学渊源、极高的天份才情、无限的经济支持之类。不过这些都没有普遍意义,所以目前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至多只能通过“素质教育”(在台湾称为“通识教育”)聊作弥补。
有人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整合,可以通俗化地理解为“文理兼通”,这恐怕是未经深思熟虑的看法。以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文理兼通”不应该是向广大公众提出的要求。它只能是一部分学者向自己提出的努力方向——是一个要求非常之高、非常不易达到的境界。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整合,则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含义。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个人来说,他都可以下决心去尝试,而不必妄自菲薄。下面是某些可能的途径,按先难后易的顺序排列:
从事跨学科的专业
先后修读不同的专业
修习某些本专业之外的课程
保持业余爱好
此外,还有一个“文理先后定律”,必须提请注意,即:
由理入文易,从文入理难。
这是因为理工科需要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专业训练,这些训练待年长之后就很难有效进行了。这也就是所谓的“进入门坎”。
虽然在可见的将来,学科分工所造成的伤害看来还无望根除,但我们至少应该设法减轻这种伤害,而不是去加剧它。文理兼通确实很难,但并非绝对办不到。更重要的是,全面发展,这毕竟是值得人类追求的一个目标。每个人都不应该、也不会愿意去过一个极端单调乏味的人生,达尔文也同样不愿意如此,否则他就不会说出“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等于幸福的丧失”这样痛心的话了。
有一个大学生曾说:“我很想让自己文理兼通,我也坚信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没有时间——我要考托福,要考GRE,我要出国,要找工作,要谈女朋友,……”。看来人生的好事,他是“一个都不能少”。但是事实上,时间绝不是问题,有兴趣就会有时间,更何况,文理兼通这种目标是要准备用一生的时间去追求的——这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收稿日期:2001-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