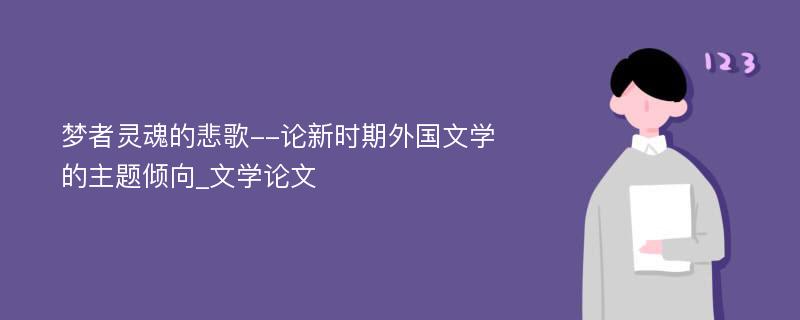
寻梦者的心灵悲歌——简论新时期旅外文学的主题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悲歌论文,新时期论文,寻梦论文,倾向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中后期,在纯文学逐渐低落的中国当代文学园地上,悄然绽开了一朵艺术奇葩——旅外文学。它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出国潮”这一社会现象在文学上的具体反映,是那些远渡重洋、寻求别样人生的炎黄子孙异域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类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新、奇、特的异域风情,崭新的视角,赢得了广大读者。所谓旅外文学,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反映文化碰撞中的留学生及打工者等边缘人心态的文学作品。这一概念是由作品所反映的对象与作者身份决定的。旅外文学的出现,填补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它所塑造的“边缘人”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坛的人物画廊,并为文化市场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仅就它的主题倾向作以如下探讨,旨在促进这一文学流派从稚嫩逐步走向成熟。
一、“边缘人”的文化归宿
所谓边缘人,是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界定的,它是指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特殊人群,他们既难以完全回到母体文化中来,又难以介入到异质文化中去,始终处于尴尬的边缘状态。就像攀附在东西两个板块上的人,无论向东还是向西,都是被撕裂的,无法将自己整合给任何一方。痛苦的边缘人心态是许多旅外者的共同心态,他们始终有着漂泊无依,找不到归宿的感觉。
文化归宿是旅外文学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每一个走出国门的大陆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由一种已经习惯了的且对自己的影响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进入到一个和东方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两难选择。“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力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一种使该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模式。”(注: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中译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它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导致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之不同。
东西方文化碰撞反映到具体生活中来,主要体现在爱情、婚姻、伦理道德和性观念这个层面上。新时期旅外文学涉及这一主题的作品较多,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反映。爱情婚姻、伦理道德及性观念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芥蒂所在。西方的婚恋观念是呈开放状态的,而中国传统的性爱观则向来是将婚姻与性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一切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将被视为不道德的。中西两种文化观念在这一问题上的巨大差异,必然使它成为困扰海外游子的一个重要原因。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在不同的国度它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评判。从这一层面切入,更容易了解文化环境对人们各个方面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易丹的《卜琳》就集中反映了大陆女留学生卜琳出国后,对在国内的男友方明的感情渐趋冷漠,对自己年轻有为的导师——美国教授菲力浦产生了好感。但她毕竟是在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东方知识女性,仍然恪守着东方的传统道德。因此当菲力浦在尚未明确表示与妻子离婚,与她建立正式的婚姻关系前就想占有她时,她便不顾一切地反抗了。一个要追求建立在理想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上的性爱,另一个则是为了达到性欲的满足。中西性爱观念的迥然相异,使卜琳和菲力浦在这个问题上心灵无法沟通,无法建立起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的真诚的交往和理解,导致其不欢而散。和卜琳相比,查建英(笔名小楂)的《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中的女主人公伍珍,这个已婚少妇显然在两性生活上要比卜琳开放得多。为了摆脱国内特定年代造成的不幸婚姻,她毅然走出国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和理想人生,但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地陷入误区而丧失自我。表面上她似乎已被西化,但实际上她与柴荣、山姆等随便的性爱关系更反映出了她骨子里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中国妇女几千年来形成的以男子为依靠,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陈旧观念的影响。但是,她在美国依然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一个人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圆自己的梦,依靠别人只有失望。《绿卡》中的常铁花亦然。纵观走出国门的这些女留学生,她们比男留学生更多一些艰辛和酸楚,在这“人间最寂寞的挣扎路上”,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泪谱写着一曲生命旅途的悲歌。
在描写东西方文化碰撞及其差异方面最出色且有较高品位的是王周生的《陪读夫人》。这是一部反映两种文化、两个家庭、两种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矛盾冲突的作品。以陪读身份而走出国门的蒋卓君是一位温顺、宽容、富有爱心的内向型的东方传统女性,更多一些相夫教子、克己奉献的精神。为了一份优厚的工资,她不得不去西好莱坞城西比尔夫妇家当保姆,连同丈夫儿子一起住进了西比尔家。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朝夕相处,一系列的冲突接踵而至。东方保姆让汤姆仰着睡,而西方母亲却要儿子趴着睡;东方厨师端出一条有头有尾的加州鲑鱼,而西方女主人却大惊失色;生着黄皮肤的中国人以白为美,而白皮肤的美国人执意要去晒黑。蒋卓君在谈到女人的美丽时说“红颜薄命”,露西亚却认为性感的女人不仅能嫁给有钱的丈夫,甚至“在危急的时刻,最先得救的也是那些性感的女人”。关于婚姻,蒋卓君认为“婚姻最重要的是感情”,露西亚却说:“感情是空的,钱是婚姻中第一重要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通过蒋卓君的眼睛,将中国的风俗习惯和美国的风俗习惯做鲜明对比。小说通过一个努力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外向型西方文化传统的典型与一个内向型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代表的比较,揭示了它的深刻内蕴,这是对旅外小说的辛酸、失意、孤独主题的一种超越,在不同的国度、种族之间呼唤沟通、理解和爱。
新时期旅外文学为东西方文化探讨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契入点。以它的“全球意识”、“开放意识”为出发点,在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尊宗祖、尚人伦、重感情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探讨中,找寻体现价值思维方式和选择方式的文化根源。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吸纳新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构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剪不断的中国情结
从此岸到彼岸的空间距离感更增强了海外游子们的责任心和爱国心。在与现实生活情境的对比中,使他们返观祖国,发现那剪不断的中国情结丝丝缠绕着自己,那缕缕乡愁无时无刻不在他们的心头萦绕。爱国主义、乡恋情结几乎体现在每一部旅外文学作品中,成为它的创作母题。
反映在新时期旅外文学中的漂泊感、失落感、孤寂感,实际上都是海外游子爱国主义精神的曲折的反映,而拼搏精神,刚正不阿的骨气,则是他们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直观表现。无论是直观表现还是曲折反映,它都浸透了游子们对祖国深深的爱戴和眷恋。《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的女主人公朱利亚虽然是一名商人,她没有见利忘义,时刻以中国利益为重,因为她清楚,自己永远代表中国。她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当看到这些中国生产的商品标上昂贵的价格,摆设在装潢考究的名牌橱窗中,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安慰和自豪”;当西班牙人故意刁难国内贸易公司,企图敲诈时,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维护中国贸易公司的意识就更加强烈。她竭尽全力帮助国内贸易公司避免了巨大损失。这里面无不包含着主人公那强烈的爱国之情。祖国意识时刻提醒着这些海外游子们要“情系中华”。正因为远离了祖国,这种思念才更具普遍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曾愤慨地说:“你再努力干,拼命地做,可就是因为你的面孔是黄色,你就永远不会有升迁的机会。美国人天天大叫人权,可骨子里,浸透了种族歧视,我受不了那种气。”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还体现在那些学成后回国效力的留学人员身上。《绿卡》中写了一位念化学系并在研究所任研究员的留学生大丑。他获得博士学位后,研究所挽留他,他拒绝了,毅然返回了祖国。他们这种立志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同时也成为新时期爱国主义小说的最重要的描写内容。
思家恋国是海外游子的一种普遍感情。他们对故乡的怀恋,对家园的向往,潜隐地表达了处于孤独、寂寞中的海外游子们对已逝岁月的一种温馨的回忆。“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种思归意识几乎浸透了新时期旅外文学的每一篇作品。将这种乡愁写得最细腻感人的是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在圣诞夜,男主人公廖沈一个人爬到格雷福斯公园山顶上的星象馆,遥望着故乡,思念着亲人。作为陪读的蒋卓君更深切地感到远离故乡、放弃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的痛苦,多次提到要回到自己的家。出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件弃之可惜拿着棘手的“宝贝”,其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最清楚。蒋卓君面对比国内强得多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感到无比的压抑。做了多年母亲的她,照顾一个婴儿还要受到责备。在痛苦的陪读生涯中,她只有靠写日记、靠回忆国内美好的生活而打发日子,一股浓浓的思乡之情浸染全篇。故乡在作品中已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更指向一种精神上的归宿。精神家园乃是人生存的根本,是对短暂人生意义在无可奈何中的升华。美国哲学家威廉·巴雷特说:“一个家乃是我们所接受的,通常包容着我们生命的框架。谁失去了心理容器,就等于被抛了出去,漂泊无依,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漫游者。”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是“边缘人”在异域生活中的共同的心灵向往。
我们把作家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关注,对母语的依恋以及边缘人心态的展示等都视为一种对家园的依恋和回归。小楂的《丛林里的冰河》展示了一个女留学生的回归寻觅的心理流程,作品通过对精神家园的寻找过程,塑造着理想人生。她在美国刻苦拼搏,得到了学业、友情与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内心又感到十分空寂。当多年相交的小伙子向她求婚,她突然感到一条“冰河”横跨在现实与过去、外面世界与内心世界之中。作为理想主义化身的小D已经葬身冰河,“我”从海外归来, 独自沿着小D去西北的方向做了一次远游,去寻找逝去的一种精神, 表现了对人生终极归宿——精神家园的执著追求。冰河在这里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一种无法摆脱的冷酷的现实。“黄河的鲤鱼到了太平洋、大西洋,有一个怎样适应的问题,再游回黄河去,又有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注:于仁秋:《留学生文学座谈会纪要》,《小说界》,1988(1)。)由不适应到适应,需要一个从心理上接受认同的过程,这需要以时间和人们的情感付出为代价。
生活在异域的海外游子们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自己的祖国,怀念着家乡的父老。“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愿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物质的诱惑并不能减轻这种思乡之情,对往昔岁月的回忆如抽刀断水,更平添了几分对现实的不满和抱怨,这些游子们在被异质文化“同化”过程中的艰难抉择表明他们既有融入其中的生存要求,又在感情深处产生着强烈的抵触。“故园在我们想像里成了一种极其奇怪的东西,一面怕与她接近,一面又以强烈的爱情怀慕着她。”(注:绿漪女士:《棘心》,221页,北新书局,1929。)在这种既爱又恨,既想远离又想亲近的故园情感中,潜隐着一份人生的尴尬。新时期旅外文学与五四时期相比,更多的是个体性的经历和体验。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所表述的基本上都是自我的所得与所失,它缺乏五四时期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国情结,便世代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蕴于每一个海外游子的心中。在对故园的无限思恋中,升华着一代人的理想求索。
三、天堂与地狱的洗礼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旅外文学由于其题材和蕴含的独特性,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系列。反映在其中的文化冲突、国家冲突、种族冲突、社会冲突、金钱与人性的冲突乃至价值观、伦理观等多种冲突构成了它的主旋律。在“出国潮”中,有成功者的辉煌,亦有失败者的沉沦,对于这一群挣扎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特殊人群,新时期旅外文学给予其深切的关注。
曹桂林在《北京人在纽约》中自始至终都唱着那首“主题歌”:“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确实, 对于“出国寻梦”的这一群中国人来说,外面的世界确实“精彩”,但也“无奈”。“那座通往成功的桥,又窄,又长,又艰险”,“桥那边,并不是一片乐土田园。桥那边,更是满地陷阱,荆棘丛生。”但必须承认,在那一片土地上,只要你能吃苦,聪明肯干,一样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正是这种种诱惑使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出国门,去寻找自己的梦,去实现自己的梦。人们渴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价值,渴望过上理想的生活,渴望事业上的最大的成功,但这其间必然要经历奋斗的残酷。“打消你的侥幸心理,碾碎不复存在的梦幻,剔除等待别人恩赐的‘邪念’,根绝过高估计自己能力的意识。东京不相信眼泪!什么都得靠自己!”只有奋斗,才是取得成功的钥匙,徘徊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人们,经历着炼狱般的挣扎和痛苦。
朱利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个经历过北大荒磨炼的女医生,在34岁那年来到了美国。她在餐馆端过盘子,当过家庭保姆,终于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凭着百折不挠的拼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起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
王起明(《北京人在纽约》),一家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来到纽约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妻子一起设计构思出全新的毛衣编织图案。他几经沉浮,也终于发展起了自己的公司……
成功者有之,失败者亦有之。《绿卡》的女主人公常铁花为了得到一张永久居留证——绿卡,费尽心机,历尽荣辱,经历了一个由人到鬼,由鬼到人的悲惨遭遇。她及与她同来异国寻梦的姐妹为摆脱厄运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的,以弱者面目采取了诸种方式(包括出卖肉体)来抗争和拼搏。作者通过几个人物的人生经历来告诫人们:一个富有的社会也包含着残酷,那里不是遍地黄金,获取成功需要付出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如果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为人们描绘了人间天堂的温馨,那《绿卡》则展现了人间地狱的凄凉。
在这里,形而下的基本生存欲求远远高于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追求,感性的物质生活意义大大超出理性的精神升华的价值。《我的财富在澳洲》中的老牛就慨叹自己出来后所经历的人生痛苦:“吃不着苦的苦比吃苦的苦还要苦。”他在生病时感到“浑身的疲惫,沉重的经济压力,目下的困境,前程的暗淡,精神的孤独,对遥远妻儿老母的怀念和牵挂……一起涌来。所有这一切在国内时并非完全没有想到过。我自然不会像孩子,把出国肤浅地理解为进天堂。我想到过失业的威胁,想到过就业的艰苦,想到过情绪的孤独,想到过前程的祸福未测,甚至想到过潦倒街头沦为乞丐,自以为精神准备足够充分,可眼下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想像毕竟是抽象的。抽象的痛苦是一条挂在墙上的皮鞭,而具体化了的痛苦则是皮鞭狠狠地抽在身上。”故而他发出了“我的澳洲之行的主旋律,始终是一支悲凉的调子”的感叹。
寻梦者到头来得到的是一个“破碎的梦”。即使如王起明、朱利亚圆了自己的“移民梦”,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王起明在成为富翁以后,失去的却是家庭的幸福,女儿的生命。尽管他在物质上不再贫穷,但他却感到自己“精神上只是零”。周励在取得事业上成功以后,既感叹那里“整个社会都是流动的水,越是大胆冲破羁绊追求自由的人,越是能获得最大的成功”;又无奈于“在大世界里,我们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充满恐怖。没有任何人知道什么时候抢劫和凶杀的灾难会降临在你的头上”。这些寻梦者从自我寻找到自我迷失,无疑成为他们最大的人格悲剧和精神悲剧。在那被扭曲的人性的背后,在那以青春、生命乃至人格的付出为代价的奋斗史中,人们强烈地渴望找回真实的自我,呼唤人性的复归,为寻找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而拼搏。在那浸润着斑斑血泪的人生体验中,在那天堂与地狱的洗礼中,只有靠顽强的奋斗精神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朱利亚、王起明是两位成功者,作家以他们自传的形式把作品展示给读者,从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感受和精神上的鼓舞,为几乎被压抑笼罩的旅外文学增添了一缕亮色。作家凭借对域外生活的了解,通过文学形式为我们展现了勇于向命运挑战,与命运抗争的创业精神,展现了海外游子们在饱经磨难的奋斗历程中所带来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
笔者从以上三个方面概括了新时期旅外文学的主题倾向。其实这三个方面是经常混合在一起的,很难从同一作品中加以明确区分,它们共同合奏了一曲寻梦者的心灵悲歌。
标签:文学论文; 北京人在纽约论文;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论文; 边缘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