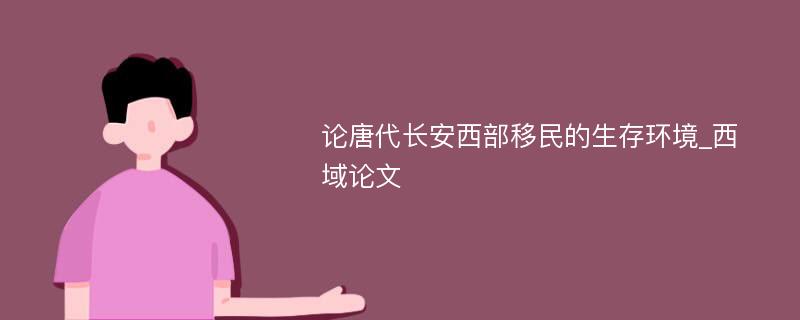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域论文,长安论文,生活环境论文,唐代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移民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外来移民人数最多最活跃的国都城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被称作“胡人”的西域移民及其后裔。我们在西安地区出土的大量陶俑或壁画中可看到,高鼻深目络腮胡须的胡人形象比比皆是、造型各异,从将军武士、文臣官吏到骑驼商人、歌舞乐人,神态不一又栩栩如生。许多出土墓志也真实地记载了西域移民的活动事迹,填补了史书遗缺。学术界由此断定唐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当时“开放、流动、融合”的汇聚地,笔者也赞同这样的判断。但人们往往对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重视不够,本文试作一点审视。
一
初唐时由于朝廷急于稳定周边,联络盟友,征服四夷,扩疆拓土,特别是为对付突厥汗国和其他民族的压力,所以对西域移民采取笼络手段和礼遇政策,不管按照何种路径和方式进入长安的胡人,都没有将他们作为国都里下层部分,常常还表现出足够的“怀柔”善意,允许与汉人通婚。即使一些胡人违法乱纪,也没有对他们采取群体“有罪推定”,《大唐新语》卷九记载贞观年间,有胡人劫盗金城坊人家,雍州长史杨纂要将京城所有胡人都捉来审问,司法参军尹伊认为不妥,因为胡汉杂处,“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这样破案线索不株连其他胡人,显示了对外来移民的信任与宽容,因而大批胡人向往长安,蜂拥而至。在北方突厥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朝廷也没有乱了手脚,而是分别对待,方寸不乱,促使许多胡人率先从军,担当起保卫长安的责任,甚至以宿卫皇宫为信任和荣耀。
胡人远来,被朝廷视为外国来朝,这是文治武功的理想境界,尽管有些汉人官吏对重用胡人有担忧,武后时薛登上《请止四夷人侍疏》,但朝廷为了地缘战略利益顶住汉臣压力,蕃将汉兵在军功面前比较平等,有时还有意提高胡人奖励“等级”,“开怀纳戎,张袖延狄”,以鼓励他们为朝廷效忠卖命。一般来说,唐朝廷为新移民提供较为公平的生活环境,打通他们及其子弟提升上进的通道,甚至“爱之如一”有意帮助他们,从而使西域胡人能和长安汉人和谐相处。所以,许多胡人并不讳言他们的胡族家世渊源,在家族墓志上镌刻自己“家世西土”、“发源西海”,描述自己“本西域康国人”、“西域安息国人”、“其先安国大首领”(注:关于西域胡人墓志的研究,论者较多,比较集中的代表作见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第13~24页;李鸿宾:《唐代墓志中的昭武九姓粟特人》,载《文献》1997年第1期;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东迁及其聚落》,载《国学研究》(北京大学)第6卷,1999年。)等等,明确保存有清晰的异族观念和外夷心态,甚至夸耀入华后“外来户”辉煌的贵胄门第来源,以便在唐朝等级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唐朝贵胄本身出自鲜卑外族,种族观念淡薄,华夷政策兼容,《新唐书》卷一七○《王锷传》记载:“天宝末,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陇右既陷不得归路,皆仰廪鸿胪礼宾,月四万缗,凡四十年,名田养子孙如编民。”这些逗留长安的胡人给唐朝廷增加很大经济负担,他们一面领取官府供给,一面举质取利、买田宅、娶妻生子,有的居住四十余年,仅检括出来就有四千多人,加上早已脱籍的胡人数量更多,官府将他们中不愿回归者全部编入神策军,并依据身份安排不同官职,继续为唐朝效力。
安史之乱搅得周天寒彻,胡兵反叛的源头和渠道当时人们还是分明的,始作俑者仅仅是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在长安时任户部尚书的安禄山堂弟安思顺还先奏其谋反,罪名戴不到所有胡人头上。即使在安史占据的重灾区里,受到拉拢和引诱的胡人也并不全都追随叛军,有很多胡人还参加了平叛战争,朝廷“以蕃制蕃”的策略仍在实施,一些蕃将严防死守,英勇对抗安史叛军赢得了汉臣的敬佩,民间众多汉化很深的胡人主动断绝了与安史叛军的联系。特别是朝廷借助回纥等胡兵平叛陡然提高了胡人的地位,迫使汉臣以谦卑的情怀来期盼强劲的胡兵镇压叛军。
但夺取收回长安、洛阳两京后,回纥倨傲态度与抢掠行径,敦促汉臣反思曾经居高临下的心理态势,刺激汉族士大夫们反思自己脆弱的特权,经历过震撼、屈辱、躲避的汉族官员涌出一种对胡人蛮横无理、不仁不义的反感。汉族臣僚开始处处提防制衡蕃臣胡将,士大夫们气势磅礴、声色俱厉地宣扬大唐的恩威,不断斥责胡人的贰心不忠,他们认为“胡人官至卿监、封国公者,著籍禁省,势倾公王,群居赖宠,更相凌夺”(注:《新唐书》卷145《王缙传》。),是长安藏奸宿乱的祸根,所以在朝廷中弥漫着一种规避风险、提防排挤外来移民的氛围,并直接影响着早已身心交瘁的朝廷统治者作出一些浅薄愚蠢的决策。
胡人在长安面临着许多起点上和程序上的不公平,在汉人眼里他们应该多一些惜福感恩,少一些跋扈轻狂,于是处处压制圈禁他们,对胡人将帅更是猜忌防备、怀疑惧怕,血气方刚、直率单纯的胡人受到汉臣的掣肘却隐忍不发,怕被排挤出长安,生存不易,只能委曲求全,退避三舍,可他们心里充满冤屈怨气,一有机会,播种的侮辱仇恨很容易就变成一种分离的破坏力,仆固怀恩、李怀光等在胡将蕃兵鼓动下抗争反叛的事例,在中唐后屡屡发生。初唐胡汉融合的正常秩序到盛唐那种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社会心理与晚唐排外情绪了。
二
在重农抑商、重儒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经商贩卖是大多数汉人所不愿做的,盛唐以前社会安定、生活环境稳定优越,这正给了胡商很大的机遇,他们要在京城长安和中原经济发达地区生存发展,从事商贸获利不失为一条生计发展之路,只要取得唐朝边境州县过所即可前往内地进行贸易,这也是吸引大量各类胡商来华经商异常活跃的原因之一。
这些源源不断来自西域的胡商不畏艰险,善于筹算,有的拥有巨资,有的博学多闻,有的善于识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唐朝的商业经济,但是,胡商要获取丰厚利润,必须具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况且胡商从事的行业各种各样,仅从《太平广记》等笔记史料描写来看,有的从事药材生意,有的开设珠宝买卖,有的出售金银、玉器,有的开办波斯邸,有的从事“酒家”、胡饼店等饮食行业,其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小本生意,胡商的出身也多种多样,《集异记·李勉》篇波斯老胡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原化记·鬻饼胡》篇云京城鬻饼胡商自称:“某在本国时大富,因乱,遂逃至此。”敦煌文书P.3813《文明判集》第114~126行记载长安胡商史婆陀:“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王侯。”在唐人眼中他们发财巨富生活非一般人可比,但“婆陀阛阓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地寒微”;没有夸耀的门阀。特别是胡商家庭亲兄弟也计利忘义,互不救济,被唐人理解为性格贪婪,伦理松弛,不耻与他们来往,这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描绘窣利(粟特)胡人特点是一致的:“风俗浇讹,多行诡诈,大抵贪求,父子计利,财多为贵,良贱无差。”胡风汉俗文化背景大异其趣,使许多西域移民只能聚居在自己认可的圈子里生活。
由于安史之乱后对外陆路时通时断,兴贩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滞留在长安的胡商生计无着,只好以质举取利为生,经营借贷业务,这又诱发唐人的嫉妒,他们向胡商借贷后恃势不还,太和五年(831 年)唐文宗颁布诏令称:“如闻倾来京城内衣冠子弟及诸军使,并商人、百姓等,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要与更改。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辄与蕃客钱物交关。委御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条件闻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负,委府、县速与征理处分。”(注:《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这里所谓的“蕃客”即指外来胡商,他们索偿不得,饱受委屈,致使停滞市易,可知从业环境非常恶劣。开成元年(863年)六月,京兆尹又奏称:“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乾符二年(875 年)朝廷南郊赦文中提出禁止举债人钱买官或纳粮求职,特别强调如果借波斯番人钱,要按脏物罚款没收。(注:《唐大诏令集》卷12《乾符二年南郊赦》。)实际上,朝廷也“籍京师两市蕃旅、华商宝货举送内库”(注:《新唐书》卷208《宦者传·田令孜》。),说明从胡商手里强夺巧取一直没有根绝,不仅严重削弱了胡商的经济实力,而且使他们无法正常生存。
中唐时期,胡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安史之乱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尤其是胡商的流动性有助于沟通南北方的商业经济互通有无。当然,胡商在盛唐到中唐的经济运行转变秩序中,也促进了唐代奢侈挥霍之风的增长攀升,许多胡商从事经营珠宝的职业,为了兴贩追求暴利不惜剖身藏珠,中唐以后笔记小说里有不少胡人贱身贵珠、身亡宝存的故事,长安达官贵人和社会富人稍遇稳定太平即追求生活享受,又刺激胡商“贡献”珍珠、玛瑙、象牙、犀角、精玉、玻璃等种种奇珍异宝。《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尽管朝廷屡次禁断珠玉器玩,不许进献异域珠宝,但在唐人看来,珍宝价值昂贵,又是财富的象征,“胡客法,每年一度与乡人大会,各阅宝物。宝物多者,戴帽居于坐上,其余以次分列。”(注:《太平广记》卷403《魏生》。)这种较量宝物贵贱和交换寻访宝物的斗宝活动,是胡人商客夸耀财富的独特表现,当时汉人却认为这是商胡投机致富、唯利是图的本性。
所以,唐人对胡商存在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经济上羡慕其富有号称“千金贾胡”,动辄以几十万甚至上千万的金钱买卖奇珍异宝,李义山《杂纂·不相称》将“穷波斯”列为十一种不相称情况,他们实用主义地希望借助胡商的财力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与困难,但又惧怕胡人力量过大,内心不情愿胡商掌握经济命脉的走向,不仅文化上宣传儒家的义利观,渲染胡商的吝啬贪婪,采取对胡商“边缘化”鄙视的态度;而且在经济上遇到危机时,对他们实施比较宽泛的打击剥夺手段,迫使许多善于经营的正派胡商也生存迷茫,难以维系他们生活的来源。
三
西域胡人带来的文化是“胡风”炽盛鲜明的标志之一。表演艺术主要是音乐舞蹈、节庆狂欢,胡旋舞、胡腾舞等。这种乐舞在民间盛行一时、风靡不衰,但在统治贵族阶层和士大夫官员们中既有津津乐道的欣赏,又有居高临下的鄙视,经常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变化而翻云覆雨,将西域艺人比做“西向悲泣”、三教九流的江湖流浪者。
如唐中宗时曾在两仪殿设宴,“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有大臣遂上书谏劝“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注:《新唐书》卷119《武平一传》。)面对胡乐的冲击与胡歌的流传,正统的汉臣鄙视或敌视胡人“夷狄音乐”是伤风败俗的靡靡之音,甚至提高到国家衰亡层面上去向皇帝说教,认为凡属胡乐,除招待异域来宾外,对内一律不得使用。
又如源于西域康国的泼胡乞寒戏,每年“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交泼为乐”(注:《新唐书》卷221《康国传》。)。相传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时,饱受干旱的百姓在国王祈祷下降雨拯救幸免于难,从此感谢王恩以水相泼成为仪式。这种民间驱邪消灾的节庆,曾在长安流行很长时间,每年十一月各坊里居民组成浑脱队擂鼓挥旗,裸体喧噪,相互泼水,腾跃竞逐,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从皇帝到百姓都喜爱这种大众游戏气氛,但此类带有浓郁异域情调的民间狂欢,既与朝廷提倡的传统礼仪互不相容,又被汉人看作是夷狄巫术余音遗响,所以中宗、睿宗、玄宗时连续有一大批官员屡次上书,认为“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呼吁禁止泼胡乞寒这类“裸体跳足、挥水投泥”的“胡俗”“胡风”,开元元年(713年)被“无问蕃汉,并加禁断”;天宝初韩朝宗再次上书要求严令禁止。
再如源于中亚的胡旋舞、胡腾舞一直在长安宫廷内外盛行,皇家贵族和官僚士大夫既喜欢这类急速旋转如风的舞蹈,又对胡人表演者持歧视戏弄的态度,嘲笑“石国胡儿人少见,蹲舞尊前急如鸟。手中抛下蒲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讥讽“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中唐时元稹《胡旋女》诗歌中甚至把胡旋女和妖胡联系起来:“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胡旋女》诗中也责备:“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余里;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元、白描写胡旋女的本意是批判“世风不古”,将这些能歌善舞的胡人男女,往往变成为被瞧不起的断归故乡路的下等人,或讥讽为“弃土不识离别苦”的寻欢作乐者,处境并不见好。
此外,西域幻术戏法自汉代以来传入中原地区,相传大秦、天竺幻术不断与中国的散乐杂技相结合,吞刀吐火,屠人截马,断舌剔肠,画地为川,这种惊险刺激表演场面,被称为“胡戎之乐,奇幻之戏”。统治者一度允许西域幻术戏法流行,目的是盛张国家威势,壮异域臣服景观,由于幻术戏法与祆教传教手段紧密联系,裸袒戏谑引起许多汉人的惊恐,列入奇诡凶兆怪术,视作有损风化的乱纪败俗,高祖时长安官吏就提出“百戏散乐,本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注:《大唐新语》卷2。)。高宗显庆元年(656年),禁胡人为幻戏者,但民间屡禁不止,仍乐此不疲,一直变化延伸到中唐。唐朝统治集团中一些慷慨激昂恪守祖制的臣僚,对外来文化的疑虑和忧患,很容易萌生出敏感的排外心态与摇摆的负面效应,即使在盛唐时期胸襟也还不够成熟阔大。
四
西域传来的宗教中,祆教、景教、摩尼教号称为“三夷教”,这三种外来宗教得到唐朝廷的正式认可,在长安建有寺院,朝廷的宽容是为了安定西域移民的人心,鼓励胡人为唐朝效忠服务,但在长安占优势地位的佛道两教却不容“杂夷”宗教扩大地盘,并影响到朝野士民也对“三夷教”持贬斥态度,不时发起对祆教、景教、摩尼教僧侣的谩骂、诽谤和攻击,迫使朝廷颁布对他们传教范围的限令,只允许在外来移民的生活圈子中活动。
祆教起源于波斯,又名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在唐朝以前就已传入中国,据《通典》记载:“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商胡奉事,取火咒诅”。长安布政坊等胡人聚居地方有五所“胡祆祠”,祆教祭祀活动时带有强烈娱乐成分,“每岁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注:《朝野佥载》卷3,中华书局,第64页。)唐朝禁止汉人信仰祆教,但祆教风习却随着胡商活动在民间渗透,有可能私下传布。会昌五年(845 年)外来诸教遭受毁灭时,管理火祆教徒的萨宝府也随之罢废。1955年发现的波斯后裔祆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志,表明祆教在晚唐禁而不止,仍然存在,民间同情者或信奉者大有人在。
景教作为基督教在东方传播的一支教派,最初入唐以“波斯经教”为名,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诏令在长安义宁坊建立“波斯寺”,在朝廷的认可和支持下开始传教,高宗时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武则天到玄宗即位时,景教一度受挫,受到佛教徒和儒士们的攻击,许多士民嘲笑讪谤,不仅景教徒处境困难,整个景教都面临危机,迫使景教士改变生存方式,为皇室修功德,进献奇器异巧,提供外来天文术等,才挽救了被压迫的局面。中唐后景教士在民间的慈善活动使他们遭受非难减少,但会昌毁佛仍没逃出衰微的厄运。
摩尼教高级僧侣慕阇乌没斯拂多诞在武则天时到中国,其教义得到朝廷赞许,但遭到“群僧妒谮,互相击难”,所以没有允许在内地传教,过了25年后,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吐火罗再次以慕阇精通天文为由,请求唐玄宗垂询摩尼教法,才在长安设置法堂。可是开元二十年(732年)又被禁止在民间传播,敕令称“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注:《通典》卷40《职官》22。),故外来移民“西胡”可以信奉摩尼教,向汉族民间传播的势头却受到了遏止。直到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借助回纥力量才逐渐在长安再度流传,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摩尼教徒建立了京师大云光明寺,有了一席之地。随着回纥势力的衰亡,摩尼教徒更是受到处处受难,会昌三年(843年)被朝廷彻底禁止,京城女摩尼七十二人死,其余流放,下落不明,踪迹难寻。
唐后期,朝臣普遍认为唐朝境内所有的外国宗教都属于“邪法”,建议一体进行打击,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毁佛时,为“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国之风”(注:《唐会要》卷47《毁佛寺制》。),祆教、景教等全部属于被禁之列,共有三千余人被迫还俗,维系外来移民内部聚落凝聚力的精神纽带从此被割断。
这种宗教冲突引发的一场冤罪,以及随之带来的种族驱逐,自然伤害了普通人的心,也是统治者在国运不济失去自信宽容后软弱无力的供认。尽管历史文献没有记载胡人以后的命运,但他们在前途未卜忧心忡忡的背景下,不可能再为唐王朝出力效忠,反而有可能加入各地藩镇军阀反叛的阵营,成为离心对抗的一股力量,加速了唐朝的动荡与灭亡。
五
大多数西域胡人进入长安后都想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地,试图和谐共存,和平共处,使出浑身解数表现友好,特别是他们既带入了中亚、西亚的饮食、医药、香料、织锦、玻璃、葡萄酒等等物质文化,也传入了西域音乐、舞蹈、美术、雕塑等艺术文化,不仅使长安官府吸纳了波斯天文、历算、建筑等科技文化,也使民间融合了宗教、节庆、方术等精神文化,极大地补充、丰富了唐文化。
但西域移民毕竟有自己的特点,胡人体态相貌、服饰装扮、生活习俗、思维习惯都与本土汉人有所区别,人口占多数的汉人往往因不习惯胡人的特点而引起鄙视排拒的心态,例如,胡人“体有臊气”,于是“狐臭”与“胡臭”相通成为胡人歧视性的代称。(注:陈寅恪:《胡臭与狐臭》,《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42页。)男性胡人截髪长髭,聍目磋齿,胡人女性梳辫盘髻,香油涂发,又引起汉人先入为主的惊异之感。即使“胡姬”之类的年轻胡人女性顾盼生姿、面容美貌,也被认为不是举止雅重、温良恭顺,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常常借“狐”(胡)隐喻影射,被描写成魅惑诱人的“狐狸精”和“妖狐”。(注:王青:《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云溪友议》载唐陆岩梦桂州筵席上赠胡女诗:“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诗的前段讥讽胡女自诩风流,调侃胡女的长相,后段嘲笑胡女舞态歌声不够超绝,文人尚且如此,一般民众对胡人外貌的歧视就更可想而知。
西域胡人中除佛教僧人穿着缁服外,普通百姓以穿白衣为常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一说:“西域俗人皆著白色衣也”。按照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解释西域服色禁忌:“吉乃素服,凶则皂衣”。胡人这种崇尚白色的服饰装扮,与汉人喜爱的服饰颜色恰恰相反,造成的心理状态更是不同,被认为是“服妖”不祥凶兆迹象。
胡汉通婚在唐代比较普遍,《东城老父传》载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广异记》说唐天宝年间“东平尉李黁初得官,自东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故人卖胡饼为业,其妻姓郑,有美色,李目而悦之,因宿其舍。留连数日,乃以十五千转索胡妇。既到东平,宠遇甚至。性婉约,多媚黠风流,女工之事,罔不心了,于音声特究其妙。在东平三岁,有子一人。其后,李充租纲入京,与郑同还。”撇开故事中胡妇死后变“牝狐”荒诞细节,以及胡妇被丈夫十五千就转卖的命运,故事结局是李黁被常呼作“野狐婿”,其具有西胡血统的孤儿远寄人家,遭受歧视,不给衣食。说明胡人女子试图融入汉族家庭仍面临困境,“少年胡心”混血儿在当时生活境遇更不会有多好。胡汉通婚家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尽管史书没有过多事例详细记载,但不难想象各级官吏和民间百姓的排拒心态,歧视丑化一笔抹杀往往视为理所当然。
此外,在唐人笔记小说中还有一些各类胡人神怪奇异的民间传说,有的美丽胡女化身变为鬼狐,有的苍首老胡畏狗成为怪尾狐,有的商胡狡猾敛财吝啬如青鬼,有的壮胡劫掠行人似歹鬼,这些负面形象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外来移民抱有偏见不愿接纳的背景,长安胡人生活环境有着不容乐观的隔阂一面,他们担心被排挤、恐惧被迫害,只能聚居一起互相照应,这可能是胡人及后裔多集中于西市周围里坊的原因之一。
遗憾的是,我们在历史文献和出土文书中看到的多是外来移民对大唐朝廷的歌功颂德、进贡献物的顺耳之言,很难找到官员及文人士大夫对唐朝廷一些保守排外思想的逆耳之音,或许是当时官方删除掉了触犯时忌的批评谏言,这就使得唐朝廷眼睛里总是国运通泰,不愿反观自身和准确认识外部世界,一遇外来冲突旋涡,马上作出狭隘的敌意反映。
外来移民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流动的标志,更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长安始终是外来移民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它比其他城市承载过更多的劫难屈辱,从隋末唐初动乱、突厥兵临城下、安史叛军蹂躏、吐蕃占据半月,军阀混战烧杀,藩镇轮流攻掠、黄巢占领京城,一次次频繁上演历史悲喜大剧,外来移民也遭受了无数次冲击。西域移民在这个国都城市生存繁衍发展,需要朝廷海纳百川胸怀、官府的优待恩惠和百姓融合相处态度,随着政治沉抑、军事冲突、民族摩擦而造成的环境变化,使他们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与歧视,“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华夷相交侵”(注:《全唐诗》卷440白居易《听李士良琵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酿成政治的保守和文化的封闭,这确实是一个不愿看到的苦果。如果说文化、信仰和价值观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与重要动力,那么没有外来移民的交流,就没有人类博采众长、多彩文明的进步。我们不能只讲盛唐文明自豪的雄风复兴,不讲唐朝时代变化背景下失去包容的文明逐步衰落,需要前后对比扩展人们重构文明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