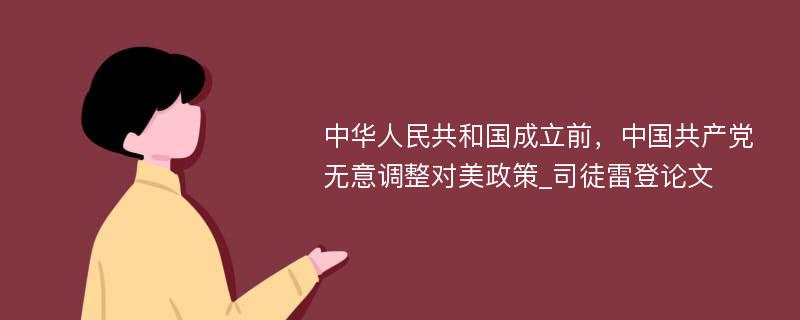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前中共没有调整对美政策的意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图论文,对美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中共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2)01-0045-04
1949年初,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有关未来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南京解放后,美国政府为了打探中共对美政策的意向,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向中共表示了一些外交上的主动,中共对此给予了相应的重视。据此,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前,正是中共在对美政策的强硬立场和杜鲁门政府没有允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才使本已开启的中美友好的大门被迫关上了。国内也有人认为,针对美国在外交上的主动,中共曾调整对美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接触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笔者认为,在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态度,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对抗。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并不存在中共调整对美政策的可能性。对于这一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笔者拟提出以下看法,以就教于学术同行。
一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总结近代以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卷四,第1471页)的结果。“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卷二,第650~667页)中国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使它从一开始就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解放战争期间,由于美国推行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对华政策,因此,革命愈接近胜利,中共对美国干涉中国革命保持的警惕性就愈高。在1949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的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面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现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2](卷五,第231页)为了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这次会议确立了不急于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规定,“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以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从此以后,“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自己的政府解决”。[3](第77~78页)但是,“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4](第809页)鉴于帝国主义国家百余年来对中国的侵略和影响,我们的方针应该是“另起炉灶”,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5](第85页)同年3月,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解决”。中共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是由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3](第80页)4月17日,针对美国国会有关承认中国问题的争议,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在原则性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它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司徒雷登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是美国政府“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因此,我们应该站稳立场,做到“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6](第323~324页)以避免对外政策上的被动局面。由此看来,中共在对美政策上的原则是坚定的,在策略上又是灵活的。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国家钻空子,利用旧的外交关系向中共施加压力,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条件下,中共拒绝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关机关和外交人员发生任何正式的交往。所以,平津战役结束后,当北平的美国助理武官包瑞德上校要求与当地政府发生接触时,遭到了中共的拒绝。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共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接触。1949年夏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就是一例。
二
对外政策既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制定的外交战略是“一边倒”,目标是争取苏联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对新中国的同情与支持,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如果中共调整对美政策,谋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与“一边倒”的战略目标是不一致的。
那么,如何对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外交主动呢?这就需要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美国的外交主动是在其扶蒋反共的政策遭到失败、对华政策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明显的两面性。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局已定,美国试图“阻止中共统治中国”的目标已经落空,对华政策的目标逐渐转变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并尽可能地保护美国在中国的传统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在外交上暂时改变了过去对中共一贯的强硬立场,从1949年春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共拉关系,试探中共的对美政策。南京解放以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继续留驻南京,寻求与中共接触的机会。作为对司徒雷登留驻南京一事的反应,4月28日,毛泽东在给总前委粟裕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2](卷五,第285~286页)许多学者以此为据,认为中共对美政策发生了变化,但笔者认为这只是中共对美国外交主动的一种灵活反应,这种反应看来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试探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向,便于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把握主动;另一方面则不能排除间接给苏联施加一点压力的考虑。众所周知,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中苏结盟的大局已初步确定,但南京解放后,苏联并没有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其驻华使馆人员也随之南下广州。为此,中共中央决定由前燕京大学学生黄华出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并指示他“除负责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外,可以同司徒雷登进行私人接触”。[7](第24页)
中共对此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是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矛盾呢?显然不是。中共不急于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并不等于不和这些国家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在对美政策上,中共既强调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黄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接触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灵活的斗争策略。从中美关系当时的状况看,中共不宜在外交上采取主动,因为这不利于在政治上与美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更不利于中苏结盟战略目标的实现。反过来,如果美国采取主动,中共则应该积极地灵活响应,一味的拒绝将会把中美对抗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从而陷入被动。为了防止美国钻空子,早在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之初,毛泽东就指示“与司徒雷登的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司徒雷登在谈话时可能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的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3](第88页)况且,黄华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对于曾担任过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来说,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双方的接触也可以看做是私人接触。这种非正式的私人接触与中共制定的对美政策并不矛盾,一则可以避中共主动寻求改善中美关系之嫌,二则可以试探美国对华政策之动向,是一种机智、灵活的斗争策略。
根据黄华与司徒雷登谈话的结果来看,中美双方接触目的都在于投石问路,均无建立外交关系的真实意图。首先,美国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美中关系。早在1949年1月,杜鲁门就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同一个共产党政权打任何交道。”[8](第127页)即使在司徒雷登与黄华接触期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仍多次指示司徒雷登说,“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以免“政治上鼓励共产党,使国民政府沮丧”。[9](第17页)很显然,美国政府既想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又不愿意彻底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但是,为了离间可能的中苏同盟,美国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与中共接触。由于美国一直把对中共政权的承认看做是美国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故而在有关承认的问题上,坚持新政权应该“在事实上控制着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关;既有能力又有愿望承担其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可”。司徒雷登在与黄华的会谈中,还提出以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未来的政府中接纳“民主人士”,不与苏联结盟等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试图从根本上影响新中国的对外政策。[9](第21~23页)其次,中共始终坚持“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关系,永远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问题”。[3](第87~88页)会谈期间,黄华严厉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认为美国应当对中国内战负责,并且在与中国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方面采取主动。此间,中共还一再声明,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停止对中国反动派的一切援助,是任何外国政府与中国新政权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且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在这些原则性问题上,中共决不让步。[3](第91页)
由于中美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从革命运动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美国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对于中共都是最令人憎恶的敌人和最危险的外部威胁”,[10](第96页)双方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美国根本不可能采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更不可能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就在司徒雷登与黄华会谈期间,麦克阿瑟还派两个美国士兵团在青岛登陆,并加强了在上海的舰队。“尽管艾奇逊在对华政策方面显得不太僵硬,但他对于寻找任何可能与中共和解、建立关系的机会仍然是不精心的。”[11](第123页)在与中共寻求接触的同时,艾奇逊还决定“美国不应该对承认问题首先表示出热情,并指示美国官方人员向西欧各国政府施加压力,希望在此问题上形成一条统一战线”。[11](第121页)与此同时,中共对这次会谈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会谈期间,中共就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可能的干涉“预筹对策”,尤其对“预防美帝国主义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作了详细部署。[2](卷五,第302~303页)另一方面中共也没有采取任何旨在缓和中美关系的实质性行动,甚至没有释放被监禁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1949年6月30日,在公开宣布新中国外交将“一边倒”的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南京市委,声明:“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10](第105页)第二野战军横流长江以后,一直在长江下游停留至9月间,主要的目标就是防备美国可能的武装干涉。因此,有理由认为,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甚至中共同意司徒雷登以私人身份访问北平,主要是中共对美斗争的一个策略,目的是向他“表明中国方面的政策,敦促美国停止扶蒋反共,如此而已”。[12](第263页)而美国国务院7月1日给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9](第769页)的指示,则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坚持反共、反华政策的顽固立场。由此可见,“即使司徒雷登成行,当时中美关系也不可能有重大改变”。[12](第264页)
三
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共对外政策形成的关键时期。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美苏冷战的国际背景,1949年中共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根据米高扬对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看法,他也认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把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置于中心地位”。[13](第21页)为了促成“一边倒”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的问题上是十分谨慎并注意听取苏联的意见的。由于苏联当时还保持着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共一时还得不到苏联的经济援助。1949年4月,当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做生意的意向时,毛泽东通过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向斯大林表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事实上的联系,但不在法律上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回电表示:“第一,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话。第二,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14](第123~124页)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既同情,又怀疑。对于斯大林在有关中共如何处理与美国关系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斯大林对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苏联与美国冷战对峙的利益;其次,由于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和中苏两党之间仍然存在的不信任,斯大林也不愿意直接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以免造成干涉中共的后果;另外,中美关系的尖锐化在当时也不符合苏联的利益,如果美国一旦出兵干涉中国,苏联将面临十分困难的选择:如果卷入,将导致美苏直接的军事冲突;如果回避,苏联就有可能失去中国这道屏障,甚至丧失在中国北方的既得利益,而这两种结局对苏联都是不利的。因此,对苏联来讲,中美之间最好是中共既与美国保持接触又不与之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从斯大林给中共的电报看,他虽然赞同中美建交,但他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根据科瓦廖夫的看法,他也认为,“斯大林对中国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态度是不十分积极的”。[15](第28页)为了保证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的建立,中共在没有摸透斯大林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始终没有接受美国任何形式的贷款和经济援助,更不用说谋求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了。但是,有些西方学者把“1949年中共不能与美国实现某种缓和的主要障碍”,归因于“苏联施加的压力”,是“苏联有意识地要恶化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或者是“中共对英美政策的强硬性和在处理英美关系上的固执”,[16](第266~267页)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近年来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可以看出,斯大林并没有对中共直接施压,他并不希望中美矛盾激化。但他对中共的不信任,则进一步促使中共执行坚决的“一边倒”战略,以求中苏战略同盟的早日实现。
渡江战役前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多次就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关于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说:“司徒雷登撒谎说美国人好像停止支持国民党政权了,我们了解的情况却相反,这种支持一直在积极进行。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等国大使馆留在南京一事,这又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假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大使馆撤离中国,我们才高兴呢。”斯大林在5月26日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请他转告毛泽东,他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评论”,“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通报的情况”。[14](第125页)中共在对美关系的问题上,之所以不停地征求苏联的意见,并不是由于缺乏对美斗争的经验,也不是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缺乏认识,主要目的就是要争取苏联和斯大林的信任,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毛泽东不能也不想为同美国建立不大可能的关系而破坏和苏联的友好关系”。[15](第30页)1949年5月,就在黄华与司徒雷登接触期间,中共中央做出了派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的决定。由此可见,对苏关系在中共对外政策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对美政策则是服从于这一目标的。刘少奇访苏的巨大成功和美国政府不许司徒雷登访问北平的决定,进一步加剧了中共对美国政府的厌恶与敌意,促成了中苏联盟与中美对抗局面的最后形成。
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美国仇视新中国的根本原因,由此而造成的双方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严重对立,以及在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方面的冲突,促成了中美对抗的格局,而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则使这种对抗进一步加深了。冷战格局使“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就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17](第455页)对于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早在与司徒雷登接触以前就已确定,不可能因为美国缺乏诚意的外交主动而在对美政策方面进行新的调整。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如果美国能继续与中共进行谈话,亚洲二十多年的许多误会和痛苦就有可能避免”。[11](第126页)但是,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美国政府有没有继续谈话,有没有让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而在于美国对中共和中国革命根深蒂固的仇视,在于美国不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以领导世界为己任、“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国家来说,[3](第165页)想要使之改变对新中国的态度,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美国对苏联的承认就拖延了16年,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不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较量,美国是不可能真正承认中国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有理由认为,黄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主要是中共外交斗争的一个策略,并不是中国调整对美政策的标志。
收稿日期:2001-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