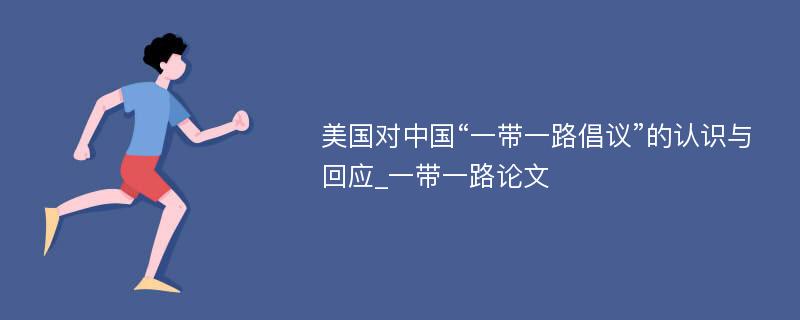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反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认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5年8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5)10-0104-29 近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后采取了更为积极进取的外交姿态,提升了对周边外交的布局意识并加大了相关工作的力度。其中尤为引人瞩目的是2013年9—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此后,经过2014年前后各部门紧锣密鼓的座谈、规划和部署,这一倡议在中国国内进一步凝聚了共识。在此期间,中国还与有关国家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为此专门设立丝绸之路基金,以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又联合发布了名为《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官方文件,①它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成为中国的一项国家大战略。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激起广泛讨论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引发了强烈反响和不同解读。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中小国家,由于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资金严重匮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所以它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总体上持欢迎态度。②还有一些沿线大国,它们既想分享“一带一路”战略可能带来的好处,但是又担心这一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因而持怀疑、观望的态度。例如,印度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看法就存在着较大分歧,“机遇论”和“挑战论”并存,官方则采取了“没有态度”的表态,显示出谨慎应对的立场。③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域外国家的态度也至关重要。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共赢性决定了参与国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不会局限于沿线各国,而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另一方面,在一个相互依存、互联互通的全球化时代,“一带一路”战略能否顺利实施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也离不开域外国家尤其是域外关键大国的理解和支持。显而易见,在众多域外国家中,美国的角色无疑是最为突出、也最为值得关注。 美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第一,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触角早已遍及包括“一带一路”辐射地区在内的全球各个角落。不仅如此,美国还是塑造中国周边环境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之一。因此,“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及其后续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的影响,这凸显了把握美国态度的必要性。④第二,美国是现有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主要创设者和主导者,是既得利益国家。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折射出的新理念以及设立的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机制,美国会竭力维护其既得利益。第三,美国虽然不是“一带一路”域内国家,但是在沿线却遍布着诸多盟国和伙伴国家。借助于同盟体系和军事实力,美国具有介入——无论是支持还是搅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事务乃至一些国家内政的多种资源和手段。第四,美国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其涵盖范围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所辐射地域具有重叠部分,未来双方将面临如何在“重叠区”进行协调与合作的问题。第五,“一带一路”倡议分别涉及欧亚大陆和“印—太”两洋,它们对美国的地缘重要性不言而喻:主宰欧亚大陆将能控制世界上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而掌控“印—太”两洋也会对其海洋实力地位走势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规划将会对美国继续“管理”欧亚大陆和维持海洋霸权方面产生影响,美国势必会予以战略关注。第六,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一对大国关系,中美两国任何一方的对外战略选择都有可能会对彼此产生一定影响。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如果双方因沟通不畅或误解误判而引起不必要的纠葛,那将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有必要照顾到美国的关切和反应。 那么美国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令美国社会产生相应认知的内在原因是什么?面对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美国已经或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回应?中国又将如何应对?迄今为止,虽然美国官方尚未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做出明确回应,但是通过对美国媒体、智库、学界的讨论和部分官员的言论进行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解答。基于此,本文将首先围绕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认知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就美国对该倡议所产生的影响与发展前景的认知进行深入解读和探讨,然后对美国采取的政策回应进行分析和评估,最后对中国的政策选择进行必要的思考和讨论。 二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认知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新闻媒体、学术界和智库机构等都对之予以一定关注,并进行了多角度报道和分析。尤其是2015年3月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外交神经。有美国官员公开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声称这种做法“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美国政府还为此发表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声明,希望“英国加入后能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确保这个由中国主导的新投资银行坚持高治理标准”。⑤此后,又有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盟友成群结队地加入,更是出乎美国决策层的预料,并由此引发了主流媒体和重要人士对政府“误判形势”的广泛批评。⑥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国内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抱有警惕和防范心理,甚至不乏偏见和误解,普遍认为中国在新时期提出的这一周边外交战略构想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多重动机。根据报道内容和学术观点差异,可以将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认知分为如下几种。 (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论 众所周知,亚洲拥有全球超过60%的人口,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1/3,是当今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然而因建设资金不足,一些国家的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口和通信等基础设施长期严重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鉴于此,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着重加强了基础设施资金筹措问题。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期间提出筹建亚投行的倡议,向包括东盟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以促进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⑦2014年11月,习近平又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他还向外界明确表示,丝路基金是开放的,可以根据地区、行业或者项目类型设立子基金,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⑧ 中国宣布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之后,一些美国媒体和观察家迅速将“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联系起来,声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其中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是相互联系的重点战略安排。⑨例如,波士顿大学的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21世纪“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它将通过帮助缩小地区资金差距而改变亚洲国家的面貌。⑩前美中政策基金会研究人员香农·蒂耶齐(Shannon Tiezzi)也撰文指出,舆论将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同二战后美国发起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并非巧合。因为二者情形相似: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大国试图用经济力量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马歇尔计划”帮助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中国也寄希望于通过两个“丝路”倡议来达到同样的效果。(11)自由撰稿人米歇尔·彭纳(Michele Penna)则进一步分析认为,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一带一路”倡议是错误的和不完整的,因为该倡议还蕴含着地缘政治“再定位”。向邻国资助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马歇尔计划”将会为中国获得巩固其扮演亚洲最重要力量角色的影响力。(12) 在美国有关“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类比的讨论中,也不乏一些客观的声音。在巡回记者佩普·埃斯科巴尔(Pepe Escobar)看来,“一带一路”规划可以与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相媲美,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画等号。事实上,前者有所超越、更富有雄心、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广阔。(13)与此相应,2015年5月27日美国国务院经济和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库尔特·桐(Kut Tong)也表示,“马歇尔计划”的目的主要是帮助欧洲国家快速恢复战后的基建与生产,促进经济回归战前水平。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规划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是一种主要针对南亚、中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战略性理论。(13)虽然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规划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共性”,但是二者在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基本原则,以务实合作为主要导向,而“马歇尔计划”服务于美国的对苏冷战战略,是一项具有附加条件的援助。同时,与“马歇尔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利益诉求更为多样化,其实施的外部环境也更为复杂,并且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域外因素干扰。(15)因此,那些将“一带一路”倡议比作“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二)中国版“再平衡”战略论 自从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不仅加大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了与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安全合作,还在经济上推动具有排他性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在海洋争端问题上持续向中国施压。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不断恶化,面临的战略压力持续增加。尽管美国政要一再声称“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个特定国家,更不是为了围堵和遏制中国,但是白宫的一系列战略布局使外界很难相信其真正的战略意图不是针对中国。实际上,“‘再平衡’政策几乎被全世界大多数媒体和分析人士看作是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的战略竞争”。(16)同时,在中国相当一部分精英和民众眼里,美国的“转向亚洲”战略已然给中国带来了威胁和不安全感,并且导致了中美两国之间日益显现的安全困境。(17) 在美国部分人士看来,为了缓解上述战略压力和安全难题,中国开始积极筹划“西进”,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谋求在陆上和海上两个方向拓展战略空间,以打破美国的战略包围圈。因而,“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种回应,它构成了“中国版的亚洲战略再平衡”。例如,美国西东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主任汪铮就认为,自从美国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中国虽然感到不快,但是一直没有予以直接回应。“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对美国“转向亚洲”战略的首次正式回应。从表面上来看,“一带一路”只是该区域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发展计划,旨在加强贸易、基建和连通性,其实这一倡议的真正目的也涉及安全问题。只不过,中国非常巧妙地借用了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降低了地缘政治含义中的敏感性。(18)蒂耶齐则进一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提供了在经济和外交上拉近与南亚、中亚和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海湾国家关系的政策工具。(19)如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样,海上丝绸之路也不完全是一种经济策略,具有明显的战略含义。中国将与伙伴国联手修建包括港口在内的海上基础设施,这与中国已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布局的“珍珠链”战略形成对接,联通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及海上基础设施,使中国的海上力量进一步西进。(20)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间的逻辑关联,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也曾刊文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深入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关系越来越显现出冲突和零和博弈性质。为了应对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带来的冲击,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将注意力从竞争激烈的东亚地区转向中亚、南亚和中东等这些幅员辽阔的西部地带。该文还援引中国学者王缉思的著述,认为中国选择“西进”战略的主要逻辑在于:其一,在战略“再平衡”背景下,美国将战略重心由中东转向东亚,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向西推进,借机填补因美国的相对“转离”而显现的地区战略真空。其二,由于实力不济,如果中国在东亚地区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对抗,显然会处于下风,并且将自身置于不利境地。而通过“西进”,则可以避免同美国发生正面碰撞。其三,不同于东亚,中美两国在包括中亚和中东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具有更多的合作空间,因为双方在该地区的经济投资、能源、反恐、核不扩散和维护地区稳定等领域拥有诸多共同利益。(21)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出于抗衡美国TPP战略的考量。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黄育川(Yukon Huang)就指出,在美国加紧推进TPP谈判的背景下,许多人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RCEP)视为中国对美国TPP战略的平衡,然而,这些努力与习近平提出的复兴海上丝绸之路相比要逊色许多。(22)事实上,即便是中国所乐意推动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也无法发挥这一平衡作用,更无法助推中国成为与美国一样的全球经济和贸易制度创设者。真正能够帮助中国回击美国TPP谈判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它没有TPP所强调的那种高标准的市场化和开放性,而是推崇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未来围绕全球贸易影响力的真正较量,也要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23) (三)“中国经济自我救赎”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迈向“新常态”,其增长速度开始从高速回落到中高速状态。如何加快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等,都成为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基于此,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和媒体认为,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在经济面临的新形势下而做出的政策调整,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上的自我救赎行为。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弗里曼(Freeman)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斯科特·肯尼迪(Scot Kennedy)和西蒙(Simon)政治经济研究项目研究人员戴维·帕克(David A.Parker)就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意义,考虑到目前中国国内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前者或许更为重要。(24)海军战争学院的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也表示,“一带一路”不是现代版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工程,它目前看起来只是一个间接带有外交、安全和军事意涵的经济计划。(25)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时机似乎也印证了上述学者的论断。泰勒·德登(Tyler Durden)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台适逢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出现下滑之际,这意味着该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服务于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因此,那些认为“一带一路”主要是出于战略和政治考虑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泰勒还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经济上可以为中国带来如下三种利益:第一,向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比国内高得多的投资回报率,还可以借此疏解国内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二,在“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建立中国的经济存在,将会促进当地对中国产品的需求,继而帮助中国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过渡。第三,通过亚投行使用人民币进行借贷,还将有助于中国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甚至会开启人民币霸权的新时代。(26)此外,亦有美国媒体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还可以促进中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作为中国传统的主要出口对象,美国和西欧的市场规模虽然庞大,但是由于近年受到经济危机打击,市场需求已显疲软。在一些行业,例如太阳能电池、机械、通信和建筑设备领域,这些传统市场要么已经饱和,要么充斥着贸易保护主义和投资限制。(27)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潜能还远未得到挖掘,因而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商品新的出口目的地。 除了以上分析外,还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对内统筹不同地区协调发展,对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例如,曾供职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弗林特·莱弗里特(Flynt Leverett)和希拉里·曼(Hillary Mann)等人认为,经过数十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东部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新的历史关键时刻,“一带一路”战略则有利于提升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促进东西部地区更为协调和均衡的发展。(28)美国海军学院的马伟宁(Brendan S.Mulvaney)中校也表示,中国试图利用这两个全球项目(“一带一路”)去指导和影响中国国内的改革,并推出相应配套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以达成改革发展的总目标。(29)蒂耶齐也发表评论称,“一带一路”与实现中国国内的经济目标相关联,是发展中国内陆经济的重要手段,它既要确保经济成长的高效率和科技含量,又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30) 此外,肯尼迪和帕克还分析指出,在区域基础设施缺口数万亿美元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强调了中国不断增长的巨额资源,并承诺将为亚洲各国提供金融支持,以激励它们深化与中国的合作。中长期而言,该项倡议的成功实施有助于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欧亚国家同外界的跨境贸易和金融流动,并进一步巩固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投资及基建模式。无疑,这将增强中国作为其邻国经济伙伴的重要性,并将潜在地提高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杠杆作用。(31)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上升,能源获得越来越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命脉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有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出于维护能源安全的考量。例如,2013年9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及,在中国能源消费持续攀升、对中东地区的石油依赖有增无减的情况下,北京更希望将中国的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和近距离化。而通过陆上管道输入来自中亚的能源,显然要比通过脆弱的海上航线进口中东的能源更为安全。(32) (四)中国“新怀柔政策”论 当前,在部分美国分析人士看来,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正在放弃“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代之以扩张性的、显示肌肉的外交政策。(33)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具有进攻性,试图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来逼迫南海周边弱小声索国就范和退让。(34)在此类学者看来,虽然2014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宣称“愿与各方共建和平之海,坚决反对海洋霸权,致力于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基础上,通过当事国直接对话谈判解决海洋争端”。(35)但是中国在追求海上领土问题上“咄咄逼人”的举动已经引发了整个亚洲的警觉,引起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真实意图的怀疑,并促使相关国家进一步寻求美国的支持。(36)毋庸置疑,如果因持续的海洋争端而加剧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危机”和“不安全感”,那么这将会显著增加美国对中国周边海洋争端的介入机会,甚至会导致中国在地区国际关系上的“孤立”。 基于此,不少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一种对周边国家的“新怀柔政策”,其目的在于稳定因海洋争执而恶化的周边局势,防止“中国威胁论”发酵。同时,通过丝绸之路合作对相关国家加以拉拢,还可以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例如,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Phillip C.Saunders)就分析称,中国的周边外交试图“左右兼顾”,其在涉海领土主权问题上日渐强硬的同时,也开始在周边展开魅力攻势。(37)詹姆斯·霍姆斯也指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邻国施以“经济恩惠”并不令人奇怪。“如果中国希望同美国针对其邻国的情感展开竞争,那么向它们提供一些有形的好处不失为一项合理的方式。事实上,这一方式也植根于中国的传统当中: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通常都会以各种各样的途径向周边邻国提供馈赠和其他物质利益,以换取后者对中国的政治顺从。”(38) 具体来看,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实施“新怀柔政策”的主要意图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施展安抚外交。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威廉·耶鲁(William Yale)认为,如同中国过去发起的很多倡议一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也具有外交、经济和战略等多重目标。其中,这一计划最重要的考量在于安抚周边国家,消除它们因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的领土索求而产生的威胁感。(39)与此相应,美国亚洲研究所(NBR)的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adege Rolland)也表示,“基建外交”反映了中国在与沿海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争端的背景下,加强与其陆上邻国关系的必要性。规划中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会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将沿线国家置于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交通和多边机构关系网络,从而提升中国在其贫弱的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40)二是投射软实力。例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的高级顾问、亚太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就分析称,“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努力提升其软实力的一部分,以弥补因在东海和南海的主权争端中使用强制外交而付出的声誉成本。其中,亚投行即是中国向沿线周边国家投射软实力的一个例证。(41)三是提供公共产品。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时公开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这被外界广泛解读为是对此前奥巴马指责中国在过去30年来一直是一个“搭便车者”,没有承担起相应国际责任的回应。对此,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过去向来是一个国际事务的参与者、追随者,而非活跃的领导者、发起者或者公共产品供给者。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需要,中国开始转变国际姿态,努力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从一个“搭便车者”向“公共产品提供者”转变的现实写照。(42) 上述三种观点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意图的主流看法。事实上,单纯地从一种视角来审视“一带一路”战略意图的并不多见,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有地缘战略的考量,也有地缘经济的谋略。当然,由于研究人士的背景差异和观察视角的不同,一些分析和评论难免带有“过度解读”之嫌,甚至不乏一些偏见和误解。这也正表明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域外国家进行沟通说明、增信释疑的必要性,以尽可能获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三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与前景认知 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进行多角度揣测之外,美国各界还围绕该倡议对美国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面临的现实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美国部分观察家和媒体看来,“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将会对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影响力产生潜在冲击,美国需要密切关注这一倡议的实施进程,并积极应对。与此同时,也有美国分析人士“一分为二”地指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计划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尽管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优势,也积累了丰富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差别巨大,一些国家政局复杂而多变,再加上某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印度、俄罗斯等关键大国的战略顾忌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 (一)影响认知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美国学者就对该倡议产生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多维度解读,其中不乏一些理性客观的声音。例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肯尼迪和帕克在其访谈中就指出,抛开动机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彰显了中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实力以及中国政府对之进行海外部署的目的。若执行得当,它将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发展与一体化。此外,若该项倡议能导致更为持续与包容性的增长,还将有利于强化区域内的政治体制,继而減少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和机会。(43)然而,在美国实施亚太战略“再平衡”,将中国视为防范和围堵的对象这一大背景下,上述中肯的评价也就显得十分稀缺。相较而言,美国国内更多地以竞争性思维来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普遍认为该计划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挑战也多于机遇。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在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试图在亚洲取得对美国竞争优势的重要举措,它将会挑战美国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例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Ralph Cossa)和执行主任布拉德·格洛瑟曼(Brad Glosserman)曾联合撰文指出,“一带一路”或将改变亚太及欧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和权力架构。在新一轮权力竞争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处于劣势地位。因为中国在该地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经济举措,并且有实际投入,而美国只能扮演防守的角色,例如让其盟友和伙伴国远离亚投行。同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习近平正带领着中国实现民族复兴;而中期选举后的奥巴马成了“跛脚鸭”总统,在推进TPP等议题上步履蹒跚。美国看起来像是一个衰落大国在一个崛起国家面前挣扎着维护自身霸权。(44) 詹姆斯·霍姆斯也认为,长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将会帮助中国将美国挤出亚洲,同时使盟友逐渐疏远美国。“假如中国想要在欧亚地区创建一个平行体系,并让其他国家相信该体系比美国的更强,那么中国就必须兑现其(经济)承诺。一旦这些国家上钩了,中国就可以从它们那里要求得更多,包括要求它们限制或者拒绝美国进入其海港。”(45)特别是在中亚地区,中国领导人正在利用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和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时机,通过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来扩大本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对此,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就表示:“中国正在做出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习近平在中亚地区发现了充满着贸易与经济机会的窗口,而美国迄今却不加利用。”(46)还有学者声称,长期以来,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于限制中亚五国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依赖,现在看来更应该担忧中国与中亚日渐紧密的贸易和投资关系。(47)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使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相形见绌。早在2011年7月,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印度参加第二次美印战略对话期间就提出了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48)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后期推进力度并不大,该计划中的两大核心项目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和CASA-1000输变电项目(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进展亦十分缓慢。(49)与之相应,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实施,其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美方的关注和类比。例如,《华盛顿邮报》于2013年10月的一篇报道中就声称,中国正在利用本国的两条丝绸之路还击华盛顿。中国领导人借助于数百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和古老探险家的浪漫故事,来推广其新版本的丝绸之路倡议,目的是将中国与西方连接起来并确保能源供给安全——一条在海上,另一条在陆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黯然失色,两个计划相比——一个已经将巨额资金摆在台面上,另外一个却迟迟难以面世——足以凸显出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正在向美国发起挑战。(50) 此外,从官方层面上来看,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埃米莉·霍恩(Emily Horne)极力淡化中美“丝绸之路”计划的竞争性色彩,表示中国的倡议“反映了我们对于新丝绸之路的想法,美国的战略为该地区带来了实际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合作也是受欢迎的”,“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当今世界上经济最为分散的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51)然而,考虑到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是“纵向”或曰“南向”计划,意在将中亚国家“引向”南方,背离俄罗斯或中国,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横向”战略,首先是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并由此贯通中国西向之路,二者虽有交叉点,但在战略方向上却背道而驰。(52)因此,中美两国的“丝绸之路”规划在事实上具有明显的竞争性。目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全景呈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趋向加深,认为中国通过拓展贸易、修建油气管线等方式不断深入欧亚大陆,紧密加强了与相关国家的联系,但是“扩展的范围还远远不够”,中国力量还将继续在陆上向西延伸,在海上加速扩展,追求陆权和海权的齐头并进及再平衡。(53)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众所周知,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角色,这不仅表现在传统的政治和安全领域,还体现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方面,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建立和运作。不过,随着全球化时代地区国家的多元化崛起、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美国霸权的式微,世界不断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的供给制度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为代表的新兴机构的创建可谓是顺势而为。它们既是对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有力支撑,也是对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有益补充,更是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现实体现。 然而,在美国决策者看来,随着上述由中国发起的经济金融机构的成长和运行,其势必会对美国长期主导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例如,亚投行就被一些人士视为是对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金融秩序的直接挑战。在其筹建之初,美国就曾游说并施压其全球盟友,要求它们慎重加入。即便是在美国盟友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以及美国国内也出现了支持加入亚投行的声音后,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也只是做出了希望亚投行与世界银行等现存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的表态。(54)美国的担忧在于:其一,亚投行的治理标准是否能够满足借贷所需的社会和环保标准要求。其二,该机构中的多数投票权流向中国使其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否决权,这意味着美国将居于边缘化地位。其三,新机构或将贷款给那些从其他多边机构无法融资的项目,继而导致后者的借贷约束性条件失去效力。其四,中国利用亚投行作为提升自身领导地位和实现战略利益的工具,继而影响到美国及其盟友的主导地位。(55)事实上,一国将金融资本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无一不是如此。“正如当年进入美洲市场曾经是美国外交的关键要件一样,中国也正在利用其金融和贸易‘肌肉’来赢得更多的朋友和影响力。”(56)因而,美国的各种担忧可谓是多余的,并且“忘却”了世界金融和政治的互动规律。 (二)前景评估 在美方看来,尽管“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振奋人心,中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切实的行动,但是该战略能否顺利推进,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在“一带”建设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将构成威胁沿线安全的重要因素,而中国能否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将影响“一带”建设的前景。在“一路”建设上,中国固然可以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影响力增强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但是其在南海等问题上日益强势的立场也会加剧东南亚国家的不安。(57)综合而言,美国各界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前景将主要面临着如下五个障碍。 第一,投资与回报隐藏着潜在风险。“一带一路”规划涉及国家众多,资金巨大,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形形色色的执行风险问题。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就认为,“一带一路”计划表面上看起来高歌猛进,但是其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诸多绊脚石。例如,该计划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努力虽然受到了普遍欢迎,但是宽松的借贷标准或将会破坏计划的进展。如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使用资金来开展不合理且缺乏可行性的项目而导致还贷困难,那么中国的投资将蒙受损失。同时,如果项目在环保或人权领域产生了意料之外的丑闻,也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一贯良好亲切的形象。(58)肯尼迪和帕克也分析指出,中国过去在基建投资方面遭遇的困难表明,许多拟建项目最终可能会以一系列“劳民伤财”而告终。考虑到中国建筑企业在海外运营的不良记录(包括对当地工人的虐待),这些企业对外活动的扩张增加了破坏性的政治压力的风险,可能有损中国形象或引发东道国动荡,尤其是当“一带一路”无法为当地经济带来持久利益时。此外,当借款者无法还贷、企业无法收回投资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额外压力也将会陡增,从而无法缓解其经济衰退趋势。(59) 第二,周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大都对中国的基建资金充满期待,但是也不乏个别国家囿于现实的利益纠纷和战略考量而对该计划充满不安和猜忌。特别是在近年中国对外政策趋于所谓“强势”,在边海领土争端上的立场愈加“自信”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引发了不小的地缘政治恐惧。在美国观察家眼里,“一带一路”倡议很容易让一些周边国家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系,担心当代丝绸之路是中国恢复向古代“天下”观念努力的一部分。有媒体甚至妄加臆断,认为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实质上是同美国瓜分太平洋水域,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则在于将东盟海洋空间划归到自己的太平洋水域势力范围。(60)尽管中国坚持海上丝绸之路只是一个经济倡议,并且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利益,但是相关海上邻国并不完全相信中国的好意。因为在精心设计的外交辞令背后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大面积的海上领土争端。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小国在前者的“恫吓”面前必然会寻求美国的支持。除非中国能妥善解决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海上争端,否则东南亚国家很可能会成为其通向印度、非洲和欧洲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61) 第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在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美国学界均不同程度地提及了宗教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问题。在他们看来,“一带一路”涉及的中东、中亚和南亚地区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一些国家甚至存在政局不稳的内患,这些都对“一带一路”建设构成了现实挑战。例如,在中东地区,近期也门局势的激变和“伊斯兰国”的兴起,表明中东乱局仍在恶化中,这使得“一带一路”战略在中东的布局充满了变数。在中亚地区,随着美国及北约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很可能卷土重来,继而威胁到“一带”沿线的稳定。在南亚地区,“一带”的西端是海上连接能源运输通道的瓜达尔港和陆上连接中国的喀喇昆仑公路,两者均位于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集中的巴基斯坦境内,如何确保相关港口和道路不受上述“三股恶势力”的干扰,成为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62)对于上述挑战,《外交政策》杂志资深记者基思·约翰逊(Keith Johnson)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在他看来,如果无法有效打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激进分子,那么中国所寄希望于其能源来源多元化的新丝绸之路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场“白日梦”。(63)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动机在于推动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包括穆斯林占多数的新疆地区。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在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群体中日益上升的极端事件的担忧和深化与中亚、中东以及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64) 第四,地区关键大国的掣肘。在美国分析家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俄罗斯和印度等关键大国的传统地缘范畴,因而必然会引起对方的警惕和防范。就俄罗斯而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弗吉尼亚·马兰泰德(Virginia Marantidou)等人认为,中俄表面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能源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两国的战略关系也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然而双方实际上互信并不足,可谓“同床异梦”。俄罗斯对于中国通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介入其传统后院中亚地区而感到“担忧”,中俄在中亚的战略竞争将不可避免。同时,中国试图通过上海合作组织(SCO)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也遭到俄罗斯的“冷眼相对”,因为后者反对该地区任何不以自身为主导的多边框架。(65)雅各布·斯托克斯和罗里·梅德卡夫(Rory Medcalf)等人也指出,印度方面同样对中方的“地区雄心”持保留意见,因为来自中国的计划可能会影响其“东进”和“连接中亚”的政策。并且,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特别警惕,新德里一直将后者视为其后院的一部分。此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洋上的扩张——特别是可以用于中国海军作战的港口,也会增加印度的不安和疑虑。总之,由于美国在阿富汗的作用降低导致其中亚的戏份减弱,中国对于欧亚地区、印度洋和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将考验其平衡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即与邻国及全球其他政治力量合作而非对抗的能力。(66) 第五,“心心相通”任重而道远。持这一观点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主要挑战并非来自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即能否树立起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认同,以推动该倡议从地理上的“互联互通”到价值上的“心心相通”的飞跃。例如,威廉·耶鲁就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不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协定签订,虽然这些无疑也是“宏基伟业”,但它们在本质上属于工具性的任务,不会受到地区国家太多的反对。对中国而言,更为艰巨的目标还在于如何将投资和贸易转化为地区性联盟建设,以使相关国家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目标与中国的相互协调,认同中国而不是其竞争对手(例如美国)的理念。(67)美籍华人学者汪铮也指出,在国际关系中,金钱买不到忠诚。对他国的影响力并非来源于一国的“小金库”,而是来自共同的价值观和软实力的提升。中国能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其战略目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激发邻国与其共享“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此而言,仅仅通过修建铁路、公路和输油管道并不能促进亚洲一体化的生成,而更应当取决于亚洲各国是否能够建立起共同的身份和价值观。(68) 四 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回应 “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主要地缘范畴——欧亚大陆对美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经指出,“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在欧亚大陆举足轻重的地位,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69)同时,从美国霸权的逻辑来看,二战后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大战略并不受体系结构的主导,而是受经典地理政治思想中蕴含的权力政治逻辑的支配,正是这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冷战期间与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延续。(70)由此可知,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目标在于实现欧亚大陆各国的互利共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特点,不排斥域外国家、不谋求势力范围、更不搞军事扩张,但是该规划贯穿欧亚大陆这一美国极为看重和推崇的地区意味着,它必然会触动美国敏感的权力政治神经,并引起其战略关注和潜在的政策回应。 目前,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及其推进,美国社会的心态可谓五味杂陈,不同群体和部门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不尽一致。有人呼吁美国应当面对现实,积极参与;有人主张美国审时度势,有选择性地参与;也有人建议美国密切关注,加紧应对。从美国官方的表现来看,其对“一带一路”倡议则采取了选择性回应:一方面,从整体上对该倡议进行“冷处理”,官员较少公开提及甚至有意淡化其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在需要借助于中国的特定领域,例如大中亚地区的“维稳”和“发展”方面,则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与合作立场。不难理解,基于惯有的“霸权护持”思维,美国私底下并不希望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规划做大做强,因为在美方看来这将会挑战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侵蚀其全球影响力。尽管如此,通过对美国官员已有的零星表态以及智库、学界等发表的相关看法,大体上还是可以管窥到美国的一些政策选项和主张。 (一)为“一带一路”建设设置障碍 虽然美国无法直接阻止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但是却可以在其实施过程中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不惜对抗,以延缓“一带一路”建设的脚步。例如,奥巴马政府就将亚投行的创建视为中国对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挑战,并一直质疑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有机构的标准。早在中国筹划建立亚投行之初,美国就表达了“关切”。2014年10月,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Jen Psaki)声称:“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已经明确向中国以及其他伙伴国家表示,美国对成立亚投行的想法表示欢迎,但是我们强烈要求该银行必须符合国际的管理和透明标准。”(71)2015年8月,克里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还不忘继续“敲打”亚投行,声称美国支持中方创建亚投行的努力,但美方需要这种努力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一样透明和可靠,必须达到其他银行类似的高标准。(72)显而易见,美国所谓的“欢迎”和“支持”只不过是一种表面说辞,其真正目的在于从外部利用现有的国际标准、国际规则以及它自己假设的一些问题来干预、干扰亚投行的筹建进程。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亚投行筹建谈判期间,美国还被爆出试图劝阻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加入。虽然后来美国的劝阻计划多半落空,同时奥巴马也对外界流传的美国的“劝阻行为”予以了否认,(73)但是美国至今一直游离于亚投行之外本身就说明了白宫的真正“隐忧”,即担心亚投行会动了美国的“奶酪”,冲击由美国主导的亚洲秩序,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地位。(74)正如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所顾虑的那样,“美国政府未能成功劝阻盟国加入亚投行这一事件或将成为美国丧失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地位的标志而载入史册”。(75)从美国的态度和阻挠行为不难看出,亚投行之争背后的本质是一场规则与制度的竞争,是一场关于亚洲甚至世界经济金融控制权、主导权的争夺。 与此相应,美国的一些智库机构还纷纷发表报告,呼吁政府坚决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亚洲的“扩张”。例如,2015年3月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其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中就强调美国应当改变对华大战略。该报告声称,中国在当前和未来几十年都将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战略竞争对手。虽然美国一直致力于将中国“纳入”自由的国际秩序之中,但是中国并未朝着美国所希望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迈进。与之相反,中国正在施展自身的大战略,包括加强对国内社会的控制、安抚邻邦、巩固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美国需要调整对华大战略,将重点放在制衡崛起的中国,而非继续扶持其不断上升的地位。(76)几乎与此同时,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和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等人也指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努力将自身打造成为海洋强国,并发布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愿景,力图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中国与中东、欧洲地区更为紧密地连接起来。现如今,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中国已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等待时机“有所作为”。为此,美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有必要在解放军日益活跃的地区增加军事介入和存在、维持和深化与关键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推进区域和多边合作。同时,还要密切关注中国加强和建立多边机构的努力及其推动和强调的“亚洲人的亚洲”区域安全架构。(77) (二)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竞争 在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挑战面前,美国国内也不乏一些现实和理性的声音。例如,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Gal Luft)就认为,美国应当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因为如果美国继续以“沉默”回应或蓄意破坏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不仅缺乏逻辑清晰、有建设性的地缘政治根据,并且在道德层面上也站不住脚。在勒夫特看来,美国应该努力发挥其如下几项比较优势:首先,美国的“钱袋子”或许不如中国丰厚,但美国拥有超强的投放能力、国土安全和网络防御能力,能够在保护“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基础设施方面发挥作用。其次,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美国科技、工程和建筑公司可以提供最佳实践、高质量和安全标准。最后,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美国还可以敦促中国坚守国际劳动、环境和商业标准。为了实现上述设想,美国首先应该下决心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对美国而言,增强中国的项目不一定会削弱美国,但站在一边生闷气而任由中国打地基,则注定会削弱美国。(78) 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的另一个现实选择是重振和推进美国版的“新丝绸之路”计划。2014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J.Burns)在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上发表的名为“扩展大中亚地区经济联系”的演讲中表示,无论是“新丝绸之路”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现在都是携起手来恢复这一地区作为全球商业、思想和文化枢纽的历史角色的时候了。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美国将继续支持如下四大任务:建立地区能源市场、促进贸易和交通建设、简化海关和边境手续以及加强地区人文交流。在伯恩斯看来,虽然打破彼此边界是一项艰巨工作,但是幸好这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有先例可循。基于此,美国将和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伊斯兰开发银行以及“伊斯坦布尔进程(Istanbul Process)”中的伙伴国家合作,尽可能地帮助中亚地区和人民早日迎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79)与此相应,针对外界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一系列质疑和批评,美国国防大学的艾里卡·马拉特(Erica Marat)还给出三项政策建议:其一,美国应该将对该地区的安全援助和民主发展脱钩,更加重视经营人权和民主化,因为这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政策中所缺失的要素。其二,安全援助应以军事训练和知识交流的形式,而不仅仅是武器和装备供应,这将有利于避免该地区的独裁者利用西方馈赠的先进武器对付其人民。其三,援助应当聚焦于商业阶层,因为中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要求对政府进行更好的问责。(80) 还有学者认为,既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发展规划,那么美国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聚焦经济事务,在该地区与中国展开经济竞争。例如,2014年11月,《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和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的埃利·拉特纳的分析文章,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来势汹汹,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而针对中国的经济活动采取防守政策将是一个失败的策略。在两位学者看来,在亚洲,经济才是王道,并且在未来若干年内,经济将一直是美国政策的重中之重。尽管亚洲确实存在军事竞争和领土争端,然而在事实上,领导力和影响力源自“钱袋子”,而非“枪杆子”。此外,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美国的贸易政策和经济决策不能再局限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甚至财政部门,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等应考虑将经济、贸易、投资和发展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要素。这就要求美国重拾敢为人先的精神,在诸如清洁能源、金融和高等教育等领域提出有意义的倡议,以满足该地区的需求,并发挥美国的优势。(81) (三)在大中亚地区事务上拉中国合作 随着俄罗斯在中亚实力的相对下降和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中国在中亚经济和安全事务上的角色日益凸显。尽管美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崛起保持警惕,但是美国官员还是鼓励中国在阿富汗国家重建和地区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013年9月,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特别代表詹姆斯·多宾斯(James F.Dobbins)曾表示,中美两国经常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相关问题进行密切磋商,美国支持中国在阿富汗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包括中国已经或未来在阿富汗进行的投资。同时,美国也很清楚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亲密关系。中美两国在该地区事务上拥有许多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关注该地区暴力事件的增长,都希望看到该地区更加安全,也都希望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不再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之源。(82)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南亚和中亚局助理国务卿帮办林恩·特蕾西(Lynne M.Tracy)亦声称,虽然美国也是中亚各国的重要伙伴,但是由于邻国关系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中亚地区贸易和投资领域天然的“领头羊”。美国欢迎中国为中亚国家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做的努力,并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这一互惠互利行为。美国希望与中国以及本地区其他国家共同促进中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愿意在丝绸之路项目上与中国展开合作。(83) 值得提及的是,针对社会上盛行的中美“丝绸之路竞争论”,美国官员和学者还予以了澄清。2015年年初,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瓦尔(Nisha Desai Biswal)在华盛顿伍德罗·威尔逊中心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一些人将中国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描绘成一种竞争关系,但是事实上美国欢迎中国在该地区的建设性参与,并且认为这种参与对美国的努力发挥着巨大的补充作用。(84)2015年3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在布鲁金斯学会就“中亚的长久愿景”发表的演讲中也宣称,中国在中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中国的参与并非“零和游戏”,可以加强亚洲在陆上和海上的互联互通。而中亚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成为美国努力的重要补充。(85)同年6月,美国第一副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格兰(Richard Hoagland)在访问中国时再次重申,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相通之处,可以互为补充,特别是在中亚地区能源资源开发以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美国希望与中方加强沟通交流,探寻开展在第三国合作的具体形式,以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86)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进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阿里拉·维耶赫(Ariella Viehe)在出席中国“2015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国际论坛”时也强调指出,中美两国一起致力于全球发展以及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方面拥有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美国所提出的倡议有很多相似之处,双边合作互补性远大于竞争。尤其是在中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中美是互补而不是竞争的关系。(87) (四)适度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倡议被普遍视为是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回应。随着该倡议在陆海两个方向上的不断推进,它将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形成对冲作用。甚至有美国学者声称,中国的丝绸之路战略将产生全球地缘政治影响,连接三大洲的贸易路线一旦完成,将会对欧亚经济区和北美贸易网的持久性构成挑战。(88)有鉴于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应当对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进行适度调整,以应对新的地缘环境变化和挑战。具体来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的方向包括: 首先,在空间上将西亚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视域。例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SAIS)院长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就认为,长期以来,美国人提及亚洲时,他们所想到的首先是东亚,而不是西亚。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转向”亚洲战略,也是意指从西亚转向东亚。然而,当前亚洲国家正着眼于连接中欧贸易的丝绸之路将如何改变“亚洲”概念和全球秩序。丝绸之路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东亚和西亚的联系与融合,其反映的是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崛起,而不是单就亚太地区而言。虽然过去亚洲并没有像欧洲那样发挥出整体的效应,但是如今局势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美国需重新思考“重返亚洲”战略,关注整体的亚洲概念,将西亚也纳入其亚太战略布局之中。(89) 其次,在内容上将“新丝绸之路”计划整合进新亚洲战略之中。与上述第一点相适应,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基于历史和文化的关联,中国对亚洲的理解与美方并不一致。在中国人眼里,亚洲不仅包括东亚,还涵盖了俄罗斯的北部、中亚和阿富汗的西部、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西南部等广大区域。随着奥巴马政府高调实施“重返”亚洲战略,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们也向政府建议推出本国的“西进”战略,即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和利益触角向西穿越中亚,扩展至伊朗和大中东地区,以缓解美国在亚洲东部方向上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考虑到中国的战略触角如此之广泛,美国不能再无视“新丝绸之路”计划和“转向”亚洲战略之间的割裂状态,而应当将前者整合进后者,以确保美国新亚洲战略的持续性和有效性。(90) 最后,在安全上加大对“印—亚—太”地缘战略的关注力度。2015年3月,美国海军在其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文件中,首次提出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概念(意指从美国西海岸到非洲东海岸的广泛地区),声称目前全球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一些国家正在构建和部署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国全球海上进入能力构成了挑战,美国需要应对之。(91)不仅如此,新的海洋战略文件还公开指责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使用武力“恐吓”其他国家,再加上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这导致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和动荡,可能带来误判甚至紧张升级。为此,美国除了在威慑、海上控制、力量投送和海事安全这四大传统的海上力量上加强支撑能力外,有必要引入第五大支撑能力“全域进入”——在竞争区域投送军事力量,并拥有足够行动自由实现有效部署的能力,以表达美国的决心、保护美国利益、促进全球繁荣。(92)新版的海上战略文件表明美国已经将安全视野扩展到“一带一路”战略规划涵盖的大部分区域,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后者构成“反制”。 五 中国的策略选择 如前文所述,虽然美国不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但是其全球性影响力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都决定了“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必须考虑美国的角色,顾及美国的利益和反应。目前,从中国方面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设立国别范围,更不会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事实上,在中国政府于2015年3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官方文件中,即写明了要坚持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强调“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93)可以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门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始终是敞开的,并不具有排斥特定国家的意图。 然而,就美国方面而言,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全球的实力地位日益凸显,相对而言,美国掌控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能力则有所下降。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在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使得美国社会看待中国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华防范心理和危机感骤升。正如有学者所言,冷战后美国的“超强”状态使其难免产生超强者特有的那种对权势分散化的强烈戒心甚至过头恐惧,尤其是当这种趋势出自非西方大国时,美国的这种心态将会更加严重。(94)基于此,面对中国在新世纪推出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尽管美国国内也不乏一些客观、理性、合作的声音,但是各界整体上对中国的意图还是存在较大疑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将为中美之间带来更广泛的竞争,并会威胁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和领导地位。 中美两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看法无疑会置中国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欢迎美国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因为没有美国参与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不完整的,并且“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事务在事实上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与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又忌惮“一带一路”倡议遭遇美国的破坏和阻力,担心其插手或阻挠“一带一路”项目的实施,甚至拉拢、离间有关国家,排挤、抵消中国的合理存在。因此,如何破解“一带一路”上的“美国风险”,推动其扮演积极角色而非充当麻烦制造者,就成为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几项策略选择。 第一,扭转“观念市场”,引导美方树立“我们的事业”意识。所谓观念市场,是指一国民众对他国形象和行为形成的一种集体认知,它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为负面。目前,既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认知偏差,那么中国就应当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对美开展公共外交,扭转美国对华“一带一路”倡议认知的负面“观念市场”,不断向美国各界阐释“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共赢性,进一步淡化该倡议的“抗美”色彩和战略属性。同时,在塑造美国“观念市场”过程中必须遵循审慎的原则。一方面,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恰当表述中国的愿景,不宜夸大“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避免给人以浮夸之嫌;另一方面,要注意倾听美国各界的不同声音,尤其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汲取美方有益的质疑和善意的批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对美舆情疏导,取得增信释疑的效果。此外,还要逐步引导域内外国家树立起“我们的事业”意识,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强调中国方面的相关战略规划,只是“一带一路”整体事业的一部分,而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与合作国家共同的战略规划。 第二,从最易处着手,打造吸引美国合作的示范工程。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横贯欧亚大陆,覆盖区域人口规模庞大,沿线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以及对华亲疏关系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这意味着其在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面临着众多潜在的地缘、安全、经济、法律甚至道德风险。(95)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也极为庞杂繁多,不仅包括政策协调、经济贸易、基建投资、人文教育等方面,还涉及交通物流、能源资源、产业合作、科技交流等领域。建设内容的繁多固然有利于多样化选择,但同样也会给实际操作带来选择性难题。由以上可知,“一带一路”倡议将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笔者建议中国遵循“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顺序原则,优先从那些风险最小、最能体现互利共赢和最容易取得成效的国家和项目入手,在“一带一路”沿线打造若干个共建、共享的“示范工程”,让美国在内的域内外国家切实领略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正面价值,从而吸引它们认可或加入“一带一路”事业。显而易见,一旦美国的抵触情绪得到化解,开始发挥“带头”作用,那么其他还处于观望中的外围国家或将会陆续跟进,这无疑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整体性推进。 第三,争取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对接,避免双方恶性竞争。目前,虽然美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例如地区内相关国家基础设施滞后、基建资金匮乏、相互信任缺失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等,但是美国从未放弃该计划。事实上,2015年1月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斯瓦尔就“新丝绸之路”发表的演讲中还声称这一计划是“奥巴马政府对该地区持久承诺的体现”,强调“在该地区内扩大贸易联系并通过巴基斯坦和印度将其引向南方,将会起到‘游戏改变者’的作用。通过连接新的市场,这种贸易联系还会促进地区内的政治稳定以及激励各国合作共同应对挑战”。(96)更为重要的是,美方深知中国在“后阿富汗”战争时代所享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因而一再表示中美两国的“丝绸之路”计划并非竞争关系,美国鼓励中国在地区稳定和经济重建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上述认知显然为中美两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创造了巨大的合作空间。基于此,中国应积极寻求将“一带一路”倡议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进行对接,寻找两国能够深度合作的领域和项目,扩展共同利益,避免双方陷入恶性竞争的旋涡。 第四,妥善处理好周边海洋争端,防止相关国家加速“倒向”美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海洋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也是中国所遇到的一个“成长的烦恼”,处理不当将会直接影响到“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成效。以南海问题为例,众所周知,东盟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枢纽区”,争取东盟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然而,由于中国巨大的“块头”和强健的“肌肉”,其在南海争端上的正当维权行为很容易被外界和周边小国炒作为“海上威胁”,也更易于引起国际社会较多“关注”。(97)其结果是,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的海上争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会外溢至中国—东盟整体关系中,从而危及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还值得警惕的是,当前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这一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的同时,为自己购买“安全再保险”,持续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98)在此结构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争端或将成为美国离间中国与“一路”沿线国家关系、曲解海上丝绸之路本质、破坏“一带一路”建设的工具。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妥善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不断加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战略互信,防止它们加速“倒向”美国,沦为后者制衡中国崛起的棋子。 第五,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地位,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企业创造平等参与机会。毋庸置疑,“一带一路”走出去的主体是资本、企业,而不是政府,其推进过程中需要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在外交倡议、宏观布局、信息传递、平台建设、海外保护、合作机制以及政府间融资机构建立等方面扮演引导和保障角色。换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当遵循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模式,用足用好市场力量。与此同时,多元化的参与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一带一路”建设所涉及的众多跨国、跨地区项目中,中国不应当仅仅诉诸双边途径,而是应该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多渠道融资、多样化所有权”。具体来看,政府不仅要创造条件引导国内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跟进,鼓励它们落实“亲诚惠容”理念,服务于经济外交目标,还应当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企业提供公开、平等的参与机会,促进各企业根据产业链分工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如果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吸引到美国企业广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那么赢得美国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也就为期不远。 第六,注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合作,化解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随着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融资机构的创建,其必然会面临如何与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平共处”的问题。不可否认,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机构存在竞争的一面,但亚投行不应也无法取代后两者的地位。事实上,双方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都是为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作用。正如2015年3月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所言,由于定位和业务重点不同,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亚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则强调以减贫为主要宗旨。(99)反过来讲,如果中国推动亚投行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竞争,那么这不仅会收窄亚投行的融资渠道、弱化其信贷标准,不利于亚投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引来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对抗,继而导致“一带一路”融资项目频频被“政治化”,成为一场场国际政治博弈。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亚投行应注意与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金融机构进行协调合作,以化解多边阻力和政治风险。此外,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才刚刚起步,还处于经验摸索阶段。它们无论是在当前“建章立制”,还是在未来促进自身科学决策和高效运行等方面,都存在着向现有国际同类机构借鉴和学习的空间。 ①《中国三部门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8/c_1114795089.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16日。 ②《郑永年重磅演讲深度解读“一带一路”战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3/27/con-tent_35169987.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17日。 ③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42-57页。 ④邢广程:《理解中国现代丝绸之路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22-23页。 ⑤"US Anger at Britain Joining Chinese-Led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Guardian,March 13,2015,http://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5/mar/13/white-house-pointedly-asks-uk-to-use-its-voice-as-part-of-chinese-ledbank,登录时间:2015年8月18日。 ⑥Michael Curtis,"The White House Loses Face," April 4,2015,http://www.americanthinker.com/articles/2015/04/the_white_house_loses_face_.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18日。 ⑦《中国印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3日。 ⑧《丝路基金的“五个W和一个H”》,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4/21/c_127716693.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19日。 ⑨"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November 11,2014,http://www.wsj.com/articles/chinas-marshall-plan-1415750828,登录时间:2015年8月19日。 ⑩"Is Infrastructure Bank China's New Marshall Plan for Asia?" March 30,2015,http://www.nationmultimedia.com/opinion/Is-Infrastructure-Bank-Chinas-new-Marshall-Plan-fo-30257016.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11)Shannon Tiezzi,"The New Silk Road:China's Marshall Plan?" The Diplomat,November 6,2014. (12)Michele Penna,"China's Marshall Plan:All Silk Roads Lead to Beijing?" World Politics Review,December 9,2014,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4618/china-s-marshall-plan-all-silk-roads-lead-to-beijing,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13)Pepe Escobar,"The 21st Century Belongs to China:Why the New Silk Road Threatens to End America's Economic Dominance," February 24,2015,http://www.salon.com/2015/02/24/the_21st_century_belongs_to_china_why_the_new_silkroad_threatens_to_end_americas_economic_dominance_partner/,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14)《美国务院高官:“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完全不同》,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5-05-28/100814372.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15)金玲:《“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第88-99页。 (16)魏红霞:《对奥巴马政府“再平衡亚洲”战略的再评估》,载《美国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55页。 (17)Dong Wang and Chengzhi Yin,"Mainland China Debates U.S.Pivot/Rebalancing to Asia," Issues & Studies,Vol.50,No.3,2014,pp.57-101. (18)Zheng Wang,"China's Alternative Diplomacy," The Diplomat,January 30,2015. (19)Shannon Tiezzi,"Why China Needs the U.S.in Afghanistan," The Diplomat,March 25,2014. (20)Shannon Tiezzi,"The Maritime Silk Road vs.The String of Pearls," The Diplomat,February 13,2014. (21)Yun Sun,"March West:China's Response to the U.S.Rebalancing," Brookings,January 31,2013,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1/31-china-us-sun,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22)Yukon Huang,"Courting Asia:China's Maritime Silk Route vs America's Pivot," The Diplomat,April 25,2014. (23)Min Ye,"China's Silk Road Strategy:Xi Jinping's Real Answer to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Foreign Policy,November 10,2014,http://foreignpolicy.com/2014/11/10/chinas-silk-road-strategy/,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24)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25)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 April 12,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2015/04/11/taiwan-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25353561/,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26)Tyler Durden,"‘One Belt,One Road' May Be China's ‘One Chance' to Save Collapsing Economy," June 8,2015,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5-06-08/one-belt-one-road-may-be-chinas-one-chance-save-collapsing-economy,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27)Shuaihua Wallace Cheng,"China's New Silk Road:Implications for the US," Yale Global,May 28,2015,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E2%80%99s-new-silk-road-implications-us,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28)Flynt Leverett,Hillary Mann Leverett and Wu Bingbing,"China's Drive for a‘New Silk Road’," World Financial Review,January 29,2015,https://consortiumnews.com/2015/01/29/chinas-drive-for-a-new-silk-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29)《国外学者谈“一带一路”》,http://news.hexun.com/2015-04-10/174858810.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30)Shannon Tiezzi,"The Belt and Road:China's Economic Lifeline?" The Diplomat,July 14,2015. (31)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32)Jane Perlezsept,"China Looks West as It Bolsters Regional Ties,"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7,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9/08/world/asia/china-looks-west-as-it-strengthens-regional-ties.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33)Elizabeth C.Economy,"China's Imperial President:Xi Jinping Tightens His Grip," Foreign Affairs,Vol.93,No.6,2014,pp.80-91. (34)笔者于2015年7月16日同麻省理工学院南海问题学者傅泰林(Taylor Fravel)博士的交流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5)参见李克强在2014年6月20日访问希腊时的演讲:《李克强阐释“海洋观”:共建和平、合作、和谐之海》,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6-21/6305312.s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0日。 (36)John C.K.Daly,"China Focuses on Its Maritime Silk Road," July 17,2014,http://www.silkroadreporters.com/2014/07/17/china-focuses-maritime-silk-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37)Phillip C.Saunders,"Commentary:China's Juggling Act," April 14,2014,http://archive.defensenews.com/article/20140414/DEFREG03/304140038/Commentary-China-s-Juggling-Act,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38)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 April 12,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2015/04/11/taiwan-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25353561/,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39)William Yale,"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Gamble," The Diplomat,April 22,2015. (40)Nadege Rolland,"China's New Silk Road," Commentary,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February 12,2015. (41)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 Strategy," April 12,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2015/04/11/taiwan-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25353561/,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42)Zheng Wang,"China's Alternative Diplomacy," The Diplomat,January 30,2015. (43)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44)Ralph Cossa and Brad Glosserman,"A Tale of Two Tales:Competing Narratives in the Asia," Pacnet,No.84,Pacific Forum CSIS,December 1,2014. (45)Wendell Minnick,"China's ‘One Belt,One Road’Strategy," April 12,2015,http://www.defensenews.com/story/defense/2015/04/11/taiwan-china-one-belt-one-road-strategy/25353561/,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46)Simon Denyer,"China Bypasses American ‘New Silk Road' with Two If Its Own," 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4,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ypasses-american-new-silk-roadwith-two-if-its-own/2013/10/14/49f9f60c-3284-11e3-ad00-ec4c6b31cbed_story.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47)Jeffrey Mankoff,"Work with Moscow in Central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March 21,2013,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work-moscow-central-asia-8242?page=2,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48)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A Vis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Chennai,India,July 20,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8840.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49)Reid Standish,"The United States' Silk Road to Nowhere," Foreign Policy,September 29,2014,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9/29/the-united-states-silk-road-to-nowhere-2/,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50)Simon Denyer,"China Bypasses American ‘New Silk Road' with Two If Its Own," 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14,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ypasses-american-new-silk-roadwith-two-if-its-own/2013/10/14/49f9f60c-3284-11e3-ad00-ec4c6b31cbed_story.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51)Simon Denyer,"China Bypasses American ‘New Silk Road' with Two If Its Own," The WashingtonPost,October 14,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bypasses-american-new-silk-roadwith-two-if-its-own/2013/10/14/49f9f60c-3284-11e3-ad00-ec4c6b31cbed_story.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52)陈宇、贾春阳:《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现在怎样了》,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第31页。 (53)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第35页。 (54)《美日抵触亚投行,担心挑战其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4/6066960.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55)John Kemp,"China's Silk Road Challenges U.S.Dominance in Asia," Reuters,November 10,201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10/china-apec-silkroad-idUSL6N0T03CY20141110,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56)John Kemp,"China's Silk Road Challenges U.S.Dominance in Asia," Reuters,November 10,201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11/10/china-apec-silkroad-idUSL6N0T03CY20141110,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57)龚婷:《“一带一路”:美国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想的解读》,载孙哲主编:《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合作发展》,北京: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8页。 (58)Jacob Stokes,"China's Road Rules:Beijing Looks West Toward Eurasian Integration," Foreign Affairs,April 19,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19/chinas-road-rules,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59)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60)转引自龚婷:《“一带一路”:美国对中国周边外交构想的解读》,载孙哲主编:《中美外交:管控分歧与合作发展》,第385页。 (61)John C.K.Daly,"China Focuses on Its Maritime Silk Road," Silk Road Reporters,July 17,2014,http://www.silkroadreporters.com/2014/07/17/china-focuses-maritime-silk-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62)《美国为何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疑虑重重?》,http://copy.hexun.com/172628783.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63)Keith Johnson,"Rough Ride on the New Silk Road," Foreign Policy,May 1,2014,http://foreignpolicy.com/2014/05/01/rough-ride-on-the-new-silk-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64)Flynt Leverett,Hillary Mann Leverett and Wu Bingbing,"China's Drive for a ‘New Silk Road’," World Financial Review,January 29,2015,https://consortiumnews.com/2015/01/29/chinas-drive-for-a-new-silk-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65)Virginia Marantidou and Ralph A.Cossa,"China and Russia's Great Game in Central Asia," The National Interest,October 1,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hina-russias-great-game-central-asia-11385?page=2,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66)Jacob Stokes,"China's Road Rules:Beijing Looks West Toward Eurasian Integration," Foreign Affairs,April 19,201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15-04-19/chinas-road-rules?cid=rss-asia-chinas_road_rules-000000,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Scott Kennedy and David A.Parker,"Building China's ‘One Belt,One Road'," April 3,2015,http://csis.org/publication/building-chinas-one-belt-one-road,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Rory Medcalf,"Asia's ‘Cold Peace’; China and India's Delicate Diplomatic Dance," The National Interest,September 24,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sias-cold-peace-china-indias-delicate-diplomaticdance-11338,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67)William Yale,"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Gamble," The Diplomat,April 22,2015. (68)Zheng Wang,"China's Alternative Diplomacy," The Diplomat,January 30,2015. (69)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70)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71)Finbarr Bermingham,"China Launches AIIB to Rival World Bank Without US Allies After Pressure from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October 24,2014,http://www.ibtimes.co.uk/china-launches-aiib-rivalworld-bank-without-us-allies-after-pressure-washington-1471582,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72)John Kerry,"Remarks on America and the Asia Pacific:Partners in Prosperity,"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Singapore,August 4,2015,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5/08/245634.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73)Geoff Dyer,"Obama Says AIIB Could Be ‘Positive' for Asia," The Financial Times,April 28,2015,http://www.ft.com/intl/cms/s/0/80271e0c-eddc-11e4-90d2-00144feab7de.html#axzz3ihJ352u4,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74)贾秀东:《亚投行折射出美国战略心病》,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1月3日。 (75)Larry Summers,"A Global Wake-up Call for the U.S.?" 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5,2015,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a-global-wake-up-call-for-the-us/2015/04/05/6f847ca4-da34-11e4-b3f2-607bd612aeac_story.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76)Robert D.Blackwill and Ashley J.Tellis,Revising U.S.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Council Special Report,No.72,March 2015,pp.7-8. (77)Ely Ratner,et al.,More Willing and Able:Char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ctivism,Report of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May 2015,p.8. (78)盖尔·拉夫特:《美国应积极参与“一带一路”》,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6/6762476.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79)William J.Burns,"Expanding Economic Connectivity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September 23,2014,http://www.state.gov/s/d/2014/232035.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2日。 (80)Erica Marat,"Following the New Silk Road," The Diplomat,October 22,2014. (81)Matthew Goodman and Ely Ratner,"China Scores:A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Do Next," Foreign Affairs,November 23,2014,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384/matthew-goodman-and-ely-ratner/china-scores,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 (82)James F.Dobbins,"Current U.S.Policy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Washington,D.C.,September 16,2013,http://fpc.state.gov/214229.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3)Lynne M.Tracy,"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Silk Road," October 25,2013,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3/215906.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4)Nisha Desai Biswal,"The New Silk Road Post-201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Washington,D.C.,January 22,2015,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5/236214.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5)Antony J.Blinken,"An Enduring Vision for Central Asia," Brookings Institute,Washington,D.C.,March 31,2015,http://www.state.gov/s/d/2015/240013.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6)《美国第一副助理国务卿赴中国商谈“一带一路”》,http://intl.ce.cn/sjjj/qy/201506/05/t20150605_5559494.s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7)《美研究员:一带一路上的中美合作互补远大于竞争》,http://intl.ce.cn/specials/zxxx/201506/19/t20150619_5694156.shtml,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88)Lauren Dickey,"China Takes Steps Toward Realizing Silk Road Ambitions," China Brief,Vol.14,Issue 11,2014,pp.3-4. (89)瓦利·纳斯尔:《美国需重新思考“重返亚洲”战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790?full=y,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90)Andrew C.Kuchins,"Why Washington Needs to Integrate the New Silk Road with the Pivot to Asia," Asia Policy,No.16,July 2013,pp.175-178. (91)U.S.Department of the Navy,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March 2015,p.1. (92)U.S.Department of the Navy,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March 2015,pp.3-18. (93)《中国三部门发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8/c_1114795089.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1日。 (94)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第231-232页。 (95)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158页。 (96)Nisha Desai Biswal,"The New Silk Road Post-201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Washington,D.C.,January 22,2015,http://www.state.gov/p/sca/rls/rmks/2015/236214.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3日。 (97)笔者于2015年7月25日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的交流中,他将中国的这一“遭遇”形容为一个大国不可避免的“负担”。 (98)薛力:《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面对的外交风险》,载《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第72页。 (99)《财政部长楼继伟回应亚投行七大热点问题》,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20/c_1114712336.htm,登录时间: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