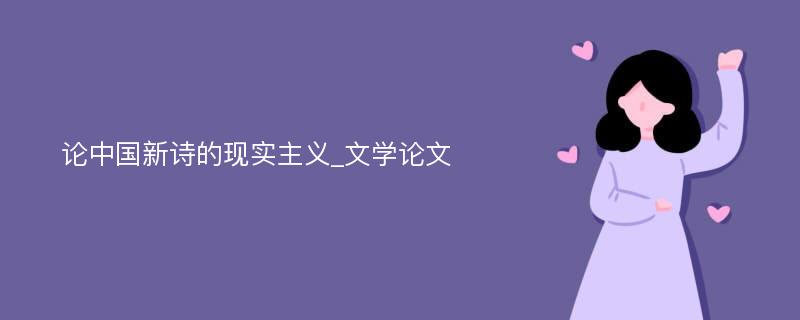
论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中国新诗的一股主潮。
诗坛出现什么样的诗歌潮流,密切联系着时代的脉搏。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是民族独立与沦亡、人民解放与禁锢进行残酷搏斗的时代,人文意识觉醒的诗人们,在光明与黑暗交叠的感受中,既直面现实,揭示生活就是这样的真实;又幻想腾飞,做着生活应该是这样的美梦。这种二级统一的时代内容,决定着这一历史阶段的新诗,既活跃着现实主义,又风行着浪漫主义,而不像西方,现实主义是在否定浪漫主义的基础上出现的。不过,就新诗草创期的实况看,三个始作俑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尝试写新诗时的倾向,还是对“歌诗合为时而作”这一中国传统诗教的忠实继承,类似于“唯有刻刻不忘人生二字,然后有以立其本身”[(1)]这样的言论,在那时的诗坛是震荡得最响亮的。所以“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实是新诗最早形成的一股潮流;而新诗几十年演变的历程也证实着:现实主义始终是一股巨流,奔腾在中国现代诗潮的主干河床上。
一
现实主义有其存在的复杂性。它还被人称作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者中,颇有些人是把这两个称谓混为一谈的。白留替尔的《法国文学史》就笼统地称之为自然主义,并概括出三大特征:第一是“非个人的”或“没人格的”,即作家在作品中不特别流露自己的性格及倾向,只要求他如实地描写所要再现的对象,忠实地复制所要模仿的生活;第二是尊重科学,认为决定艺术的真实和表现的真伪是科学,由科学证明的总是真实,否则都是虚伪;第三是“无感觉”,即作家面对的事实必须只当是事实而已,只需记录这一事实而不该加以判断,显示出一种“绝对无关心”的态度。对此,日本学者木间久雄认为:“将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分别着观察的时候,那么他的解说的第一、第三条是写实主义的特征,第二条才真是自然主义的特征。”[(2)]这就是说:把受诸自然的感觉印象,如所见所闻的那样如实再现出来的,是写实主义;把感觉把握住了的事实再掺入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客观分析态度,使主观印象色彩淡化,更近于事象客观存在规律的,是自然主义。对后者,英国学者麦克唐尔认为“是哲学的或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转用”,其“一切题材,不外是当作人间的机械观上的科学的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价分析。”[(3)]由此看来,写实主义尊重事实,在主体感受印象的如实再现中显示出事实的本色;自然主义也尊重事实,不过强调要让精确的科学分析介入,从而显示出事实的本真,却也限制了主观感觉印象的如实再现。当然这二者的立足点是相同的:反对脱离现实的真实描写,架空生活的理想主义。由此可以说:现实主义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写真实上的辩证统一。但现实主义存在的复杂性却也全出在如何辩证地对待写真实这一点上。现实观察的感觉确实性是写真实的基础,这是由于它总是受着审美内在规律的制约之故,所以分寸容易把握。现实经验的科学制约性能使写真实成为生活真实的升华,其中审美内在规律能起潜在作用,但主要还是受科学分析的控制。当然,科学说到底是对物质与精神结构的发现,而时间的局限,会导致它发现的局限,故科学的分析会因人因时而大有真伪深浅之分。也必须指出:让科学的分析去过分控制写真实还会有两个副作用:一、从接受的角度看,因人因时的不同会出现价值判断的不同;二、严密的客观原则控制,会对主体审美内在规律起排挤作用,淡化文学本体的审美性。如此说来,自然主义所具有的特征,在现实主义创作追求中,既特别重要,又会带来不少麻烦。
值得注意上引麦克唐尔的那句话:“文学上的自然主义,结局是哲学的或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转用。”的确,作为“科学运用到文学上的一种方式”,[(4)]自然主义所遵奉的科学精神,既包括自然科学的原理,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的原理。“作社会小说的未曾研究过社会问题,只凭一点‘直觉’,难怪他用意不免浅薄了。想描写社会黑暗方面的人,很执着的只在‘社会黑暗’四个字上做文章,一定不会做出好文章来的,我们应该学习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读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理,否则无法免去内容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5)]茅盾的这一段话承袭和发展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简称“左拉主义”)的好的一面,却也不能不看到:左拉在把握他的艺术世界时,主要是根据自然科学中的遗传学、病理学等把人作为动物来解剖、来实验的;他即使也写到人的心理状态,目的也为了科学实验。因此,这方面如果强调过分,则会出现一种“专在人间看出兽性的偏见”,这就不能低估“‘左拉主义’的危险性”。[(6)]如果不正视这一点,甚至还再把左拉主义抽象成一条创作艺术思路,从遗传学、病理学等推延开去,让哲学、社会科学去左右艺术世界,那就会出现另一严重后果,使文学不仅失去审美的质的规定性,还因此成了政治的传声筒。
此上就是我们对西方传统观念中现实主义存在的复杂情况所作的回顾。那末,这一股诗潮又是如何被中国新诗坛所接受的呢?
如同前面已指出的:现实主义是中国新诗中最早形成的一股诗潮。新诗草创期间,三个始作俑者就以为人生而歌唱显出忠于现实的特色,特别是刘半农,写于1917年的《相隔一层纸》,成了中国新诗现实主义的起点;接着“星期评论派”的刘大白、玄庐,“新潮”派的康白情等紧跟而上,写出了《田主来》、《卖布谣》、《十五娘》、《草儿在前》、《江南》等,为新诗的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础。20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前奏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五卅惨案”,华夏共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几十万人头落地而告终,白色恐怖蔓延遍神州大地。这种种都迫使有良知的诗人们睁大了心灵的眼睛,去直面现实人生。于是文学研究会打起“为人生而艺术”的旗帜,大力提倡现实主义,并以《小说月报》、《文学周报》、《文学旬刊》、《诗》等为阵地,推出了徐玉诺、何植三、朱自清、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王统照、王任叔、万曼、鹤西、刘枝、徐蔚南等诗人,把这一股现实主义诗潮正式汇进中国现代诗潮的主干河床。在国难家仇引发了社会剧变的三四十年代,诗人中即使还有想在象牙塔里讨生活的,也不得不走向街头、田野、战场,在残酷而又壮烈的现实斗争中寻求自己的生存依傍,于是现实主义有了更为深广的影响,以《文学》、《新诗歌》、《文学季刊》等杂志为阵地,推出了臧克家、蒲风、杨骚、王亚平、柳倩、江岳浪、毕奂午、李雷、贾芝、张泽厚、邵冠祥、严杰人等一大批“捉住现实,具体描写”的诗人,并把现实主义诗潮推向一个高峰。40年代的中国,是深入展开民族抗争、全面掀起人民解放的大斗争时代,现实主义在容纳了一部分浪漫主义的激情表现后,显示出更波澜壮阔的流势,并以《抗战文艺》、《七月》、《文艺阵地》、《文艺复兴》、《诗创造》等杂志为阵地。推出了艾青、力扬、马君玠、严辰、方敬、玉杲、孙钿、邹获帆、苏金伞、青勃、莫洛、辛劳、李季、贺敬之、阮章竞、黎光耀、袁水拍、牛汉、田地等一大批追踪时代、批判现实,在现实斗争中探求真理之路的诗人,并以七月诗派为首,把现实主义诗潮推向了鼎盛。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新诗中的现实主义从20年代的形成,到30年代的发展,再到40年代的鼎盛,是随着时代斗争的深入、扩大而深化拓展的,西方文艺思潮中现实主义概念范畴的不统一和实际存在的复杂性也反映在这一代现实主义诗潮追求者们的认识和实践中。特别是现实主义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这样那样理论认识的混乱和创作实践的失误。
二
20年代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首所追求的现实主义,其实是写实主义——这批诗人自己就以这个名字替代现实主义的称谓。为明确起见,我们就叫它写实主义型现实主义。
文学研究会诗群的这一追求,出发点是“为人生而艺术”,这个认识态度,其实意味着文学应当去反映社会现象,表现有关人生的问题。这就是他们一致的文学观。不过这里也有两点差别。沈雁冰认为:“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7)]俞平伯则认为:“诗是人生的表现,并且还是人生向上的表现。”“人生是诗的血和泪,但现今的诗,有些离人生很远,有些只能代表局部的人生。我们应该挽回这个‘离魂’的恶征,使诗国建设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8)]可见“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诗要表现人生;二、诗是人生表现。一般总把第一方面看成是文学研究会诗群“为人生而艺术”的核心,这当然不算错。但他们中也有人——尤其像俞平伯,更意识到第二点:诗是人生表现,人生表现可以有多种形态,诗则是其中的一种。而人生表现总是自然的、如实的,毫不受超乎具体人生存在的外在势力所左右的。俞平伯说:“诗不但是人生的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诗人只要能把人生的声音从他个性里投射出来,就是他的唯一的光荣的使命,更不用闯入别的科学的范畴,去僭号称尊。”[(9)]这要求诗人通过真切的感觉、印象、感受、入乎人生之内,再在结晶成诗中融于人生,使诗成为人生的一分子。这种态度是这一批诗人普遍地具有的。朱自清在长诗《毁灭》的结束处说:“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这几行诗多次被该派机关刊物《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作为卷头语引用过,说得上是他们执着于人生,使主体及诗都成为人生表现的宣言。而人生是有着许多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人生,更是充满着血和泪的。这些充满血和泪的实实在在的人生内容,通过主体的感觉、印象和具体的感受,融入主体,使之成为充满血和泪的实实在在的人生的缩影,再通过诗如实地再现出来,也就使他们的诗成为自然而然的人生的表现。为此,这一批诗人强调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印象来写诗。叶绍钧在谈徐玉诺的诗歌创作时就谈到过“他有特别灵敏的感觉”这一特点,并认为正是靠这一点使徐玉诺“自己与自然融化”,“混同于自然”了,而“不是从外面观赏自然”的,是遵奉“感觉是如此,所以如此写下来了”的原则的,因此这位诗人的诗才“这么自然,没有一点雕琢的痕迹;这么真实,没有一些强作的呻吟。”[(10)]郑振铎为文学研究会八人诗合集《雪朝》写的《短序》中呼吁诗人,要“坦白无饰地表现自己强烈的感触。”这“感触”包括“感觉”、“情绪”两个方面,或者说包括由感觉触发出来的情绪。这表明他也强调写诗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印象,忠实于由感觉印象引起的情绪感受。而那个时代由于是“一片血和泪的人生”的时代,因此他要求诗人忠实于血和泪的人生感触,写血和泪的诗。他还因此发表《血和泪的文学》一文,大声疾呼:“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
以上种种说明: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首,一批“为人生而艺术”的诗人所提倡的是用作为人生表现的诗去表现人生,强调忠于自我感触化的客观人生表现。在他们看来这乃是不让“闯入别的科学的范围去僭号称尊”的一种真正写实追求,而这样的追求正是前面提到过的写实主义。因此,把20年代“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说成写实主义当是恰如其分的。
就创作实际情况而言,20年代流行的写实主义诗歌,写得最多的是阶级高压、军阀混战中的黑暗时代和痛苦人生。作为文学研究会诗群中最有影响的诗人,徐玉诺有乡土写实的出色才能,他生活在“兵和匪的出产地”——河南鲁山农村,现实给予的只有兵匪在破寨后抢劫放火,农民在为田主守堡中惨死,醉汉在尘埃里挣扎,妓女在只求赏一个钱,烟鬼、赌棍匍伏在绿莹莹的灯光下……,而他能把握到的生存印象则“到处是——/如林的洋枪/光芒的刺刀”,“山陵似的白骨/河流似的红血”。于是,在《夜声》里他作了这样一场对时代的心理感受的写实:“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这是何等惊心动魄而又真切。像徐玉诺这样对社会人生的感觉印象由于异样真切,所以其现实主义自有特殊的艺术魅力。而20年代这一类现实主义追求者纵使以印象的高度提纯而化为心理感觉直接写出来,也更多地显示为生活印象的如实再现。比较典型的是徐蔚南的《荒港风雪》[(11)]和李景阳的《土匪走后》。《荒港风雪》是劳动者悲苦生涯的再现:一个风云弥漫的薄暮时分,航班船上有个老妇人回忆着一场发生在50年代以前同一天同一个地点的往事。那时她还只七岁,跟打渔的爸爸妈妈顶着风雪漂泊在这个“荒港”里,由于橹已折断,小船既靠不了岸又赶不回村,在饥寒交迫的漫漫长夜里,他们最后以破芦席烧了一锅热水充饥添暖,方逃脱“荒港风雪”中死神伸来的魔爪。但50年后她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老妇人在回忆后嗫嚅道:“呀,这些情景犹在我眼前/不知今天可有和我五十年前一样。”这个从孩提年代到行将走完生命之路的“她”,永远离不开“荒港风雪”中的飘泊的生涯,莫测的前程。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灾祸是20年代这一类现实主义诗人致力抒写的,李景阳发表过多篇这一类诗。《土匪走后》写的是一个农家在土匪破寨后的悲惨遭遇。李景阳在这首诗的“附言”里说:他是亲历土匪破寨后惨不忍睹的场面的,而自己则是个“幸得免者”;由于数年来“此惨剧之图像时映眼际,乃提笔以写此篇”。这些诗是凭诗人在生活中的印象去把握住客观对象,作艺术再现的。由于对象的典型意义和再现中主体情感在对象中十分自然的潜隐,而使它们获得了20年代诗坛写实主义型现实主义的较高成就。
不过,纯客观的写实,无视科学研究的精神渗透,这样的写实主义是难以达到为人生而艺术的境界的。当年,即使像沈雁冰,也在写实主义的见解上,出现过机械论的倾响。如他在谈到文学如何反映人生的问题时竟然说:“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反映出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12)]这种纯客观化,也曾使这一类诗人的写实主义追求出现过记帐式缺乏艺术魅力的倾向。叶绍钧的《浏河战场》虽也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但他对事象的客观描写,却是报导有余而典型抒情不足;康白情的《律己九铭》完全是无聊的记帐。这里特别值得提一提刘宇的《械斗》[(13)],它通过血淋淋的事件,把宗法制农村“黑暗王国”异化人性为兽性的真实,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来展览,自有震撼人心之力。诗写的是边地省份的两个村子只为了老庄不懂事的孩子骂了新庄的大人,为争祖宗一口气而闹出一场械斗。在宗族“太公”捧祖宗神牌压阵下男女老少齐出动,直杀得天昏地暗,不分胜负,而多少勇壮汉子倒在了血泊里,多少年轻女人就做了寡妇。显然,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何要如此仇恨对方,只是被维护祖宗名誉的念头去干野兽一样的勾当。诗的审美追求如果能明确地定位在这一点上,那是会有很高的现实主义品位的。但诗人却致力于去写两方如何处死俘虏,剁成“肉酱”,做成“肉饼”,并在市场上互相拍卖,各自以敢于吃自己村死者的人肉饼,以及谁吃得多来定胜负等等内容,这种太野蛮太原始的生活表现,不是美而是丑,没有悲剧的崇高而只有闹剧的卑俗,从而使积极的审美追求倾斜到消极面上。写实主义没有理性的科学精神渗透和潜在的制约,其弱点也就暴露了出来。正是这种种使郑振择提出:“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是忠实的写社会或人生的断片,而其截取此断片时,至少必融化有作者的最高理想在中间。”[(14)]沈雁冰也由此中悟出了一个新认识;忠于写实的作家应“把科学上发见的原理”应用到创作中,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否则恐怕没法免去内容单薄或用意浅显两个毛病”[(15)]——这显然是想以自然主义的主张来对写实主义的弊端作矫枉。
就这样,到20年代后期,不仅文学研究会诗群的诗人,以自然主义的主张来为风行一时的写实主义纠偏,还扩大到整个诗坛。特别是以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的一批无产阶级诗歌派,接受了苏联“拉普”派的主张而提倡“普罗现实主义”,最是典型。于是,从20年代末起,到30年代,现实主义追求又出现了一股新的倾向。
三
如果说在20年代末以前现实主义只是一种比较广泛的文学精神在流派和思潮中体现着,那么到这时期却被称作创作方法了。这要归之于“拉普”派的主张。创作方法这一概念对于促进人们更自觉更全面地认识和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提出这一概念者原意是想用哲学、社会科学精神、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规范文学创作活动,因此,在提出创作方法这一概念后,他们还作了更极端化的推延,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创作自身规律的理论,竟把活生生的生活用来图解上述科学精神(即辩证唯物主义,或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材料,以致成了自然主义主张的变种——这也许是“拉普”派始料未及的。中国30年代文坛,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通过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家臧原惟人的著作接受了这个主张,在文学界广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普罗现实主义,认为只有靠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使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繁荣。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就梦幻般提出:“革命文艺家应该用辩证唯物论的眼光来分析客观的现实,把这客观的现实再现于他的作品。”[(16)]像钱杏村的长篇叙事诗《暴风雨的前夜》就是这类理论指导下的产物,一切人物抒情和事件冲突都围绕着革命暴动的阶级斗争意图而设计。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理论混乱: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普罗现实主义”,普罗现实主义作家忠于现实生活就是忠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革命的世界观,真正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实感则成了可有可无的。这种现实主义理论显然要窒息创作生机。在这方面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为主的无产阶级诗歌派是个典型例子。好在不久以后,苏联解散了“拉普”,批判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在吸收“拉普”主张的某些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代替“普罗现实主义。”于是,30年代诗坛的现实主义也终于部分地摆脱了“拉普”理论的纠缠,但又始终难以摆脱自然主义型的现实主义道路,就是说它们对题材的现实性、现实的倾向性与典型性等问题都没有在创作实践中解决好。
应该说这一类现实主义的追求者们是把题材的现实性看得十分重要的。中国诗歌会在其机关刊物《新诗歌·发刊诗》中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我们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17)]为此,中国诗歌会还列举九个方面的重大题材要求同人们去“捉住”。这使中国诗歌会派诗人在现实主义的追求上跃进了一大步,如穆木天,从一个超现实派转向了现实主义,怀着“流亡者”的痛苦、愤怒和为祖国献身的真情,唱出了《在喀拉巴岭上》这样有较高现实主义层次的长诗,而这正是他紧紧“捉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大题材所获得的成果。杨骚从一个新浪漫派转向现实主义,怀着向旧世界复仇的激情,唱出了《乡曲》,成了这位诗人一生创作的顶峰,该派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柳倩曾是“受了好些新月的格律的影响”[(18)],一心寻求“生命的微痕”的诗人,但他也终于“捉住”了重大的现实题材,为“一二八”战争写出长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被人誉为“史诗”。[(19)]这些作品“捉住”的都是处于时代焦点的重大社会题材。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臧克家、艾青和田间,他们是全身心感受着3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重大生活内容,作着真挚抒唱的。他们为农村而歌,臧克家写了《难民》,《老哥哥》,艾青写了《大堰河——我的保姆》,《九百个》,《死地》;田间写出了《春荒》,《农民的歌》;他们为都市而歌,臧克家写出了《罪恶的黑手》,艾青写出了《马赛》,田间写出了《没有太阳的街》;他们为国际而歌,臧克家写出了《中原的胳膊》,艾青写出了《复活的土地》,田间写出了整整一卷《中国牧歌》。但左翼理论家及自然主义型的现实主义倡导者,在提出题材现实化,抓现实重大内容的主张中,表现出绝对化的要求,认为除了表现重大的现实内容,即与革命斗争有关的题材,其它都是非现实主义的“虚伪的题材”,还有人提出写重大题材要获得真正的成功必须“定位在作品所表示的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20)]
以“观念形态是否属于无产阶级”来为现实主义作品作价值定位,使这一类现实主义追求者还对采用的现实题材作倾向性的思考。穆木天有段话是有代表性的。他说:“分析现在中国的社会的矛盾,把握住它的因果关系,而以现实的态度,真地把它们描写出来,给一般的民众指出新的道路。”[(21)]这要求诗人在观察与描写现实时必须在整体存在的格局中去辩证地对待,或者说现实主义的现实表现要显示出认识世界中具有鲜明倾向;即把现实置于时代的洪流中去显示其历史地发展的趋向,展示历史前景——这就是对现实的倾向性要求。这种倾向性处理得好,的确能提高作品的现实主义品位。臧克家的《难民》,艾青的《死地》,都是写农民的天灾人祸,而饥饿线上挣扎的现实画面也都逼真感人,因此成了30年代诗坛现实主义的佳作,但比较一下,它们的品位是有高低之分的。《难民》写大饥饿中的农民集体逃荒到一个小城镇上,却被当地政府以“年头不对,不敢留生人在镇上”为借口当夜赶走。诗在结束处说:“铁门的响声截断了最后一人的脚步/这时,黄昏爬过了古镇的围墙。”作为一幕人道主义的悲剧,的确很感人。但难民们今后往哪里去,他们的明天会怎样,诗篇没有暗示其更合于时代大背景的倾向,而只是勾勒出一片凄凉、茫然的境界。《死地》不同。这首诗在抒述尽大旱之年农民遭受的无尽灾难,以及他们悲哀绝望的心境之后,笔锋一转,把处于生死关头的“地之子”比之为狂卷而来的“黑色的旋风”,并设问:“从死亡的大地/到死亡的大地/你知道/那旋转着的,旋转着的/旋风它渴望着什么呢?”诗人的回答是:“我说/如有人点燃了那饥饿之火啊……”这就显示出一种要革命暴动的倾向,这倾向指出了历史的明天:反叛中求解放。所以一个诗人如若能有先进的世界观,那末在把握真实世界时,就会比生活现实站得更高,展示出现实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趋势。这样的倾向性就使《死地》的真实世界比《难民》更真实。但也应该指出:这类现实主义一般强调的倾向性要求,实质上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来规范现实主义创作的,这就容易走偏;若再强调过分,甚至会走向一个脱离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极端。穆木天就有过这么一种说法:“作品中的内容的组织过程,社会的变化的过程,人物的心理过程,一切的作品中的过程,是要合于辩证法。”[(22)]这实际上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去限制和取舍生活,其结果,倾向性是有了,却不是诗学的倾向,只是观念、目的的传声筒。蒲风的《农夫阿三》就很有代表性。这首诗写一个“不愿当官兵,匆匆逃命忙”的青年农民阿三,在逃亡的路上感慨于别人收割庄稼喜气洋洋,自己却要背井离乡凄凄惶惶之际,忽然想到他乡也在抓丁,“小百姓只有死”,“迟早也是一条命”,还不如回家去,团结众弟兄,“拿起锄,翻过山来换过地,”因此就掉回头“匆匆忙忙回家去”了。阿三成了革命意识——预定的观念目的的牵线木偶,丢掉了生活形象发展的内在逻辑,人为地处理了人物思想情绪的转变。阿三逃亡到“欢欢喜喜转过头来”,觉悟是提高了,倾向性是鲜明了,却没有倾向性的诗学真实。有关文学的倾向性,恩格斯早就在《致敏娜·考茨基》中说过:“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这就是说:倾向性既来自于,又要归结于形象的真实——按艺术内在规律营构的形象真实。由此看来,倾向性是和艺术的真实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从本质上看是区别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20年代以文学研究会诗群为核心的写实主义诗人也重视真实性。朱自清写过《文艺的真实性》[(23)]一文,认为文学创作是“表现”而不是“再现”,他以想象作主要材料和向导,对现有的记忆材料“加以删汰、补充、联络,使新的生活得以完满地实现”,即会造出一种新的生活。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若透出一种新的生活,完成一件作品,就具有“表现”所达到的真实性。这正是写实主义的真实性见解。30年代自然主义型现实主义追求者不像朱自清那样从创作内在规律出发来理解真实性,而是从能否求得“某种标准”出发——具体说他们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来理解真实性的。周扬写有和朱自清类似题目的文章——《文学的真实性》[(24)]。他从“某种标准”出发,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对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唯物论的态度,大胆地、赤裸裸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到文学的真实之路。”这种抱纯客观的、唯物论的态度去作再现,是指不带主观心灵感应而生的想象活动而言,这就使周扬进一步发挥说:“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线的阶级,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认识客观的真理。换包话说,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真实性。勃兴期的资产阶级就是一个这样的阶级,它以‘自然科学的’世界观作基础,打破了封建文学的‘宗教的’偏见,更进一步地接近了客观的真实,给予了全人类的文学的发展以很多的东西。”这正是自然主义型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只不过以周扬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所提出的这一类现实主义,求的不是左拉们的自然科学——遗传学的“标准”,而是社会科学——具体点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标准”。唯其如此,周扬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才是到现实主义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这显然是把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归之于政治的正确,丢掉了对真实的审美本质要求。应该说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所要求的,是重造新的生活的想象活动的真实以及促使这种想象活动展开的情绪感受是否和历史真实取得了辩证的统一。30年代左翼文坛所主张的现实主义真实性存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此,而要使这二者统一,就有必要考虑真实的典型性。
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努力使上述二类真实通过典型化取得辩证的统一,这就会出现比生活的真实更集中更有审美感受真切味,更能体现历史发展趋势,因而是更高形态的艺术真实,而我们也就称之为典型。当年,有人就对此作过这样的论析:“艺术家在创造典型的工作里面,既需要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还需要认识人生,分析人生的能力,使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是本质的真实的东面。这样创造出来的‘典型’,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扩大’,‘深化’。”[(25)]这大致上合于把典型看成两类真实辩证统一的提法,而这也是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理论相吻合的。恩格斯所说细节描写的真实,是就小说而言的;应用到诗里,是指氛围渲染的真切。至于现实主义,可以说是除了氛围渲染的真切以外,还要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这里的细节描写的真实或者氛围渲染的真切,指的是不违背客体对象的主观感受的记忆原生态。展现人物性格成长的情节,离不得细节的真实;显示人物情绪流变,离不得氛围的真切。这些指的即朱自清所谓重造新的生活的想象真实而言,或者如胡风所谓需要想象的直观来熔铸作家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的真实而言。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或典型情绪,则显然是指人物性格或情绪所能体现历史发展的趋势,或如胡风所谓“从人生里面取来的本质的真实”。根据这些分析,我们认为现实主义必须真实,艺术真实必须具有典型性,典型性则必须由上述两类真实辩证地统一而成。
所以30年代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左翼作家提倡的现实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进入了误区的,“捉住”的现实和具体的描写有意无意地排斥了主体诚实的感受,和主观真切的体验,而以哲学社会学的“科学精神”来摆弄主体的艺术构思,图解“科学精神”——特定的政治目的意识。中国诗歌会是这类现实主义忠实的贯彻者,而该派主要的负责人穆木天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虽然“努力去接近现实,可是有些诗歌成为了现实的拷贝了。有些诗,是韵文的故事,而不是诗,情绪不够。”[(26)]
四
于是,现实主义在40年代新诗坛又不得不去作新的探索。这一场探索是更其艰难的,因为既要发挥写实主义之所长,对主体感觉到的客观对象作不能走样的如实反映,又不能丧失主体能动性;既要发挥自然主义之所长,严格按科学精神解剖客体对象,又不能丧失主体精神性,也就是说必须取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各自之所长,来真正把握现实主义。
值得首先提出来研讨的是胡风的主张。
胡风虽然在30年代就已对现实主义问题十分关注,但真正形成一个理论体系的,是在抗战以后。这位批评家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抵制抗战八股,目的是克服抗战文学中的上述不良倾响。为此,他提出反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口号,并从中建立他现实主义创作论的基本体系。这两个口号直接触及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弊端,而其本意则在于让写实主义积极开展印象联想活动、再现生活感觉真实同自然主义致力于科学解剖客体,再现生活本质真实辩证地统一起来,并借此来完成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胡风展开这一理论思考的切入点是“人”,把现实主义孜孜不倦追求的“现实”与“人”挂上钩,从中强调出人的精神性的存在意义。在胡风看来,这一存在意义显示在两个方面:一、现实主义所忠实表现的客观现实必须溶入人的主观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实主义的艺术世界具现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27)]二、现实主义诗人在把握客观现实中必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即显示人在自然世界与社会网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任务和主要内容。因此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就要穿透外在的人生现象而揭示出由人的精神活动所达到的“血肉的现实人生”,在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里,“被体现者被克服者既然是活的感性的存在,那体现者克服者的作家本人的思维活动就不能够超脱感性的机能”,而“被体现者被克服者”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因此,胡风认为“体现者克服者”必须警惕,不要被“这种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要有批判的力量”[(28)];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正是“一代的心理动向”,要通过包括“负担痛苦、愤怒、反抗”和“潜在的热情,追求解放的渴望”在内的“人的精神斗争”,以对“一代的心理动向”作真实的反映。[(29)]
正是从这一种现实主义写真实的认识出发,胡风为力矫写实主义弊端作了一场严肃的思考。在他看来,写实主义者只是忠实于主观感觉、印象所及的客观对象,而没能深入把握对象的灵魂,因此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指出:这导致了创作中的“主观公式主义”。陷入进主观公式主义者对客观对象所作的不过是“主观浮影的描写”,“抄录”“死样活气的外在形象”而已,而不懂得现实主义的写真实必须深入到生活的“内在的形象”,要是不懂得这一点,也就无法“反映强大的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和火热的生活要求的生动性”。有鉴于此,胡风对田间战前和抗战初期的诗作了深入思考。他说:“我曾说到,诗‘应该是具体的生活事象在诗人的感动里面所扰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对于这个‘诗的大路’,田间是‘本能地走近了’,虽然在他现在的成绩里面还不能说有了大的真实的成功。为什么只是走近了而已呢?因为,‘在他的诗里面,只有感觉、意象、场景的色彩和情绪的跳动’;因为,他还没有达到‘和他所要歌唱的对象的完全融合’。”[(30)]这是胡风对田间写实主义的弊端——客观对象的主观浮影式抒情发出的警告。
如果说客观对象的主观浮影式抒情,导致主观公式主义的弊端,究其原因是现实主义追求者丧失了历史主义精神在艺术构思中的渗透力所致,那末客观对象的科学精神、哲学观念的图解式抒情则会导致客观主义的弊端,究其原因是现实主义追求者丧失了主观战斗精神在艺术构思中的能动性所致。为此,胡风在现实主义探索中,又对诗人把握真实世界的主观能动作用作了严肃的思考。他曾说:“文艺作品是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保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31)]胡风提出主观战主精神是策略的。这种策略的提法,建基于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凭这一点,诗人在感受和把握生活真实的过程中方能以主观战斗精神为中介,使客观现实生活的历史趋向和主体社会实践的先进体悟作交融,而胡风就以此下断语:“我们把那叫现实主义。”[(32)]与此相应合,他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客观主义的主张。胡风认为文学的客观主义“只是凭着‘客观’的态度,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人对象,进行搏斗”的一种审美倾向,由此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不可能是“在作者自己的血肉的经验里面把握到因而创造出来的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形象”,它所向往的只是“通过科学理解的现实的客观意义”,“却不能把认识和反映现实当作一个实践斗争”,因此客观主义所追求的现实不可能“在强大的历史动向里面激动着”,和历史相“呼应着”,并且建立“彼此相通的血缘关系”,甚至会“使现实虚伪化了”。于是,他十分尖锐地指出:“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有着类似之点,而且保有某种渊源的”。[(33)]就这样胡风在对以客观主义为标志的自然主义作严肃的指评中高扬主观战斗精神,力求树立一个让主客体真正结合的现实主义真实形象,并以这样的理论去审视中国新诗在抗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特征。他曾这样解析一个诗人的现实主义倾向: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发现需要主观精神的突击。在诗的创造过程上,客观事物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燃烧才能够使杂质成灰,使精英更亮,而凝成浑然的艺术生命……你的那些叙事诗,就是由于主观情绪的贫乏而成了非诗的东西。当然,你是诚恳地肯定那些故事的,所以能够提起笔来。但你的肯定只止于理念上的肯定,并没有达到和对象本身的情绪的交融,因而你的诗还是止于义务地叙述出来的故事。你太相信题材本身了,以为既然是题材本身,那么好,作者只要尽了叙述的任务就尽够。但你忽略了,题材本身的真实生命不通过诗人的精神化合,就无从把撮,也无从表现,更何况诗的生命还需要从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的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呢。[(34)]
这些话无疑给现实主义诗潮中的客观主义倾向以有力的抵制。
吕荧也是40年代致力探讨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他恰恰在主观战斗精神这一点上对胡风的偏面性作了有分寸的修正。他认为:“如果理论上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意义,反对表面化的政治倾向,可是实际上向游离现实的个人主义艺术方向发展”,那末,“这一种表面上强调主观的力量,实质上削弱了主观战斗要求的意义的”。因此他告诫说:“并不是说有了主观的精神就有了一切”,“也不是说主观的战斗就能代替现实斗争的全部实践”。在他看来,主观战斗精神是促使现实主义作家去“描写人的真实的内心生活和精神境界”——或者说去表现“精神生命”的真实,但要是这种追求只是“以作者的主观精神、内心燃烧和冲击来烛照的时候”,那末“生命的真实的一面就要显得微弱”,“精神的生命就不能具有突破一切坚城的猛力”,从而使作品“流为空虚的主观的绘画”,“作品中的现实面趋于隐晦。”[(35)]当然吕荧是基本上认同胡风的现实主义主张的,特别是对“自然主义”的看法,他比胡风要明确、坚定。他认为“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要素是观念的思维,客观现实、并且浮化现实,铺张生活细节的枝叶来代替社会现实的本质。”可见自然主义的致命点是“观念的思维”,这不仅包括左拉们的遗传学自然科学的“观念的思维”,也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社会科学的“观念的思维”,因此他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思想内容上只是用唯物史观‘勉强的去凑合’历史或现实上的事物,而不是用它做深刻研究认识历史或现实的‘指导的线索’,就会出现观念论的东西;在生活态度上不是深入现实,全身心和人民结合,以人民的生死哀乐为自己的生死哀乐,而采取冷冷的客观的态度,就会产生新的客观主义;在创作方法上不深入现实,把握本质,表现典型的环境中的典型的人物,而用生活表象代替现实本质,铺张事物的枝叶来凑合理论教条,就会产生新的‘自然主义’。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或多或少的重复了左拉的创作道路。”[(36)]
艾青在《诗论》里也多次论及现实主义的问题。他反对“摄影主义”式的写实主义追求,并认为“这大概是由于想象的贫弱”造成的;他还进一步揭示写实主义的病根:“浮面的描写,失去作者的主观;事象的推移,不伴随着作者心理的推移,这样的诗也就被算在新写实主义的作品里,该是令人费解的吧!”[(37)]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对写实主义表示不满中强调“作者的主观”,事象的推移一定要“随着作者心理的推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艾青的现实主义观点和胡风、吕荧有相通之处,即强调主观精神的发挥。他甚至提出过一句颇有煽动性的话:“问题不在你写什么,而是在你怎样写,在你怎样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角度上看世界,在你从怎样的姿态去拥抱世界……”[(38)]这里有关“你”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和“姿态”的提法,不仅显示着艾青强调主体精神在构筑现实主义诗歌真实世界中的作用,更体现了主体精神中理性的、科学意识的渗透,世界观的潜在作用,因为选择什么样的角度就是受科学意识所制约的,采取什么的姿态就是受世界观的支配。所以他的现实主义思考是本能地走上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之路。在初版本《诗论》的《技术》一书的第27节,艾青还这样说过:“在诗里,必须是生物学的地处理观念、思想、情感……诸般抽象的东西。”[(39)]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所谓“观念”,“思想”,都要“生物学的地”去处理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说一个现实主义者要以科学的观念去设计、营构诗歌真实世界时,这科学的观念一定要本能化,而不能采取客观的、冷漠的态度。这一见解可说是艾青企图把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更好地结合起来以完成现实主义创作的精辟见解。
以上种种现实主义主张,如果归纳一下,可以理出这样一个现实主义的追求体系:写实主义追求中必须让科学观念渗透,使其有自然主义倾向;自然主义追求中必须强调主体精神的作用和情绪的渲染,使其有写实主义倾向;而写实主义的自然主义化和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化则在主观战斗意志的干预下,方能把握到现实主义的真实生命。以这样的现实主义体系精神来观照40年代的创作,则我们首先总觉到田间的诗始终难以进到更高的现实主义层次,抗战初期他写的大量诗作大多显示为印象式的写实主义倾向,但正当他刚有所挣脱迹象,写出了《抗战诗抄》里的《炉火正红》等短诗和长篇叙事诗《柏树》以后,不久,配合政治宣传要求,革命世界观替代现实主义的真实感受去把握诗歌世界的理论左右了他,他又迷糊起来,于是写出了《戎冠秀》、《赶车传》等诗,走上了观念化的自然主义之路。晋察冀诗群的多数作者,以1942年为分界线,分别显示着像田间这样的两极转化特征。这也许是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现实主义诗人所走的共同道路。写过现实主义典范之作《火把》的艾青,虽然1941年到达延安后不久所写的长诗《雪里站》,还能显示出他对现实主义的本色追求,但1943年写的《吴满有》,同样有观念化的自然主义意味。在这批根据地的现实主义追求者中,李季无疑是最有成绩的。他写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为题材,表现中国农民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勇敢地投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去寻求自己阶级幸福的心理大转型,李季显然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看待和概括那个风起云涌的阶级大搏斗时代的,尤为可贵的是能把这个动荡时代生活现象的如实描写与诗人的主观激情在主人公历史性心理大转型中的渗透交融,这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一块里程碑。
应该说七月诗派是在现实主义抒情中做得很有特色的。这个诗派在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把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各自的所长结合起来,在虔诚地、历史地拥抱客观现实中融入主观战斗精神,来完成富有浪漫主义意志高扬情调的现实主义抒情。如果说孙钿的诗集《旗》,胡征的组诗《白衣女》等较偏于客观如实抒写,主观战斗激情是隐伏在客观事象中的,那末绿原的诗集《又是一个起点》,彭燕郊的长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等,则是让主观战斗激情牵引着客观现实在作悲壮的腾跃,而天蓝的《队长骑马去了》,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长诗,邹荻帆的《雪与村庄》,杜谷的《江·车队·巷》等组诗则是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所长,让严峻而具体的客观现实受历史地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淘洗,又在主观战斗激情大面积的渗透下完成了的一场艺术真实的呈现,它们成了七月诗派的现实主义典范之作。与七月诗派这种现实主义追求很接近的,如玉杲的长篇叙事诗《大渡河支流》,力扬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莫洛的长篇抒情诗《渡运河》等,同天蓝、牛汉、邹荻帆、杜谷等作汇聚在一起,显示出新诗中的现实主义在40年代已走上了康庄大道。
注释:
(1)孟真:《中国艺术界无病根》,《新潮》第1卷第1号。
(2)木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等182页,沈端先译,开明书店1930年5月版。
(3)转引自木间久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第163页。
(4)左拉语,转引自黄仲苏《什么是自然主义》,傅东华编《文学百题》第49页。
(5)(15)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期。
(6)茅盾:《“左拉主义”的危险性》,《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第50期。
(7)《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6月版。
(8)(9)《诗的进化的还原论》,《诗》第1卷第1号。
(10)《玉诺的诗》,收入徐玉诺《将来之花园》,第113至14页,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版。
(11)《荒港风雪》,《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
(12)《文学与人生》,《茅盾文艺杂论集》(上)第110页。
(13)《械斗》,《新月》第2卷第9期。
(14)《文艺丛谈》,《小说月报》第12卷第3号。
(16)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上谬误》,《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
(17)《新诗歌》创刊号,1933年2月。
(18)穆木天:《〈生命的微痕〉序》,生活书店1934年10月版。
(19)蒲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蒲风选集》(下)第813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版。
(20)汉年:《文艺通信》,《现代小说》第3卷第1期。
(21)(22)《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北斗》第2卷第1期。
(23)《小说月报》第15卷第1号。
(24)《现代》第3卷第1期。
(25)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胡风评论集》(上)第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6)《一点意见》,《新诗歌》第2卷第2期。
(27)《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
(28)《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胡风评论集》(下)第20至21页。
(29)(33)《论现实主义的路》,《胡风评论集》(下)第336页。
(30)《关于诗和田间的诗》,《胡风评论集》(中)第99页。
(31)(32)《现实主义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第319页。
(34)《关于题材,关于“技巧”,关于接受遗产》,《胡风评论集》(中)第362页。
(35)《艺术的政治》,《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第9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36)《释自然主义》,《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第133至134页。
(37)(38)(39)分别见《诗论》第24、26、40页,新新出版社1946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