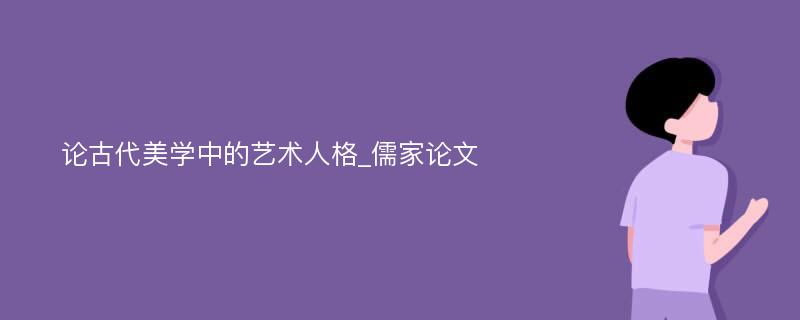
古代美学中的艺术人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学中论文,古代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美学重视理想人格的培育,重视在审美创作中实现艺术人格的建构与提升。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价值目标,构成了古代美学艺术人格论的两种深层文化心态: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其精神实质是立足于人,追求人格的完美与升华。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所展现的内心世界及其艺术人格,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凝聚为三种审美情调:追求浩然之气的社会美;追求无限和永恒的自然美;追求率性而真的情感美。
关键词审美价值 理想人格 艺术人格 忧患意识 超越意识 情感美
中国古代美学很早就注意到审美创作主体的人格对其作品艺术境界和审美价值的影响,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强调理想人格的培育。于是,艺术作品也就成为理想人格的体现者。理想人格作为一种内在尺度,指引着审美创作活动,规范、调节着创作主体对现实人生的基本态度,并通过艺术作品物化为一种审美境界,熔铸为真善美相统一的艺术人格。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美学是以人格为中心的美学。自先秦以来,以儒道思想观念为代表的美学家和作家、艺术家,无不注重艺术人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无不力图在审美创作中实现艺术人格的建构与提升。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所形成的艺术人格论,作为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是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的。
1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派别不同,观念不同,如儒道诸家,他们对真善美的理解及其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他们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模式也各不相同;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重视理想人格的培育却是一致的。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最大的善,也是一种内在的美,极高的人格美。孔子理想人格的基本规定是“礼”和“仁”,“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仁”是内在的精神原则。孔子的“仁”和“礼”固然有其历史的特定含义,但把“仁”作为善的总称看待,其所包容的诸如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丰富内涵,已是一种宽广的道德感情或崇高的精神境界了。至于孟子进一步把仁义推广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普遍人道主义的高度,以及把主体修养推广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精神,更是对人的伟大力量的充分肯定。当善的实现表现为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自我肯定时,我们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不同时也看到了美吗?
儒家理想人格的可贵之处,是他们明确意识到理想人格或美的人格的实现是一个修养过程,艰苦的磨炼过程。孟子十分重视生活遭际对于砥砺人的内在精神力量的重要性,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 〕孔子更强调这是人的一生的修养过程,从“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四十而不惑”,从“知天命”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几个发展阶段,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人生的自我实现的完美境界。孔子把完美境界称之为“尽善尽美”(《论语·八佾》),“尽善”即是极好,自然是和道德的价值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孟子也说“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这里的“美”也包括道德价值判断的意义。所以在孔孟看来,“尽善”就是最高的美,就是理想人格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显然,孔孟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是一种道德人格,并且强调道德的自我修养和理性自觉。“仁”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应是人们内心情感上的一种自觉要求,而不是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孟子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就是说,人的道德精神也能给人以心灵的愉快,所以无需强制,这就从美的高度极大地强调了人格修养的意义和价值。以此为出发点,儒家思想注重感化人心,并把艺术作为感化人心、使人们乐于行“仁”的重要手段。孔子的“成于乐”、“游于艺”以及“兴、观、群、怨”等论述,既是他的艺术观和艺术功用论,也是他的人格建构论。“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成于乐”、“游于艺”就是要通过艺术感发人的心灵,创造具有完美人格的人。“兴、观、群、怨”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情感去感染、陶治个体,使个体人格在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对立统一中得到愉快和满足,获得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提升。可见,基于“仁”学为基础的艺术观、艺术功用论,也是孔子建构理想人格、艺术人格的内在尺度,体现了美善的统一。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他们所设计的理想人格是建立在自然无为人道观基础之上的“至人”、“神人”和“圣人”。这种理想人格的核心是不为世俗所累,不为纷争所扰,顺其自然本性,他们认为这才是天下最美的人格。《庄子·逍遥游》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并不是三种不同的人,而是庄子理想人格的异名;“无己”、“无功”、“无名”则是从内在精神的不同角度对其理想人格的定性。儒家追求建功立业和名称于世,庄子则主张“削迹捐势,不为功名”,努力从功名与权势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与“道”合一的圣人境界,所以说“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至人无己”则体现了庄子轻视功名利禄以及要求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彻底忘记自己,回归自然本性、与天合一的人生价值取向。庄子说:“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2 〕所谓“无待”,就是要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的绝对自由,达到人与道和谐统一的境界。这种自然无为的人格理想无疑具有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价值,但是它只存在于庄子的精神世界中,或者说,只存在于美的境界中。顺乎自然本性,不为世俗所累,在自然无为中,人性的自然美得到了保存,这既是庄子人格的精义,也是庄子人格与美的相通之处。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3 〕这里说的“大美”,就是合乎自然之美,“真人”之美。他在《田子方》篇中还描绘了一个具有这种自然之美的“真画者”的形象:“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槃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真画者”就是自然无为、率性而行的最美的人性。庄子认为,儒家的礼法是破坏自然天性,束缚人的个性发展的。他曾以“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庄子·天地》)为喻,指出“牺尊”作为一种礼器,它虽然很华美,但是它已经“失性”,即丧失了活生生的“百年之木”的本性,当然也就失去朴素自然之美了。那么,“解衣槃礴”便是艺术家冲破束缚表现真率自然天性的一种方式,而所谓“真画者”,也就是庄子心目中保存了自然天性的理想人格了。庄子之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强调文章的“自然之道”,钟嵘在《诗品》中提出的“自然英旨”,李白主张的“清水了芙蓉,天然去雕饰”,苏轼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文理自然”之美等等,既是他们的审美创作原则,也是审美主体人格美的标准,这与庄子自然无为的人格美思想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2
中国古代美学的理想人格论铸合了作家、艺术家的美学人格,它是尽善尽美的,它既是作家、艺术家现实的实践精神的支柱,又是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此作为人生的价值目标,构成了古代美学艺术人格论的两种深层文化心态:即忧患意识与超越意识。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入世的。他们或追求人生道德价值的完善,或追求人生功利价值的实现,总是在现实生活中自强不息,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体需求与人类需求、个人愿望与社会现实又往往是矛盾的。从个人不同境遇来说,这一矛盾则表现为“穷独达兼”的文化心态。孟子云:“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 〕“穷独达兼”是在现实生活的不可解脱的矛盾中,保持高贵品格的体现。这种文化心态和人格价值取向深深沉淀在千百年来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凝聚为深沉悲怨的忧患意识,成为民族心理、艺术人格的象征。从孔子的“诗可以怨”,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梗概多气”,到韩愈的“不平则鸣”,到李贽的怨而必怒的主张,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忧患意识一以贯之的发展线索。当人们的理想愿望和情感要求得不到实现,或长期遭到压制、否定的时候,“怨”、“愤”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成为一个基本审美范畴,悲怨人格成为作品中的一种基本人格,就是很自然的了。勃兰兑斯在《20世纪文学主潮》中曾说过:“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特别基调。”的确如此,翻开古代诗词篇章,变《风》、变《雅》的哀怨,《离骚》、《天问》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杜甫的沉郁,陆游、辛弃疾的慨叹以及关汉卿的抗争魂、曹雪芹的辛酸泪等等,这忧患悲怨的“特别基调”一直绵延不绝,也铸造了一个又一个“慷慨”、“雅怨”的艺术人格。他们将儒家那“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泰伯》)的弘毅之气与“发愤之所作”的创作精神凝成一种悲壮沉郁的格调,给人以超拔崇高之美。尽管他们的作品因作者与题材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但是,它们总是在不同程度上贯注着这种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已积淀为代代相承的深层文化心理,渗透到古代作家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审美创作的“特别基调”了。
忧患意识作为一种人格境界,不同于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焦虑、困惑、苦闷等忧患心绪,它是一种从忧患境遇中体验到人的尊严和价值,力图突破现实困境,以达到提升人格境界的特殊心态。清末作家刘鹗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并称这些哭泣为“有力类”之哭泣,是“不以哭泣为哭泣者,其力甚劲,其行乃弥远也。”〔5〕所谓“有力类”之哭泣, 即指他们的“哭泣”中所包涵的深沉博大的社会内容和高尚悲壮的人格精神。在他们的创作中,作家的忧患意识积淀着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这种理性思考往往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升华为对现实生存不合理的批判;由对传统人生理想的执着升华为对生存价值的九死不悔的追求;由对自我人格的肯定升华为对自由个性的追求。此即刘鹗所谓“有力类”之“哭泣”。于是,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小小悲怨之情,不仅仅是一种忧患心绪,而成为人类良心的代表,崇高人格的化身。被称为“惊采绝艳”的屈原,面对楚国内政腐败、外交失策忧心如焚,司马迁说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他在《离骚》中处处表达着“恐皇舆之败绩”、“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愁幽思”,却“虽九死其犹未悔”,始终坚持自己的基本信念。他虽然在现实面前感到失望和焦虑,但并未因此而忘怀故国,也不因此而放弃高洁的人格。同屈原一样,许多古代作家大都容士吏于一身,这就使得他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和尖锐。既有“进与退”、“穷与达”的冲突,又有“安与危”的冲突。在进退、穷达、安危方面,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作出选择;由于他们所面对的是威严的封建权势,这种选择尤其能显露出其人格的价值。有的直言上书,指责朝政,陈述民生疾苦,“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有的虽报国无门,却不甘寂寞,仍为国分忧。辛弃疾面对金人入侵,统治者苟安江南的危殆国势,他“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却依然“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不忘报国之志;有的摆脱功名羁累,退隐田园,保持内心纯洁,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如陶渊明,虽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悲歌沉吟,却仍旧要发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长歌浩叹。不管哪种情况,其共同点在于,他们始终保持了“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不失进取精神和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保持人格的完整和内心世界的纯静。在可能的情况下,既努力在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又时刻保持精神人格的完满自足。
忧患意识的产生是同认同现实、肯定自我的人生信念分不开的,这种人生信念和入世品格又反过来使这种忧患意识得以不断提升和稳固。由于认同现实,便常常把自我关怀与群体关怀联系起来,由悲天悯人的深沉的同情心而内化为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6〕又说:“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困于心, 衡于虑,而后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7〕可以说, “生于忧患”的责任意识是人格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凡“有志于道”的优秀作家,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角色意识。在这种“角色意识”的视野里,社稷安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主题思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他们的一个核心伦理观念。这样,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艺术人格,处处洋溢着以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为重的热情。尽管有的作品也不乏“悲士不遇”和“忧生之嗟”的个体忧患,但就总体而言,以忧国忧民为特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始终是忧患意识的主导思想,构成了艺术人格的精神内核。“‘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8 〕正是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构成了他们作品的基本情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陆游、辛弃疾等作家作品自不必说,即使任性自得、潇洒狂放如阮籍者,也可以从他深刻的内心冲突中看到忧患意识的精神内核。阮籍本是个“有济世志”的魏晋名士,由于社会政治原因不得已才退身自保。他曾登上广武山观看楚汉战场,慨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可见其内心仍怀有远大抱负,有拯世救民的愿望。他在《咏怀诗》中所表达的“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的惆怅忧思之情,只不过是他痛苦矛盾的心理表现罢了。总之,责任感、使命感所展示的忧国忧民的宏大抱负,居安思危的警世意向以及愤世疾俗、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抗争精神,及其高扬主体内心世界,升华人格境界的精神,正是忧患意识的灵魂。
如上所述,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与有志之士的理想愿望往往是矛盾的,并常常成为阻碍他们实现其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的否定性力量;他们长期处在一种被限制、被压抑的精神状态,不断寻求着摆脱痛苦心灵的出路,以实现其精神的超越与升华。于是,回归自然、审美创作就成为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基本方式,作家、艺术家在这里找到了各自的精神家园,并在这里实现了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统一,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统一,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意识实质上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在心灵的解脱方面与道家的自然无为、追求“道”的最高境界有着更多的沟通罢了。我们前面讲到,庄子最高的自由境界是“道”,他以“道”为本,以“道”为至美境界。庄子言“道”,是出于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特别是他对现实社会人的异化和不自由的深刻体验。在庄子看来,现实人生充满苦难,而苦难的表现则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失落与自我的疏离。他认为人的全部身心日益为自己所创造的各种社会化存在所奴役、所规范,追逐名利、丧失人格、媚谄权贵,“莫不以物易其性”、“伤性以身为殉”(《庄子·骈姆》),根本不可能有自由的生命存在。庄子所提出的“心斋”、“坐忘”、“虚静”等自我修养方法,其核心是“忘”。所谓“忘”,一是表达对社会的厌恶,二是为了消解忧愁。庄子企图由此达到复归失落的自然本性,复归与道为一的生命自由境界。可见,在主观精神上实现忘我,忘而得“道”,展现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庄子的理想人生追求,也是庄子美学的本质所在、庄子艺术人格的本质所在,它对古代文艺创作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既然处处充满着苦难,处处充满着“有志不获骋”的悲哀,既然在社会现实中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有志之士就只好自觉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回归自然的审美体验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驰骋理想的高度自由的精神空间,惟有在这种审美体验和精神空间中,方保有心灵完美的精神自足性。有的作家把老庄精神转化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寄意于田园,追求归朴返真的境界,陶渊明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当陶渊明发现仕途生涯有违素志,不利于他对人生真谛的追求和独立人格的展现时,他决然弃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将整个生命存在融汇于大自然之中,去体悟“此中有真意”的生命境界,以实现自己心灵的自由,人格的尊严。可见,陶渊明的辞官归隐,不但是他对于黑暗政治腐败官场的批判和决裂,更是他人格独立的表现。这种人格独立不仅表现在他从最平凡的生存方式中,真正使心灵提升到体悟大道的境界之中,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同时也表现在他从社会罗网政治桎梏中解脱出来回归个人,寻回自己的世界,在没有礼义行次之拘、没有世俗官场杂言之困中,体验着一种任真肆志的人格美。他与志趣相投的友人赏文谈心,与朴实淳厚的农民共话桑麻,与子孙亲戚同享天伦之乐,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自由天地的向往与热爱,表达了他在这种新的生存方式中所获得的内心宁静与愉悦。尼采说过:“一切伟大之物,都是远离市场与声誉才发生的:新价值的发明者居住在远离市场与声誉的地方。”〔9 〕陶渊明正是在“心远地自偏”的地方,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求得了自我精神的提升和安顿。
超越意识更多的是企冀于某种自身内在的精神超越,这种内在超越过程,是在社会现实中从“不堪其忧”到“乐以忘忧”的转化,是在悲怨忧患的现实体验中从精神上暂时解脱出来,在审美活动中以心灵自我清洗的方式消解痛苦和忧烦,求得情感的“释放”和“净化”。古代作家首先是一个现实的人,总不能脱离现实的人生体验。就他们所标榜的理想人格而言,其自我超越也必然是与现实体验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真正的“忘我”、“无我”之境是没有的,而在文学艺术中,可以暂时找到这种境界的存在。这样,审美创造活动便成为他们自存自保、自娱自乐的一块“乐土”,“不堪其忧”的现实体验在创作中遂转化为“乐以忘忧”的审美愉悦。情况往往是这样,对现实痛苦的体验愈深,在艺术中所表现的审美境界就愈高,“操心也危”、“虑患也深”的审美主体形象就愈光采,其艺术人格也就愈加高尚。正如宗白华所说:“生活严肃的人,怀抱着理想,不愿自欺欺人,在人生里面体验到不可解救的矛盾,理想与事实的永久冲突。然而愈矛盾则体验愈深,生命的境界愈丰满浓郁,在生活悲壮的冲突里显露出人生与世界的‘深度’。”〔10〕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虽然深刻体验着现实的痛苦,却能在创作中实现其理想的追求和精神的自足。他们或直抒其志式的慷慨,或悲其不遇式的怨愤,或孤芳自赏式的幽雅,都体现着某种“人生与世界的深度”,表现着某种超越现实的境界状态。如诗人苏轼,虽仕途屡艰,却不改初衷,处处表现出一种达观和自信,“无所往而不乐”。他虽然不断唱着“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千古”,“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出世退隐之曲,但他的内心始终是“走遍人间,依归却归耕”的。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内在的精神超越,却因深刻的现实体验比前人更深刻、更沉重。
3
忧患意识和超越意识所展现的内心世界,不是走向狭小的自我天地,而是在个体与社会的对立统一中,把人提升到心灵宇宙的时空尺度上,让心灵与宇宙融为一体,产生出浩博、伟岸的人格之美。表现生命的伟大,把生命的有限性与精神的永恒性统一起来,这是古代美学艺术人格所展现的基本审美情调。这种审美情调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追求浩然之气的社会美;追求无限和永恒的自然美;追求率性而真的情感美。
在社会力量面前,追求浩然之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11〕孟子认为,这“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才称得上“充实而有光辉”(《孟子·尽心下》),才是最高的道德修养,也是美的最高标准。“浩然之气”作为内在尺度和路标,其终极指向是朝着社会政治历史舞台的,因而浩然、伟健、信心、勇气、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等等,既是自我力量的高度肯定,也是最完美、最伟大的理想人格的基本要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正气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种浩然之气的本质上是超越,它超越的是无法实现的社会价值,成就的是人们心灵世界自我实现的个体价值,是人的崇高的价值追求。陆游《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诗云:“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历代诗余·词话》引陈子龙评文天祥的词时也说:“气冲斗牛,无一毫委靡之色。”这“浩然之气”确实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强大的原动力,注入了光辉的英雄气概,从“虽九死而不悔”的屈原,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李白,到“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的杜甫;从“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他们都坚守着人的使命感、正义感、尊严感,并把这种人格价值凝聚为回肠荡气、浩然伟健的精神力量。对于他们来说,生活遭际、坎坷经历不仅不是人生无意义的根据,而恰恰是自身人生价值和意义存在的根据,是悲壮之美产生的根据。朱光潜曾引西方美学家斯马特的话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12〕在古代封建社会,从许多仁人志士为“治国平天下”,为“一世之否泰”而不顾“一身之休戚”这一面说,他们那种坚毅的抗争精神,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它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伟岸崇高的人格之美,是光照千古的。
在自然力量面前,追求无限和永恒。中国古代美学非常重视对自然造化那种蓬勃生命力的显示。在大自然中,宇宙是无限的,而人的生命是极渺小的。人总希望能主宰宇宙,与天地同大,与日月同光。在古代早期宇宙观中,把天、地、人看作是整个宇宙的三个组成部分,称之为“三才”。天、地、人三位一体,而人在其中占核心的地位,故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强调人与天认同,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实际上是人对自身本质特性的一种自我发现、自我确证。“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都反映了以有限去追求无限和对自身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价值的肯定。于是,宇宙之无穷,天地之广大,山川之壮丽,海洋之浩淼等等,便成为古代作品反复歌咏的对象。这里有几种情况:
一种是歌咏大自然本身的雄奇伟美,作品中流露着创作主体的宽广胸怀和进取之气。李白《蜀道难》中的飞流惊湍,奇峰险壑,天梯石栈,悲鸟古木,呈现着飞动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真是“驰走风云,鞭挞海岳”(陆时雍《诗镜总论》),仿佛可以看到诗人那“落笔摇五岳,笑傲凌沧洲”的人格形象。王之焕笔下的黄河、白日、山峦,景象壮阔,气势雄浑,把诗人高瞻远瞩的胸襟,向上进取的精神表达无遗。而杜甫的《望岳》更是大气包举,“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压卷,屹然作镇”(浦起龙《读杜心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无疑,它将与泰山同垂不朽。
另一种是在阔大的空间感中显示无穷的力量之美。庄子所描绘的鲲鹏,在无穷大的空间中展翅高飞,他借助于超凡的想象力使自己的精神自我伸向无限的时空之中,塑造出一种“博大真人”形象,这形象正是他人格力量的写照。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沈德潜说它“有吞吐宇宙气象”;李白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表面上在写庐山的屏风九叠,黄云万里,但在“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的字里行间,却展示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磅礴胸襟,无限的空间驰骋已融汇为精神自由和豪迈心胸飞驰的场所了。
第三种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寻山问水或沉浸田园之际,作者心神与自然风物契合无间,不仅寄托着缱绻多情,而且寓有与道俱往,与天同在的高蹈自放之意。陶渊明在清新自然的田园中,才真正找到了归朴返真的至上境界;苏轼在无穷无尽的长江之中,方体会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的生命意蕴。江水与明月“逝者如斯”,“盈虚如彼”,“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苏轼《前赤壁赋》)只有融汇于大自然之中,才能找到“无生无死”的境界。这种对人生价值终极关怀的追问,因诗人的旷达心胸而变得如此神圣、永恒和至上,以致超出了现实生命的存在价值。
与上述情况相对应的,则是面对茫茫宇宙、大千世界,发出对生命有限的哀叹和对时间无限的感喟,以及对人生之短暂与宇宙之永恒极其敏感而复杂的觉察与体验。在《古诗十九首》中,固然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哀叹,但同时又有“伤彼兰蕙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的不甘消沉。传为后汉宋子侯所作的《董娇娆》,曾借花开花落道出“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的旷达,因为花是永恒的,不死的。中国古代艺术所表现的大自然的无限永恒之美,不正是深深浸透了这种生命的辩证法吗?
在情感力量面前,追求率性而真。中国古代作品侧重于心灵的抒发,对自然外物的描写从属于主体的情感表现。因而,率性而真的情感力量美,也就构成了古代美学艺术人格美的一个突出特点。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3〕陶渊明说:“傲然自足,抱朴含真。”〔14〕这里讲的“真”,既指自然万物的本真状态,也是自由心灵之真,是真实生命的写照。
本真状态从艺术人格来说,就是情真。创作主体总是以真实的感性生命冲动及其沉淀的理性人格规范去把握现实,并以它作为情感激发的内在动力和情感评价的内在准绳的。创作主体的“心”之“真”是艺术作品“情真”的基础,诗之“真”乃是人之“真”。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15〕童心说强调真情感与“顺其性而作”,它的锋芒所向,一方面指向封建礼教,另一方面指向程朱理学对人性的禁锢和扼杀。从人的感性生存出发,以人的主体的确立和个性自由为目的,高扬人的本性、价值,是当时个性解放思潮在美学领域中的反映。李贽之后,王夫之的尊情达性说,袁枚的性灵说,以及近代龚自珍的诗人面目说,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说,都继承了李贽的美学主张,他们在情感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方面,在作者的内在心灵结构与作品的内在意蕴结构的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即人格意蕴的一致性,并成为中国美学情感力量的主调,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情感之真并不一定就能产生美,只有积淀着深沉的、进步的社会理性的情感,才是诗的情感,美的情感。龚自珍说:“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16〕他正确指出了爱憎是非是产生感慨激奋美感力量的前提。艺术家真实的感情和鲜明的爱憎态度决定着作品的面貌,而审美判断的正确与否,则是艺术作品品格高下的最重要的标志。故然,古代美学认为诗中应排斥纯粹的道德说教,但并不排斥情感中所积淀的道德力量和思想指向性。作品之情实质上是一种被情感所融化了的、渗透了审美理想的“诗情观念”(别林斯基语),这种“诗情观念”蕴含着作家、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体现着他们对生活的审美判断,具有深沉的社会底蕴,而这恰恰是率性而真的艺术人格的灵魂。
古代美学的艺术人格论,其核心思想是立足于人,着眼于社会,强化主体意识,追求人格的完美。艺术人格作为内在尺度,一方面规范作家的创作活动,使作家的个体需求、个人情感与人类需求、社会情感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艺术人格的建构过程,也是创作主体自我确立价值目标的过程,情感自我提升的过程,艺术价值形成和升华的过程。艺术人格说到底是作家、艺术家的一种生存样态。“立文先立品”,这是古代美学艺术人格论对我们的基本启示。
注释:
〔1〕〔7〕《孟子·告子下》。
〔2〕《庄子·消遥游》。
〔3〕《庄子·知北游》。
〔4〕〔6〕《孟子·尽心上》。
〔5〕刘鹗:《老残游记自序》。
〔8〕王国维:《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
〔9〕陈鼓应:《〈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摘译》, 《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书店,1987年,第353页。
〔10〕宗白华:《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1〕《孟子·公孙丑上》。
〔1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13〕《庄子·渔父》。
〔14〕陶渊明:《劝农》。
〔15〕李贽:《焚书》卷三。
〔16〕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五辑《上大学士书》。
标签:儒家论文; 忧患意识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离骚论文; 读书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国学论文; 庄子论文; 孟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