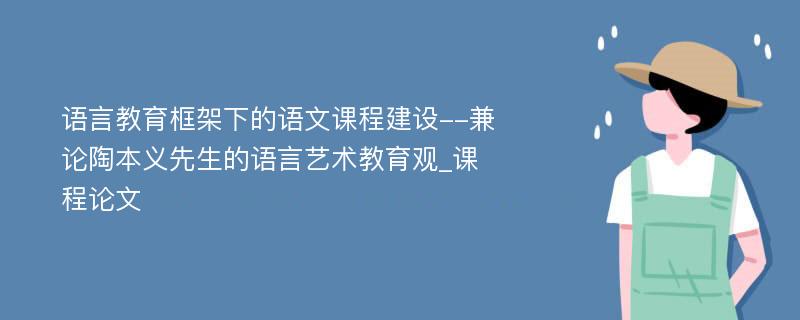
语言教育框架中的语文课程建设——兼评陶本一先生的语言艺术教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框架论文,语文论文,课程建设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陶本一先生的语文致用情怀
陶本一先生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点的学科带头人时,曾亲自给博士生上《学科教学论》。他喜欢组织博士生讨论,话题有时来自报纸上的新闻报道。结果,有位博士生就向他人抱怨:“一个博导上课怎么能读报纸呢?”这个事件深刻地说明了某些研究者自筑学术樊篱,将学术与生活对立的治学观。我想通过这个事件说明两点,第一是陶本一先生博采兼修的治学风格。作为一名学术人,他对我们身边的世界,从自然界到现实社会再到虚拟社会,都抱着无限的好奇,而正是这份好奇心,才让他保持了对教育教学不拘一格、推陈出新的创造热情。第二,作为一名语文教育家,他的授课风格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语文人”的特质:重视阅读习惯的培养、强调学术与生活的互动、注重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等。
20世纪末,语文教育界对八九十年代的语文教改和素质教育运动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陶本一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本问题是语文教学没有按照学科内在的规律来进行”。为此他大声疾呼“让语文教学轻装上阵”。何谓“轻装上阵”?即语文教学“必须紧紧把握住语言这个中心环节”,“必须把现代社会中一个成员所必须掌握的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作为教学的最基本任务来落实”,卸下那些本应由其他学科共同承担的任务,如人格教育、爱国教育、审美教育等。而“最基本的语言能力”,他认为应该是“理解、表达和思考”。
今天,当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走到第九个年头的时候,陶本一先生提出的语文应该为学生需要而教、教学生正确地运用语言、教学生养成得体的“语言行为”,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因为语文课堂教学仍然难以从“应试”的泥淖中拔擢而出,走向“应用”的应然之境。
二、语文学科“实用派”的杰出代表:叶圣陶
语文课程的功能目标是语言教育,提出这样实用的课程观,陶本一先生并不是第一人,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先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其中尤以叶圣陶为杰出代表。
叶圣陶先生早就意识到纷繁芜杂的语文教育目的观背后语文学科特性的模糊。他指出,把其他学科所共同承担的责任都放在语文学科的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语文学科有它特有的任务,那就是“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叶老所指的“国文”,并非指作为学科的国文,而是指“语言文字”。他说,“语言文字本来只是一种工具,日常生活少不了它,学习以及交流各科知识也少不了它”。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叶老是语文学科性质的“工具论”者。如果要概括叶老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那就是八个字:实用为主、文化次之。可以说,叶老的语文教育思想都建立在“语言文字是工具”这样一个本体性认识之上,他以“方法”与“训练”为关键词,在语文课程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创新:
1.语文课程观:课程即训练。
语言文字既然是一种工具,要熟练地运用工具,提高技能,就“必须经过反复的历练”。
2.语文教材观:教材即例子。
既然“课程即训练”,那么,如何训练才更有效呢?当然要讲究训练的技术。叶老注重“举一反三”的“举一”训练,他认为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只有示范性的“一”举得好,教学才会收“反三”之效。因此,他倾心投入语文教材建设,注重语言文字运用技术的开发。
3.语文教学观:方法至上。
在教学方法上,应该少讲,多启发,尽量做到“一语语人”“相机诱导”,变知识灌输为学法指导,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转向主动;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强调语言形式而不是阅读内容,使学生知其所以然,得阅读与写作之“法”,最终达到“不需要教”。
4.教材选文观:以普通文为主。
叶老认为,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应该只占少部分,大部分应该是非文学作品——普通文。叶老的教材选文观对我国20世纪语文教材的编辑要旨、选文内容和编排体例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国文教材一改传统的“经史古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两分局面:一派是文学作品,另一派就是叶老所说的“普通文”。普通文在教材中以“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形式呈现。
三、“实用”之殇:语言教育的障碍与歧路
尽管叶圣陶、张志公等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为致用的学科理想寻求种种技术化的改革途径,例如修订教学大纲、解决教材选文的文学化倾向、改变教学方法等,但是,语文学科的应用功能并没有得到各方的承认,而其“应试”的功能以及由之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却常常为社会各界所诟病。我以为,语文学科“实用化”的理想受挫,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1.应试:自信与他信的丧失。
20世纪80年代,标准化考试传入我国,测评的量化标准把语文学科推到了学校应试的“弱势学科”行列。在应试教育中,语文的弱势地位与其在考试中所占的分值构成了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又进一步挤掉了语文教师培养学生语言艺术的耐心与空间。
在应试的效率和应需的效用上,语文课程丧失了自信和他信。出路在哪里?就考试改革而言,应以多元的评价方式获知学生真实的语言运用能力,比如用表现性评价来弥补结果性评价的不足。表现性评价要求学生完成一个活动或制作一个作品以证明其知识与技能等,即主张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去表现其所知与所能。我想,随着高校自主招生权的扩大、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语文命题技术的提高,应试和应需并轨,语文才能真正成为“致用”的学科。
2.传统:文学化的倾向。
现代语文学科脱胎于传统语文教育。传统语文教育以《文选》为教学内容,强调对选文的研习与模仿。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开我国文选型语文教材之先河,直到今天,文选型教材仍是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中学语文教材的一种主要编撰模式。
前面所述,叶老希望通过教材改革,让学生在读写非文学类文章即“普通文”的训练中,养成语言运用的良好习惯。但是,语文教材因为典范性的选文原则和文学化的选文传统,选的又都是文学化的“散文”,这样就造成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不协调。用文学的内容训练学生非文学的技能,最后必然是两败俱伤:一方面,文学作品不被当作文学作品来教;另一方面,教师又无法通过大量的文学化散文来训练学生实用文的读写技能。这就是语文教学难以走向实用的困局:“内容制约着方法,语文教学按两不靠、两不像的方法在低效中摸索着。”
文学教化的学科价值取向也为许多语文教育工作者所笃信。有学者指出,“如果把语文和写作教育仅仅当作应付生活的实用需要,不仅是贬低了语文和写作教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也为应试教育大开方便之门”。这番话,道出了语文教育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观点:工具论和人文论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工具性、实用性是语文教育的低级追求,文学性、人文性才是语文教育的高级追求。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重温叶圣陶、张志公对语文教育致用所做的努力,我们也很有必要重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语文教育科学化追求中所取得的一些成绩。
3.普通文:有待完善的训练文类。
回顾致用化的语言教育历程,就不得不提“普通文”,因为叶老把“普通文”作为训练“普通公民”读写技能的重要载体。
什么是普通文?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对“普通文”和“实用文”这两个文类进行了说明:普通文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总称,或称“通用文”。实用文为书信条告的总称,或称“特用文”。
此后,语文教材中的选文被分成三大类,分别是文学作品、应用文和普通文。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应用文包含书信、布告、计划、报告、请假条、说明书等各种“特用文”;普通文包括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
语文课程实施的理想模式是文学教学和非文学教学“双轨并行”的模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把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当作“普通文”来处理,并把它与“应用语体”“文艺语体”并列,为后来的“普通文”教学内容在文学语体和实用语体之间的摇摆、“两头够不着”埋下了隐患:
第一,由于对普通文的重视,导致对应用文教学的轻视,应用文的读写陷入单调的格式模仿,在教学功用、效率、意义与价值上受到了非议,并逐渐淡出语文课堂。
第二,普通文的读写训练难以有效地培养学生实用的语言能力。以写作为例,记叙、描写、议论、说明是四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但在生活中,不存在所谓“记叙文”或“说明文”的写作,它们在各类文体中常常是被综合运用的。训练学生的“记叙”的表达技巧,实质上是写作技能的单项操练,类似于舞蹈中的压腿练习。仅有很好的腿脚基本功,到了舞台上,是不能跳芭蕾舞或拉丁舞的。同理,只有“记叙文”“说明文”或“议论文”的基本功训练,学生是无法应付生活中实用文的读写要求的。要让学生真正掌握生活所需的写作技能,就必须“整散结合”,即把单项的表达方式融进具体的语体与文体训练中。
四、语言教育框架中的语文课程建设
语文课程理应凸显为人生、为交际、为生活的实用价值,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语言文字应用技能,满足学生迈入社会生活或进一步升学的需要,为此,语文课程在以下几个方面要有突破:
1.目标建构:注重“训练价值”。
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的语言素养,这是无须争辩的常识。关键是我们究竟要培养学生怎样的语言素养。了解语言素养的基本构成,无疑是语言教育的知识基础。但是,关于语言素养的认识与语言教育的目标,学界多有分歧。在语言素养内涵上,陶本一先生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从11个方面解析“语言素养”的内涵,分别是:语言单位、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语言态度、语言艺术、语言体验、语感训练、语言行为、语言价值、语言教育、思维创造。我个人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借鉴有关知识内涵的理论,将语言素养分成三方面:第一,知道语言“是什么”,即拥有关于语言的事实性知识,如语法知识、修辞学知识等;第二,知道“怎么做”,即掌握语言运用的技能;第三,是关于语言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包括对语言学习的兴趣、情感、习惯以及对语言的认识等。
不管语言素养的培育目标建立在怎样一个逻辑基础上,语文教育研究者都应致力于一个多层级、可操作的语言素养表现标准的探讨。“语言素养”的标准或者内容的制定,应该突出其“训练价值”,即它能使教师“拿来”训练学生有效地阅读、写作与口语交际,提高相应的语言能力,而不仅仅只有“导向价值”。
2.课程设置:突出选择性。
世界各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在课程设置上体现的共同特征是:时代性、多元化、选择性。为了适应课程发展的趋势,我国高中语文课程也有了结构性的变革,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大块,其中选修课程设计了五个系列,每一个系列分工明确,功能清晰,为不同发展方向、不同学习需求与不同语言能力的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语文学习空间。
尽管目前在应试环境下语文选修课的实施存在很多问题,如选修课“被必修”的问题。但要实现语文课程“实用”的“语言教育”目标,就必须走实用与文学分离的路子,必须走选修课的路子,为学生提供功能单一、种类丰富、开放多元的课程菜单和教材菜单,培训胜任选修课的教师。
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伴随着我国语文课程结构的改革,课程实施和教材建设将是推进多元开放的语文课程改革的关键。
3.教材开发:完善学习支持。
要实现语言教育目标,就必须建设配套的实用教材。在中外母语教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母语教材好似“中医”,注重对学生学习态度、情感的培养,强调“养身”。比如记叙文的写作教学,常见于教材的写作知识是“学会积累素材”“学会观察”“学会思考”等。而美国的母语教材更像“西医”,注重可操作的读写技能训练,强调“治病”。以美国加州中学写作教材《作者的选择》为例,编者在每一节都为学生提供了“处方式”的技术支持,包括各式各样的图表、知识清单、知识链接、知识运用示范等,以及贯穿整个单元的某学生写作过程及其文本的追踪分析,在样例分析中丝丝入扣地解释写作各环节的技巧。
美国语文教材中基于程序性知识的“学习支持”为我国教材所缺,但是我国基于事实性和价值性知识的“人文教化”,尤其是强调语文学习要关怀人生、介入社会的训诫类知识,则为美国语文教材所缺。因此,我国语文教材改革也要“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努力实现教材“学材化”,为学习者提供更多关于“如何做”的程序性知识。
当然,课程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教师也是关键。当下,教师专业发展是世界教育发展的热点。要实现语言教育的目的,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语文教师?在这方面,陶本一先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承担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课题“教师教育高地”的子课题——“《中国发达地区基础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的研制”,率领研究团队,在江浙沪中小学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初步研制了《中国发达地区语文教师专业标准》。该成果引起了教育部和相关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我以为,语文教育研究,只有做这样扎扎实实的“工程”,才会有切实的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