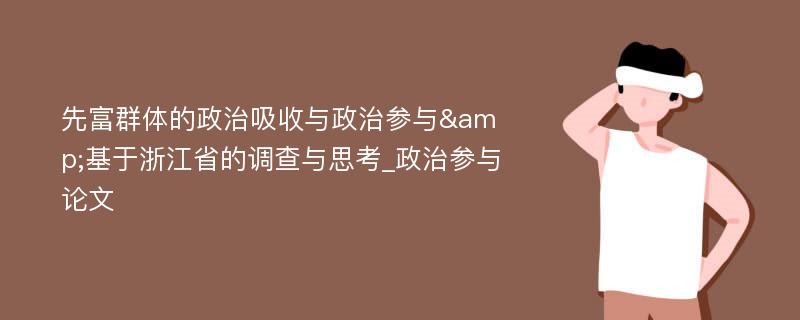
政治吸纳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浙江省论文,先富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1970年代末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拉开了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经过30年的发展,在中国城乡尤其沿海经济相对发达的城乡出现了一大批新的富裕人群,即所谓的“先富群体”。而近些年来,这些先富群体尤其私营企业主对政治参与的热衷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作者2004-2005年在浙江所做的实地调查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一、资料来源与分析框架
本文所分析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三次问卷、多次访谈和相应的地方文献。第一次是对温州女企业主的调查。温州市女企业家协会始建于1995年,是以全市女厂长、女经理为主的群众团体,协会拥有会员124位,来自市本级及9个县(市、区)遍布39个企业,充分体现了广泛性和代表性。2004年2月至4月,笔者通过问卷形式对协会的会员进行了参政情况的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86份,7月份又对部分女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获取了更为直接、真实而生动的资料。第二次是对具有人大代表身份的先富群体所做的一次抽样调查。2004年5月着手准备问卷调查表的设计。2004年7月将问卷送往温州、台州、宁波等进行试填,8月正式确定问卷调查表,并在9月向宁波、金华、温州等地的具有人大代表的先富者发放问卷350份,共回收到有效问卷201份。第三次是对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抽样调查(与第二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调查对象并非全都是先富者)。2005年7~9月在临海市和杭州市余杭区进行,共发放问卷216份,其中有效问卷190份,有效率为88.0%。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一大批劳动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拼搏,合法经营,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并成为一批先富起来的社会人群,这就是所谓的“先富群体”。这一批先富群体主要是指,“私营业主、国有企业负责人、工商户、种养大户等相对富裕的人群,其中私营企业主是先富群体的主体。”①此外,诸如有高收入的大中企业的高层经管人员、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列入其中。但是,主要的是私营企业主。这个先富群体大体上属于中共中央统战部所指认的所谓“新社会阶层”。本文将“政治投资”与“政治吸纳”两个概念作为分析框架并在转型视野下研究浙江省先富群体的参政议政问题。
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最基本的政治过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先富群体尤其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却格外引人注目。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民众来说,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往往涉及到一个社会政治的正义与公共的问题,有对“黑金政治”的担忧因素;二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否接纳和如何安排这些人的政治要求,的确相当重要,因为这涉及到政府权力的重新分配或安排问题。
本文提出用“政治吸纳”与“政治投资”两个概念来解释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现象。前者用来解释先富者自身政治参与之动机,即为何他们现在热衷政治参与以致出现所谓的“富人从政”之政治现象;后者用来解释政府为什么接纳或如何对待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之热情和要求的。
“政治吸纳”概念主要借鉴于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概念,它用来解释香港的治理,“指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把社会中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②“政治吸纳”主要指执政党建立一种能够表达政治意愿的政治结构,让社会上有些群体或阶层可通过这个结构表达出他们的政治意愿,从而使其利益得以实现。
二、主要发现
先富群体主要通过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监督体制(如党纪政纪监督、行政监督和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民意表达体制(如信访制度、调研制度、人民公仆接待日制度、政府办公热线等)等渠道来实现其政治参与。入党也是一种政治参与。对于民营企业主来说,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为他们多开辟了一条参与政治的渠道,即通过政党参与政治。另外,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还包括:通过村委会选举担任村干部;政府给予有实力的企业家一定的职务或政治待遇;通过传媒反映意见;通过与政府领导人保持经常联系来反映问题,等等。
我们对浙江先富群体政治参与所做的研究有下列具有学术和政策意义的发现。
第一,我们的研究表明,相比较而言,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更积极,机会与渠道更多。
拓展政治参与性,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由于缺乏物质条件,实现这一点在中国还为时尚早。只要人们还忙于解决切身的社会问题,忙于解决日常生存问题,政治参与的程度通常都是很低的。所以说,“先要有经济上的保障,然后选举和参与才会成为核心因素。”③总体上,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先富群体的情况则有所不同。正如义乌市人大的一位官员所说,“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义乌人对参与政治并不感兴趣,直到私人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参政诉求才开始强烈起来。通过参政保护私有财产的利益,这是财富拥有者的天性。”④我们的研究表明,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除政府党政官员外,先富群体的比例最高,村级选举中先富者当选的比例越来越高,浙江省约超过50%的村庄的村主任为先富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也大大地高于过去,妇女中先富者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明显高于其它群体。从浙江的经验来看,先富群体在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并且从趋势来看会越来越高。在浙江省第十届人大代表中属于先富群体的为164名,已经占总人数的26.75%;在市一级的人大代表中,除衢州外其它各市的先富群体在人大代表中都占了近三分之一;从所选取的样本可见,在县级人大代表中,先富群体在人大代表中比例呈现不规则性,即有的地方如义乌市先富群体的比例很高,高达62.67%,而有的地方则较低,如常山县仅有7.65%,就平均水平来看,大约在28.5%左右;从统计数据来看,镇级人大代表中先富群体的比例比较低,一般在10%以下。社会经济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人大代表的构成群体。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比较,但是,我们从有关其它学者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得出,先富群体的政治态度更加积极,在我们对当选为人大代表的先富者和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先富者所做的问卷调查中得知,他们对于政治参与的态度更加积极、更为主动。例如,刘春萍在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省台州市L区为例》一文中也提供数据证实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意愿强烈:L区有7%的私营企业主愿意进入人大、政协等政治组织,仅有17%的私营企业主表示不愿意;在回答“是否支持私营企业主参政议政”问题时,有11%的人表示不支持,有22%的人表示无所谓,有67%的人表示支持;又据统计,在L区二届人大20名常委中,私营企业主占3名,196名人大代表中私营企业主代表占29名,其中不包括既办企业又担任村级领导的“两栖”委员。⑤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企业协会发布的2002年、2005年的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的资料也表明了这一点。
这个发现至少某种意义上检验并证实了西方的政治参与诸理论中的“资源拥有论”,即资源如收入、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拥有越多或越高,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越高。正如科恩所说的,“只有丰衣足食的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个公益的公民。”⑥美国社会政治家安东尼·奥罗姆对此也曾经指出:“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些差别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⑦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决定一个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的条件和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和不可分割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水平与其经济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无论入党,当选人大代表,还是参与村委会的竞选,基本上属于自我保护型的政治活动。
入党是一种身份,更是一种政治安全之保证。他们热心政治,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归纳起来无非属于下列这几种:要求政策的稳定、要求加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要求进一步提高其社会地位、要求进一步拓宽与党和政府联系的渠道、要求建立自我保护与协调的机制和组织。说到底,这些要求是属于自我保护的反映,出于利益的保护要求。
张建君、张志学认为,温州的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许多头衔,“这些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当作政治待遇,但更多的是想得到同官员熟悉的机会以获得利益。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很懂得如何为商业利益而参与政治。”他们“通过成为党员、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等达到与官员结识从而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⑧《温州商人的政治观与政治诉求》一文也认为,温州商人“潜心研究政治,不是因为崇拜或害怕,而只是为了某一笔具体的生意”。⑨此话正好印证了奔驰公司的开山鼻祖卡尔·本茨所说的,“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关”。浙江省第一位入党的民营企业主浙江瑞安市长江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建国说,“我的入党动机,无非是搞好企业管理,努力服务社会,更好地带动职工拥护党和政府。我年轻、我有钱、我要求进步,这有什么不好?”⑩这显然与中国目前整个政治框架有关联。董明教授分析了温州市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三种状况,并指出他们的政治参与“主要以维护经济利益为目的”:“政治要求的内容多种多样,但无论其政治参与处于何种层次,政治要求是何内容,大多数都与其切身经济利益紧密相关。私营企业主普遍关心政治,是为了了解有关政策是否稳定和政治动向,以决定自己的经营走向。私营企业主提出的政治要求,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在经营发展中有安全感。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寻求反映他们利益的渠道和保护他们利益的场所。”(11)自我保护要保的就是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或期待,如要求政策的稳定,要求加强对私有企业财产的保护,要求进一步拓宽与党和政府联系的渠道,要求建立自我保护与协调的机制和组织,等等,基本上都属于自我保护的举措,属于自我保护型的政治参与。
第三,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的政治运作,没有形成所谓的“富人政治”,更不是“对抗政治”。
我们的研究表明,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之积极并不意味着浙江的地方政治是“富人政治”,我们并不认同有些学者所说的浙江尤其浙江乡村“富人政治”初露端倪之说,也不意味着走向“对抗政治”。
先富群体参与政治主要是出于一种政治荣誉感和社会责任心。正如秦言先生所言,“不过,也不能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政形式的作用估计过高,因为在很多具有这些身份的人看来,‘代表’、‘委员’等的意义首先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其次是一种社会承认,是社会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肯定和赞同;然后才是政治参与的途径和舞台。”(12)因此,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的政治运作。
我们认为,作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先富者还难以说是一个“先富群体”,只是一个分类意义上的“群体”,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意识,自然也未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他们只是在主观和客观上被逐渐建构起来,某些问题的认识上倾向性非常明显,还不是作为一个阶层的集体意识出现”(13),因此,确切地说是“先富人群”。事实上,从一开始先富群体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并且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他们的政治参与形式呈现出个体性、分散性特点,即便是通过社团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也都是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
当然,说“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其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的政治运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政治运作毫无影响。的确,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一定的影响,相信越来越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政治参与的确扩大了政治市场的“容纳性”,即更多的先富者被纳入到政治领域之中,成为“政治人”。但是,目前他们的政治参与依然没有改变政治结构、政治运作本身。浙江的地方政治并没有出现“富人政治”,更不意味着走向“对抗政治”。美国中国问题专家Bruce J.Dickson教授正确地指出,中国企业主“还远远不是变化的推动者,而是将显示出讨好的政治现状,而不是表达反对”,企业家“更有可能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14)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会长尹明善曾经坦言,对中国大批民营企业人士进入政界,一些不友好的人曾有这样那样的传言和期盼,他们以为,中国的非公人士不会跟党走,不会坚持社会主义,“然而他们的估计错了”。(15)
从以上这些发现,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已经从分配性、动员性的政治参与转变为竞争性、自主性、自我保护性的政治参与。
三、政策建议
当人们还在争论先富人群的参政是善还是恶,是应该鼓励还是抑制时,我们将我们的研究集中于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的现状,例如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渠道与途径,为什么近几年来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积极性高涨,他们为什么要参政,其政治态度与期待又是怎样的这类问题。我们还要追问与探索怎样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先富人群的政治参与得到有效地实现?怎样才能将其政治参与纳入有序的参与轨道上来?
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沟通政治意愿、制约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先富群体尤其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主要目的是,寻求反映其参与政治的渠道,寻求参与公众事务的政治舞台,寻求实现自身政治愿望与价值的载体,寻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政治机制。我们应该认识到把政治参与纳入现有的组织架构之内,使公民政治参与进入秩序化轨道之必要性。正如亨廷顿所言,“没有组织的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16)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目标。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使然。他们对于政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应该“疏”而不是“堵”,正确的态度与做法就是,把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架构,一方面可以促使其政治参与有序化,使其多层次的政治参与需求得到有效释放,另一方面,有利于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体的形成与发展。
那么,如何将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纳入到现有政治体系之中、进入有序状态?总的要求就是开放政治空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强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第一,开发现有政治资源,开放政治空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先富群体尤其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但是目前的政治体制对于先富者政治参与的吸纳渠道与能力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要求。例如,在农村,向农村先富者所开放的政治参与空间依然有限,目前主要的是两个:一类是农村基层干部;另一类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代议性政治角色。在如此政治生态下的浙江农村,先富者特别热衷于竞选村级领导岗位,也就不难理解了。开发现有政治资源,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对现有制度功能的进一步开发与挖掘。具体说来,一是要疏通原有的政治参与渠道。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方面,进一步开发人大的政策决策功能,加强人大的监督力度。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尽可能让先富群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在工商联和人民团体方面,完善其表达机制,使之成为有利于反映、协调、维护和引导先富群体利益诉求的有效组织形式,从而将其各种政治诉求纳入到民主协商的政治框架和制度中来。在已有其它的参与渠道如民间协会方面,尽可能发挥这些协会在表达先富群体政治意愿、政治期待和政治利益诸方面的功能。二是积极探索各种切实可行的民意表达形式,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例如,加强党政部门特别是相关单位与先富群体之间的联系,组织各种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诉求,反映热点、难点问题,供决策参考;建立与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在制定和出台涉及先富群体利益、领域的政策法律之前,征求他们的意见,保证先富群体的利益诉求与意见,能够顺畅地传递到决策中心,准确反映到决策过程。
第二,强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的确,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高涨热情和高期望值与政治制度化建设之间的格局不平衡还是明显的。要实现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关键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构建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机制,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从政治参与制度性环节入手,来实现其政治吸纳之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实现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就是要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进行必要的法律确认和必要的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公民的政治参与经常化、秩序化。这就要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它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开举报法、申诉法等等。
此外,还应注重各阶层政治参与的平等性与公正性,设计相应的制度保证各阶层政治参与渠道与机会的平衡性。在向先富群体敞开参政议政的大门、吸纳先富群体的同时,应该注意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政治参与在各阶层中的公平与公正性。执政党与先富群体之间越来越接近,而与其它阶层的关联似乎愈来愈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事实。例如,近一些年来,先富群体已经成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不少美丽的“政治光环”戴在他们的头上,似乎享有不少政治的“特权”。“统战”成为先富群体参政议政的一个特殊的“通道”。公允地说,党与政府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在建构某些制度让弱势群体能够平等的参与政治。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毕竟是政治系统汲取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政治权利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不能依据某种标准,赋予他们有差别的权利。先富群体尤其私营企业主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有必要为他们提供政治参与的诸种渠道,但是,此问题只能通过完善制度化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的方式加以解决,而不能以对部分群体赋予政治特权的方式来解决。在整个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应当防止贫富差距演变为社会与政治权利的不平等。
无论是开放政治空间,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还是强化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注重政治参与权的平等性,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将吸纳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提升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与高度,并化为具体的各项政策,强化制度建设。
四、评价与理论意涵
1.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实质:政治吸纳与政治投资的双重过程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作者对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作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从分配性、动员性的政治参与到竞争性、自主性、自我保护性的政治参与。而这种政治参与实质上是政治投资与政治吸纳的两重过程。
以往的有关政治参与的理论是否能够解释先富群体政治参与之现象?我们提出用“政治投资”与“政治吸纳”两个概念来解释。对于先富群体来说,他们积极寻找政治参与的机会与渠道,出于一种“政治投资”。对于先富者来说,参与政治是一种投资,一种政治投资。那么为什么要进行政治投资?这是先富群体基于自身社会地位、环境及制度安排所作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它不只反映了先富群体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更是反映出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当代中国先富群体积极参与政治、进行政治投资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玛丽亚·乔纳蒂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连带十分紧密(17),在中国,政治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的获取。某种意义上正如《政治与市场》一书的作者林德布洛姆所说的,“各人不断地努力为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18)先富群体的政治投资旨在获得自我保护之机会与渠道,当然也包括对政策制定与执行之影响。正式的如入党、竞选人大代表、争当政协委员,非正式的如与政府官员建立私交,如此种种构成先富者“接近政治”之图景。
那么,执政党为什么要进行政治吸纳?一是客观使然;二是政治发展面临一些挑战,这其中包括财富对于执政党所带来的挑战。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19)事实上,回顾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有类似的现象:清末新政地方自治的试验为地方绅商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通过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拓宽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广度。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先富群体正产生着巨大影响力。随着财富的积累,这些先富者有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他们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谋求在各政治组织中的职位,追求政治代表性,并传达出自己的声音。他们从政治边缘向政治中心走去。因此,体制外的先富者的政治参与诉求如何在体制内得以有序的释放,就成为执政党不得不面临着的一件大事。
这种吸纳有两种基本功能:一是通过“吸纳”包括先富者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例如吸收先富群体中的优秀者入党,获得先富群体的政治认同;二是其政治参与纳入到有序的轨道,促进了政治体系的整合,避免挑战或麻烦。这种政治吸纳是一种新的政治治理模式。这种吸纳本质上属于一种控制,就是康晓光教授所说的“分类控制”(康晓光认为政府建立分类控制体制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维护既得利益,即防范社会组织挑战自己的政治权威;二是“为我所用”,即尽可能发挥社会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功能(20)),通过政治吸纳达到“控制”,只是控制方式不同而已,对于富裕了的先富者以“政治参与空间”的扩展而实现之。其“控制性”体现于这一情形:限定政治参与的空间、方式与内容,任何超越框架下的政治参与都是不允许也是不太可能的,即纳入可控的有序化的参与轨道,而先富者可以通过有限度的政治参与达到自己政治参与的目的或者愿望。执政党在吸收先富群体政治参与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先富者的政治参与必须在执政党限定的制度规则内进行。
2.理论议题
(1)西方“政治参与”概念的适用性
通过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之实践,我们相信中国的政治参与的方式、目的与实质都有中国之特色、内涵。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可能远远比人们想象中的要积极并且多样化。例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的解释或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说明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先富群体的参与行为。事实上,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史天健教授在其《北京的政治参与》中,就对西方的“政治参与”概念作了拓展,把诸如送礼、公关等在中国极为普遍的半合法化行为也纳入政治参与的范畴,参与不局限于影响政府的行为选择,还包括所有影响政策结果的行为方式。他详细考察了选举、与官员私人接触、通过体制内渠道表示不满、送礼形式的利益交换、罢工或消极怠工、大字报、示威游行等近三十种北京人的政治参与形式。
(2)“有序的政治参与”:中国先富群体政治参与模式
青木昌彦在其《比较制度》一书中曾提出三种国家的模型:自由民主的模型、法团资本主义模式和勾结型的国家模式。(21)那么,当代中国先富群体政治参与模式应该是怎样的呢?根据以上的主要发现与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先富群体政治参与属于自主性与控制性互渗的参与模式,即中共第十六大所提出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先富群体的“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一种自主的政治参与。自主,是指具有独立的参与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政治过程。先富群体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又是一种可控制性的参与,它是在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民主权利的范围内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与监督之下的政治参与。
(3)从政治动员理论到“自主性与控制性互渗的政治参与”理论:政治动员理论的再检讨
“政治动员”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政治学概念。有些学者从广义的角度使用“政治动员”这个概念:“政治动员就是获取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22)大体上说,政治动员就是“发动人们参加政治活动”。当然,“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最常用的术语之一。在中国,政治动员同政治参与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政治参与的组成部分。
显然,“政治动员理论”不能完全有效地解释中国公民至少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自二十世纪50年代,集权模式理论一直主导西方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认知与分析。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在集权模式下,国家和政党完全主宰了社会力量,只有体制导向下的政治动员,政治参与不过是当权者用来构筑其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不具有影响政策的实质性意义。因此,西方学者通常都是以“政治动员理论”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但是,浙江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的实践表明,有必要修正原先西方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政治动员”的参与理论。政治动员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的控制性一面,却不能给出作为个体他们为何积极参与政治的答案,不能解释其自主性。从浙江的先富群体政治参与经验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从分配性、动员性的政治参与转变为竞争性、自主性、自我保护性的政治参与。从先富群体来说,他们的政治投资是属于自主性的政治行为,而对于执政党来说,所采纳的政治吸纳属于控制性的政治策略/战略。
(4)需要进一步观察的两个问题
最后,有必要指出,有关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问题有两个方面需要进一步观察:第一,富有阶层参与及其在政治上影响力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富人政治产生,而党/政府与社会底层关系的日益紧张是否会导致政府与富有阶层的结盟?人们有理由产生这种疑问,因为富人从政实质上就是从经济权(economic power)转向政治权(political power),或者说两者的结合、联盟。因此,先富群体中的某些人士可以步入政坛、政治参与有着更多的“特权”,那么,可能和公权相互勾结,满足自己的利益。这个假设应该说是合理的。“富人政治”的兴起,权力与资本的合流,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第二,尽管其政治参与热情日趋高涨,但是,先富群体是否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如自由选举、多数原则同样热衷呢?因为目前来看,先富群体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功利性参与,而不是理念性参与”(23),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先富群体与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的关联性。
注释:
①郎友兴:《先富群体对社会贫富差距状况的认知:浙江之调查》,《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1期。
②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载《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5页。
③[德]托马斯·海贝勒着/鲁路译:《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以社区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3期。
④牛吃草:《被财富改变的浙江基层选举生态》,《外滩画报》,http://www.sina.com.cn,2002年2月24日。
⑤刘春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浙江省台州市L区为例》,《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44~45页。
⑥卡尔·科恩:《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11页。
⑦安东尼·奥洛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⑧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管理世界》2005年第7期。
⑨王孔瑞:《温州商人的政治观与政治诉求》,《第一财政日报》,转引自《浙江在线》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138665/node257861/node257865/node257874/userobject15ai3708660.html,2007年3月15日。
⑩王孔瑞:《温州商人的政治观与政治诉求》,《第一财政日报》,转引自《浙江在线》,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138665/node257861/node257865/node257874/userobject15ai3708660.html,2007年3月15日。
(11)董明:《关于温州市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调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2)陈冠任、易扬:《中国中产者调查》,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13)何忠洲:《新社会阶层步入政治生活,尚未形成共同意识》,《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12月29日,文章来源于http://news.sina.com.cn/c/2006-12-29/093711914432.shtml,2007年3月11日。
(14)Bruce J.Dickson.Capitalists in China:The Party,Private Entrepreneurs,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23.
(15)张帆、雷霞:《民营企业家步入高级政坛第一人》,《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2月28日。
(16)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1页。
(17)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8)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9页。
(19)塞缪尔·P·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0)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2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22)Amitai Etzioni,"Mobilization as a Macrosociological Concep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1968,p.24.
(23)汪永成、谢志岿:《关于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取向与执政党建设的调查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体制改革》2004年第7期。
标签: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论文;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