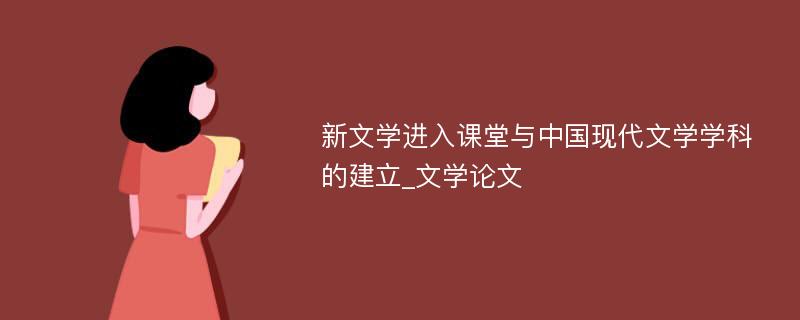
新文学进课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课堂论文,文学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文学作家与新文学课程
以“新文学”为基本特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大学体制,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大学体制内的创新。从1917年胡适进北京大学(当然,他的身份不是作家,但他很快成了著名的诗人),到现代作家约半数以上在各类大学中文系、外文系执教,现代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么,其办学的功能也就相应的有了培养作家的可能。
在何其芳的文学之旅中,沈从文实际上起了很关键的指导和帮助作用。1929年9月—1930年8月,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作家沈从文任中国公学的的文学讲师,何其芳正好这一学年在中国公学读预科。在沈从文的鼓励和指导下,何其芳携小说《摸秋》(笔名“禾止”),登上了以《新月》(1930年3月10日,第3卷第1期)为起步的现代文坛。1930年9月,何其芳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因入学时的高中毕业证书是假的而被退学。1931年9月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33年9月,沈从文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对何其芳关爱有加。何其芳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诗文,得到奖励(1937年5月《画梦录》)和受到赞扬(注:上官碧(沈从文):《何其芳浮雕》,《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39期(1935年2月17日),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204—205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并成为“京派”作家,沈从文自然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朱自清进清华大学是胡适推荐的。1929年春,朱在清华大学开出“新文学研究”。他在1931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35卷第11、12期上发表的《清华大学的中国文学系概况》一文中说,在1928年杨振声主持中文系时,就提出了一个新的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注:《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40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他们所开的新的课程为: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注:《朱自清全集》第8卷405页。)。1931年8月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就十分重视聘请新文学作家任教,以实现他“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的理想。随之,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方令孺就归到他的麾下。因为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就必须先培养新文学的人才。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1913年成立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经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3年)、国立武昌大学(1924年)、武昌中山大学(1927年)多次改名,1928年更名为武汉大学。新文学的势力在这所学校的形成较早。1924—1925年间,新文学作家杨振声、张资平、郁达夫先后在武昌师范大学任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学生新文学社团“艺林社”,并培养了胡云翼、刘大杰、贺扬灵等青年作家。这曾引起后来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沈从文的注意,他在《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特别提到由于新文学作家的授课,“学生文学团体因之而活动”(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98页,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进而产生青年作家。
“现代中国文学”或称“中国新文学”进大学课堂,列入学校的正式课程表,成为中文系同学的必修课,一直是沈从文所关心的问题。1930年下半年曾任教于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沈从文,在1931年由武汉大学印出了他的《新文学讲义》。沈从文之后,1931年秋到校任教的苏雪林继续开“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同时武汉大学又增开“小说入门”和“戏剧入门”两门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48—51页所刊登的“文学院课程指导书”(一)“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影印本)。)。“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在武汉大学立定,与“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此时占据武汉大学有关。《现代评论》主要成员王世杰、李四光、王星拱、周鲠生、陈源、凌叔华、沈从文、杨端六、袁昌英九人在这里任教,加上留学法国归来的新文学作家苏雪林,特别是两位新文学作家闻一多、陈源先后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1928年9月—1930年6月任文学院院长,陈源1930年8月任代理文学院院长,1931年10月被聘为文学院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5年10月续聘为文学院院长)(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13—16页、23页。),使1928——1937年间,武汉大学的文学院,新文化的势力占据领导主权,中国语言文学系则相反。据1935年的《国立武汉大学一览》中的“各学院概况、课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所示,苏雪林承担的三门课程“作文一(刘异、朱世溱、苏雪林合授)”、“中国文学史”、“新文学研究”,有两门与创作实践有关。其一是“作文一”,指导书中说“练习普通应用之抒情、描写、记叙、议论各种文体。或翻译,或笔录,或就教员提出之参考材料作为综合、分析、批评之工作。每次皆当堂交卷以期练习敏捷之思考力”(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28页。)。每周两小时,一年授完的“新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新的内容。指导书中说“本学程讲授五四运动后之国语文学。先叙新文学之运动,及文坛派别等等,用以提挈纲领。继分五编,评论新诗、小品文、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一面令学生研读名人作品,养成新文艺之鉴赏力,随时练习创作,呈教员批改”(注:《国立武汉大学一览》(民国廿四年)第31页。)。文学院的教师中,闻一多、陈源、凌叔华、沈从文、袁昌英、苏雪林都是新文学作家。
文学院中文系的保守势力却是相当大的。1928年之前,中国语言文学系(国文系)有黄侃、胡小石等注重国学的保守势力,新文学作家郁达夫因与黄侃冲突而很快离开。1928年之后黄侃、胡小石到了南京的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权长期在刘颐(博平)、刘永济(弘度)手中。前者为黄侃高足,长文字、声韵、训诂;后者为“学衡派”成员,吴宓的清华同学,长古典文学的词曲、文论,平时会“借题发挥,大骂五四以来的新派”。实际上1931年以后,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新文学作家只有苏雪林,陈源、凌叔华、袁昌英主要是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授课。苏雪林虽开“新文学研究”的课程,但她自知自己“只知写写白话文,国学没有根柢的人”(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面对着“中文系几位老先生由保守而复古”(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3页。),她也逐步转向古典文学研究与新文学批评并重。苏雪林在后来回忆说:“大凡邃于国学者,思想总不免倾向保守。武大中文系几位老先生都可说是保守份子。”(注: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龙泉明、徐正榜编:《走近武大》第52页。)
1937年7月4日,沈从文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第241号发表了致胡适的通信《关于看不懂》。胡适在《编辑后记》中有专门的答复。沈从文主张将新文学传播到中学生,引导学生对中国新文学有一个正面的认识,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中学老师。而中学教师又是大学(国立大学或师范大学)出身。因此,他提出:“在大学课程中,应当有人努力来打破习惯,国文系每星期至少有两小时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作为每个预备作中学教员的朋友必修课。”希望胡适请“所有国立大学(尤其是师范大学)文史学系的负责人注意注意”(注:《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338页。)。
胡适的答复是:“对于从文先生大学应该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提议,我当然同情。从文先生大概还记得我是十年前就请他到一个私立大学去教中国现代文艺的。现代文学不须顾虑大学校不注意,只须顾虑本身有无做大学研究对象的价值。”(注:《胡适全集》第22卷第57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经过杨振声、朱自清的努力,1929年,“中国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多次开讲此课,留下了《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讲义。1940年代,他的研究生王瑶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有意继承这门新课,并于1951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中国新文学”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一个新学科。随后,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都采用“中国新文学”这一学科名称。一门课程逐步发展为一门学科,源头在朱自清。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最为重要发动点在《新青年》,《新青年》及这场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立身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作为一门课程,起源于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发展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及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朱自清、沈从文、苏雪林到王瑶,他们逐步将“中国新文学”发展为一门学科。他们的背后的老师(或伯乐)是胡适。从“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名称的变化,是1950年代讨论历史分期以后的事。
中文系学科改革以新文艺的创作建设为目的
“新文化派”与“学衡派”的对立自然也影响到大学中文系。据何兆武回忆说:“当时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汪辟疆先生,在新生入系时,他就开宗明义地告诫说:‘本系力矫时弊,以古为则。’驯致我们中央大学附中的学生都被教导要做文言文。而入西南联大之后,读一年级国文,系里(系主任是朱自清先生)却规定,作文必须用白话文,不得用文言文。”(注:何兆武:《也谈“清华学派”——〈释古与清华学派〉序》,见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已经是抗战时期的事了。
出身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特别关心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尤其是新文学的地位和融通中西文学的问题。抗战期间及战后,《国文月刊》(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和开明书店联合办前40期,自第41期始由上海开明书店独家经营)是讨论“大学中文系改革”的主要阵地。讨论的起因自然是1938年教育部颁发了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
在新文学作家胡山源看来,大学里的国文系有三个名称:国文系、中国文学系、中国语文系。他倾向于用“中国语文系”(注: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国文月刊》第49期(1946年11月)。)。为响应教育部的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胡山源在1939年12月《中美日报》的“教育随笔”栏上刊发了《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1946年11月重刊《国文月刊》第49期。他认为:(一)任何大学,国文系必须成立,并且必须按照教育部所颁布的科目充实其内容。这样可使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不失。(二)国文系的目的是整理并欣赏旧的文学,同时创造新的文学,这决不是复古。(三)目前的作文应该使得白话和文言一样的看待。要将眼光放在将来全用白话的地步上。(四)有内容地充实国文系,使有天才和兴趣的学生加入。(五)学有专长的国文系毕业生决不会没有出路(注:胡山源:《论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国文月刊》第49期(1946年11月)。)。
程会昌(千帆)在1942年10月的《国文月刊》第16期登出《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是应《国文月刊》的主编余冠英之约作的。真正意义上的讨论是从《国文月刊》第28、29、30合期开始。建设性的意见是杨振声的《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批评性的意见是陶光的《义理、词章、考证》。杨振声认为他编此书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殚精竭力于学习古文,不能为努力创造新中国服务。(二)古文不能表达一个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思想与情感。(三)近代文明国家,没有不是语文一致的。那么,这个参考文选“都是能忠实于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作品”。从此发展开来,“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也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注: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国文月刊》第28、29、30合期(1994年11月)。)。
1945年11月《国文月刊》第39期刊出新文学史家丁易的《论大学国文系》。他的话是有特指的,特别是中央大学的国文系。他说:
现在大学国文系一大部分竟是沉陷在复古的泥坑里,和五十年前所谓大学堂的文科并没有两样,甚至还不及那时踏实。创造建设中国新文艺,他们固然作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对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又几曾摸着边缘,甚至连乾嘉学者那种实事求是的谨严精神都谈不上。只是一批五四时代所抨击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以及一些标榜江西的诗人,学步梦窗的词客,在那些大学教室里高谈古文义法,诗词律式。论起学术来,更是抱残守阙,狂妄荒诞。例如:讲文字摒斥甲骨文金文;说音韵抨击语音实验。甚至述文学发展不及小说,讲文学批评蔑视西欧。而作文必限文言,标点尤须根绝,更是这些大学国文系的普遍现象。……结果最倒霉的自然是学生,恍恍惚惚的在国文系读了四年,到头来只落得做个半通不通的假古董。(注:丁易:《论大学国文系》,《国文月刊》第39期(1945年11月)。)
丁易的改革方案是提倡新文学的创造,并主张现在的国文系应该分为三组:(一)语言文字组;(二)文学组;(三)文学史组。随后,他又在1946年3月《国文月刊》第41期刊出《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进一步发挥了上文的观点。
丁易的文章立即引起新文学同人的响应和进一步的讨论。1946年6月《国文月刊》第43、44合期上李广田的《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王了一(王力)的《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注:此文先刊于3月3日昆明《中央日报》的“星期论文”栏,这里是重刊。)两文在部分观点上认同丁易的,并就具体的问题做了发挥。王了一在《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一文中说,他同意丁易上面引述的对国文系的批评,但不同意丁易所说的文学组的功课着重在文艺的欣赏和批评,创作和实习是本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应占本组课程的二分之一。王了一说自己并不反对新文学,文学的修养是可以在学校里养成的,他文章的要点有两个:第一,大学里只能造成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第二,现代中国所谓新文学也就是欧化文学,所以要从事于新文学创作的人就非精通西洋文学不为功。具体地说:
在西洋,文学只有宗派,没有师承。文学只是主义的兴衰,不是知识的积累。大学应该是知识传授的最高学府,它所传授的应该是科学,或科学性的东西。就广义的科学而言,语言文字学是科学,文学史是科学,校勘是科学,唯有纯文学的创作不是科学。在大学里,我们可以有文学讨论会,集合爱好文学的师生共同讨论,常常请文学家来演讲。我们可以努力造成提倡新文学的空气,但我们无法传授新文学,或在教室里改进中国的文学。
老实说,如果说新文学的人才可以培养的话,适宜于养成这类人才的应该是外国语文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注: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合期(1946年6月)。)
李广田对王了一文章的两个要点提出了商榷,表示只有部分的同意。针对第一点,他说自己赞同大学中文系不以造就作家为目的,这个作家包括有旧文学作家和新文学作家。关键问题在于,大学不但是应该研究传统的旧文学,而“对于大学里的新文学研究与创作的问题,也只当问问应该不应该”。因为目前的许多大学中文系是没有新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指导的。针对第二点,李广田指出了王了一文章的片面,因为新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当然是受西洋文学的影响,但“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影响是能够单独支持一个运动的”。很显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欧化只是一个开始和外因,或是说形式,本质还是中国文化自己的东西。
接着,李广田谈到对丁易文章的看法。他说丁易关于文学组“是以新文艺的创作建设为目的的”,意图是理想化的,因为文学组的新旧文学并重的提法就不容易,旧文学长,而新文学短。文学的通史从旧贯通讲到新的“现代文学”是可以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有“现代文学”这门课,但和旧的相比时间是很短的。他还进一步表示“赞成大学中文系应当有创作实习的课程”,但“不赞成文学组的课程以创作为主,创作的比重不能占二分之一,更不能占二分之一以上,原因是:中文系或文学组的目的,既不在于旧文学之创作,也不在于新文学之创作”。“中文系并不以造就作家为目的”。中文系的目的是大学的教育目的,是批判地接受旧的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创造并发展新的进步的文化。因为中国新文学是新文化的一部分,是从旧文学蜕变新生而出的,同样也是由于世界文学的影响而革新发展的。李广田引述了杨振声的《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的意见后表示,杨振声的话是公平通达的,他论文学是占在整个文化的立场上,是用历史的观点和世界的观点,“他主张在大学里提倡新文学或教授新文学,正是‘勇于承认现代’的精神,而承认现代乃是为了将来,总之,是为了文化的发展”(注:李广田:《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国文月刊》第43、44合期(1946年6月)。)。
王了一针对李广田的意见,在自己重刊的文章后面加了“附记”,表示有的观点他们是“差不多”的,他说:
我并不反对中国文学史一直讲到现代文学;我和李先生一般地不满意那些绝口不谈新文学的文学史家。我不赞成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那是包括新旧文学而言的。对于新文学家,我不赞成在大学里用灌输的方法去“造成”,却还赞成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去“养成”;至于旧式的文学家,连“养成”我也反对。(注:王了一:《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国文月刊》第43、44合期(1946年6月)。)
接下来,傅庚生发表了《中文系教学意见商兑》。他觉得丁易的文章说得太“痛快”了。针对王了一在自己重刊的文章后面加了“附记”,把一般人对于大学中文系意见分为(一)旧派;(二)悲观派;(三)纯文学派;(四)纯研究派;(五)研究与创作并重派;(六)研究与创作分立派六派。他认为自己是赞成研究与创作并重派的。说“并重”也许是“中庸不可能也”,但却是十分“应该”的,是理想,是未来。“在系里开一些新文学研究与试作的课程,应该是绝对需要的”(注:傅庚生:《中文系教学意见商兑》,《国文月刊》第49期(1946年11月)。)。
讨论暂时停了下来。就在这年年底,即1946年12月,由顾廷龙、魏建功、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等新文学作家、学者33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语文学会”。1947年4月9日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陈望道为理事长,章锡琛为总务长,方光焘为研究部主任(注:《中国语文学会之发起与成立》,《国文月刊》第55期(1947年5月)。)。《国文月刊》也相对平静,多是谈论专业的学术文章。
大学里应该而且可以传授新文学并教给人怎样创作
1948年1月《国文月刊》第63期上刊出闻一多的遗稿《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文章提出:“将现行制度下的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文字组)与外国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外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言组、印欧语言组)。”(注:闻一多:《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二系机构刍议》,《国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又见《闻一多全集》第2卷第43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同期还刊出朱自清的《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他们的讨论进一步涉及到“大学里传授新文学”以及“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的基本问题。
朱自清的第一个意见是说自己赞成李广田在《文学与文化——论新文学和大学中文系》一文中的观点,大学里应该而且可以传授新文学,并教给人怎样创作。第二个意见是赞成闻一多的意见,融通中西文学(注:朱自清:《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国文月刊》第63期(1948年1月),又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113—118页。)。
响应朱自清的议案意见,清华大学外语系的教授盛澄华在北平的《周论》上登出《试说大学外国语文系的途径》,他站在外语系的立场上同样看出文化融合的趋势,主张进一步沟通两系。即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并重。他说:“总之,欲再造中国在学术上固有的光荣,对本国文化的认识已成当前急务。这一份丰富的遗产对外语系或文法学院学生固然特别重要,即对理工学生也同样有它不可汨没的价值”。因为“外语系,想对本国文化有所贡献,大致总逃不出这两条路线:(一)站在自己的文化观点上去批判西方文化;(二)藉摄取西方文化的精华来弥补并滋养本国文化所患的虚弱”(注:盛澄华:《试说大学外国语文系的途径》,《周论》第1卷第6期(1948年2月20日)。)。
浦江清在1948年4月16日《周论》第1卷第14期上发表《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一文,他的观点是,语言与文学不能分开,现有的文学院的分系体制已形成固定的格局,也有了自己的所谓“传统”,将中国文学系与外国文学系合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容易的事,干脆在文学院里再新设一个“近代文学系”,从事文学的比较研究。这实际就是后来不同国家和不同语种的所谓“比较文学系”。而原有的中国文学系,他认为可改称“古文学系”(注:浦江清:《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周论》第1卷第14期(1948年4月16日),又见浦汉明编:《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42—24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邱春的《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是对上述教授的文章的补充,他试图调和、超越新旧文学的对立和学界的争论,提出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重要性及价值问题。认为大学国文系的课程的价值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一)社会的道德价值,即使学生养成公民资格并解答中国文化问题;(二)审美娱乐的价值,即使学生养成欣赏优美文学的习惯与特性;(三)实用的职业价值,即培养学生写应用文的能力;(四)形式陶冶的价值,即增进学生的想象力、鉴别力、判断力和思想力(注:邱春:《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周论》第1卷第10期(1948年3月19日)。)。
1948年3月《国文月刊》第65期刊出了“上海公私立大学教授对于中国文学系改革的意见”的专栏讨论文章。这是上海学界对几年来由西南联合大学到复原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里新文学作家、学者们关于中文系学科讨论的一个集体回应。共有陈望道的《两个原则》、徐中玉的《读闻朱二先生文后》、陈子展的《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建议和意见》、朱维之的《中外文合系是必然的趋势》、程俊英的《我对于中国文学系课程改革意见》五篇讨论文章。陈望道提出改进中国文学系课程的两个原则是现代化与科学化(注:陈望道:《两个原则》,《国文月刊》第65期(1948年3月)。)。徐中玉是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他十分了解母校保守的课程设置,尽管没有批评自己的母校,但表扬的却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强调在“沟通融会中西文化的工作”上,北大、清华诸位先生的努力值得重视和赞扬,浙江大学在遵义时期,郭斌主持中文系时也有过此愿望。徐中玉的立足点是如何沟通融会中西文学(注:徐中玉:《读闻朱二先生文后》,《国文月刊》第65期(1948年3月)。)。陈子展1930年代就关注和研究现代新文学,特别注重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他认为“中外文合系”虽不易做到,但将来一定可以做到。“大学里传授新文学”,这个容易。陈子展的主张实际上是超出中文系的课程问题,是更大的对大学教育的意见。他要求放弃一党专政,党团退出学校,活动不挂党旗,也不搞“总理纪念周”,不准学校宣传党义,自动放弃三民主义为必修科(注:陈子展:《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建议和意见》,《国文月刊》第65期(1948年3月)。)。
随之是徐中玉的《国文教学五论》(刊《国文月刊》第66、67两期),和吕叔湘的《关于中外语文的分系和中文系课程的分组》(刊《国文月刊》第67期),是上述讨论的进一步具体化和细致化。一些相关的问题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达。
任何事情在1949年的大转折关头,都有一个了结或变化。这场持续十年的讨论,以邢公畹的《论今天的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为结束语。他说,以南开大学中文系为例,要把中文系建成“为人民服务的中国语文学系”(注:邢公畹:《论今天的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国文月刊》第81期(1949年7月)。)。
事实上,在随后的时光里,中文系的课程中,从中国新文学到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政治的强势话语渗透其间,这门学科由过去那种被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强力排斥的学科,一跃而成为和“文学概论”一样重要的大学中文系里的强势学科。由不被重视到被特别重视,从“为人民服务”到“为政治服务”的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又面临新的不幸。
当然,这并不是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错。
金陵大学的国学研究和国文系(后为中文系,以后扩大为文学院),一直和南京高师一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中文系有形影不离的关系,教师互聘者颇多。程会昌(千帆)在抗战之前曾是《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的编辑部主任,他在1942年10月的《国文月刊》第16期和1943年2月1日的《斯文》半月刊(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办)第3卷第3期上登出《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文章,指出今日大学中文教学中存在着“不知研究与教学之非一事,目的各有所偏,而持研究之法以事教学,一也。不知考据与词章之非一途,性质各有所重,而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二也”。他说考据重实证,词章重领悟。“研究期新异,而教学必须平正通达”。“考据重知,而词章重能”。若将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一起来看,“义理者意,所以贵善;考据者知,所以贵真;词章者情,所以贵美。则为用不同”(注: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1日)。)。程会昌实际上是提出了大学中文系教学、研究总体上应当并重,但落实到具体的教学与研究时,是有不同的取向。同时,他也提出了“从习作旧文体去欣赏旧文体,及从习作旧文体去创造新文体”的主张。而这一点颇似顾实1923年在《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中所主张的“以国故理董国故之办法”。
程会昌本人在大学读书期间是新文学的迷恋者和实际的积极参与者,自己也成了1930年间“土星笔会”与《诗帆》诗人群的成员。但他后来放弃了白话新诗的写作,改写旧体诗词,同时自己也走上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路。程会昌之文在随后遭到了不同意见的批评。1944年11月《国文月刊》第28、29、30期合刊上有陶光的《义理、词章、考证》,1948年4月、5月的《国文月刊》第66、67期连载徐中玉的《国文教学五论》,对程会昌提出批评性的讨论。于是,程会昌在1948年6月《国文月刊》第68期刊发了《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回应文章,承认自己“关于从习作旧文体去欣赏旧文体,及从习作旧文体去创造新文体这个意思”是不合潮流的偏见。尽管这一主张有他自己的文学体会和意图。
1978年以后,程千帆回到昔日“学衡派”的阵地——今日的南京大学设坛讲学,招生授徒。他仍要求自己研究古典文学的弟子“从习作旧文体去欣赏旧文体”,特别是写作旧体诗词。就古典文学研究而言,这可视为进入古典文学文本研究的一条有益路径。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朱自清全集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艺术论文; 胡适论文; 文艺论文; 朱自清论文; 中文系论文; 武汉大学文学院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