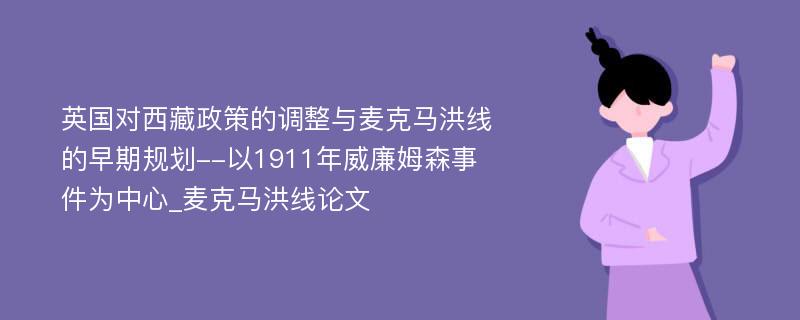
英国对藏政策的调整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以1911年威廉逊事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英国论文,威廉论文,事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中国内地发生了辛亥革命,而在西南边疆,踌躇满志的英印政府调整侵略步骤,以其官员威廉逊之死事件为借口,直接入侵中国西藏阿波尔地区,开展勘察、测量活动,为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出笼做着精心的准备。
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不少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诸如杨公素、①伍昆明、②周伟洲、③吕昭义、④吕一燃、⑤王宏纬、⑥兰姆(Alastair Lamb)、⑦梅赫拉(Parshotam Mehra)、⑧多萝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⑨温迪·帕雷斯(Wendy Palace)⑩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涉及这一问题。但上述学者对威廉逊之死与英国政策转变之关系,以及英国在当地进行大量测绘活动与“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的联系,均涉及不多或者没有深入论述。本文试图利用汉、英文文献资料,对此进行考察,以期有所深入,并请方家指正。
一、背景: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藏后的对藏政策
(一)从“前进”到“不干涉”
1903年至1904年间,英国侵略军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武器残忍屠杀使用大刀长矛的西藏人民,引发了世界舆论对印督寇松(Lord George Curzon)、入侵军首领之一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等人的批评和责问,而这场入侵也引发了以寇松为首的英印政府和伦敦英国政府之间的激烈矛盾。“众大臣认为荣赫鹏的行动损害了国家利益”。(11)寇松的“前进政策”(Forward Policy)因此也受到质疑。
1905年11月18日,寇松结束了他印度总督的任职,(12)明托(Lord Minto)接任总督。12月,保守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以坎贝尔·班纳尔曼(Campbell Bannerman)为首的自由党政府在12月4日上台执政,公开表示“英国对西藏不抱任何野心”。(13)格雷(Grey)担任外交大臣,莫利(John Morley)则成为新一任印度事务大臣。(14)新当选的自由党极力反对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而是对中国西藏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Non-interference Policy),又称为“精明无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15)但是,当清朝的川边大臣赵尔丰等积极经营西藏南部事务时,英国的态度又有了新的变化。
(二)英国插手喜马拉雅部族地区事务
英国对山地部族地区的渗透由来已久。在阿萨姆地区,英印政府承袭阿洪王朝⑧向珞巴族等部落交纳布沙(Posa)(17)地租的做法。当阿萨姆地区经济出现迅猛发展势头时,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开始要求其政府放弃“不干涉政策”,向北扩张。其中不少投机者业已前往珞巴族居住地区盗伐森林,但也遭到珞巴族的强烈反对。英国政府于1873年制定《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The 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 of 1873),提出一条称为“内线”(Inner Line)的边界线,规定:所有英国臣民以及外国居民,在没有通行证或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向北越过“内线”。而“外线”(Outer Line)则是指在“内线”以北几英里的“山脚沿线”(the line of the foot of the hills)。对于“内线”和“外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即中国珞巴族居住区),英国既不收税,也不设立行政机构。印督明托和印度事务大臣莫利均不愿在阿萨姆地区采取积极行动,也不愿向北越过“外线”。(18)
1906年11月,西西锯木厂贸易公司(Sissi Saw Mills and Trading Co.Ltd.)和麦克拉努迪锯木厂(Meckla Nuddee Saw Mills)两家阿萨姆木材公司向阿萨姆政府提出修改有关内线的内线章程(Inner Line Regulations),希望越过内线去砍伐木材。(19)由于珞巴族人对木材公司征收“森林使用费”,而随着木材公司砍伐森林数量的增多,费用自然也相应增加。(20)这些公司为了免交“森林使用费”,便提出将“内线”扩大至“外线”。1907年,兰斯洛特·海尔(Lancelort Hare)担任阿萨姆副省督,同年9月他向印督明托提出几条建议:(1)不准山地边缘部落在内外线之间地区征收“森林使用费”,否则诉诸武力;(2)允许阿萨姆助理政务官威廉逊(N.Williamson)带领150名巡警到内外线之间地区向阿波尔人(Abors)(21)征收人头税和户籍税,并在阿波尔人居住村落巡游;(3)取消英国向部落交布沙的办法,改由威廉逊购置礼物赠给表现良好的部族头人;(4)将山地部族向南迁移,使之“文明化”。(22)
不仅停止交纳“森林使用费”和布沙,反而要征收人头税和户籍税,显现出英国对内外线之间的珞巴族的强取豪夺。印督明托赞同征收人头税,但印度事务大臣莫利担心该计划违反1907年的英俄协议,没有批准该计划,只同意停付“森林使用费”。(23)
二、威廉逊之死:从“不干涉”到“前进”
(一)诺埃尔·威廉逊之死
英国兼并阿萨姆地区之后,英印政府军政官员、欧洲探险家及传教士等多次窜入僜人(24)地区及察隅(25)边境地区活动。后来,英印政府新设萨地亚(Sadiya)政治助理官员以协助处理边境事务,其第一任政治助理官尼达姆(J.F.Needham)继续越过内线,经僜人居住区到缅甸北部活动。
1905年,年轻而野心勃勃的诺埃尔·威廉逊接替退休的尼达姆,担任助理政治官,他坚决反对英印政府执行的不干涉政策,希望通过深入探索山地部族地区而改变局面。(26)1907年12月至1908年1月,威廉逊溯洛希特河(Lohit River)而上,到距离我国西藏察隅35公里的地方进行考察,执行所谓兰斯洛特计划,返回后提交报告建议:英国向米什米方向扩张,在当地建立警岗,将该地区纳入英国统辖范围之内;发展萨地亚与米什米人的贸易,开通向西藏东北的商路。(27)
1908年3月,威廉逊再次越过“外线”,进入珞巴族居住区,抵达帕西加特(Pasighat),后又向西南行至列杜姆(Ledum),再至西永河(Singyong River)对岸的迪季木尔(Dijmur)。此次探险历时一年,1909年2月他因患急性肺炎而返回印度。1909年3月,威廉逊再次来到珞巴族居住的卡邦村(Kebang)。1909年末至1910年初,他穿越米什米人居住区行至察隅;1910年1月,再度来到察隅河谷,抵达瓦弄。
英人在中国边界频繁的活动引起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28)的注意,他令管带程凤翔(29)进占桑昂曲宗,(30)一方面配合北路川军入藏,另一方面设法阻止英国蚕食中国领土。1909年11月29日程凤翔接到命令后,自札宜出发,1910年元旦进入桑昂曲宗,2月11日抵达桑昂。得知英人在察隅活动,赵尔丰即命程凤翔派兵南下察隅。程风翔抵达察隅后,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采取了充实边防、设置界碑等措施,以巩固边防。(31)
得知赵尔丰属部在察隅的经营措施,兰斯洛特·海尔立刻报告印督明托,并建议英国政府,最好的办法是宣布所有米什米人为英国臣民,并逆洛希特河而上,直至占领瓦弄(Walong)的领土。(32)接受这种观点的印督明托在1910年10月建议印度事务部:解决阿萨姆问题的最佳办法是通过“越过外线”向西藏方向推进,从而“获得缓冲区”。(33)但不久他退休,而由参与过制定1907年英俄协议的哈定(Lord Hardinge)继任印督,越线计划被搁置。(34)
威廉逊却不顾上级的反对,“在没有获得任何正式批文的情况下,无所畏惧,一意孤行”。(35)威廉逊的仆人卡多基(Katoki)就在写信给妻子的信中说道:“已经抵达帕吉哈特(Pangighat)。这里的卡邦(Kebang)阿波尔人不允许我们继续前进。威廉逊先生坚持要进入村庄。我想我们可能再也回不来了。”(36)
在1911年1月初,威廉逊和格雷戈森医生(Dr.Gregorson)一行出发。(37)他们沿着洛希特河走,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查证中国人究竟在日马附近做了些什么”。(38)2月4日,他们抵达曼尼克莱(Menilkrai),在此附近,威廉逊发现了赵尔丰派人所立界碑。3月22日,他们抵达卡邦村,越过底杭河(Dihang,又译作底项、迪杭、迪汉、德亨河等),(39)来到阿波尔人居住地西辛(Sissin),在此一些脚夫生病了。威廉逊当即决定由一位米里人(Miri)带着他写给英国驻帕西加特(Pasighat)官员的信,将其中三位病情严重的尼泊尔脚夫送到帕西加特,而格雷戈森医生和其他病人留在西辛,他本人则继续前往空辛村(Komsing)。然而就在此时,威廉逊一行被当地阿波尔人所杀。(40)
对于威廉逊一行被杀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米里人错误地向阿波尔人解释威廉逊所写信件,从而引发阿波尔人的愤怒;(41)另一种说法则是威廉逊因口粮和酒被偷而与阿波尔人产生纷争,最终被杀。(42)无论是何种理由,隐藏在背后的实质,则是长期以来积压在阿波尔人心头的怒火和仇恨:英国人不仅偷盗伐木,甚至取消布沙、停付“森林使用费”,还逼迫他们交纳各种苛捐杂税(人头税和户籍税)。威廉逊被杀事件看似颇具偶然性,实则具有一定必然性。威廉逊之死是中国珞巴族分支阿波尔人对英国长期侵略压迫的强烈反抗,表现了他们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精神。
(二)英国的回应
在英国人眼中,富有悲剧性的威廉逊之死,(43)正成为英国从“不干涉”到“前进”政策转变的最佳借口。(44)英印总督哈定立刻改变政策,同意明托先前的主张,在1911年6月29日致电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建议派遣一支远征队,以便“惩罚”杀死威廉逊等的中国西藏珞巴族人。同时,英国趁机组织几支测绘队,深入门隅、珞瑜和察隅地区测量,为将来侵占中国领土做好前期准备。(45)伦敦的印度事务部很快批准了英印政府的这个建议,克鲁勋爵(Lord Grewe)在1911年7月21日致电英印政府:“我赞成按你们建议的路线对阿波尔人采取惩罚。”(46)
英军的“远征军”兵分三路:阿波尔远征军(Abor Expedition)、米什米使团(Mishmi Mission)和米里使团(Miri Mission)。
1.阿波尔远征军
阿波尔远征军的任务有五个:第一,惩罚阿波尔人。他们获得命令,“阿波尔远征军应在1911年10月出发,抓拿杀害威廉逊的凶手,将其绳之以法;并要好好教训这一地区的部族,让他们永远铭记此事”。(47)第二,尽可能多地拜访底杭河和香河(Dihang-Siang)(48)两岸的阿波尔村庄,让这些部族百姓了解到他们此时处在英国的宽松政治控制下。(49)第三,证明雅鲁藏布江和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同一条河,且与底杭河—香河相连。(50)第四,劝说或驱逐在已承认的“中藏”边界南边的中国人,令其撤到北边。(51)第五,获得划定新边界的信息。(52)在“中藏”边界与不丹到米什米(Mishmi)地区(53)之间的边界上尽快确立一条合理而具战略性的边界线,这应当是英印当局的主要目标。虽然和威廉逊事件没有丝毫关系,此支远征军却沿着迪邦河(Dibang River)与洛希特河(Lohit River)深入到米什米地区,并沿着苏班西里(Subansiri)河深入到米里地区进行调查。(54)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
阿波尔远征军由少将汉密尔顿·鲍威尔(Major-General Hamilton Bower)担任总指挥,拉钦普专员本丁克(Bentinck)和警察部队的邓达斯(W.C.M.Dundas)担任助理政治教官。阿波尔远征军共计1000多名士兵,(55)一路烧杀劫掠。珞巴族人民奋起反抗,用简陋的大刀长矛和毒箭对付侵略者,但最终未能阻挡入侵的英军。
这支英军按原计划在1912年1月开始测量和探查工作。他们沿着迪杭河谷北进,经潘吉、空辛、里乌(Riu)、叶克(Yeke)、西蒙(Simong)等村子,到达了距离“麦克马洪线”30英里的辛金(Singing)附近。(56)
2.米什米使团
米什米使团的任务包括:第一,前往叶普河(Yepak River),“为了以一种准确无误的方式表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边界”,在中国树立的界旗旁边竖起一个堆石界标。(57)第二,尽力探索洛希特河谷以西地区,最终确定通向迪邦河上游的边界。第三,打算修建一条从洛希特河到叶普河的小路。第四,要将现在英国领土上的中国官员“礼貌地”驱逐出去。(58)
米什米使团的行动由萨地亚助理政务官邓达斯负责率领,又分为两支分队。一支分队打算沿着洛希特河向管带程凤翔在叶普河附近插界旗的地方前进,另一支分队,包括贝利(F.M.Bailey)在内,主要任务是探索洛希特与迪杭河至香河之间的迪邦河谷(the basins of Dibang)和西塞里河(Sisseri River)。(59)他们最后了解到,中国在迪杭河上游第一个藏人居住的阿连波(Alenpo)村驻有400名士兵。邓达斯还派人探察了德赖河(Delei River)。德赖河是察隅河的支流,大约距离萨地亚90英里的流程。他们在此遇见了米什米头人马扎农(Mazanon),向他们讲述了“张大老爷”(Chang Ta Lao-yeh)(60)给当地人发放护照的经过。(61)米什米使团及时向英印政府汇报了这一情况,称:“中国官员召集米什米人开会,宣布他们是中国臣民,要服从中国命令。还发给他们每人一张用赵尔丰名义颁发的、有汉藏两种文字表明是中国臣民的身份文书。哈德卡斯特尔上尉(Captain Hardcastle)收集到15份这种护照文书。”(62)
3.米里使团
米里使团的任务是在苏班西里河及其分支进行考察,由科尔伍德(G.C.Kerwood)带领,目的是“同当地部族建立友好关系,调查探索该地区,以获得印度与西藏-中国地区之间进行令人满意划界的信息”。(63)
科尔伍德带领的米里分队来到苏班西里河附近,和阿波尔远征队一样,在1911年至1912年间并没有抵达中国西藏,尽管他们抵达了苏班西里河卡姆拉支流(Kamla tributary)附近的塔里村(village of Tali),而且看到了当地人同西藏人之间颇为活跃的贸易往来(藏盐换取当地的皮革和大米),但米里使团并没能越过塔里村,因为当地村民对英人怀有极大的敌对情绪。他们认为,虽然塔里村充斥着西藏生产的货物,如铜铃、念珠、剑等,但西藏并没有对该地发生直接的政治影响,藏人从未到达如此之南。(64)
据英印档案记载,1912年7月11日夜,当科尔伍德一行在塔里村宿营之时,遭到了珞巴族人的偷袭,一些英军被杀死。由此,直到11月,英军仍然寸步难行。12月,当英军企图再次前进时,又遭遇恶劣天气,不少士兵患病,无法前进,只能撤回印度。(65)
(三)阿波尔远征产生的影响
英国政府和英印政府在1911年9月悍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战争,这是自1903年至1904年英国第二次大规模武装侵藏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66)此次战争由一次偶然事件引起,但却成为英国对藏战略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英印政府和伦敦英国政府之间罕见地达成了意见统一,抓住机会越过所谓“外线”,企图制造一条“新外线”(下文将会详细述及),从而将英国的战略边界线继续向北推移。因此,可以说,威廉逊事件引发的“阿波尔远征”,象征着英国对藏政策由“精明无为”(或曰“不干涉”)政策转向“前进”政策。英印政府的“远征”行动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的“惩罚”实际包含着更大的阴谋,那就是借此远征阿波尔人的机会进行地理测量、策划领土扩张。
然而,阿波尔远征不仅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反对,也遭到英国议会不少议员的谴责。不少英国议员认为,此次远征破坏了1858年法案第55条内容。为了避免尴尬,印度事务部在编写《阿波尔蓝皮书》(Abor Blue Book)的时候,“尽可能消除其国际因素”,尽量不告诉媒体有关阿波尔远征事宜,甚至对米里使团和米什米使团的行动严格保密。(67)
三、威廉逊之死与“麦克马洪线”的策划
从英印政府和伦敦之间的往来公文不难发现,在威廉逊死后,英国打算充分利用这一“偶然事件”,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问题,也即所谓的“新外线”,而这条“新外线”正是“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或“麦克马洪线”的前身。
(一)英印政策强硬:强化英国的影响,为划定“麦克马洪线”埋下伏笔
英印政府和英国政府向来分歧很多,但这次面对威廉逊一行被杀,伦敦对英印政府的强硬政策也表示完全支持。英国学者兰姆对此有如下评价:
英印政府苦苦坚持针对中国在西藏地位问题的立场,拒绝放弃他们认为哪怕是最小的英国利益;然而,一旦谈判地点从印度转到北京,他们的观点就被彻底忽略了。对于明托总督的顾问而言,英国在伦敦的外交部对印度边界安全造成的威胁简直不亚于俄国。英印政府绝不会忘记1905—1906年的教训。当1910—1912年爆发西藏边界危机时,新一轮的英中谈判似乎即将开始,而此时的英印政府勇敢地控制着事态发展,令印度最重要的利益不至于再次遭受伦敦的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的蹂躏。如果英印政府没有这么做,那么1914年的西姆拉条约必然会截然不同,而麦克马洪线或许永远都不可能被划定。(68)
此处所言“勇敢地控制着事态发展”,指的正是在英印政府强硬的政策驱动下,阿波尔远征军打着为威廉逊之死复仇的旗号,“在阿波尔部族地区树立我们的军事权威……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次远征的机会在当地展开大量调查和测量,以便尽可能获得制定中印边界线的必要信息”。(69)
《喜马拉雅三角》(Himalayan Triangle)一书作者也说:
几乎无法避免的是,这些探险队在当地的活动必然要求建立军事岗哨,开辟路线,这就令这些边疆官员不可避免地面对中国的挑战。中国势力紧逼的迫切感令阿萨姆行政长官十分担心……阿波尔远征军和米里使团都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现中国人影响的丝毫踪迹。只有在阿波尔地区最北边发现了西藏影响的征兆。(70)
可见,英国完全是利用此次为威廉逊复仇的机会,将势力渗透扩展到中国珞巴族分支阿波尔人居住区;英军调查中国西藏在这些地区统治的情况,目的正是为了将自己的力量渗透到这些地区。而英国远征军此行的确达到了目的,他们借口远征复仇,实则竭力在当地确立英国的影响,从而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打下基础。
(二)所谓的“老外线”与“新外线”
“外线”是指在“内线”以北几英里的“山脚沿线”。尽管“内线”并不是边界线,但英国人一般将其视为印度领土的有效边界。(71)而英人视为真正的国际边界(international boundary),又称为外线,在某些地区如德让(Darrang)则容易被“内线”所混淆。(72)兰姆认为,外线的划定并非基于阿萨姆人和山地部族之间的民族划分。许多山地部族长期或季节性地迁徙到外线以南生活。外线不过是遵循着山脚沿线的便利地理情况划定,它就像“自山谷而起的一面墙”(like a wall from the valley)。(73)
20世纪初,贝尔针对阿萨姆部族地区提出了建议,认为:“当前,英国应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将其影响扩展到英印与中国之间的山地深处,并尽可能与各个部族缔结条约。如,英国和不丹签订的条约就是一个模板。一旦将部族地区置于英国保护之下,英印政府至少拥有合法权力抵抗中国向该部族地区的渗透,而当前英国并没有这样的权力。即便签订了条约,这些部族地区的安全也还依赖于英国是否保持警惕。”(74)贝尔建议,这些山地部族居住区应至少分成两个边界区,每一地区派出一位英国军官进行特殊监视,并直接隶属于英国中央政府。
在贝尔此番建议下,1910年10月,印度总督明托向印度事务部提出解决阿萨姆问题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向外线扩张而获得一个缓冲区”,即划定一条“新外线”(the New Outer Line)。他认为:
从楔形地带东部的达旺地区之西藏领土部分,沿着英国边界奥达古利(Odalguri)以北,在东北方向处于东经94度北纬29度处,由此向东南方向直至察隅河(Zayul Chu),最东接近日马地区;由此再穿越察隅河至察隅河—伊洛瓦底江分流处,之后沿着分流处直至伊洛瓦底江—萨尔翁江(我国怒江——译者)的分界线。据悉,这一地区的部族是最独立的,而其中一些部族已经置于我们(指英国——译者)的影响之下。(75)
根据1914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可知,以上的边界划分几乎类似于“麦克马洪线”,可以称之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前期策划。兰姆认为:“老内线(the Old Inner Line)仍然标志着英国的行政边界。老外线(the Old Outer Line)则继续象征着英国政治官员在此地游历的有效边界。而最终,新的北部边界(指新外线)则在中国绝不允许外来势力落脚的地方划定了一处无主之地。”(76)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所谓的老内线、老外线、新外线,不过是英印当局玩弄的文字游戏,是为自己划定的一种“灵活变通”的界限,也是为自己渗透、侵略别国领土寻找借口,和“麦克马洪线”一样,中国从未在任何时候承认过这些非法的边界线。
(三)“新外线”约等于“麦克马洪线”
亨利·麦克马洪(Arthur Henty Mcmahon)对阿波尔远征队出发前的考察活动多次耳提面命。他曾告知鲍威尔:
要在印度和西藏之间划定一条恰当的边界;但是,在没有向英印政府汇报的情况下,不得划定任何边界;除非西藏和中国的领土既定边界与上述提到的边界线基本相符合,而遵循如此显著的地理特征对于划定一条令人满意的、清晰明确的战略性边界至关重要。(77)
麦克马洪爵士还补充道:
如果在考察过程中遇到中国官员或军队,应当尽力与之维持友好关系。然而,如果是在中藏既定边界一边的部族领地上遇到中国官员和军队,英方应请其撤离至中藏既定边界内,如果有必要,则可以使用武力迫使其撤离。(78)
而哈定也一再提到:“我们认为这条线(即指新外线)必须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应将阿萨姆已有的‘外线’大力向前推进。”(79)
多萝西·伍德曼认为:“1911—1912年英国在阿萨姆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在不知不觉中扩展了印度帝国的边界。”(80)兰姆坦言:“新边界(指新外线)与其说是英国主权在北部的尽头,不如说它表明了中国主权在南部的极限。”(81)这仅表明一般英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我们无法苟同。根据英印借口威廉逊之死进行报复的阿波尔远征军和其他两支“使团”的考察测量划界的结果可知,“新外线”比起“麦克马洪线”,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82)
根据英属印度总参谋部1912年6月的“东北边疆备忘录”可知,其部分文本取自PEF1910/14,认为达旺是不丹和山地部族之间的“危险的楔形地区”,总参谋部建议将整个达旺地区,包括错那,都划归到英属印度辖区。(83)这远比1914年“麦克马洪线”提出的边界线激进。
兰姆认为:“麦克马洪线是自荣赫鹏使团1904年离开之后开始酝酿发展的,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04—1911年,中国统治了西藏,填补了自荣赫鹏离开拉萨后西藏的权力真空。第二阶段,在1912年早期,中国革命(即辛亥革命)导致中国在拉萨统治的崩溃,又一次制造了权力真空。英印政府竭尽全力利用这个机会,在此过程中获得了麦克马洪线这条边界线。”(84)兰姆对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评价并非事实,但是有关英印政府趁辛亥革命发生后西藏地方的乱局,炮制旨在劫掠中国领土的“麦克马洪线”的分析,却颇为中肯。
综上所述,当1913—1914年英国执行“前进”政策,策动旨在分裂中国的“西姆拉会议”时,麦克马洪与伦钦夏扎在秘密换文中抛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它绝非一蹴而就,而是英印政府对我国珞瑜、察隅地区大量而充分的考察之后,经过英印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哈定、贝尔、麦克马洪等人精心策划、细密准备而提出的。英印政府竭力利用威廉逊之死为借口,采取强硬的“前进”政策,趁中国发生辛亥革命、中央政府无暇顾及之机,派军深入中国山地部族地区,强行测量,设岗驻军,令英印在该地的存在成为既成事实,且强行划定一条非法的“新外线”,用具体的行动为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出笼做好铺垫。
注释:
①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
③周伟洲:《英国、俄国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上下卷),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⑥王宏纬:《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⑦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1904-1914,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London:Hertingfordbury,Roxford Books,1989.
⑧Parshotam Mehra,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Tibet and China,Delhi:Oxford University,1979-1980; Parshotam 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China and Tibet,1904-1947,London:Macmillan,1974.
⑨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London:Barrie and Rockliff,the Cresset Press,1969.
⑩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5.
(11)Peter Fleming,Bayonets to Lhasa,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London:Rupert Hart-Davis,1961,pp.278-279;[英]彼德·费莱明著,向红茄、胡岩译:《刺刀指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68页。
(12)寇松返回英国后,发现自己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1907年,他被选为牛津大学校长(Chancellor of Oxford),1908年被选为爱尔兰贵族代表(representative peer for Ireland)。直到1919至1924年,寇松返回政坛,出任英国政府外交大臣(Foreign Secretary)。1925年3月20日,寇松在伦敦去世,享年66岁。
(13)[英]A·蓝姆著、民通译:《中印边境》,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127页。
(14)Premen Addy,Tibet on the Imperial Chessboard,the Making of British Policy Towards Lhasa,1899-1925,Delhi:Sangam Books,1985,pp.167-168.
(15)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1904-1914,pp.56-67。有关英国的中亚政策,可参考朱新光:《英帝国对中亚外交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系统分析了“精明无为”政策、“前进”政策、“势力均衡”政策和“干涉”政策。
(16)缅甸旧王朝。
(17)又作波萨、布萨等,指山地部落(如珞巴人)向平原地区收税的权利。
(18)Frederic A.Greenhut II,The Tibetan Frontiers Question,from Curzon to the Colombo Conference:An Unresolved Factor in Indo-Sinic Relations,New Delhi:S.Chand & Company Ltd.,1982,p.26.所谓“内线”(Inner Line) 和“外线”(Outer Line),参见 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1904-1914,Volume II:Hardinge,McMahon and the Simla Conferenc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6,pp.312-314。
(19)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1904-1914,Volume II,p.325.
(20)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Gauhati:Assam,1981,p.148.
(21)珞巴族的一个分支。门隅以东为珞瑜地区,英印一般不使用珞巴族这一总称,而只提及珞巴族的分支,他们将从东向西居住在珞瑜地区的珞巴族称为阿卡人(Akas)、达夫拉人(Daphlas)、阿波尔人(Abors)和米里人(Miffs,又作米日人、米瑞人)。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chapter 13.
(22)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pp.148-149.
(23)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pp.149-150.
(24)僜人即国外称呼的米什米人(Mishmi,又作密西米人)。参见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75页。
(25)时称杂瑜。杂瑜在汉文文献有多种写法,赵尔丰在杂瑜设县之后,将其定名为察隅。
(26)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26.
(27)Parshotam Mehra,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China and Tibet,1904-1947,p.91.
(28)赵尔丰(1845—1911),字季和,祖籍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清汉军正蓝旗人,光绪二十九年任四川总督。时叙永厅哥老会挟制官府,赵尔丰捕杀数千人,遂有“赵屠户”之名。三十四年二月庚申,赏赵尔丰尚书衔,为驻藏办事大臣,仍兼边务大臣。参见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82页。
(29)程凤翔,字梧刚,湖南人,原为赵尔丰之厨师,因勇猛善战颇受赵之青睐,任为管带。1910年率军深入察隅地区,及时阻止了英帝对这一地区的侵略。参见任乃强:《任乃强藏学文集》(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
(30)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31)吴丰培编:《赵尔丰川边奏牍》,第494页。
(32)参见Alastair Lamb,The McMahon,Line,Volume II,p.326;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第87页。
(33)威廉逊此行包括:威廉逊、医生格雷戈森、1名武装巡警、苦力管理拉尔·巴哈都尔、卫队若干人、35名尼泊尔脚夫、4名米里人。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4.
(33)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36.
(34)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37-340.
(35)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0.
(36)Amar Kaur Jasbir Singh,Himalayan Triangle,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Sikkim and Bhutan,1765-1950,London:British Library,1988,p.56.
(37)威廉逊此行包括:威廉逊、医生格雷戈森、1名武装巡装、苦力管理拉尔·巴哈都尔、卫队若干人、35名尼泊尔脚夫、4名米里人。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4.
(38)PEF 1910/13,Williamson's Diary,January and February 1911。转引自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1.有关威廉逊此行的目的,Alastair Lamb在The McMahon Line一书中提到:“调查西藏与阿萨姆之间、从日马到萨地亚的路线是他的此行阿波尔的主要目的之一”(p.343);此外,“探究西藏在此地统治的范围,中国是否在该地区取得了任何进展”也是他的目的之一;他“希望各部族将他的出现理解为大英帝国权力的象征,并希望这些部族最终能归于英国保护之下”(p.344)。
(39)中外相关图书中对“Dihang”即雅鲁藏布江下游段的译法分别为:底杭大峡谷(徐近之编著:《青藏自然地理资料》,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底杭峡(《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德亨河([英]F·M·贝利著、春雨译《无护照西藏之行》,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1983年内部编印);底杭峡(《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1983年版);底杭峡(《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大拐弯峡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底杭峡(《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版);雅鲁藏布江峡(《北京青年报·壮士四月要远行》1997年4月2日)。参见武振华:《世界最大峡谷应命名“雅鲁藏布峡”》,《中国测绘》1997年第5期;房建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40)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44-345.
(41)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战地记者安格斯·汉密尔顿(Angus Hamilton)。他在代表作In Abor Jungles,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London,Eveleigh Nash,1912)中持有此观点。对此观点表示赞同的有F·M·贝利(贝利著、春雨译:《无护照西藏之行》第13页)和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44-345)。贝利在其著作中这样提到:“汉密尔顿的书极不寻常,他写此书是签了合同的。但他到现场才知道讨伐队不允许记者相随。因此他不得不用废话充斥其书,以迎合出版商的需要。尽管如此,他对威廉逊和格雷戈森之死的记述要比目前流行的其他解释更加可靠。”(F·M·贝利著、春雨译:《无护照西藏之行》,第219—220页)
(42)这一种说法是巴普雅利根据“阿波尔远征军”助理政治教官本丁克(H.W.Bentinck)给上级的报告所述:威廉逊一行由于一些口粮和酒被阿波尔脚夫偷了,威胁要回去惩罚他们。结果阿波尔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将威廉逊一行干掉(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p.168)。本丁克所撰写的文章《阿波尔远征:地理成果》(发表在《英国地理杂志》1913年2月,43卷,第99页)却持有另一种看法,即威廉逊一行被杀的原因是“由于一个信使的愚蠢和空辛、罗同村年轻人的冲动而促成的”,这与他给上级报告的完全不同,转而赞同战地记者安格斯·汉密尔顿的看法。本丁克持有两种观点的做法令人深思。笔者推测,由于英国官方说法,即“阿波尔远征军”新闻报告人普尔少校(Major Poole)所持有观点是第一种观点,故汉密尔顿以及本丁克等人在公开发表的著作或刊物上都须与英官方保持一致,而本丁克在给上级汇报中(内部资料)则是第二种观点,故第二种观点的可信度或略高一些。
(43)有关威廉逊之死,英国和印度有很多报道,报纸上多赫然写着:The Abor Massacre,the Massacre in Assam,Treacherous Abors,Frontier Tragedy.Indian Officials Murdered.Act of Savages(参见http://trove.nla.gov.au/newspaper)。可知英印舆论在拼命为英国出兵远征阿波尔造势。
(44)温迪·帕雷斯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尽管威廉逊一行遇害事件性质严重,但发生在阿萨姆喜马拉雅的事件仅仅是1911年英国对藏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出现在缅甸边界小村庄皮玛(Pienma)的问题才是影响英国对整个印度态度的关键所在。参见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p.75。
(45)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535号,第14卷,第52页。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第621—631页对此问题有所论述。
(46)英国《外交部档案》,全宗535号,第14卷,第54页。
(47)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p.348.
(48)Siang又译作“西昂”。参见房建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称的由来及历史地理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将其译作“香河”,参见该书下卷第627页。
(49)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3.
(50)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3.
(51)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3.
(52)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p.353.
(53)米什米一词有多种译法。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一书中使用“密西米”译法。[英]阿拉斯太尔·蓝姆著、民通译《中印边境》一书中,译为密闪密人即米什米人(第117页)。伍昆明在《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一书中仍用“米什米人”,参见该书第325页。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也将其称为“米什米”,参见该书下卷第628页。本文采用“米什米”这一译法。
(54)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9.
(55)包括部分廓尔喀兵,第32锡克先锋队,1个孟加拉工兵连,及从纳迦(Naga)、卢赛(Lushai)、拉钦普和达卡撤回的军事警察营等军事力量,几千名纳迦搬运工(Naga porters)。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p.173.
(56)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4。
(57)最终并没有竖起堆石界标。
(58)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13-354.
(59)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53-354.
(60)程凤翔派出的哨长张绍武,当地人将其尊称为张大老爷。吕一燃也提及“赵尔丰的川边军队一汉官Chang Ta Lao-yeh”,参见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下卷),第615页。
(61)据记载,赵尔丰曾批示“外人竖旗之后,因查询居民业已……领有护照,即将旗帜拔去。兹由本大臣随批发下护照千张”。参见《程凤翔禀复洋人插旗拔旗情形》,《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04页。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56-357.
(62)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7.
(63)PEF 1910/13,India to G.C.Kerwood,5 October 1911.转引自 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4。
(64)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55.
(65)L/P&S/11/19,P908/12,Miri Mission; FSE,1912; November,Nos.599-600; Kerwood,Report on Miri Mission.H.K.Barpujari,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North-East Frontier,1873-1962,p.176.
(66)参见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第324页。
(67)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61.
(68)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pp.54-55.
(69)Amar Kaur Jasbir Singh,Himalayan Triangle,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Sikkim and Bhutan,1765-1950,p.56.
(70)Amar Kaur Jasbir Singh,Himalayan Triangle,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Sikkim and Bhutan,1765-1950,pp.56-57.
(71)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13.
(72)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13.
(73)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15.
(74)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35-336.
(75)PEF 1910/13,Minto to Morley,23 October 1910.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36-337.
(76)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9.
(77)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p.145.
(78)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p.145.
(79)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p.146.
(80)Dorothy Woodman,Himalayan Frontiers: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Chinese,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p.146.
(81)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349.
(82)参见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所附地图便可知。
(83)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I,pp.352-353.
(84)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Volume I,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