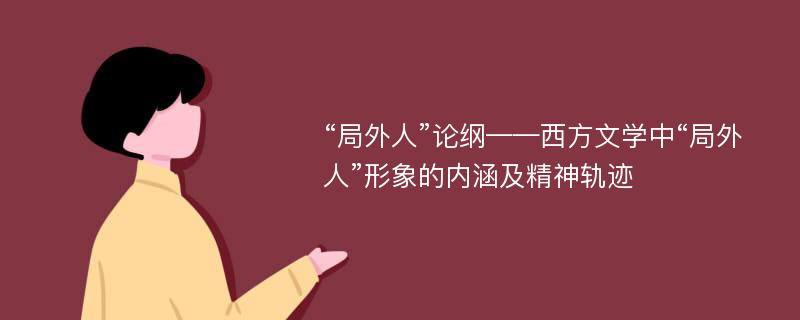
李洋[1]2002年在《“局外人”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照了社会学对“局外人”相关概念的研究和阐述,在文学理论界对“局外人”现象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文学世界“局外人”所具有的特殊性。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局外人”形象是那些无法与他们所生活的现实和谐共存并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人。他的基本精神特征是:倒置的观念,逆反的行动,孤立的境遇和自足的自由。本文根据“局外人”在种种冲突中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把“局外人”划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哈姆莱特型,堂吉诃德型,唐璜型,撒旦型和K型,并结合作品阐述了这五种“局外人”的精神特征。 本文依据不同类型的“局外人”形象在文学史中的影响和变体,对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局外人”形象及其发展与演变的轨迹作了综合考察,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的历史原因、内在精神原因及其特点进行了归纳分析。 本文在对“局外人”的分析基础上,尝试对这种特殊文学形象的审美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对文学“局外人”与社会“局外人”进行了区分。 本文涉及的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家,且历史时间长,人物众多,是一篇纲要式的文章。
张广勋[2]2015年在《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英美乌托邦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文本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对乌托邦城市的想象和书写,力图描绘出乌托邦城市在这一文学文类中形成、兴盛、消解和嬗变的发展历程和乌托邦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及其与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现实城市间的影响与互动关系。这其中乌托邦城市是指一种理想的城市形态,即理想城市,其内容包括乌托邦小说中所想象的城市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物质生活、文化风尚、思想观念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对英美乌托邦文学传统做一纵向、历时性的简略概述,同时采用纵中有横的结构方式,重点是对不同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乌托邦作品中的城市想象进行不同角度的透视分析,而在研究中尽可能以同一时期的西方城市理论为参照。在方法论上,本论文在对小说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文史互证和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由文本分析出发,逐步扩展到对文本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多方阐释,构成一个由文本聚焦到文化意义辐射的综合性整体研究。本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正文五章。绪论部分主要是梳理与乌托邦相关的定义和概念,简述英美乌托邦小说演进过程,同时对西方城市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演进及其特征作出理论背景上的描述。绪论也简要论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现状和意义。在正文历时性的论述中,第一章讨论的是乌托邦文学在其萌芽时期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柏拉图在面对雅典城邦的危机以及对远古失落的美好城邦的追思中,通过《理想国》构想了正义的理想城邦,但也显露出这一“理想城邦”的不正义。在《圣经》中,耶路撒冷的城市形象经历了罪恶之城、毁灭之城、救赎之城和圣城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对现实城市中种种罪恶的抨击,也富含着对理想城市的想象。托马斯·莫尔是乌托邦文学的开创者,《乌托邦》中的理想城市既有英国伦敦的影子,又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的批判和超越。第二章主要以爱德华·贝拉米和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作品为文本,探讨了现代乌托邦小说中的理想城市景观和城市精神文化。贝拉米以回顾的方式对新旧波士顿加以对比,揭示出19世纪末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美国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展现了未来新波士顿城市图景的辉煌壮丽,由此也造就了美国乌托邦文学的第一次繁荣。而作为“世界近代史上最出色的一部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所想象的伦敦则是一个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花园般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城。第叁章讨论现代英美反乌托邦小说中理想城市的失落。伦敦一直是莫尔、莫里斯等乌托邦作家对美好城市想象的寄托,但是在阿道斯·赫胥黎和乔治·奥威尔笔下,这座理想之城呈现为幻灭之城和监禁之城。科技的进步有可能带来物质的丰裕,却也有可能导致对人性压抑与戕害。尤其是当科技与极权意识形态联姻,人将成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在一个安定、富裕和为虚幻幸福所包围的“美丽新世界”中,人类失去自由的选择和独立的思想,丧失了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沦落为权力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此外,美国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也对未来消费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城市异化发出警示。在他所想象的未来的焚书之城中,大众娱乐文化所造就的超现实符号错乱摇曳,带给人们的只是无深度的城市消费文化和精神错乱的狂欢景象,这一恶托邦大都市成为未来美国社会的缩影。第四章论述重点是理想城市形象在当代英美生态乌托邦小说中的嬗变。首先是对生态乌托邦文学这一新出现的乌托邦文学亚文类的概述,然后对相关文本中所想象的生态乌托邦城市和生态恶托邦城市进行解读。欧内斯特?卡伦巴赫所设想的未来旧金山是这一文类中少见的对未来持有乐观基调的生态理想城市,而保罗·奥斯特和奥克塔维娅?巴特勒等作家的生态乌托邦小说则描绘了未来污染、人口激增、气候异常等生态灾难所导致的迁移、饥荒、疾病等众多危机,城市在种种灾难的冲击下日趋衰败,处于崩溃的边缘。他们通过对未来都市恶托邦恐怖图景的想象对当今世界的都市危机发出警示。第五章关注当代伊托邦小说对未来城市和赛博空间的城市特质的想象。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和赛博空间的生成使得伊托邦成为当代乌托邦小说发展轨迹的新现象,对赛博空间的“城市化”想象构成了伊托邦小说的重要主题。这其中,菲利普?迪克想象了未来洛杉矶因核战争和星球移民变为收缩城市,市郊已成空城,只有共鸣箱所创造的虚拟城市空间维持着现实城市的社会互动和意义运作。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和尼尔·斯蒂芬森的《雪崩》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后现代的都市认知地图。未来国家政权的衰退和跨国资本的扩张使得未来都市被无情地分裂为两半。二元城市兴起,门禁森严的社区升级为堡垒单元郊郡,“法外之地”则表现了今日城市衰败、隔离、污染、和贫穷在未来可能造就的最可怕的后果。未来有可能成为理想城市的赛博空间,也可能沦为现实二元城市的镜像。
周颖菁[3]2010年在《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文中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跨越国界的“空间移位者”大规模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对跨越国界的“空间移位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曾冠以“华文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留学生文学”、“旅外文学”、“洋打工文学”、“域外文学”、“留洋文学”等名称。这些名称的重点虽然不同,或强调创作者身份,或强调地域特征,或强调写作语言,但此种观念却是相通的:认为作品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创作的,属于中国本土以外的文学;创作者的身份被界定为域外的华人。这些名称都凸现出中西地域之隔,将中西切割成截然对立的两个空间,写作者被认定是身在异乡的中国客,写作是“写在家国之外”的行为。我认为,这些名称忽略了在全球化语境中更具流动性的现实存在:人们游走于中西之间,在居住国和出生国之间比较自由地流动,国籍和地域对他们不起限制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本文使用了“跨文化写作”概念,目的是想突破空间对研究对象的限制,突出多元文化对写作者的交互影响。本文论述的是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论述的作家包括查建英、严歌苓、刘索拉、陈丹燕、唐颖、张翎、周励、王蕤、朱晓琳、郁秀等。这些作家长期往返在“中国”和“他国”之间,“国界”对她们并不起限制作用。她们的法律身份或不相同,但拥有相同的中国血缘背景,出生国文化是她们看重的。并且,她们也有长期异国生活的体验,对“他者”社会和文化有切实的体验。她们的创作有明显的全球意识和文化对比意识,和单一文化背景下的写作相比,这些作家写作的主题、视角、风格都明显不同。多元文化对本文所论述的作家们的人生态度、价值选择、身份建构、文化观念、文学观念产生着复杂的影响。本文选取“中国”作为“女作家”的定语,主要是强调“中国”这一血缘背景,强调文化母体在空间“移位者”身份认定中起到的作用。中国血缘是作家们在自我身份认同中被强调的,在女作家们的自我身份表述中,她们对自己的中国血缘认同更强于法律身份认同。在她们的作品中,出生国为中国的人物的身份认定也大抵如此。本文所说的“大陆背景”,指作家出生地为中国大陆、成长在中国大陆,作家直接从中国大陆到他国。本文希望揭示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对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产生的影响。本文第一章分析了西方“他者”形象的确立。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必然产生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像。想认清“自我”,“他者”是重要参照系。中国对西方“怎么看”和“看什么”,也表现出中国对自我的想像方式。本文首先归纳了中国历史中的西方“他者”形象,目的是追寻近叁十年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西方形象的发生渊源。在中国历史上,西方形象主要以“套话”的形式出现,是时间性的历史产物。中国视角中的西方形象经历了空白化、离奇化、理想化、二分化、丑化等一系列变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西方被本文所论述的女作家们塑造成了“救世主”的形象。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本文得出了以上结论。本文还分析了此形象产生的原因。西方“救世主”形象的产生,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中国“卡理斯玛”失范的文化精神状况有很大关系。其次,“救世主”形象的产生和以“他人”为镜确认自我、建构意义的现实需求有关,也和异国情调有关。西方“救世主”形象是中国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带有幻想性的神话色彩,表现出文化解读过程中的误读和局限性。把一个“异质体”当成“救世主”,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盘根错节的问题。本文第一章第叁节从空间、跨语言文化交际活动中的对话、叙事这叁个角度出发,分析女作家的作品怎样建构跨越国界后的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从文化地理学中空间的角度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空间对中国血缘的空间移位者来说,没有文化根基,没有家园根基,是流离他乡者伤感情绪、不可知命运的承载物。中国血缘的空间移位者进入真正的西方之后,眼中的西方形象是强势的、冷酷的。强势的西方形象消解了移位者“越界”前对西方世界的幻想。本节还从作品中选取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会话实例进行分析,认为近叁十年来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的作品中的“中西对话”有以下特点:违反“合作原则”、采用回避策略、不对称性、焦虑感,是有效性很低的交际活动,西方人和东方人之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中东西方人的不同态度、立场、情感、策略是东西方关系的表现。从跨文化会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对于东方的压制作用,看出东方面对西方时的弱者心态和表达困境。本节还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从叙事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严歌苓的一些作品中,当叙述者叙述“西方”时,存在视觉盲点和对自身话语权威否定的特点,“西方”是叙述者“看不清”和“说不出”的。从叙事的角度以严歌苓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笔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人对东方人来说,依然以“谜”的形式存在。西方对东方人来说,仍旧是一个空白的图景。并且,西方以其强势对东方人形成了压制,引发自我怀疑和灵魂扭曲。女作家们的创作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能掩盖和解决民族、种族、国家之间的差异和矛盾。相反,近距离的接触,撕破了许多因距离而产生的温情面纱,使真实的差异和矛盾浮出水面。在对西方空白的、强势“他者”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女作家们逐渐抛弃了对西方虚幻性的浪漫情感,沉入到复杂冷酷的现实中去。本文第二章论述在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中国形象。女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是在自我与他者比照的动态关系中进行的。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各不相同,本章对张翎的“古典中国”、虹影等人的“悲剧中国”、刘索拉的“荒诞中国”、陈丹燕“自我东方主义阴影下”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分别论述。笔者选择这几类中国形象进行论述,主要是因为这几类中国形象的塑造角度很不相同。从这几类差异很大的“形象”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文化碰撞时对血缘国差异很大的反观视角和文化反思样式。如果说跨文化背景的女作家对“西方”形象的塑造可以用“空白”字概括,那么她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则表现出了“分裂”的特点:作家们看“中国”的角度不同,所持的态度不同,情感不同,塑造出的中国形象大相径庭。从中国形象的分裂性,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分裂性对中国血缘作家的持续影响,以及相同血缘作家进入异文化后精神世界的不同转向,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从多角度、多侧面揭示了中国国家历史、政治、文化的状况。她们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是对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的反拨,是确认个人血缘身份的途径,体现出第叁世界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自我呈现和发声的意义。本文第叁章分析了女作家作品中的身份问题。本章选取了两个角度考察女作家们作品中的身份问题:边缘人形象塑造和作品中的记忆问题。边缘人是一个“身份”处于“永不完结”的生产中的群体。近叁十年跨文化背景女作家的作品中,有大量这样的“边缘人”形象:如临深渊,但不放弃思索,以个人之渺小承担中西文化碰撞的沉重主题,展现出丰富复杂的思维向度。边缘人现象说明,多质性和流动性使人们面临身份界定的困惑,但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生存和想像空间。此外,在身份寻找过程中,女作家们的写作表现出明显的记忆情结。记忆被作家们用来对抗孤独的异乡处境,也用来质疑和抗衡全球化神话。作家创作中对记忆的聚焦,可以说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寻找精神家园的尝试。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是家国记忆和个人记忆的融合。女作家们在身份认同过程中把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结合在一起,作家们的个人记忆中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因此,女作家们写作表现出了“史诗性”和“抒情性”的结合。两者的结合也使作家们的记忆写作常常体现出悲凉和温馨、壮阔和柔美二元共生的美学内涵。不过,在记忆中,作家们并没有获得身份认同感,反而表现出了对历史的疑虑。女作家们的写作充分表达了对身份确认的需要,她们的写作过程本身也是探寻自我身份的过程。她们身份寻找的非终结性说明了在全球化时代身份是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命题,也是一个处于建构过程中的命题。本文第四章论述了跨文化写作中的女性问题。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基本上都是以女性为主要写作对象的。跨文化背景为女性看待自己、寻找自身主体性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在中西接触的背景下,女作家们对中国女性身份和特质的挖掘新意迭出。其中,她们对中国女性传统精神的重新认识、对现代女性理性精神的发现尤其值得关注。中国女性传统精神和现代理性精神,表面上看,是对立的,矛盾的。但它们又具有本质上的相同性:都是以女性的独立和尊严为基础,强调女性的自主性。女作家们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女性形象建设的一种可能性:把传统坚韧、宽厚、仁慈和现代独立性、理性结合在一起,既有传统意义上女性的“阴柔”,又具有现代女性的思考力。就跨文化背景对女性写作的意义而言,跨文化使女性的写作视域得到拓展和深化,表现出女性对“宏大”叙事的参与能力,也表现出女性对国家、历史、政治、跨文化等重大命题的阐释能力。同时,她们的创作,也表现出女性视角下的“宏大”叙事的独特性。她们的创作表现出性别、种族、国家、民族经验的相关性。本文第五章论述了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跨文化写作中的语言问题。语言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语言是全球化时代非常重要的个文化符号。本章首先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查建英、严歌苓、陈丹燕等人的作品中,中文和英文的关系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同构的。以上作家作品中对汉语地位的表达,和边缘人的生存窘境、文化断裂、身份分裂、认同缺失等主题联系在一起。作家们对西方语境中中文地位的阐释角度各有不同,但有这样一个共同点:中文的使用、英语的不娴熟表现了小说人物面对西方时的“静默”,使用中文者的“静默”是中国血缘的空间移位者采用的无可奈何的回避策略,也是对在西方语境中从属阶层边缘化状态的隐喻。与中文在西方语境中的“静默”处境相对,近叁十年跨文化写作的女作家们有明显的汉语写作意识。本文对女作家们的写作进行了整体上的考察,并做了许多细部分析,发现她们的写作注重对中国语言传统的继承,而不看重语言方面的试验性和先锋性。她们写作语言的“中国”特色,表现出了她们的语言归属意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感归属和文化归属。作家们的写作中还有使用方言的特点。方言延续祖先话语,作家们对方言的使用,使个人的族裔背景更加具体化,更加生动可感。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从本质上看,是“中国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看中国、看西方、看中西方接触等问题的写作。从跨文化角度看,女作家们笔下的中西形象、中西文化呈现出了特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女作家们的写作反映出反本质主义的“分裂性”和“混杂性”。她们的创作执着于意义的寻找,充分体现出了忧患意识和真诚性。
王德刚[4]2018年在《民俗学的当下意义》文中认为民俗学的当下意义——中国当代民俗学者民俗价值观研究。今年恰逢“歌谣运动”100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探讨作为对民俗价值的根本观点和评价标准的“民俗价值观”这样一个本体论命题,既是民俗学科发展的现实诉求,也是对民俗学百年历史的呼应!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下,民俗有什么价值?民俗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民俗学对于文化进步、意识形态建设和社会发展到底有什么作用、应该如何去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既是民俗本体论研究的核心命题,也是民俗学者在学术领域、社会领域角色定位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也必然成为当代民俗学者们在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学科和学术格局不断变化的情况下,经常伏案自问并试图求解的现实问题。同时,在民俗学领域之外,人们对民俗、民俗学的作用和存在价值也心存疑问:民俗学有用吗?甚至一些人会用这种疑问式描述来作为否定民俗学存在价值的意见表达方式。因此,“民俗学的当下意义”的确需要我们在“当下”给出明确的回答。本项研究以“民俗价值观”为主题、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研究对象,选取20位民俗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了 30多万字的能够充分表达个人学术思想的口述资料,采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将口述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经分析、聚类、归纳和综合论证,总结出了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民俗学者”这一价值观共同体的民俗价值观共识。论文分为8部分,包括绪论、第一章民俗价值观概念辨析与理论借鉴、第二章访谈过程与口述资料初步分析、第叁章主题阐释、第四章民俗的价值、第五章民俗学的价值、第六章民俗学科的地位与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第七章总结与展望。通过研究所形成的民俗价值观共识,具体包括几个方面:(1)民俗和民俗学的价值,体现在“人类个体、特定人群、整个人类”叁个维度上,具体表现为:在人类个体日常生活层面,民俗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民俗学具有“解释、服务和提升人的日常生活”的价值;在人类特定群体意识形态层面,民俗具有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的价值,民俗学具有“服务于国家、民族发展和意识形态建构”的价值;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建构层面,民俗具有“完整地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民俗学具有“建构完整的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2)关于民俗学的地位:一方面,民俗学在社会上从来就没有被弱化,一直在服务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社会文化发展、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是在“非民俗学领域”,也一直都在使用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处理各种与民俗和社会文化相关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学理,还是民俗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上看,民俗学都具备上升为一级学科的基本条件。(3)民俗学者社会价值的发挥途径,在现行社会体制下,民俗学者要发挥自身的价值和民俗学的社会价值,要树立命运共同体观念,以价值共创理念为指导,在坚守、保持学者独立性的前提下与政府及其他价值主体合作,共同进行价值创造。同时,要将老一辈民俗学者的团队精神发扬光大,把民俗学的事情办好,把民俗学的价值做大。本项研究在国内民俗学领域,无论是在研究命题、研究过程、还是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都具有一定的实验性、探索性和开创性,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研究内容。“民俗价值观”概念的提出本身在民俗学领域即具有特殊意义;民俗的价值、民俗学的价值、民俗学和民俗学者作用于社会的途径等,以往的学术论着中虽也有涉及,但多是呈碎片化地散见于不同的研究论述中,缺乏系统性研究,本项研究试图对这些民俗本体论的关键性命题展开系统研究,形成民俗价值观共同体的共识。二是研究路径。本项研究采取由个人叙事到集体共识的研究路径,把民俗学者的书斋作为“田野”,采取深度访谈的方法采集民俗学者的个体学术思想信息,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聚类、归纳,由个人叙事过渡到集体叙事,形成民俗价值观共同体的群体共识。叁是资料的鲜活性。通过对20位民俗学者和民俗职业人的深度访谈,获得了 30多万字的口述资料,受访者的年龄从50多岁到92岁,访谈过程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个人和学科发展史的深情回顾,获得的口述资料主题鲜明,语言鲜活,既有理论深度,又注入了受访者的情感。这些资料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关于民俗学发展的口述史资料。“民俗学从来都不寂寞”。访谈过程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教授的观点给笔者以很大的鼓舞。笔者因此也设想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继续沿着这条路径走下去,进一步完善前期研究,争取取得更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成果,为民俗学理论建设尽一点微薄之力。
董小玉[5]2003年在《暮色中的寻找》文中认为一、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选题的背景:两年前,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参加了华东师大人文学院211工程项目《现代化历史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文学卷《沧桑巨变中的形象描述》中第六章“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派”的研究,并撰写了4万多字的文章。为此,我对西方现代主义在新时期小说中的表现产生了兴趣,并确立了以《暮色中的寻找——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研究本课题的意义:其一,较为系统地认识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应和,以期寻找自身发展的现代性,把握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核心即对于生命本体的思索与审美叙事观的变化;其二,通过论述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向“世界小说”的目标前进与发展的现代意义,认识其创作理念、主题走向、文本结构以及在艺术上反传统的特色给文学领域提供的新的观念、新的艺术视野;其叁,通过对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阐述与批判,促进21世纪中国小说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促进人们对建立多元化的小说创作景观与风貌做进一步的思考。 一、本课题的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为:以历史流向的回顾方式,在对新时期以来有代表性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以及作家作品进行解读的基础上,从哲学、文化学、美学、艺术精神的角度,运用中西比较文学批评方法、阐释学派批评方法等,采用理论寻绎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宏观审视与微观剖析相结合、作家论与作品论相结合、思潮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较为系统地论述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引进、借鉴、融合,突破小说原有的审美规范,进行小说文体新实验的发展历程。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导论部分,在“历时”与“共时”交错的话语背景下,追溯与论述西方现代主义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西方现代主义在新时期文坛“复活”的契机;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走向。本论部分,论述新时期中国文坛对西方现代主义借鉴、吸纳、融合,突破原有的审美规范,进行小说文体新实验的发展历程——即从艺术形式、艺术技巧的探索开始起步,反思历史、探索“人”的意义;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寻找与扬弃中,重建民族的“文化”主体,以走向现代世界;关注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揭示社会的贫乏、专横、庸俗、虚伪和窒息的一面,寻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文本的叙述革命,揭示作品对人这一主体的怀疑,在小说中直接描写“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人自身本质的复杂性;对城市化、世俗化生活的窥望与期冀,对其作品中多元化的欲望进行透视,揭示当今社会中人的现代主义的虚无与后现代式的焦虑,指出其书写的局限与精神提升;论析女性作家“个人化”躯体写作的意义、特色以及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的精神困境。通过对小说中人的生命本体与审美观念嬗变的追问,梳理出中国新时期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轨迹。
刘菲[6]2013年在《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研究》文中指出“零余者”又称“多余人”或“多余的人”,是中外文学史上比较经典的文学群像之一。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描写知识分子“零余者”形象的先河。从此,以“零余者”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品不断涌现,而走进文学,与“零余者”形象对话,也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趋向。新时期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不仅包括孤独、苦闷、漂泊、沉沦、无所适从的边缘“文化人”,也涵盖了那些无根徘徊、饱经风霜、游走于城乡之间的民工“候鸟”。他们从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走来,背负着不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本文的研究从这两个角度展开,立足文本,走进历史,对知识分子“零余者”和民工“零余者”进行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双向剖析,重点从精神文化认同危机的视角探究这两类人物形象呈现“零余”感受的不同表现和原因。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叁章、结语。绪论主要分为叁个部分:一、主要对论文的选题和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本文的研究视点;二、以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为切入点,分析其文学渊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探寻“零余者”的生存苦闷和绝望感,进而将中国小说中的“零余者”与外国文学中的“零余者”进行比较;叁、在明确“知识分子”定义的基础上,通过对现代文学史上“零余者”形象的流变研究,结合中国时代文化变迁,得出中国新时期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研究的必要性,并对新时期小说中“零余者”形象进行文学界定,分为知识分子“零余者”系列和民工“零余者”系列。第一章将新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零余者”形象分为四个互不相同的系列,分节阐释,重点分析人物形象特点:精神价值迷失的“无主题变奏者”,如《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中的主人公;生活于文化夹缝中的痛苦“畸零人”,如《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挣扎在河与岸之间的孤独“零余者”,如《河岸》中的库东亮和库文轩;欲望中深陷的“沉沦者”,如《废都》里的庄之蝶、《桃李》中的邵景文、《风雅颂》中的杨科等。这些人尽管形象各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零余”体验,面临着认同危机的尴尬,成为无所归属、漂泊于世的“波希米亚人”。第二章重点分析民工“零余者”形象,本章分为两大节。第一节结合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城乡变化,城市与乡村呈现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描写农民工题材的作品相继出现,并分析民工“零余者”奔向城市的原因,一是民工的“向城求生”之梦,二是乡村文化的凋敝和城市文化的吸引。第二节从小说《高兴》、《别人的城市》、《瓦城上空的麦田》、《接吻长安街》、《送你一束红花草》、《异乡》、《北京候鸟》、《民工》等作品入手,通过民工“零余者”形象的生活境况、精神世界,重点分析他们的身份认同危机,并阐释该类形象的苦难性审美。第叁章用总述和分述相结合的方法,从自我认同危机的角度阐释“零余者”形象的本质特点和苦闷、漂泊的根源。本章分为两大节。第一节,文化冲突与自我认同危机,从文化的视角展开论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前两个视角主要对应知识分子“零余者”,后两个视角主要对应民工“零余者”。第二节,分析“他者”目光也是造成自我认同危机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结语映照现实,结合新时期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精神特征,思考形象启示。
王晓文[7]2006年在《二十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论纲》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意在考察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表现形态及其流变。市民文学是市民社会思想观念和情感方式即市民文化的文学性表现。市民文化,是体现着市民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特征的文化。由于中国社会封建宗法文化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城市文化笼罩在农村文化、宗法文化的阴影之中。20世纪中国的市民及市民文化在封建文化、农民本位文化与西方文化、殖民文化两者的挤压中的生存状态比较柔弱。在这种情形下,以市民为接受主体和表现对象的市民小说,屡屡遭受主流意识形态不屑一顾的命运。然而,如果我们从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来看中国市民文化的变迁,就会看到它与中国现代化同步演进和价值观念不断重构的过程。20世纪的中国现代城市毕竟渐趋繁荣,市民文化几经沉浮终归日益勃兴;与此相应的是与城市、市民和市民文化有千丝万缕关联的市民小说,同样在历史的夹缝中艰难发展。本文试图从20世纪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发展状况对市民文学的形态演进的影响及二者的关系角度出发,理清20世纪市民小说流变的线索。通过对20世纪的具有代表性的市民小说流派、作家和文本的研究,力图回溯上一个世纪中国市民文化和文学蜕变发展的具体情状,揭示中国市民文化、市民文学不断地摆脱农耕文化、宗法文化的阴影,走向城市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历程。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对与20世纪市民小说有关的几个概念加以界定。通过对“市民”、“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民文学”等概念的历史演变的考察,本文将20世纪的中国市民小说界定为一种反映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小说,以广大市民为接受主体的小说。文章还涉及到它与都市小说与通俗小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通俗文学中的市民小说与新文学中的市民小说之间的关系。 本章通过对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历史流变进行宏观考察后发现,20年代末,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后,市民小说开始体现出新的特质,张资平、老舍、张恨水等作家分别创作了各自市民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品,标志着市民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以老舍小说为代表的着重表现传统市民文化的市民小说和以张爱玲为代表的着重表现现代市民文化的市民小说是20世纪中国市民小说的两种基本形
常娟[8]2011年在《恶的书写:现代小说叙事的伦理境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恶的命题是伦理学思考的基本和核心论题,而文学和伦理学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的精神实践方式虽然相互独立却也彼此联系,两者的联系的表现之一就是文学活动在完成审美功能的同时会生成价值判断。文本中诸如人物、主题、题材、结构、艺术手段等以及作者的写作动机、写作态度,读者阅读的审美效果等等都可能与价值判断相关。就小说而言,传统小说中关于善恶的价值判断较为明晰和简洁,文学借助审美方式达到道德熏染的效用和目的也相对明显。这种状况到了现代小说发生了变化,与传统小说相比,对恶的题材的重视甚至迷恋是现代小说创作的重要特征,暴力、血腥、伤害、死亡、痛苦、恐惧等等充斥于文本中成为重要的叙事内容。如果说传统小说虽然在题材上有着恶的因素的存在,但是恶基本上处于被善统领和支配的地位,恶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表现和衬托善,但在现代小说中,恶摆脱了作为善的附庸地位,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审丑大行其道。与此同时,在叙事立场上,小说写作传统的鲜明伦理价值观被有意识地逐渐淡化,叙述人在面对善恶的价值判断时策略性的将自我包裹起来,采取所谓的非道德立场,这进一步将恶的书写复杂化。论文共分四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主要是对恶的概念的厘定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善恶的辩证法。本文认为,恶是以否定性和消极性为基本特征和核心性质的价值判断,在一般意义上,恶是由于需要和欲望的不能满足的价值属性,在狭义上指的是道德的恶,它是人们对社会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的违犯。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善形成的辩证法表现在叁个方面:一是恶有时会是善的实现的手段,是必要的恶;二是善恶的存在是相互依存的,恶会激发善的向往和追求;叁是善恶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在时空维度上是动态和相对的。第二章是将文学活动与伦理活动联系起来,考察二者之间的复杂纠葛关系,以建立分析现代小说恶的书写问题的理论背景和前提。论文从历时和共时的双重视角梳理并阐释了文学的审美特征和道德的价值判断属性之间的既相互交融影响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关系状态。本文认为文学的情感功能追求呈现人的个体生存状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道德伦理则是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提出普遍性、规范化的要求。文学的伦理特征往往会突破理性道德规约的僵硬规定,借助审美情感的丰富体验使得伦理规范表现出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同情和反思。从文学的本质上来说,文学应当始终具有道德在场的姿态——不论它是显在的抑或是隐蔽的,它与文学的道德超越性构成富有张力的矛盾统一。第叁章主要研究恶作为现代小说的书写对象的根源、表现及其特征。本文从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和文学史背景来分析恶的主题在现代小说中凸显的根源,说明现代小说对恶的主题的重视是具有必然性的。从叙事形态上看,小说的伦理叙事模式经历了从民间故事型的人物因品行而善恶报应到经典故事型的人物性格善恶交织,直到发展至现代小说阶段,不再仅仅以人性的善恶为伦理叙事的全部,而是表现为恶的多元化叙事,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多个维度上展开,反思和批判包括人性恶、制度恶、技术理性之恶以及物之恶的种种状况。在审美特征上,现代社会的邪恶和残酷引发了人的情感的抑郁,把人推到了悲观绝望的境地,文学将关于现实世界的体验进一步虚构和夸大,借助艺术世界的想象折射出来,现代小说将艺术的表现对象推到极端化的境地,形成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在叙事态度上却趋向于客观化,采用冷漠化叙事的手段,以和恶的叙事主题在强烈的反差中引发审美震惊。第四章主要在美学层面来讨论现代小说对社会的批判意识和功能。现代小说以恶作为文学的重要表现对象,并不能代表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就沉湎于恶而无力自拔。现代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与传统小说的断裂,这种反叛性成为实现对社会的否定认识和批判的有效手段,本文主要以阿多诺的审美自律性理论为基础分析现代小说如何在审美自律性中实现社会的批判功能。本文认为艺术自身对美的鄙弃,导致了艺术走向了反面,而这种艺术反动的重要目的就是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实现对现代社会之恶的抗衡。
王强[9]2012年在《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文中认为在视觉文化转向的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生动实践,为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关于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整合性、系统性的考察和研究,尚有待于深入开展。本文将通过以下四个论题深入推进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研究:首先,中国古典诗画传统的现代传承研究。在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研究中,仍需回溯和检视中国古典诗画融合的传统。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中潜藏着诗画传统变异性传承的隐蔽线索。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因此,诗画传统其实可以被视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伴随着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诗和中国画都踏上了植入现代性的进程。中国诗和中国画的总体发展趋向都是致力于表现现代人特有的“情感结构”,二者再度朝着精神(意境)契合的方向迈进。诗歌和绘画的合作关系由到显明变得潜隐,形式上的直接结合(题画)已经趋于衰落。在现代,诗人和画家合力“发明”诗画传统,通过诗画并置创造一种现代诗画艺术。这种诗画艺术成为诗画传统现代传承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意象创设和情感表达诸方面,中国新诗与绘画彼此交流汇通,通过取法和借镜对方来塑造自身的风貌,“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的艺术传统得以延续。此外,关于汉字形象与中国新诗视觉造型的议题同样涉及“传统的发明”,本文也将加以关注。其次,视觉媒介的变革与中国新诗视觉传播形态的研究。新型视觉媒介层出不穷,新诗视觉传播的形态经历了数度变迁。从静态到动态,从实景到虚拟,从单向到交互,日新月异的视觉媒介技术为诗人和艺术家打开了自由创造的天地。新诗艺术与众多类型的视觉媒介进行互动,呈现出丰富驳杂的融合方式,创造出摄影诗歌、诗歌电视(PTV)、超媒体诗歌等诸多崭新的综合艺术样式,成为“影像诗学”建构和探索的重要表现形式。通过深入解析这些综合艺术的生成机制和内在理路,可以探寻出中国新诗与新型视觉媒介的合作和交锋的复杂互动。此外,这些综合艺术的“诗意图式”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因此,它们也可以视为诗画传统的一种变异性传承。再次,地理空间的诗性建构与影像书写,以及诗意景观的塑造研究。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都将地理空间纳入自身观照的视镜,使得地理空间成为诗歌与视觉媒介所表现素材的重要交集。经过诗性建构的地理景观则是诗歌艺术与视觉媒介共同书写的对象。透过“诗性地理”这一表现对象,可以探究摄影、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介表现和处理抒情题材的修辞方式以及现实困境,从而为抒情文体尤其是新诗的视觉传播提供启示。考察新诗与视觉文化关联的另一维度是诗意景观的塑造与凝视。伴随着经典性的生成和知名度的提升,中国新诗对众多景观进行着诗意建构和颠覆性重塑。在观光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诗意景观在诗歌视觉传播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对景观的诗意建构和重塑其实构成了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的一个隐性渠道。最后,关于现代诗人形象塑造与想象的研究。当下,现代诗人正逐步将自身视觉形象的展示纳入新诗传播的策略当中,大众传媒将诗人形象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加以征用,而一些影视剧则参与到诗人形象的演绎和虚构当中。诗人形象的塑造与想象,直接关系到诗歌生态的建设和诗歌受众的培养,因此,对诗人形象的考察是中国新诗视觉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与诗界正面形塑自身形象的取向大相径庭,基于各自考量的大众传媒刻画出面目斑驳的诗人形象,使之变为“被污染的塑像”。而虚构的影视剧则强化和放大了媒体和公众对诗人的刻板印象,使之成为影视人物画廊中的一个“俗套”。总体而言,诗人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真相与虚构共生、交锋与合谋并存的复杂的文化编码过程。
赵秀兰[10]2014年在《司岗里:佤族的生态和谐审美理想》文中研究指明“司岗里”是盛行于中缅佤族当中的神话传说、史诗,文章以之为核心对象,立足于田野和文本,以生态和谐等理论为指导,力求厘清“司岗里”艺术的根脉、谱系,挖掘其承载的人类生存愿望和审美理想。根据地方性知识的解说,“司岗里”意为“万物或人从石洞和葫芦出来”,“司岗”即“石洞”、“葫芦”,“里”即“出来”。通过同源词研究,“司岗里”应该还包含居所、祖先、祖先居所、图腾、家园等意。由于穴居和生殖崇拜的复杂原因,“图腾”之意逐渐模糊,“祖先居所”在宗教信仰机制下和神话传说语境中逐渐转义或引申为石洞和葫芦,然后又隐喻生存家园和大地,并具有双重家园的象征意义。“司岗里”各层次语义之间的逻辑关系,大致对应于“司岗里”的艺术化规律,即从生存方式经宗教化而走向艺术化的规律。此艺术化的过程又是整生化的过程,即神话传说“司岗里”整生了原始生存哲学、宗教观念、艺术观念等。神话传说“司岗里”由特定的自然生境和文化生境所共生,文化生境包括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承人等侧面。在分形机制下,“司岗里”派生或形成了不同的文本形态,按照生态谱系大致可分为原生态文本、再生态文本、衍生态文本、仿生态文本,文本生态是佤族传统核心审美价值观和理想的重要传承体制。口头艺术“司岗里”蕴含着佤族先民关于宇宙起源、万物同源、各族同宗、天人合一等生态和谐的生存审美理想,这正好构成原始形态的同生之美、依生之美、竞生之美和共生之美等审美范式;洪水滔天和人兽婚配两个典型的非和谐形式蕴含着深刻的和谐本质,并以再生的特殊形式彰显原始形态的整生之美;民族迁徙则表征佤族祖先追求生态和谐理想的历史足迹,贯穿于神话传说创作者寻求大美家园的历程。“司岗里”生态和谐的核心审美价值观和理想在衍生态、仿生态文本中均得以继承,有些仿生态文本逐渐构建真善美益宜的中和价值体系,已初具当代整生的意义,在提升“司岗里”品质的基础上,螺旋地复归“图腾”和“家园”之意。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民族艺术应坚守合乎生态规律和目的的核心审美价值和理想,并对之进行不断完善和优化,使之能持续地良性循环,整生出中和的价值体系,构建生态和谐家园,并实际地引导审美人生的实践。
参考文献:
[1]. “局外人”论纲[D]. 李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理想城市的建构与解构[D]. 张广勋.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3]. 近叁十年中国大陆背景女作家的跨文化写作[D]. 周颖菁. 武汉大学. 2010
[4]. 民俗学的当下意义[D]. 王德刚. 山东大学. 2018
[5]. 暮色中的寻找[D]. 董小玉.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6]. 新时期小说“零余者”形象研究[D]. 刘菲.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7]. 二十世纪中国市民小说论纲[D]. 王晓文. 山东大学. 2006
[8]. 恶的书写:现代小说叙事的伦理境遇研究[D]. 常娟. 南京大学. 2011
[9]. 中国新诗的视觉传播研究[D]. 王强. 苏州大学. 2012
[10]. 司岗里:佤族的生态和谐审美理想[D]. 赵秀兰. 云南大学. 2014
标签:文艺理论论文; 文学论文; 跨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视觉文化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现代小说论文; 民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