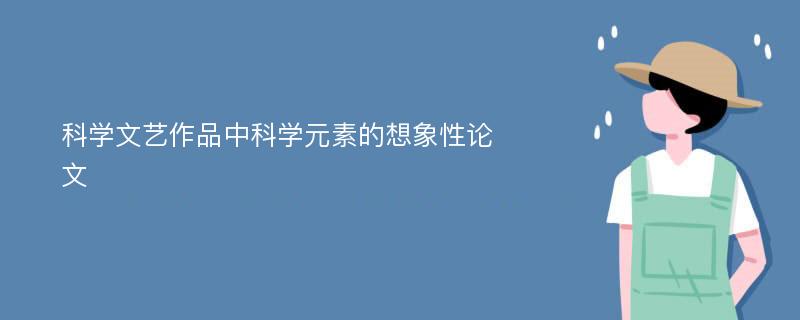
科学文化与传播
科学文艺作品中科学元素的想象性
姚利芬
(中国科普研究所)
摘要: 当一部科学文艺作品描摹出的世界不符合科学理论向我们展现的世界时,这个作品是否还能被称为科学文艺作品?本文认为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可以有想象性。第一,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别很难说清楚。第二,虽然科学是一个家族相似式的概念,但带有想象性科学元素的作品也叫科学文艺,而不是单纯的幻想文学。第三,带有想象性科学元素的科学文艺作品并非是伪科学,而是非科学,应该鼓励其发展,但本文不主张可以随意地歪曲科学知识。科学文艺中的“科学性”和“想象性”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牺牲微小的科学性而增加大量想象力和趣味性的科学文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应当被鼓励。
关键词: 科学,科学文艺,非科学,伪科学,想象性
众所周知,科学文艺作品(科幻小说、科学童话、科学故事、科学寓言等)有助于想象力以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在作者建构出的一个迥异于日常生活的全新科学幻想世界里,读者可以得到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进而达到开脑洞、习新知、察世情、娱人心的效果。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科学文艺作品所涉及的科学元素是否一定要符合科学事实,这也是自20 世纪70年代末至今在科学界、科普科幻创作界一直讨论的问题。如果科学文艺作品中所涉及到的科学元素不符合科学事实,是否应该被摒弃?如果一部科学文艺作品向我们展现的世界不符合科学理论向我们展现的世界,那么这个作品还能否被称为科学文艺作品?本文通过梳理科学文艺的论争,分析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文艺的文学本性以及科学文艺作品的非伪科学性和想象性,认为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可以有一定的想象性。
一、从两场论争说开去
科学文艺的第一场争论发生在20 世纪70年代末期,其时,“科文之争”刚显冰山之角。1977年,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连载于《少年科学》杂志(2——3 期),讲的是一个关于从珠穆朗玛峰找到的没有变成石化的恐龙蛋如何被复活的故事。1979年7月19日,《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刊登甄朔南的文章《科学性是思想性的本源》。该文批评了根据《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改编的连环画《奇异的化石蛋》,认为其背离了起码的科学事实,没有思想性,是伪科学的标本。叶永烈在1979年8月2日《中国青年报》以《科学·幻想·合理——答甄朔南同志》一文回应,认为科幻小说的幻想内容只要大致符合科学认知,就能给读者以启迪和思考。[1]
排除标准:(1)急性局部或全身性感染;(2)责任节段存在腰椎失稳:(3)有腰椎手术史;(4)年龄≥22岁。
无独有偶,时隔近40年后的2015年,科学童话界也发生了一件“鄂教版小学二年级课文遭吐槽”事件,牵动了许多学生家长的心。科学童话《会上树的鱼》是童话作家张冲创作的一篇作品,最初发表在1986年5月3日的上海《幼儿文学》上,文中讲了一个“弹涂鱼上树吃蜗牛”的故事:海边一棵大树上有一群小蜗牛在吃树叶,弹涂鱼爬到树顶,将这群“害虫”全吃光了。2003年,经有关教材编委会筛选,编进鄂教版小学二年级语文教科书。2015年,学生家长、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与昆虫学院副教授付新华看到这篇科学童话,撰文指出弹涂鱼吃蜗牛不科学;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创始人刘毅同时也在微博撰文《“弹涂鱼爬树吃蜗牛”到底有什么问题?》,指出“蜗牛既不下水,耐盐性也不行,如何出现在红树植物的树上”等科学性问题,认为这种杜撰出来的故事出现在小学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中,恐误人子弟,值得三思。[2]此事很快引起媒体注意,《武汉晚报》记者明眺生写出了《“弹涂鱼上树吃蜗牛”纯属杜撰》的新闻稿,该文发表在2015年10月24日的《武汉晚报》上,一时间全国数十家网站纷纷转载,引来700 多万次的点击量。对此持不同意见的读者也纷纷发声,湖南武冈市小学教师刘传斌撰文《鱼上树吃蜗牛,有违常识又何妨》指出,“孩子之所以喜爱童话,就是因为其中的故事充满幻想,能满足其好奇心。我们怎能奢望童话中的想象都符合常识?又何须对所有的想象都验证对错?毕竟,科学童话不同于数理化教材,适当运用夸张、虚构手法,更符合童话文风,更能培养孩子的想象力。”[3]
无论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童话,均属于科学文艺的范畴。从上面两例论争我们看到一些对科学文艺创作而言长期存在的共性问题——“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能否具有想象性”?一些人主张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必须符合现有的科学理论,不能有半点差错;另一些人则主张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可以带有一些想象性,可以出现与当今科学理论不一致的提法。
20 世纪80年代初科幻文学领域闹得沸沸扬扬的“科文之争”,其争议的焦点在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认为科幻文学姓“文”的一派指出,科幻小说重在以文学叙事,潜移默化地培养读者热爱科学、勇于追求美好未来的情操,尽管使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的推理,但不担负传播科技知识的任务,因此必须遵循文艺的一般规律。认为科幻文学姓“科”的一派指出,科幻小说是用文艺性笔调写成的科学作品,不同于一般文艺作品,应以科学内容为主,属于科普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穿着文艺外衣的科学之身,因此发挥艺术想象、创造形象是次要的,只要涉及科学知识就需要准确无误。还有一派认为科幻小说既不姓“科”也不姓“文”,而是由两者结合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它通过艺术形象传播一定的科学知识,是一个崭新独立的门类。因此,科幻小说既不能忽略科学内容的正确性,否则就会混同于一般文艺作品;又不能忽视作品文学意象的塑造,否则就会失去了文艺的特性,与一般科普文章相似,不是文艺作品了。[4]
这一争议不只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存在,而是科学文艺类作品创作的共性症结。由此来看,2015年科学童话创作领域发生的关于《会上树的鱼》的论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们要反对伪科学知识,因为伪科学知识无论在理论抑或是在实践上对我们都是有害的。在指出炼金术为空想的伪科学(fantastical pseudo-science)时,历史学家安德鲁(James Pettit Andrew)首先使用了伪科学(pseudoscience)一词。伪科学不是科学知识,它是一种非科学知识;不是所有的非科学都是伪科学,形而上学、伦理和宗教等是非科学,但并非是伪科学。我们通常认为伪科学是非科学的一种,它也是带有贬义意涵的,或称坏的科学。从词源学上看,“Pseudo-”就意味着错误。
其实,不只科学文艺界,在一般性文艺作品中也时常会见到关于“科学性”问题的争执。1988年由李冰雪填词,王赴戎、徐沛东作曲的一首儿童歌曲《种太阳》,表达了少年儿童要使世界变得更加温暖、明亮的美好愿望,其中写到“播种太阳”,一个送给南极,一个送给北冰洋——这也难逃被质问的命运。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对这首歌曲的指责,认为其不符合科学认知和科学精神。
综上,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是否必须符合现有的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还是可以有一定的想象性,是一个长期以来争执未果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科普科幻创作愈加繁荣的形势下,廓清对这一问题的认知,有助于科学文艺创作的良性发展。在本文看来,要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首先应该回答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有什么样的不同,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科学知识。
二、科学究竟是什么
这里主要研究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有何种不同,究竟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科学知识。对这个问题,首先需从词源学上考察科学知识究竟指的是什么样的知识。
我国古代有“科”和“学”这两个字,但这两个字经常单独使用,没有“科学”一词,“科学”是对英文单词Science 的翻译。然而,虽然Science 一词早就存在,但直到19 世纪,英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仿照artist 一词创造了scientist 一词后,它才被大规模地关注和使用。纵观历史,Science 一词的意思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古希腊,“科学”还没有从“哲学”脱离出来,它们被认为是一回事,这就是西方的理知传统。“从用语上说,代表这个理知传统的是希腊文的episteme 和拉丁文的Scientia。拉丁文Scientia 是从希腊文episteme 的直接翻译,它们的意思如果译成中文,可以差强人意地译成‘知识’。”[8] 然而,英文词汇Science 与中文词汇“科学”的意思却与此不同,它指现代的自然科学。与英语和汉语的习惯不同,我们通常认为德语中的Wissenschaft 可以翻译为科学,主要是指知识。我们知道Wissenschaft 一词是由动词wissen 加上的名词后缀-schaft 构成,其中wissen 的意思是知道、明白。因此,德语的Wissenschaft 主要指知识或学问。
从上面论述中可知,“科学”一词的意思不断变化,并且不同国家和民族都可能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那种主张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是否必须符合现有的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
以我院2017年01-2018年01月内收治的50例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为研究对象,包括男性28人,女性22人,患者年龄65.0-80.5岁,平均(68.3±7.2)岁。基于治疗的奇、偶顺序将之分为实验组(奇数组)和对照组(偶数组),每组25人。
(1)The natural frequency of each subsystem of an EHA is not the main reason restricting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system,and the main reason is the output power of the motor which restricts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EHA.
毫无疑问,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应该被归为科学文艺作品是基于科学与非科学有着清晰明了的区分。可以说,把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区分开是研究本文主题的关键一环;只有明确了科学划界标准,我们才能研究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应该被归为科学文艺作品。
幼儿园开展一日活动已经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幼儿教育的这种改革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重视。一日活动主要是为了使课程的难度、知识点与幼儿的智力、接受知识的方式之间严密契合。在幼儿园的教学过程中,将课程引入游戏、运动、生活中可以使幼儿的学习变得轻松,进而提高幼儿的学习效率,使幼儿能够轻松愉快的学习并成长。
逻辑经验主义者主张科学划界的绝对标准。他们关注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差别,他们想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形而上学的伪命题。所谓伪命题就是,既不真也不假,而是无意义的命题。在逻辑经验主义主义者看来只有两种类型的有认知意义的命题,即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所谓分析命题就是命题的真理性或有效性只依赖于语词的意义。例如,逻辑和数学命题是分析命题。然而,综合命题是对事实与经验的陈述,其真理性需由经验检验。与形而上学命题相比,科学命题一定能被还原为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是没有认知意义的科学命题。
最早的系统分类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动物学分类,他首先根据动物的繁殖方式划分大类,然后再根据同源器官之间的差异划分类。然而,这种分类的依据到底是什么?类到底是共同本质的事物的群体,还是人类对之归类的结果呢?这就是关于类的描述主义与本质主义之争。其实,这两种争论源于唯名论(nominalism)与唯实论(realism)之争:唯名论认为通名或共相(universal)存在于思想之中,唯实论认为共相“先于”个体事物而存在。
与科学划界的决定标准不同,历史主义者主张科学划界的相对标准。随着历史主义的兴起,与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的衰落,科学划界标准开始呈现相对化趋势。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把科学发展看作是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发生的过程。在库恩看来,只有在常规科学内,我们才能把科学从非科学知识中区分出来;是否形成范式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然而,由于范式本身包含形而上学信念和社会、心理等因素,因而在范式内部很难找到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不仅如此,由于“不同范式(常规科学)之间又是‘不可通约’的,没有合理比较的共同基础,那么现代科学与古代思想可能只是范式的不同,没有科学与伪科学之分。”[10]库恩的科学划界标准越来越趋向于模糊化与相对化。
鉴于类的自然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缺陷,本文想引入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alance)来解决此问题,我们暂且称之为类的家族相似理论。此理论认为范畴的成员不必具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而是AB、BC、CD、DE 式的家族相似关系,即一个成员与其他成员至少有一个或多个共同属性。各种有相似性的东西构成一个家族,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与其他成员有或多或少的相似性,但没有一个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的共同点。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主张范畴没有固定的明确的边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形成和变化发展的。
由图1可知,红茶浓度和浸泡时间的交互作用显著。由响应面图可知,当浸泡时间保持在30~42 min范围内时,延长浸泡时间将会增加感官分值;当浸泡时间保持在42~50 min范围内时,延长浸泡时间将会降低感官分值。同样,当红茶浓度处于0.8~1 g/L范围内时,感官分值随红茶浓度的增加而提高;当红茶浓度处于1~1.2 g/L范围内时,感官分值随着红茶浓度的增加而下降。综上所述,感官分值随着红茶浓度、浸泡时间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比科学划界的相对标准更为激进的是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观念,他主张取消科学划界标准。费耶阿本德认为“那种认为科学能够且应该依据一些固定的法则来发展,认为理性是由这些法则所构成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说它不现实,是因为它把人类的才智以及促进或者导致这些才智发展的环境条件看得过于简单了。说它有害,是因为强化这些法则的努力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会在提高我们的职业素质的同时降低了我们的人性。”[11]
在费耶阿本德看来,人类探索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个未知的世界,我们绝不能武断地说哪种知识是合理的,哪种知识不是合理的,应该保留自己的选择权。不仅如此,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教育与宗教一样,它自大、富有侵略性,完全束缚人的发展,因此,与其他非科学知识相比,科学知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科学与神话、宗教之间的区别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到底哪个更合理应该由个人决定。科学与巫术处于同等地位,享有同等发展的自由。
也许,费耶阿本德主张的科学与宗教本质上没有区别的观点太激进了。鉴于此,许多哲学家提出了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认为多元的科学划界标准要优于一元的科学划界标准。萨伽德(P.Thagard)认为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科学与伪科学:科学经常使用关联思维方式、追求经验的验证与证伪、关心理论与竞争理论的评价、采用高度一致、简单的理论、不断进步;但伪科学使用相似思维方式、忽视经验因素、不关心竞争理论、采用非简单理论,并求助多特设性假说、在教条与应用上停滞不前。然而,萨伽德以上五种划界标准并非是科学或伪科学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另外,他还指出,当判别某一知识是否为科学时,我们需看某领域更接近典型的科学特征,还是更接近典型的非科学特征,以此判别此类知识是否为科学或伪科学。[12]与萨伽德一样,哲学家邦格(M.Bunge)也坚持科学的多元标准,他提出了十要素标准,认为任何知识都有以下十个特征,即E=(C,S,D,G,F,B,P,K,A,M)。[13]
为了解决第三节遗留下的问题,我们先要区分两个概念,那就是“非科学”和“伪科学”。所谓非科学知识就是除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如文学和艺术等。毫无疑问,美术和音乐是非科学知识,但我们绝不会因为它不是科学知识,就应该摒弃。爱因斯坦谦虚地认为,莎士比亚对人类的贡献比他对人类的贡献还要大。这就是说,存在许多非科学知识,并且这些知识是合理的;我们不仅要保留这些非科学知识,还要支持它们的发展。
纵观科学划界标准,它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绝对标准、相对标准、消解标准、多元标准。下面将考察以上哪个划界标准更具合理性,以便解决上述提出的问题。
三、科学文艺的文学本性
在本文看来,想要回答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是否必须符合现有的科学,不能有半点差错,就必须回答科学文艺到底是科学还是文学,这是因为如果是前者那么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就不能有半点差错,如果是后者那么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就容许具有一定的想象性。其实,以上问题涉及到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分类问题。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可证实标准不能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此标准不能把科学从伪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出来。占星术的一些结论也具有可证实性,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是不可证实的,因此可证实标准甚至不能把科学从占星术等伪科学中区分出来。有鉴于此,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9]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理论都能在原则上被证伪,如狭义相对论,但非科学理论则在原则上却不可证伪,如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因此,原则上的可证伪性就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然而,波普尔的科学划界理论也是有问题的,例如,占星术和精神分析学被他誉为典型的伪科学,但占星和精神分析学有些结论却可以被证伪。
数学创造力发生发展于学生、教师和教学任务3者的互动中.一方面,创造力教学应该立足每一个成分,努力实现其最佳的创造性状态;另一方面,应该认识到3者是不可割裂的创造力整体,当3者以某种状态同时呈现时,其结果往往就是创造力的展现.希斯赞特米哈伊以“福流状态”定义这个创造力的高峰状态,侧重描绘个人体验;Renzulli则从整体教学角度将其称为“理想的学习行为”[60].
关于类的描述性观点主张用性质描述来定义自然类。例如,我们说老虎就是“毛色浅黄且布有黑色横纹的、尾巴粗长并具黑色环纹的、圆头短耳额面有白斑的、四肢健壮有力的、生活于山林中的、大型食肉动物”。然而,这种观点存在许多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根据内在性质还是外在性质(关系)来划分?虎的基本性质是圆头短耳额面有白斑、四肢健壮有力、还是大型食肉动物?也许我们还能凭借直觉对这种简单的例子进行区分,但直觉对复杂的例子无能为力。其次,概念的涵义会随科学的发展而改变。我们现在知道黄金是化学元素金(化学元素符号Au)的单质形式,但黄金的本质是我们近一百年来才知道的事情,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一点。如果这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来描述他们?
自然类的本质主义的观点主张用本质属性,而不是任意的必然属性来定义自然类。例如,无论是东北虎、华南虎、马来虎还是孟加拉虎都具有老虎的基因谱。然而,此种观点还是有其缺陷的,那就是关于纯度的问题。我们知道不仅每一种类的老虎,甚至每一只基因谱都不相同,按这种观点,每一只老虎都是一个自然类或物种。
课堂教育是高校红色教育的重要环节,目前仅是《形势政策》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的一至两个模块,教学时间总计在4-6学时,没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进行深入探析,不能全面、系统地进行教育引导,导致学生对红色教育的理解仅限于听几个英雄故事,看一部战争电影。同时,教学内容陈旧,沿用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课件,跟不上红色教育研究的最新进程,脱离时代特色和学生实际需要,不能激发学习兴趣,无法引起学生重视。
文学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创造艺术形象、反映客观现实、表现内心情感,以及表现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具有情感性和想象性的特征;而科学文艺是以艺术形象思维为基础,通过科学创意的构织,对现实做艺术上不同层次反映的品种。尽管使用了科学知识和科学推理,它向读者传达的仍然是文学信息,而不是科学理论,与一般的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丰富的科学创意幻想。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说科学文艺更像文学,而不是科学。因此,我们应该允许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有一定的想象性。
也许有些人会批判本文的观点:我们不是不赞同一些作品可以有一些想象性,但这就不是科学文艺了,可以称之为幻想文学。对此本文认为,一个事物的名称不是用限定摹状词(definite description)来定义的,专名是非描述性的,因为这种描述的可能是偶然性的。本文赞同索尔·克里普克(Saul Aaron Kripke)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名称的指称最初是在现实世界中通过“洗礼”的方式被确定下来,随后通过历史的因果链条而传播开来。例如,小明之所以叫小明并不是因为小明这个名称更能描述出他的本质,而是他父母在他出生后对他的命名,以后无论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都是小明。因此,科学文艺之所以称之为科学文艺,科幻小说之所以称之为科幻小说,不会随着其作品中的科学元素是否具有想象性和具有多大程度的想象性而变成“幻想文学”,而依然是科学文艺,依然是科幻小说。
即便如此,还有一些科学工作者认为,无论如何,带有想象性的科学文艺应该被摒弃,因为它们歪曲了科学,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可是,带有想象性的科学文艺真的应该被摒弃吗?我们主张不摒弃这样的科学文艺,甚至鼓励其发展,理由何在?
四、科学文艺作品的非伪科学性和想象性
本文也支持科学划界的多元标准;科学与宗教之间并非是无区别的,但划界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多元化的标准更符合实际。由此,本文更加坚信那种主张科学文艺中的科学元素不能具有想象性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哪种知识是科学,哪种知识不是科学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溯本追源,“科”“文”之间梳而不清的纠结背后是对科学文艺的概念认知。科学文艺的兴起与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密不可分,最初是指苏联伊林的《五年计划的故事》《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作品。伊林对中国现代科普创作发展的影响巨大,他认为“科学文艺是用科学全副武装起来的文学。”[5]科学文艺的名称从苏联引入之初,更多指的是科普作品。后来则将“科学文艺”归为“儿童文学”旗下,例如,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方卫平认为科学文艺是文学的一种,他在《儿童文学教程》中指出:“科学文艺是以文学艺术特有的方式向儿童介绍、解释和传递科学知识,或者利用科学知识编织和讲述故事的一类儿童文学文体。”[6]另一名儿童文学研究学者贺宜认为科学文艺作品应该具有广泛、充实、丰富的科学知识内容,而且,这些知识必须符合科学事实。也就是说,科学文艺所讲述的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以及它们的应用范围、发展方向等都要以正确的科学理论和实验作为依据,尊重科学事实,客观进行分析。[7]将“科学文艺”片面地纳入儿童文学的麾下,这也是导致对科学文艺的特性认知发生偏颇和犹疑的一个站位基础。实际上,科学文艺作品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光是儿童,还有成年人。随着时代发展,科学文艺这种体裁早已越过伊林式作品的界限,囊括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样式,这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
那么,伪科学为什么是坏的科学呢?从理论上讲,把伪科学标榜为科学就是一种不诚实的欺骗行为。从实践上讲,这种区分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都十分重要。比如,无论是监督局官员、药品厂家还是病人,都需要区分医药科学与伪医药科学。因为依据医药科学生成出来的药品对病人是有效的,但依据伪医药科学生产出来的药品不仅会危及到消费者的健康,还会引起社会对医药公司、政府,甚至是对科学的不满。
对于高校的知识产权管理而言,主要的目标是对科研技术成果及其他智力成果的开发、利用、转让和发展进行系统化的管理。但是在目前的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中,还存在以下方面的诸多问题。
毫无疑问,科学文艺是非科学知识,但科学文艺是伪科学知识吗?科学文艺的作者虽然有科学家,但大多数是文学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创作的作品是科学作品,而认为是文学作品。不仅如此,小学课本的编者也没有把科学文艺作品放在“科学”的课本中,他们自然地把这些作品放在了小学语文课本上,甚至还放在了童话等板块。科幻小说作家、科学童话作家、语文教科书编者并不是要通过科学文艺作品来直接传播科学知识,在写作中引入科学元素一方面是增加可读性与趣味性,另一方面是培育对科学的兴趣。因此,本文认为,科学文艺绝不是伪科学知识,而是非科学知识。因此,既便科学文艺中存在一些想象性的成分,也绝不应该反对科学文艺的存在。
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从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恐龙蛋开始他的故事,这里无疑包括了一些想象的因素。很多人批评这个小说不合理的,因为喜马拉雅山上不可能发现恐龙蛋。本文认为这种批判并不合理,这个文章是一篇小说,需要一些想象的空间。毫无疑问,科学元素也可以成为小说或童话的组成。这些元素一旦放在小说或童话之中,就会有某种小说性或童话性。
为了考察各因素交互作用对纤维素酶活力的影响,对模型进行降维分析[11],研究接种量、固液比、冬凌草与麸皮比两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其对应的响应面及等高线图如图2所示。
物种衰退数量减小,许多珍稀动物濒临灭绝或已灭绝。经确认曾广泛分布,但近来没有发现的鱼类33种,如中华鲟、白鳍豚等已在湿地消失。生物灾害加剧,表现为血吸虫病和东方田鼠危害等。保护湖区生态环境链刻不容缓。
不仅如此,本文还支持具有一些想象性的科学文艺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因为科学文艺允许有想象的成分,还因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14]另外,科学文艺不仅可以激发我们对文学的兴趣,而且可以激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当然,本文并不赞成称严重违反科学理论的文学作品为科学文艺——称这样的文学作品为幻想文学则更为合理。
五、结 论
根据论述,本文主张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可以具有一些想象性。第一,无论是从词源学上来看,还是从科学划界标准上来看,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区别很难说清楚。因此,我们应该允许科学文艺作品中的科学元素可以具有一些想象性。第二,虽然科学是一个家族相似式的概念,但带有想象性科学元素的作品也可以是科学文艺作品,而不是单纯的幻想文学。第三,带有想象性科学元素的科学文艺作品并非是伪科学,而是非科学。我们应当反对伪科学知识,不应该反对所有非科学知识,我们应该鼓励文学、音乐和艺术等非科学知识的发展。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想象力比知识可能更重要。语文教材不过是教学的素材和工具,批评语文教材虽无不可,但以“科学”的名义对其苛责,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同时也未尝不是对语文教育的一种伤害。
最后,本文并不主张可以随意地歪曲科学知识。科学文艺中的“科学性”和“想象性”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牺牲微小的科学性而增添大量想象力和趣味性的科学文艺是合理的,应该被鼓励。
志谢:西安交通大学初维峰博士对本文的写作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吴岩.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8:272.
[2]刘毅.“弹涂鱼爬树吃蜗牛”到底有什么问题?.http://weibo.com/1904104290/D0mSMq0RZ?sudaref=www.baidu.com&retcode6102&typecomment.[2017-08-02].
[3]刘传斌.鱼上树吃蜗牛,有违常识又何妨.科教新报,2016-05-12(3).
[4]蒋风.新编儿童文学教程.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218-219.
[5]孔宝刚.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95.
[6]方卫平.儿童文学教程.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246.
[7]贺宜.儿童文学讲座.北京: 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121.
[8]吴国盛.“科学”辞源及其演变.科学,2005,67(6):6.
[9]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北京: 三联书店,1987: 28.
[10]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第2 版).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66-167.
[11]博兰.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思考: 波普尔的两种观点.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06-220.
[12]P.Thagard.Computation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ass: MIT Press,1988: 170.
[13]马利奥·郑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张金言译.哲学研究,1987(4): 46-51.
[14]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增补本).许良英等编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0: 284.
The Imaginary Problems of Scientific Elements in Scientific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YAO Li-fen
(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question whether a work of literature could be entitled to a science-literature-art work if the world it presents to us does not conform to the world that scientific theory presents to us.This article supports that scientific elements in scientific literary works can be imaginative.First,it is hard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non-scientific knowledge.Second,although science is a family resemblance concept,works with imaginative scientific elements are also science-literature-art works,not mere fantasy literature.Third,scienceliterature-art works with imaginative scientific elements are not pseudo-science works,but non-science works,and we should encourage their development.However,this article does not claim to distort scientific knowledge at will.There is a certain tension between scientificalness and imagination in science-literature-art works; Science-literature-art works of sacrificing a small amount of science to increase imagination and interest are not only reasonable,but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
Keywords: science,science-literature-art,non-science,pseu-doscience,imagination
中图分类号: N0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9524/j.cnki.10-1009/g3.2019.02.079
作者简介: 姚利芬,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普科幻创作。
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18BZW145)。
(责任编辑 黄小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