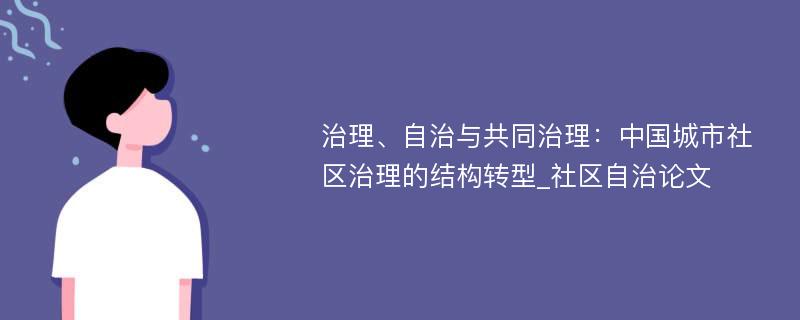
管治、自治、共治: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区是我国城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也是城市居民自治的主要空间。改革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的调整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也发生了社区体制重构和社区自治发展的两次转型。近年来随着住房商品化、业主委员会的兴起以及业主维权行动的涌现,当前亟须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第三次转型,构建起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共治型”社区治理结构。
一、行政重构社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兴起
改革之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在街道——居委会的管治之下。然而,在单位体制盛行的城市社会,街居管治的空间是边缘而局促的,作为街道办的“腿”——居委会的管理对象主要是那些城市中的非单位成员如“五保户”、盲流以及无业人群,主要职能限于政策宣传、民意收集、治安保卫、民事调解、优抚救济及消防等。改革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冲击了单一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冲击了依附于这一体制上的单位制社会结构。单位制之外的社会人,那些在外资企业、私营部门、自谋职业的流动商贩,乃至失业群体等,不仅使传统单位体制作为国家管理网络的有限性,同时也孕育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社区。大量社会人聚居在社区,但却非同一单位的社会成员。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传统“同业型”的居住空间逐渐让位于“同居型”的社区空间。
与社区扩张相伴随的另一个趋势在于,社区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与供给不足之间存在严重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居民的不断增长,与之有关的社区治安、社区环境、文化娱乐、社会救助、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然而,以居委会为主体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显示出能力不足的缺陷,不仅在人员构成和业务素质上已无法适应更为复杂和更为专业化的社区服务,而且在工作经费和职能范围上也无法覆盖日益广泛的社区事务。这就造成了常见的“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的城市基层治理的尴尬处境。
社区空间的扩张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让行政部门开始“重新发现社区”,社区的重要性被重新评估。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社区建设概念的提出开始,到2000年中央“两办23号文件”的颁布,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酝酿经历了约10年的时间。这一过程中,民政部门通过举办学术研讨,进行地方性社区建设试点,开展“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评选等活动,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探索实验。关于社区进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社区的范围与层级的确定、政府与社区的职责与权限的界定,社区治理结构的重组等问题得到广泛试点。[1]这些探索的背后,除了强化城市社区给该服务的提供,也更注重如何实现对于这一治理空白的填补,特别是对于那些生活在单位之外的社区成员的管理。
行政主导下的社区建设,推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第一次转型。这一转型过程除了进行社区空间区域的重新规划、社区办公与硬件设施的配置,更重要的是对街居管治体制的改造与重组。2000年颁布的中央“两办23号文件”,对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重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推进公共服务覆盖日益扩展的社会空间的同时,将行政力量也填充到这一空间,要求完善社区党群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的组建。在这一文件实施后,社区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此前的居委会被重新规划整合改造成社区居委会,作为“党领导下的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同时,又新成立两个组织,一是社区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城市基层社会的触角和网络,接受街道党工委的工作领导,担当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功能,统筹协调执政党在社区的各项工作。二是建立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工作能力和热情。许多地方通过公开招聘、到了2002年前后,这一过程大体上业已完成。
二、走向社区自治: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转换
在2000年代前期,行政主导下的社区治理体系重组阶段完成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进行了第二次转型,即以开展社区直接选举为导向推进社区自治体制的构建。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民政部门将社区定位为基层自治的制度层级。传统的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与村委会同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造后的社区居委会承继了传统居委会的这一属性。它是社区居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其成员经民主选举产生,负责社区日常事务的管理。因此,社区是居民自治的场域,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也被确定为实现社区自治。
现实当中,民政部门也以扩大社区自治为目标导向,极力推动社区民主的探索实践和社区直选的扩展。1999年,民政部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作纲要》中就明确提出“社区自治”的概念,并先后在全国26个社区建设实验区中加以推广实施。从1998年到2003年间,民政部先后在青岛四方区、上海卢湾区、浦东新区以及北京石景山区先后进行社区直选的零星试点。2000年底到2001年11月,省级社区居委会直选首先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始,南宁、柳州、武鸣等地展开城市社区直选。广西直选的一个重要探索是在将村委会选举的经验与技术如竞选演说、秘密划票间等,移植到城市社区,从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选举热情。2002年社区直选开始在一些大中城市大范围推开,北京、广州、深圳、沈阳、南京、宁波、苏州、上海、长沙等城市先后进行社区直选的试点。[2]1998年到2003年期间的城市社区选举呈现选举逐步规范化、直选模式多样化等特点。
在社区直选的基础上,各地又进行了社区自治体制的探索,形成了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盐田模式及海曙模式等各种创新实践。其一,沈阳模式是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重组社区治理体系,分别设立了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和社区委员会三个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是社区的决策组织,由社区居民和驻区单位选举产生。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是社区的协商组织,通过推选驻社区单位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区德高望重者组成,发挥民主议事、协商监督的职能,社区党组织负责人一般兼任委员会主任。社区委员会则是社区的执行组织,由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时吸收驻社区民警和物业公司经理共同组成,行使社区管理、服务、教育和约束等项职能。
其二,江汉模式在参照沈阳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设计社区组织结构,成立了社区党组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它们之间分工明确,社区党支部为领导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为决策层,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为监督层,社区居民委员会为执行层。其中,社区居委会成员产生需要经过笔试、面试、竞选演说、居民代表初选、正式选举五个程序,在坚持提升成员素质的同时,又坚持发扬民主。[3]江汉模式的另一个创新是按照社区与政府两种“机制结合、功能互补、资源整合、力量互动”的原则重新界分了政府与社区的职能领域。街居之间被明确为“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并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向社区转移职权与资源;要求政府职能下沉到社区,如人员配备、工作任务、工作经费等。
其三,盐田模式是在“议行分设”的理念进行社区治理结构的调整,设立“一会两站”的社区组织结构。社区工作站由社区居委会的下属机构,归并到街道办事处,作为街道在社区的工作平台,专门承担政府交办的行政性工作。社区居委会则回归到居民自治组织的属性,开展居民自治活动,监督政府工作。社区服务站则由居委会作为举办主体,按照相关法律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开展社区各类公益服务活动,做社区居委会的“手”,为社区居民服务。
其四,海曙模式按照“选聘分离”、“街聘民选”的原则重组社区治理体系。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进行社区居委会的重要改革。社区居委会由本社区居民经过直接差额选举产生,行使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权;社区居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工作人员是由街道面向社会招聘社区工作者,经过笔试面试等程序,推荐给社区。这些转制社区工作者由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聘用,政府支付成本,承担社区居委会交办的自治性工作以及政府在社区层面的相关公共管理和服务工作。[4]从行政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的角度来看,海曙模式与盐田模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自治导向下的社区建设,在社区直选和自治结构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社区治理结构的第二次转型。当然,自治导向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并非完全抛开政府的自治,而是合理界分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扩大社区自治组织的权限。地方探索模式的经验也显示,社区自治必须在尊重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基础上,妥善协调社区自治与政府行政的关系,明晰社区事务的决策、执行与监督功能。
三、社区矛盾凸显: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挑战
随着城市社区的分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社区面临的任务与问题也发生了转变,并凸显出既有社区治理结构的限度。第一是社区利益多元化与表达机制单一化之间的张力。当前,社区利益多元化的趋向日益明显。在社区场域内,社区居民与驻区单位、租户与业主、开发商与业主等都成为具有明确利益的主体。同时,基于不同的利益基点,各个社区主体之间如业主与开发商之间,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居民与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不信任、不合作乃至对立关系也隐然显现。然而,在当前的社区治理体系中,单纯依赖于社区居委会很难包容如此多元广泛的社区利益诉求,并且自治性的社区居委会也无行政职权来统筹如何复杂多元的利益关系。
第二是社区矛盾尖锐化与协调机制的有限性。近年来,社区矛盾的凸显化集中展现在各种形式的业主维权现象。围绕房屋质量和产权相关的商品房销售、拆迁,物业管理,公共工程建设等引发的业主维权现象,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此起彼伏,掀起一场“城市运动”,如深圳建设“西部通道”侧接线而出现的大规模维权事件、上海规划磁悬浮而引发周边业主的“散步”现象。[5]尽管许多业主维权事件的起因,已超出了社区的空间,但事件的治理主体往往又会回归到社区本身。从这些事件发生、扩散和消解的过程来看,都凸显了社区治理体系的局限性。作为居民的“头”和政府的“脚”,社区居委会在面对业主维权行动时处境两难:它既不能破坏社区和谐支持维权,也不能脱离民意阻止维权。因此,业主维权活动的频繁出现并日趋扩大,展现了社区自治体制的失灵。
第三是新社区治理主体的出现。随着社区空间的扩张和社区主体的增加,各类社区草根组织也在不断涌现,社区服务组织,社区老年组织,社区志愿组织,社区经济组织蓬勃发展。尤其是业主委员会,不仅是一个基于产权而组成的业主自治组织,还因其与业主有着密切的利益关联度,成为名副其实的居民利益代言组织。业主委员会成为维权行动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在其与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乃至公共部门的博弈行动中,积极为业主争取利益从而获得了社区业主的广泛支持,从而也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区治理力量。在许多地方,业主委员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治组织”,成为社区利益集中表达的组织,这一状况,反过来弱化了社区居委会作为自治主体的地位和功能。
概而言之,当前社区成为社会矛盾的多发地和集聚区,社区自治与民主日益让位于社区和谐与稳定的目标。社区利益的多元化和社区矛盾的复杂化,凸显既有社区治理结构的失效,即社区居委会作为定位于社区居民开展自治的组织,无法涵盖和包容日趋分化的多元社区利益,以及错综复杂的社区利益矛盾。从构建社区和谐稳定出发,应当充分发挥政党、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及社区草根组织等多元参与,推动社区自治走向社区共治,实现社区治理结构的第三次转型。
四、推动社区共治的结构转型
在社区矛盾日趋凸显的背景下,民政部门在推进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中,也在不断强化社区共治的发展导向,要求充分发挥各类社区治理主体的功能。2007年11月,《民政部关于开展“建设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提出,要建设“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和谐社区,其中“管理有序”就强调健全“民主协商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共建机制、民情民意反映机制”。2009年11月,《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积极推进街道管理体制创新和农村综合改革,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
显然,在社区利益多元化和社区矛盾复杂化的现实下,社区和谐秩序的重构有赖于社区各种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与利益关系的有效调处。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尊重每一个社区组织的主体地位和合理利益,而不单是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此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利益整合与协调功能,发挥社区草根组织的利益表达功能,以及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从而形成一种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格局。
其一,强化执政党在社区的利益整合功能。充分利用社区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拓展其在协调社区利益矛盾,平衡利益关系上的积极作用。不断加强执政党在社区的组织网络建设,在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老年协会等组织中成立党支部,并在此基础上组建社区党委或总支。将社区党委改造成利益协商的平台,党的组织网络变成利益谈判的纽带,让社区党组织积极协调发生在社区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与业主维权会等相互间的纠纷,形成党内协商的格局。同时,发挥社区里的党员的积极作用,发动他们参选业主委员会、楼栋长、社区居委会,帮扶社区内的弱势人群,主动调解社区矛盾,引导业主依法理性维权。
其二,发挥社区草根组织的服务与引导功能。社区内的各类自治组织,如老年协会、科技协会、志愿者组织、爱心慈善组织等,既是社区的行为主体,也是社区的利益主体。要尊重和发挥它们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矛盾疏导上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发挥社区老年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社区里的老人,特别是那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老党员,老专家、老模范等的作用,发挥他们的余热,调解邻里纠纷,化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的和谐局面。其次是发挥社区慈善组织的作用。采取政府引导,民间主办的方式,成立各类社区爱心组织,如“爱心驿站”、“爱心超市”等,让社区各阶层的居民都参与到社区关爱行动,密切邻里关系,凝聚社区亲情,形成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最后,发挥社区志愿组织的作用。通过政府引导,物质补贴、精神激励等方式,积极推动各类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发展,包括社区义工队伍,社区治安巡逻队等。充分发挥这些社区志愿者组织在提供社区服务,改善社区治安与环境上的积极作用,降低政府在社区治理上的负担。
其三,发挥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功能。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维权的主要推动力量,在其领导与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驻区企业,乃至公共部门的行动中,获得了社区成员的广泛支持,从而也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社区治理力量。业主委员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业主(社区居民的一部分)自治组织,它有助于业主的利益表达、激发社区基层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城市基层民主。[6]当前,基层政府尤其要避免将业主委员会边缘化,要尊重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利益代言组织的地位,有序引导其聚合业主利益诉求,表达利益主张的行动。面对业主维权的激烈行动时,基层政府更需要利用倾听业主委员会在表达利益和缓和矛盾上的积极作用,通过谈判、协商、妥协而非僵化地压制的方式化解冲突。
其四,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功能。社区不仅是居民生活和休憩的场所,也是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区域。社区发展离不开居民的参与。要充分发挥那些经常关心社区事务,热心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代表的作用,利用他们在居民中的声望,引导他们理性合法的表达行为。充分落实居民自治,尤其是通过推动社区居委会的直接选举,以及切实下发社区居委会充分的自主权,进而激发社区居民的民主热情,提高他们在治理自身事务上的能力。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通过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培育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消除彼此的陌生和隔阂,形成共同的社区意识。通过激发居民社区参与,凝聚社区意识和归宿感,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协商与和谐关系,从而最大可能地化解社区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