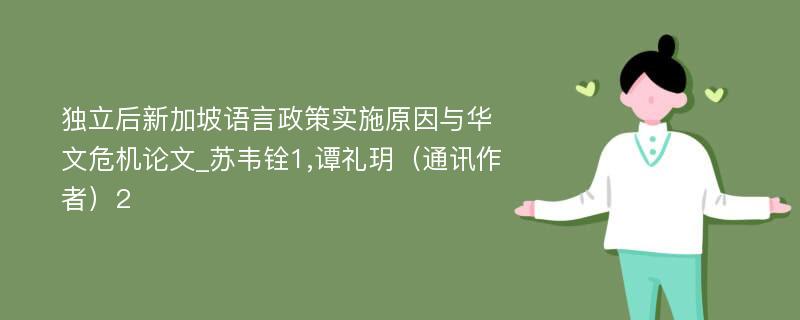
苏韦铨1 谭礼玥(通讯作者)21.普洱学院 665000;2.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650000
【摘要】新加坡建国后,受李光耀政策理念、语言发展不平衡性造成的语言危机、复杂民族矛盾、经济发展与国际定位等因素影响,实施了“双语政策”使其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提高。但由于“双语政策”以英文为基石的不均衡在解决了发展问题的同时又导致了其它语文衰落。新加坡是外海华人人口占比最多的国家,华文使用占有比例仅次于英语,研究新加坡语言政策实施原因和面临的华文危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新加坡华人的现状。
【关键词】新加坡;语言政策;华文危机
中图分类号:G6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1672-2051 (2018)07-040-02
一、新加坡语言政策调整的原因
(一)李光耀的语言政策理念影响
李光耀曾在英国的莱佛士学院学习,深受英文教育影响,又作为华文和国父等多重身份,他曾告诫说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华人虽为主体,但并不能由此而有特权和优越性,新加坡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地缘位置、国情特征,不搞“中国沙文主义”,做到原则的基本平等和社会的多元种族融合。李光耀的理念一方面对于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坦诚地承认,认真对待,承认差异造成的语言不平衡性,建议调整语言政策,作为“教化”国民的重要手段,[1]这对国家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一方面人为需要进行由“工具性”向“依附性”的转换,从而产生“感情依赖”,[2]建立新加坡认识。因此最他而言最好的语言政策理应是平衡英语和其它语言的,可称之为“差异化下的语言平等融合”政策。
(二)缓解语言发展不平衡
自莱佛士以来英国分区统治模式,导致了各民族地区间以母国语言为主要教学和交流手段;新加坡独立后是由于民族众多方面语言各异,各民族在教育方面水平高低不等,国家也没有统一的语言规划,不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现状。因此急需平衡语言发展,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语言以特殊照顾。如新加坡宪法中就强调给予本土马来人特殊地位,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予其相应的照顾,尤其体现在教育、文化和政治权力方面,用以传承民族文化。李光耀就曾强调:各个不同人种、文化、语文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保存下来。[3]
(三)民族矛盾再平衡
新加坡作为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城市国家,一方面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在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发展不平衡影响下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本地民族与“母国”的关系微妙,经常发生各种联系。语言作为承载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也是民族间在日常交往中最直接、最明显的特征,如果对语言政策的处理不当,极易引起敏感的民族问题,甚至和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新加坡的独立是从原马来西亚联邦而来,马来人和华人作为新加坡的两大种族,矛盾积累一直比较深,建国后,为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消除各民族间语言的冲突,维系政治统一,加强国家认同,兑现承诺对当时脱离马来西亚时候对马来人的承诺,将少数民族马来人的马来语规定为国语。[4]与此同时,新政府选择英语(不代表任何民族具有很强的中立性)作为各民族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积极鼓励运用英语交流消除民族隔阂。实施源流学校合并策略,即将不同民族学校、不同民族学生的学校统一合并为一所学校,以便于消除民族隔阂。1991年《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更充分反映了了新加坡在民族共同认同的价值观,举国上下,从学校教育到日常生活,都在不停强调和贯彻,[5]充分说明了新加坡施行这种语言政策的法律约束和发展必然。
(四)经济发展与国际定位的需要
新加坡独立后还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好自身定位和发展经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是在选择全球中适用范围最广泛的英语作为行政语言并首先推动新加坡的国际化战略,积极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建立密切联系,李光耀曾说过如果在那时(建国时)选择华语或马来语新加坡将不知何处何从,在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占主体比例和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中,在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促进通用语的有效提升以促进经济发展方面,[6]选择英语也许是当时新加坡发展经济和对自身国际定位的最佳选择。
(五)国际再平衡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迅速崛起,是当代世界和东亚经济的一个划时代转变。在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以华人为主体民族的新加坡,为继续掌握本国经济和政治主体地位,更好地搭乘顺风车,适应历史发展,在地缘政治上考量上不得不转向东亚和东南亚,与中国的贸易也促使新加坡与中国于1990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适应发展趋势,加强与中国的往来,在语言政策方面,新加坡在1999年初提出过“华文精英计划”,但是遭到国会内多名议员的担忧和反对,特别是少数民族议员。针对这些质疑,李显龙总理做了解释,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客观对这一争论进行了评价,并认为“华文的地位和前途(在新加坡)仍然是个敏感的政治课题”,[7]但是最终的结论是英语已大势所趋。
二、新加坡的华文危机
(一)语言危机
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在推行中确实使得新加坡民族认同感加强、经济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语言环境的改变,新加坡的英语地位已经在四种国语中占据了极大的份额,华人学生人数日渐减少,马来文学校甚至没有学生入学,造成了语言学习的严重倾斜,这些现象违背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民族语言和所载文化的遗失是现代新加坡面临的主要危机。因此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政府也努力作出一些改变,希望倡导华文、马来文等语言,可惜很难做到有效的改变,只能在英语主导的语言环境中去摸索、去努力发展其华文及马来文和文化。不过从一个方面而言,新加坡毕竟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新加坡英语中也有很多汉语的词汇和语法参杂,形成某种形式的新加坡式英语,华人的某些文化也沉淀在了英语本土化的过程中。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8]
(二)华文危机
第一,缺乏与时俱进
据周海清老师研究,新加坡的华语主要以五四前后汉语书面语为基础而形成的;[9]且受到方言的影响;新加坡1990年才与中国建交,也客观反映出受到现代普通话的影响不强。基于上述原因和英文的渗透,长期以来华文的标注化与现代汉语还有一定差距,造成了新加坡华语在读写方面的特殊性,缺乏华文发展的与时俱进。
第二,使用频度低
《联合早报》是新加坡最具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在继承和宣传华人语言与文化传统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早报发行量日均18-20万份之间,而英文《海峡日报》日均发行量是早报的2倍以上达40余万份[10], 目前早报的发行量和阅读量基本保持了稳定,日均阅读超过70万人次,[11]正如早报总编辑林任君先生所言的那样,从新加坡华文最高机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后……华文事业凋零……较有规模的华文机构所剩无几……《联合早报》已经成为其中最突出的代表。[12]但即使这样如果以2011年新加坡统计的华人人口2808.3万为基数,其阅读占比为2.49%,而以全国人口3789.3万为基数计算占比更低仅为1.85%,[13]这个频率结构仍然是触目惊心的。仅从影响力最大的华文报纸一个方面就可以看出英语的主导地位对华文的冲击力度已经使得华文纸质媒体处于危机中,华文和华人传统文化的遗失正一步步危及新加坡的华人世界。而曾经作为方言的话语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目前学生使用的日常用语基本上也都转向了英语,最常讲方言的学生甚至不足1%。[14]
第三,适用范围窄
新加坡华文的适用范围也是危机表现的重要方面。第一是从家庭交流层面,华文仅仅作为华人社区或家庭使用的语言,并且近年来家庭中,特别是年轻一辈家庭中的华文使用比例下降形势严峻。[15]第二是在社会交流层面,普遍以英文为主。第三是职业发展,就业或进入国家核心机构,英文都是必须条件而非华文。第四是教育层面,推行了以英语为语言政策教育核心的“1+N”双语模式,英语所占教育比例和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华文,华文仅作为一个单科而教学。第五是社会期待方面,英语在这一层面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团结认同的重任。
第四,文化精神遗失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和价值观的体现,在华文教育衰落的环境下,民族的传统文化遗失和传统精神遗失现象严峻,部分英语比较流利的华人甚至贬低对英文不谙的华人。[16]新加坡政府作为华人掌权政府对这个问题也认真对待,1969年为了提升汉语学习效率颁布了《简体字表》开展华文改革运动,广受华人好评;[17] 1979年推广一项长期的“华语运动”;1980年到1989主要是华文推广;90年代后则侧重于华族认同,让受英语教育的华人去学习华文;[18]1990年华族、马来族、印度族举办文化月;1994年制定《奉养父母法》坚持母语教育在大学设立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华文教学系,灌输东方价值观和道德伦理等措施以通过恢复母语活力而促进民族传统精神和文化的传承,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三、结语
新加坡“双语政策”的实施是基于新加坡国家稳定和发展而言的,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家认同方面有助于新加坡国家观念的形成,但在各民族的语言发展中却也造成了语言危机,影响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新加坡作为海外华人占比最高的国家,在华文方面的危机也比较突出。未来在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推行的影响下,其华文政策或许还有所调整,以进一步增强文化联系,搭乘“顺风车”促进国家发展。但在具体执行方面还有很多困难,需要新加坡国内的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努力推进。
参考文献
[1]潘少红.新加坡语言教育政策的教化作用[J].东南亚纵横,1999(5\6):50-52.
[2]安绪丽.浅析新加坡的语言政策[J].文学教育,2012(7):70.
[3]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M].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1994:399.转引自: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51.
[4]毕世鸿编著.新加坡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1):112.
[5]鲁虎编著.列国志`新加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54.
[6]安砚贞.易露霞.全球化与民族化之平衡——马来西亚、新加坡教学语言立法与政策评析[J].中国证劵期货,2011(2):150-151.
[7]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95.
[8]戴卫平.新加坡英语:语言迁移与华文元素[J].社会科学前沿,2012(1):25-30.
[9]陈晓锦.张双庆主编.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1):156.
根据论文表述,此处的华语指的是新加坡华人社区的高层语言,也就是通用的普通话华文,而非一般性质的方言。
[10]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9年3月26日报道转引自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180.
[11][12]陆建义.向新加坡学习-小国家的大智慧[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1):132,131.
[13]数据来源: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2011.Population Trends 2011, Singapore,p4.转引自毕世鸿编著.新加坡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1):57.
[14]黄明.新加坡双语教育模式与语用环境及语言转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版),2012(4):190-192.
[15]“中学生以华语为家庭用语的比例很低……仅为32%”数据来源:陈晓锦.张双庆主编.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1):156.
[16]吴英成.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与语言传承[J].语言战略研究,2017(3):81.
[17]刘汝山.鲁艳芳.新加坡语言状况及语言政策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3):56-60.
[18]詹伯慧.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与华文教育[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1(3):1-3.
作者简介
苏韦铨(1987-),男,历史学硕士,普洱学院人文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历史学;高等教育学;通讯作者:谭礼玥(1989-),女,语言学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通识部讲师,研究方向:教学管理,语言文化与政策。
论文作者:苏韦铨1,谭礼玥(通讯作者)2
论文发表刊物:《中国教师》2018年7月刊
论文发表时间:2018/6/15
标签:新加坡论文; 语言论文; 英语论文; 民族论文; 政策论文; 华人论文; 国家论文; 《中国教师》2018年7月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