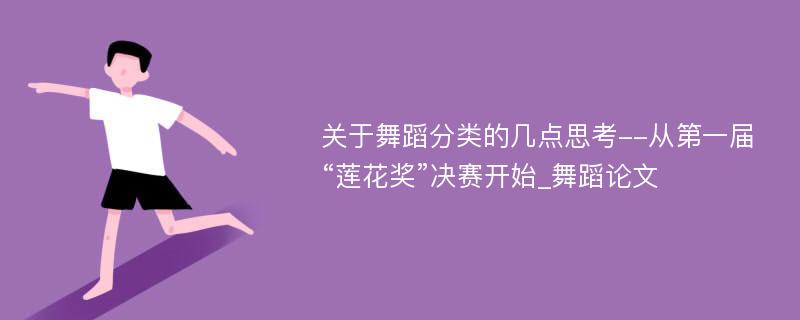
关于舞蹈分类的若干思考——从首届《荷花奖》总决赛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决赛论文,舞蹈论文,荷花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舞蹈分类的问题,是个从理论上到实践中都存在着许多麻烦的问题。当类似“《荷花奖》总决赛”这样按舞种分类进行比赛之时,“麻烦”就显得更为突出了。舞种命名的欠妥当、舞种界定的欠清晰不仅困扰着舞赛本身,而且有可能影响着舞业日后的发展。这说明,舞蹈分类的问题,不再是理论书斋中的“智力测试”,而是发展着的舞蹈创作日益强烈的“知性需求”。在似是而非的“新舞蹈”的舞种命名面前,我们不仅无法划定“新舞蹈”的圈地,而且难免使其盟友“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自惭形“旧”;其实,就“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的舞种命名而言,舞蹈创作者的精神火花也难以被“古典”和“民间”所定义。作为一种理论的思考,我想从首届《荷花奖》总决赛的“中国民间舞”的赛事启程……
一、中国民间舞的多界面与临界线
通过参加“中国民间舞”决赛的作品来透视评委们的抉择,我们可以看到评委们特别关注在不同界面上存在着的作品。中国民间舞评委组长资华筠特别强调要注意中国民间舞比赛中“多界面”和“临界线”的问题,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在决赛作品中(以群舞为例),《顶碗舞》是一个界面、《看看》是一个界面,《长调魂》是一个界面,《石头·女人》是一个界面,《东方红》又是一个界面……
仅凭直觉,人们就很容易判断《顶碗舞》是最接近“原生形态”的民间舞。这种“接近”,是指由职业舞蹈家编排、呈现在现代剧场环境中的《顶碗舞》,在基本步伐、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基本节奏型等舞蹈要素方面都接近该舞蹈在“民间”的存在形态——比如“压脚横移”的基本步伐,“牵裙移项”的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和“││:Dong.Da Da Da│Dong Da Dong Da:││”的基本节奏型就是如此。当然,由于从户外场地进入现代剧场,又由于是众多的职业舞者共同表演,《顶碗舞》显然在动作风格的修饰定型上、在群舞队形的组织编排上、在灯光布景的氛围营造上被艺术家“艺术化”了;使之近于“原生形态”又高于“原生形态”。
高于“原生形态”,其实是所有作为“创作舞蹈”的民间舞的共同追求;但不同的舞蹈编导对于“高”有着不同的视角;《看看》的编导是想在保持基本步伐、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和基本节奏型的前提下,倾注一股浓郁的民俗情趣;《长调魂》的编导是想将基本步伐、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和基本节奏型加以解构,根据自己对当代民俗精神的理解进行重组;《石头·女人》的编导是在谙熟民间舞构成要素后,从日常劳动生活中提取了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躬背侧倾的扛石体态,从“扛石体态”中生成一种或数种基本步伐,然后植入到一种较为普遍的民间舞节奏型(通常是“三步加”,详见下文。)中;《东方红》的编导则是抽取某些民间舞(“鼓子秧歌”和“跤州秧歌”)的基本步伐和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去塑造新的舞蹈性格和形象,其间对于民间舞构成要素的最大悖离是“基本节奏型”的悖离。
基本步伐、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基本节奏型这几个概念,是研究员资华筠通过“因子提取”来进行“舞蹈形态分析”所使用的概念;对于同一舞种比赛中不同界面上的作品,我们也可以以其各自的“因子变异”来说明。事实上,“民间舞”作为一定民俗境遇中的舞蹈,其基本步伐、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是来自一定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所促成的“原住民”的自然体态;不同民俗境遇中的舞蹈差异,根本上在于这种“自然体态”及其运动形态的差异。而“基本节奏型”作为“民间舞”要素构成的一个重要因子,却具有跨越具体境遇的特点——这就是“三步加”。“三步加”现象是关注并研究民俗舞蹈的老一辈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的发现。她通过对世界各地民俗舞蹈的考察,能列举70多种“三步加”现象,如维吾尔族舞蹈的“三步一抬”、藏族舞蹈的“三步一撩”、彝族舞蹈的“三步一弹”、汉族秧歌的“三步一回”等。实际上,“三步加”现象是由四步来构成一个“舞动周期”,第四步的变化意味着上一周期的结束(附随动)和下一周期的发端(预动);作为跨越具体境遇而存在的民间舞“基本节奏型”、“三步加”是应当为创编舞台民间舞的编导所关注的,这是民间舞编排最重要的节奏处理原则。所谓“临界线”,我认为最重要的便是“三步加”节奏处理原则;无论是解构“原生形态”舞蹈动作(如《长调魂》)还是将原住民身体动态定义为“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如《石头·女人》),恐怕都应考虑民间舞的“基本节奏型”,这首先是“三步加”。
二、历史文化精神与古典舞形态内质
在首届《荷花奖》总决赛的参赛舞种中,中国古典舞和芭蕾舞(应为“古典芭蕾”)都属于“古典舞”的形态范畴。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超越具体地域文化限制的,都是较长时期由感悟到总体民族精神的职业舞者来身体力行的;“古典舞”事实上是历史文明古国之历史文化精神在“身体文化”中的呈现——“中国古典舞”自不待言;古典芭蕾也应追溯到古罗马的历史文化精神。而中国古典舞和古典芭蕾的差异,简言之就是历史文化精神的差异。
在当代人的文化视野中,中国古典舞和古典芭蕾的历史文化精神已藏匿在冷却的舞蹈形态之后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中国古典舞圆融、周游的内敛型形态和古典芭蕾开敞、挺拔的外展型形态,形态本身的审美价值在许多情形已不需要内容的表现来支撑。说古典舞是“形式大于内容”既不夸张,也不贬损。想想《踏歌》和《旦角》成功的要义,你就能很容易明了这一点。《踏歌》和《旦角》,无疑是最符合“中国古典舞”定义的作品,但二者形态内质的依附仍有所不同:《踏歌》是为集种历史文化精神重塑形态外观;《旦角》则是借助中国古典舞的近世遗存形态来喻示一个习舞者的人生——在古典舞作品中,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近年来有《旦角》、《戏痴》、《戏娘》、《出科》是如此;往前还有《丝路花雨》中的英娘和《铜雀伎》中的郑飞篷。
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既然古典舞的形态内质在于某种历史文化精神,那我们怎样成功地实现其“现代转换”?对于古典芭蕾而言,更为困难的是在实现“现代转换”的同时还要实现民族文化精神的转换;否则,我们就只能看到如这次决赛中出现的情感类型化、性格抽象化、内涵虚幻化的作品。应当说,中国古典舞的创作,在其“现代转换”的进程中有较大的飞跃;自群舞《黄河》、独舞《江河水》而降,优秀作品川流不息。首届《荷花奖》总决赛中的《萋萋长亭》、《漫漫草地》也都在人们可以默许的形态范畴内展现出民族的现代文化精神。可以说,虽然我们还高举着“中国古典舞”的大旗,但这大旗已经插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以致于国内有人说这是“中国新古典”而海外有人说这是真正的“中国现代舞”。
还是想回过头来说说《踏歌》。在中国古典舞的多元化探索中,高金荣的“敦煌舞派”和孙颖的“汉魏舞派”都体现出对主流的“京昆舞派”的偏离。虽然取向有别,但都着眼于中国当代民族舞蹈文化的建设,自“京昆舞派”启程的“中国古典舞身韵”建设,通过对既往形态“行当专属性”与“语言描述性”的扬弃,在对民族时代精神的有效传达中使传统的形态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与之有别,“汉魏舞派”认为要改变中国传统舞蹈的“末代风气”必须去发掘“盛世气象”。《踏歌》作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溯寻,希冀重建中国古典舞开敞、明亮的舞风从而使中国古典舞的形态内质吻合于时代精神——这是一种不再压抑、不再拘谨、不再固守、不再因循的时代精神。
三、现代舞与新舞蹈的本体指向
虽然首届《荷花奖》总决赛空缺了“现代舞”,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舞种,它在赛事中已得到了确立。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界定“现代舞”与“新舞蹈”差异,凭一种朦胧的感觉,以为二者的差异有些类似于“古典芭蕾”和“中国古典舞”的差异——即“现代舞”是西方多种现代舞形态在中国的移植,而“新舞蹈”是依据中国当代生活和理念创生的舞蹈形态。二者的共同点有二:其一,一般地说来是“内容大于形式”,新形态的建构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堪内涵的重负;其二,都强调对传统舞蹈形态的偏离甚至是叛逆,但却不能在新的舞蹈形态建构上达到共识。正因为如此,“现代舞”和“新舞蹈”不象其他舞种那样可以从舞蹈形态范畴上去识别,共本体指向在于某种“观念”——一种“自由表达”和为这种表达寻求“形态自由”的观念。
但事实上,无论是“现代舞”还是“新舞蹈”建构的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没有传统舞蹈形态的痕迹;作为“新舞蹈”的《川江·女人》曾以“中国古典舞”名义参赛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留有传统舞蹈痕迹的作品并不妨碍其成为“新舞蹈”,那么就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古典舞作品《萋萋长亭》、《漫漫草地》和中国民间舞作品《石头·女人》、《东方红》也应当归入“新舞蹈”;其“创造性”在“新舞蹈”的舞种范畴内会得到更好的确认。这说明,在同一舞种内会有不同界面的作品,在不同舞种间则会有处于临界状态的作品。更确切地说,“新舞蹈”的参赛作品,有不少是对传统舞蹈形态“临界”状态的突破,是不受传统舞蹈内质所限定的形态,研究员资华筠称这类舞蹈为“非限定性形态”舞蹈。
其实,对于“非限定性形态”的“现代舞”和“新舞蹈”,也不是完全没有从形态上对其定义的可能。比如作为古典芭蕾叛逆者的欧美现代舞,珍妮·科恩就描述了其形态建构的倾向,即“强调空间的过程而不是目的,强调身体的重量而不是轻盈,强调韵味的顿挫而不是流动,强调构图的失衡而不是平衡,强调过程的提示而不是遮掩……”。我们的“新舞蹈”,不是“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其典型性显要部位动作,是对现实生活动作的提炼和加工;在其间,舞蹈动作的历史风格让位于现实生活。其基本节奏型,不是“三步加”的节奏复沓,也不是某种动作韵味的旋律展开,它是现实性格呈现时的“主题变奏”。其基本步伐,虽不乏对现实形象的关注,但也全方位地借用和改造作为历史文化传统的舞蹈形态。
说到此,我们已经接触到了首届《荷花奖》总决赛中“舞蹈分类”的某些实质性问题了。作为按舞种分类进行的比赛,我们的着眼点不是舞蹈的功能而是其结构;在舞蹈结构的视野中,又主要是形态结构而不是形象结构。在舞蹈的历史形态结构与现实形象结构之间,至少存在着三种关系,或是前者决定后者,或是后者决定前者,或是二者恰好找到某个锲合点。由历史形态结构决定现实形象结构的,属于“限定性形态”的舞种,其间又可以分为“古典的”和“民间的”两类;由现实形象结构决定历史形态结构的,属“非限定性形态”的舞种,现在的“新舞蹈”就是如此。很显然,作为比赛评判的准绳,“限定性形态”和“非限定性形态”是不同的:前者强调历史形态的约束力,后者关注现实形象有独创性,这就是为什么在金奖作品中,前者推出了《踏歌》和《顶碗舞》而后者评上了《走·跑·跳》和《天边的红云》。
在思考上述舞蹈分类的若干问题之时,我也在思考怎样的比赛规则才会有益于舞业的发展。我在想,中国舞蹈《荷花奖》的赛事是按舞蹈、舞剧交差进行的,舞剧大概会以大型、中型、小型来界分而不至于再冠以舞种的限定;那么,舞蹈的赛事可不可以按体裁而不是按舞种来进行呢?如此,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比赛分类可以粗分为“单、双、三”和“群舞”两大类。在两大类中,前者又可细分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这样三类;后者有两种分法:一是按群舞构成材料的量级,分为12人以下组和12人以上组;二是按群舞构成类型的差异,分为“情绪舞”和“情节舞”两类……当然,这种方式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好在舞界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首届《荷花奖》赛事中“舞蹈分类”及其命名的问题,好在有识之士们也认识到舞赛的进行是为了舞业的发展,那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和思考这一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