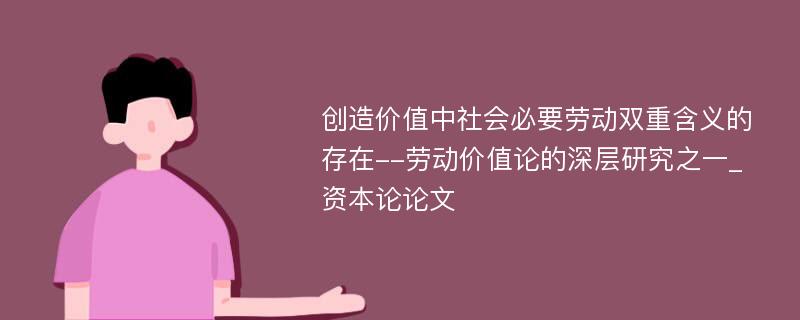
创造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两重含义的存在性——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层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价值论文,含义论文,两重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背景和当前态势
根据手头上掌握到的资料,在我国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论,从1956年起到1994年,大约经过四次比较大的回合(即50年代中后期、60年代前半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书刊上,至少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1]几乎每一位理论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人员,都关注这方面的讨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看法。
去年第五期《当代经济研究》,发表了辽宁大学宋则行先生的题为《对“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再认识》一文,预示着又一次讨论高潮即将到来。
这是因为,讨论双方都认为这里是“事关政治方向、事关重大原则”(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语)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科学的经济学还是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是唯物论辩证法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谁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任何禁止争论,压制争论的作法,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态度在不主张另一含义即所谓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论(以下简称“第二含义”)的人(以下简称“否定论者”)早就表明了。1995年第6期《当代经济研究》第68页一份关于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学会年会学术观点的通讯报导说:“通过讨论,多数代表认为,目前对劳动价值论的探讨,远远超出了广义狭义之争,而发展成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对此,《资本论》学会必须坚定立场,表明态度,在坚持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同时,对一些错误观点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给予澄清和回击。”报导列举了四种倾向,其中就把有的“将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联系起来”(这是否定论者责难肯定论者惯用的责难)与有的是“‘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有的是“直接违反劳动价值论原理”,有的是“故意混淆视听,制造矛盾”等倾向并列,是颇令人惊讶的。
而在此之前,1990年胡寄窗先生曾著文说,此一问题,是“非常严肃”、“绝对不能含混”的问题,第二含义把供给与需求引进来,是“十足的流通决定论,从而成为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观点。”[2]苏星先生则于1992年著文,含蓄地警告主张第二含义的人,在“在理论上很容易走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境地。”[3]在上述会议报导的几乎同时,1995年10月樊纲先生著文,则从另一角度批评第二含义,他硬说马克思自己和后来的研究者把“需要也决定价值”引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除非语病,我敢断言没有一个郑重的研究者会这样),结果使它“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他(马克思)“前门”排斥“需求决定价值”,而“后门”又“通过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让需求“进来”“也决定价值”,由于马克思价值论自己“发生不可解的逻辑矛盾”,又排斥100年来价值理论上其他人的“科学成果”,结果使“自己”“陷入绝境”。[4]
宋则行先生的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到了樊文“提醒”,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写的,用他的话:“是应该对这一个问题作一次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宋先生过去曾与第二含义的中国首倡者谷书堂先生有过合作关系,容允了合作作品中由谷先生加入的第二含义的内容,今天可要划清界限,表明自己的“立场”,反戈一击。迹象表明,批判第二含义可能也正在成为理论经济学新的热占和时髦。否定论者现在正要“对着风车作战”了,越疑神疑鬼就越象有神有鬼。
而主张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论者(以下简称“肯定论者”),那能甘心示弱,已经有人起而应战,说批评者“言过其实”,“不足服人”,并有栽赃之嫌:把“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出发”,得出了“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论,说成是“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出发”,得出的结论。[5]《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全国劳动价值论研讨会综述》的报导,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的关系”一节,看出从肯定的观点来论证的,也不是后继无人。
我也自命属于这种主张者之一。我承认那是受到1958年谷书堂先生在《学术月刊》上那篇文章的启发,由此我至今仍然保持对谷先生敬重的心情(但近年来谷先生在“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上出了格,我不敢苟同。这已是另一回事)。我写过几篇包含了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决定价值内容的文章,[6]则都受到已故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的鼓励与支持。一篇专论第二含义的论文(原题《关于宏观价值规律问题》,今天看可能取名“总产品价值规律问题”更为准确),则是在参加1983年在无锡召开的纪念孙冶方同志逝世的理论评论会上提供的,后来收入《孙冶方经济理论评论》,该文总结了我自己和其他同代人的成果,也因为还没有受到证伪科学的考验,所以至今我对它仍保持信心。最后一篇文章是《为‘资本论’+争生存权——我的‘资本论’今日价值观》,载于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7年4月17日)。《理论信息报》(3月16日)及其他内部和公开刊物,则把“马克思的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商品总量符合于社会需要量时所费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决定商品总价值及其每一商品价值”视为马克思的“均衡价格的价值基础”,并以此作为为《资本论》争取生存权的理论依据之二。由此看出,肯定论者也是从政治方向、从重大原则问题的角度,来看待第二含义的。据我观察,近年来,有些人大喊大叫,说《资本论》过时了,因为它没有研究资源配置理论,而一些《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者未能挺身而出,都是因为没有弄懂我们面前的这个理论问题。因此,它的最终解决,也许会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解上、应用上,引起一场对传统的革命。它会使价值理论从“实验室”走向大千世界,从苏式教条解脱出来变成日常生活的指导方针。
既然讨论双方都认为事关政治和重大原则,而是非判断又如此南辕北辙,大相径庭,那末,唯一的办法是继续开展大讨论,摆根据,讲道理,能统一认识就统一,不能统一就让后一代人接力争论下去。我不信,经济学上第二含义的争论就永远无统一认识的一天。
这次大讨论应该集中讨论和统一认识的有哪些问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个:1.究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无两种含义?2.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能创造价值吗?3.第一含义与第二含义究竟谁决定谁?4.第二含义只是与价值实现有关吗?5.否定论者失误根源在哪里?6.并非概念之争。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就前两个问题提出我的看法。
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有两种含义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究竟有没有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作出两种规定,这的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九十年代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持否定的看法。以最近的宋则行先生的文章为例。他说,重读《资本论》以后,他发现:“只存在一种含义(而不存在两种含义)”、“所谓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所谓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者同一含义,都是指在现有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某种商品的生产与社会需求总量一致时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不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而只有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只是《资本论》第三卷中明确点明了商品供求总量一致这个前提,而在第一卷中只是隐含着这个前提而已“[7]。胡寄窗先生早在前述论文中,也从“社会”二字,判定两者“都是同一种社会必要劳动。”
宋先生是在用马克思对两种含义重合时的表述,以取代马克思对两种含义分别作出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规定。而后一种表述,并非偶尔,而是大量,且更明确。我只举出其中四例。
“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一切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引者注:“所影响的”一词译文不如1953年郭大力、王亚南译为“所说的”更为确切,英译本为"with reference to",见第745页,没有“影响”之意)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相互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社会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引者注:“特定数量的”译文不如郭、王译为“数量上已经规定的”更鲜明),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虽然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只体现了一定条件下为生产这个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引者注:此句译文有误。郭、王译文为:“虽说在棉织品的总生产量中,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它必要的劳动时间实现在里面”。这意思是:虽然总产品的每一件都是由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所生产,它是指的第一含义的劳动。而《全集》译文则有第一含义与第二含义相结合的意思。实际上,第二含义是后面才要讲的)。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已经过多;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因此,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引者注:这句话译文又完全失真。郭、王译文为:“所以,全部只能照生产保持着必要比例的时候一样出售”,这准确。因它与即将要引证的“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所说的话相同)。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引者注:“整个价值规律”郭、王译为“价值法则一般”,后者准确。英译为"law of value in genenral"。一般与抽象相似,而“整个”与个别相对立。不能将第一含义当作整个规律看待,第二含义当作个别规律看待。事实恰恰相反)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8]这一大段引文正如苏星先生所云,只要“认真读一读,有些争论就可迎刃而解”,不过结论会恰和他相反。
“在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如果1码麻布的价值只等于1小时,并且这就是社会为满足自己对1码麻布的需要所必须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由此还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如果生产1200万码麻布,从而花费1200万劳动小时,或者同样可以说,花费100万工作日,使用100万工人来织麻布,那末,社会‘必须’花费在麻布织造业上的,就正好是社会劳动时间的这样一个部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已知,就是说,一日内所能生产的麻布量已知,那还要问,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日数必须花费在麻布生产上……。虽然产品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象它不断打乱这种分配一样。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降低多少,总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如果原来生产4000码,现在生产6000码麻布,而6000码的价值是12000先令,那么它们还会按8000先令出卖。每码的价格将是1(1/2)先令,而不是2先令,即比价值低1/3。可见,这好比在每码的生产上比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多花费了1/3。因此,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已定时,商品的价格降低到商品价值以下的事实证明,虽然花费在产品的每一部分上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假定生产条件不变),但花费在整个这一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总量过多了,超过必要量了。
由生产条件的变化引起的商品相对价值的降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已经在市场上的这块麻布,过去值2先令,假定等于1工作日。但是现在,每天能用1先令把它再生产出来。因为价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决定于个别生产者要用的劳动时间,所以,生产者生产1码要用的1日,只等于1个社会规定日的一半。他的1码麻布的价格从2先令降低到1先令,即一码麻布的价格降低到他在这块麻布上花费的价值以下,这不过表明生产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表明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如果麻布的生产费用不变,而所有其他物品,除了金即货币材料以外,生产费用都提高了,……,一句话,一切不加入麻布组成部分的物品的生产费用提高了,那末1码麻布就仍然等于2先令,它的价格不会降低,但是它以小麦、铜等表示的相对价值降低了”[9]。这里讲了使市场价值或相对价值降低的三种情形,其中包括了花费在一个部门的总劳动超过社会必要水平这一为我们现在正在争论的情况。
“社会分工使商品所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所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保证他的20码麻布就有使用价值。社会对麻布的需要,象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商品是无用的了。……。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证明自己有使用价值,因而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业的许可而在他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仍然可能包含耗费过多的劳动时间。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在市场上,全部商品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化身。”[10]。读者也许对以上引证马克思论述两种含义的文字会嫌太多。但这是为了给读者以系统的印象,同时也为了在后面涉及上述引文时,只提示一下出处,省去再引原文的麻烦。
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84年10月在他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指出:“洛贝尔图虽然也用两句话提到一下劳动强度的差别,但劳动还是非常一般地当作耗费的东西,因而是当作度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付出的……。他的劳动时间是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产品和社会需要的数量上呢,还是费在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上,或者虽然需要却在数量上比需要的过多或过少,……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形式,怎样创造了价值,从而决定和度量价值,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说,不论就它对社会总的需要说都是必要劳动。”[11]
综合以上四例,可以看出,社会必要劳动的两种含义的区分,是十分明显的。在研究对象上,一个是指单个商品(个量),一个是指商品总量(总量);对个体来说是如此,便据引而认为对整体来说也是如此,这叫“合成推理的谬误。”[12]在必要劳动形成的前提条件上,一个只要求生产使用价值,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一个不仅要求能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求能生产有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总量。在必要劳动的本身内容上,一个是指耗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平均劳动量,是对不同生产条件而言的,一个是指耗费在生产满足社会需要总量上的劳动量,是对生产规模而言的。在逻辑学上,两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的关系,光有必要条件而无充分条件还是不行的。在辞义学上,两者关系被概括为“不仅”与“而且”、“虽然”与“但是”、“即使”与“仍然”的关系。这些关系表明一种递进关系、侧重关系、并列关系,并非两者同一的关系。
这些不同,在经济学上都渊源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不同。一种竞争是属于部门内不同生产条件者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使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的劳动量,成为社会公认的标准的劳动,此即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另一种竞争是一个部门总产品的生产者、供给者与购买者、需求者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使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总劳动成为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此即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13]离开两种不同的竞争,就使上述种种区分成为不可理解,变成为先验的神喻的产物,或一种主观任意规定。许多误解,由此产生。
由此可见,不管从那一方面看,两种含义是不能混成一团、合而为一的。
当然,两者在运动中可能交叉、重叠。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但重叠不等于取消各自的独立性,正象物理上合力不能取消分力一样。
宋则行先生论证两种含义关系避开引证上述任何一处,而独独挑出《资本论》第三卷第722页,那里讲商品价值是由“在当时的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以证明只有一种含义,不存在两种含义。实际上这正是两者处于重叠时的情况。也是第一含义在实现为价值时不受第二含义的修正(打折扣或提升),第二含义实现为价值时不给内部成员带来盈亏的不平等后果,因而是两种含义都进入最佳状态时的表述。宋先生批评两种含义说,主张一种含义说,实际上是在用两种含义共同决定批评两种含义共同决定。
二、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不创造价值之说是不妥的
卫兴华先生在其论文《价值决定和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吗?”他的结论是:“价值只能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能同时或只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14]这样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简直把劳动价值论搞神秘化了。
所谓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生产社会需要的商品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它为什么不能创造价值呢?它是总劳动,也是实实在在的。除非它被浪费,除非它创造的使用价值超过了社会需要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的确存在劳动不能创造价值的问题。但在我们的场合,第二含义概念本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实际上,商品交换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是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分工。因此商品交换首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部门与另一个部门的商品交换。价值理论正是用来回答部门间商品交换比例的最终依据和尺度的。请看,马克思是怎样讲部门总劳动决定总价值的:
“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的全部价值中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15]
“事实上,每一码麻布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16]“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17]
“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18]
“商品(它是某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为生产这个生产领域的全部商品量即商品总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不决定于这个生产领域内部单个资本家或企业主所需要的特殊劳动时间。[19]
“竞争—……—在这里就导致这样的结果:某个特殊生产领域的每一个个别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个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商品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而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20]
“单位商品的价值(价格)等于产品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总量。”[21]
“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出来的商品,与我们据以出发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商品不同。现在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并使个别产品成为商品的,不再是花费在个别的特殊的商品上的劳动时间(……)而是总劳动,总劳动的相应部分,即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得出的平均数。”[22]
“以较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交换价值”,“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如果我们说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特殊的单独的劳动部门就表现为必要的。”[23]
“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这样来决定的(价格涨落相互抵销——引者)。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24]
以上略举十例,足以证明生产社会必需商品总量的劳动(即第二含义劳动)不仅可以独立、应该独立决定商品总价值,而且单个商品的价值乃是由这个价值派生(“分摊”)而来。
卫兴华先生非难第二含义劳动价值的理由是难以成立的。
卫兴华先生理由之一是:“当商品量小于社会需要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怎么能由这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劳动时间决定呢?说由它决定,实际上就是说由供求关系决定。”这种责难,只要用以下反问题就可以回答。当价值由第一含义劳动决定时,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优等生产条件的生产者来说,也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别劳动时间。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用“现实中不存在的”第一含义劳动决定价值呢?说由它决定,是否也是因为他提供了同社会必要劳动所提供的同样商品及其使用价值,因而就是效用价值论呢?其实,之所以能如此,那是由于市场竞争的缘故。在价值由第一含义决定时,“竞争”使得“在比较有利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同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相比,包含的劳动较少,可是却按同一价格出卖,具有同一价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它实际上并不包含的同一劳动时间。”[25]同样,在价值由第二含义决定时,“竞争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26],使得在商品量小于社会需要,现实中的总劳动量小于应该分配的总劳动量时也能按照应该分配的总劳动量来出卖。这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同样是实际的劳动低于社会必要劳动,同样存在竞争的环境,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按照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没有理由说不可以的。[27]实际上,所谓决定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也正在这里。不懂它就不算真正懂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卫兴华先生理由之二是:“当产量大于社会需要”、实际总劳动量超过第二含义的社会劳动量,同时“假定每个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时“价值除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外,怎么还会同时再由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呢”?“它只是决定价值实现的程度”。卫文还举了计算例证。这是一个老的辩难。其根源在于对“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即《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235页关于另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段述的不同理解(这个问题本人将在《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层研究之二》,以下简称“之二”中探讨)。现在只要指出,卫文这样的理解,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在假定的条件下,第二含义就是要对第一含义起校正、修改的作用,就是要给它再打折扣。因为,这时,作为价值形成的前提的使用价值规模已经超过标准,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本身超过了标准,而超过这两个标准的社会劳动时间是怎么也不能形成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的。马克思在本处已经讲明,此时商品的“价值”,只能“按应该分配的”劳动时间(即第二含义的),而不应由“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第一含义的劳动量乘总产量)决定。《资本论》第一卷第126页讲了此时“其结果就象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超过了社会必要时间一样。这正象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这就是说,大家都来分担价值形成中的损失。如果说这里只是价值实现问题,那就和第一含义上的超标结果不“一样”了,那就要还活着再跑一段路程或逃脱刑场了。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卫兴华先生理由之三是:“如果供求一致,……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总量上相等,……。这似乎是由两种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其实,仍然是由第一种含义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第二种含义必要劳动时间不能再起另外的决定作用。两种必要劳动时间相重合,只能决定价格同价值相一致,即价值全部实现而已”。
事实上,这种重合正表明两种作用的交叉,决不是一种劳动的作用是价值决定,另一种劳动的作用是价值实现。说一种劳动的作用只决定价值实现。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通的。劳动只有直接变成价格,才能谈得上是实现(在卫文的意义上的实现),但劳动如果不通过形成价值,又怎么能变成价格呢?说有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本身根本不创造价值,这本身也是费解的。第二含义社会劳动,也是劳动,它既不是生产废品,也不是生产的商品超过了社会需求量,怎么不创造价值呢?莫非两种劳动象化学上两个元素放到一起,就起化学变化,变成第三种物质?!莫非有一种魔术能把它变成幽灵般的存在?!说只有第一含义起决定作用,不需要第二含义另再起作用,这本身就有些奇巧。因为第一含义按其定义本身来说是指生产单个商品所费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简而言之,是平均数,试问,这个平均数从何而来?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底冒出?这不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实际上,平均数只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关于这个问题,在“之二”还要谈到。
作这种论断的文章本身,本来也承认“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离不开对整个部门总产品的劳动消耗和价值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不过是总产品的价值总量的可除部分。”可是后面又说,只有总劳动的可除部分,即他所指的第一含义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可除部分”的发源地总劳动自己却不能。这不是自己同自己矛盾?!
注释:
[1]1956—1982年的文章请看《经济研究》1982年第1期第18页谷书堂、扬玉川文章脚注的统计。此后,《经济研究》1983年第3、12期,1984年第1期,1986年第3期,1988年第7期,1989年第2期,1990年第3、8期,《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1994年第5期,以及《湖南财经学院学报》、《湖北大学学报》、《兰州学刊》、《南京社会科学》、《江汉论坛》等期刊。还有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都发表过此问题讨论的文章和论著。
[2]《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第37—39页《社会必要劳动不存在两种含义》。
[3]《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4]《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苏联范式”批判》。
[5]何炼成:《也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6]见《光明日报》1964年7月6日《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没有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中国经济问题》1979年第6期《从质与量的统一看价值决定的含义》、《经济研究》1981年第8期《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存在依据的再认识》、《武汉学刊》1991年第6期《论价值规律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关系——兼论价值规律的作用》(此文为1959年3月我参加某大学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学术讨论会的发言稿,经整理后,曾寄请孙冶方同志批评,孙老曾推荐与《经济研究》,后因故收回,1991年重新发表)。
[7]《当代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第3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25卷第716—717页,这一段由《全集》编译局于1974年11月出版的译文,竟有五处修改了1953年的郭大力、王亚南译本,其中多属把本来明确的变成模糊的,有的则属曲译,其用意似在避免读者由此激发出价值规律必然调节生产的强烈意识,足见“文革”之风无处不及。
[9]《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234—237页。
[10]《全集》第23卷,第124—126页。
[1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12]人们举例看球赛,一个人站起来,看得清楚。当所有观众都站起来,反而看不清楚了。量变到一定点引起质变。
[13]在市场经济中,还有第三种竞争,这就是各生产者(厂家)为争取获得平均利润的竞争。但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
[14]《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第49—51页。
[15][16]《全集》第23卷第52页、126页注文。
[17][18]《全集》第25卷第203、205页。
[19]《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第226页。
[20][21]《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第228、294页。
[22]《全集》第26卷第三分册第120页。
[23]《全集》第46卷下册第18页。
[24]《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3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5]《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第228页。
[26]参阅《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235页。
[27]社会上,市场上承认的价值与生产者实际形成的价值(个别价值),有多有少,不相一致。这是商品经济中“异巳”力量的表现。市场功能的长处和短处都在这里。
标签:资本论论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文; 商品价值论文; 价值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