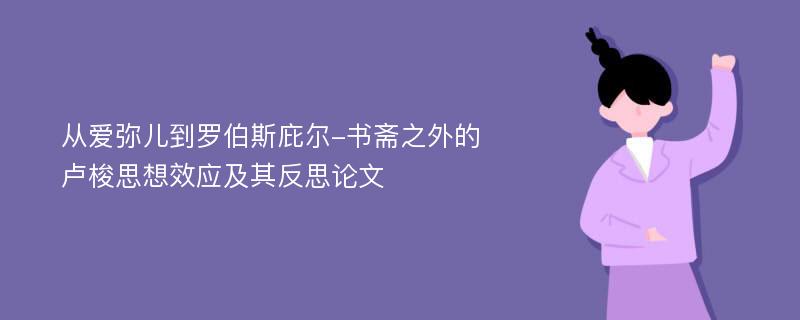
从爱弥儿到罗伯斯庇尔
——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及其反思
胡君进
(上海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 《爱弥儿》不只是一部教育论著,更是一部政治论著。《爱弥儿》一书的最大政治性特征就在于,卢梭试图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位立法者。由于卢梭旨在让爱弥儿成为公民群体中那个最为特殊的立法者,这使得在爱弥儿身上发生的教育自始至终都带着强烈的政治性倾向。而这个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形象,最终得以人格化和现实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面对这样一种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除了要认清爱弥儿式教育具有极端放大教育政治功能的潜在危险,更是要看到其本质上是一种反民主性质的精英教育学。为此,现代社会需要建构一种民主情境的制度教育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卢梭式爱弥儿教育的内在超越,以推动现代教育的合理发展和稳健转型。
关键词: 爱弥儿;立法者;罗伯斯庇尔;精英教育学;制度教育学
卢梭的《爱弥儿》是现代教育思想建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许多研究者往往将《爱弥儿》这样一部欧洲十八世纪教育小说的问世看成是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哥白尼革命”,认为《爱弥儿》一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儿童作为教育研究的关注对象和独立个体,这在客观上促使了教育重心从成人转向儿童。然而,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倾注的复杂情感、隐微教诲以及真实写作意图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深入来看,卢梭并不只是试图将爱弥儿培养成“自然人”,而是赋予了爱弥儿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身份,即“立法者”。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形象也最终得以人格化和现实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也正是如此,卢梭的《爱弥儿》并不只是引发了教育思想史意义上的革命,而更是与真实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潜在的血缘关系。深入分析、挖掘这样一种从爱弥儿到罗伯斯庇尔之间的意象联系,有助于深化当前学术界对于卢梭教育思想的诠释和理解,继而进一步推动丰富、多元的卢梭教育思想研究图景的形成。
一、爱弥儿的立法者面孔:卢梭的真正教育意图
《爱弥儿》的副标题是“论教育”,这使得《爱弥儿》看起来是一部教育著作。当然,卢梭论述教育的著作很多,在给百科全书派写的小册子《政治经济学》中就有专门论述教育的内容,而在《波兰政府改革方略》里更是有直接以“教育”作为题名的章节。然而,《爱弥儿》与之不同的特殊地方在于,它不是针对整个民族的公共教育而言的,它的适用语境只限于一个人的教育。而且有一个细节需要我们注意,在《爱弥儿》正式出版的时候,卢梭有意在自己的名字“让-雅克·卢梭”前添加了“日内瓦公民”这几个大字。而在1761年发表的《新爱洛伊丝》第二版的前言中,卢梭曾这样写到:“日内瓦公民”的字样仅仅用于可以被称作政治论著的书的标题页中。[1]可见,在卢梭的心目中,《爱弥儿》绝对不只是一部教育论著,而更应该是一部政治论著。甚至在卢梭的整个写作计划中,《社会契约论》只不过是《爱弥儿》的一个附录而已。[2]45而且卢梭在后来的《山中来信》里也曾反复提醒读者:《爱弥儿》并不是为广大公众写的书,许多人把《爱弥儿》看成是一本供家长教育孩子的指南,这其实完全误解了他的本意。《爱弥儿》其实是“一种供圣贤之士探讨的书”。[3]因此,根本就不能仅仅从表面上把《爱弥儿》看成是一本家庭教育小说,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卢梭的真实用意,而应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进一步理解《爱弥儿》。在这里,通过对卢梭各种文本的反复琢磨,以及对卢梭微言大义式写作手法的充分把握,我们认为卢梭并没有将爱弥儿当成一个普通的自然人来对待,而是赋予了爱弥儿一个最为特殊、最为重要的身份:立法者。[注] 卢梭试图将爱弥儿培养成立法者的问题一直尚未得到国内教育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大多数的学者往往只是以单纯教育学的眼光来看待爱弥儿身上的教育,而对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所倾注的复杂情感和隐晦意图有所忽视。对此,刘小枫、刘良华等学者曾对《爱弥儿》一书中高度复杂的文本结构和微言大义的写作方式进行了探究,并指出卢梭的真正教育意图可能在于将爱弥儿培养成《社会契约论》中的“立法者”。(可具体参阅:刘小枫.《爱弥儿》如何“论教育”——或卢梭如何论教育“想象的学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刘良华,曾世萍.卢梭的教育意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1).)然而,这些认识并未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回应,依旧处于当前卢梭教育思想研究的边缘。鉴于此,本文在充分吸收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进一步将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与法国大革命期间作为人民领袖的罗伯斯庇尔进行意象勾连,并对这样一种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希望能表达一点管窥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这个“立法者”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复提及的那个能够为本民族及国家创制、重新塑造民情风俗和道德风尚的“非凡人物”。而只有将“立法者”作为爱弥儿整个教育历程的目标期许,才能真正勾连起《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使得《社会契约论》真正成为了《爱弥儿》的注脚或附录。为了充分论证“立法者”是爱弥儿的真实面孔,我们将结合《爱弥儿》中具体的文本依据来加以佐证。
控制弹性系数α,β都为常量,令p0-v+g-cr-cd-λ1>0,当NG(q)>Q*时,供应链期望收益可表示为
(一)爱弥儿:一个特殊的学生
首先,爱弥儿在卢梭眼里,始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生。在《爱弥儿》中,卢梭就曾多次提醒读者,爱弥儿身上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性。在第一卷的一开始,卢梭就点明“爱弥儿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儿童,必须对他采取一套特殊的教法”[4]33;在第二卷中,卢梭这样评价爱弥儿:“我们可以说,连大自然都在听他的命令,因为他知道怎样使一切事物都服从他的意志的指挥。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去领导和管理他的同伴:他的才能和经验,可以代替他的权利和权威。随你给他穿什么衣服和取什么名字都可以,没有什么关系;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超群出众,都可以成为他人的领袖”[4]230-231;而到了第三卷,卢梭再次提醒读者,“爱弥儿并不是一个平庸的人,真实的爱弥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任何人想学他的榜样也是学不会的”[4]276;而在第四卷,卢梭又重新强调,“爱弥儿将培养成一个跟世人完全两样的人,你可以把爱弥儿看作一个可爱的外邦人”[4]547。这些细节都反复向读者提醒甚至是叮嘱这样一件事情:爱弥儿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
其次,就连“爱弥儿”(Emile)这个名字都是卢梭有意选取的。受柏拉图的影响,卢梭认为在给一个事物命名的同时就等于在表明这个事物所具备的天性,因此不能轻易取名。[5]卢梭之所以要将想象出来的学生命名为爱弥儿(Emile)或是艾米利斯(Aemilous),其背后其实有着特殊的隐晦含义。表面上看,“爱弥儿”这一名字意味着“勤奋的”,但这个名字还能引起其他一些联想。卢梭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书信里表达过对《卡托之墓和艾米利斯的文化遗址》(Tomb of Cato and the ashes of the Aemilians)一文的崇高敬意,其中的艾米利斯是谁?根据研究发现,艾米利斯就是那个被世人视为古罗马最聪明的立法者努马·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的儿子,而艾米利斯家族的人正是作为光荣的罗马爱国者自兹延续的。[2]83可见,卢梭之所以将“艾米利斯”作为自己学生名字的拉丁词源,就是希望爱弥儿可以成为这个家族中的一员。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就把雅典的梭伦和罗马的努马看成是伟大的立法者,他们都曾为各自的民族设计了一套特定的法律。因此,卢梭似乎通过“爱弥儿”这个名字来告诉世人,倘若爱弥儿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可以尽可能地与这些先贤们接近的话,那么这将会最大限度地保证爱弥儿教育的本质特征,以及让作为导师的卢梭自己充分实现个人的教育目的。因此,靠近先贤,或者说培养“立法者”,既是卢梭为爱弥儿取名的最初用意,也是卢梭想象出教育“爱弥儿”这一学生的潜在教育目的,亦是《爱弥儿》一书起笔的真实原因。
(二)立法者:从《爱弥儿》到《社会契约论》
思想家个人的愿望往往与历史现实呈现出一种悖谬的反差,甚至是一种令人惊悚的恐怖。爱弥儿的“立法者”面孔并没有如同卢梭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重建本民族道德风尚的英雄,反而被现实化为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而“立法者”在被道德化和神圣化的同时,也必然意味着要发生一场恒久的道德改革乃至政治革命。而就卢梭的这种培养“立法者”的教育意图而言,无论其是否存在能够被转化为政治动员的可能性还是就其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而言,在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一种阿尔都塞所谓的“向意识形态逃遁”的倾向性。因为“立法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整个政治结构向天撑起的供心石,本身就需要天国,或者说宗教意识形态。这真是一种理论自身的“错位”,而这一“错位”由于先于现实事物本身,因此不得不把其中的那些难题和解决方法都赶到了该理论难以解决的地方。[26]为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爱弥儿教育的政治性倾向给予更为细密的解释和反思。
此外,能否培养出“立法者”,是卢梭非常在意的事情。用卢梭自己的话讲:“我遍观当今的世界各国,会起草法律条文的人多得很,但真正称得上立法者的人,却一个也没有”。[8]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立法者”呢?在《社会契约论》中,“立法者”除了是指那些能为本民族或国家创制的人之外,卢梭还做出了这样一个界定:“敢为一国人民创制的人,可以说是一个自信有能力改变人的天性的人”[7]45,“他能把每一个本身是完整的和孤立的个人转变为一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使他按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更大的整体中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并改变和增强其素质,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的有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得自自然的个人身体的独立的存在”[7]45。很明显,立法者的一个重要工作或职责就在于将人从自然的存在转变为伦理的存在,而这个工作恰恰就是卢梭在《爱弥儿》中作为爱弥儿导师所需要开展的教育活动。这种改变人的天性,将人从“自然人”转变为“公民”的神奇力量其实就是卢梭为爱弥儿量身定做的教育本身。[9]可见,《社会契约论》中的“立法者”就相当于《爱弥儿》中的“导师”,只不过立法者面对的是人民,而导师面对的是一个学生。在这里,抽象意义上的人民就被具体化为“爱弥儿”一个人,而作为爱弥儿导师的卢梭似乎就如同立法者。[10]而“立法者”卢梭作为爱弥儿的导师,显然一个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将自身“立法者”的潜质继续传承下去或重新生产出来,而这个传承和生产的对象就是爱弥儿本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社会契约论》是在具体探讨最佳政体及其法律制度,那么《爱弥儿或论教育》就可能是在探讨怎样培育最佳政体的立法者。[11]
(三)立法者的教育:普鲁塔克与色诺芬
在卢梭的教育意图以及政治筹划里,爱弥儿以“立法者”的身份进入到社会里面,则需要通过社会契约。社会契约一方面组建人民主权政体,另一方面实现单个公民的道德自我立法。这是因为“卢梭把通过社会契约来构成人民主权想象为一种生存方式性质的结社行动,通过这种行动,个体化的、取向于成功而行动的个人转变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取向于共同福利的公民。作为一个集合性实体的成员,这些公民融合进一种断绝了与仅仅服从法规的私人的个体利益之间的联系”[22]125。可见,社会契约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意味,其对于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一个公民都提出了自我道德立法的伦理要求,并把这种要求放到最高位置。而“公民的自我立法的观念,要求那些作为法律之承受者而从属于法律的人,同时也能够被理解为法的创制者”[22]147。因此,对于爱弥儿而言,他并不仅仅只是个体意义上的道德立法,而是伦理意义上的政治立法。也就是说,在卢梭的社会契约里,爱弥儿作为一个特殊的公民,其并不仅仅只是法律的遵守者,同时也是法律的创制者。而这样一种立法意志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罗伯斯庇尔等人提升为一种爱国主义形式的革命激情。这种革命激情恰恰成为了维系一个国家得以存在最为关键的东西,其亦是成为了其他所有美德的源头。作为一种特殊的情感,革命激情并不只是简单形式的政治激情、政治承认和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追求,而是一种爱国主义形式的政治美德,它透露着公民内在地将国家视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强烈情愫。[23]正如卢梭自己所言:“可以肯定的是,美德所具有的最伟大的神奇一直是由爱国主义造成的:这一美好而可爱的感情因为赋予了自爱的力量以美德所具有的一切美而使它具有了活力,而这种活力能够在不损害其形象的同时又使它在所有的热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象”[24]350-351,而“国家作为一种首要的道德化力量,因而也就代表了最高的道德价值。个人乃是从国家中获致其精神的和道德的能力的,而且也正是由于国家,他们才成其为人;基本的道德范畴是公民而不是人”[24]343-344。也因此,在一个结构混乱的大革命中,从立法意志走向革命激情的卢梭式思想就非常容易滑入集体主义性质的政治动员模式,成为革命者寻求群众支持的政治工具。而这一点,正是罗伯斯庇尔在卢梭思想中所最为看重的革命潜力。
在卢梭的教育意图里,爱弥儿是公民群体中那个最为特殊的“立法者”,这使得爱弥儿身上发生的教育始终要区别于社会大众。换言之,爱弥儿作为那些天生就具有优良品质的少数人,注定了其身上的教育要与普通人不同。因为在卢梭心目中,爱弥儿是那个“自信有能力改变人的天性的人”,是那个能够为本民族重建道德风尚、制定法律法规的“立法者”,这也意味着爱弥儿始终是人群中的一个英雄,或一个领袖,乃至是一个神明。用现代的眼光看,爱弥儿是一个精英,而且是一个具有克里斯马(charisma)气质的政治精英。由此,爱弥儿身上的教育就不应该是大众性质的,而是政治精英性质的。而正是由于这一点,爱弥儿身上的教育就带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性倾向。也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性倾向,使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不再只是限于教育领域,而是与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难以割裂的联系。法国大革命可谓是顺着卢梭思想的节奏而逐渐演进。[15]其中,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形象,也最终得以人格化和现实化,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卢梭的教育思想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引发革命的炸药,成为了暴力之母。因此,从客观效果上看,卢梭心目中的立法者教育其实并未得到具体的实现,反而被利用为一种崇拜革命领袖的的政治动员。而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式爱弥儿的道成肉身,是立法者教育在书斋之外的思想效应。
其次,卢梭的《爱弥儿》一定程度上是在仿照色诺芬的长篇政治教育小说《居鲁士的教育》(On the Education of Cyrus)。正如卢梭在《爱弥儿》第一卷正式引入“爱弥儿”这个想象的学生之后,曾对爱弥儿的教育内容进行过说明:“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要教给孩子的,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4]34-35。接着,卢梭说了一段经常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视的话:“不管当年色诺芬对有关波斯人的教育曾经说过什么,这门学科是一个整体,是不能被分割的。此外,我宁愿把教这门学科的老师称为导师而不称为教师,因为问题不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怎样做人”[4]35。在这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卢梭的“导师”身份上面,而忽略了在卢梭眼里曾经有人已经做过与之类似的“导师”工作,而这个人就是色诺芬。很显然,卢梭非常清楚这一点,并潜在地将当年色诺芬对于波斯人的教育作为爱弥儿教育的一个重要参照。而这个重要参照则充分体现在色诺芬撰写的《居鲁士的教育》之中。该书以波斯居鲁士大帝作为主人公原型,记载了他的教育历程、言行、谋略以及最终缔造波斯帝国的事迹。西方古典学界往往将这本书视为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以及第一部教育小说。[13]对于深谙古希腊作品的卢梭而言,自然能够准确认识到《居鲁士的教育》一书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将自己对于爱弥儿的教育意图与色诺芬进行对比。而在色诺芬笔下,居鲁士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者”,是“应当在别人眼中成为活的法律”。[14]因此,当卢梭潜在地将自己的“导师”身份与色诺芬进行对比时,那他就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学生爱弥儿与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大帝进行一次潜在的对比[注] 需要注意的是,《居鲁士的教育》与《爱弥儿》一样,都是小说体裁性质的作品,换言之,都是虚构性的故事。色诺芬其实旨在通过这样一部历史小说来阐明自己心目中一个理想君王理应具备的素质、才干和技巧,旨在提供当时希腊城邦陷入危机的解决路径。因此,虽然是一部虚构性的小说,但其实服务于一个极具政治性的现实目的。而反过来,同样深谙此类写作手法的卢梭,极有可能将爱弥儿视为与居鲁士相类似的“立法者”,并故意三缄其口,而只是提供一个有待“智识之士”思索的镜鉴。 。
二、作为革命者的罗伯斯庇尔:书斋之外的卢梭思想效应
为适应当今高新技术的发展,应结合目前机械自动化方面的问题已经当今社会的发展进行一系列的改进,确保机械制造自动化技术长久健康的发展。
铁锅易生锈,并且它在生锈过程中会释放对人体有害的物质。炒菜长时间放在锅里,会导致这些有害物质进入食物,成为身体健康的一大隐患。
(一)道成肉身:从立法者走向革命者
2.巴基斯坦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在路线选择上。巴基斯坦政府在规划经济走廊路线时充分考虑了各方的利益诉求,推出了多路线方案,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从根源上减少某些“变相恐怖主义”的袭击。
罗伯斯庇尔充分接受并领会了卢梭对于爱弥儿作为“立法者”的职责期待,即不仅要教会民众公民美德的原则,而且要让民众理解那种建立在公民美德基础之上的统治国家的崇高艺术,也就是所谓的“人民主权论”[注] 在对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身上,卢梭发现了人的“自爱”和“同情”这两类原初情感。尤其是“同情”,卢梭认为这是形成人的内在良知、形成一种正确对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情感基础。而“同情”这一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亦是大放异彩,甚至连“人民”这个词都是由“同情”所产生的。在大革命中,“人民”这个词并不是指参与政治事务的公民,而仅指下层群众,其成为了不幸和悲苦的代名词。而当“人民”被狭隘化至底层人群、边缘群体时,对这一群体的同情,就是一种不愿意见到不公正现状而产生的情感关切。故而若是没有考虑到“同情”在法国大革命进程的筹划者和行动者心目中起的关键作用,就无法理解为何大革命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群众基础。正是基于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由此也成为一种情感政治,同情成为了政治生活的规则,成为了革命的动力。而那些代表人民的革命者,他们个人行动的正当性,就在于跟广大底层群众一起受苦的能力,伴随着这一正当性的是那种把同情心升华为无上的政治激情和最高政治美德的意志,而这其实是整个法国大革命的道德主义基础。然而,在卢梭的《爱弥儿》中,“立法者”的身份其实仍旧与人民群众有着一定的距离;而只是到了罗伯斯庇尔那里,“立法者”的道德意涵却直接源自人民群众。在罗伯斯庇尔看来,法国大革命似乎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撕毁法国上流社会的伪善和奢靡,打破极度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露出底层人民淳朴、诚实的面庞。(参阅: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62-67;黄璇.情感与现代政治:卢梭政治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4.) 。具体而言,就是作为一个“立法者”,他有责任将“人民”提炼为一种自然神论意义的崇拜对象,并相信人民天性善良,继而将人民的统治权和共同意志转化为一种道德化的政治术语。[20]这正如大革命前夕罗伯斯庇尔在公开演讲中所强调的:“政治的目的必须是道德在政府中的具体化;道德,或美德,来自人民,并且只来自于人民;因此,道德是人民的意志而非不可靠的腐朽的统治者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必然至高无上,压倒一切”。[6]171“我告诉大家,我已经理解了让-雅克宣布的这一伟大的道德和政治真理,那就是,人们永远也不会真心爱那些不爱他们的人,只有人民是善的、公正的、宽宏大量的,腐败与专制是那些蔑视人民的人的特有属性。”[6]176可见,在罗伯斯庇尔这里,“人民”作为政治实体,实现了同质化和无差别性,那种由人民作为主权者的国家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情感融合的国家。这种融合是作为“立法者”的自己和作为“统治者”的人民之间的情感外延的融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伯斯庇尔才会说:“我既不是人民的弄臣,也不是人民的仲裁者和保护者。我自己就是人民!”[6]178而这就是罗伯斯庇尔各种政治举措后面的卢梭式逻辑,一种高尚而危险的政治逻辑:“人民是美德的化身,我是人民的化身,因为我就是美德的化身。因此,所有与我为敌的政治分歧和对抗只能有一种判断:他人在堕落,他人在犯罪。”[21]于是,所有的政治斗争都被转化为了道德斗争,罗伯斯庇尔也因此确定了他在制宪会议以及在国民公会中的角色,其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代表”或一个“代言人”,而是作为一个“立法者”,并且是爱弥儿意义上的“立法者”。
如果说在卢梭笔下爱弥儿的“立法者”面孔仅仅只是停留在书斋里面,那么罗伯斯庇尔就是爱弥儿“立法者”面孔在书斋之外的思想效应,是这一面孔的实体化和人格化。这不仅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声称自己是最后一个看到活着的卢梭的人,更是因为他与其他大革命的领袖相比,他是一个更为彻底的卢梭主义者。[16]卢梭对罗伯斯庇尔的魔力是真实深刻的,在后者人生的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印记。虽然最终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但在一开始,两人就有着一种莫名的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一方面是对于自由的过分热爱,另一方面是对权力的极度过敏。正如海涅所言:“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手而已,一只从时代的母胎中取出一个躯体的血手,但这个躯体的灵魂却是卢梭创造的”。[17]为何有此判断?这是因为罗伯斯庇尔是卢梭诸多信徒中最为特殊、最为重要的一位。在1830年出版的一部著作《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回忆录》里记载,青年时代的罗伯斯庇尔会见正值人生暮年的老年卢梭之时,如同朝圣一般。罗伯斯庇尔是这么说的:“我在您最后的时光见到了您,这是我最愉快和最自豪的事情。我凝视着您威严的身躯。人间的不公让您失望,我看到了这些遗恨。因此,我理解了崇拜真理的高贵生命的一切痛苦。但这并没吓倒我。如您一般,我愿奉上一生以求此殊荣——即使早逝也在所不惜。”[18]怀着这一朝圣的仰视和敬畏心态,以至于在大革命爆发之后的1794年5月,罗伯斯庇尔为了纪念卢梭,举行了“上帝日”的仪式,并把卢梭定义为“神授之人”。[19]在某种意义上讲,卢梭培养“立法者”的教育思想就像是一个四处游荡的灵魂,一直到只有给予其一个肉体,一个能够承载其思想的感性身体,其才能够真正地安静下来。毕竟,思想要变成行动,语言要变成肉体。在这一点上,爱弥儿的“立法者”面孔与罗伯斯庇尔最终成为“人民领袖”可谓有着血缘意义上的亲密性。因为爱弥儿的“立法者”母体之所以能够道成肉身,之所以得以人格化和现实化,罗伯斯庇尔绝对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二)政治动员:从立法意志走向革命激情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之所以会把爱弥儿视为“立法者”来培养,还受到了普鲁塔克与色诺芬的潜在影响。首先,卢梭之所以认为历史中存在“立法者”,很大原因在于读了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复提及的“立法者”包括斯巴达的吕库古(Lycurgus)、雅典的梭伦(Solon)、古罗马的努马(Numa)等人,而这些都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都有所记载。而就《爱弥儿》当中,这一影响也亦是存在。卢梭经常用“小卡托”“凯撒”“努马”“亚历山大”“一个小小的海格立斯”“一个步履矫健的阿基里斯”等政治家或古希腊神话英雄的名字来称谓或对比幼年的爱弥儿[注] 卢梭之所以喜欢用政治家或英雄人物的名字来称谓爱弥儿,这与其深入阅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紧密相关。在《忏悔录》里,卢梭就声称自己最喜欢的书就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而到了晚年,卢梭再次声称:“在为数不多的我仍旧偶尔阅读的书籍中,普鲁塔克的作品是我最喜欢的和受益最多的书。它是我童年时候阅读的第一本书,也是我晚年阅读的最后一本书。可以这么说,他几乎是唯一一位我每次读过之后都不会空手而归的作者。”(参阅: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42.)对于卢梭而言,普鲁塔克是一位能够让他在变老的过程中都可以不断学习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普鲁塔克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本书。也正是因为普鲁塔克,卢梭才相信历史上的立法者是真实存在的。这也使得在卢梭的心目中,将爱弥儿培养成立法者的教育企图就不再只是停留于其个人的一次想象性实验,而极有可能成为某种历史事实。(关于卢梭对于爱弥儿身上各种形象的类比性称谓,可具体参阅: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1,167,186,193,370.) ,似乎爱弥儿从小就具备了这些古典英雄人物的品质。而在第四卷中,卢梭要给成年的爱弥儿准备阅读作品时,选来选去最终还是选择了普鲁塔克的书,这是因为“普鲁塔克以一种不可模仿的优美笔调,细致刻画了历史上伟大的人物,而且往往就是用一句话、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就足以表达主人公的性格特征”[4]37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卢梭的《爱弥儿》就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放大本。普鲁塔克的智慧和训诫,在卢梭那里得到了完美的回应。[12]
在卢梭的教育意图里,所有的教育意向和教育行为似乎最终都要聚焦在爱弥儿这个特殊的学生身上,这意味着爱弥儿式教育主要是一种个人性质的精英教育学。在这种教育学中,教师将会显得极为关键,对教师作为教育者的能力也要求极高。换言之,隶属于一种精英教育学的爱弥儿教育,需要一种高度脉络化的师生情境作为外部支持。而这一点,在卢梭式的爱弥儿教育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爱弥儿之所以会具有“立法者”的面孔,这与作为导师的卢梭自身作为“立法者”有着一种重构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卢梭是以想象中的自己作为原型,并以此刻制了爱弥儿这一教育样板。因此,如果说爱弥儿或许是另一个让-雅克的话,那么他的老师就是另一个卢梭。“立法者”既是爱弥儿灵魂朝向的一种理想类型,亦是卢梭交替使用的一个想象性身份。
三、个体式精英教育的反思:潜在危险及其应对
在卢梭心目中,《爱弥儿》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而实际影响更大的《社会契约论》只不过是《爱弥儿》的注释性附录。从表面上看,在《爱弥儿》中,卢梭向人们展示了如何培养一个有道德的人;而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塑造一个有道德的公民。[6]66-67然而,知道这一点还远远不够,两者之间的真实联系还需进一步揭示。进一步讲,爱弥儿作为“立法者”其实是《爱弥儿》与《社会契约论》发生实质勾连的过渡纽带。仔细审阅《爱弥儿》的读者可以发现,在关于政府形式、法律分类、国家权力结构等内容的论述上,《爱弥儿》第五卷的相关部分与《社会契约论》的第三卷内容基本一致,以至于这一部分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契约论》的简写本。卢梭为何有意如此写作?很大的原因可能就在于那个反复在《社会契约论》中被提及的“立法者”就是卢梭在《爱弥儿》中所精心培育的学生。而且在卢梭的心目中,立法者最重要的工作就在于为本民族或国家创建法律,最重要的法律并不是民法和刑法,而是一个民族、社会和国家的道德风尚。道德风尚作为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其既不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镌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7]61。因此,立法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帮助人民克服判断力的不足,建立起最适合本民族的道德风尚。用卢梭自己的话讲,“道德风尚的作用还尚未被政治家们所认识,但伟大的立法者无一不为实现这一点而不声不响地悄悄工作着”[7]61-62。而为了培养出能够熟悉各个国家道德风尚和法律习俗的立法者,在《爱弥儿》的第五卷,卢梭单独以“游历”作为标题,并在爱弥儿的游历过程中反复强调爱弥儿必须要理解社会契约、国家政治的真正内涵,必须要研究各种政府形式和政治制度的优点和弊端,必须要知晓各国人民的长处和德行。[4]757-767而这些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爱弥儿所学习的一切内容,都是使其成为《社会契约论》中的“立法者”而进行的准备。
1919年5月6日,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浙江。经亨颐与刘大白立即以浙江教育会名义拍电报致国务院和教育部,要求立即释放“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并于当日召开全校师生紧急大会,动员师生立即响应。又以教育会名义召集各校校长商议办法,成立“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动员杭州各校师生立即参加到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中去。从而,浙江一师成为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魏金枝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全国响应,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成为当时中国东南部文化运动的重镇。”⑤这时,魏金枝成了一个学生运动的热中者。
(一)精英教育的政治化:教育功能的极端放大
在一定意义上讲,旨在培养“立法者”的爱弥儿教育试图以实现教育情境与政治情境的绝对统一,并将塑造人群中的政治精英作为教育的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一种极端形式放大了教育的政治功能。而且在卢梭这里,爱弥儿之所以能够作为“立法者”,并不是一个人民选择的过程,而是一个先前就被注定的过程。因此,爱弥儿的教育虽然是高品质的,凝结了最大可能的政治能力和最大限度的政治美德,但这种教育注定只能是一个人的,而非普遍性质的。成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只能是一个人,而不可能是一群人。在卢梭眼里,爱弥儿是那个能够改变社会民情和道德风尚的“上智”,而民众相对而言则是需要启蒙、需要爱弥儿教诲的“下愚”。对此,卢梭是这么说的:“人民总是希望自己幸福,但她们总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幸福”,因此,为了使“理性与意志在社会集体中结合起来,使全体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就需要有一个立法者。”[7]44可见,人民虽然渴望好的事物,但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故而是盲目的,而作为“立法者”的爱弥儿则是高度理性的,其能够看到人民认识不到的东西,其能够以增加公众福祉的名义而让人民自由地服从。也由此,爱弥儿的灵魂必须是特殊的,甚至必须带有一定的神性,其代表着神的旨意。正所谓“立法者必须利用一种超出一般人的理解力的崇高的说教,把他的决定说成是来自神灵,利用神的权威来约束那些靠人的智慧不能感动的人”。[7]48在这里,卢梭似乎预定了爱弥儿在灵魂上的高贵品质,而爱弥儿的教育是这一高贵品质的自然化和外在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朝向“立法者”的爱弥儿式教育带有一定的血统性,是远离大众的,更是脱离民众的,甚至对民众存在一定的敌视。而这种教育,显然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相违背,现代社会不会预设爱弥儿这样一个“立法者”的先天存在,现代教育更不会以培养这样一种高度个人性质的“立法者”作为自己的目标,那种单独瞄准培养政治精英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毕竟,教育领域终究不是政治领域,本质上作为知识和德性教化活动的现代教育,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政治运作活动。现代教育是以一种普遍化的方式培养出普遍身份的公民,而决不是培养出一个人群中的政治精英。
(二)个体教育的封闭性:师生情境的高度依赖
正是人人都想要成为具有立法意志的爱国者,故而在这样一场大革命中,人类的情感能力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理性能力,由于爱国而革命这样一种“人民起义权”的概念在群众心目中被具象化了,它将推动群众在大革命的各个关键时期一次又一次地诉诸这种手段,从而成为大革命激进化进程的强大而直接的精神动力。[25]且只有当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充分爆发,革命的彻底性才会越大。而且那种试图成为“立法者”的公民形象成为了大革命期间人人都想要遵循的教育样板,以至于在那个时期到处可见这样的人,即他们的公民德性是如此的优秀,结果成为一股爱的潮流宣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最终成为了一种流行病形式的精神躁动感,并被推向了极端。然而,也正是由于大革命的动力过分依赖于人的情感,这导致大革命的目标缺乏清晰性,以至于变得模糊不清。于是,从教育上看,卢梭在《爱弥儿》中认为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所需要经历婴儿、儿童、少年、青年的长时间过程,需要经历爱情、宗教和公民游历的缓慢过程,都遭到了忽视,而只剩下一种摧毁原有旧教育制度的革命激情,以谋求快速地制造出新的人性和新的人格。也因此,卢梭教育思想中培养“立法者”的政治性倾向并没有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真正的贯彻,而是异化为一种塑造“人民领袖”的革命激情。卢梭培养“立法者”的教育意图虽没有在革命的母体中流产,但却不得不以早产儿和畸形儿的形式提前走向历史的舞台。
不过,爱弥儿和作为导师的卢梭并不是一种完全重构的关系,而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作为导师的卢梭之所以有资格和能力对爱弥儿进行教育,一个前提就在于他自己一开始就是一个反思的存在者,能够应付在教育过程中各种可能发生的困难。而爱弥儿一开始是不具备反思能力的,其是一个纯粹的感性存在者,这决定了爱弥儿一开始就不得不完全听从于老师所施展的所有教育意向。故而这种反思的存在者和感性的存在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积极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培育性的,也是教育性的。前者对后者施加的是一种外在的干预,首先是为了依照秩序与良善来引导他,随后为的是启发他去清楚明白地认识这种秩序与良善。[27]226也正是因为这样,这种外在的干预虽然看起来是一种介入性的“暴力”,但其实是一种“善意的暴力”,爱弥儿在不知不觉中习得政治德性的过程,恰恰需要得益于卢梭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老师,以至于爱弥儿的整个教育过程或所处的整个生活世界其实都是他老师的“杰作”。可见,爱弥儿和他老师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化的教育情境,在这一情景中,爱弥儿看起来是自己意志发号施令的老师,但其实自始至终,卢梭才是真正的老师。在许许多多隐形的约束性条件中,卢梭调控着爱弥儿的一举一动,他成为了预言及规划爱弥儿直接性生命的先知,他也似乎“窃夺”了他的学生的自由,为的是让爱弥儿更好地应对将来的生活。[27]228这也使得爱弥儿和卢梭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教育关系,本质上成为了一种政治关系,其是在以两人同意为基础上来确定治理与服从的关系。[28]
然而,一种特殊性质的师生情境虽然可以确保高水平的教育品质,但也让内在的教育过程被限制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层次,或者说停留于一种个人性质的精英教育学层面。这种精英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需要教师经过专门修炼或学习相关教育技艺的专业教育学,以确立教师在教育关系建构中的绝对地位和话语权,并形成一系列赖以依存的操作标准。而以此审视卢梭的爱弥儿教育,可以发现爱弥儿教育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实对于作为教师的卢梭本人的理性及其教育教学技艺有着高度依赖性。换言之,卢梭式的爱弥儿教育作为一种个人性质的教育学,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以依赖爱弥儿与卢梭之间的特殊师生关系,并转化为相应的教育情境和教育资源。然而,这也随之会带有一定的风险性。因为如果教师居心不良,那么那种由他完全掌控的教育关系就会令人感到恐怖了。尤其是爱弥儿教育中的“立法者”这一形象,既抹平了教育情境和政治情境的差异性,也预设了爱弥儿在血统上的高贵和特殊,这都不利于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而在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正是爱弥儿“立法者”形象在历史情境中的人格化和具体化,作为人民领袖的他也借此试图成为全法国人民的革命导师。为此,如果想要让卢梭式的爱弥儿教育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保留优势,而且同时不陷入一种潜在反民主性的危险,就需要一种超越个人的教育学,需要借助师生情境之外的教育力量来开展相应的教育实践。
(三)超越个体的教育学:现代社会的民主情境
当卢梭在1762年宣称:“我们正在走向危机状态和革命世纪”时,他使用了一种已被习用的意义,即用这个词来描述在世事流转中迸发出来的突变和失序。为此,卢梭认为需要从人群中培养出一个“立法者”来整合无序化的社会秩序。而到了罗伯斯庇尔这里,这种“立法者”的存在意义则与危机状态联系起来,而成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内毁灭力量的幽灵。[29]因此,《爱弥儿》这一著作可谓发出了某种颠覆活动的第一个信号,不管对于当时的教育制度,还是对于政治制度,都几乎是致命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卢梭的推理过程如何精当,但他确实知道如何使他的论点看起来具有说服力,令人满意而又不能抗拒。[30]而作为国民议会领导人的罗伯斯庇尔,真正践行了卢梭的思想意志,将卢梭心目中的爱弥儿这一“立法者”形象树立为革命领袖思想和行动的典范,“他们把他的血液灌输入他们的心灵和生活方式之中,他们学习他,思考他,他们用从白天卖力的胡闹或夜晚的放纵中挤出的全部时间把他加以反复考虑”。[31]这真可谓是《爱弥儿》在书斋之外的思想效应。
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待互联网金融所带来的影响,不仅需要看到它所带来的挑战,同时也要看到它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与发展转变了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加剧了各种业务之间的竞争,提高了业务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官商作风、垄断经营、竞争力差等情况长期存在,导致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不足,而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该市场格局被打破,进而促使商业银行不得不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然而,在《爱弥儿》中,“立法者”的教育终归只是一种个体形式的精英教育,仰赖的是一种以高度情境化的师生关系为依托的个人教育学。这种个人教育学虽然与卢梭试图培养“立法者”的政治精英取向高度吻合,但在形式上却是相当封闭的,其不仅杜绝了普通人接受高品质教育的可能,也为教育政治化的过度衍生提供了屏障。因此,如果卢梭式的爱弥儿教育要在现代社会得以接受,就需要一种超越个体形式的教育学,即一种制度教育学的参与。这里的“制度教育学”主要强调的是一种制度情境中的教育学,是一种蕴含在社会结构中的教育力量,是为个人性质教育学的合理应用提供情境支持的制度框架、结构关系与默会共识。[32]制度教育学强调要为个人性质的教育学建立起一种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共制度情境,从而为个体乃至群体的教育实践提供可行的价值规范与技术策略。而结合卢梭式爱弥儿教育自身的特点,为了防止其政治化倾向的过度衍生乃至恶化,就需要建立一种民主的制度情境加以制衡。这是因为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均等化性质的制度情境,其可以让个体性质的精英教育走向普遍大众。正如杜威所言:“必须要对民主形成一种更为深刻的理解: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33]可见,民主既是一种勾连人与人之间不同经验接触点的生活方式,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场域。民主作为一个开放的日常经验场域,需要通过每时每刻的经验交流来实现。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域当中,没有人会是专门的教育者,也没有专门化的教育活动,但每个人最终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教育的重要制度情境,教育则是民主的最大功能。
统筹起来看,卢梭的《爱弥儿》并不只是一部教育论著,而更是一部政治论著。《爱弥儿》一书的最大政治性特征就在于卢梭试图将爱弥儿培养成一位“立法者”。然而,卢梭这种试图为本民族道德风尚和法律规范的重建提供路径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反而被利用为一种崇拜革命领袖的政治动员。而这位“立法者”最终得以道成肉身,成为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民领袖罗伯斯庇尔。这既是一种思想家思想在书斋之外的客观效应,又是客观历史对于思想家思想的再次验证。对此,我们既要重新审视卢梭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也要谨慎规划培养现代人格的教育制度情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于卢梭式爱弥儿教育的内在超越,以推动现代教育的合理发展和稳健转型。
参考文献:
[1] 卢梭.新爱洛漪丝[M].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27.
[2] 刘小枫.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 卢梭.山中来信[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6.
[4] 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5] 刘良华,曾世萍.卢梭的教育意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1):11-17.
[6] 卡罗尔·布拉姆.卢梭与美德共和国: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语言[M].启蒙编译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 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8] 卢梭.论波兰的治国之道及波兰政府的改革方略[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6.
[9] Eve Grace,Christopher Kelly.The Challenge of Rousseau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144.
[10] Judith N.Shklar.Men and Citizens :A Study of Rousseau ’s Social Theory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165.
[11] 刘小枫.《爱弥儿》如何“论教育”——或卢梭如何论教育“想象的学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26-146.
[12] 张竞生.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M].莫旭强,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5.
[13] 塔图姆.色诺芬的帝国虚构——解读《居鲁士的教育》[M].张慕,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14]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M].沈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10-411.
[15] 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M].曹海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04.
[16] 欧文·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M].孙宜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6.
[17] 亨利希·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M].海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03.
[18] 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M].张雅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9.
[19] 威尔·杜兰特.卢梭与大革命[M].台湾幼狮文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032.
[20] Graeme Garrard.Rousseau ’s Counter -Enlightenment :A Republican Critique of the Philosophes [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3:58-59.
[21]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171.
[22]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修订译本)[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3] Martha C.Nussbaum.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 [M].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Press,2013:45.
[24]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第四版)[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5] 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增补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6-227.
[26] Louis Althusser.Politics and History :Montesquieu ,Rousseau ,Hegel and Marx [M].London:New Left Books,1972:157.
[27] 让·斯塔罗宾斯基.卢梭与有罪的反思[C].汪炜,译//莫伟民.法国哲学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8] 渠敬东,王楠.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78.
[29] 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M].刘北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625-626.
[30]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M].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0.
[31] 陈志瑞·伯克、卢梭与法国大革命[J].史学月刊,1997(5):75-83.
[32] 康永久.制度世界及其教育学[J].教育研究与实验,2013(1):1-6.
[33]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7.
From Emile to Robespierre :Rousseau ’s Thought Effect outside the Ivory Tower and its Reflection
HU Jun-jin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34,China)
Abstract :Emile is not only an educational treatise,but also a political treatise. The greatest political feature of Emile is reflected in Rousseau’s intention which is that he regards the legislator as an educational goal of Emile. Because Rousseau aims to make Emile the most special “legislator”among the citizens,Emile’s education has a strong political tendency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is image of Emile as a“legislator”was finally personified and realistic,and became the people’s leader Robespierre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addition to recognizing the potential danger of Emile education’s extreme amplification of education’s political function,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ee that Emile education is an elite pedagogy of anti-democratic nature. Therefore,the modern society needs to construct an institutional pedagogy in a democratic situation,so as to truly achieve the internal transcendence of Rousseau’s Emil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stabl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education.
Key words : Emile;legislator;Robespierre;elite pedagogy;institutional pedagogy
收稿日期: 2019-02-25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9M650087)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 胡君进,E-mail:junjinhu@126.com
中图分类号: G40 - 09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3969/ j.issn.1005-2232.2019.03.002
(责任编辑:鞠玉翠,戴 孟)
(责任校对:戴 孟,李 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