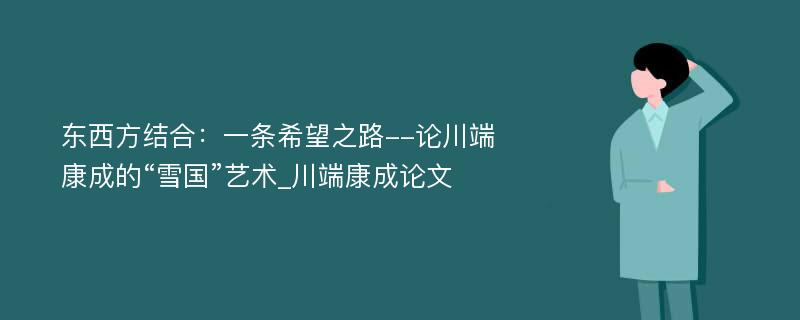
东西合璧:一条希望之路——川端康成《雪国》艺术摭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川端康成论文,之路论文,东西论文,艺术论文,雪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眼前摆着传统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条道路,明天的艺术究竟走哪条道路呢?恐怕这两条道路都要走,或者走两者很好融合起来的道路吧。”[①]
这是川端康成《乡土艺术问题概观》中的一段话。无庸置疑,关于一九六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该说的已基本道尽,不该说的或许也还说不透,然有感于川端康成上述的创作论,再取日西文学融合的视角,仍望获得某些启示。
众所周知,东方近、现代受西方文化冲击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它既是自近代始世界交通贸易急剧发展的结果,更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东方的直接产物。冲击势必造成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形成一种动力,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日本,在东西文化的交融和对抗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文学流派和灿若星辰的作家群体,而川端康成正是这条东西文化汇合的银河之中的一颗明星。
与他的许多先行者一样,早期川端康成及其创作品格的塑造也是在日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完成的。他曾在帝国大学英文系就读过,接受外来文学思潮尤如近水楼台,在芥川龙之介、菊池良宽等西方文化传播者的培养下,川端康成脱颖而出,成为“新感觉派”的核心人物。那时川端康成盲目追随西方文学,他甚至“把表现主义称作我们之父,把达达主义称为我们之母。”[②]我们在《梅花的雄蕊》、《浅草的少男少女》等早期作品中,不难发现他模仿西方现代主义的痕迹。
但是,正如一个认识过程的逐渐深入、成熟一样,面对日本本土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的选择,川端康成虽因袭了前人的选择方式,但事实上仍然有许多矛盾和困惑。他在自诩西方现代派父母精血产儿的同时,仍然割舍不断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传统文学的眷恋。加上川端康成父母早逝,十六岁时祖母亦作古,近乎盲人的祖父面容宛若一幅孤绝、寂寥的肖像画,却为川端康成磨砺出异常锐利的艺术目光。少年的川端康成参加了那么多亲人的葬礼,这样的遭遇使他沉默寡言。川端康成自己就说过:“可能由于我是个孤儿,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哀伤的、漂泊的思绪缠绵不断。”[③]孤儿的根性,婉郁的情怀,使得弥漫在他作品中哀婉凄清的氛围与日本传统文学在气质上一脉相承,与日本文学中力主表现情绪,表现纤柔悱恻感情的主体倾向暗中契合。本土文化对他的向心力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他一步一回头,最终很难在两种文化之间依循前人的轨迹。他本人也承认“我虽算作新感觉派,但没有什么符合新感觉派特点的成功之作。”[④]
荆棘密布之中,他必须再次回首,另作选择,另要求新。什么是他所追求的“新”呢?川端康成的回答是:“强烈地自觉做一个日本式作家,希望继承日本美的传统”[⑤]。在调整对待日本、西方文化选择内在机制的关键时刻,川端康成叛逆了他的前人,也背叛了“新感觉派”的自我,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这委实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因为川端康成之追求实质并非单纯沿袭古文的旧迹,而是在传统之中溶入了不少现代意识,在表现传统美的方法和技巧上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本文以《雪国》为例,略论川端康成文学创作上日西契合的特色。
一、虚无美与虚无主义
“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⑥]
长期以来,日本民族特性中的“孤寂性”、“侘性”、“孤绝性”构成日本人“灭”的美学意识。“灭”美意识反映了日本人的虚无主义世界观。这种虚无主义发源于日本佛教的无常观和末世思想,它基于对世态的“祸福同道,盛衰反常”的急遽变化的感受,把现世的一切看做是苦恼的,把现世视为“浮世”、“人生朝生暮死,万物无常,宛如似花瓣朝露。”[⑦]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到日本文学中,则通过幽寂,侘以及对隐世、对死的向往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爱落花,爱秋月,向往隐居,追求羁旅。《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中都以描写秋季风物为多,这是因为秋之萧条,最能突出无常观的感受。日本人爱樱花,但与其说是爱樱花盛开的繁茂,勿宁说更爱樱花败落的萧瑟。这种“灭”的景象给日本人带来惆怅、伤感、空漠、孤寂、幽怨和侘美的艺术享受,即“物哀”。中世纪日本人提倡死的美学,鼓励武士以死为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象三岛由纪夫等人通过“切腹”来体现他们对死的“爱、美和力”的追求。紫色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钟爱,是因为它总是带有很快就要消灭的命运的色彩,它离不开日本人的心理深处的爱的短暂和飘渺无常的虚无意识。总之,这种惜春、悲秋、爱霜月、叹花落的“灭”的审美意识是日本文化思想长期以来形成的潜流。
这一“虚空”的文化潜流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的震波中,与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想很快取得了共同的摇撼。震后日本政治经济的混乱,加之苏联革命的胜利,工农运动的发展,引起日本人意识领域的巨大淆零。正当人们面临乱世,无所适从的时候,西方破坏性的虚无思想,瞬间的享乐风潮席卷而来,造成人们精神上的极度窒息与荒废。他们对自己在社会的存在感到不安、彷徨,产生消极和绝望的情绪,竭力挖掘自我内心的不安,追求刹那间的美感,官能上的享受和日常生活中非现实的东西。这种精神上的极度颓废,不能说与西方虚无思想的介入无关。
西方虚无思想者是反对一切权威偶像的破坏者,因其只具有破坏意识,故常常裹挟着渺茫的人生失落情绪。他们否定一切价值并揭露其虚妄性,“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⑧]但他们无法合理地扬弃传统的价值,只是想到破坏传统价值,推倒精神偶像,对新价值的建立却无从谈起,在难以名状的迷惘、困惑中,欲逃离而不能。无论如何,他们无法构想出一个精神的新世界来。
川端康成却构想出了这样的精神世界,从而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新价值。时代背景的大气候和主体上的凄婉因素决定了在否定现实、逃避现世方面,川端康成的虚空与西方的虚无如出一辙。《雪国》开篇那脍炙人口的范句——“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⑨],“长长的隧道”暗示了时间的转换或现实通往虚幻。主人公岛村、驹子、叶子表面上的确呈出现一种三角恋爱式的性爱模式,但与此同时,三个人物又均为具有深层意蕴的能指符号。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虚幻色彩,同时三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也体现了川端康成两种不同层次的美学追求:其一,美是虚幻,对立于现实之丑,但美丑又令人困惑地时时共处同一的对象之中(岛村与驹子的关系);其二,要求超越现实与虚幻的对立或同一趋向“至善至美”的“空无”的哲学境地(“雪中火场”和“银河坠落”中叶子及岛村的结局)。
“镜中映像”更是受西方虚无思想意识潜流的影响,它代表了《雪国》中的时时蕴含的象征与暗示。岛村在列车上邂逅的叶子、行男,正是“镜像”般宿命式的人物构置。行男是驹子的艺师之子,未婚之夫,患有不治之症,而叶子却痴情于彼。这种既定的人物关系,也是一种指向虚幻的“意符”。同样,驹子实质上有某种观念化的暗示意义:“人世徒劳”。替行男治病是徒劳,订婚也是徒劳,写日记是徒劳,对岛村的思恋更是徒劳。《雪国》中的“徒劳”同样也是一个观念“意符”,既表示虚幻等于美,又表示现实等于丑;既是日本传统的苦海无边的超度,又是西欧破坏意识的进化。总之是对人生社会一切价值的彻底否定,“一切皆虚妄,一切皆允许”!
那么火灾中叶子的死以及“银河坠落”的意象是否象征着驹子执着的爱与追求——双层含义的“徒劳”之死呢?不仅仅是。在“一切皆虚妄”的同时,川端康成的艺术作品有强烈的观念性,他不相信什么家庭、婚姻,更不相信男女之间情爱的真实。川端康成骨子里所真正崇奉且构成其文学观念基础的,乃是某种东方禅学式的“主客如一”认识论。他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一文中就说过:“天地万物之中有自我的主观,以这种情绪去观察事物,这是主观的扩大,就是让主观自由地流动。而且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变成自他一如、万物一如,天地万物丧失所有的境界而融合在一种精神里,成为一元的世界。另一方面,万物之中注入主观:万物就具有精灵。”[⑩]那么“徒劳”之后又是什么呢?是“空悟”,川端康成虽则从传统的“灭”美中来,以凄婉幽怨的笔调写了雪国的红叶飘零,暮雪纷飞,虽则写了四季的变迁和人世的无常,虽则以“雪中火场”来毁灭现实和虚空的无法解脱的对立,但“银河坠落”意味着其亡的同时,并不等于原有的美的价值的冰释溶化,而是进入了更高层次的“空悟”之境,这当然不同于西方的“虚无”。
二、唯美主义和“江户情调”
“我在美丽的日本”。(11)
虚空是空灵博大的,虚空也是美丽无限的。川端康成在构筑美丽的虚空精神之一元世界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也形成了自己的唯美主义风格。
新感觉派出身的川端康成的多数作品,都具有唯美主义倾向。从艺术角度看,他的这些作品无一不是观察细致,文笔委婉,情景交融的。它们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不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而倾向于描写人物的心理、体态和客观风物在人物主观上的反应。他笔下的人情和景物,大都是清清淡淡、疏疏落落、注重含蓄、讲究余韵,往往把读者引入他的艺术魔宫。中篇小说《雪国》除了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西方唯美统一主张下,描摹了自然美景,表现了享乐主义,突出了性的解放之外,传统的“江户”色彩的唯美倾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户情调”是川端康成唯美作品的独立特征,也是日本唯美派不同于西欧唯美主义的独立特征。
所谓“江户情调”,就是江户时代本居宣长所宣扬的“人命即天理”、“不必从圣人之道”而“自躬享乐”的精神混合,与江户川柳式的戏谑和好色的审美意识结合,虽然放荡却并不龌龊,卑粗却并不鄙俗。也就是遵从“乐而不淫”的原则,对快乐的追求限定在一定的尺度之内,经过艺术的磨炼而成为官能美或感性美。正如木下圭太郎所云:“日本唯美派一个独具的特征,就是用欧洲的艺术形式,发挥日本的趣味。”(12)从此种角度出发,川端康成的《雪国》不失为一篇江户趣味的艺术宣言。
首先,川端康成在《雪国》中着力表现的是女性的美。川端康成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美永恒女性”的境界。他认为“在所有艺术领域里,处女是被别人歌颂的。”(13)《雪国》中作者写了两位艺妓:叶子和驹子。川端康成通过两种形式不同、内容一致的“镜中映像”来把她们当作美的象征刻画出来。而这种美又是与悲哀相联系的,她们都有一种与悲哀纯真相联系的柔和美,进而她们心中的爱意也能给人一种温柔的感伤,素雅的哀愁,有着古典的情趣。尤其是叶子,她宛如一尊矜持脱俗的雕塑,美在肉体,美在心灵,凛然而不可侵犯,充分体现了作者美的理想。“雪中火场”叶子这一涅盘升天式的结局,是作者对她最美好的赞歌,更富于日本典型美学的情致。
其次,崇尚卑贱美。川端康成说:“我觉得浅草比银座,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们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味。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14)川端康成在穷街陋巷里、在下层群众中,发现了一种既卑贱又纯朴的美,并且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雪国》中,作者不惜笔墨描写了日本下层民众的风土人情,通过“晾晒哈蒂”和“曝晒麻绉”两个典型场面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赤诚,对美的孜孜追求。这世外桃源般古色古香的风情正是中世纪日本民俗的现代延续。“在雪中缫丝,在雪中纺织,在雪中漂洗,在雪地上晾晒。”川端康成几次援引古书的记载,使小说更透出素淡的中古之情。
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雪国》的颓废色彩。川端康成认为为了追求美,为了表现美,可以不顾人类正常的伦理道德。他说:“尽管在作风上我表面没有锋芒毕露,却有违背道德准绳的倾向。”(15)《雪国》中,川端康成着力刻画的是雪国的风光和女性袅娜多姿的肉体,绵绵的情话和悱恻缠绵的官能接触。桃源仙境般的温泉旅馆,生活着“从社会性走向生理性的人们”(16),皑皑白雪辉映着艺妓玉洁冰清的肌肤。岛村、驹子在三弦琴音中如痴如醉,宛若忘怀人世的一切尘埃音讯,陶醉于知音的相悦气氛中。继尔从《千只鹤》到《一只手臂》,川端康成这一系列作品的故事情节越来越离奇,思想感情越来越颓废,与文学的正轨偏离亦越来越远了。
这种有失偏颇的情绪固然是受到西方“世纪未”颓废思想的影响,但是在驹子这一人格分裂的人物与岛村的关系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川端康成还是崇尚“乐而不淫”的江户情趣的。这种关系在作者笔下不是赤裸裸的官能接触,而是较为含蓄婉转的,俩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平淡从容的,给读者留下了更宽的玩味空间,正是所谓“放荡却不龌龊,卑粗却不鄙俗”的江户情调的典范。应该指出,作者肯定驹子对真正爱情的正当追求,肯定她那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正确的。但是置驹子那种放浪、淫欲以及官能上的快乐于不顾,一味美化她,从现实的角度看,应该加以批判。
为什么日本文学自古而今,却充满《源氏物语》及江户色彩的唯美倾向,而思想性普遍较弱呢?这要追溯到日本一贯的统治秩序和日本岛国的地理位置的影响。自古以来,日本处于闭关状态,加之日本很早就建立了天皇的绝对权威和统一的国家,作家往往顺从于一个政治体制之内,因此,日本人只易接受感情的表象,很少懂得抽象的思想,日本文学也就专重抒情而极少言志了。此外,日本四面环海,季风吹佛之下,四季风光绮丽,变化鲜明。这使人们养成温和、纤细的性格,对于大自然富有感受性,使人和文学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
川端康成一方面依恋于本土的上述传统,另一方面战后亡国末世之民的观念以及没落家世和孤儿遭遇的影响,加上外国文化的渗透,使他形成了个性分明的唯美观。
三、光源氏——岛村——“多余人”
“岛村不是我。他似乎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男子存在罢了。”(17)
驹子、叶子是“莫须有”的,也是美的,就象飘落的樱花花瓣一样。然而,男主人公岛村是何等样人?
岛村在内在气质和外部追求上与《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十分相似:同样的内向忧郁;对生活冷漠虚聊;同样追求感官刺激,渴望肌肤之亲,放荡淫逸,朝三暮四;同时,也一样的有时萌发内疚和自责,对被玩弄的妇女深表同情和怜悯。然而,两人在忧郁的内容和借寻花问柳排遣郁闷的方式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光源氏的忧郁基本是政治上的失意引起的,实质上是没落贵族面对无可挽回的崩溃之势的忧郁,不少女人在光源氏手中是追逐显赫地位的工具,他猎艳的方式往往是主动出击;而岛村的忧郁完全是对人生意义丧失信念引起的,不用说读者,连他自己也对“舞蹈艺术研究者”的名目而自嘲不已。正是这种自我价值的失落所引起的郁闷使他三访雪国。但是,与驹子的幽会并没有驱散他心中的郁结,肉体的性感过后,他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忧郁之中。一种不可名状的自我失落感使他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小说中的岛村和驹子的合聚,几乎全是驹子主动跑来,于是,迷离恍惚之中,其归宿早已指向了死亡,只是他惯于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对他零落的状态和他的死全然混沌无知。直到小说最后“待岛村站稳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象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倾泻下来。”这才暗示了他对死——他的唯一归宿的顿悟。
由此可见,岛村的忧郁实质与光源氏不同,他是现代日本社会自我价值失落之后的“多余人”的忧郁。在岛村前列,我们可以看到小野哲、苦沙弥、哥尔等一系列现代文学中的人物,他们都是在接受了西方文化之后,对现实社会不满,又苦于找不到出路,进而忧郁苦闷,无所依托的“多余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与岛村之间无疑更具有血缘关系。
岛村是作为“多余人”形象出现的,然而他却并没有真正生活过,也没有真正思考过,他的存在“只是作为一个男子的存在”,他的等待就是死的唯一终结,他如同一个沉默的灵魂独倚墙角,在温泉旅馆的乐园中消磨人生最后的时光。
倘若以奥涅金为首的一系列俄国“多余人”形象与之比较,岛村则黯然失色。岛村充其量只是一个迟来世间的奥勃洛摩夫。如果说奥勃洛摩夫是一具僵尸,那么岛村则是一堆枯骨,连做梦梦着睡觉的能力也没有了。
因此,川端康成所表现的传统美中的人物构置,既饱含着历史的颗粒,又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融入了西方文化因素之后的新的现代日本传统美中的人物。
四、关于表现
“企图蔑视文学上的感觉的人,就是妄想以炭火代替太阳来温暖世界的蛆虫。就是不想永久在天空翱翔而折断自己的翅膀的飞鸟。”(18)
在表现现代传统美的艺术手法上,川端康成也同样具有有机融合日西文化的特点。他崇尚语言之外的感觉,因此常常借助表现中介语言的美使读者“此时无声胜有声”式地体会到多种美妙的感觉。《雪国》以若即若离的文笔刻画了若即若离的人物关系,也刻画出多幅色彩素淡的自然画面,种种感觉隐藏于语言背后,不言而喻,不点自明。
首先,川端康成借助“花道”、“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增添作品余韵,加强读者对美的感受,力求表现所谓“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19)的传统美境界以及“和敬清寂”的茶道所表现注重的“古雅、闲寂”(20),特别在表现“四季感”上,他更是不遗余力。川端康成的作品特别注重对草木山川、气象万千的大自然的描绘,注重由于季节的转换,草花盛衰带给人们的心灵颤动,纤细微妙的心理变化。
四季轮换的同时,川端康成还以明快洗炼的笔墨描绘出一幅幅展现日本民俗风情的优美画卷。《雪国》中有两处典型日本风情的着墨之点,其一是晾晒“哈蒂”,表现的是青年男女的勤劳和驹子在秋的收获之后流露出的愉快心情,画面鲜明快活,反衬出岛村忧郁寡聊的虚空心境。其二是晾晒绉纱,“晨曦泼在曝晒于厚雪上的白麻绉纱上面,不知是雪还是布,染上了绮丽的红彩。”短短两行字即把雪地晒场的幽寂皓阔之景表叙出来,这皓阔无边的洁白世界在作者的笔端之下也沾染了宇宙阳光的灵气,不禁使人忘却世间无尽的纷争与尘垢,但是“岛村既没有在穿着绉纱的炎夏,也没有在织绉纱的严冬来过这个温泉”,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同驹子谈绉纱的事”,也就根本不知道绉纱之中“倾注”了女性“全部的挚爱”。弦外之音,《雪国》中的绉纱其实是人类情爱不能永恒的象征。
由上可知,在“四季感”以及民俗风情等传统表现艺术手法上,川端康成不愧为具有日本风格的作家,但他又不是一个真正的“国粹派”,他在表现日本传统美时,借鉴了西方文学的经验,表现为注重运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通过人在刹那间的感觉,展示内部人生的全面存在和意义。《雪国》中的人物关系、民俗风情和人物命运的结局都充满了象征和暗示的作用。《雪国》中的“镜中映像”也是如此,既带有象征和暗示人情的虚无和美的难以把握,又以令人惊叹和费解的美妙玄虚的语言写出了岛村那一刻的心理活动,表现出虚无即是美的主旋律。
川端康成在借鉴西方经验中,尤其表现在借鉴了意识流的手法。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意识的流动性和飘忽性,借此更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复杂性格、情感波澜。《雪国》虽然写了两年内初夏、晚秋、初冬三个时令里岛村三次雪国之行,然而却是从主人公晚秋去雪国的途中写起,由岛村左手食指的“几许感触”勾起他对驹子扑朔迷离的记忆,暗示他们之间在初夏的肉体关系;由火车玻璃窗为镜面,反映出叶子的容貌,进而写“镜面映现的虚像与镜后的实物”,通过岛村的飘忽的意识活动,把梦幻和现实,虚影和实景、憧憬和回忆交错重叠在一起,凸现出主人公忧郁烦闷的心情、迷离恍惚的神态和百无聊赖的处境。
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川端康成运用西方表现手法是有选择的。在他的作品中,意识有跳跃,却不杂乱;有交叉,却不散碎;有联想,却不突兀。他所运用的象征和暗示以及由奇特的语境所形成的奇特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神秘虚玄,而是一种常规思维中明白易懂的“尽在不言中”的象征意象。他虽崇尚感觉,但各感觉点是连环纠结,相互依托,浑然一体的,是符合东方人的欣赏习惯的。
川端康成曾说:“我们的文学虽然是随着西方的潮流而动,但日本文学的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21)川端康成及其创作品格的塑造正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完成的。然而,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负面的影响,也使川端康成小说中带有不少不健康的色调。这说明两种文化的碰撞无疑会带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但从作家个人角度出发,无论对外来文化还是对本土文化,合理地吸收,适当地扬弃则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
① 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页。
② ④ ⑤ 转引自《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3页。
③ (15) (16) 川端康成:《文学自叙传》,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4、114、112页。
⑥ (11) (19) (20) 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见《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9、696、705、705页。
⑦ 鸭长明:《方丈记》。
⑧ 尼采:《权力意志论》。
⑨ 川端康成:《雪国》,见《川端康成小说选》,叶渭渠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6页。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故不再一一注明。
⑩ 川端康成:《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谓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1页。
(12) 吉田精一:《明治大正文学史》。
(13) 川端康成:《纯真的声音》,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3页。
(14) 川端康成:《日本美之展现》,见《川端康成散文选》,叶渭渠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16) 川端康成:《文艺时评》。
(17) 川端康成:《关于〈雪国〉》,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3页。
(18) 川端康成:《关于表现》,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6页。
(21) 川端康成:《近来的感想》,见《川端康成谈创作》,叶渭渠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