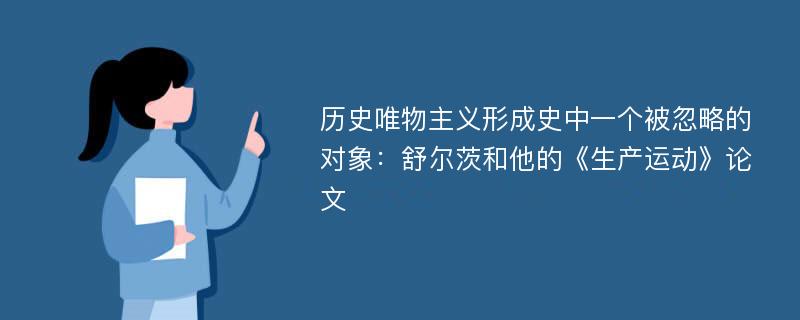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中一个被忽略的对象:舒尔茨和他的《生产运动》 *
李乾坤
[关键词] 舒尔茨;《生产运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物质生产;精神生产
[摘 要] 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史的研究中,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近年来进入到我国学界视野之中。舒尔茨的一生分为学习成长、第一次流亡、参加1848年大革命、第二次流亡四个阶段。《生产运动》一书1843年出版于舒尔茨第一次流亡瑞士期间,在问世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思想史上,对于舒尔茨思想的忽视,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研究的特点决定的。《生产运动》一书以回应社会矛盾为目的,以分工理论为方法,分析了物质生产中的规律,探讨了精神生产中的发展变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深入,许多在传统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来源”之外的研究对象也被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威廉·舒尔茨也是其中一位,他的《生产运动》一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重视。(1) 张异宾在1999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中,敏锐地注意到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一书,并判定此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想对于研究青年马克思思想有参照意义。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4-166页。此外,关于舒尔茨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还可参见拙作:《舒尔茨的〈生产的运动〉:青年马克思生产范畴形成的重要坐标》,《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如今,对于舒尔茨及其思想的研究,可供参考的文献资料很少。我们有必要从舒尔茨的生平、《生产运动》一书的出版情况和研究情况,以及《生产运动》一书的基本思想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总之,法家的“说”是察言观色的“说”。他们注重运用说服技巧,时刻揣摩君主心理,想方设法摸准君主意图,让君主采纳他们的见解,达到说服的目的。法家虽然有着完善的游说技巧,但他们是“禁言”的。“好辨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亡征》),韩非把善辩者列为治理国家必除的五蠹之一,他这是在以辩止辩。“法”是君主意志的代称,同时也是思想钳制的工具。“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言论,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言论自由,法家“以言去言”的历史局限性显而易见,但法家关于口传的见解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席之位不容忽视。
一、舒尔茨生平
威廉·舒尔茨1797年3月13日出生于德国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一个新教公职人员家庭。他的家族祖孙三代在封建贵族眼里,或许都是“头生反骨”的人,舒尔茨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因多次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统治而受到惩罚。舒尔茨的一生,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834年之前,是他早年的学习和成长时期;1834—1848年,是他第一次流亡时期;1848—1849年,则是他返回德国参加革命活动时期;自1849年一直到他1860年逝世,是他的第二次流亡时期。
则主塔桩基满足邻桩人工开挖要求,但为了避免施工相互影响,采取间隔交错施工,群桩开挖及浇筑顺序为:1#、8#、15#、4#、11#、18#→3#、13#、6#、16#→2#、14#、5#、17#→7#、9#、10#、12#。
1.早年时期。1811年,年仅14岁的舒尔茨就因反抗一位老师的等级偏见而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而后,他在父亲的支持之下加入了领主的禁卫军,并参加了拿破仑战争,先后效忠于法国和普奥俄阵营。在战争期间,舒尔茨于吉森大学学习了数学和军事学,可以说,他学习的这两个专业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研究。1814年他在吉森大学通过“德意志读书会”(2) “德意志读书会”是1814年由吉森的70位大学生在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的领导下建立的进步组织。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Adolf Ludwig Follen,1794—1855),德国自由主义作家和出版家。 结识了卡尔和阿道夫·路德维希·福伦兄弟,并加入了当时学生政治运动组织——“吉森黑衣军”,(3) 吉森黑衣军(Gießener Schwarzen),德国19世纪初的一支激进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学生组织,由德意志读书会发展而来。吉森黑衣军并不寄希望于精英阶层的革命所带来的变革,而是转向大众,关注受压迫的市民和农民,试图通过抗税运动来进行积极的抗争。 自此迈出了政治生涯的第一步。1818年,舒尔茨匿名发表了宣传单《对德意志祖国所有特别困境的问答》,这份宣传单在1819年奥登瓦尔德农民起义期间产生了广泛影响。后来舒尔茨因这份传单被捕入狱,以叛逆罪被拘捕了一年。出狱之后,迫于贵族的压力,舒尔茨最终决定离开黑森。
舒尔茨之所以主张军事制度改革,是因为在他看来,1848年革命的失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俄国这个欧洲最彻底的反动势力的干涉。要使资产阶级左派在革命中获得胜利,就要使西欧国家对俄国进行联合征讨。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作为封建统治者家丁的军队,改造为属于人民的现代军队,这就要求进行深入的军事制度改革。1855年,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他在莱比锡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军事政治:论瑞士的阻力和对现存军队相抗争的民兵部队》。在其中舒尔茨把现存军队称作“军事奴隶”,人民供养军队,但军队却只服务于统治者阶层而反对人民,相互争夺。他鼓吹民兵应该学习北美的民兵体制,在欧洲建立起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军队。与此同时,舒尔茨对诸如自由和人民团结的理念力量表示怀疑,他更多地看到人性的自私,因而他侧重于通过物质刺激的体系来维持民兵的军纪和士气,所有这些又依靠于一部进步的宪法。
(4)数据、图形、原始资料、整体发动机特点、采用了哪些新工艺、新材料、相关技术规范、相关标准、类似案例,零部件特点、材质、相关制造工艺。首先对该发动机进行功能性和维修经济性评估,然后讨论制定修理方案、工艺、标准、制定采购清单、外委加工事宜等。
1831年末舒尔茨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关系》为题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他就已经注意到经济学的统计测量对政治权力关系的影响。我们可以推断,舒尔茨的博士论文奠定了他后来在《生产运动》中的理论雏形。在此之后的1832年到1833年间,舒尔茨因为出版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报纸,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多次被当局驱逐。最终,在1833年秋天的法兰克福暴动半年之后,黑森司法机关决定逮捕舒尔茨。
2.第一次流亡时期。1834年6月18日,他被黑森当局判处5年监禁,但不久之后他就在其妻子的帮助之下越狱成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流亡。他先是和很多当年的德国革命人士一样逃往法国,而后在1836年,舒尔茨申请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并获得批准,此后赴瑞士生活。有趣的是,至今人们还可以在苏黎世大学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舒尔茨当年开设的课程。我们可以看到,自1837年夏季学期至1838年冬季学期,舒尔茨开设了四门课程,主题都是政治学领域的问题,如一门课的名称就叫做“瑞士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状况: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5) 参见http://www.histvv.uzh.ch/dozenten/schulz-bodmer_w.html. 也是在第一次流亡瑞士时期,他结识了著名的德国进步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并与他结下了终生友谊,毕希纳后来就是在舒尔茨夫妇的陪伴下逝世的。
在瑞士的这段时间,是舒尔茨从事理论研究的关键时期。在流亡的头些年里他研究了国民经济学、统计学和瑞士的政治结构。他开始在科塔的《奥斯堡公报》、布劳克豪斯的《文学评论报》和卡姆普的《德国电报》发表通讯报道。自1842年起,他为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写评论报道。1843年,舒尔茨最具理论高度的著作《生产运动》一书在瑞士出版。
可怜的法比此刻像个全没主意的孩子,英格曼神甫站起来,袍子胸口上长长刀伤使袍子里子露出来,那是深红色的里子,创面一样。可怜的他自己,竟也是个全无主意的孩子。
在这一时期,舒尔茨还积极投身于瑞士的农民运动和自由宪法运动。因“影响到德国同瑞士关系”,舒尔茨受到梅特涅的谍报人员的严密监视。1843年,舒尔茨匿名出版了《神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狄希之死》的小册子。他在详实的文献证据基础上,深刻揭露德国的残酷刑罚和政治状况。这篇文章获得了广泛的流传并造成了巨大影响,激起了德国政府内部的政治浪潮,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1845年,舒尔茨参与了福伦等人同阿诺德·卢格和卡尔·海因岑的“苏黎世无神论论战”。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舒尔茨站在福伦一侧,批判卢格为代表的无神论。
4.第二次流亡时期。回到瑞士之后,舒尔茨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军事制度的经济和政治分析之上。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他一开始强调军事制度改革,后来鼓吹裁军与和平主义。
对联是写在墙上的,字体匀称,还画了稻穗图形做装饰。可见当年执笔的人花了一番心思,是把这当做艺术品来写的。
1848年下半年,保罗教堂议会彻底失去了它的政治影响。普鲁士国民议会的瓦解,维也纳十月大起义的失败,对罗伯特·布鲁姆的暗杀,彻底宣告了1848年大革命的失败。舒尔茨在此后还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继续捍卫激进的革命性主张,如要求废除封建贵族特权。最后,舒尔茨再次被宣布为“政治犯”而被通缉,在1849年7月初,舒尔茨逃回了瑞士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涯。
3.1848年革命时期。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吸引了大量流亡在外的德国革命人士返回德国从事革命运动。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流亡生涯之后,舒尔茨在1848年3月第一次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以国民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举行的宪法会议。在议会中,舒尔茨站在左派行列的一侧。此后,自由保守主义代表的多数倒向了贵族势力,当遭受这一挫折之后,舒尔茨放下其共和理念,致力于推动君主立宪制政体。他主张君主立宪政体必须在容纳议会的反对力量和人民的声音的情况下才能够真正施行,所以在保罗教堂国民议会结束十天之后,他强烈呼吁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解决底层人民的失业和贫困、创办民兵部队、设立执行委员会来监督议会决议的实行。然而舒尔茨的提案和呼吁收效甚微。舒尔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左派已经遭遇了必然的失败命运,左派的提案一再被否决,一系列反动政策被推行。左派最后也陷入破裂之中,在1848年9月17日,法兰克福爆发了流血起义。
智慧公交APP可以显示公交线路和站点,选择某个站点,可以看到最近车辆的到达时间、车辆估计距离和站数,在提高乘客出行效率的同时,查看电子公交站牌上摄像头拍摄的公交站实时视频,相关界面如图7所示。
《生产运动》一书出版之后,在德国理论界很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引用了它。当然,这本书的出版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论。其中就有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这两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舒尔茨的批判。舒尔茨在《生产运动》导言中对赫斯的行动哲学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激进主张进行了批判,抨击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废除货币的主张是一种如废除文字一样的幼稚主张;(8) 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 Zürich,1843, S.79.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对舒尔茨的批判进行了回应,他批判舒尔茨“忽略了我们在货币中所占有的物质资本和我们通过文字能够占有的精神资本之间的区别”。(9) 赫斯认为,“我们通过文字能够占有精神财富。但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要把我们通过文字和著作占有的(精神的)财富硬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然后把它传给其私人后代。”(10) [德]莫泽斯·赫斯:《赫斯精粹》,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货币财富是可以占有的,而精神财富是无法私人占有的,这是舒尔茨没有认识到的。
舒尔茨的军事政策理论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反响。舒尔茨认为,他曾经在无神论论战中的立场使他与大众产生了距离。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不是向大众靠近,而是在此后的岁月里更加努力地试图将他的军事政策和计划向政客与军人阶层兜售,但显然这也是天真之举。一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他还积极撰写宣传裁军政策和和平主义的传单。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1860年,舒尔茨在苏黎世去世。
如果要对舒尔茨进行一个身份界定的话,我们可以把他称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评论家。他坚定地反对德国的封建专制和保守力量,看到了大众所遭受的压迫和不公,但他又拒斥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反对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立场。而这些政治上的主张,其实正是由舒尔茨思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所决定的,这些正体现在他1843年出版的代表作《生产运动》之中。
二、《生产运动》的出版及影响
《生产运动》一书1843年于苏黎世出版,出版商是同为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尤里乌斯·弗吕波尔。《生产运动》一书内容本是为《德意志季刊》(6) 《德意志季刊》(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由科塔出版社发行的一份理论刊物,自1839年至1869年间发行。《德意志季刊》刊文主题广泛,但主要集中在经济、政治理论方面。 撰写的文章,其中第一部分在1840年便以“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态的影响”为题在《德意志季刊》上发表。而第二部分则拖了三年,最终,舒尔茨将两部分合并为一本书出版,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生产运动》。
舒尔茨退役之后在吉森大学学习法律,并于1823年通过了法律专业考试。然而由于已经得罪了黑森大公国的贵族,当局拒绝舒尔茨从事法院的工作,他不得不另谋职业以糊口。在1825年到1831年间舒尔茨为德国著名的出版人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4) 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1764—1832),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出版家,工业先驱、政治家。1822年受封为巴伐利亚男爵。在他的经营下,他的家族企业科塔出版社蓬勃发展,成为歌德、席勒、荷尔德林等众多德国当时知识界名流的出版商。 的《金星》杂志做编辑和翻译。1828年舒尔茨同自由主义律师卡尔·布赫纳在达姆施塔特创立了《友谊月报》。之后,他同卡洛琳·萨托修斯结婚。
舒尔茨在《生产运动》一书中所运用的方法,其实就是他在博士论文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一种统计学的研究方法。这本书的副标题——“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需要注意的是,舒尔茨所说的统计学方法,并非当代意义上的那种数理统计学方法,而是19世纪上半叶语境中的国势学派(7) 国势学是现代统计学的重要源头之一,最早产生于17世纪的德国,奠基者是海尔曼·康令(Hermann Conring,1606—1681)。康令是一位博学家。1660年11月20日起,他开设“国势学”(Notitia rerum publicarum)的课程。康令去世后,他的弟子戈贝尔于1730年整理出版了他的六卷本《康令政治法律讲义》,其中第四卷为《国势学》(Staatenkunde)。康令将过去的地理、历史和法律研究与国家治理的实际目的结合起来,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探究原因,总结规律。在康令之后,阿亨瓦尔(Gottfried Achenwall,1719—1772)继续推进了康令的国势学理论。阿亨瓦尔1749年发表了《欧洲各国国家科学引论》,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第一次使用了“Statistik”(统计学)。阿亨瓦尔认为“统计学为国家显著事项的结晶体”,是通过对这些显著事项(包括地理、法律、政治状态等)的记述,为国家管理提供支持。阿亨瓦尔继承了康令的研究方法,并将康令视作开拓者,称其为“统计学之父”。国势学派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奥古斯特·路德维希·冯·施略策(August Ludwig von Schlözer,1735—1809)有一句名言:“统计是静态的历史,历史是动态的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运用统计学研究历史趋势的做法。 和政治算术意义上的统计学。在舒尔茨这里,统计学则体现为对物质生产组织变化规律和精神生产规律的探寻。
4) 系统所需的控制器不能与现有部件干涉,并且处理速度要快,环境要求度不能太高。因此选用嵌入式开发板作为控制处理单元以满足上述要求。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大段摘录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但此时马克思对舒尔茨的评价并不高,将他认作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加以批判。其实当时马克思对舒尔茨的判断,或许正是受到了赫斯和格律恩等人的影响。此后,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这一著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机器问题时,再度引用了《生产运动》,并称“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生产运动》的阅读横跨了他的不同阶段,而马克思对《生产运动》的评价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格律恩在他1845年主编出版的《新轶文集》中专门为《生产运动》写作了一篇书评。在这份书评中,格律恩详细地批驳了舒尔茨的观点,特别指出了舒尔茨思想中的诸多矛盾之处。格律恩批驳了舒尔茨将民主等同于新教产物的看法,也批判了他一方面赞颂法国大革命在文化上带来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回避革命的做法;(11) 与赫斯一样,格律恩也批判了舒尔茨将货币的意义与文字等同的做法。(12) 最后,格律恩还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就舒尔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进行了回应,认为舒尔茨一方面将青年黑格尔派视作是客观的、理想的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立场,这两种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13) Karl Grün,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 in Neue Anekdota, Damstadt, 1845, S.231-232,S.241-242,S.243-246.
罗四强笑了起来,说:“爸爸你也莫太贪心了。我们还得有姆妈,还得有老婆,还得有自己的伢。爸爸你占个角落就蛮好了。”
《生产运动》再度进入人们视野,是在20世纪20年代了。我们现在可以找到两篇关于研究舒尔茨的博士论文,一篇是法兰克福大学1919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1797—1860):德国三月革命前的自由主义研究》;另一篇同样是法兰克福大学1926年的一篇名为《威廉·舒尔茨和他在1830年革命之后(1836—1860)的政治影响:三月革命前自由主义史研究》的博士论文。此后,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古斯特·科尔纽在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二卷中专门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思想进行了评述,并探讨了舒尔茨的思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系问题。科尔纽做出这样的判断:“马克思还同意舒尔茨的这样一个观点,即生产的发展在需要扩大的基础上的分工决定着各种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的依次更替,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的斗争。”(15) [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II 1844—1845》,王以铸、刘丕坤、杨静远译,三联书店,1965年,第144页。 科尔纽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个探讨舒尔茨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学者。
1979年,奥地利裔以色列历史学家瓦尔特·格拉布出版了《舒尔茨传》,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研究了舒尔茨的生平和思想。这本书尤为醒目地以“一个给予马克思灵感的人”为正标题,在其中对《生产运动》的理论思想及其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格拉布敏锐地抓住了《生产运动》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表述和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上的相似性,认为舒尔茨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的重要理论来源。(16) Walter Grab, Ein Mann der Marx Ideen Gab ,Wilhelm Schulz ,Weggef ährte Georg B üchners ,Demokrat der Paulskirche , Düsseldorf, 1979, S.211-213.格拉布的这本《舒尔茨传》,因此也成为历史上第一本直接探讨舒尔茨和马克思理论关系的著作。
在格拉布之后,还有两本研究舒尔茨和马克思思想关系的著作。一本是日本学者植村邦彦1990年出版的《从舒尔茨到马克思:近代的自我认识》,这是作者1981年完成于一桥大学的博士论文。作者比较了舒尔茨的统计学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异同,对比了两人在社会改造上的不同立场和主张。另一本是德国学者米夏埃尔·沙利希1994年在汉诺威大学的博士论文《舒尔茨与马克思:论马克思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接受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行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影响》。这一著作系统地研究了舒尔茨《生产运动》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基本概念以及舒尔茨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索中的潜在影响。
但是总体看来,既往对于舒尔茨和《生产运动》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如何来理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舒尔茨《生产运动》的忽视(也包括马克思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如李斯特、赫斯等人),本身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些研究过程中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思想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来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形成史的问题是根本不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承认马克思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但坚决反对苏联教科书体系中确立的严整的、体系化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因而也极少探讨这一哲学世界观的来源;同样,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也反对这种体系化的哲学世界观理论,将其视作恩格斯的臆造,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做这种哲学世界观的生成史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苏东学界来说问题则是另外一种情形的。苏东学者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列宁指认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来源之上,因而很少进行这种细致而微观的思想史研究。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2017年11月,德国MEGA2编辑专家福尔格拉夫博士来南京大学访问,笔者负责接待,趁这个机会与这位成长于东德的老专家请教《生产运动》的翻译问题。令笔者极其惊讶的是,当福尔格拉夫听到舒尔茨的《生产运动》这本书时,很平静地说:“das war mein Liebling!”(这曾是我的最爱!)原来,据他讲述,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他就已经认识到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他一度计划要写一篇论文,但最后遗憾的未能成文。福尔格拉夫先生说道,在他年轻时的研究过程中,就认识到例如舒尔茨、李斯特和李嘉图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关键意义,但是,他在科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总是认为他在做一些不重要的研究,关注的都是这些次要的“小角色”,而他们要关注的则是如黑格尔这样的“大角色”。福尔格拉夫先生所讲的亲身经历,足以证明当年苏东理论界的整体研究风格,是不大可能重视这本著作的。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国际上一些走在马克思思想,特别是文本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对舒尔茨和他的《生产运动》的意义和地位都不陌生。在今天,舒尔茨和他的《生产运动》走进我们中国学者的视野内,也正是我们学界前辈艰辛积累和锐意探索的水到渠成之事。
三、《生产运动》的主要思想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舒尔茨《生产运动》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生产运动》一书共分为“导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三章,其中精神生产部分又划分为“历史的角度”和“统计学的角度”两部分。
在“导言”中,舒尔茨分析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撕裂的危险,批评了蒲鲁东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激进主张。认为“废除私有财产”的口号,只会激化社会的矛盾,成为加剧社会分裂的经济危机的原因。(17) 舒尔茨还分析了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德国的反映,这其中尤其以赫斯的行动哲学为代表,他批评赫斯的行动哲学不过就是脱离了大众书斋中的哲学而已。(18) 但是,舒尔茨并非简单否定当时的激进主张,而是要“像对待所有东西一样,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一事情,考虑它的原因和结果。”(19) 最后,舒尔茨提出了自己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发现社会背后“自然发生的东西”,也就是符合规律性的物质生产的全部过程,即“对生产及其组织的当代结构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20) 这种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在舒尔茨这里就是斯密的分工规律的具体表现。(21) 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 S.3-4,S.7,S.6,S.8,S.9.斯密的分工理论构成了舒尔茨剖析物质生产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论来源。
“物质生产”是《生产运动》这本书最关键的一章。舒尔茨首先申明,“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22) 这其实是舒尔茨对人的创造性的强调,正是人创造了物质的财富与精神的财富。因此,“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就被描述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方面,从而运动规律的两个方面也必须要被证明。”(23) 以历史的线索梳理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他划分不同阶段的标准,就是人物质生产能力和物质生产组织的发展水平。舒尔茨明确将生产力区分为手的劳动(Handarbeit)、手工(Handwerk)、工场(Manufactur)和机器(Maschinenwesen)这四个不同阶段。(24) 舒尔茨探讨物质生产的一个中心逻辑,就是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上,探讨物质生产的三个主要分支,即农业、行业和商业的发展变化。但是在探讨中,舒尔茨已经通过对不同的物质生产力的研究,探讨社会关系和等级、宗教和法律的形式、脑体分工、人口构成、城乡分化等问题都相应有不同的表现。历史的视角不仅是纵向的,还可以是横向的。舒尔茨将英国、法国、德国乃至俄国等欧洲主要国家的人口构成、土地用途、生产力状况都加以详实的数据比较,进而指出不同物质生产力和生产组织之上的差异在政治层面的反映。这里充分展现了舒尔茨受国势学统计方法的影响。在这一章的后面,舒尔茨还通过数据的比较,指出了物质生产的进步,特别是与之相伴的自由竞争,带来的是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些并没有给工人阶级的生活境遇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加剧了贫富的对立。(25) 但是,克服这种情况的途径在哪里呢?在这一章最后,舒尔茨则相信伴随着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扩张,会使人们的精神交往更加成熟,从而建立起共同生活和共同行动的可能性,来彻底征服盲目的自然力和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种共同的市民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它绝不是任何一种庸俗的平均主义思想——才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意识之中。”(26)
在“精神生产”章的第一部分,舒尔茨从历史的角度,将物质生产运动之中的分工规律继续推进到人的精神活动之中。舒尔茨指出,“物质的生产运动可以被视作一种扩展(Entfaltung)……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从一种由自然决定的一定的定在的核心和萌芽中扩展出来,这一定在正在其规定性中背负着它发展的规律……”。(27) 对精神生产的分析,首先从语言开始。语言的形成是人的精神生产的基础,它从一开始就与感性世界纠缠在一起,从中不断获得自我的独立性,通过音节和符号语言,图像和拼音语言发展的。精神生产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宗教领域,舒尔茨概括了自然宗教、泛神论、多神论和基督教这样几个不同阶段。他将基督教视作对之前不同宗教发展阶段的吸收与超越。舒尔茨高度肯定基督教的价值,认为其内涵了自由、平等和统一,是精神生产中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也是国家和社会领域新科学的根本动力。此后,舒尔茨继续探讨在文化和科学领域之中的规律。同样是在历史的维度下,舒尔茨详细考察了艺术、政治学、教育、法律乃至国民经济学等对象自古希腊到罗马时期,再到近代以来的不同发展状况。研究的领域尽管宽泛,但是舒尔茨贯穿始终的方法就是各个对象内在的分化规律。
舒尔茨在“精神生产”章的第二部分统计学中,则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基督教民族之中。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把握住当代精神状况的划分,在其合规律性的前进运动中和过去区分开来的时候,科学才会产生。”(28) 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S.10,S.10,S.38-39,S.65-69,S.74,S.75-76,S.122.也就是说,在舒尔茨看来只有基督教民族那里才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明确的不同环节,也才有科学地加以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舒尔茨的观点颇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色彩,在本质上也代表了舒尔茨哲学观上的保守立场。基督教本身也被舒尔茨按照希腊教会、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这三个不同分支,按照从低到高的不同阶段加以审视,考察其中的教义和组织原则,并通过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教徒人口数量等统计数据来对三个教会的发展走向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尤其高度颂扬了新教教义中的自由原则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舒尔茨在这一部分的后一段,继续探讨了雕塑、诗歌、小说和哲学领域在最近的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在这里,舒尔茨尤其强调了无产阶级在诗歌、歌曲等方面的艺术创造;(29) 而且还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特别对青年黑格尔派作了评述,将他们称作“哲学暴徒”,(30) Wilhelm Schulz,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S.160-161, S.166.这主要是对他们的无神论观点的批评。联想到上文中赫斯、格律恩与舒尔茨之间的争论,我们发现青年黑格尔派和舒尔茨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有趣的“视差”:青年黑格尔派主张无神论,但在历史观上却是唯心主义的;而舒尔茨尽管站在基督教立场之上,但他在看待历史时却常常坚持实证的方法,始终注意分析现实中的矛盾运动。或许,这种“视差”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诞生的思想语境。
我到里间给姑娘热米饭,端碗出来的时候,却见她正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一边烤火,一边烤衣服。她长得本就非常漂亮,而当时橘红的火焰又正映照着她的全身,更加显得她娇艳无比。
结 语
我们研究舒尔茨及其《生产运动》一书,是为了批判地比较这本书的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舒尔茨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清楚且严重的,他的有神论立场,将新教的自由原则视作时代弊病的解药,以及在这种立场之上的西方中心论的观点,这都是我们要坚决加以批判和拒斥的。但与此同时,舒尔茨对物质生产运动发展过程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关系的揭示,对精神生产内在规律和文化现象的论述,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产生过程及其伟大飞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很少有哪位理论家的理论是完美无缺的,何况这样一个生活在大变革时代的理论家。
A Neglected Ob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hulz and 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Li Qiankun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Key words ]Schulz;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material production; spirit production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hist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hulz’s 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has entered the field of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in recent years.Schulz’s life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learning and growth, first exile, participation in the 1848 Revolution, and the second exile. The Movement of Production was published in 1843 during his first exile, and it caused some controversy after public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the neglect of Schulz’s thought wa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arxist stud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in the 20th century. In order to respond to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Production of Movement analyzes the laws in material production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spiritual production.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舒尔茨《生产运动》翻译”(项目号:17 HQ00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苏 南京 210023)。
[责任编辑 孔 伟]
标签:舒尔茨论文; 《生产运动》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论文; 物质生产论文; 精神生产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