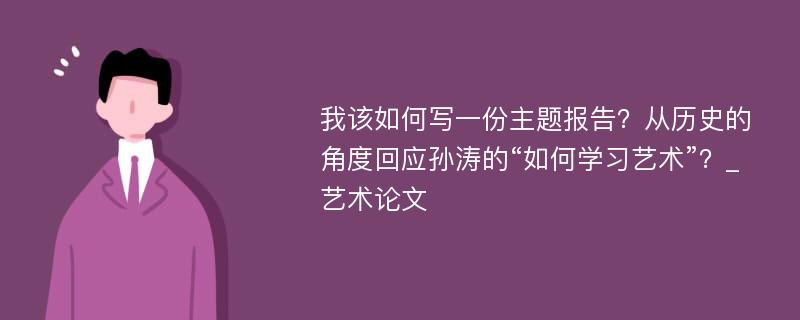
应当怎样写学科报告?——回应孙焘《艺术学如何“以史出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学论文,学科论文,怎样写论文,报告论文,史出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信奉,然而,一个人只要对自己所写有了相当的投入,会时常对之牵挂。“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是一项在教育部组织下的学术写作。我自2005年参加这一项目中的艺术学年度报告的写作以来,每年写完之后,都时常反躬自审,一旦自己发现或经友人指出不足之处,就在来年的报告里或自己的文章中予以补正。2008年写作的艺术学三十年学科报告,是一项比年度报告更艰难的工作。写完之后,同样常常自省,也非常希望得到同行与读者的批评指正。前些天,一位同事告诉我,有一篇长文在批评我写的学科报告。但我一看到题目就有些失望,继续读下去是大失所望:我面对的是一篇只顾抒发个人读书感想的率意文章。如此之文,也许对批评者自己所感所想的问题来说,不是没有一定的意义,但对于批评对象(即如何提高学科报告的写作和如何提升报告中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几乎没有帮助。我对此类评论,历来不予理会。然而,这一次,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不得不来进行一下解说。
一、以偏论全的文章标题
前面说到,我一看见题目就大失所望。大家知道,关于三十年艺术学的学科报告,要对学科的整体发展作一全面的呈现。首先要呈现学科演进的历史概况(上编),其次要讲学科体系的发展、学术研究的状况、出现的重大事件(中编),最后,要对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归纳(下编)。而书评的题目是什么呢?——《艺术学如何“以史出论”——评张法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正标题针对的问题是本书(下文简称《报告》。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中下编共五章里面的一章(第七章)中共四节当中的一节(第三节)讨论的问题,而副标题却笼盖全书。如果要人感觉不到逻辑毛病,文章名称一定是这样的:《艺术学如何“以史出论”——评张法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孙焘加上后面这些字,我就不会来写这篇回应文章了。
由于孙焘文章一开始就定位在(对整个报告来说)一个小点上,以后洋洋洒洒的宏论,都围绕这一点说去:一、重“史”与轻“论”,二、艺术学之“学”,三、史与论如何统一:谈“理论感”。并且在最后的“结论”中,不无骄傲地宣告:
本文的观点是:在学术研究内部的“史”、“论”关系上,无“史”即无“论”,无“论”亦无“史”;在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实践的关系上,研究不是被动地解释艺术创作,而是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持。中国艺术学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的不是放弃理论的追求,而是对理论体系做一番更新,使之更好地与艺术史研究和当代艺术实践互动。这个意义上的“论”当然与《报告》所批评的那个脱离了“史”的“论”不同。真正的“论”要求一种“理论感”,即是通过对于具体史料、史实的洞悉,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或者方法。这才是“史”、“论”配合的正途。
就这样,从文章标题到小标题到结论,以一个“如何以史出论”的提问开始,以“要史论结合”的标准答案结束,来评一本内容远不止此的学科报告。这好像魏晋时的阮籍对自己喜欢的人用青眼,对自己不喜欢的人用白眼。然而,阮籍不只是好用青眼白眼,他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还会音乐,还能饮酒,还写了名垂千古的《咏怀诗》,等等等等。如果这时,一位批评家写一篇宏文《应当怎样正确地使用青眼白眼——评阮籍这个人》,当时的人会怎样看呢?
二、“重史”错了吗?——评“重‘史’轻‘论’”的错误判断
其实此文并非没有对《报告》作一全景式评述,行文中不断地纵横前后,为其立论挑选例证。这里我姑妄“大胆假设”一下,孙焘读到下编第334页开始的第七章第三节“艺术学的理论模式:‘以论带史’与‘以史出论’”,于是蓦然悟出《报告》的“主旨”(这对于作者来说算是有心得,但对于《报告》主旨来说确实太偏离),而且沿着自以为得之的“主旨”,下了一个对《报告》来说完全是错误的判断:整个《报告》是重史轻论!于是以此为主题,在《报告》的前前后后去挑选对自己的立论有用的事例,完成整个批评宏文。
这里且对孙焘所谓《报告》的“重史轻论”一一进行申辩。先看其对“重史”的责难。
一看《报告》的书名,《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艺术学》,谁都应该知道,这是一本写史的书,写史的书不重史,岂不是文不对题?而对一部写史的书指责其重史,总觉得怪怪的。因此,孙焘对《报告》的批评不应该是重不重史的问题,而应该是怎样写史的问题。《报告》上编“艺术学三十年学术发展概况”是写史,分三章写三个时期:走出“文革”与艺术学的多重演进(1978-1985),解放思想与艺术学的形式更新(1985-1990),社会转型与艺术学的多元互动(1990-2008)。一个好的批评应该指出,第一,这三个时期的划分及其主要论题是否有不当之处;第二,对三个时期中每一方面大论题和小论题是否有不当之处;第三,对每一方面论题的呈现叙述方式是否有不当之处。细读孙焘全文,对第一方面没有(实对实的)提问。在第二方面,提了两个问题,一是:
缺乏对艺术学历史沿革的背景考察。社会整体环境的影响无论有多大,毕竟是“外因”;中国艺术学之所以具备今天的面貌,更多地还是受到在改革前基本奠定的学理资源、讨论平台乃至教材话语等“内因”的影响。《报告》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不够充分,影响了分析问题的深度。
这一责难是不确实的。《报告》第一章一开始就写了“文革”艺术学模式是四大要点(一是对艺术学的定位,二是歌颂暴露的文艺视角,三是“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四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并指出改革开放的艺术学正是从这里告别“文革”走向新途的(第17-18页)。这正是孙焘文讲的“内因”,也正是“学理资源和讨论平台”。至于“教材话语”,非常希望孙焘能够说出他心中的“教材话语”指的是什么教材(据我所知,改革开放前未出过“艺术概论”的著作,第一本《艺术概论》出版于1983年;当然也可能他指的是一些艺术门类性教材,但也应该指出究竟是哪些门类艺术教材构成了艺术学的“教材话语”),这些教材是怎样不同于《报告》讲的四点,以及怎样影响改革后的艺术学的?
孙焘提的第二个问题是:《报告》“遗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领域”。究竟是哪“一些”呢?哪怕是罗列一下名称也好让人明白。孙焘没有这样做,而是“仅以‘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为例”,然后就大谈“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艺术学如何重要,而《报告》“未有任何关注”。只举一例,在学术上是孤证,不具说服力,退一步讲,你只能举一例,那么这一例一定要非常非常典型,有巨大的说服力,才能减轻其孤证之缺陷,而孙焘仅举的这一例,恰恰是错例!如果孙焘翻读一下学科目录,就会知道,在中国目前的学科体系中,美学属于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文艺美学属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二级学科文艺学下面的一个方向,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主要在文艺学界,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呈现和讨论是放在《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之中的(在该书的第173-176页)。
其实,如果孙焘下笔之前,有耐心研究一下艺术学三十年的发展史,是应该真正地发现被遗漏了的问题的。我写了《报告》之后,时常自省,已经发现了一些遗漏的且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且举数例:一、水墨画的问题(从实验水墨到现代水墨到水墨画和从文人画到中国画到水墨画的复杂而绞缠的演进);二、从中国现代艺术到中国前卫艺术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变换引出的问题;三、关于何为主流电影的讨论;四、关于音乐剧的问题;五、关于电子音乐的问题;六、关于张继刚舞蹈现象;七、关于中国当代舞……这些重要问题,虽然一时间不易被发现,但只要多读多想,还是可以悟出的。我在后来的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的“艺术学”一章以及以后的文章中,对上面七个问题,都予以了重点介绍,算是补遗。另外还有一些问题,会在以后的年度报告和个人文章中进一步补充。
孙焘对《报告》批评得很多的是第三方面,在这一方面,孙焘评点《报告》在史的叙述里,哪些应该详写而哪些应该略写。孙焘说,1988年美术界进行的有关“伪古典”和“伪现代”问题的讨论,“第六代”电影的思想文化地位展开的讨论,笔墨用少了,而1989“中国现代艺术展”当中“卖大虾”、“枪击事件”,“第五代”电影代表作的剧情、流行歌的歌词,写得过多了。对上面两个理论事件(“伪古典”、“伪现代”和“第六代”电影)关注得少了,对张艺谋的《红高粱》、崔健的《一无所有》或蔡国强在纽约搞的焰火艺术兴趣过多了。首先,任何文章,字数的多少得一看行文语境,二看表述方式,字数不代表重要,重要处,可在文内而实写,也可在文外而虚字,所谓“无字处皆其意”也。第二,就孙焘所举之例,他提的写少了的两个问题(“伪古典”、“伪现代”美术和“第六代”电影),在我看来,远不如“中国现代艺术展”和“第五代”电影重要,也不如张艺谋、崔健、蔡国强重要,当然这是我的见解,你可说你是对的,但不要轻易说别人错了,应当改错。最有意思的是孙焘教训说,《报告》下编在“全球化”部分(第366页)“仅把十七篇文章的题目列举出来,既没有说明挑选它们的理由,也没有交待它们之间有何交集或碰撞”。这里,《报告》只列举文章是要说明“全球化在世纪之交成了中国学界的关键词,很快成了艺术学界的关键词”(第366页),而不是要去细讲大家在论全球化时观点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正如,有一群人来了,应关注的是有没有一群人,因此我说有一群人,你批判我:只说有一群人,没有区分一群人中有小孩大人男人女人。也许别人分了大小男女,你还可以说:没有写出男人女人发型不同,衣着不同……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孙焘是以怎样的中国艺术学史的“史学”和“眼光”来对《报告》中的所谓“重史轻论”中的“重史”进行批评的了。
三、“轻论”存在吗?——再评“重‘史’轻‘论’”的错误判断
孙焘给《报告》定了“重史轻论”的结论之后,一再加以强调,一会儿是“重史轻论”一会儿是“厚史薄论”,甚而还有“因史弃论”之词。读者只要翻一翻《报告》就知道所谓的“轻论”、“薄论”、“弃论”之说与事实不符。《报告》分为三编,中编讨论艺术学三十年的学科体系、学术研究,重大关节,全都是与理论相关的。用一章来呈现艺术学学科的结构、机构类型和学科层,就是要让人清楚中国艺术学的现状是怎样的;用一章来讲艺术学三十年进行的学术研究,通过期刊、重大课题、著作三个方面,呈现艺术学的研究状况;用一章讲艺术学三十年来的重大事件、重要成果、理论创新,呈现艺术学演进中的重大理论关节。这三个方面呈现,都是为对艺术学理论状况的总结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都是与“论”紧密相关的。由于“学科报告”的性质,重要的是提供客观的材料,在客观材料的基础上做谨慎的归纳,而忌轻率结论,因此,其“论”是以呈现事实的方式出现的,但是围绕“论”而进行的,而且又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性质的判断,如在艺术学的机构类型里,提出“中国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具有五个系列”(第244页);在学科层级上,提出“艺术类院校与综合类院校将会成为两个互补的群体”(第259页);在对期刊的数据分析中,提出“艺术院校的学术优势正在相对地失去,综合类院校正在追赶上来”;在对论著的分析中,提出了“如何把艺术概论与艺术史更好地结合起来,与艺术门类概论结合起来,是三个艺术学科的学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为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型艺术学的“论”服务的,而不是为“史”服务的。其实,整个报告的这一篇,都不应该从“史”或“论”的角度去看,而有自身事实角度,但当你被孙焘强以“重史轻论”扭过来看整个《报告》,把你拖进不得不从“史”或“论”的两分法来看问题的时候,这一编无疑是与“论”相关的,关系到整个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和现状的一系列问题。就此而论,“轻论”何在?
《报告》下编,把整个艺术学三十年的重大问题,归结为五个理论问题来呈现和讨论:一、艺术学的重要理论点: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二、艺术学的重要关键词:传统性与现代性;三、艺术学的重要关键词:全球化与本土化;四、艺术学的最近关键词:艺术中的中国形象;五、艺术学的未来关注点:在大国崛起和文化复兴中的全球互动。哪一个不是谈艺术学的理论问题?用整个下编来呈现和谈论艺术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读了整个下编的人怎么会得出“重史轻论”、“厚史薄论”、“因史弃论”的结论呢?
《报告》上编,虽然是写三十年发展概况,属于“史”,但写史是需要一个“论”的框架的。三十年艺术学史分为三段,每一段都是要归结为一个理论性的主题的,三章的标题就是一个大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主题。艺术学最初的“走出文革,回归人性,追求艺术特性”;继而在思想解放中引起艺术现代形式而对旧的艺术陈规、以及内蕴在陈规后面的思想意识形成巨大冲击,形成了中国型的现代艺术;最后,在市场改革中出现大众艺术,现代艺术在新的格局中与世界互动而产生多方面的变易,主旋律艺术形成自身的样态,从而三大艺术在时代的演进中呈现为多元互动。在对艺术学演进的三十年的史的呈现和叙述中,是需要一个理论框架而又确实有一个理论模式在驾驭叙述和驾驭史实的。由于《报告》的体例,尽量要把理论放在叙述的后面,有“论”而不凸显“论”,不凸显“论”而又有“论”在其中,要以“寓论于史”的方式进行。如果读者只看见如此叙述出来的“史”而看不见“史”的叙述后面的“论”,作者只能对这样的阅读表示遗憾。也希望这样的读者去读一下同类的著作,看看其基本框架、史实呈现、资料组织、叙述方式与《报告》有什么不同。多读两本,看见了不同,就知道“史”的叙述后面是有一个“论”在其中的了。
总而言之,《报告》三编,中编与“论”相关,下编全是“论”,上编史中有“论”。真不知道“重史轻论”、“厚史薄论”、“因史弃论”之“论”从何谈起?
四、何谓艺术学之“论”?
其实,孙焘的整个“重史轻论”的立论,都是建立在对《报告》下编第七章第三节讲的“以史出论”和“以论带史”的误读和错解上。那节主要是讲从政治看学术的苏联模式和从学术看学术的西方模式的差异带来的艺术学学科结构方式的不同。而对学术的学术反思成为中国历史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热点。“以史出论”和“以论带史”强调的是:理论应当从哪里来,是来自政治权威话语关于艺术的认定,还是来自对艺术历史存在进行学术性总结。或者说,理论应当怎样保证学术的真理性,是由政治权威话语来保证,还是由学术的小心求证来保证。“以史出论”和“以论带史”,这两个“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孙焘是看到两个“论”的不同的,但在论述中却只从一个“论”出发,而把问题偏到“史”与“论”何为重要上去了。因此在论述基调中,只有一个“论”。而“以史出论”和“以论带史”,一个是学术性的小心求证之“论”,一个是政治性的垄断真理之“论”。不理解这两个“论”之间的区别,不读读中国历史学界自90年代以来一直提倡的追求真理的“论从史出”,反对惟上惟书的注释权威的“以论带史”,仅从字面去看这两个口号之争,当然会绕到一个从本质上讲与此论无关的什么“无史亦无论”和“无论亦无史”的“史论结合”的所谓“正途”上去了。
孙焘既不了解中国史学界讨论“论从史出”的学术背景,又把《报告》的一小节里仅限于学科状态和艺术概论写作模式的“以史出论”和“以论带史”的讨论,扩大成整个《报告》的主题,从而把“论”变成了所谓艺术学的“学理”,进一步说,《报告》的“不足之处是对学理发展的关注相对不够”。孙焘对“论”、对“学理”是怎样理解的呢?这就关联到他对艺术学之“学”的理解。因此,我把二者放到一起来讲。
五、何谓艺术学之“学”?
孙焘的一个批评重点,是说《报告》“对于‘学’的模糊认识”,因此文章一节的题目就是“何谓艺术学之‘学’”。而孙焘所谓《报告》对“‘学’的模糊认识”却只建立在下编第七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上,从而“艺术学的‘学’就被等同于那个‘以论带史’的‘论’”。这是对《报告》关于“学”的曲解。只要认真把《报告》“引言”、中编第四章、下编第七章结合起来看,就不难理解《报告》关于艺术学之“学”的内容。艺术学从学理或曰学术体系上讲,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文学、电影、电视这八大艺术和舞蹈、书法等一些小艺术门类的统一体系,从学科上讲(经国务院1997年学科目录公布以来的调整),是艺术学(二级)、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舞蹈学组成的结构。从这两个角度的统一就可以得出今日中国的艺术学之“学”。因此,艺术学之“学”不是“以论带史”的“论”,也不是艺术概论。孙焘只读一节,把《报告》在一节之中主要从学术管理方式讲艺术学的言说,武断地扩大为是《报告》对整个艺术学之“学”的定义,然后不顾前后地对之进行批评。这说明孙焘对什么是“艺术学”之“学”知之甚少(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受命写艺术学学科报告之前也不懂。在写的过程中,我向一些门类艺术领域的专家请教,说我在写艺术学的学科报告,他们几乎都不知道艺术学是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搞的门类艺术,我不得不给他们解释艺术学的学科体系和范围)。在孙焘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对近三十年艺术学学科史的梳理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学’的层面,对象是艺术实践,包括绘画、音乐、电影等艺术门类;二是‘学之学’的层面,对象是三十年来中国艺术学的理论成果,其中包括针对艺术现象的各种观点、讨论、思潮等。”艺术学学科史的“学”和“学之学”真“应该”像这样定义吗?
艺术学之“学”既与学术体系也与学科体系相关,这是中国艺术学的现实,如何处理这一现实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如何从在平衡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方面总结出作为艺术学的总体之“论”,目前是在“艺术概论”这一领域进行,各艺术门类的门类概论也与总结艺术学之“学”有关,而且是其基础。只有了解了艺术学之“学”的复杂性,才谈得上讲什么“艺术学”的学理。而孙焘对这一复杂状况基本上是忽略的,因此,才“勇于立论”地大讲艺术学的学理。孙焘在文章中不时地高举学理大旗,一会儿说《报告》的“不足之处是对学理发展的关注相对不够”,一会儿又说《报告》“既缺乏艺术学内部的逻辑线索以统摄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史,又对三十年来的中国艺术学的学理发展过于淡漠”。我真想搞清楚,什么是孙焘心目中的“艺术学内部的逻辑线索”?什么是孙焘心目中的艺术学的“学理”?
六、这样“评”是否为实事求是?
前面说了,我读了孙焘的文章“大失所望”,既在上面说的几点,更在作文的“风格”上。如下几点是我觉得有问题、值得提出来的。
第一点,无视本意的率意归纳。
其一,孙焘在总论里说:“该书也存在若干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厘清‘艺术’与‘艺术学’的关系,因而无法充分实现揭示‘艺术演进与艺术理论演进的互动’的初衷。”且不论问题抓对与否,《报告》明明讲仅仅“上编从艺术演进和艺术理论演进的互动中对艺术学进行总体描述”,不是中编和下编,因此不是全书的初衷,正确的提法应是“该书上编的不足”。
其二,“这几处都是把理论建树与文艺实践两方面的发展脉络结合在一起分析的好例子。遗憾的是,这些亮点仅散见于个别门类的艺术学,并没有贯彻于全书”。且不论他所谓“好例”选得对不对,请问:需要贯彻到本不是讲理论建树和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中编和下编去吗?
其三,“对近三十年艺术学学科史的梳理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学’的层面……二是‘学之学’的层面……但作者刻意地突出前者、淡化后者,不仅把艺术实践的发展与学理讨论分开论述,而且对前者不厌其详,对后者则明显简化。”驳论见本文第二和第三部分。
其四,“书中提到艺术学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时,就‘文’与‘艺’的地位有一段颇为精彩的论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和‘艺’(以及‘文人’和‘艺人’)不是一个等级,前者高而后者低。然而时代变迁,中国原有的‘文’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隐而不显,尤其90年代以来,市场化、世俗化与电子媒介的勃兴更令文学降位而影视大行。‘艺人’已经在影响力上明显高于‘文人’了(第337页)。‘文’和‘艺’位置的这种倒转看似微小,却投射出整个20世纪的所谓‘现代性’的秘密。《报告》虽已注意到这一纵贯百年、以小见大的好题目,却仅仅将之作为艺术学从文学门类当中独立出来的文化历史根据,没有指出通向艺术的社会功能、地位的历史演变以及古道隐废、雅俗消长这类更为深广的社会背景,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一个讲学科关系的举例中,需要偏离主题地去讲别的关联吗?
第二点,无视文本内容规定的强作要求。
其一,“《报告》的‘中编’包含了大量有关艺术学学科结构、学术期刊、重大课题等统计图表、权威数据等,除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对数据的有效性作了一些说明之外,多数仅限于对文章、著作、会议等学术成果的平面罗列,没有归纳它们的核心论点、理论影响,更没有基于归纳之上的分析和提炼。”《报告》中编的立意就是以呈现为主,隐分析提炼于呈现之中。
其二,“作者仅把十七篇文章的题目列举出来……其实,碰撞还是存在的……把这些观点、角度各异的文章放到一起进行对照,本应成为此类总结报告的任务之一。”驳论前面已讲。
其三,“对近三十年艺术学学科史的梳理应该有两个层面,一是‘学’的层面……二是‘学之学’的层面。”这个“应该”从何说起?
第三点,望文生义的“作者认为”。
其一,“作者认为,当前中国艺术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史研究、艺术实践的关系没有理顺,后两者在‘学’的名义下被理论凌驾其上,难以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所以建议今后的艺术学建设要以艺术史和艺术实践为重”。
其二,“作者提倡以‘以史出论’代替‘以论带史’,抛弃目前的‘理论为上’的思路,把更多的关注放到艺术史的具体问题中去”。
其三,“作者主张艺术院系回到建国初期形成的以艺术创作为主、艺术理论研究为辅的教育结构”。
其四,“当前中国的艺术理论的研究不是如《报告》所言的重视太过,《报告》对此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误解。它倾向把(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等同于‘艺术理论’,又把‘艺术理论’缩小为习见的‘艺术概论’。而对于艺术理论的作用,也仅仅认为它能够弥合被学科体系割裂的艺术学知识体系而已”。
以上议论都来自下编第七章第二节“学与艺术学的特殊性”和第三节“艺术学的理论模式:以论带史与以史出论”,主要是从艺术学的管理制度上讲,一是要怎样兼顾艺术学科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决定一个学科的学术级别(硕士点和博士点)时应当以什么标准(论著还是作品),二是讲两种学科设置方式对学科面貌的影响。虽然也涉及到理论问题,但只是就与学科状态和学科管理相关的一些点和一些面讲理论。而理论全貌并不在这里呈现。细心读者是不难正确地理解文中原意的。而孙焘由之引申出的“作者认为”都不是真正的“作者认为”。
讲了这么多,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两点:一、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学术批评?是学术求真的方式(小心求证)还是发表自己感想的方式(只管自己这么感受的);二、对于《学科报告》这样的文本,应该注意文体的要求,而不要把非文体的要求强加其上而加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