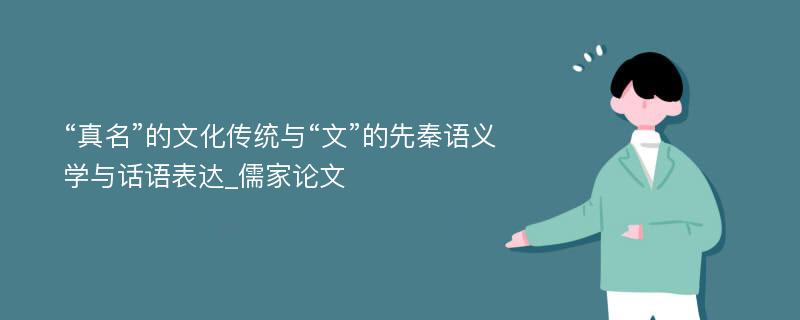
“正名”文化传统与“文”的先秦语义及话语表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先秦论文,话语论文,传统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5)03-0034-07 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个体的等诸因素,作用于社会实践主体,生产着实践主体本身,并生产了与观念相关的产品。由此而言,作为高度发展的观念性产物,中国历史上主要由士人创造出来并发展着的文道观念,绝不是什么天才人物风云兴会而发扬蹈厉所致,必是不同的士人群体承继了前代的文化积淀,并适应着新的历史文化需求而成就其复杂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士人群体的文道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士人文道观念的由来、发展与变化,从而准确把握其文化品格和历史贡献。 梳理学术研究史可见,百年来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如1931年出版的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0年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96年出版的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大都没有认识到士人文道观念之“文”、“道”及“文道关系”的复杂性,只是想当然地把文道观念之“文”看作是“文学”、“文章”或者是载“道”的形式。而通过考察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之“文”可知,他们所用的“文”具有“礼乐制度”、“文明”、“文化”、“道”、“文章”、“文采”等多种义项[1]。这种情形的存在,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古代士人文道观念的不小障碍。本文欲从中国文化中的“正名”传统及“名”的语义层次入手,对中国古代士人文道观念之“文”做些探讨,或有助于学界正确认识特定历史时期士人文道观念内涵的复杂性。 一、中国早期文化中“名”、“实”的非对称性与“正名”文化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名”与“实”关系的探讨,向来为各派思想家及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孔子强调:“必也正名乎!”强调的是以“名”来规范礼用的不同层级,使人们各守其分而不逾矩。他在表述相关历史事件时,经常采用不同的笔法,后人总结为《春秋》“义法”。杜预《春秋左传序》所列其“义法”有五种,其中其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在彼”。如《春秋》成公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这里,称“叔孙侨如”用了氏族名“叔孙氏”,目的是尊君命,称“侨如”而略“叔孙”,是为了尊重夫人。显然,“叔孙侨如”、“侨如”都指的是名称背后的“那个人”。其三曰“婉而成章”。如《春秋》记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事件。其时鲁国有许田在京城,郑国有祊田在泰山,两国交换则祊田抵不上许田,郑国就以璧为补偿。两国之田是周天子赐予的,按照周礼是不能交换的。故《春秋》为之隐晦,只说用璧来借许田。由上述可见,孔子在删定《春秋》时,一件事情有多种表达方式,其名称是多样的。孔子的这一思想,贯穿于儒家的传统经典之中,并得到了后世儒者的不断尊崇,从而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名称共同指向于背后的同一个事物,大概是中国早期文化重要的文化现象。不惟孔子对此有所注意,同时代的老子也看到了“名”之于事物的非对称性。他在《老子》中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云:“强字之曰道”。他认为,就“道”指向的事物而言,其实是不可以说出来的,也就是“道”这个“名”实际上不能涵盖、说明“道”指向的背后的那个“物”。要说明那个“物”,只有勉强地给它起一个“名”。仔细玩味其中的含义,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名”是无法与其所指称的背后之“物”相对等的;二是对于此“物”的取名,是勉强的,亦即只是大致而言的。《老子》的上述两句话,说明了一个关于人类认知问题的常见困惑:“道”是无法言说、无法确指的“物”,“名”无法给与“道”以确指的界定和指称,但要想对它有所认知,又必须给它厘定一个名字,以便于对它的认识、把握和运用。 到了汉代,前代文化中存在的“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引起了董仲舒的注意。他在《春秋繁露·竹林》中写道:“《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邲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董仲舒认为,为了强调同一类事物,《春秋》使用了“常辞”、“变辞”这两种不同的命名方式。他又举《公羊传》释《春秋》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邲,晋师败绩”之文来强调说明,依“常辞”而言,《春秋》当称“晋荀林父”为“晋人”。这里变称其“名”,是因为楚君有礼而晋大夫无礼,是用“变辞”来贬低晋荀林父。显然,如以“常辞”而言,“晋人”也就是“晋荀林父”。可见,不同的命名方式固然受到其“义法”的影响,但转换角度来看,不同的名称都是指的同一个人。 上述在中国早期文化中存在的“名”与其指向的“实”的不一致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事物固然可以给予命名,以方便于对其指称性的认知、识记和语言使用,但由于不同的命名人、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文化环境等因素,往往导致对事物的命名并不一致。比如古人常有名、字、号等,如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我们在使用“欧阳修”、“欧阳永叔”、“醉翁”、“六一居士”、“欧阳文忠”等名称时,指向的都是这些名词背后的“那个”人。可见,名词背后的“那一个”,才是我们研究问题时应关注的对象,而非某一个名词本身。亦即某一“簇”名词可能都指向某一个事物的实质,对问题的研究应该关注这一“簇”名词共同指向的事物本身。 人类文明的发展,必然给人类自身提出如此要求:当社会规则或者标准要求人们必须遵循某一规范时,人们就要以共同承认的、约定俗成的事物名称(此事物可以给与“名”来指称)来衡量或者作为标准判断,如此才可以认识事物。由此,对于这一标准的确定,以及以他物来衡量于此标准,就非常重要。前一个“标准”可以称之为“名”,而后一个以他物来衡量于此“标准”的过程,就是“正名”。当然,确定前一个标准的过程,也是需要不断采取比较、归类等逻辑思维方法的。大概也是因此之故,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都纷纷强调“正名”。其中,荀子、墨子对“正名”的方法、原则等都进行了认真探讨,代表了先秦时期各学派对于“正名”问题认识的高度。荀子为了“正名”而强调“类”:“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杨倞注:“类谓礼法所无、触类而长者,犹律条之比附。《方言》云齐谓法为类也。”[2](P8)《荀子》中《王制》、《大略》两篇文章,均有“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的说法,可知“类”相当于案例。为了“正名”,荀子又讲“分”。《王制》:“人何以能群?曰分。”“分”就是辨别、区分。《非相》:“分莫大于礼。”显然,他认为礼义法度是为了区分层级而服务的。《墨子·非命中》则进而提出了认识事物必须先“立义法”:“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这里的“义法”指的是《墨子·非命上》提到的“三表”:“本之者”、“原之者”、“用之者”。可见,“三表”与荀子所讲的“类”功用相似。当然,孔子、孟子等“正名”,是为了恢复伦理型礼乐制度,而老子、庄子等的“正名”,则是为了强调“道”的重要性,其目的是不一样的。不过,由此发轫,人们开始重视事物与指称事物的“名”之关系的探讨,庄子的“蝴蝶晓梦”说、名家之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韩非子的“说难”等,都已经认识到事物本体与事物之“名”的非对称性问题。 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重要特征,客观存在之“物”与其“名”往往是不一致的,一个事物往往有多个“名”。令人困惑的是,伴随着人类文化的进程,本来指向于同一事物的诸“名”,慢慢由于“正名”的需要而发生了语义的转变,有的语义发生拓展或者缩小,有的语义发生转移,新的语义与之前的没有了联系,更有一些事物的“名”干脆消失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了。 二、“循名责实”的认识方法与士人文道观念之“文”的语义层次 以“正名”方式来考察事物之“名”与事物之体、用等问题的关系,这一认识过程和研究方法,可以称之为“循名责实”。既然“正名”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那么,“循名责实”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认识方法。如果我们对于上述“正名”及“循名责实”问题的认识大致不错的话,那么,在对“文”、“道”、“文道关系”等进行梳理时,就不能单纯考察这三个“名”,还应考察不同的“名”所指向的“实”。对其“实”的考察,可能更为接近事物本身。就拿本文所要探讨的“文”来讲,在历史上“词”、“辞”、“文化”、“乐”、“礼”、“诗”、“笔”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常常代替“文”来使用。显然,对某一历史阶段的“文”的考察,也应拓展视域,对这些承担了“文”的功能的不同的“名”进行全面考察。举例来讲,至迟到理学开始建构的北宋中期,士人就非常重视从“名”与“实”关系的角度,来考察事物的全面属性。如王安石讲:“儒者之争,在于名实”。而被尊崇为理学先行者、“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往往视学生个人兴趣及才华所在,让其分别入“经义斋”或“事务斋”,前者修习儒家传统的经学,后者学习治河、治兵、算历等经世之学。后来胡瑗的高足刘彝在回答神宗“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问题时说:“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3](P25)这里的“体”,是事物的本质特性,“用”是事物的功用、价值等,而“文”则是事物的显露在外的形状、颜色等。这一思想,对后来理学家的认知方式颇有影响。几乎与刘彝同时,宋代理学“五子”之一、张载的重要传人李复,在《答人论文书》中,也对中国早期文化中“文”的不同含义有所研究。他写道: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所谓人文者,礼乐法度之谓也。上古之法至尧而成,故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周之德至文王而纯,故《传》称曰:“经纬天地曰文。”此圣人之文也。后世有一善可取,亦有谓之文者。孔文子、公叔文子之类是也。此皆以其行事谓之文也。昔之君子,欲明其道,喻其理,以垂训于天下后世,亦有言焉,以为言之不文,不可以传,故修辞而达之,此言之为文也。非谓事其无用之辞也。以载籍考之,若《书》之《典谟》、《训诰》、《誓命》,皆治身、治人、治天下之法,此《书》之文也。《国风》、《雅》、《颂》,歌、美、怨、刺,皆当时风化政德,可以示训,此《诗》之文也。广大、幽微、远近、善恶,开天地之蕴,极性命之理,以前民用,以济民行,此《易》之文也。言约而理微,褒善而贬恶,以明周公之制,以为将来之法,此《春秋》之文也。礼之《中庸》言至诚为善,率性之谓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此《中庸》之文也。今观《春秋》则不知有《易》,观《书》则不知有《诗》,岂相蹈袭剽窃以为已有哉!其言之小,天下莫能破;言之大,天下莫能载。后世尊之以为经,而无不稽焉。此其为文,炳如日星,而光耀无穷也。自汉之司马相如、扬雄而下,至于唐世,称能文者多矣,皆端其精思,作为辞语,虽其辞浩博闳肆,温丽雄健,清新靖深,变态百出,率多务相渔猎,自谓阔步一时,皆何所补哉,亦小技而已。岂君子之文欤!苟能发道之奥,明理之隐,古人之所未言,前经之所不载,著之为书,推之当世而可行,传之后世而有取,虽片言之善,无不贵之矣。夫文犹器也,必欲济于用。苟可适于用,加以刻镂之藻,绘之以致美焉,无所不可;不济于用,虽以金玉饰之,何所取焉。[4]李复于上文中论及儒家经典之“文”的不同含义,提到了“文”的“文化”、“文明”、“礼乐制度”、“文辞”、“文章”义,也初步涉及到了“文”的功用,以及“文”与“道”的关系问题。李复提及的“文”,基本涵盖了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之“文”的含义。由上亦可见,李复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宋代人认知和把握方法,亦即重视从“体”、“用”、“文”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来认知和把握事物。 通过对上述中国早期文化中的“正名”传统以及基于这一传统的“循名责实”的认知方式的考察,可知中国古人已经对“名”与“实”的问题有了比较细致的分类认识与总体把握。大体而言,其内容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一是不同的“名”可以指向同一个“实”。如前文所举《春秋》、《春秋繁露》所使用的不同名称,都指向同一个人。二是同一个“名”,背后可能具有不同的“实”。如前述李复指出了“文”的多种含义。既然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名”与“实”的不相侔性,而先人又有认识事物所坚持的“正名”传统,因此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神产品时,必须充分估量到“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以“循名责实”的认识方法来观照作为概念或者范畴的文道关系之“文”的语义,对“文”之内涵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研究,这样才能认识士人文道观念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士人不同类型文道观之所本及其发展变化情况,进而才能对士人文道观念的历史地位有较为准确的定位。 以此来考察“文”之义,则“词”、“辞”、“诗”、“乐”、“礼”等都可能与“文”的“体”、“用”有紧密联系。由此可见,遵循中国古代“正名”的文化传统,我们对士人文道观之“文”、“道”、“文道关系”的探讨,就转化为对这三个概念内涵所指向的“物”的探讨。而不同的名词组成的概念“簇”,都共同指向了名词背后的“物”,因此,我们对于“文”、“道”、“文道关系”这三个概念的探讨,也就转化为对这三个不同名词组成的概念“簇”的探讨。对先秦时期人们文道观念之“文”的含义进行探讨,其意义就在于此。 三、先秦时期“文”的语义内涵及多样性的“名”类表达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使用语境中,其含义往往各有不同,断章取义、比附取义、混淆取义而导致的偷换概念等,更使得“文”之含义极为复杂。而且,如前所言,在“文”的语义逐渐固定化的进程中,“词”、“辞”、“乐”、“礼”、“诗”、“笔”等词都承担过与其类似的词语含义及词语功能。因此,在分析“文”之发展流变时,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应有不同的含义。特别是,从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而言,一些学派经常使用一些核心的词语来组织、架构或者说明其理论体系。这时候,词语便具有了其特有的意味和含义。尽管在先秦时期,一些学派在组织、架构或者说明其理论体系时,大都出于不自觉的情况。 由此,我们需要对先秦时期的一些学派所使用的“文”等词语进行考察。正如历史上很多学派都用“道”、“理”等而其实际含义各有不同一样,“文”等词的含义在不同的学派体系中也有所不同。对此,前辈学者已经有所认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郭绍虞《中国批评史》等已经注意到了“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如郭绍虞在谈及“孔门之文学观”时,提到“其论‘诗’则较合于文学之意义”[5](P15),在谈及《墨子》的文学观念时,重视其中关于“言”有“三表”的问题等[5](P29)。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则承中有变,如该书对《庄子》文艺观的探讨,继承了郭绍虞、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特点,而又有新的发挥。朱东润、郭绍虞、王运熙等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值得重视。我们可以继承前辈学者的治学传统,继续对先秦时期各家所用之“文”进行探讨。 (一)儒家之“文” 1.孔子之“文”。从《论语》等典籍来看,孔子所用的“文”,主要含义有: 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朱熹《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文采。《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孔子所用之“文”,往往与道德修养相联系。如《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与“德行、言语、政事”并列的对儒学经典的学习、研究与传述。《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文学:子游,子夏。”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文学”是指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等典籍的学习、研究与传述。 文献知识。《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集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5](P68) 文辞。《论语·卫灵公》:“吾犹及史之阙文。” 作动词使用,文饰。《论语·宪问》:“文之以礼乐。” 与孔子之“文”相近、相关的词有: 乐。《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这里的“乐”强调的是艺术的美与善标准,这一标准对“文”而言,也是适用的。 言。《论语·宪问》:“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里把“有言”作为有德者的条件,认为有德者亦应有言。可见,“言”与“德”相联系。《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也是强调“言”当以道德为根本。 辞。《论语·卫灵公》:“辞达而已矣。”这里的“辞”,按照《集解》引孔安国解释:“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则当为“言辞”、“文辞”。而苏轼《答谢民师书》则辨析说:“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强调文采的重要性。 诗。孔子论诗,比较重视诗的功用。依孔子看来,诗是整个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他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的“诗”,除了强调其社会实用性之外,已有情感性、艺术审美性等要求了。 2.《易传》之“文”。一般认为,《易传》当为孔子至战国时期所作,其中含有儒家学派的若干重要观点。《易传》论“文”,既有对孔子思想的传承,又有一些新的发展。《易传》之“文”之义有: 礼乐文化制度。如:“文明以止,人文也。”这里的“人文”,指的是人类的礼乐文化制度。 纹理。如:“物相杂,故曰文。” 与《易传》之“文”意思相近的词有: 言。其义为“语言”,很多时候与“辞”同义。如:“言行,君子之枢机。” 辞。其义为“言辞”。如:“修辞见其诚。” 象。其义为“象征符号”。如:“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八卦。因为相传八卦是最古老的文字,而文字又与文学相联系,因此,八卦同时具有“文字”、“文学”之意。如:“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3.孟子之“文”。在《孟子》中,“文”之基本用法有: 文辞。如《孟子·离娄下》:“晋之乘,……其文则史。” 文字。如《孟子·万章章句上》:“不以文害辞。” 作动词用,文饰。如《孟子·离娄上》:“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总的看来,孟子所用之“文”并未出《论语》之用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在很多地方表达“文”的语义时,不是用“文”而是以其他词来代替。如: 乐。《孟子·梁惠王下》:“世俗之乐犹先王之乐。”强调既然人心都是善的,世俗之俗乐当然亦会与先王之雅乐具有同等的王道教化功用。 言。《孟子·公孙丑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文中之“言”为“文辞”、“语辞”义,是与立足道德修养的“浩然之气”相联系的。 说。《孟子·滕文公下》:“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朱熹《集注》:“辞者,说之详也。”这里的“说”,是“学说”义,而“说”、“辞”等都与道德相联系。 4.荀子之“文”,则在孔子、孟子之后有所发展。荀子提出“性恶”说,强调“学之不可已”(《荀子·劝学》),在《礼论》中又说:“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强调文饰而成伪,进而提出以“文学”来纠伪去恶。他在《大略》中言及:“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磨琢也。”《王制》篇提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里的“文学”是两个词,指的是“文化”、“学术”。 荀子所用之“文”,还有如下意思: 礼物威仪等礼乐制度。《礼论》:“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 文采。《礼论》:“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这里谈及“文”、“情”的关系问题,已经有了探讨文道关系的思想萌芽,对后世士人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启示。 与荀子之“文”意思相近或者相似的词有: 辩。荀子经常使用“辩”来表达文辞的语言表现。如在《非相》中提出:“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这里的“辩”指辩说。荀子在推崇“辩”时,经常重视的是“正名”。他在《正名》篇强调“分别制名以指实”,又在同文中提出“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的观点,这些都强调了“辩”的目的是“正名”,而“正名”除了要符合政治伦理名分之外,也要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规律。进一步讲,这为后人开启了为文首要辨体的思路,同时,因为“正名”在符合逻辑的同时,亦需要精审地遣词造句,因此,“辩”便有了推崇语词、文法等作用。 乐。荀子强调,乐出于人情,他在《乐论》中指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强调“乐”是为了政治教化而创作。这个语义与“文”的“礼乐制度”义非常接近。 由上可见,儒家之“文”,其义除了“文饰”、“文采”、“文辞”、“文献”之外,大多数又与礼乐文化制度有密切关联。一些与“文”含义相近之词,亦是如此。 (二)道家之“文” 1.《老子》之“文”。“文”出现在《老子》中仅一次:“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其义为“文辞、文字”。但《老子》一书,更多的是用了与“文”义相近、相关或者大体相同的词,来阐说与“文”含义相近的内容。 名。《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这里的“名”是“道”的语言表示,是与“道”相一致的,因此,“名”即“道”。类似的意思,在《老子·第二十五章》又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这里的“名”与“道”、“大”都是为了方便于认识事物而使用的名称。《老子》中“名”与“道”的关系是,这两者都指向于概念背后的事物本体,这一思路对于宋人处理文道关系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言。《老子》的“言”,其基本含义为“言说”、“语言”,重在语言表达。《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第二十四章》:“希言自然。”从《老子》本文来看,“言”的使用较为简单。 象。《老子·第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故混而唯一。……无物之象,是为惚恍。”这里的“象”是与“一”处于同一层次的名称,因此,“象”与下文“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中的“道”具有一致性。 上述可见,《老子》中的“名”、“言”、“象”作为名词使用时,往往与“道”指向的对象具有一致性,这样,《老子》中的“道”与“名”、“言”、“象”就具有了相统一的属性。一些宋代理学家的文道观念,把“文”与“道”相混同,与《老子》关于“道”、“名”、“言”、“象”的名称使用以及对上述名词的关系界定,其用法是一致的。 2.《庄子》之“文”。《庄子》使用“文”并不多,从文献来看,其“文”之含义主要有二: 文采。如《内篇·逍遥游》:“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又如《外篇·骈拇》:“是故骈于明者,乱五色,淫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成玄英注:“青与赤为‘文’,赤与白为‘章’。” 文饰、外表。如《内篇·应帝王》:“吾与汝既其文,未既其实。”此处的“文”取“外在的文饰”义。又如《外篇·缮性》:“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此处之“文”,陈鼓应引李勉说,认为是上文所指的“俗学”。按:这里的“文”仍然是“文饰”义。 《庄子》虽然很少使用“文”,但文中却出现了几个与“文”的观念或者功用相近的词语: 言。《庄子》中,经常使用“言”字,其义多为“言语”、“言辞”等。实际上,当“言”用书面语表达时,同时也就有了“文字”、“文章”之义。如《庄子》提到的“寓言”、“重言”、“卮言”、“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等皆是这种用法。 辞、说。《庄子》中有把“言”、“辞”连用的情形。如《杂篇·天下》提及“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这里的“说”、“言”、“辞”都是指言辞。 (三)《墨子》等战国诸子之“文” 战国时期,同列为显学的墨家代表人物对“文”也很重视。《墨子》之“文”的含义主要有: 文饰。如《辞过》:“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 文章、学识。如《天志中》:“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这里的“文学”,按照郭绍虞先生的意见,当为“学术”。但仔细考察其义,作“文章”、“学识”解更为恰当。 《墨子》中与“文”相近的词语有: 说。指“言语”。如《修身》:“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 言。其义亦为“言语”。如《非命上》:“言必立仪”。 以上考察了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及墨家代表人物的“文”。至于法家、纵横家之“文”,由于大致不出上述三家之“文”的语义范围,故本文于此从略。 行文至此,可以对先秦时期诸家之“文”的内涵进行梳理。大致而言,“文”字,从其字源来进行考察,是“纹理交错”的意思。如《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用的就是本义。到了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人们开始赋予“文”以更多的含义,主要有: 作名词用,有“纹理”之意。如《左传·隐公元年》:“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 由“纹理”而引申为人伦秩序。《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文”而“化成天下”,因此“文”又引申为“文明”、“文化”。 礼乐有修饰、规范作用,合礼的则为文雅,因此又以“文”来指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在这个语义上的“文”,逐渐被“礼乐制度”所代替。 从“纹理交错”义作引申,而为“文雅”,常与“质”或“野”相对。《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因汉字初期是模仿天地万物形状而来,因此由“纹理”而引申为“文字”、“文辞”。《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在这个意义上,后来常写作“词”、“辞”、“笔”。“词”,《说文解字》:“意内而言外”,段玉裁注:“文字形声之合也。”引申为“文辞”、“言辞”。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演化的过程中,另外一些词,如“词”、“辞”、“乐”、“礼”、“言”、“语”、“辩”、“象”、“诗”、“笔”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文”的概念、功用。因此,我们以“循名责实”的方法来考察“文”之含义及其发展演变时,当注意到这一点。进而言之,在对士人文道观念进行探讨时,应对与“文”在性质、功用、含义等方面相近或者相同的一些词进行考察。 由上述可见,中国古人对事物之“名”与事物本体的认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事物之“名”往往与事物本身不是对等的关系,因此,就形成了“循名责实”的文化传统。以此来观照中国士人的文道观念,则发现其中之“文”内蕴丰富并表现为不同的“名”,而这些不同的“名”有些对应着所指之“名”的体用等。由此言之,在对士人文道观念进行研究时,必须充分注意到“文”、“道”、“文道关系”的语义层次及其嬗变问题。 [收稿日期]2015-02-13标签: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孟子论文; 庄子论文; 孔子论文; 墨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荀子论文; 礼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