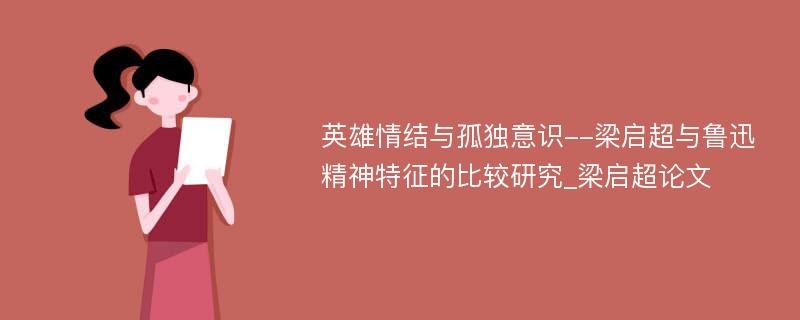
英雄情结与孤独意识——梁启超与鲁迅精神特征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情结论文,特征论文,孤独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梁启超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一方面,他们虽持有以身许国的同一人生价值标准,但因各自拥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思想而表现出迥异的精神特征;前者终生不改英雄情结,后者饱含深刻的孤独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不同的精神特征又最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实践;前者受古典人格的制约,由叛逆回归传统;后者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现代人格),毅然与传统决裂。追溯梁启超和鲁迅的精神历程,对后人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意义重大。
感时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精神的代表,梁启超与鲁迅是这种文化传统的典型继承者。他们“报国惟忧或后时”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殷勤自励,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报国热情一脉相承。只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梁启超与鲁迅虽然都取以身许国的同一价值标准,但表现出迥然相异的精神特征;梁启超瞩目于英雄超时势的功业,高吟着“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终生不改睥睨天下的英雄情结;鲁迅则很快意识到“我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体味着寂寞与虚无,具有深刻的孤独感。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文化思想孕育了他们不同的精神特征;这种精神特征反过来又影响了他们的人生实践。在梁启超与鲁迅两种精神特征的背后,就站立着两种人格:一种是奉行着“立德、立功、立言”与“内圣外王”之道的古典人格;一种是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上,具有清醒的“历史中间物”意识的现代人格。因此,在最终的文化选择与人生归宿上,梁启超由叛逆传统又回归传统,鲁迅则义无反顾地与传统决裂,成为真正属于20世纪的现代思想家。他们的精神历程对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有深刻的启迪。
1
在追寻他们人生经历与精神特征关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注意到青少年时期人生经历对他们精神特征形成的作用。现代西方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12—18岁之间是人格建构的重要阶段。这种人格建构极大地影响每个人今后的精神特征与行为倾向。
梁启超与鲁迅的家庭文化背景是相似的:一个是“半为农者半为儒”,一个是破落的士大夫。但是,早期人生按下的音键却大不相同。
梁启超的祖父是个和蔼的老秀才,终生未仕,把满腹希望寄予了聪颖的长孙:“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①父亲也对他劝勉有加,每当梁启超言行不慎,就训斥道:“汝自视乃常儿乎?”这种期望甚殷,督促甚严的教诲,潜移默化,使梁启超以英雄自许,向往功名。12岁时,梁启超登上家乡的凌云塔,吟出“我欲问苍天,苍天长默默。我欲问孔子,孔子难解释”的诗句,表现出对苍天圣人等闲视之的宏大气魄。梁启超天资聪颖,少年成名。他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在科举道路上,春风得意。这无疑更加刺激了他生发出雄视天下的豪迈气概。
少年鲁迅留下的心灵印记是黯淡抑郁的。新台门周家到鲁迅父亲这一代,已经开始败落。老爷少爷们以吸鸦片为乐,壮志消磨,形毁骨立。曾任京官的祖父每当回家目睹家风颓败,总是脾气暴戾,动辄骂人。到鲁迅13岁时,祖父因科场案下狱;不久,父亲又病逝。在家道中落的过程中,鲁迅目睹族人之间的倾轧,饱尝了世态炎凉。从此,他对社会人生总有一种阴郁的把握方式,对国民精神的痼疾看得甚重:“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自憾有些隔膜。”18岁时,鲁迅去南京求学,其心境也是苍凉的:“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青少年的人生际遇给鲁迅留下了寂寞与孤独的精神印记。
他们早期人生经历打下的精神印记,随着往后人生经历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精神特征的历史文化意蕴也日益丰富,影响着他们的人生实践。
如果不是进入万木草堂,从师于康有为,历史上的梁启超也许就只是一名宿学大儒。在万木草堂,康有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比例推断之”②。这使得梁启超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文化的天地,并确立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思想。历史玉成了梁启超。在变法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梁启超以对国难时危的敏锐感受和爱国热情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以欧洲启蒙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以《时务报》为舆论阵地,以明白晓畅,富于情感的文字倾倒国人。梁启超“言满天下,名满天下”,成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杰出的宣传家、思想启蒙家。“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询问变法大计,并赐六品官衔。这种人生际遇,更加激发了梁启超忠君爱国,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豪情。这也使梁启超从情感上把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帝王之业结合起来。
梁启超最辉煌的人生与他的青春同步。这种以献身民族,报效国家为内涵的英雄情结,深刻影响了他的人生实践。第一,他以觉世为责,自觉选择作“觉世之文”。1897年,正当梁启超发表以《变法通议》为代表的大量时评的时候,严复写信给他,认为他发言草率,“劝其无易由言,致成他日之悔。”③梁启超则在回信中明确表示:“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④他宣称:“若鄙人者,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⑤梁启超平易畅达,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风格,正是出自这种作“觉世之文”的自觉选择。第二,英雄情结赋予了他在困厄之中不坠青云之志的勇气。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他维新之志不变,爱国之心不改;学日语,读日文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见之理,腾跃于脑”。⑥他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向国内宣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开启民智;并由于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以致思想激变,倡言破坏与革命。章太炎曾这样描述梁启超当时的精神风貌:“松柏非遇霜雪,不能贞坚,斯人今是之深沉,迥异于前日矣。”⑦第三,英雄情结激励梁启超不断地追赶时代步伐。1903-1915年,是梁启超一生中政治上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时期。由于受到康有为的制约等因素的影响,梁启超由倡言革命退回到开明专制,并与革命派展开保皇与革命的大论战。1912年回国后,又加入袁世凯的“名流内阁”,几至助纣为虐。但是,以爱国救民为己任的梁启超,并未由此走上政治上的末路。当他察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祸心后,不惧威逼利诱,甘冒生死,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揭露袁世凯称帝阴谋,此文被人们誉为倒袁的嚆矢。继而,又与弟子蔡锷密谋云南起义,举起倒袁护国的旗帜,使人复睹他戊戌变法时期战士的风采。“五四”运动时期,梁启超正出使欧洲,他为争取国权奔走呼号,爱国精神与时代要求是一致的。到20年代,梁启超已完全脱离了政界,从事著述与教育,但其英雄情结仍使他流露出强烈的入世愿望:“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是恢复我二十几岁时候的勇气,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我很盼望最近的将来,有真正的国民运动的出现,倘若有么,我梁启超应该使役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⑧此时,梁启超已进入人生暮年。同样是一代学人,如果我们比较胡适对时势的态度——战争的喧嚣难以打搅他的学术研究,入侵国土的暴力也不能分散他在书斋的沉思,我们就会更加感到梁启超报国热情的可贵。
当我们讨论鲁迅孤独意识的时候,首先面临这样一个事实:鲁迅毕生从事的救亡与启蒙的事业并非孤独的事业。从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光复会,到30年代成为“左联”盟主,鲁迅都与时代最进步的事业连在一起。从生前被青年们拥为导师到死后尊为“民族魂”,鲁迅的名声并不寂寞。然而,鲁迅却终生与孤独相伴,也正是他深刻的孤独意识以及与黑暗现实的抗争才成就了鲁迅的伟大。从本质上讲,孤独是一种精神上的忧患,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态度。鲁迅的孤独意识来自他的人生挫折感——也即改革社会现实的热望与冷漠的社会现实的矛盾,来自他对先驱者寂寞命运的感受,来自对自我在历史进化中地位的认识。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鲁迅的孤独与他一系列人生挫折相连。带着对孔夫子的失望,鲁迅去日本学医。可是,四年求学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⑨1906年,鲁迅作出弃医从文的选择,想从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但打击仍接踵而至。1907年鲁迅与同人们办《新生》的计划流产,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也售出甚少。在此期间,鲁迅大量阅读了西欧近代文学、哲学、自然科学著作;研究了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接受了他们的生命意志与超人学说的影响。对基尔凯郭尔、施蒂纳等19世纪非理性主义对孤独个体生命形态的体认识也甚有会心。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迪与现实人生感受,使鲁迅提出了“立人”的主张。然而,鲁迅的主张并未得到反响:不仅大多数民众不理解,就是当时的改革者、革命党人也并不以为然。一系列的人生挫折,强化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留下的精神印记。因此,鲁迅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⑩而1909年回国后,他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更是深感中国改革之难,先驱者命运之寂寞。民国革命后仅几年,不少先烈的坟墓已杂草丛生,“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1920年,鲁迅在小说《头发的故事》里,借N先生之口表达了这种忧愤。1925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也直白了自己这种寂寞的人生感受。
1926年,鲁迅反复用文学与哲学语言,表述了“历史中间物”的观念,这使他的孤独意识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鲁迅意识到自己一方面反抗现实的黑暗,另一方面又与传统有着无法割断的历史联系。这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解释,就是在文明解体的时代,“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不‘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11)鲁迅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进化中普通一员的历史地位后,他的孤独意识与早期尼采式的孤独区别开来。鲁迅说:“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12)他的人生态度是:“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13)表现出与旧的传统与黑暗一同灭绝的悲壮精神。
鲁迅孤独意识对他人生实践的影响,就在于他终生坚持在精神领域进行改造国民灵魂的工作。在中国现代史上,很少有人象鲁迅这样十分执着地把自己的文学与思想情感紧紧和变革现实连在一起。但是,从辛亥革命到30年代,当有人劝鲁迅直接从事冒险的政治活动时,又被鲁迅很明确地回绝了。这倒不是鲁迅过于爱惜自己的生命。是鲁迅的孤独意识促使他坚定地选择了在精神领域以身报国的方式;从“立人”到“立国”是他贯穿一生的社会改革的基本思路。鲁迅认为,没有民族精神的彻底改造,新的社会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为改造民族精神,鲁迅一方面剖析国民沉默的灵魂,另一方面,则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这样,我们便读到鲁迅笔下两种风格的文字:一种是如雷声而渊默般的沉郁冷峻,一种是如匕首投枪般的犀利泼辣。如果通读鲁迅的全部文字,我们就会感到这是在与20世纪中国最孤独而又最崇高的灵魂作心灵的交流。鲁迅的孤独与崇高,正与他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以及在精神领域改造民族灵魂的执着连在一起。
2
仅仅从人生经历的角度理解梁启超与鲁迅的精神特征是不够的。梁启超的英雄情结与鲁迅的孤独意识还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思想以及人格结构,并且这不同的文化思想与人格结构最终导致了他们不同的人生归宿。
梁启超是高擎着18世纪以来欧洲启蒙主义思想的旗帜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欧洲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为他提供了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与理性激情,他还吸收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14)“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蓄而发现者。虽谓世界之历史,即英雄之传记,殆无不可也。”(15)在梁启超文集中,有不少是古今中外英雄豪杰的传记。在这些文字里,他着力阐释英雄豪杰对历史的作用,也寄托着自己对英雄功业向往的情怀。与梁启超英雄史观的思想相联系,是他对自由思想的倡导。为了创造历史,人人要有独立自由的精神;而自由之价值,梁启超认为“非对压力而言之,乃对于奴隶性而言之”。“若有欲求真自由者,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为除心奴,梁启超提出:“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16)除心奴,以张大个人之人格,积极创造历史,努力追求“卷舒一代兴亡手”的英雄功业。
但是,梁启超的英雄史观与自由思想又是和他“内圣外王”之道的传统思想连在一起的,并且融和着他对“立德、立功、立言”传统人格的追求。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一语,包括中国学术之全体,其旨在内足以修养而外足以经世。”(17)就在论述自由的文字里,他将被清朝统治者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人物曾国藩尊为勋名赫赫的人杰:“试一读其全集,观其困知勉行,厉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无所养而能定大艰成大业者。”(18)梁启超表现出对曾国藩人生功业的赞许之情。西方资产阶级的英雄史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人格精神相融和,这正反映了梁启超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过渡时代人物的历史特点。因此,梁启超尽管有不少论述自由的文字,但他并没有真正把自由归于实在的个人。他将自由分为“文明”与“野蛮”两种,他认为,“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19)梁启超提倡自由的最终目的,是“向上以求宪法”,对外“以伸国权”。他对自由的认识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把握,并没有摆脱“修齐治平”的传统人格,人生道路也没有超出古代以来“贤相”“宰辅”的轨迹。这正是梁启超英雄情结所包含的最根本的时代属性。
1920年,梁启超旅欧回来。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看到了物质文明发达的背后存在的种种弊端。几十年来,梁启超深情瞩目的资产阶级理想王国在他心中破灭了,“好象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过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个科学先生。”(20)
随着对资产阶级科学理性的失望,梁启超又把目光投向了他曾经批判过的中国传统文化,他试图以此来救治西方文明的危机,并拯救正在沦丧中的整个世界。下面这段取自其《欧游心影录》的话代表了梁启超晚年的文化观:“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有一致’,我想不知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梁启超生活的晚年,中国历史已进入用科学与民主取代蒙昧的封建主义的现代革命时期,他虽然仍想自觉地肩负历史重任,甚至想挽救世界文明,但却选错了道路。他背弃民主与科学,举起东方传统文化的旗帜,恰恰是逆时代潮流而动。1927年,康有为70大寿,梁启超执弟子之礼,献上一幅寿联,将康有为喻为孔子。10余年前,那个倡言革命,劝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的梁启超已经不见了。到人生暮年,梁启超从文化思想到伦理情感都已回到传统的怀抱,以忠君复古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
从文化思想的角度分析,鲁迅的孤独意识受到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先驱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尼采到当今的代表海德格尔、萨特,他们都强调个体的生命意志,在个体与类的矛盾的解决方式上,都竭力揭示人体精神与抽象的类的精神的尖锐对立,竭力张大个性,强调自我选择与精神自由。从鲁迅早期文化哲学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一现代哲学精神的把握,看到他和人本主义哲学先驱者思想的诸多联系。如鲁迅:“意力为世界之本”,“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21)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学说;“与其抑英哲以就凡痛,曷若置众而希英哲”(22)与尼采的超人学说:“真理准则,独在之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23)与基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体为世界唯一实在的学说”等等。鲁迅对“朕归于我”“人各有己”的强调,使自我与类,与代表着群体的传统对立起来,于是,也就带来了弗罗姆《逃避自由》所描述的那种结果:“自由,虽然它给人带来了独立性和理性,但也使人变得孤立无依。”
鲁迅的孤独意识并没有导致他隔绝现实,没有象海德格尔、萨特和加缪那样,导向对生命与存在的非理性思考;鲁迅也从未试图去构建一个经院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体系。鲁迅所谋求的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4)因此,鲁迅的孤独意识所激发的是他改造现实,批判黑暗的理性激情。鲁迅说:“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正是这种“绝望抗战”的人生态度,赋予了鲁迅精神的崇高。
一方面是与传统和黑暗作绝望抗争,一方面又自觉意识到自己与传统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这种历史中间物的意识本质上是对个人在历史中地位的认识。尽管自觉地承担历史使命,但仍确认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地位,这与梁启超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区别开来,表现了鲁迅的现代人格。这正如荣格所说:“‘今天’处于‘昨天’和‘明天’之间,是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除此之外,不能再做别的解释。‘现代’代表着一个过渡的程序,而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自称为现代人。”(25)“千万桥梁和阶梯引向未来”(26),鲁迅正是这千万桥梁中伟大的一座。
早在1908年,鲁迅就对西方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发展后的弊端作过尖锐批判:“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但鲁迅没有象梁启超那样,对资产阶级文明失望后就转向传统文化,而是一方面继续从科学和民主思想中汲取批判中国封建主义的力量,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人的精神解放与自由。鲁迅把自己赋予了现实而具体的个体,关注着每一国民的精神解放,而不是象梁启超那样,自由不具真实的主体性,被“宪法”“国权”所消融。这样,鲁迅就在改造民族灵魂的总目标下将19世纪科学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哲学交融在一起,建立起富有实践理性精神的思想体系。在批判现实的过程中,鲁迅不断寻找着改造民族精神的物质力量。这样,当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真正从思想上服膺马克思主义后,他便充满激情地宣布:“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完成了向无产阶级战士的转变。
每一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都会出现特定的自我批判的时代。梁启超、鲁迅所生活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就是这样的时代。清王朝日之将夕,封建统治大厦将倾。梁启超与鲁迅作为自我批判时代的先驱者,他们都以深刻的感时忧国精神肩负起历史重任。然而,他们的精神历程和人生归宿也告诉我们:在批判现存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批判者首先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人格改造,要从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上反省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彻底与传统的社会制度,与传统观念决裂,否则,在实现人生理想的过程中,遇到阻碍或理想破灭时,又会退回到传统的怀抱。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不缺乏这样的例证的;晚清时代以翻译《天演论》《民约论》宣传进化、民主、自由思想,唤醒过一代国人的严复,最后回归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中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者的一代斗士,在“五四”运动之后,他们又走起了回头路:胡适走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刘半农又重新抄古书,标点起《何典》来;钱玄同则重新热衷古文字。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7)对历史进化过程中人们告别传统的复杂性,马克思早就有过论述。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涉及到人们精神领域的深刻革命。这样,回眸先驱者在历史进化中的精神历程,对我们努力实现自己现代化人格的构建,愉快地告别传统,不是没有意义的。
注释:
①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三十自述》。
③《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8页。
④《饮冰室合集·与严幼陵先生书》。
⑤《饮冰室文集·自序》。
⑥《饮冰室合集·论日本文之益》。
⑦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83页。
⑧《饮冰室文集·外交欤、内政欤?》。
⑨⑩(12)(13)(21)(22)(23)(24)《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417、286、286、368、52、54、56页。
(11)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4)《新民丛报》第1号。
(15)《饮冰室文集·英雄与时势》。
(16)(18)(19)《饮冰室文集·论自由》。
(17)《饮冰室合集·庄子天下篇释义》。
(20)《饮冰室文集·欧游心影录》。
(25)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26)尼采《毒蜘蛛》。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