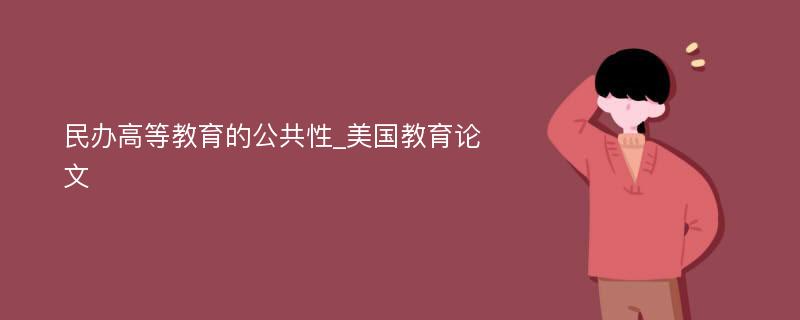
私立高等教育的公共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私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之后,私有化重新受到广泛的关注。因此,这里有必要先简要地回顾一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重要事件。然后,我将着重介绍私立大学的公共控制问题。最后,我将阐述的是当前许多教育系统对公共资源的私人利用问题。我将以美国作为案例,主要是由于美国在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对其他一些正在经历私有化改革的国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将探讨过去二十年间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现象——私立学院和大学的空前繁荣以及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最后,我将简要总结一下与上述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
一、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
一般来说,20世纪70年代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国有化程度都达到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70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质疑上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并提出了“福利国家危机”(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问题,但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却未见指责。据我所知,唯一的批评与白金汉大学(Buckingham University)的建立有关。学者们指责这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行为。这一时期,在有些国家根本就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如法国和瑞典。而在其他国家,只有很弱小的私立高等教育。
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私立高等教育领域,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如私立大学逐渐被公立部门同化。在日本和比利时,大量公共资金投入到私立高校。然而,政府在提高对私立办学经费投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私立高校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政府部门并不信任私立高校,担心私立高校能否保证其教育质量。日本政府通过一套复杂的质量评估表对私立高校进行测试,然后依据测试结果来决定补贴的增加或削减。在比利时,政府将严格的公式计算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以确保对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平等的投入。在菲律宾,政府在没有对私立高校投入经费的情况下,加大对私立高校的监管,譬如班级的日常出勤报告必须在教育部记录存档。
20世纪70年代,这种预言甚至在美国也得到反映,即政府对私立高校的财政拨款越多,来自政府的控制就越多。也就是说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来加强对私立高等教育的控制。于是,大学的运作和管理受到联邦政府的管制,管理成本增加了,而自由度却降低了。到70年代末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处在低谷。随后,事实证明这一情况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国际现象。
进入80年代后,高等教育私有化开始兴起,并自此迅速发展起来[1]。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公立院校教育经费中来自私有资源的部分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大学与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在规模、声望或影响力等方面,私立院校在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80年代,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上述前两个方面表现得比第三个方面更加明显。在各国政府面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而无力或不愿意提供相应的大量经费时,通过学费、市场调节机制或与企业合作等举措来解决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具有吸引力了。在欧洲,一些实验性私立大学相继建立,成为对同质性或政府无能表现的反应。最大的冲击大概发生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的建立打破了原有的公立大学一统天下的局面。[2]然而邦德的出现只是个别事件,事实证明,它也是一所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学校。
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俄罗斯,原有的共产主义教育体制不足导致的高等教育中的真空地带,正逐渐由私立高等教育所填补。这个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由完全没有私立高等教育,突然间转变为必须通过大量的、形式多样的私立院校来满足其高等教育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但是,正如丹尼尔·利维(Daniel Levy)所指出的那样,前苏联的这一特定状况应作为重要的教育现象给予一定的关注。[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出现的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之间并没有真正地进行分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私立大学是依赖公共资源而建立起来的。
这也是我要着重阐述的问题。我发现,这一现象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一方面,高等教育私有化使公立院校的教育经费越来越依赖私有资源;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私有化也引起了“镜像反应”现象,导致私立大学日益依赖来自政府的公共资源。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一些支持私有化的议案已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开始实施,从而促成上述现象。
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将结合美国高等教育现状就这一问题给予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首先,我将解释和说明私立学院和大学怎样将政府向学生提供的助学资助转换为学费,并以此取得空前的繁荣。其次,我将着重阐述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增长最快的部分——营利性高等教育。也许有些人会认为上述现象是一种美国独有的教育现象。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这种通过将学费和政府助学资助联系起来、达到支持私立高等教育的现象。例如,英国所实施的“额外费用”(top-up fee)政策,可以被视为这一现象的最新例证。这一政策可以与美国最差的私有化教育实践等量齐观。此外,在经济和法律环境好转时,营利性高等教育可以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潜在威胁。
二、美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
让我们重新回到私有化的开端。1978年,我参加了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一个信息会议。那时耶鲁大学几乎要破产了,该校正面临结构性的营运赤字并已开始冻结人事。除了极小部分,耶鲁的5亿美元捐款大多被套牢在受限制的基金中,让耶鲁大学的日常运转资金处于“最低容忍限度”(lowest tolerable level)。雪上加霜的是,当时的竞争环境不允许提高学费。1978年,耶鲁大学的年学费为4400美元。
当然,今天的耶鲁大学尽管仍需追赶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正处于其历史上最辉煌的发展时期。2003年耶鲁大学的学费是29000美元,与此收费水平相近的其他私立学校在美国大概还有100多所。显然,私立大学的经济状况与学费有着密切的关联。
不仅是耶鲁大学,几乎所有著名的私立大学都正享受着高等教育私有化所带来的成功。1980年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每个学生的年平均开支为10000美元(不变价格),而私立大学为11000美元;2000年公立大学的费用为14000美元,其调涨幅度是40%,而私立大学为22000美元,涨幅接近100%。对于私立大学来说,70%的办学支出来自学生的学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这一数字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私立大学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学费的增长,同时,由其他渠道获得的经费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4]
私立大学的空前成功不仅取决于学费的长足增长,同时也在于成功地吸纳了其他渠道的资金。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私立学校的经营者和社会的捐赠。学校的声誉是吸引资金的关键,一般是学校的名气越大,收取的学费越高,获取的捐赠越多。
在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声誉主要取决于“筛选”(selectivity)——通过筛选获得高质量的生源。但是,学校的声誉以及由杂志评出的大学排名榜只会对少数美国学生产生影响。据粗略估计,美国大约有15%的四年全日制本科学生寻求在一流的私立高校就读。他们的选择代表了一大批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的心声。他们相信通过理智的选择进入享有盛名的大学学习,将会为其带来终身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职业发展。从这一角度出发,私立大学则坚信通过增加教育支出而进行的质量竞争能够使学校更具吸引力,使学校的声誉更加卓著。在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上述竞争机制一直大行其道,但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高等教育领域的“筛选—竞争原则”(selectivity and qualitative competition)已经扩张并统制了整个教育系统。[5]这种机制还进一步加剧学费的快速增长。因为水涨船高的关系,学费高涨使政府的奖、助学金负担也愈加繁重。
下面将就这一机制的发展历程作简要回顾。[6]1978年,哈佛大学收取当时最高的学费,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大幅度提高其学费标准。同时,哈佛大学提高助学资助力度,向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提供补贴。后来,这一举措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支持,国会调整对学生的经济援助政策,向所有学生提供助学贷款。这一政策的出台正值美国经济出现严重通货膨胀之际。自此,不管需要与否,大量学生向政府申请各种助学贷款。虽然政府随后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与控制,但是目前助学贷款的发放总量仍呈上升趋势。这一现象与“美国人喜爱借贷”的社会与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由此,80年代,我们见证了“学生贷款文化”(a student loan culture)的产生和发展。
80年代末所创立的学生资助系统,为美国高校的长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学生就读高等教育的费用通常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获得。
1.确定学生在家庭经济状况基础上的支付能力,这也被称为“家庭预期贡献”(expected family contribution)。它可以通过专门的计算公式来确定。
2.直接经济资助(direct financial aids)。这是一种“以经济需求为基础的资助”(the basis of financial need),只面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工读方案(work-study programs)的申请也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
3.联邦补助性和非补助性贷款。补助性贷款只限于家庭收入在某个水平之下的学生,这种贷款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在联邦非津贴贷款迅速增长的同时,联邦补助性贷款尽管只是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是它还是在解决学生就读高等教育的费用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4.院校提供的学生奖、助学金,也被称为“学费减免”(tuition discount)。一所大学通过前三种途径得到最多的资金之后,这所大学将剩余部分作为院校助学金或以学费减免的形式向学生提供资助。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教育改革。学生借贷文化的出现,使学生可以利用其“未来的收入”(future earnings)消费那些目前超出其消费能力的教育服务。这种“额外的购买力”(additional purchasing power)使高校可以更加容易地提高其学费标准,这样学校又提高了对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能力。此前,常青藤学校往往能够提供较高的学生助学金,相比较而言,其他多数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则提供的较少;80年代后状况发生了变化,具有优势的“高学费/高资助”(high-tuition/high-aid)学生资助体系在更多的学校中得到了推广。
“高学费/高资助”现象的实质在于学费的最后增加部分来自于院校学生助学金。根据每一名学生的支付能力来调整学校的资助和学费减免,最后形成了一种差别定价系统(a system of differential pricing results)。在这一系统内,学生支付他所能承受的最大份额。对学费价格变化比较敏感的学生可以获得多种资助;对于那些可以承担的学生来说,则要收取全部费用。这样,在这种资助系统的帮助下,各类院校就可以无任何阻力地提高其学费,即使有时会听到一些反对的声音,但高等教育需求并未出现下降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享有盛名的大学面对的是一种真正不受学费价格影响的入学需求情况。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积极倡导“高学费/高资助”政策,认为这是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有效手段。尽管这一观点并未以政策形式明确提出,但是学生资助体系通过上述过程演变形成了。以前,联邦助学贷款被看作是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求学的有力保证;在20世纪80年代,该贷款成为联邦政府为高等教育提供经费的主要形式。然而,这种由高学费创造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
首先,现行政策已经导致著名的私立大学招收越来越多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随着学费的暴涨,只有少数学生能够承担得起全部费用,而绝大多数学生不得不依赖院校资助。然而,随着院校资助的增长,又必然导致学费作用的下降。从1999~2002年,私立大学的学费减免率由原来的20%上升至30%。最新的数据显示,学费每增长10美元,学校实际收入只增加7美元。私立学院的学费减免率也由低于30%上升至高于40%。[7]由此可见,收取较高学费本身又会成为进一步提高学费的压力。
其次,大多数一流的私立大学通过扩大录取全额付费学生的数量保证了稳定的学费减免。那些享有盛名的顶级私立大学可以实施这一举措,因为财富、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杰出的成就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然而我们发现,事实上一所大学录取学生时的选拔性越强,符合申请学生资助条件学生所占的比例就越小。以常青藤学校为例,54%~60%的学生拿不到资助,也就是说,这部分学生每年必须负担总额超过40000美元的学费。这样,可能仅有6%的年龄在45~54岁的家长能负担起这样一大笔费用。另外,大多数得到资助的少数民族学生并非来自真正意义上的贫穷家庭(worthy poor),而是来自中上层家庭,即使这样的家庭也需要获得额外的资助才能承受这样一笔开支。由此,可以贸然地下一个结论:富有家庭从高学费政策中获得的好处要远远大于非富有家庭从资助政策中获得的帮助。
第三,当前在大多数私立院校,每个学生正在为同样的教育服务支付不同价格的学费。在一流的私立高校,“全额付费的学生”所占比率正在急剧下降。在声望差一些的私立院校中,高达90%的学生能够获得财政资助。由此不难发现,联邦政府对学生提供的财政资助实际上支撑着高涨的学费,并维持着当前美国高等学校的运转。一些私立院校约三分之一的经费收入来自联邦助学金和贷款,这些资金是通过学生学费进入私立院校的。
第四,虽然差别学费政策符合经济学的原理,但是事实上当前的学生资助政策并不是一场非常公平的游戏。现行的高等教育“招生管理”(enrollment management)旨在选拔具有潜质的优秀学生,同时又兼顾学校收入原则。在学生资助方案中有多种变量,学校通过采用不同的助学资助形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操作方式也可以被称为“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买主须自行当心质量”(Caveat Emptor)。有些学生不仅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而且还与该制度进行博弈。但是,非营利私立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基础之一是人们对其采取的信任态度。现行的学生资助政策正在被广泛推行的对优异学生提供资助的政策所改变。院校学生资助制度使得一些质量较差的学校可以吸引到优秀的学生,这种状况被认为是对教育资源的低效率使用。
第五,通过高学费所获得的收入通常被优秀的私立大学用来进行教育质量的竞争。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好事情。然而,目前这种院校间的竞争有一些像军备竞赛。此外,原有的在争夺优秀生源方面的竞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学生消费主义”(student consumerism)倾向。这促使许多著名的私立大学尽量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如兴建新的图书馆、学生活动中心和运动中心。从这一角度出发,学校之间的竞争不仅仅体现在为学生提供其未来发展所必备的丰富知识,而且还体现在是否向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服务。
三、营利性高等教育
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与选拔性高校相对应的另一种高等教育形式为营利性高校。选拔性学校的主要对象是来自富裕家庭、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学生,然而营利性学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来自中低收入家庭、不太喜欢上学的学生群体。这部分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大部分美国营利性学校主要提供职业或技术方面的培训,毕业后授予资格证书、副学士学位或学士学历。近几年来,营利性学校的客户群体主要是在职成年人,他们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职业发展。目前,传统高校也提供大量的这类课程,而营利性学校则能在这个市场中与传统大学进行有效的竞争。创建于1976年的凤凰大学就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所营利性大学,它是美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营利性私立大学。
近几年,营利性高校被视作美国高等教育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一支生力军(注:有关营利性大学的数据既不一致,也不可靠。有关美国营利性高校最新的数据来自美国教育统计中心(the latest data from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reports),营利性高校在校生人数由1999年的430199增长至2000年的450084,其增长幅度为4.6%——占总注册人数的3%。以下数据的来源为公司的财政报告以及最新的院校介绍。)。在世界范围内,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这些商业公司不仅仅在其位于城市的教室里传播知识、颁发文凭,它们还在华尔街出售股票。“《高等教育记事》营利性高等教育股票指数”(Chronicle[of Higher Education]Index of[the stocks of]For-Profit Higher Education)尽管近来有所回落,但是在2000年该指数一度达到500点(500%)[8]。在该指数系统中,进行公开交易的九家上市公司已经获取近30倍的盈利,这一数值是其他市场交易盈利的两倍。不同于早期建立的营利性院校,当前的营利性高校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机构”。高等教育通过何种途径演变成这样一种营利性企业呢?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商业模式的“复制”;二是学生的助学资助。
此处以凤凰大学为例进行说明。凤凰大学依据美国高等教育市场的需求创立了一个商业计划,并成功地向世人证明这一商业计划是可以进行复制的。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独树一帜的办学模式创造了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以职业、技术培训为办学主旨的营利性高校也非常依赖政府提供的学生财政资助。在过去的十年间,整个营利性教育领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营利性职业教育在美国有着悠久历史,事实上它先于美国公立大学。直至近来,营利性学校往往被描述为非常分散的教育培训机构:几千所独立的提供非学位培训课程的商业学校。某种意义上,营利性高校常常要与当地的社区学院竞争生源,但却成功地填补了美国公立职业培训教育的空白。在这一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营利性培训学校应运而生,如创建于1892年的斯特瑞尔教育公司(Strayer Education),1931年建立的狄沃里大学(DeVry)。近年来,这两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大型的营利性教育公司。以狄沃里大学为例,这所学校自创立之日起一直不断地发展,不过大部分校园设施都是1997年后兴建的。其他几所营利性高校则是新近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过去的十年间,营利性教育领域兴起合并(consolidation)风潮。高额的办学利润不仅可以通过复制和推广成功的商业计划获得,而且也可以通过购买及兼并其他院校获得。营利性教育由早期分散的机构逐渐集中于一些公司,至少对于授予学位的教育机构来说是如此。
为什么直到近几年大批企业才开始寻求在高等教育领域发展?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答案非常简单。在美国产业结构中,教育名列第二(仅次于医疗保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此外,其中70%的教育投入来自政府公共资金。由此可以看出,企业投资教育并不是为了向教育提供更好的“捕鼠器”或是教室,而是旨在染指如此巨大的公共资金资源,以期获取丰厚的商业回报。(注:有关营利性公司在教育领域的商业运作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小学、中学阶段的教育,主要涉及教育券、特许学校、企业代理管理学校系统。)
1972年美国政府设立联邦学生助学金系统时,在营利性学校学习的多数学生也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这种资助。然而,这就立即为滥用学生助学金提供了可能。一些具有欺诈性质的商业学校通过诱使学生注册学习一些可疑的课程来骗取学生的奖学金(现在被称作佩尔奖学金)。随着80年代学生借贷文化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合法学校利用这一机会,录取学业准备不充分的学生,并为其申请政府提供的联邦助学贷款,最后导致联邦学生助学贷款的拖欠(default)率迅速上升。鉴于此种情况,美国国会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相关政策进行修正和调整。几项重要的预防性措施相继出台,如:拖欠率过高的学校将被取消申请联邦贷款的资格;在一所学校的总收入中,联邦政府提供资助所占的比例不应超过85%(不久更改为90%)。然而,上述滥用联邦贷款的行为只是一些小的投机行为。部分营利性院校意识到,它们从能够升学和毕业的学生身上所获得的好处要远远大于中途退学学生。1992年学生贷款额的限制被提高,对于营利性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对于某些营利性高校而言,这一政策无疑增加了他们的盈利机会,从而使营利性高等教育成为一桩赚钱的生意。营利性私立大学的运营情况请见表1。
表1
“《高等教育纪事》营利性高等教育股票指数”上市公司情况
名称
日期
注册
校园
销售额
利润率
市场资产
IPO
学生数#
数量 (美元百万) (%) (美元十亿)
阿波罗集团(Apollo Group)
1994
200052
71
1700
19.8
12.73
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
1998
83200
78
1500
10.8
3.14
科林斯学院(Corinthian Colleges)1999
52000
81726
11.1
1.08
狄沃里学院(DeVry)
1991
49000
717857.4
1.36
教育管理(Education Management) 1996
58000
438539.0
2.03
ITT教育服务(ITT Education Services)
1995
38000
77572
11.1
1.49
卓越教育(Laureate Education) 1993
130000** 12**
5529.4
1.45
斯特瑞尔教育公司(Strayer Education)
1996
20000
27166
23.3
1.43
凤凰网络大学(U.PhoenixOnline) 2000
79400
NA NA NA
1.26
*数据生成日期:2004年8月24日;**国际学校数量和注册学生数
没有任何一所院校可以通过学生自己交纳的费用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职业技术学校(technical schools)通常较为依赖联邦和州的学生资助,该类型学校的学费每年为9000美元到11000美元。然而事实上,学费的大部分是通过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学生贷款(student loans)来支付的,院校资助(institutional aid)似乎可以通过适当的调整解决经费不足部分。对于消费者来讲,并不存在“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在这里,“消费者”是指那些具有获得联邦资助资格的学生。实际上,如果一名学生想要申请联邦学生资助(FAFSA),首要条件是他必须在学校中注册学习。职业培训或商业私立学校主要依赖通过录取学生获得的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作为运行费用。以凯普兰学院(Kaplan College)为例,这所学校80%以上的办学经费来自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9]。颁发学位的企业高校(corporate universities)正尝试限制学生资助在其学校预算中的比例。由于企业高校的财政情况并不是完全公开的,每个院校从联邦获得学生资助的资格不完全相同。据粗略估计,在绝大多数私立高校的办学经费中,联邦政府学生资助所占比例高于50%。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私立高校的维持与发展主要依赖于联邦学生资助,尤其是联邦学生贷款。
凤凰大学又称为阿波罗集团,其创立始于一份独特的商业计划,发展到今天已成为营利性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支生力军。凤凰大学向某一特定顾客群体提供其教育服务,学生必须是年满23岁、有正当职业的成人。学校76%以上的学位课程与商企管理有关。凤凰大学迅速崛起的秘诀在于其独树一帜的授课方式,而不是所提供的教育内容。[10]通过向同一年级学生提供为期5周的模块化课程,凤凰大学强调最大限度地降低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s)和获取学位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在这方面,其他一些营利性私立高校做了更进一步的尝试。例如,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允许学生在完成夏季5周学位课程后,获取教育学硕士学位。当把获得某种资格作为学习的目标时,教育就可以被当作是一个生产线。
在凤凰大学就读的在职学生不可以获得联邦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但是,大多数学生可以从其雇主那里得到占学费比例一半以上的补贴。同样,校董事会将会向在剑桥学院学习五周硕士课程的教师提供补贴,然后在该教师获得学位后,在其工资待遇方面给予一定的提升。[11]
与非营利性高校不同,营利性高校通过创立新的分支学校来进行复制,以达到迅速扩张的目的。同时,知识的商业化也有助于学校的扩张。在凤凰大学,专业课程设计人员负责设计“课程目标”(learning objectives),相关教材、辅导材料被设计用于满足这一“目标”。所有的教材是精心准备、内容简单的,便于非全日制教师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学生传授这种标准化课程,最终使学生能够通过课程学习完成既定“目标”。[12]在传统大学中,学生的学生证被看作是开启知识宝藏的一把钥匙,而在营利性大学,学生通过支付学费购买一种可以测量的“产品”。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市场,营利性高校瞄准特定的市场需求,对其消费者许诺,为其提供一种以“职业提升”(career-enhancing)为目的的学历教育。从这一角度出发,营利性高校积极开发和拓展这一特定教育市场。他们竭尽全力地向其特定客户群体提供令人信服的服务,而这正是传统大学不能很好承担的那部分服务。营利性高校所扮演的角色得到部分人的认同。[13]但是纵观整个营利性高等教育,我们发现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对知识的商业化和简化、颁发令人怀疑其真实价值的文凭、缩短学分学习的时间,这些活动都是部分地通过利用公共资源实现。更令人担心的是,上述利润的获得已经远远超越了营利性大学的市场许可范围。
下面,我们有必要回到规模增长(growth)这一主题上,因为学生规模的增长才能给营利性高校的投资人和管理者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营利性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ies)的经营者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的教育市场,另一方面,他们一直不断地将触角伸向美国传统高等教育领域。在营利性私立大学中,学生注册增长最快的课程是硕士学位课程和学士学位课程。凤凰大学降低了其入学年龄标准,由原来的23岁下调至21岁,还设立了一个旨在招收18岁高中毕业生的课程项目。凤凰大学还宣布2005年将建立7至9个分校。近来,狄沃里大学在巴哈马群岛已经获准开设兽医课程,主要原因是巴哈马群岛的学生有资格获得美国联邦学生资助。[14]由此可见,美国营利性大学之间的利益竞争集中体现在其“机会成本”之上(更加方便、努力程度低)。营利性高校所提供的培训课程主要是针对市场急需的特定行业,在公立高校和非营利性私立高校纷纷上调学费的背景下,营利性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在价格方面更具竞争优势。
网络教育(online education)被视为一个崭新的教育领域。在新形势下,凤凰大学迅速将其下属的网络教育部门组建成一家独立的网络教育公司。另外,目前至少有三家营利性高校(Strayer,Career Education,Laureate Education)建立了自己的网络教育系统。实践证明,营利性高校在向学生提供商业化课程内容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发展网络高等教育过程中也是可行的。在营利性高校高速扩张的过程中,它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是如何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在营利性大学学习的大多数学生不可以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营利性高校正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争取政府在这方面的支持,如果获得成功的话,可以预见的是将会有更多的公共资金被“令人怀疑其价值的文凭”(dubious credentials)所滥用。
如前所述,美国营利性高校的运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这个论断与对营利性大学正面或负面的偏见是无关的。持支持意见的人认为,营利性高等教育一直致力于在教育这个一度封闭和自给自足的行业中建立一种高度自主的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可选择的专业培训。然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指责道,营利性大学通过向学生提供赝品或是肤浅的教育项目欺诈学生,使其不能获得全面、完整的教育。但是,营利性大学得到第三方支付者(the third-party payers)的经费支持才得以建立,而后者对于营利性大学提供的产品却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能。长期以来,美国的营利性大学以“轻松取得文凭”来取悦其消费者。在其教学管理方面,营利性大学的经营和管理者似乎更倾向于欺骗政府,而不是他们的学生。正如前文已提及的那样,在生涯教育大学(Career Education)、科林斯大学(Corinthian)及凤凰大学正在展开联邦学生资助的非法使用问题的调查。营利性大学把联邦政府提供的学生资助转化为其利润的增长,因此,营利性大学的命运与其说是依赖于市场,还不如说是决定于政府的财政资助政策。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其他一些著名的具有选拔性的非营利性大学的发展过程中。
四、政策问题
在结论部分,我将进一步论证前文所描述的美国现行教育政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目前从联邦政府角度看,国会面临着要修订联邦政府学生资助政策的问题。在州政府的层次,上述争执还在继续,但是,目前似乎私立高等教育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营利性私立高校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政治手段[15]。“职业学校协会”(Career College Association)是一个代表营利性高校的组织,在华盛顿特区,它已被看作是在议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游说组织。与其他高等教育协会不同,“职业学校协会”直接向国会议员提供竞选基金。此外,一些营利性私立高校还直接向某些议员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今年,正值共和党在国会中占多数席位,撰写立法修正案的委员会对营利性私立大学给予明显的支持。
这方面的有关证据很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列出。尽管2004年联邦学生资助的相关立法不会出台,然而政府表示将取消关于联邦政府学生资助在学校办学经费所占比例不得超过90%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学校的办学经费可以完全来自联邦政府对学生提供的资助。此外,政府将允许在网络大学学习的学生申请学生资助。营利性高校将被纳入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高等院校”(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体系之中,这样,营利性私立高校就可以拥有获得各种各样的联邦财政投入的资格。上述这些变化将会对营利性私立高校以及企业家们各种值得怀疑的活动给以更多的经费资助和支持。由于许多营利性高校会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一定的公共经费,这样就会卷走一部分本应投放到传统学院和大学的公共经费。[16]
从州政府层次来看,州政府倾向于通过对学生提供资助的形式来资助高等教育。目前,有几个州已经开始考虑将其所有对高校的政府拨款转化为对学生颁发的学券(student vouchers)。这项政策将适用于非营利性和营利性高校以及公立高校。上述提议可能不会很快付诸实践,但是某些举措正朝这一方向发展。近年来,州政府对学生资助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其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拨款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政府似乎赞同和支持“高学费/高资助”政策。这直接导致了州立高校的学费迅速上涨。在目前经济不景气和政府预算缩减的情况下,各州政府基本上赞同将更大比例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学生身上,通过学生贷款方式实现。
从国家层次来看,在联邦政府财政政策核心——助学金和贷款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华盛顿特区,有关学生贷款政策与学费的高涨有关的论述被视为异端邪说。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甚至组织了一次专门调查,试图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化的关系。但是立法者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在立法时谨慎地对待成本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家庭)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方面,有必要提高学生补助性贷款的上限,从而使之与不断上涨的学费相适应。一些收取学费较低的学校则反对提高学生补助性贷款的最高额度,他们认为,这种政策往往使那些富有的、收费高的大学受益,最终导致不同学校在教育经费支出方面的差距。在这一情形下,适当地提高贷款限制似乎是一个最可能出现的结果。对于低收入学生来说,发放助学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即将修正的立法可能将佩尔助学金冻结在目前的水平。
从某种意义上,联邦学生资助政策已经成为“高学费/高资助”政策的保护伞。值得关注的是,联邦助学贷款已经被看作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特权之一,对这一特定阶层的学生提供越多的资助,其需求也就越大。从这一角度出发,国会有充足的理由在制定政策时对成本及其影响予以谨慎的考虑。但是,这种思路也会将针对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财政资助的政策排除在外,这些学生特别需要获得财政补助,以满足学费成本的增长。
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希望通过制定财政资助政策来提高高等教育财政资助的效率,也就是说,促使高收入学生为其教育支付更多的费用,同时对那些低收入学生实施财政资助。但是正如我叙述的,我们尚未看到这种制度的结果。这里,我用“没有看到”(unforeseen)一词,而不是“不可预测”(unanticipated)一词。经营营利性高校的企业家们已经预测到这些变化对于市场力量(market force)的影响,并采取了对公司有利的行动。他们还积极对政治过程进行干预,以争取对自身利益更有利的法律条款。
市场营销学有一条公理,企业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的产品或降低产品的成本来获得相对优势。但是第一种策略和第二种策略不可相互混合,否则必将导致失败。[17]这一原理在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有所映射。利用公共资金扩大学生的教育消费能力,对选拔性私立学院和大学十分有利,它们利用这部分资金提供不同的教育质量,又可以提高其学费水平。营利性大学也积极参与竞争,吸引获得政府补助的低收入(对价格敏感的)学生。在这场竞争游戏中的失败者是公立高等教育,它们眼睁睁地看着日益崛起的私立大学夺走了本应属于它们的政府补贴。这样,公立大学只能竭尽全力为大多数传统大学生提供低价位且质量较高的教育服务。
译者简介:盛晓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8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