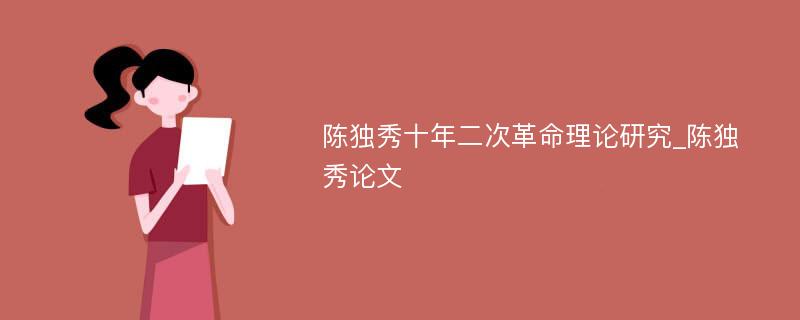
近十年有关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十年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二次革命论”,一般是指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过一段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待各种条件成熟后,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一词是蔡和森在1928年11月1 日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一文中最早总结出来并公开使用的,在该文中,蔡和森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观点总括为“二次革命论”。随后,“二次革命论”这个概念几乎一直被等同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并且被人们沿用下来,以致在当今学术界,还一直是陈独秀革命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笔者这里将近十年来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时间及其发展变化
在学术界,关于“二次革命论”的形成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3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形成于1926年。
持1923年观点的人基本上是以陈独秀在1923年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作为“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标志,认为这两篇文章完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阐述。其理由是在这两篇文章中,陈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是明明知道民主革命的成功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并且在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而资产阶级的势力“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故尔陈设计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是第一次革命,它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权为目标;第二次革命,则是必须等到“资产阶级崩坏时”,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1〕。 持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认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思想上就已夹杂着二次革命思想因子的民主革命意识,国共两党合作正式提出前,“二次革命”已具雏型,是“二·七”惨案促成了“二次革命论”的最后定型〔2〕。 目前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人比较多。
持1926年观点的人一部分认为陈独秀在思想上确立“二次革命论”观点的标志是在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扩大会议上。 其理由是陈在这次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推动民族资产阶级,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一是由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3〕,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二次革命论”的内容。 另一部分人认为陈两个月后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更加清楚的回答:“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因此认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是陈“二次革命论”形成的标志〔4〕。
持1926年观点的人否认陈的“二次革命论”理论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有的人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谁掌握政权,“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说明陈当时已没有写《造国论》时那种乐观情绪和估计了,又基木回到了中共“二大”时民主革命前途的思想状态——“不定论”状态,而并非“二次革命论”思想状态〔5〕。还有的人认为这两篇文章中虽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 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也未明确提出“二次革命论”的公式;并且陈发表这两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和意图不是为了阐述他的“二次革命论”,而是在于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在于纠正当时党内反对和国民党合作的“左”倾关门主义情绪,来阐明国共合作的必要和可能,排除国共两党党内阻碍国共合作的因素,以促进国共合作的最后建立〔6〕。 所以,陈“二次革命论”并非形成于1923年的两篇文章。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发展变化,研究者们又有不同观点。持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3年观点的人基本上认为从1922 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到1923年的这一段时间为“二次革命论”的萌芽阶段,而从1924年到1925年则有某些纠正和反复,1925年以后到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二次革命论”进行彻底批判之前则为“二次革命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并且以1926年12月中旬党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的召开为标志〔7〕。另外也有人认为, 从1924年秋到1925年底这段时间里陈放弃了“二次革命论”,而把所谓后来“二次革命论”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认为是“二次革命论”的重新抬头〔8〕。而持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于1926年观点的人则认为1926 年7月以前陈独秀对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看法处于“不定论”阶段,而后才是“二次革命论”,到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又逐渐转向了“一气呵成论”。
总之,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表现得几起几落,数次反复,很难把握,笔者这里对此不再一一赘述。
二、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
关于“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问题,经过近十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已成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民主革命前途的错误分析,是他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根源。认为在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上,陈忽略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所显示出的伟大革命力量,而被“二七”惨案后暂时的工人运动低潮所迷惑;在对农民的认识上,不懂得中国民主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则片面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9〕。
(二)当时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各种理论层出不穷,陈独秀对此批判又吸收,是“二次革命论”的理论来源。认为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并没有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立场、观点、方法仍然停留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的思想主体仍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所揭露的资本主义弊病,所规划的社会主义前途,都没有超越三民主义的范畴〔10〕。
(三)由于当时历史处于革命衔接时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形势复杂,易出偏差是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的主要客观原因。因为当时可供共产党人思考的民主革命前途观只有两种:一种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治主义的国家,经过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发展,再来进行一次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另一种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除此以外,当时并没有第三种前途观可供共产党人思考或选择。然而中国的社会性质变化也不能超越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能发生民主革命;并且在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贫穷落后、受辱挨打的根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分化,尚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资产阶级还能够革命,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小的资产阶级对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争斗”(《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固然民主革命不能使劳苦大众获得彻底解放,资产阶级旧民主政权也必然包藏着许多腐败与罪恶,但较之封建专制,毕竟要进步得多。陈独秀选择“二次革命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11〕。
(四)共产国际指导理论的失误及苏俄实用主义倾向的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的重要客观原因。由于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没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虽然也曾多次批示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两个明显缺陷: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实现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制约。共产国际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革命的结果将不可能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12〕。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所以陈独秀不能够正确对待共产国际在列宁逝世后对中国革命的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右倾错误的指导,这为陈独秀形成“二次革命论”创造了巨大可能。这种观点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反复变化,学术界基本上把它直接归因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是其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基本错误与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建立联合阵线的合理因素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前途与二次革命保守方法的矛盾的一般表现〔13〕。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的评价
第一种观点是基本否定的观点,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违背中国革命规律的错误理论。其理由是:
1、陈独秀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和表面性。 针对陈独秀1923年发表的两篇文章,许多学者认为陈在其中虽然试图以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但是,他偏重于“唯生产力论”,未能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未能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文章中错误观点的根源在于陈没有摆脱早年受到的进化论的影响,仍然以顺序进化的观点看待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而陷入了庸俗进化论和机械唯物论窠臼之中。当时陈看到了中国生产力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一面,也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唯物主义的正确认识,但是他却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绝对化了,看不到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他不懂得在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武装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也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应当力争,从而忽视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主观能动性〔14〕。
2、陈独秀未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 在评价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时,一些学者认为陈所强调的“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社会”教条地对待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并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理,脱离了中国国情。仅仅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社会形态沿革的相承关系,不懂得根据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国内外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可以避免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同时也不懂得,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一个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真正的历史阶段〔15〕。
第二种观点是基本肯定的观点,认为:
1、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并非与马列主义相悖, 并非是机会主义,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的统一。“二次革命论”在民主革命理论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上与马列主义的民主革命理论大致吻合,是在辩证、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后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十分幼稚,党的自身力量以及党所掌握的革命力量的不足,不可能将两次革命一气呵成。既然中共及其革命力量远不足以夺取全国政权,通过政权力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使两次革命一气呵成;既然广大群众尚未认识到革命应该一气呵成,那么中共唯一合理的历史选择,就只能是二次革命——先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华联邦共和国,然后再伺机图谋第二次革命。否则,不顾当时的具体实际,推行“一气呵成”的革命战略,只能使党与广大群众脱离,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之境,加速民主革命的失败〔16〕。
2、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力量和作用的夸大, 承认国民党的领袖地位,提出革命后资产阶级拥有政权,并不等于承认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许多学者认为陈没有认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的必然前途,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设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彼此互补,集中统一于国民党,也就是说陈并不是不要领导权,甘当附庸与追随者,而是积极地争取领导权的〔17〕。
3、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功大于过。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二次革命论”影响了党对政权和军权的争夺,也是陈对国民党让步,限制工农运动的根本原因,对中国民主革命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二次革命论”对克服党内的“社会革命”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形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革命力量的发展和推动国民革命的进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启迪与借鉴作用〔18〕。
另外,还有许多研究者不认为陈独秀具有“二次革命论”观点。他们认为:在陈独秀的思想中,虽然有许多错误的观点,有所谓“二次革命论”的倾向,有的甚至于近乎“二次革命论”,但是,他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程度的认识。一种认为陈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紊乱性。认为他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时,就带有所谓“二次革命论”倾向;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时,就带有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倾向。并且在革命形势高潮时,他的思想就激进一些,所谓“一次革命论”的色彩就浓一些;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他的所谓“二次革命论”的调子就高一些。陈这种思想上的摇摆性表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浅薄,这种浅薄的认识使他难以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使其无论是“一次革命论”或“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都没有在他头脑中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19〕。
另一种则认为陈独秀思想中更多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否定。认为陈虽然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即被认为标志陈“二次革命论”的三篇文章)中认为无产阶级非常幼稚,农民居处散漫难以加入革命,但却肯定地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最勇敢的先锋队”,农民有诸多原因可能加入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的“伟大潜势力”;陈是认为国民党应该站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陈主张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因为在陈看来,“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并不是同一概念:国民党在国共合作后,已作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由于各国国情不同,中国社会进化将是个例外,不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工人阶级想要取得政权,要依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所以对陈的国民革命成功后必须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不能单一而论。所以陈主张革命的领导权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实现社会主义〔20〕。否定陈独秀具有“二次革命论”观点的人为数不是很多。
注释:
〔1〕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2〕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第一章。
〔3 〕文培森:《陈独秀的“国民革命”前途观:兼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4〕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
〔5〕文培森:《陈独秀的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6 〕罗玉明:《论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等两篇文章》,《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
〔7〕顾丽梅:《“二次革命论”的由来及评析》, 《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2期。
〔8〕徐光寿:《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
〔9〕肖贵清:《从1923—1925年陈独秀的思想变化探微》,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10〕罗玉明、杨明楚:《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探源》,《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
〔11〕段治文、钟学敏:《略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的原因》,《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2〕刘诚:《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的两次转变》,《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3〕朱洪:《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
〔14〕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
〔15〕郭绪印:《重评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学术月刊》1991年第7期。
〔16〕唐恒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和2期。
〔17〕蔡文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中的领导权思想辨析》,《南开学报》(哲社)1995年第6期。
〔18〕唐恒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研究》,《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9〕苏长聚:《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安徽史学》1993年第1 期。
〔20〕武满贵、仇书耘:《陈独秀并非“二次革命论”者》,《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1年第2期。
标签:陈独秀论文; 二次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安徽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