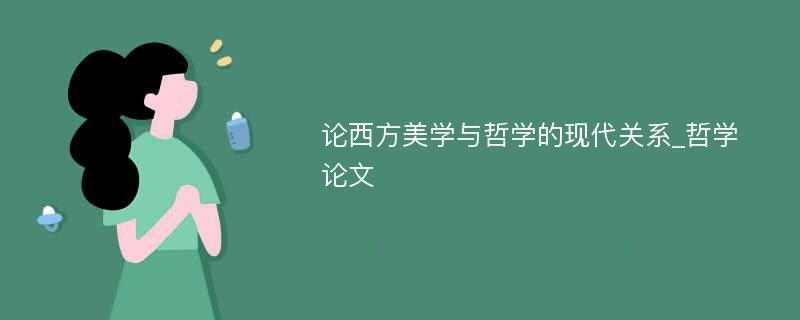
略论西方美学与哲学的现代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美学与哲学的联系由来已久。现代美学虽然越来越独立,与心理学也越来越亲密,甚至还更专注于艺术领域,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被削弱,美学始终是一门具有哲学性质的学科。
现代西方哲学,在我国一般是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西方哲学。但对现代西方美学的起点则有不同的说法。笔者认为,它与哲学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它们几乎是同时进入现代形态的。这种“现代形态”的标志,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与美学共同具有的反理性和反思辨的特点。这一划分标准以哲学与美学发展的自身特点为根据,不仅将现代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和美学区别开来,而且也更加符合意识形态发展史的实际情况。本文的讨论就在这一界定下展开。
一
现代西方美学与哲学的联系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美学思潮与哲学思潮的关系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个现代西方美学流派的后面都站立着一个哲学流派,或者说,差不多每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会引伸或变化出一个美学流派来,而不同流派汇聚而成的思潮更使得美学与哲学的现代联系呈现出宏观态势。
我国哲学界一般将现代西方哲学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认为两者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倾向。这两大思潮的理论渊源虽然十分久远,但是如果着眼于“现代”的话,则可以归之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批判黑格尔哲学为开端的反理性主义和反思辨理性的思潮。前者导引了人本主义的洪流,后者则成为科学主义的源头。
与此相呼应,现代西方美学,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也存在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并且同样是从直接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起步的。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美学思潮的最初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美学。这一美学直接从他们的哲学中引伸出来。叔本华把世界分为“表象”和“意志”两部分,并且认为“意志”是真正本质的,而美则是“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即“理念”的展示。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主体的作用,并且进一步认为,美实际上是“理念”和“纯粹主体”的结合。①紧随其后的直觉主义美学则来自于柏格森自己的“生命哲学”。柏格森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的“绵延”,是“生命冲动”。要把握这本质只能靠“直觉”,因为“所谓直觉就是指那种理智的体验,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而艺术和审美就是这种直觉过程。②到了二十世纪,首先是胡塞尔,然后是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和法国美学家杜夫莱纳共同建立起了现象学美学。胡塞尔认为,一切意识都具有“意向性”(指向性和建构性);而“现象”就是意识中的全部“事物本身”;我们只能通过“还原”法(先验的和直觉的方法)直观地把握和非因果性地描述“纯粹的现象”乃至“先验的自我”。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现象学美学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意向性客体”,而审美活动则是一种特殊的“还原”,即把一切经验因素都排除掉之后的直观,它最终指向的就是“先验的自我”。③本世纪中叶先后崛起的存在主义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是现代西方最为自觉的人本主义美学流派。存在主义宣称,“存在先于本质”,而一切存在的出发点是个人的存在,因此“人”是中心。据此,存在主义美学认为,艺术作为一种非现实的意象,它的存在先于它的本质,而美则是适合想象的事物的一种价值,它们都离不开“主体”(即人)的“创造”。④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的美学立足于“社会批判理论”,特别强调艺术对异化人性的拯救和现存社会的批判。该学派主要代表马尔库塞曾经指出:“一种不再是剥削主体或客体的新型男人和女人,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发展在人和物中被压抑的审美可能性幻想”,因此,“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这一概念的本意不是要美化既定的现实,而是要建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与既定的现实相对抗的现实。审美想象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除了上述直接从特定的哲学流派中发展出来的美学流派外,人本主义美学还包括另一大部分——心理学美学流派。这其中主要有德国美学家李普斯为代表的“移情说”美学,瑞士美学家布洛的“距离说”美学,德国美学家朗格的“幻觉说”美学,英国美学家贝尔和弗莱的形式主义美学等,而最重要的流派则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美学。作为心理学美学流派当然不是直接从特定的哲学流派发展而来,但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因而特别注重心理功能的研究,把情感、想象、本能等非理性心理因素提到首位,其中精神分析学美学表现得尤为突出。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弗洛依德是德国意志哲学的继承者,所以偏重本能和情感”。⑥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本主义美学思潮中,无论是哲学美学流派,还是心理学美学流派,都非常强调审美活动中的非理性因素,强调主体(人)的决定作用。这既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美学背道而驰,又同人本主义哲学的思想一脉相通。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起点是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创立的实验美学。他认为,美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应当把美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部门,采用实验、观察、归纳等“自下而上”的经验方法来加以研究;而“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方法则“好象是泥足巨人”。⑦几乎与此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英国哲学家斯宾塞为代表的生物学美学和英国生理学家艾伦为代表的生理学美学等。这些美学流派的产生,从哲学上看,一方面得益于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丹纳的《艺术哲学》就完全是实证哲学的美学产物,他甚至认为,“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⑧而斯宾塞作为一位著名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则是人所共知的。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正在崛起的马赫主义的影响,在费希纳的《美学导论》和艾伦的《生理学美学》发表之前好几年,奥地利哲学家马赫已经写出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向牛顿乃至黑格尔发起了又一次冲击。到十九世纪末,则进一步产生了以德国人类文化学家格罗塞为代表的社会学美学。格罗塞反对“思辨美学”,主张把美学建设成为一门“艺术科学”,他广泛收集和利用人类学、人种学的资料,深入考察原始艺术,力图揭示心理、社会、文化、自然等因素与艺术的关系。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科学主义美学思潮开始倾向于语言的逻辑和意义分析。由英国美学家瑞恰兹创立的语义学美学就是循着这一方向的最早代表。瑞恰慈认为只有在对语词、句子和意义作出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与审美判断有关的问题才有意义。他主张区分“情感语言”和“符号语言”,指出艺术中使用的是“情感语言”。⑩随后,分析美学的大潮便汹涌而来了。分析美学的后盾是分析哲学。从广义上说,分析哲学包括作为语义学美学哲学基础的逻辑实证主义,因此,语义学美学和分析美学实际上都是第三代“实证主义”的产物。分析美学虽然自身包容着不同的倾向和观点,但是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对“美”的命题进行“语言清洗”。这种“清洗”的结果就是“美”是不可定义的。而之所以不可定义,不仅因为“美”是形而上命题,更因为“美”是多义的,相似的。(11)稍后,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也在美国心理学家阿恩海姆的努力下,以更加“实证”的姿态出现,以致于有人认为,“艺术心理学的各个专题……等一次获得了科学的基础”。(12)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美学异军突起,直接向人本主义美学宣战,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达到人文学科的科学化。并且认为结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包括审美和艺术活动)的普遍有效原则。(12)
由此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属于科学主义美学思潮的各流派也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倾向,这就是特别强调“实证”,强调经验,强调归纳和“分析”。这同黑格尔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与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却心心相印。当然,在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马赫主义和“科学哲学”对于美学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它们所孕育的美学产儿也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二
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进行“综合”的趋向。这种“综合”并不是折衷主义的调合,而是试图兼收并蓄这两大思潮的精华,从而在更高层次上保持反理性和反思辨的特点。哲学释义学和哲学人类学便是这一趋向的集中代表。哲学释义学的研究中心是关于“本文”的理解问题,但是,它不再如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等那样单纯从对象着手,而是注意了主体的作用,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把这种对客体的理解看成又是主体的存在方式。(14)哲学人类学则明确宣称自己的讨论中心是人,但不仅仅是意志的、情感的、非理性的人,而是“完整的人”,这“完整的人”既是被科学所研究的人,又是为自己所理解的人。(15)显而易见,这同存在主义等也大有区别了。哲学释义学和哲学人类学都有一段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流派却方兴未艾,它们正代表着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这种“综合”倾向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现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形成之初,就已经奔腾着第三股洪流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先后形成的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就是它的最初代表。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的对峙展现了“综合”的原始形态,而新黑格尔主义的理性和非理性混杂也显露了早期“综合”的特征,这股潮流的进一步发展便产生了实在主义和影响很大的实用主义。在实在主义中,无论是新实在论的“中性实体”,还是批判实在论的“特性复合体”,都在继续着“综合”。如果说这还是一种含糊的“综合”,那么,实用主义就变得十分明确,它一方面强调“经验”,另一方面又力主信仰的重要性,这使它成了哲学释义学和哲学人类学之前最自觉的“综合思潮”哲学。值得指出的是,十九世纪末兴起的价值论思潮与“综合思潮”交织在一起,一直贯穿至今,甚至成了“综合”哲学的代表。当然,早期和中期的“综合”是不能与当代的“综合”同日而语的,这是因为当代的“综合”哲学是建立在对以往全部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它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也更加自觉。
现代西方美学也毫不例外地涌流了这一“思潮”,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所创立的表现主义美学一般被认为属于人本主义美学,但是如果把他与柏格森的美学相比较,却可以看出他的某些“综合性”。表现主义和直觉主义都讲“直觉”,都认为“直觉就是美”,但克罗齐的“直觉”既表现了情感,又创造了事物,“没有在表现中对象化了的东西就不是直觉”,“直觉的活动能表现所直觉的形象,才能掌握那些形象”;(16)而柏格森的“直觉”则是一个单纯的进程”,“它使我们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17)显然,克罗齐作为新黑格尔主义者比生命哲学家保留了较多的“客观性”和“理性”。美国美学家桑塔亚那所创立的自然主义美学则往往被归入科学主义美学,然而桑塔亚那不仅强调美感经验的重要性,也强调艺术和本能的密切关系,甚至还强调理性是艺术和愉快的原则。(18)这恐怕是同其实在主义的哲学背景分不开的。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继续了这一进程,而且由于同其哲学的直接血缘关系更加具有“综合性”的特征。杜威特别强调“经验”,认为“艺术的源泉存在于人的经验之中”,因此要“恢复美的经验与正常生活进程之间的延续关系”。(19)但同时也强调了审美中的“直觉”性,并且力图把“经验”和“直觉”统一起来。(20)发端于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论美学同样具有这一特征。符号论美学一方面用“符号”统一了文化,认为各种文化现象都不过是人类“符号活动”的产物,艺术也是这个“符号世界”的一部分,是“情感的符号”。对这种“情感符号”,符号论美学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这使它与科学主义美学相似,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用“符号”统一了人性,指出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符号性”就是人高于动物之所在,也就是普遍人性之所在,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是与人的生命,情感紧密不可分的。(21)这又使它同人本主义美学相通。新康德主义就这样在美学中树立了自己的代表,而卡西尔对马堡学派的“背叛”则更证明了他的“综合”倾向。这种美学中的综合交融到了本世纪六十年代同样变得更加明显也更加自觉。释义学美学就是最明确的代表。该派美学的创始人,德国美学家伽达默尔既强调理解者(欣赏者)的能动作用,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不同时代与条件下的不同理解者的解释的总和,又指出作品(本文)的重要性,并且对其作了比较精细的分析。(22)由释义学美学开始的这种当代意义上的美学“综合”则导引了接受美学的产生。与此同时,价值论在美学中也进行了广泛地渗透,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属于“综合”思潮的美学流派几乎都同价值论有着某种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哲学人类学对于美学的影响目前虽然还没有直接的结果,但是它已经取得的广泛发展,它正产生的深远影响,比起释义学来绝没有丝毫的逊色,甚至还更为深刻。近年来兴起的比较美学也许就是这种影响的第一声春雷。
现代西方哲学大潮中还有一股力量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宗教哲学。产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新托玛斯主义和人格主义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新托玛斯主义美学则是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尤其是新托玛斯主义哲学的直接产物。现代西方的宗教哲学和美学并不等同于神学,也不同于上述的各个思潮。它也具有一定的“综合”倾向,但是它的核心始终是上帝,并以此来统摄科学和人性。宗教哲学和美学源远流长,在现代也仍然不断有新的发展。这是一条独特的思路。难能可贵的是,哲学人类学已经把“综合”的触角伸向了宗教哲学,这是十分发人深思的。
三
现代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极其多样,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美学方法已明显呈现出多元化状态。但是,哲学作为一般的方法、总的方法,对于美学的影响却要比那些具体的方法深刻得多。现代西方美学的各个流派几乎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总离不开与其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哲学流派和思潮的总的方法。即使同某一哲学流派和思潮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有的美学流派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方法论的影响。
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五花八门,纷繁杂陈,但是就其对美学方法的一般影响而言,我以为主要有这样几种:
首先是“实证”方法。这是实证哲学的方法论。它强调经验的描述和实验的证明,认为经验之外的东西是无意义的。这种“实证”方法对于现代西方美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实验美学、生物学美学、生理学美学和社会学美学,等等,无疑都是运用这一方法的第一批美学成果。费希纳的十三条美学规则就是来自于他创立的心理实验。艾伦则通过对人的生理特点方面所作的实验来探讨审美活动的规律。斯宾塞也着眼于对美感心理机制的分析。而丹纳、格罗塞更是收集了大量社会学、人类学、人种学的材料进行实证研究。由此开始,“实证”方法始终贯穿于科学主义美学思潮。语义学美学、分析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无不包含着“实证”的精神,即使在结构主义美学中也依然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而在属于人本主义美学的各心理学美学流派中,也不期然而然地显示出它的影响力。这种“实证”方法在当代也仍然不失光彩。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新实验美学”引进和改造包括系统论在内的一大批自然科学的方法,从而产生了“自上而下的实验美学”。(23)这实际上恰恰是“实证”精神的当代闪光。
其次是“分析”方法。这是分析哲学的方法论。它继承并且发展了“实证”的方法,也可以说是“实证”方法的“现代化”。这一方法强调“语言的分析”,强调只有通过对语言的逻辑或意义的分析才能够把握世界。二十世纪曾被人称为“分析的时代”,可见其影响之巨。语义学美学和分析美学当然是这一方法的直接受益者。瑞恰兹用语义学方法考察了十六种传统的与现代的“美”的定义,指出了“美”这个词在不同使用中的多义性,并藉此建立了语义学美学的基础。分析美学进一步把美学的各种问题纯粹地作为语言问题进行语言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论和语境论分别代表了该美学的两种模式,但二者都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语言清洗(即分析)精神。分析美学由此产生极大影响,并且成为科学主义美学的中坚,结构主义美学虽然不是“分析”方法的直接产物,但在其中还是可以发现它的间接影响。这种“分析”的影响不仅在本来意义上发挥着威力,而且带着某种泛化的倾向展示自己的力量。符号论美学就是一个明显的代表。此外,在实用主义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美学中,这种“泛化”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现代西方美学虽然似乎由“实证”和“分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第三种方法不仅存在,而且还远远没有发挥出自身全部能量,它对于现代美学的影响或许只是开了个头。这个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现象学方法不同于经验归纳,也不同于先验综合,更不同于逻辑推理,它是一种本质直观的方法。它要求认识的主体摆脱对世界的素朴的看法和科学的看法,把对外部世界实在性的种种看法统统“悬置”起来(即加上括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面向“事物本身”,才能返回到“现象”(即呈现在意识中的一切东西),才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现象学方法被誉为西方三大哲学方法之一,它包含了对人类认识的深刻反思。现象学美学是它的第一个产儿。英伽登运用这一方法把文学作品规定为“意向性客体”,又将这“意向性客体”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紧紧联系起来。他的文学美学理论由此而成立。杜夫莱纳更是从审美对象开始现象学直观,继而进入审美知觉结构,最后达到本体论,建构了现象学美学的完整体系。由现象学美学开始,这一方法又逐渐影响存在主义美学、释义学美学和接受美学,甚至在结构主义美学那里也有着它的痕迹。我们可以从存在主义美学著名的论点——艺术的存在先于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本质——看到这种影响;也可以从释义学美学的“语言”和“言语”分析中依稀发现这种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方法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哲学人类学对于美学的影响正如前述还远未发挥出来。这也许更表明对于现象学的开掘还只是处于表层。
最后,古老的哲学方法——思辨方法并没有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反理性和反思辨而消声匿迹。它在美学领域中,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仍然发挥着作用。叔本华的意志主义美学虽然以反对黑格尔而著称,自身却仍然带着浓重的思辨色彩。桑塔亚那的自然主义美学尽管诞生在美国,却还是染上了思辨方法的“顽症”。而克罗齐的表现主义美学更是摆脱不了思辨的影响。即便是首创“自下而上”美学的费希纳也并没有将“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一棍子打死。一般地说,当研究以美”为主题时,大多会采取思辨方法;而把焦点放在“艺术”上时,则往往倾向于“实证”研究。现代西方美学把研究的重点从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转向主体的审美心理和艺术,这确实使思辨方法退居幕后,从而引发了美学方法上的“革命”。然而,当现代美学经过了几番迂回曲折,最后又不得不面对美的本质(或者叫“美的普遍性”,抑或叫“美何以能够”)问题时,大多数美学家便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思辨”之路。这在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和释义学等晚近的美学流派中同样可以得到证明。出现这种情况大约是因为“在美和艺术中能够按科学方式处理的现象却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美与真、善一起所构成的三大理念,属于哲学的永恒课题;艺术作为人的自我证明的方式之一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而文化只能是应该由哲学来探讨的本质性的问题。”(24)
西方美学与哲学的现代联系还可以从更多的方面来加以说明。例如,从美学基本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关系的现代嬗变上,即对美的本质问题探讨形式的变化中考察。又例如,从现代艺术的发展中,即美学与哲学联系的对象化过程中考察。但是,仅就上述思潮和方法两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出,西方美学和哲学在现代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
这种联系当然不是偶然的,它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表明美学是具有哲学性质的学科。我们过去曾经特别缺少美学的“实证”研究、美学的“应用”发展,补上这些课,加强这些方面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没有哲学的真正发展,美学的进步依然是十分困难的,因为,美学始终和哲学在一起俯视着人生。
注释:
①⑦⑨见李醒尘《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德国卷》第383,392,393,417-422,22-32,684-692页。
②⑩(16)(17)(18)(19)见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卷》第128,131,379,381,382,54,55,128,259,261,264,267,334,337页。
③④⑤(11)(13)(22)见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卷》第260,261,263,224,225,230,436,80-83,102-122,28,29,465,466,467,469页。
⑥《朱光潜文集·1》第348页。
⑧丹纳《艺术哲学》第11页。
(12)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第1页。
(14)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32-55页。
(15)见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第3-9页。
(20)见王鲁湘《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第336页。
(21)见卡西尔《人论》第32-34,189-193,281-282页。
(23)(24)见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第35,172,22页。
标签:哲学论文; 美学论文; 现代西方哲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人本主义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现象学论文; 生活方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