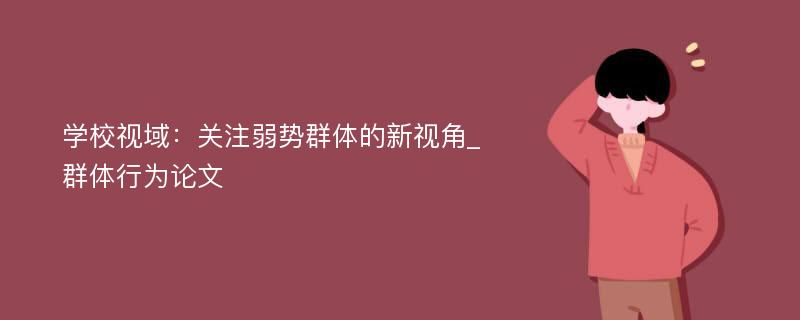
学校场域:一个关注弱势群体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场论文,弱势群体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2-0064-07
全球化带来的一种多元转变正日益将人们裹挟其中,欲置之度外而不能。这种转变的一个鲜明标记,就是“时空凝缩”(大卫·哈维)。一方面,日臻完善的现代信息技术消弭了地域的阻隔与断裂,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个“地球村”,似乎正应了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一切皆流[1](p.1);另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的时空距离关系,人们的互动不再受制于必然“到场”这一条件,“缺场”的联系同样变得习以为常[2](p.114)。“时空凝缩”内蕴着一种演绎:全球化是“在场”与“缺场”的交叉,是“相距遥远”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本土的具体情境的交织,是时空穿越和脱离了必然在场这一先决条件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人际互动的重组。作为这一演绎的逻辑结果,有学者试图用“全球场域”的理念代替通常使用的“全球体系”[3](p.115)。
置于“全球场域”开放、动态的时空视野,教育日常生活中同样有一种“在场”与“缺场”的交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与“缺场”交叉,这是一种常常不为人关注的“在场”与“缺场”交叉。这就是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希冀进场,却被排除场外;虽在场内,却不被场内接纳;表面在场,实际并不在场;物理场的在场,意义场的不在场。由是,一个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是:学校场域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如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如何体现?
一、弱势群体——阳光下的隐匿
1.微根末节上跳动着时代脉搏
不知道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清晰度,能否达到感觉饥饿那样的清晰?那是一种真实而具体的饥饿——既不是接受扁桃体手术者不能进食的人为饥饿,也不是正在节食瘦身者故弄玄虚的饥饿[3](p.115),生存处境应该是一种真真切切、伸手可触的感受!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自我的生存处境是不言说或不便言说乃至不知如何言说的。同样,在教育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会这样自问:我是弱势群体吗?我怎么是弱势群体的?为什么我是弱势群体?但这种抽象话语的变式却可能常向心灵发问: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会这样?我该怎么办?
我们能感觉到人们手里总捏着一把尺子,度量着不同的人的不同地位、身份,不同成就、资本以及家庭、社会的关联,再抽出相应的标签一一标定。也许,“蹲下身来看孩子”这种教育眼光的下移,恰恰缘于我们对孩子太多的俯视、歧视和贬损。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就连被俯视也无法拥有!他们是一个被遗忘、被无视和被漠视的群体。
诚然,教育中的强势弱势、中心边缘,可以说是某种客观存在,表明的都是一种特性与个性,正体现了教育的多元与多样。问题是教育过程中我们并不陌生的人为划分和刻意固化,往往形成强势弱势、中心边缘之间的坚壁区隔和过于冷漠,且在强势与中心、弱势与边缘之间轻而易举地划上等号。而那些占据中心的人也“已经确立”了自身对资源的控制权,使他们得以维持自身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人的分化[4](p.222)。
对此,人们会表现出种种不平,但却很少去追问:为什么教育中的边缘化现象与弱势群体值得关注?为什么强势弱势、中心边缘总要变成一种实质上的认可而固定下来?是什么制造了这种等级化的教育空间?教育通过什么样的排除系统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外?……
康德曾说:“对于人类进步的可预见性特征,我们不应只从那些伟大事件中去寻找,而应到那些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事件中去搜索。”这种“搜索”在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研究中体现得相当出色。他不是把眼睛总盯在那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主题上,恰恰相反,而是善于从一些被人忽略了的微根末节上去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他的研究对象虽然都是些被称为越轨行为的社会边缘现象,但透过这些,却让人们真切触摸到了时代的印记。
学校场域中的弱势群体是那种“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群体,在对他们生存境遇的关注中,我们难道不能触摸到一点时代跳动的脉搏?!
2.你很强,你也很弱
“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一个丰富而开放的概念,它动态变化,而不是固化标定的。这也就是说,那些身处边缘,被俯视、被贬损、被遗忘、被漠视的弱势群体,只是常人眼中的“常态”弱势群体;那些成绩优秀者、那些公认的教育者、那些学校运作的管理者,同样可能被置于不利境地,成为与被他们标定的弱势群体相同的弱势群体;而那些看起来是弱势群体的,又可能并不是实际的或真正的弱势群体。这恰恰是一些为常人所忽略的、被误读和过度解释的、不断突变断裂的弱势群体!
一个值得警示的话题就是:你不一定在弱势群体之外!
这并非一种危言耸听、无所适从的人为制造,在不同的教育时空中,强势群体变为弱势群体的可能性的确存在;而若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说,这一话题何尝不能成为逼迫我们关注弱势群体的一个借口呢?!“弱势群体”不应作教育日常生活中已有的窄化、固化的单一理解,而应作为一个较为宽泛、不断变化的开放性概念使用,它更多指涉的是“此时此地”处境不利的特殊群体,且可能涵包三种类型:一是被人们认定是弱势群体,实际也的确处于不利境地的群体;二是人们以为是弱势群体,但实际并非弱势的群体;三是人们眼中的强势群体,可能被置于或变为弱势群体。必须说明的是,所谓强势、弱势仅是相对而言,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某种状态呈现,并非固定不变。
既然是弱势群体,所呈现的生存境遇就是特定教育情境下的具有一群人或一类人影子的“这一个”,如果非要从中去找寻什么普遍性,非要说“在我们这里不是这样的”,那无异于将自己拉上一条生产流水线,去参与一个个产品标准件的制造。
二、解读场域——穿越时空隧道
对场域的解读应追求一种精髓的把握,而非直接的功利获得。布迪厄曾提及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一种是犬儒式用法,指通过这种用法力图在对社会机制的分析中寻找一些工具,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世界,或指导在学术场域中的策略,也就是说将其当作一种特别强有力的符号战争的武器;另一种是临床用法,指通过这种用法将科学分析的结果当作一种祛除了自我吹嘘的自我理解的工具,或者说提供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与他人的手段[6](p.276)。也许,从布迪厄始终竭尽全力阻止犬儒式解读,鼓励临床式解读中,我们或多或少可以得到对场域解读的有用启示。
1.“场”的历史掠影
对“场域”的解读,是一个不断理解、辨析、深化的过程,它的起步应从其语义学的解释开始。在《辞海》中,“场”的主要解释为:(1)平坦的空地;(2)特指市集;(3)特指考场;(4)一件事情的经过;(5)物理场;(6)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有时也指空间区域本身。“域”的主要解释为:(1)邦国、封邑;(2)区域、地区;(3)疆界、境地;(4)分划居民区域。必须提及,《辞海》、《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与《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均未出现过“场域”二字,因而也就无从谈及对“场域”一词的整体语义解释。英文中似乎"field"一词更与“场域”接近,与其相关的意涵有:(1)(作某用途的)场地、场所;(2)场(存在某种力的效应的范围或空间);(3)某物的有效作用范围。从语义学的解释中,我们获取的只是对“场”的最为基本的信息。
应该看到,“场”的概念在各门学科中出现,既是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轨迹显现,也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使然。
“场”首先在物质世界中“抛头露面”。物理学上“场”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在电磁场理论的研究中确立的。法拉第在1844年就提出力线和力场的概念,并假定带电或磁的物体周围弥漫着一种电磁以太即电磁场。他认为,电磁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实体,它没有不可入性,且能传递电磁相互作用,实粒子则是力场中的奇点。其后,经麦克斯韦、赫兹,经典电磁场论得到确立,且“正和他所坐的椅子一样地实在”。从法拉第开始,科学家们就在为场论的确立和场概念的确立而奋斗。统一场论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爱因斯坦在本世纪20年代以相对论为基础试图建立的统一场论;第二个里程碑是海森堡在50年代以量子场论为基础试图建立的量子统一场论;第三个里程碑是在对称理论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规范的统一场论。统一场论的建立是现代物理学上一次伟大的思维革命,它试图告诉我们:其一,宇宙是同源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不仅表现为物质统一性,还表现为宇宙发生上的同源统一性,即自然界尽管演化为现在的千姿百态、复杂多样的世界,但万物同“宗”,“理”一分殊,都归结为“场”。其二,自然界万物的构成,都是以四种基本作用场(强作用场、弱作用场、电磁作用场、引力作用场)即物质基本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宇宙原生场只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着。其三,人体生物场、社会场都是从自然场的复杂作用的演化中派生出来的,是自然场的产物。自然派生场作为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场层次,除了具有高一层次场所具有的一般规律和性质,还具有本身属性决定的一些特有的场规律[9](pp.25-42)。
虽然几乎在爱因斯坦创立广义相对论场论的同时,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驱们也在完形理论中出现了场的概念,但从物质世界进入人的世界,从物质世界的“电磁场”进入人的世界的“心理场”,毕竟表明“场”的理论已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代表之一克勒认为,整体的量值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机械力以加法关系组成,不具有格式塔(完形)的性质。整体的完形是通过场的作用发生的。格式塔心理学把“感知场”或者说更一般性地把“认知场”作为知觉整体,科夫卡将其又作了具体划分,其中包括表征外部环境的“物理场”、表达意识行为的“行为场”、描述生理过程的“生理场”、表达行为内环境的“环境场”以及心理行为和生理结合的“心物场”,并把除物理场之外的各种场总归为“心理场”。格式塔先驱们的工作,奠定了心理场论的基础。莱温作为克勒的学生,发展先师们的理论而创立了心理场论。他在《社会科学中的场论》一书中说:“心理学场论的基本特质之一是这样一种要求,即影响个体的场不应以‘实体物理学’的术语来描述,而应用个体在某时间所处的场这样一种方法来描述。……在心理学中,‘客观地’描述一种情境实际上意味着去描述作为那些事实并且仅仅是那些事实的整体的情境,这些事实构成了那个体的场。”莱温还致力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认为改变人的生活空间的力有两种:一种是产生于人自身需要的“自身力”,另一种是来自周围环境的“诱导力”;而对社会变化影响最显著的,是那些既有个体自身的力又有来自外部影响个体的各种“能量场”的诱力[9](pp.84-85)
与“场”在物理场、心理场中的意义有所不同的是,“场”在哲学中表达了一种更为整体、更为抽象、也更为强调关系的意义。在当代,首先从本质上把场所作为哲学问题提出的是西田几多郎。西田的场所论实现了迄今作为西方哲学共同前提的主词逻辑主义立场向宾词逻辑主义立场的转变。然而,西田几乎没有对场所进行具体的、现象学考察,他彻底的逻辑主义化立场,使场所成为无,至少在中国尚未获得人们的全面理解和接受。从场有与绝对实体之对立的角度出发,唐力权的场有哲学是一种主张存有即场有,万物皆依场而有的哲学。这里的“场”是一种哲学观念而非数学或物理学观念,“场有”乃依场而有或有在场中之意。按照场有哲学的观点,一切都存在于事物之相关相依、相克相成的相对性的势用里,一切都作为场有者存在于由事物的相对势用所构成的关系网中。而以场有的观点来看人,则人就决非某种孤立的实体,他只能是置身于将其包围、限制或他们所关心、牵挂的“场有”中的“场有者”[10](pp.329-331)。
“场”在社会学中的使用,似乎更多地与所要分析的社会现象相联系。迪尔凯姆是较早使用“场”概念的大师。他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在一定的“场”中才能存在和表现出来,社会现象的“场”就是社会环境。因此,必须把社会现象放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上去作综合的考察,去发掘存在和影响它们的各种社会联系[11](p.5)。至于布迪厄,则对“场(域)”本身作出了较为系统的阐释,为人们对它的具体应用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综上所述,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心理学,无论是哲学还是社会学,“场”在其各自不同的学科领域均有或多或少的使用。虽然它们的意涵因各学科特点而异,但一些共同的东西仍然可以捕捉。
其一,在整体中统观对象。“整体”作为事物间相互作用而发生联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场性的表征。如果不参照整个的场力,就无法确定个别物质分子运动的结果。“因此,要考察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社会现象的产生,不能在那些组成集体的各个分子中去寻找,而必须对这个已经组成的集合体进行研究[9](pp.84-85)。”
其二,在关系中厘清对象。一切事物都处于某种相互关系之中,只有在关系中才能真正把握研究对象的命脉。
其三,在自身逻辑与变动不居中把握对象。那些既有个体自身的力又有来自外部影响个体的各种“能量场”的诱力告诉我们,各种力量的组合变化、竞争抗衡,足以对场及其场中的人产生各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和作用,而这些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作用于各种力量。
2.“场”与“场域”
如前所述,在《辞海》、《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与《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里均未出现过“场域”二字,这一方面由于新生词的缘故,另一方面可能更缘于专业词汇之故。其实,从总体上说,“场”与“场域”二者的共通使用并非不可能,在一些相关研究或译著中,就屡见其通用的现象(注:如《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中译为“场的逻辑”,而《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则译为“场域的逻辑”。)。其大致通用似可遵循“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可以认为,“空间的”、“整体的”、“关系的”更体现出二者的“大同”之处,而没有确定的“界”和有一个相对范围的疆界似是二者的“小异”之处。
本研究之所以最终选用“场域”这一概念,其一,能更有效地突显关系。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有相对疆界的范围中,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与剖析研究对象,立体透辟地分析场域与人、人与场域、场域与场域、场域中的人与人等纵横交错的关系。因此,场域的“界”决不仅是一种物理的“界”,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的“界”,是与资本的效力界限相伴相随的“界”。形象地说,空地上围着的篱笆是疆界;妈妈吩咐儿童不能离家外出,妈妈的吩咐也成了疆界;加入一个社会团体须有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也是一种疆界[12](p.361)“疆界”为关系的突显给出一个既可能把捉又有充分空间的平台。其二,能更有效地彰显差异。场域中的参与者,即使不有意寻求差异,也存在一种导致差异的生产,他们维护自己的卓而不群,一方面是想竭尽所能建立自己对场域的某个特定局部的垄断,另一方面恰恰是为了防止被剔除在进“场”伊始。差异只有在场域与场域的分析、比较中方能显现,若使用“场”的概念,恐与物理场中所表达的万物同“宗”、“理”一分殊,都归结为“场”的“场”难以区别。
3.布迪厄“场域”的尝试拿捏
应该说,对“场域”问题本身作出较为系统阐释的当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他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对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尝试拿捏,直接关系到这一理论在学校场域中的具体运用。
在谈及“场域”的概念时,布迪厄主张作为一种开放式概念使用,并认为只有将其置于关系系统中,才能获得概念的真正意涵。由此,依据“临床式解读”原则,对“场域”的把握可以大致涵盖这样几个方面(注:以下所归纳的布迪厄关于场域问题的几个主要观点,因其在拙文《指向“改造性实践”的教育反思》(《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中有详细阐述,故此处只列提纲,有兴趣者可参阅拙文。):(1)场域:关系的网络。(2)场域:共时与历时的交融。(3)场域:形塑的中介。(4)差异:场域的动力机制。(5)场域、资本、惯习的相互关联。
在上述对场域的解读中,必须强调的是:第一,由场域诸多特征形成的对场域的总体把握,始终建立在关系系统之中。无论是作为共时与历时交融的场域,还是作为中介形塑的场域,无论是场域差异所形成的动力机制,还是场域、资本、惯习三者的相互关联,都只有置于场域的关系系统中才能准确地加以把捉。第二,布迪厄对场域的系统阐释决非一种为场域而场域的人为,而是最终指向反思社会学和实践理论的,或者说就其本质而言是根植于科学实践和面向科学实践的。
三、学校场域——触发“问题”意识
可以尝试这样界定学校场域,即学校场域是学校中各种复杂矛盾的多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多元关系的网络,是有形与无形的整体集合与各种力量的不断重组。这里,“场域”更多的是意义场域,或者说是物理场域与意义场域的互相交融;要努力呈现的是学校场域的境脉,即人与场域如何共同打造入“场”规则,搭建在“场”优势,中介塑“场”策略,控制清“场”技术,引发争“场”冲突,甘心退“场”主动,潜沉临“场”契合,共谋建“场”联合的复杂过程;要着力突显的是学校场域中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及其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这里,必须说明学校场域与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说对学校弱势群体的生存关注只能置于学校场域的境脉之中,但学校场域却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关注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研究天地。学校场域所呈现的关系网络、意义空间、中介形塑以及资本的争夺、惯习的潜沉等诸多特征,将更淋漓尽致地呈现“此时此地”处境不利的弱势群体们被遗忘、被贬损、被误读和被过度解释的经过与历程,并可能使置身其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个体的、群体的)鲜活地跃动在读者面前,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干瘪的符号的人。
在学校场域中,可能留有更多研究与再研究的开放空间。在学校场域这个物理空间与意义空间的组合与生成中,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位置分布与联系;他们所拥有的各自的优势、运用的策略,这些优势与策略的决定权以及如何利用这些优势与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他们如何参与资源分配和资本竞争;如何履行游戏规则,达成某种共谋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为研究留下一个更大的出口。与此同时,场域与人融为一体的“身份特征”亦告示我们,不论是客观位置的空间,还是主观立场的空间,都应该被放在一起分析,应视为斯宾诺莎所说的“同一句子的两种译法”[6](p.143)。
在学校场域中,可能呈现更多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组合。与场域一样,学校场域同样是关系的系统,存在各种对应或不对应关系,如控制与抗争、冲突与再构、规训与退让等;存在各种复杂矛盾的关系,如虽有冲突与纠葛的师生可能一起联合建构了“我们”的活动和“我们”的场域等;存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各种转换、流变等关系。这些诸多关系组合的呈现,恰恰为场域边界的把捉提供了可能。因为从学校场域的关系出发,就可以在勾划研究对象(这里具体指弱势群体)所在的空间中,了解实际包含了哪些关系,了解形塑这个空间结构的各种主要力量线及其相互制约力量,这样我们就会在所研究的弱势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求其原因与机制,而不致误入歧途。如此,似乎可以说,场域的界限位于场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6](p.138),而关系的停止作用则意味着场域效果的停止作用。
在学校场域中,可能突显更多变化与再变化的差异群体。存在于一个特定的场内,就意味着存在于差异性之中,就意味着区别于他物,就意味着必须维护其差异性[13](pp.145-146)。学校场域中的确存在一种差异性的生产,但这种差异性的生产并不应等同于一种差异产物的追求。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是一种差异存在,但并不应是人为差异的生产,更不应是固化差异的生产。它们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这些差异是如何产生的?与哪些因素有关?又在什么情境下发生转变?……都可能成为进一步考察与解释教育问题的复杂变化的动态因子。
在学校场域中,可能触发更多反思与再反思的“问题”。正是在学校场域这个开放空间中,存在着复杂多元的关系组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同位置与差异,才促使置身其中的人不断进行着反思:处于不同位置的人如何进行关系的组合?拥有不同资本的人如何进行相应的兑换?场域与惯习的关系如何在学校日常生活中表现的?作为“教育者”,如何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作为“研究者”,如何实现“对象化的对象化”?这些诸多反思同样都应是根植于教育实践和面向教育实践的,从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也将表现出更为自觉的趋势。
标签:群体行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