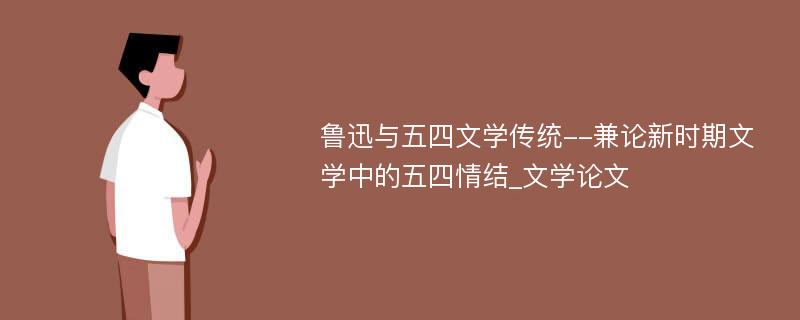
鲁迅与“五四”文学传统——兼论新时期文学中的“五四”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时期论文,情结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鲁迅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尽管海外有的学者如夏济安、林毓生(注:两人的文章均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等否定鲁迅的“代表性”意义,而国内的学者却有一致的定论,认为鲁迅是这场运动的主将和正宗,代表着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但是,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及本身所呈现的复杂性,使怎样认识和评价鲁迅与这场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成为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也是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譬如,究竟什么是五四文学传统,就可以作出诸如“科学与民主”、“反帝爱国”、“冲击和改造自己民族的古老文化”、“选择和引进西方的近代文化,建设多元的、开放的新文学”等多种结论。这些确实都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和发扬的优秀传统,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以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所构成的价值取向和创作风范,这是实现上述所有一切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五彩缤纷的五四文学的本质所在。
一
人文或人文主义(humanism),最初是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的,也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旗帜;启蒙运动为enlightenment, 它的词根是启发、照亮、摆脱愚昧与偏见的意思。无论从理论意义抑或实践意义上说,人文精神与启蒙主义都有着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人文精神离开广泛的启蒙运动,就无法深入到广大民众;而启蒙运动若不以人文精神去照亮蒙昧者,用知识、科学、理性使之摆脱愚昧和偏见,就会变得虚泛和肤浅。正是在二者的契合关系上,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人文主义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概而言之,指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态度,认为人、人的价值具有十分神圣的意义,它尽管也强调世俗生活和积极行乐,但更关注人与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尊严和自由意志,关注民主与个人价值。从哲学层面讲,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它最初是彼特拉克、薄伽丘、蒙田、莎士比亚等一代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类的生存价值观和生命意义的深沉昭示。
历史事实表明,无论在五四前还是五四时期,在鲁迅身上一直流淌和激荡着的,最浓郁的就是人文精神的血液。早在1907年他就断定,欧美之强的原因“根柢在人”,认为中国“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后而凡事举;故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注:《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鲁迅在对物质与精神、众数与个人等的反复探寻中,最终看清了健全、积极、独立的精神个体对民族振兴的根本性意义。这就已经在预示和传播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题——个性解放思想。因而当五四新文学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鲁迅在这方面的劳作是十分自觉和不遗余力的,《狂人日记》对几千年封建社会制度“吃人”本质的揭示和“救救孩子”的呐喊,《阿Q正传》对国民性劣点的高度概括, 以及《坟》、《热风》中强烈反封建的声音,都表现出对人的价值、尊严、“人性的解放”的热切追求,并积极探寻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在人格构成上,鲁迅对那种以“不撄”、中和、顺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性十分反感,强调:“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注:《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企盼在中国出现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在创作(包括小说和杂文)中不仅塑造了狂人、疯子一类的反封建斗士,而且无不渗透着作家(即审美创造主体)自身的一种独立不倚、奋然前行的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韧性、执著、反省……的现代人格力量。这是相当值得称颂的建树,因为在贬抑个性的传统已经像上帝的影子一样主宰和制约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情况下,能够真正高扬人的自主意识和独立精神,努力冲破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禁锢所造成的奴性意识,无疑是整个民族建设现代文化、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鲁迅以“人性的解放”和个性意识为核心的人文精神的自觉,固然受到西方近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中施蒂纳、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在对启蒙主义以来的物质发展、政治体制和理性原则的抨击中所建立起来的“个体人”的观念,对鲁迅影响尤大;但根本原因还是由民族解放的社会历史要求所决定的,从抗拒外侮、反躬自责到搅醒“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鲁迅无时不把“国民性”问题看作是影响和制约民族自强自立的焦点,并执着地要为人的觉醒与解放作不懈的斗争。这就使他的人文精神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为人生”的基础上,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和崇高的历史价值。他因此与西方某些人文知识分子的“唯我主义”和反理性趋势以及后来某些中国作家陷入与外界隔绝的孤立个体、以咀嚼小小悲欢为满足的狭隘性,划开了明显的界限。胡适把这种“担干系,负责任”的人文精神看作是一种“社会化的新宗教与新道德”(注:《易卜生主义》,载1918年6月《新青年》第4卷第6号。)。 它不仅仅出于校正“唯我主义”所产生的弊端的善良愿望,更是反映了被压迫民族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在要求。他既不能容忍封建主义对人性的长期压抑,也为被压迫民族的屈辱感与使命感搅动得骚动不宁。这是真正的人文精神,虽说并非成仁取义才算得上有人文精神,但人文精神的确往往要牺牲一己利益才能成全。在这意义上,人文精神的要求具有康德所讲的“绝对命令”的性质,它不仅要求高尚的道德操守,也要有一种殉道精神。鲁迅就正是如此。
正是从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出发,鲁迅的“人文精神”必然走向“启蒙主义”的道路,这是顺理成章的。鲁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几乎是根深蒂固的,直到30年代他还说:“说到为什么作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启蒙就是以一种新的、进步的文化价值体系否定乃至取代另一种垂死的、保守的文化价值体系。具体到鲁迅和五四时期,就是以人类现代的“科学”与“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取代愚昧保守的封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以深刻的理性精神去开启蒙昧的中国心智,以现代健全的人格向民族“硬化”精神展开强有力的挑战。这就使鲁迅的文学创作与传统文学相比,产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第一,由于启蒙主义文学观注重文学的反映性、社会性,尤其是注重文学作用于人的情感和灵魂的特殊功能,因而它首先强调作为启蒙者的主体——作家自身精神、人格力量的建构。鲁迅说他一向“严于解剖自己”,惟恐将自己灵魂深处的“古老的鬼魂”传染给读者;第二,重视作为启蒙对象的普通民众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与对文学作品的接受。鲁迅率先在创作中把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且多为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推到小说表现的中心位置,即包含着对审美表现对象的“人”的发现的意义。而白话文的提倡,也同样包含着对审美接受主体在文学作品价值实现程度上的关注,鲁迅尽管不是五四白话文的首倡者,但却是最早、最有力的实践者;第三,不拘一格选择文体。鲁迅在写小说的同时,更以大量的精力和心血进行杂文创作,把写这种当下能震撼人心的具有“时效性”的“小品”看得比去创造可以流芳百世的“鸿篇巨制”重要得多,也正是出于“启蒙主义”的需求。
二
不消说,人文精神与启蒙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文艺思潮,这就必然要遇到传统文化的强有力的挑战。中国古文化系统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长期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统治中,获得了一种较为完备的隔绝机制,长期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体系,这虽然使它得以使华夏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采”(鲁迅语),但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惰性,这就严重禁锢和扼杀了全民族的精神活力,在思想上形成了愚顽、保守、盲从、排他的根性。鲁迅说:“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已经“衰朽到毫无精力了”。(注:《忽然想到(5至6)》,《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在“重新估价一切价值”(胡适语)这一理性的批判旗帜下,五四先驱者们对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礼教、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进行了根本的质疑和全面的清算,这不仅是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且也是它自身的重要一环,因为非人道的社会、人性普遍受压抑和精神饱受奴役之苦又不肯觉醒的状态不仅直接构成对人文精神的敌对和排斥,而且也为封建传统的继续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和温床。这样的传统倘不加改造,则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终究要撞碎在封建势力的厚壁上。二者就是这样彼此消长、水火不容。在这方面,鲁迅的认识和追求仍然是最自觉的。被看作是五四文学第一个创作实绩的《狂人日记》,即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吗?”的质问,这是最深沉激越的时代强音。
就同时期的全部文学作品而言,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仍然足以代表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的思想倾向。在《灯下漫笔》里,鲁迅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称作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亦即一“治”一“乱”的交替,在这样的循环交替中,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权利。鲁迅的结论根本上是出于对广大普通人的地位、价值的考虑的。这可以看作是他“反传统”思想的全部根据、本质所在:他反的是“君主专制”、“将人不当人”的传统,并非其他。他的一系列作品,都是这一总体认识的具体化。《狂人日记》猛烈攻击的是“仁义道德”的吃人的旧礼教,这种礼教犹如《春末闲谈》中所说的“细腰蜂”,实则是封建君主的一种统治术。《孔乙己》深刻揭示了科举制的弊端,是它把读书人引上了邪路。《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原来都曾有着充满光辉的人格,然而经过后天的重重打击,终于都变成了奴隶中的一员,他们一再受压迫、受剥削的过程,就是奴隶根性逐渐形成的过程,在他们的生命力和生命沉沦的悲剧的背后所潮涌发酵的,是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封建统治的悲愤的批判的激情。鲁迅写于五四时期的大量杂文,从对“国粹主义”的无情嘲弄,到对“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议论,从对妇女所受“三从四德”束缚的批判,到对“生命的路”的指示,也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由这里出发,鲁迅的批判锋芒实际上已经发展为对整个传统文化体系的全面否定(他劝青年人要少读或不读中国书),并有着不同层面的深广度:既从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之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否定中国固有的“文明”,也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揭示现实人生的病苦,更有像《阿Q 正传》那样的集对国民性的批判于一身的作品。同时,由于鲁迅在与传统的全面对抗中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等与传统文化之间均有割不断的血肉联系,因而其批判从来不隔岸观火,而是始终带着一种“原罪”式的自我意识,把自己也摆进去,或者干脆“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自己”,《狂人日记》和《写在〈坟〉的后面》就对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自我作了无情的否定。这就使鲁迅的“反传统”行为具有了社会性和“自我救赎”的双重意义,在真诚中显示出理性和激情的力量。当然,我们所能举出的仅仅是鲁迅的作品,大部分五四文学的创作水准远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和广度,然而不管是吴虞的“只手打倒孔家店”,还是胡适的把文言文定为死文学,抑或陈独秀的期盼“国粹之消亡”,五四先驱者的追求却是一致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强有力的合唱,震动了一向迷恋传统的中国。
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几近绝对化和偏激的批判态度,是由当时的处境和批判对象本身所决定的。五四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是不可能依仗政治之权势获得成功的,只能靠一群势单力薄的文化人作艰苦卓绝的奋斗,期间又面对着复古势力的激烈反对,形势所迫,必欲“费厄泼赖”也不可得;同时,五四人深感传统的过分强大,无力的中庸、全面之论根本不能撼动封建“铁屋子”的一片瓦砾、一根毫毛,不得已而必须实行“矫枉过正”,鲁迅说这是“物反于极”,也可以说是一种“深刻的片面”。这其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彻底的反省精神,一种知耻而后勇的气度。正是这种姿态,才在引进异质文明中冲击了中国文化的防线,克服了传统的巨大惰性力而实现着人的觉醒和文化改革,本质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的进步就是在这偏激里孕育萌发出来的。
三
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五四新文学运动尽管一度很有声势,但却是在较为短暂、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在人文精神和启蒙主义的追求远没有深化、也没有被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历史就匆忙地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最具现代性和历史意义的新传统,未能为后来几十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所自觉发扬,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度曲解、中断甚至窒息。个中原因,决不是“救亡压倒启蒙”的结论所能完全回答的,其中还有更深层、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自身的原因。
五四新文学是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借助外力的推动而产生的,缺乏由元明清文学的变异因素自然发育成熟的过程,因而难以强有力而又持久地抗拒中国传统文化束缚和禁锢人们的心理的强大压力,再加上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就势必造成五四以后整个新文学发展道路的曲折和坎坷。从五四文学革命演化为革命文学,再到30年代“左联”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从历史的表层现象看,这无疑是大幅度的跃进,然而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和“救亡图存”的现实的冲击,五四文学中个性解放(人性的解放)的传统,就逐渐受到质疑和挑战。这里有一个看似“合理”的逻辑程序:对于救亡图存的中国来说,集体的梦想大于个人的梦想;对于历史战车上的“军队”来说,文艺应当服务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而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是最讲究整齐划一的。这样,五四文学传统便必然桔生于淮北,水土不服了。郭沫若这样表述他(们)的“转变”过程以及在“转变”后获得的新观念:五四时期创造社“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要求,他们藐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无形之间便是他们的两个标语。……然而天大的巨浪冲荡了来,在五卅之潮前后,他们中的一个郭沫若把方向转了,同样的社会条件作用于他们,于是创造社的行动得到划了一个时期,便是《洪水》时期”;“我们要要求从经济的压迫之下解放,我们要要求人类的生存权,我们要要求分配的均等,所以我们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注:《革命与文学》,载1926年5月16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这就是从“个体自由”的追求向社会平等的理想,从个体意识向阶级的、社会的群体意识的根本转变。这是颇有代表性的。这样,五四传统中“救出你自己”的个体自由原则和个性文学的观念,便像扔掉一件废旧物件一样被轻易地抛弃了。与之相应的“启蒙主义”文学,也随之而悄然冰释,“化大众”变成了“大众化”。强调阶级意识和集体主义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如果离开了人的自由意识和独立精神这个前提,使“人之自我”“泯于大群”(鲁迅语),这样的群体是不可能具有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的,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因之,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 72年版,第273页。),同时, “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上), 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2页。)。只有个性解放和社会群体解放完满结合,只有在社会群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到充分实现,整个社会才在真正意义上获得自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尽管鲁迅前期偏重倡导的是个性解放和独立意识,强调对“庸众”宣战,但决不是对集体主义的简单化否定,他否定的是对“独特者”极尽扼杀之能事的“庸众”社会:“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注:《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他之强调“人各有己”,最终还是立足于实现“群之大觉”。他从五四开始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进行创作并将眼光注视着如何实现社会群体的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已经包含着集体主义的成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时代的文人能像一代五四先驱者那样在团体和个人之间鲜明地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也没有哪个时代的文人能像他们那样在那样分明的区别中保持着如此的“同志感”和同一性。后期的鲁迅更是自觉地沿着这样的思想轨迹不断前进的。只可惜在庸俗社会学和封建专制主义面前,这座完整的思想“金字塔”越来越严重地遭到歪曲、割裂,被抽掉了“个性解放”这个坚实的底部,剩下的只有阶级斗争和集体主义。其消极的后果必然要在对待五四文学传统上充分表现出来。
从三四十年代直至十年“文革”,五四文学的宝贵传统,大致说来确实是趋于逐渐消失的状态,这就从总体上决定了当时的革命文学创作以及全国解放以后的文学面貌,虽然不否认也产生过个别优秀的作品,但大多显示出色彩的单调和个性的贫瘠,甚至被虚假的阶级斗争的公式化和概念化所困扰,这就根本无法走向丰富和深刻,无法产生能够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
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毕竟是影响深远的,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吃过了历史的苦果之后,走到新时期的人们终于自觉不自觉地重新认识了五四文学传统的不朽价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生的文学,无论在话语方式还是精神印痕上,几乎都是从回归“启蒙主义”传统开始的。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中,好学生谢慧敏和坏孩子宋宝琦虽然在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但在“蒙昧”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就是当时开始的文化启蒙活动的反映。更有典范意味的是,张老师作为优秀教师的形象,始终处于作品的中心位置,为“救救孩子”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这恰好表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活动中的特殊重要性。五四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知识分子都在启蒙中扮演过先行者的角色,他们既有殉道者的悲壮与执着,也有教师的循循诱导,更有思想家的深沉、睿智与特立独行。因之,这篇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也是新启蒙文学开始的标志,是它接通了与五四传统的血脉联系。紧接着,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韩少功、卢新华等大批作家纷纷涌现,他们几乎都是在借着鲁迅的话语,述说着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的期待。这是一些久违的声音了:以《灵与肉》为代表,张贤亮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透视,在几近宗教式的谶语里,明显留有魏连殳、子君等鲁迅笔下知识者的精神痛苦。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对50年代中期以来20多年畸形生活的梳理,更从社会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思索那一代人的悲剧,呼唤从政治生活中还原人性的自由。同时产生的《伤痕》、《布礼》、《蝴蝶》、《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人到中年》、《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一大批产生轰动效应的佳作,无不在血与泪凝铸的艺术形象中蕴藉着人文精神的力量。就主导倾向而言,虽然作品大多还只是停留在对“左”倾思想“伤痕”的清算上,不大注意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揭示生活的原色,但他们要求发现人、把人当人、从神崇拜和个人迷信的蒙昧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强烈愿望,却无疑反映了时代的心声,这是这些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的根本所在。
四
五四传统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延续,最明显的还是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化热”而兴起的“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主要来自于拉美作家关于印第安文化阐扬的启示,但当人们开始从长长的历史传统中去寻找中国人生存的深层文化问题时,却又自觉不自觉地把鲁迅当作灵魂的先导。韩少功《爸爸爸》中以大写意的方式塑造的丙崽,许多人一眼就看出了他与阿Q的历史联系,丙崽混世处世的的两句格言“爸爸, 爸爸”和“×妈妈,×妈妈”,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像阿Q 一样的具有奴性和专制性的精神实质。丙崽赶不尽也杀不绝,即使拿他的脑袋祭了神,其幽灵仍然会在山林间徘徊。丙崽生活的鸡头寨,也像一块活化石一样凝聚着民族文化中“惰性”的沉积:时间似乎在这山林的深处滞止了,从古到今,尽管无尽的天灾人祸曾逼迫着人们不断地迁徙,然而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观念情感,民风俚俗,包括极其低下的耕作方式、鬼神崇拜、禁忌法规以及寨子之间无休无止的打冤家等,好像毫无变化。丙崽和鸡头寨是“纯种”的民族文化遗迹,它超越了时间的风化,在“文化隔离”中悄无声息地存留了下来,它早已失掉了生机和活力,只能是可供鉴赏的“活古董”。王安忆《小鲍庄》中的小鲍庄人,仍然受着封建意识的严重制约,主人公捞渣是个“仁义”的化身,他长相仁义,举止仁义,为仁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他的仁义之心与仁义之举,竟被新时代的人们视为“共产主义思想”而广泛宣扬,他并在身后受到了迁坟立碑的礼遇。封建意识夹杂着愚昧无知,说不清是一种怎样的昏昏噩噩。写于“寻根文学”呼声最高时期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把审美批判精神贯穿到了那酱缸般的封建文化的最深层:对生命力的压抑和生命的扼杀。主人公倪吾诚虽然是西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但由于已经开始瓦解的封建文化仍然紧紧地束缚和吞噬着他——犹如还在少年时母亲对他所进行的吸鸦片和手淫的教唆,使他的生命力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都受到扼杀,变得不能选择、不能应变、不能发展、缺乏自信心和自决能力。在现代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他自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只能成为孔乙己式的悲剧人物。
当然,“寻根”文学的美学意蕴决非这样单一,有的作品则不乏爱国主义的礼赞,不乏儒、道文化强大生命力的阐扬,不乏底层民风的讴歌,不乏对敦厚、善良、吃苦、耐劳等民族文化精神的诗一般的肯定与传达;也有的注重以现代人的感受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诸如考察原始大自然,考释民族文化资料等。然而对当代生活、特别是民族心理中所存在的旧文化因素的挖掘与批判,无疑是其创作的主体。“寻根文学”的最初动因,原本是想以“寻根”的文本来弘扬民族的地域文化,弥合由五四新文学运动形成的“文化断裂带”(注:郑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载《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然而,十分有趣的是, 这次由作家发动的理论运动,其主旨恰恰在其文本的悖反中悄然冰释。韩少功在《归去来》中面对传统文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这就再恰当不过地揭示了“寻根”作家的难堪而又矛盾的心境,无论是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与李杭育的“最后一个”系列流露出的失落感,还是阿城《孩子王》关于渴望文明的叙述和作为“寻根小说”殿军的莫言的“种的退化”的悲哀,均是其内在矛盾的形象化表现。可见,不少作家对鲁迅的重复是不十分情愿和自觉的,但又是无可奈何无法绕过的。这又一次反映出五四传统的可贵和历史发展的必然。
但是,“伤痕文学”与“寻根文学”(本质上都是以人文精神为支点的启蒙活动)的发展都是不很彻底的,尤其是后者,它像阵雨一样刚刚渗润进大地的表层之后,就迅速烟消云散了。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生活中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外,商品经济对它发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商品经济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也确实给文化、时尚等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过分膨胀的物质欲已经导致了不同程度的人性的异化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反映在文学领域,俗化、商品化和人文精神的淡化,便成为一种潮流,至少在表面上,不少作家已失去了对生存价值的关注,表现出一种“躲避崇高”、放弃责任、存在迷失的精神状态。这就导致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文学创作的不景气。
面对这一状况,鲁迅和人文精神的话题,便又不断地被人们提及。1993年6月,由《上海文学》开始, 在全国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历时二三年之久的讨论尽管议锋驳杂、争异颇多,但意欲重振鲁迅精神、在商业主义浸迷中倡导崇高和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想,却是一致的。孙郁说:鲁迅精神“这份遗产的最大价值在于,他对人类僵硬的文化惰性核心,是一个异端,它的意义就是消解惰性的核心,把人从物化和非人道的文化程序中拯救出来”。(注:《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作家有关这方面的言论还很多, 如张承志说,当下文坛最需要的是树起鲁迅精神的旗帜,“使耻者有所忌惮”(《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童庆炳说,“鲁迅二三十年代所说的话并没有过时”,通过文艺来“改良这人生”“仍然是鲁迅对当代文艺家的恳切呼唤”(《文艺研究》1994年第1期)。 )这就把鲁迅精神的当代性的话题明确化和深入化了。如果说,前两次的“文学启蒙”活动是在反“左”和声讨“文革”罪行结成的“契约情势”基础上的“集体无意识”行为,那么,这一次的大讨论则十分理性化并逐渐化解为文人个体对当前文学位置及其作用的独立思考和重新审定,进而清醒地意识到了20世纪人文启蒙所应关注生存危机和生存价值的最基本的命题。从张炜的《宗族》、格非的《欲望的旗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张欣的《岁月无敌》、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陈建功的《放生》等优秀小说中,可以看出它所导致的创作精神面貌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文学由流俗和消解、拒绝批判而重振理性批判的伟力,这当然不是对表层生活现象的指手画脚,而是以人之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为坐标,对现实与现世的种种生活状态,展开纵横捭阖的评说和“历史的”、“美学的”批判;第二,在这种评判中,他们已不再过于苛求人的生存环境、现实变迁以及政治话语所辐射的权威意识形态,而是侧重关注支撑人的存在的精神支点,其中既有对颓废的、无望的、带着世纪末悲观情调的绝望的呐喊与颤栗,更拥有浓郁的人文关怀,闪耀着人类引以自豪的生命向力;第三,追求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表达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忧虑。统而观之,虽然很难说明这些作品与五四文学之间的具体联系(其中新时期关于环境意识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则是五四文学所不具备的),但作家在内在精神上的对启蒙主义的执着追求和张扬文学的人文本质,却无疑受到五四传统的“照彻”。正如张炜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所说:“五四是有光芒的,光芒照彻了愚昧。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需要这种光芒。如果今天有人说在这光芒下还应作点什么,寻找点什么,这是正常的。如果要从根本上遮去这光芒,就未免有点意气用事和昏聩”(注: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8期,第116页。)。这就清楚地揭示了他们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既受五四润泽,又有新的、服务于现阶段时代要求的独特贡献。中国新文学的未来前途,也即在这里。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人文精神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文化偏至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启蒙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