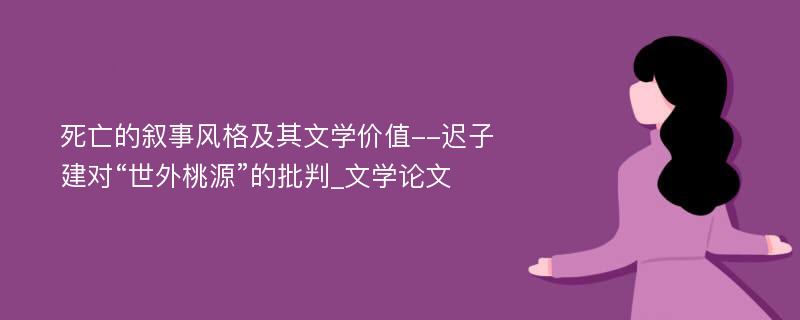
死亡的叙事方式及其文学价值——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上论文,夜晚论文,批评论文,价值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8)04-0067-03
死亡对于人生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束方式。而死亡作为文学的一种叙事资源并不一定被充分利用,因为死亡无论如何意味着不幸、凄惨、悲哀、绝望,不易承载人类的审美理想,寄托未来的希望。尽管死亡是人类不能不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人类社会剧烈动荡的岁月,死亡既是巨大的威胁,又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但文学史上关于死亡的叙事并不多见。和平年代文学对于死亡的表达更为稀少,可以理解,人类历来不愿意通过更多地陈述死亡湮没希望。然而,迟子建的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钟山》2005年第3期,该作品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却选择了死亡叙事,让我们领略了死亡叙事的文学价值。
一、迟子建的死亡叙事方式
毫无疑问,迟子建对死亡有着切身的感受。丈夫遭遇车祸死亡给迟子建人生带来巨大不幸,这种死亡在迟子建情感世界产生的巨大激流,让她不仅要直面死亡,而且用极大的精神能量抒写死亡。
对于死亡的叙事可以有多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莫过于对死亡状态和血腥场景近乎自然主义的描摹和陈述,但这无疑是最蹩脚的一种方式,因而只能让人产生恐惧而不能产生美感。迟子建在抒写死亡时仅仅把死亡作为一种现象和事实,重在表达死亡对人们生活和精神上形成的冲击力。
作品自然是从“我”的“哀伤”中开始的。魔术师被“跛足驴”撞死在芳洲苑路口,相依相偎、情感深笃的夫妻自此天上人间,生活就像魔术师表演的魔术一样旋即改变,现实——空白——虚无成为“我”不可避免的精神历程。而造成“我”这一重大变故的居然是“跛足驴”“一泡尿惹的祸”,可见人世间包括死亡这样的重大事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存在着某种玄机。
死亡作为人的重要经历在不同的时期感受是不一样的,所谓人生三大不幸“少年丧母,中年丧夫(妻),老年丧子”即言死亡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人们造成的特殊伤害。丧夫之痛使“我”感觉自己无意间丢失了“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但是,死亡已经赐予“我”的生活,生活不能就此死亡,“我”需要从死亡事件中挣脱出来。作者为“我”设计的路径是去三湖山做民俗学的调查,“收集民歌和鬼故事”。作者铺设在文本中的内涵十分清楚,死亡是人世百态中的一态,民间大众对死亡的感受和阐释是一种真正具有历史感和生命原义的死亡价值观,无疑能够给“我”真正的启迪和超越。
作者让“我”在民俗学的调查中对死亡以及死亡对生者的影响有了更多的观察和感受。三湖山之行由于遭遇暴雨,“我”不得不在乌塘下车。乌塘是煤炭的开采区,同时也是死亡事件的高发区。不期而遇的经历中死亡即堆积在“我”的面前,足以说明死亡对于人类来说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死亡之外隐藏的故事和问题。作品中涉及的死亡事件有“我”的丈夫、蒋百、陈绍纯、小食摊摊主老婆、云领母亲,以及煤矿区隐藏的死亡和鬼故事表达的死亡。
最令人关注的当然是蒋百的死亡。本来是简单的矿难和简单的死亡,但蒋百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众人测猜不定,蒋百嫂放荡异常,连蒋百嫂的狗都在痴痴地寻找,蒋百的死亡成为一个难解的谜。正是蒋百的生死悬念让蒋百嫂对死亡生发出不同于常人的感受。而解开蒋百死亡之谜的竟然是作品中的“我”。共同的遭遇和蒋百嫂的离奇让“我”产生走进蒋百嫂的强烈欲望,于是“在这样一个夜凉如水的夜晚”,“我”不请自进地跨进了蒋百嫂的门槛。两个有着共同遭遇的寡妇相遇并没有产生如遇故知的感觉,相反,蒋百嫂对“我”的不请自到“连打了几个寒颤”,只是因为酒的作用始让蒋百嫂消释了对“我”的戒备。在“蒋百嫂彻底醉了”之后,“我”取下了蒋百嫂腰上的黄铜大钥匙进入了挂着“黑沉沉的大锁头”的房间,“扑向我的是檀香气和光影,屋子吊着盏低照度的灯,它像一只蔫软的梨一样,散发着昏黄的光。这屋子只有七八平方米,没有床,没有桌椅,四壁雪白,拉得严严实实的窗帘也是雪白的,有一种肃穆的气氛”。掀开嗡嗡响着的白色冰柜,一个天大的秘密揭开:“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他的那身蓝布衣裳,已挂了一层浓霜,而他的头发上,也落满霜雪,好像一个端坐在冰山脚下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蒋百了。我终于明白蒋百嫂为什么会在停电时歇斯底里,蒋三生为什么喜欢在屋顶望天。我也明白了乌塘那被提拔了的领导为什么惧怕蒋百嫂,一定是因为蒋百以这种特殊的失踪方式换取了他们升官进爵的阶梯,蒋百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个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难怪蒋百嫂那么惧怕夜晚,难怪她逢酒必醉,难怪她要找那么多的男人来践踏她。有这样一座冰山存在,她永远不会感受到温暖,她的生活注定是永无终结的漫漫长夜了。”作品与其说在抒写死亡,不如说在叙述死亡背后的故事;死亡是不幸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不幸的事。蒋百的消失就不仅仅是一个死亡的问题,而蒋百嫂之痛也不仅仅是一个丈夫的死亡之痛,其背后隐含着人性被颠覆的荒谬。
小说也从下同的层面和角度叙述了其他人的死亡,所述及的每人都有不同的死亡方式。如陈绍纯老人是为牛枕母亲修饰一幅牡丹图被画框砸死的;小食摊摊主老婆是得了痢疾乱投医被兽医治死的;云领母亲则是被宠物狗抓挠后不经意染狂犬病死亡的。作者叙述这些人不同的死亡方式和死亡的频繁,实际上所要表达的也许是,死亡对于人类并不是十分吝啬的,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也都会对死亡有所感受,但死亡并不能击垮人类的体魄和精神,附加给死亡的某些因素也许更可怕,从死亡中解脱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人生观。
作品虽然没有刻意描绘死亡,但作者渲染的情绪、调制的色调和作品中营造的氛围已经足以告诉我们,死亡的严重和对人们心理与精神的深刻触动。小说从头到尾笼罩在昏黄和暗淡的色调中,“我”的丈夫魔术师倒在灯火阑珊的夜色中来到乌塘,“乌塘的色调是灰黄色的,所有楼房的外墙都漆成土黄色,而平房则是灰色的”,“天色越来越暗淡,这座小城就像泼了一杯隔夜茶,透出一种陈旧感”,“乌塘街巷的名字,很像一个坐在夕阳底下饱经风霜又不乏浪漫之气的老学究给起的,如青泥街、落霞巷、月树街等”。当然还有回阳巷,显得古朴而暗淡无光。“我”则多在夜色中活动,触景生情也多萌发于月光下,夜色和月色也许更能虚掩“我”的哀伤和泪痕,而且更能融合“我”的心情。
作者关于死亡的叙事方式还直接与民歌、民间故事、鬼神故事等勾连起来,其实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叙事传统,《西游记》、《封神演义》、特别是《聊斋志异》等无疑是这种叙事资源的渊薮。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隐喻关系,在传统民间叙事包括文学作品中,历来指认为阳间和阴间二分世界,阳间即生的世界,阴间即死(鬼)的世界;阴间是阳间的延伸,即死是生的延伸;换句话说,在民间叙事中,生和死、人和鬼是生命的两种状态,民歌、民间故事、鬼神故事成为一种有力的引证,说明生命不灭,生命永恒,死亡只是生命进入另一种状态的关口,他人的哀伤、哭泣就成为了祭奠生命转入另一种状态的仪式。这种叙事方式满足了作者理性世界的需求,实现了精神升华的期望。
二、死亡叙事的文学价值
死亡之于文学,应该是一个难以避开的话题,更是一种开掘不尽的叙事资源。因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任务在于表现和揭示人性的多层面、多视阈的存在形态。死亡自然是人物质生命的终结,但物质生命的终结并不是一个人完全意义的终结。因为人是一种能动的有影响的存在物,人生存过程中生发出的精神、意识、以及于他人、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不因物质生命的终结而完全终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宗教哲学把人的死亡阐释为升入了天堂,中国文化则把死亡解说为进入地狱,实际上一个指归:生命不灭。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无论是人们的臆想还是实际状况,生和死是人的生命的两种状态,人的物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人性,人的死亡状态同样能够折射出一个人的人性,因此,文学对于死亡的表达就不是一种无意义的作为。
更重要的是,死亡对于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对于活着的人们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的撞击。人类社会是一个因因相传、持续不断的过程,从哲学意义上说,死亡孕育着新的生命和新的发展。但无论如何,死亡对于生者来说都是一面镜子,只要我们善于严肃认真地审视死亡,就一定能够折射出人类生存中的问题,或者是人类的共性问题,或者是人们的个性问题,而生者对待死者的态度更能使生者的人性得到根本的展示。人们对待死亡可谓众人百态,有恐惧,也有悲戚,有坦然,更有冷静和从容,当然还可能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死亡让人呈现的不同样态成为我们观照人们灵魂的独特视阈。
应该说,生和死、人和鬼在我们的感知和认识范畴是实和虚两个世界。实的世界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知的,阐释的依据具体、牢固;而天堂和地狱之类的虚拟世界并不是具体可感的,如果说能够感知,那一定需要人们用虔诚的心情和纯洁的灵魂去感知,因此,对虚拟世界阐释和叙事的空间就相当地寥廓。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合理地利用死亡这个虚拟世界形态的特性,以自己对死亡的切实感受牢牢确立对死亡的阐释权,让死亡反照现实,让死亡叩击灵魂,达到了高度的文学效果。
作者把“我”车祸死亡的丈夫幻化为魔术师,这就为“我”的生活涂抹了一层魔幻色彩。魔术师的魔术技艺为“我”的生活平添了无穷乐趣,因此,魔术师的死亡于“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虚无,仿佛魔术师自己施展的魔技,让自己在“我”面前出现片刻的藏匿,“我不知道我的魔术师是否在云层的后面,他仍如过去一样在温柔地注视着我么?太阳与月亮之所以光华满面是不是容纳了太多太多往生者的目光?有一缕云,轻飘舒朗得像一片鹅毛,它令我想起婚姻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日子”。亦真亦幻让“我”生发无限遐想以及无尽哀伤。“我”的魔幻感受和作者的魔幻叙事无疑是作者对死亡事件的精神界定,当然也是对作品本身格调和氛围的限定。
死亡事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死亡引发的人们的多重感受。所以,民间对死亡的认识是人们多重感受的体现,也是社会大众对死亡的多重阐释和重要的价值判断。其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场阈,并且保持着巨大的张力,它使众生的死亡在这里得到解释,并使死亡引起的波澜在这里得到平息。因此,“我”的魔术师的死亡给“我”造成的凄苦、哀伤何以消弭,民间场阈能够帮助释放和挥发。在乌塘,史三婆和卖笤帚的女孩为“我”讲述的鬼故事,表达的是民间对死亡的理解和体悟,体现着民间基本的是非善恶观,重要的一点是,生死在这里得到了还原,人生多苦,人生多难,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是一种民间的智慧和豁达,它要实现的是对道德理想的肯定和昭示。这就提升了我们对死亡的认识水平,死亡固然给人造成了很大伤害,恶的死亡固然罪有应得,但善的死亡也不必过于伤感,因为善的死亡对人是一种昭示,一种惊醒,即使进入虚无世界仍然受到人们的尊崇。而陈绍纯老人悲凉哀婉的民歌无疑是对死亡情感寄托的祭奠。因为陈绍纯唱的都是悲曲,人们都说那是“丧曲”,对于活人来说似乎不吉利,没有人愿意听;但对死亡来说不能不说是最好的仪式和祭礼。陈绍纯老人说,“他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次死亡,有一天他被一挂受惊的马车掠倒,送到医院后,昏迷了二十多天。……苏醒后,耳边萦绕的就是凄婉的歌声,那种歌声特别容易催发人的泪水,从此之后,他就痴迷于这种旋律”。在乌塘,最爱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剩下的就是“我”,因为只有对死亡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领悟到这种悲歌所蕴涵的价值。“他的歌声一起来,我觉得画店仿佛升起了一轮月亮,刹那间充满了光明。那温柔的悲凉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光,丝丝缕缕都洋溢着深情。在这苍凉而又青春的旋律中,我看见了我的魔术师,他依门而立,像一棵树,悄然望着我。没有巫师作法,可我却在歌声中牵着了他的手,这让我热泪盈眶。”这是一种关于死亡的艺术,是一曲死亡的交响乐。
小说亦真亦幻,在悲戚中叙述死亡的故事,娓娓道来,随着作者的情感流动舒缓推进。在考察了民歌和鬼故事,感受了民间死亡故事之后,应该说“我”的情感和精神得到升华和洗礼。来到三湖山,“我已经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坐在红泥泉边,没人能看见我的哀伤了”。实质上,在感受了众多死亡、经历了民间生死观洗礼之后,“我”已经无伤可哀了,因为死亡也许是一个人生命最高境界的延续,尽管生死不是魔术,但我们应该为死者祈祷超生。少年云领祭奠妈妈的方式别有意味,“我”请求七月十五和云领一起去放河灯。“我”和云领来到清流,“据云领讲,清流是离三湖山最远、也是最清澈的一条小溪。他妈妈曾对他讲,一个人要是丢了,只要到清流来,唤几声他的名字,他的魂灵就会回来”。在这个澄明的世界,魂灵永远不会丢失。“月光下的清流蜿蜒曲折,水声潺潺。这条一脚就能跨过去的小溪就像固定在大地上的一根琴弦。弹拨它的,是清风、月光以及一双少年的手。云领放下篮子,撩开野菊花,取出两盏河灯,又取出火柴,一一将它们点燃,将一盏莲花形的送给我。……我打量着那盏属于魔术师的莲花形的河灯……从随身的包中取出魔术师的剔须刀盒,打开漆黑的外壳,从中取出闪着银光的剔须刀,将槽中那些细若尘埃的胡须轻轻倾入河灯中。我呼唤着魔术师的名字,将河灯捧入水中。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小的旋涡处耸了耸身子,仿佛与我作最后的告别,之后便悠然向下游飘荡而去。……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地衔接在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上。”在这个清澈洁净之地,“我”为亡者招魂,亡者灵魂高度升华。
然而,故事并没有戛然而止,弦外之余音仍然缭绕。从清流回到旅馆,半倚在床头,“突然,我听见盒子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已。……没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这分明是庄周化蝶和梁祝化蝶的翻版。作者秉持的是唯美主义的理念,她要让情感的抒发和精神的表达淋漓尽致,“这美妙而经典的一笔,极具仪式感地完成了女主人公向死而生的全过程”[1]。作者用她优美、舒展、隽永的语言和细腻的笔法尽善尽美地完成了一篇死亡叙事,在无限广阔的精神空间,文学得到了升值。
标签:文学论文; 迟子建论文;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论文; 死亡方式论文; 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