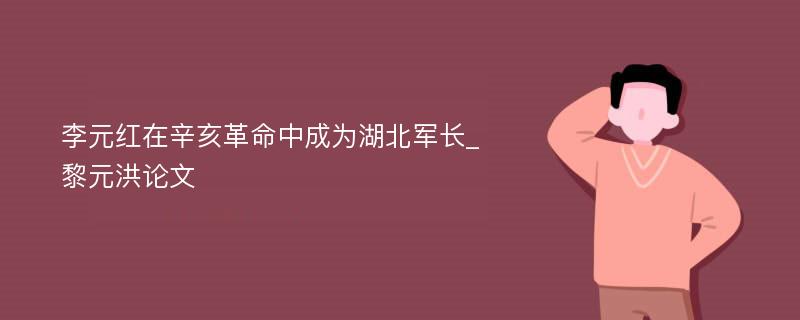
黎元洪出任辛亥革命鄂军都督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都督论文,始末论文,黎元洪论文,鄂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初无全算”的状况下仓猝起事,居然赢得占领湖广会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新政权。然而,武昌起义猝然爆发,本地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革命军总司令部原有二十一名干部,起义时在武昌参加战斗的仅蔡济民、吴醒汉二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则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于是便有清军将领黎元洪被推举为鄂军都督一幕的出现。
一、革命军据咨议局为总司令处,建立湖北军政府
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负责人应齐集全省最高民意机关——湖北咨议局,会商组建新政权大计。
10月11日黎明,经一夜激战的起义军人,带着浓重的硝烟气息,陆续赶到武昌蛇山南麓、阅马场北端的湖北咨议局,将其“据为总司令处”①。自此,这幢1908年筹划、1910年落成的西洋式二层红色楼房,成为革命的军政指挥中心,继而在此组建湖北军政府②。
武昌起义后立即组建军政府,这是依据同盟会的成议采取的行动。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起草《军政府宣言》,提出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在《宣言》开头拟出如下格式:
天运岁次年月日,中华国民军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③
武昌起义后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此一名称是据同盟会政纲、仿《军政府宣言》起始格式拟成的。
10月11日,湖北咨议局景象一新:大门铁栅栏前,悬挂两面红底黑色九角旗,上缀黄色18星,这是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昭显关内十八行省共谋革命的铁血旗,12名起义士兵(为测绘学堂及陆军第三学堂学兵)持枪护卫于门前旗下④。
前来参加10月11日上午会议的起义军人疲惫而又兴奋,他们是: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据共进会负责人之一、湖北沔阳人李作栋(春萱)后来回忆,在首义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⑤
遵照蔡济民的意见,“总司令处十人具名发出请帖,广召官绅。移时,劝业道、武昌府、县及各绅士到局,惟领袖绅士柯逊庵未到”⑥。柯逊庵,即柯逢时(1845-1912),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曾任各省土药统税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辛亥革命前夕授浙江巡抚,未赴任,是当时武昌在籍家居职位最高的官员,故称“领袖绅士”,湖北新军武昌暴动,他取观望态度,当然不愿出席11日党人在咨议局召开的会议(后来大局稳定,柯曾组织绅商成立态度中立的武昌保安社,为第二任社长)。
与会党人提议,通知咨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当即责成咨议局秘书长石山俨派人分头去请。驻会议员、湖北江陵人胡瑞霖(1878-1943)陪同共进会成员陈磊(1890-1912)、费榘(1885-1922)亲往议长汤化龙寓所敦请。据曾官费留学美国、加入同盟会、辛亥时任湖北咨议局当选议绅的襄阳人陶德琨(1883-1970)回忆,汤化龙是由陶德琨在土药统税大臣柯逢时家中觅得,引往咨议局的。另说:10月11日上午,共进会员吴醒汉、李作栋、陈磊分头寻找汤化龙,邀其支持,但均未觅得,后胡瑞霖在柯逢时家中找到汤,劝其出山,汤化龙遂由胡瑞霖陪同前来咨议局参会,时至11日正午。
二、10月11日中午咨议局楼下联席会议·都督提名
经上述筹划准备,10月11日中午1时许,在咨议局楼下会议厅举行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首义军人、湖北咨议局议员及原地方官员、绅商代表。
参加联席会议的原地方官员,噤若寒蝉,并对起义军人邀请他们任职新政权,强推软辞,不肯就范:
革党以劝业道高松如为行政长官,推为度支司,所有官钱局事务,请其主持。高欲却不能,强而后可。又推武昌府[赵]为安民局长,赵守答以“赵某年已七十有余,今日杀我,正得其所;如欲用我,则已精力不及。”革党一笑置之。江夏县李令,默无一言。⑦
可见,起义者本拟延请旧政权的地方官员担任军政府行政职务,却受到旧官僚们冷淡的拒绝。相形之下,咨议局成员则对新政权表现了热情,他们是:议长汤化龙(1874-1918),副议长张国溶(1878-?)、夏寿康(1871-1923),议员胡瑞霖、阮毓菘、刘赓藻、沈维周,秘书长石山俨等。
10月11日中午,在咨议局楼下会议厅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先有军人推举汤化龙出任都督,汤氏不置可否,“未有绝对拒绝意”⑧,倒是驻会议员、汤的儿女亲家胡瑞霖考虑到革命“成败尚未可知”,从旁婉辞,说现在是军队起来革命,汤议长不便领导,最好在军队中推一有声望的人⑨。汤化龙随即发言说:“革命事业,兄弟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无所知,须先通电各省,吁请一致响应,革命大功才能告成。再者瑞澂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派兵来打湖北,同我们为难。兄弟一介书生,军事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胡瑞霖在会上说:“革命军真乃仁义之师,连夜作战,市廛不惊,人民箪食壶浆,革命军亦辞而不受。兄弟万分敬佩。暂时需用款项,兄弟可以代为筹办。”⑩胡瑞霖提议由咨议局垫支一万元(另说五万元)作费用。据李翊东(西屏)回忆,起义士兵10月10日晚通宵作战,废寝忘食,11月11日晨已觉困饿,咨议局司会计的议员胡瑞霖“乃奔告商会垫借五万金分配作临时食费”(11)。
关于都督人选,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1864-1928)(12),黄陂籍议员刘赓藻马上大声说:“黎元洪现在城中,我已得到消息,知道他的隐藏地方,如果大家一定要找他,我愿介绍前往”(13)。张难先记载的会议情形是,刘赓藻率先提出请黎元洪出山:
省议员刘赓藻曰:“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适,当导觅之”,众赞成,蔡济民率少数同志,偕刘往。(14)
以起义翌日的形势论,军中革党拥有话语权,推黎元洪任都督的建议,首先由革命军人提出,议员附和较为可信。
聚会湖北咨议局的年轻起义军人,面对纷至沓来的建政事务,正感无从着手,听到汤化龙、胡瑞霖、刘赓藻等人“赞成”革命的侃侃言辞,以及对黎元洪的推荐,颇为之吸引。党人们以为,咨议局既是“民意机关”,议员又系各县选出,能得到他们合作,革命可以早日胜利;黎元洪的人望不错,由黎元洪、汤化龙分掌军、民两政,岂不大好。
会议决定,咨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济民、刘赓藻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可凭乡谊请动黎元洪。
11日下午,受联席会议委托,蔡济民、刘赓藻出发敦请黎元洪,先觅至武昌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管带(营长)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其时,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的起义军已攻克督署,吴兆麟率激战一夜的部队暂屯楚望台军械库,礼迎黎元洪到来。蔡济民、刘赓藻等人赶赴楚望台,与吴兆麟等共拥黎元洪到咨议局与会(15)。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对于黎元洪被寻出的情形,记述如下:
10月11日晨,党人马荣等巡街,发现黎元洪的夫役担三皮箱出,遂质问夫役,得黎行止,并由夫役导至黄土坡黎宅,找出黎,拥至楚望台。此时刘赓藻、蔡济民亦至楚望台,拥黎至咨议局。
黎元洪这位本与革命并无渊源的前朝军官,自10月11日起便被强拉入民国“开国元勋”的途程,此种矛盾状态,使他拥有一个“床下都督”的不雅名号。
三、“床下都督”辨正
“床下都督”说的证实或证伪,不应由论者的好恶决定,而取决于黎元洪在首义期间具体表现的披露。
(一)10月10日夜、11日上午黎氏行状
关于武昌首义当晚黎元洪的反应,熊秉坤有一段比较真切的记述:“黎元洪初闻工程营兵变,不甚措意”,因工八营属张彪的第八镇,与己无关,这显示了黎氏“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心态。但是,“继接张正基电话报告,知自领之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之一部亦变”,黎氏有些着慌,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遂集合第四十一标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盖借此有秩序之集合而防范之也。工程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同志送信该协。周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黎讯明来历,即用杀一警百之计,手刃周于会议厅。(16)
随后炮声四起,众心已乱,黎令官佐各自回营,自行其是,黎本人“即带执事官王安澜往黄土坡某号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继避谢国超管带家,后被士众从谢家觅得,带到楚望台,与时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等见面(17)。
黎元洪本人1913年对居正追忆首义当夜情形,与熊氏所说基本吻合:
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引者)夜九时,余在黄土坡司令部,得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即派炮营往打,不十分钟,言炮营亦变,又不到半时,听说第八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架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十时,瑞澂逃至楚豫兵舰,十一时,督署电话不通。又十一时半,有一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护兵将此人擒至司令部手刃之,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后经各方面查询,始知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联络各营周荣棠也。此时已十二时后矣,革命军遍布司令部对面之蛇山,向司令部射击,参谋副官等见大势已去,力劝暂避,乃往黄土坡参谋刘文吉家,易便衣,再由刘家至黄土坡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工程营目兵马荣、程正瀛偕同各军代表,率兵一排,寻得余在谢家,群趋而前,为彼等拥至咨议局,推余为都督。(18)
在另一场合,黎元洪回顾1911年10月10日夜及10月11日的情形说: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所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19)
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这些陈辞,并未文饰自己。黎氏自称:他在武昌起义之际,先是抗拒革命,令护兵“手刃”召唤起事的士兵,并试图派炮营攻打革命军,未果,后见革命军势大,避至协参谋刘文吉家更便衣,再往管带谢国超家躲藏,直至被党人寻出,被强行拥至咨议局。
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也有类似记述,惟“手刃”革命士兵的,并非护兵,而是黎氏本人:
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20)
此处“军械局”,当指楚望台军械库。
黎元洪本人对居正的陈述,是说黎由管带谢国超家拥至咨议局,而章太炎1933年撰写的《大总统黎公碑》则说,先去“军械局”(即楚望台军械库)。据熊秉坤、李西屏等11日上午在楚望台军械库的当事人回忆:黎氏先被带到楚望台军械库,与吴兆麟所率起义士兵相见,随后蔡济民、刘赓藻至此,由蔡济民、刘赓藻与吴兆麟等拥簇着前往咨议局。
熊秉坤10月11日上午在楚望台,亲见黎元洪被程定国(正瀛)等士兵从黄土坡拥至楚望台的情况:
有马荣送信在先,故吴总指挥派兵一排,站队鸣号以欢迎之。黎服青呢马褂,灰色呢夹袍,瓜皮小帽,王安澜随其后。吴总指挥出为招待,黎笑语众曰:“各位辛苦。”吴当与同志诸人,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首与吴小语,责吴不应为此,吴以为众所挟持对。(21)
此文所述黎元洪被挟持至楚望台,对起义部众采取比较温和的不合作态度,对吴兆麟轻加责备,这符合黎氏的性格特征与政治倾向,故真切可信。
(二)“床下都督”说并无确证
关于黎元洪被勉强拉来充任起义政权首脑,长期流传“床下都督”的故事。然经笔者多年考析,以为此说似是而非。“似是”,指其说与黎氏当时行为倾向基本吻合;“而非”,指黎氏从床下拖出,并无直接材料证实,不可确信。
与辛亥首义有关的人士所撰首义史著多种,如曹亚伯(1875-1937)的《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7年),张难先(1874-1968)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李廉芳(1878-1959)的《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胡祖舜(1885-1948)的《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杨玉如(1878-1960)的《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论及黎氏被革命士兵寻找时,或言黎氏“避入房中”,或言黎氏与执事官王安澜坐谈,等等,皆无从床下拖出之说。
盛称“床下都督”之说的,多为与武昌首义距离较远者,如活动于广东及海外的胡汉民(1879-1936)在自传中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活动于广东及香港的邹鲁(1886-1954)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称黎从床下搜出。然胡汉民、邹鲁皆武昌起义局外人,所言当然来自传闻。
武昌起义参加者说黎氏从床下拉出的,是李西屏(翊东)。李氏撰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昌首义纪事》称,10月11日晨,黎元洪先被拥至楚望台,黎当时窘态十足,“神色仓惶”:
武昌一夕光复,主帅一席犹悬。是日黎明,众纷纷围集楚望台麓下。黎统领衣米色长袍立其中,神色仓惶。李翊东诘之曰:“异哉统领,何至此耶?”或曰自其床下挟出,或曰自黄土坡友益径某参谋家挟至此者。(22)
首义时李西屏是测绘学堂学生,10月10日夜率学兵奔往楚望台,11日上午他担任军政府(原咨议局)警卫之责,并未参加挟持黎元洪的行动,故在黎氏是否为“床下都督”这一论题上,李氏并非当事人,李氏《武昌首义纪事》言此,用语也是谨慎的,称黎氏由“床下挟出”,冠以“或曰”,显系耳闻,故李氏之说并不能作为“床下都督”的直接依据。
1933年章太炎撰《大总统黎公碑文》,李西屏致函章氏,对碑文某些记述表示异议,其中也论及“床下都督”事,章太炎复函李西屏,称“黎无伏于床下之事,乃诸君所自言”(23)。
章氏谓“诸君所自言”,指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自己所说。可见,民国年间围绕此事多有争议,经章氏与当事诸人讨论认为,黎氏并无“伏于床下之事”。
(三)“床下都督”说流传原因探略
既然事如上述,那么,“床下都督”之说又何以流传广远,人们耳熟能详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黎氏为清军高官,10月10日夜士兵发难,黎氏惊恐万状,一再隐藏,次日晨被起事士兵强拉出来,逼其主持军政府。对于一个与革命党素无渊源的旧营垒中人而言,事起后逃避、抵制势在必然。黎氏10日夜、11日晨恐惧与惶惑,当然会有种种表现,皆被部属及前来挟持他的起义士兵(如马荣等人)看在眼里,当时对黎氏的讥笑之谈应运而生,事后被演绎传播,也在常理之中。“床下都督”的故事,便产生于此际。
其二,“床下都督”说流传广远,与同情革党的新闻传媒的宣扬颇有干系。黎元洪在湖北军政府期间同革党发生权力之争,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黎氏与袁世凯勾结,杀害张振武;黎氏引北洋军入鄂等等,使革党痛恨黎氏,致使一些倾向革党的报刊声讨黎氏,不免揭露黎氏种种不堪,“床下都督”说便成为当日盛传的故事。
《震旦民报》在中断发行后,获国民党鄂支部和赣督李烈钧资助,于1912年9月重新发刊,后蔡寄鸥为《震旦民报》主笔,撰社评《新空城计传奇》,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1911年10月11日晨黎匿于床下)、“逃跑都督”(汉阳失守,黎弃武昌而逃)。《震旦民报》还连载马野马所撰《床下英雄传》,讥刺黎元洪为不识抬举的“床下英雄”。《床下英雄传》、《新空城计传奇》连载下来,《震旦民报》“声誉大噪”,“日售数万份,为汉上所仅见”。这类生动的报刊文字,使“床下都督”说不胫而走。
胡汉民、邹鲁等民国要角,素来不喜黎氏,他们当然沿用上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也就顺理成章。而胡汉民、邹鲁等是主持民国舆论的人物,所言影响力不小,与民间传说彼此呼应,使“床下都督”说声势更张,其余韵流风至今未息。
四、10月10日夜及11日上午黎元洪路线图
11日晨黎元洪在部属家被革命士兵寻出以后的行程,有两说,一为直接带至咨议局,二为先带至楚望台,然后去咨议局。
据《湖北省志·人物志》之《吴兆麟传》记述,时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在楚望台,“自认声望不足服众,欲推原协统黎元洪为首,黎不允,马荣举刀欲砍黎,吴止之,劝黎‘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当日中午,在咨议局商讨组织军政府,吴陪黎元洪前往,以总指挥身份提议公举黎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24)。参之以吴兆麟、李翊东、熊秉坤等当事人民国年间所撰回忆文章,上列《马荣传》、《吴兆麟传》记述大体可信。李翊东、熊秉坤的回忆及马传、吴传都说,11日起义士兵先将黎元洪挟至楚望台,由吴兆麟与蔡济民、刘赓藻陪同从楚望台去咨议局。
楚望台的起义士兵为黎元洪找到座骑,黎上马,由吴兆麟、蔡济民、刘赓藻及多名士兵簇拥着,从楚望台前往咨议局,其时已至11日下午。李春萱(作栋)11日一直在咨议局,他下午亲见——
黎骑酱色大马,身着黄灰色呢袍,前后十余骑护卫,到了咨议局门前,卫兵举枪示敬,黎摆出协统的旧有威风,从容下马,步行至咨议局楼上大厅,绝不像一个被迫出席的样子。(25)
黎氏抵达咨议局的情形,当时在咨议局大门执行警卫的测绘学堂学兵、湖北黄冈人童愚(1881-1962)后来有更详细的描述:
十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午正,我们的领导来传达命令,要我们立刻集合,由中和门经黄土坡转东厂口到咨议局,负守卫责任。布置就绪,已下午一点钟。有人说:“黎协统来矣。”我和同学十人正在咨议局头门守卫,我荷枪与谢流芳同学立在门的右方,只见一簇人拥着黎元洪由东场口匆匆走来,有穿便衣的,有着军服的。黎头戴瓜皮青缎红顶子帽,身穿蓝呢夹袄,夹衣上穿一件海狐绒对襟大袖马褂,脚下穿的双梁青缎子靴,背后的豚尾尚未剪掉,完全前清官僚神气。黎面容沮丧,毫无愉快表情,似一肚皮的闷气无处宣泄者。(26)
综述之,10月10日晚、11日上午黎元洪的行止路线为:
—在武昌大东门内左旗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获悉新军暴动消息,试图组织军力弹压,又手刃前来召唤起事的士兵周荣棠
—见革军势大,无力阻挡,由部属引领,避入参谋刘文吉黄土坡寓所,更换便衣
—再避管带谢国超寓所
—在谢国超宅被革命士兵发现,带至楚望台军械库,见到吴兆麟等起事者,稍加责备
—被蔡济民、刘赓藻、吴兆麟等拥至咨议局
五、10月11日傍晚咨议局楼上会议·强令黎任都督
黎氏抵达咨议局,约在11日下午。黎氏请到,起义党人再次举行会议。会场从中午的一楼大会议厅改在咨议局二楼小会议室,咨议局议员没有再被邀请(27)。与会人员,除参加11日中午会议的起义军人外,增加了黎元洪、吴兆麟,以及邓玉麟、向訏谟、李翊东、方兴等起义军人,另有胡瑛、张廷辅、牟鸿勋等刚从模范监狱解救出狱的党人。
在咨议局二楼会议室,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议:推举黎统领任都督,汤议长负责民事。蔡济民说:“两公为湖北人望,革命一定容易成功。”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一力推辞,他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众听罢哗然,黎元洪暂退会场。会议继续论辩,激烈者如张振武说:“黎如此不识抬举,干脆另外找人。”邓玉麟主张耐心等待。还有人说,此刻不过暂时利用黎元洪的名声,遂先将黎安置在楼上议长室,从长计议(28)。软禁于二楼的黎元洪由测绘学堂学兵监视。
自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之说传出,“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如杜锡钧、何锡蕃等”(29),不少官僚政客也闻风依附;黎元洪的亲信人等,纷纷对黎劝进,甚至以“黄袍加身,逆之不祥”为喻。黎元洪到此不能不有所抉择:为清廷殉节,不必要也不情愿;顺从革命却有可乘之机,但又担着颇大风险。所以,他勉强接受都督职位,却消极处之,以观事态发展。
湖北军政府在湖北咨议局议定并成立,又推举原清方的汉官为都督,构建了一种范式,以后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军政府大都在各省咨议局议定并成立,以“民意代表”现身的咨议局议员们纷纷进入新政权,一些“反正”汉官相继出任都督。这显示了:
(1)革命运动对立宪运动的承袭与联系。
(2)在“排满革命”宗旨下党人对汉官的容纳。
六、推举黎氏为都督早有预案
黎元洪这样一个直至起义爆发之时还“手刃”起义士兵的清方高级军官,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为什么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不约而同地推举黎元洪?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不能以“偶然机遇”一言以蔽之。
武昌起义猝然爆发,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在秘密运动期间,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对都督一席,各有打算。共进会认为,刘公为同盟会员,又系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且以第三任共进会会长资格回鄂主盟,成为同盟会法定湖上七都督。虽然刘公表示放弃,但在9月底的联合大会上,再度被选任总理,负责民政,以示有别于军民两管的都督。刘公平时不大出面,与同志接触不多。从魄力、胆识、资望看,刘公任都督一职均不理想。
文学社当然属意蒋翊武。但蒋本人以为,在湖北举义,都督一席应属鄂人,如吴禄贞、蓝天蔚在此,自然众望所归;次如刘公、孙武、蔡济民亦未为不可,又恐力有不逮。这样,蒋翊武等党人在有关会议上,曾提名黎元洪为未来的都督人选。
据湖北黄冈人、文学社社员万迪庥(鸿喈)20世纪40年代致曾省三的信中说,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赴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一次党人会议途中,蒋翊武说:“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到宝通寺后,蒋翊武、孙武、蔡济民、万迪庥等都登上宝通禅寺后面洪山山麓之宝塔,在塔内,“蒋翊武推举黎元洪为都督”(30)。
万迪庥(鸿喈)于20世纪50年代撰《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再次详述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洪山宝通寺召开的各标、营、队党人代表会议,会上蒋诩武等提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建议。万文还陈述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1892-1916)所说的请黎三利:
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31)
万迪庥关于党人早在辛亥春已有黎任都督的设想,多有他人旁证。如孙武1938年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九十一号的机关召集干部同志潘善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机、牟鸿勋、高因群、钟雨庭、马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开会,“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遇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以保定秋操后”举行。并且,“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32)。
再如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
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33)
总之,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曾多次议及由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故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说,武昌起义前“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34)。章氏说武昌起义前即“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不准确,当时并无文字材料确认“大都督黎”,但党人“属意”于黎元洪,则大体如此。
当然,起义前所议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只是一种供选择的方案,并非成议,绝大多数党人也不知情,“同志知者少,黎更茫茫然也”(35)。所以起义后,10月11日在咨议局举行的会上,一些党人还主张推戴汤化龙;同日下午,向訏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拟举汤化龙议长为总司令长,汤推不明军旅之事,众遂要挟黎协戎元洪为总司令长。”(36)可见多数党人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并无预知,甚至连“都督”这个名称也不清楚,故向訏谟日记中出现“总司令长”之说。
蒋翊武、孙武等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之所以“属意”黎元洪,除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有互相排斥的心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党人的幼稚和软弱。他们虽然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但在权力面前却“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总希望有一个“大人物”出来号召天下。因此在考虑都督人选时,只注重“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而未“深究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37)。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势必到汉人旧官僚中寻找目标,而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著称,他曾三度赴日本考察军务,两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成绩优异。黎元洪与第八镇统制张彪相比,较少克扣军饷,对士兵、尤其是对有文化的士兵,态度较好,所以又有“爱兵”之誉。当时的报刊上便说:
鄂军统制张彪不学无术,兼以不得军心,与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相比较,逊黎多矣。黎系天津陆师学堂毕业学生,在鄂办理军务,以得军心为人所最称颂者。(38)
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毅然剪去发辫,黎元洪得知,不仅未予责备,反而加以赞扬,说剪辫是“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39),表现了黎元洪的“开通”之处。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并支持入京请愿,赢得湖北商民的拥护,更与汤化龙等立宪派建立了联系,这在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
此外,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宗旨,汉官一概被视作可争取者。凡此种种,使黎元洪既成为年轻的革命党人挑选的对象,又是立宪派所寻觅的政治代表。正是这种种缘故,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之位。而黎元洪这样的旧人物被推拥为新领袖,正生动地显示了在专制帝制时代的中国爆发的近代革命的特征。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形,颇类似马克思所说的19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40)
杨铎在《辛亥建国史纲》中则以辛亥人物比附秦汉鼎革之际的古史人物:
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41)
此“戏论”颇为传神。
七、中部同盟会领导人不赞成黎氏出任都督
黎元洪出任都督虽早有预案,但毕竟只是湖北党人的一种选项,大多数人更希望由有资望的革命领袖出任都督。中部同盟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持此议尤为强烈。
宋教仁从一开始便不信任黎元洪,认为由一与革命毫无渊源的清朝高级军官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十分危险。宋氏在武昌首义后半个月的10月28日与黄兴从上海同船抵达武昌,首先想到的便是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他立即在党人中策动,力举黄兴任“两湖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方可确保下一步组建全国政府,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此议虽得湖南人杨王鹏等的支持,却遭吴兆麟等湖北人反对,终于未果。
至于谭人凤,10月14日偕居正从上海赶至武昌,声称是黄兴派遣,当晚11时在农务学堂召集党人开会,居正声言,明将赴沪敦请黄兴、宋教仁来汉主持大计。这都是在强调军政府领导权应由黄兴等革党掌握。谭人凤见到黎元洪萎靡不振的状态,于劝勉之余,力主驱逐刘家庙之敌,并北上鄂豫交界处,“以重兵驻守武胜关,方无后患”。然黎元洪低头不应(42)。谭氏后来为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进而任民国副总统、大总统而深为愤然。在总结此一憾事时,谭氏指出:
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43)
在追究黎元洪登上宝座的原因时,谭氏归结为同盟会领袖人物未能及时赶到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组建现场,以致“统率无人”,黎氏得以“拥为都督”。
时在上海办《民立报》的于右任(1879-1964)1911年10月16日以“骚心”笔名,在报刊发表短文《黎元洪》,戏曰:
中国历史上有数洪字,皆有奇闻:
其一为朱洪武,
其二为洪秀全,
其三为黎元洪乎?
或曰:洪从共,共和政体。
嘻!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吾请看此最后之洪。(44)
较之谭人凤、宋教仁愤慨于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于右任在貌似玩笑的文字间,透露出通过黎元洪建设共和政体的期望。
八、李西屏代签“黎”字的军政府第一份布告
10月11日傍晚开始的咨议局楼上党人会议,因黎元洪不肯就任都督而进行得不顺利,与会者又大多昨夜苦战,都很疲倦,遂决定次日继续开会。
会议刚散,正是夜间十时以后,忽然一声枪响,突有清兵进犯,当由守御咨议局的测绘学堂学生兵奋起抵抗,陆军三中学学生兵亦加入战斗。李作栋等人则伴随黎元洪出后门暂避。清军被击退后,始知是武昌城内的清军残部企图劫走黎元洪。经此惊吓,黎要求回私宅一行,谋略处令守护士兵程正瀛等陪同前往。次日晨又强制黎元洪回到军政府。原来就反对推举黎为都督的张振武这时又说:“黎元洪既不赞成革命……所拟通电尚未发出,不如先将黎元洪斩首示众”(45)。吴兆麟、蔡济民二人坚持不可,并说:“都督名义归他,事情我们来做,以后再不让他自由行动就是。”
由于黎元洪表现消极,党人暂将黎禁于一室,却用黎的名义发布文告。
湖北军政府的第一份文告,是东京同盟会预先拟就的,汉口党人的政治筹备处已经印制,经10月9日宝善里机关破坏,文告仅存一份。10月11日清晨,共进会员、湖北孝感人李赐生(亦作次生,1887-1950)乘小船从汉口过武昌,绕道通湘门进城,将仅存之文告送到咨议局大楼,当即改换题头,照抄多份。11日晚至翌日晨,各校教员学生多人请求分配抄写任务,日夜工作,几忘饥疲。
诸党人决定尽快公布此一文告,但由于在下午会议上,黎元洪拒绝接受都督之职,当然也不愿在文告上签名,测绘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李翊东(后名西屏)以枪逼黎签字,黎仍不从,于是李翊东援笔,代黎签署。
李翊东撰《武昌首义纪事》记述发生在咨议局的此一过程:
翊东乃持一宿写就之安民布告,上奉黎曰:“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畏缩舌颤曰:“毋害我。”翊东怒,手秉长铳示之曰:“汝腼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皇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汝罪,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蔡济民、陈磊急掣翊东肘曰:“慎无发铳。”黎益瑟缩不语。翊东乃援笔代书一“黎”字,众鼓掌称善,遂置黎于楼上室内,以戈守之。(46)
这份由李翊东代签“黎”字的文告,“是中华民国开国第一次发布的文告,富有历史意义”(47)。文告张贴武昌城内,布告下都挤满观众,不识字的人请识字的人念给他们听。武昌街头巷尾,可谓万头攒动,群情兴奋,许多人流下热泪,感到扬眉吐气。喜形于色的市民,奔走相告。
九、命悬一线的黎氏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尸位素餐、不与政务。胡鄂公在《武昌首义三十五日记》中记述他11日傍晚见黎元洪的情况为:“与之谈国内革命形势,应于武汉三镇防守略事布置后,即派兵直捣北京,彼不语。与之谈武汉战守之策,应即日派兵将武胜关、田家镇占领,彼亦不言”(48)。黎氏的此种表现,深令起义者不满,激进者拟罢黜黎氏,乃至除掉黎氏。
(一)党人数次打算枪毙黎氏
鉴于首义后开始几天黎元洪的不合作态度,当时革命党人几欲枪毙黎氏,生此念者非张振武、李翊东二人,蒋翊武、张难先等都有这种想法,并已制订处决黎氏的计划,后因黎氏转而与革党合作,计划方放弃。张难先著文说:
武昌起义时,黎元洪本被迫而为都督,态度极为不明。三日(指10月11日黎任都督后三日,即10月14日——引者),余从汉川抵省,趋都督府,蒋翊武屏后执吾手泣语,谓黎且不可测。余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今夜汝等急切晓之,我明晨8时来,共决之耳。次晨翊武执余手贺曰:宋卿(黎元洪字宋卿)已下决心矣,余喜,即往汉川视察。先是别翊武后,出府,与数同志商;决议谓今夜黎不决,明晨即弃诸市……险哉黎元洪!(49)
故称首义后开始几天黎元洪“命悬一线”,并不夸张。
(二)黎氏剪辫
从12日到14日,黎元洪经过一段彷徨,得知汉口之役进展顺利,“汉口租界外侨观战时,都伸大拇指赞许革命军炮兵技术的优良。”黎氏暗中转变念头,逐渐接受各方人士的劝说,终于对革党表示,“我决心与你们帮忙”(50)。
10月12日,蔡济民等劝黎元洪剪去发辫,黎思索再三始允,遂由丁仁杰(1891-1920)、刘度成二人给他剪掉辫子。蔡济民抚摸着黎元洪的头戏曰:“都督好像个罗汉。”黎笑曰:“有点似弥勒佛。”(51)众人还为此燃放炮竹致贺。
(三)“黎公傀儡,大权操之党人”
10月13日,汤化龙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时的同学、湖北荆州人黄中恺(逸民)来访汤化龙、胡瑞霖,汤、胡流露出对党人的不满,故称革命党“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52),黄中恺加以劝慰,后与汤、胡及舒礼鉴(前候补知县)去见黎元洪,黎声色低沉。次日,黄、汤、胡、舒四人再见黎元洪,黎仍萎顿。黄中恺意识到:
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53)
这是军政府初几日的实际情状。
十、军政府祭天大典
立宪派目睹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实权,当然试图重作权力分配。他们决定以抬高黎元洪地位的方法达到目的。10月13日,黎元洪对前来相见的汤化龙、胡瑞霖、黄中恺等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猝,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54)表示了对汤化龙等人的倚重。而汤等深知,要从革命党人手中争权,必须使黎元洪改变傀儡地位。从这一意图出发,导演了“祭天大典”。
汤化龙、胡瑞霖等在军政府造舆论说,武昌起义乃汤武革命,应天顺人,没有隆重仪式,何以昭示光复大义。建议筑坛祭天,并祀列祖列宗。革命党人既以立宪派为团结对象,对于这一形式问题,自然接受。当时,从上海赶来武昌的同盟会员居正也“虑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也,乃议设坛场,具礼仪,请都督誓师,明白宣布,愿负复兴讨虏之责,使其与清绝,而安心为国谋,公然之。”(55)。谭人凤也赞成此举。这样,革命党人和咨议局诸人出于各自不同的意图,共同组织了祭天大典。
10月17日上午,在湖北军政府前的阅马场筑坛祭天誓师,“以太牢元酒之仪,由都督黎元洪主祭”(56)。是日坛前设燎火,坛上设轩辕帝灵位,灵前设香案,陈玄酒,旗分立两侧,在鼓乐声中,黎元洪身着军礼服,佩军刀,乘高头大马入场,在祭坛前下马,由汤化龙和胡瑞霖引导行礼,党人公推须发飘然、气度不凡的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举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创立民国之意义,大声疾呼,听众鼓舞”。然后,黎元洪跪读祝文(由前候补知县舒礼鉴草拟),内称:“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群策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日,此岂人力所能及哉!”俨然以民国元勋的姿态出现。继由读祝官读誓师词,然后三军举枪,三呼万岁。最后宣读祭天地及列祖列宗文。
祭天仪式虽然是一次礼仪性活动,但对振奋民军士气,激励武汉市民的革命热情有积极意义;此举又是黎元洪正式以行政长官和军事主帅身份公开亮相,标志着黎元洪由消极态度转向比较积极的态度。祭天大典,对于抬高黎本人以及立宪派在湖北军政府中的地位,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点是革命党人当时所未曾意识到的。
十一、黎氏任都督平议
黎元洪是一位与革命素不相干的清朝高级军官,在辛亥首义当夜,不仅“手刃”革命士兵,还试图组织炮队镇压,无果而避入部属家中。首义第二天,群龙无首的年轻革命者强行推举黎氏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氏连唤“莫害我!莫害我!”(57),并宣称:“革命二字,从未之闻;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58)这样的一个站在革命对立面的局外人,竟然登上军政府的权力顶端,初期全然消极抗拒,后来发现尚有可为,便渐次任事,逐步掌理军政事务,在阳夏战争及南北议和之际,已然举足轻重,实权在握,此确为一个诡异的历史现象。故黎氏出任都督,在当时及后世皆招来种种评议。本文就湖北军政府时期黎氏的功过试作平允之议。
先论积极效应——
第一,黎氏在湖北新军内素有“厚重知兵”之誉,获得士众信赖,由他出任鄂军都督,有利于湖北新军多数将士归附革命。章太炎认为,首义后“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湖北局势稳定,系“由公镇之也”(59),此说不无道理。追随黎氏参加民军、担任指挥官的王安澜、杜锡钧、何锡蕃、谢元恺等新军中级军官,在阳夏之役中有较好表现。
第二,黎氏出任都督,对清军有所震慑,“瑞澂始谓小寇蜂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引者)出,乃去”(60)。荫昌、冯国璋、袁世凯皆忌惮民军,这是首义后民军的初期军事行动顺利的原因之一。
第三,黎氏作为一位政声较好的汉族官员,在武汉市民中尚有佳誉,故首义后由其署名的军政府布告一经张贴,即在民众中造成轰动——“黎协戎居然革命,足见这不是草寇闹事”。湖北孝感人、新军资州起义参加者胡贽的回忆文章颇为生动传神:“黎之布告出,往观者途为之塞,白发老翁亦以先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惊异,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61)。三镇商民热烈支持革命,一批旧官吏归附革命(或不正面抗拒革命),减轻了革命阻力,与黎氏出任都督不无关系。
第四,黎氏出任都督,对列强的态度产生正面影响。据革命报人胡石庵称,他10月11日在汉口遇一洋行翻译查某,查曰:“黎元洪竟为革命党首领,真出人意料,所有租界之洋人,皆拍手称奇。”胡氏问:“洋人或有意干涉乎?”查曰:“洋人决不至此。”(62)辛亥首义后,民军不久即被各外国领事认作“交战团体”,各国对清—民交战取中立态度,除因为民军保护外侨、外商的文明表现外,也与黎氏这样的高级官员出任都督,又与领事团会谈,给外国领事留下“有大体”的印象相关(63)。
第五,因黎氏海军出身,与溯江而至的海军将士颇有渊源,其致书萨镇冰、汤芗铭等,直接促成海军反正,民军水路军事压力解除,阳夏之役得以坚持四十余天。黎氏促成海军反正,也对沪宁一带举义成功有所助益。
次论消极效应——
第一,黎氏出任都督,很快便成为旧势力集结的中心点。旧军官、旧官僚竞相投效军政府,既减轻了对革命的抵抗力,又潜伏下新政权变质的危险,这后一走向,正是围绕出任都督的黎氏展开。
第二,辛亥首义后,湖北立宪派立即由“清臣”转为“赞同革命”,并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这有利于新政权的建设与稳定。但汤化龙等立宪派觊觎权力,自己未能获得都督之职,立即同出任都督的黎氏联合,向革党争权。党人对此怨愤却莫可奈何,在前线作战的甘绩熙等说:“你我在前线拼生死,而无耻之辈在高楼大厦计较权位”(64)。推举黎氏出任都督本为党人仓促间的权宜之计,不意竟成为一种模式,继此之后,全国各省响应所建立之军政府,除广东由党人胡汉民任都督外,多由旧官员、咨议局人士担任(湖南一度由焦达峰等党人做都督,然立即被推翻,由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取代),在一派“咸与维新”的恭贺声中,新政权消弭于旧势力的汪洋大海。
第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革命派内部分化,孙武等投效黎氏,黎氏则利用其力打击文学社成员,进而借助袁世凯之力格杀张振武,排斥革命派。故首义老人1954年座谈时,总结辛亥首义经验教训,江炳灵认为“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李西屏有类似看法,李春萱也说:当时一些人“以为黎元洪可以维持秩序,事实上找他出来是错误的”(65);熊秉坤则说:“革命军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66)
概言之,来自旧营垒的黎氏出任都督,在湖北军政府时期所发挥的效力,可以喻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军政府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消解其革命性。
值得重视的是,黎氏在北洋时期虽然有过种种摇摆,但大体坚守了共和,此为黎氏政治生涯的亮点。1915年8月,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效力的筹安会杨度等谒见黎氏,以窥其意,黎氏表示不能违背民国,9月辞参政院长、副总统职。12月,袁世凯以“中华帝国皇帝”名义册封黎为“武义亲王”(“武义”指武昌起义),黎氏“拒其册,却其禄”,又誓曰:“辛亥倡义,踣军民无算,非为一人求官禄也。诸君如相迫,即立触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67)。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黎又上辞呈,表示愿为编氓,终此余年,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以示与洪宪王朝保持距离。
黎氏在北洋时期成为辛亥首义及共和政体的象征性人物,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晚年致力实业。
综观全体,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首义及民国建政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然置于历史天平,作一总的权衡,堪称一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
黎元洪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的路途的曲折坎坷。
1928年6月3日黎氏病故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氏举行国葬,建“黎大总统墓”于武昌卓刀泉,辛亥元老、反袁斗士、国学泰斗章太炎(1869-1936)撰《大总统黎公碑》。汉口则有“黎黄陂路”,以纪其人。
注释:
①⑥⑦《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2页,第632页,第632页。
②根据清廷的预备立宪安排,各省筹设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地处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咨议局建筑,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主体建筑为红色二层楼房,西欧古典风格。1911年10月11日以后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辛亥革命博物馆所在地。
③《军政府宣言》,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6—297页。
④见冯天瑜1983年5月17日采访喻育之记录。
⑤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⑧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第103页。
⑨(15)据李作栋(春萱)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⑩向訏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又见《蕲水汤先生行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512-513页。
(11)(22)(46)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5页,第33页,第34页。
(12)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皆说是吴兆麟首先提议黎元洪任都督。但11日下午1时咨议局联席会议召开时,吴兆麟并不在咨议局,而与黎元洪同在楚望台,后蔡济民、刘赓藻从咨议局赶到楚望台请黎,吴兆麟方与黎及蔡、刘一起前往咨议局。在下午的会上,吴兆麟主张黎元洪任都督。故在咨议局中午的联席会议上首先提议黎元洪任都督的,不可能是在楚望台的吴兆麟,而有可能是蔡济民。因在咨议局开会的起义士兵中,蔡济民知道1911年4月宝通寺标营代表会议和9月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会议上曾有黎元洪任都督的议案。
(13)(25)(47)(50)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2页,第172页,第175页,第177页。又见李作栋(春萱)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14)《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66页。
(16)(17)《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45页,第45页。
(18)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第85-86页。
(19)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第55-56页。
(20)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21)(29)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第45-46页。
(23)章太炎:《答李西屏一一二》,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51页。
(24)《吴兆麟传》,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人物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66页。
(26)童愚:《八月十九夜所见及其他》,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9页。
(27)当事人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记曰:“二十日(10月11日)上、下午两次会议:上午在楼下会议厅开会,咨议局议员到会很多,专讨论汤化龙的立场和推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下午仅革命同志在楼上开会,强迫黎到场承认就职。”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3-174页。
(28)(45)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34-35页,第41页。
(30)《万迪庥(即万鸿喈)致曾省三书》(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香港: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第86-87页。
(31)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32)孙武:《武昌革命真相》,未刊稿,原件存孙武小女孙莒芹处。
(33)胡祖舜:《六十谈往》,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页。
(34)(67)《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5页;又见《辛亥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年,第35页,第36页。
(35)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武汉: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
(36)向訏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37)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
(38)《民立报》1911年2月10日。
(39)《民立报》1911年1月3日。
(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41)杨铎:《辛亥建国史纲》,见《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第99页。
(42)谭人凤:《石叟牌词》,见石芳勤编《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9页。
(43)石芳勤编《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6页。
(44)《于右任辛亥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4页。
(48)胡鄂公:《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见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下),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959页。
(49)张难先:《六十以后续记》之“武昌起义时和黎元洪三日三夜”,未刊稿,存张难先家属处。
(51)《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情形实录》,见熊守晖:《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上),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第430页。
(52)(53)(54)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1927年作),(“辛”指辛亥年,即1911年;“壬”指壬子年,即1912年),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料辑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
(55)居正的《辛亥札记》(1944年)有“黎都督誓师”一目专记此事。
(56)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武汉: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第61页。
(57)李西屏等多位当事人回忆,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四辑。
(58)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8期。
(59)(60)(63)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45页。
(61)胡贽:《辛亥史话》,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7页。
(62)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见《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一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64)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7页。
(65)见《座谈辛亥首义》,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7页。
(66)《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