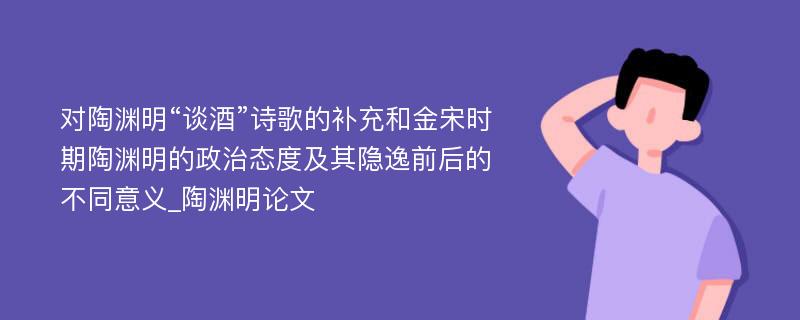
陶渊明《述酒》诗补证——兼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陶渊明论文,两期论文,态度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2)01-0068-08
陶渊明《述酒》诗,经宋代汤汉以来历代注家的注释,诗意虽已大体明白,但是仍有若干诗句存在疑难。或古典字面了解不确,或今典实指了解不足。事实上,《述酒》诗中的这些诗句,对于了解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具有关键的意义。今根据相关文献材料,对《述酒》诗中这些疑难诗句作出释证,并参证相关作品,述论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及其隐居前后两期的不同意义。
一
陶渊明《述酒》:
仪狄造,杜康润色之。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皛修渚,南岳无余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
宋汤汉注《陶靖节诗集》卷三:
司马氏出重黎之后,此言晋室南渡,国虽未末,而势之分崩久矣。[1](PP.12~20)
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离,南也,午也。重离,典午再造也。止作晋南渡说,自通。《书》“我则鸣鸟不闻”,陶正用此。鸟指凤凰,此谓南渡之初,一时诸贤犹盛也。
案:汤汉揭示“重离”指司马,吴师道补正“谓南渡之初,一时诸贤犹盛也”,各有成绩。但是应当说明,第一,此二句之今典实指,并非仅指“南渡之初”,而是指从南渡之初直到东晋中叶的历史(近典)。第二,此是针对刘裕代晋册文贬低东晋历史之时事(今典)而发。
《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设坛于南郊,即皇帝位,柴燎告天。策[册]曰:“……晋自东迁,四维不振。宰辅焉依,为日已久。……”
案:晋元熙二年即宋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晋册书述东晋之历史,所谓“晋自东迁,四维不振”,是抹煞了东晋政权建立,保住了半个中国的历史事实;所谓“宰辅焉依,为日已久”,则是表示东晋建立以后之历史,君昏于上,宰铺无用。陶渊明诗“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之句,表彰东晋历史功绩,正是对刘裕篡晋册书的驳斥。
关于“重离照南陆”之今典。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晋书》卷六《元帝纪》建武元年三月辛卯:
即[晋]王位,……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荣]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毫无定所,九鼎迁洛邑,愿陛下无以迁都为念。”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东晋元帝者,南来北人集团之领袖。吴郡顾荣者,江东士族之代表。……当日北人南来者之心理及江东士族对此种情势之态度,可于两人问答数语中窥知。顾荣之答语乃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与之合作之默契。此两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矣。[2](p.5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东晋元帝·元帝不急于践祚改元》条:
长安破,愍帝俘,司马子孙几于尽矣,琅邪[王]拥众而居江左,削平内寇,安靖东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别为君者。然而闻长安之变,官属上尊号而不许,固请而不从,流涕而权即晋王之位。已而刘琨屡表陈痛哭之辞,慕容廆、段匹磾且合辞以劝进,豫州荀组、冀州邵续、青州曹嶷、宁州王逊,合南北以协请,江东人望纪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后践祚而改元,于是而元帝之位定矣。无求于天下,而天下求之,则人不容有异志而允安。东晋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人情天理之极致。其让也,即国之所以立也。
《世说新语·尤悔第三十三》: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案:由《晋书》所载元帝与王导之合作,可见东晋再造,元帝君臣能齐心合力,以致人才济济。由《世说新语》所载元帝与顾荣之对话及陈寅恪之分析,可见东晋再造,南渡君臣与江左士族能齐心合力,共御外侮,使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奠定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王船山指出的元帝让国所以立国的态度,则可以说是中古时期并不多见的政治品行。《世说新语》所载明帝与王导关于晋得天下之由的对话,则表明东晋君臣能够正面面对西晋早期的阴暗历史并表示惭愧,这可以说是东晋皇室在反省西晋早期历史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个政治自新态度。在中国传统价值尺度衡量下,东晋自造时期的所有这些政治行为,皆是政治道德之体现,亦即政治合法性的取得。陶渊明诗“重离照南陆”,言东晋的白日重新照亮中国南方,正是对东晋元帝开国创业、保住半个中国,以及东晋再造时期所有这些政治光明面的赞美,同时,亦是对刘裕篡晋册书所谓“晋自东迁,四维不振”的驳斥。
关于“鸣鸟声相闻”之今典。
《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西晋末年北人被迫南徙孙吴旧壤,当时胡羯强盛,而江东之实力掌握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之手,……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为]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2](p.68)
陶渊明《命子》诗第四章: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
又第五章:
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案:王导激励南渡士人爱国精神,团结江东士族,抵抗外侮,不愧为东晋开国功臣。与之同时则有平定苏峻之乱的陶侃、温峤,后来则有东晋中叶取得淝水大捷的谢安、谢玄,皆为东晋安邦定国的功臣。其中,陶侃为陶渊明曾祖,渊明引以为家族之光荣。《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载永初元年夏六月刘裕诏封东晋功臣后人为公侯,云:“以奉晋故丞相王导、太傅谢安、大将军温峤、大司马陶侃、车骑将军谢玄之祀。”可见刘裕此诏亦不得不对东晋初至东晋中叶诸功臣加以表彰,以笼络人心,虽篡晋册书与此诏书前后自相矛盾,亦不能顾及。陶渊明诗“鸣鸟声相闻”,言凤鸟鸣声先后相闻,乃是对东晋初至东晋中叶王导、温峤、陶侃、谢安、谢玄等功臣先后辈出、安邦定国业绩的赞美,同时,亦是对刘裕篡晋册书所谓“宰辅焉依,为日已久”的驳斥。
刘裕贬低东晋再造之历史,是为其篡晋制造历史方面的合法性。灭人之国,先灭其史。此之谓也。陶渊明此二句诗,言司马氏东晋再造,使中国半壁河山不亡于五胡,有如白日重新照亮中国南方;宰辅辈出,辅佐晋室振兴,有如凤凰佳音连续不断。此正是针锋相对地驳斥刘裕篡晋册书对东晋历史的诬蔑。国可亡,史不可亡。此之谓也。
二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汤汉注:
魏降汉献为山阳公,而卒弑之。《谥法》:“不勤成名曰灵。”古之人主不善终者,有“灵”若“厉”之号。此正指零陵先废而后弑也。曰“不勤”,哀怨之词也。
明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卷三:
献为山阳公十五年始辛,而零陵王乃以次年进毒不遂,竟加掩杀,不得如献帝之偷余生矣。裕之视丕,倍忍心矣。[3](p.197)
案:汤汉揭示此二句诗以“古之人主不善终者”的谥法即“不勤成名曰灵”,指恭帝之不善终亦即被弑,对解读《述酒》作出突破性贡献。黄文焕补正之为“献为山阳公十五年始卒”,“而零陵王不得如献帝之偷余生”,亦有成绩。要之,此二句诗是言被废的人主死于非命。但是此二句诗的历史背景及诗意,犹可以补充说明。
《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元年六月:
封晋帝为零陵王,全食一郡,载天子旌旗,乘五时副车,行晋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用晋典。上书不为表,答表勿称诏。
《晋书》卷八十九《张祎传》:
刘裕……封药酒一罂付祎,密令鸩帝。祎……因自饮之而死。
《宋书》卷五十二《褚叔度传》附《褚淡之传》:
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二年:
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条:
此其悖逆凶毒为自古所未有,则书法自应明著其罪。乃永初二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官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一若零陵王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
案:“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二句,第一,是以汉献带被废为山阳公,隐喻晋恭帝被废为零陵王;以本无其事的汉献帝之不善终,隐喻晋恭帝之被杀害。(此点为汤汉及黄文焕所指出。)应当说明,在艺术上,此是改变古典以确指今典,即以汉献帝之古典所没有而为晋恭帝之今典所有的死于非命这一关键情节,确指恭帝被杀害。
第二,《宋书·武帝本纪》载,晋恭帝被害后,刘裕“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此正如赵瓯北所指出,“一若零陵王之寿考令终、宋武之恩礼兼备者”。换言之,刘裕杀害恭帝后,制造了恭帝善终、自己为恭帝举哀的骗局,以欺骗天下后世。陶渊明此二句诗,揭露了刘裕杀害恭帝的真相,同时亦即是揭穿了刘裕制造恭帝善终、虚伪地为恭帝举哀的骗局,以昭告于天下后世。
三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
汤汉注:“朱公者,陶也。”近人王瑶注《陶渊明集》:“‘九齿’犹‘久龄’”,“‘练九齿’指修久生之术。”[4](p.98)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西岭,西山。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不食周粟,……诗以峨峨西山内言夷、齐节慨。”[5](p.105)又云:“偃息,卧床不起。《诗经·小雅·北山》:‘或偃息在床。’陶六十岁前后,长期卧病。”[5](p.105)
案:以上诸家注释,仅逯注“偃息”欠确。《诗·北山》原文为“或息偃在床。”息偃犹安卧。偃息有隐居义,如《后汉书·李膺传》:“愿怡神无事,偃息衡门。”
东汉魏晋诗赋使用“偃息”一语,例用于段干木“偃息以存魏”之故事。据《史记·魏世家》及唐张守节《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记载,段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过其闾,未尝不轼。秦尝欲伐魏,终以魏君礼贤,国人称仁,上下和合,遂罢。
汉魏晋诗赋用段干木“偃息以存魏”之典,如《汉书·叙传上》班固《幽通之赋》:“木偃息以藩魏兮”,《艺文类聚》卷八曹丕《济川赋》:“思魏都以偃息”,《三国志·魏书·卫臻传》:“昔干木偃息,义压强秦”,《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干木偃息以存魏”,左思《咏史》第三首:“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偃息”一语,皆为隐居义。
陶渊明诗“偃息得所亲”,犹言隐居得尚友古人。
“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二句诗,是言:伯夷叔齐高隐西山,作殷之遗民,义不食周粟,我今隐居尚友古人,作晋之遗民,义不奉刘宋正朔。在潜意识层面,此二句诗,当还含有:我虽不能如干木偃息以藩魏,亦能如干木偃息以思魏,之意。
“朱公统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得所亲”,此四句诗连读,尚另有一重要意义显示,有待说明。前二句言:我早已如陶朱公归隐养生,远离世间纷争;后二句言:而今则更如夷齐高隐西山,作殷之遗民,义不食周粟。此是借以表示,自己在晋朝时隐居不仕,只是因为“质性自然”、不愿“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在晋亡后隐居不仕,则是作晋之遗民,义不奉刘宋正朔。由此可见,此四句诗,是用上下对比句法,表明自己隐居前后两期之不同性质。
陶渊明用对比句法,以表示自己隐居两期之不同性质,和用夷齐典故,以表示自己不奉刘裕政权正朔,不仅见之于《述酒》一诗,而且见之于《读史述九章·夷齐》一诗。
陶渊明《读史述九章》序:
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
其第一首《夷齐》:
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
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晋恭帝元熙二年条:
“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当是革命时作。……详味先生出处大节,当桓灵宝僭窃位号与刘氏创业之初,未尝一日出仕,而眷眷本朝之意,自见于诗文者多矣。东坡云:“《读史述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岁,吾犹识其意也。”[6](pp.20~21)
案:关于《夷齐》作年与意义,吴仁杰所论甚是。但是《夷齐》诗意犹有待进一步说明。
复按,《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又云:“武王己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正义》:“《孟子》云:夷、齐避纣,居北海之滨。”可见,夷齐在殷周易代之前的隐居地点是北海之滨,隐居是为了让国;在易代之后的隐居地点是首阳山即西山,隐居是为了义不食周粟,即不奉新政权正朔。简言之,夷齐在易代后之隐居的意义,是作遗民,这是不同于在易代前之隐居的新意义。
陶渊明“二子让国,相将海隅。天人革命,绝景穷居”四句,上二句言,夷齐在殷周易代之前,隐居海隅,是为了“让国”;下二句言、夷齐在易代(“革命”)之后,隐居西山(“绝景穷居”),则是“绝”不奉新政权正朔,是作遗民。此正是借以贴切地喻示,自己在晋宋易代之前的隐居,是不愿意“心为形役”;自己在易代之后的隐居,则是绝不奉新政权正朔,是作遗民。”这是不同于在易代前之隐居的新意义。
《述酒》“朱公”四句、《夷齐》“二子”四句,皆用对比句法,表示自己在晋在宋前后两期隐居之意义并不相同。可见这是陶渊明特别要明白地告诉后人的一件事。
《述酒》用陶朱公之归隐,《夷齐》用夷齐在易代之前之归隐,喻说自己在晋之归隐。两诗下二句,则皆用夷齐在易代之后的隐居,喻说自己在易代之后的隐居。用典精密,分毫不爽。
四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汤汉注:
西岭当指恭帝所藏。帝年三十六而弑,此但言其藏之固,而寿夭置不必论。无可奈何之辞也。
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为废帝之死再申低回也。裕即杀帝而君臣之分自在,千古所不能磨灭也。然则帝何尝死哉,是不待以彭殇较论者也。用意至曲至愤。[9](p.198)
清陶澍注《靖节先生集》卷三句下注释云:
且以天容永固、彭殇非伦赞其君,极其尊爱之至。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于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7](p.168)
又于诗末总释云:
天容自永固,谓天老、容成,与下彭殇为对。言富贵不如长生,即《楚辞》思远游之旨也。[7](p.171)
案:汤汉以“天容”指恭帝。近人王瑶注《陶渊明集》从之,谓:“这里祝他偃息丘山,天容永固;至于寿夭,则不必深论。”[4](p.98)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亦从之,谓:“天容二句,谓恭帝虽死,天颜自永在民心,岂可以寿夭论之哉。”[8](p.168)王叔岷《陶渊明诗笺征稿》亦从之:“‘天容自永固’,谓恭帝之仪容永垂不朽也。”[9](p.362)
黄文焕则以“天容”指“君臣之分”。
陶澍解释“天容”,于句下注释认为是指“君”,于诗末总释又认为是指“天老、容成”。其解释“彭殇”,于句下注释认为是“以见乱臣贼子,乍起倏灭于天地之间者,何足道哉”;于诗末总释又认为是“与下彭殇为对,言富贵不如长生”。是自相矛盾。(陶澍于句下注释解释“彭殇”,近似诗意,惜无文献证据,又自相矛盾。)近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从陶澍诗末总释之说,谓:“故作游仙之词,以寄其无可奈何之哀思”[10](p.178),杨勇《陶渊明集校笺》全用陶澍、古直之说[10](p.178),是又从之。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则别出一解:“天容,天人之容,即出众人物的高大形象,指伯夷、叔齐。”[5](p.105)
所有这些解释,似皆滞碍难通。
了解此二句诗的关键,是了解“天容”、“彭殇”的古典、近典和今典。
“天容”一语,出自汉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是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哲学术语。
《春秋繁露·符瑞第十六》: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极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随天之终始,博得失之效,而考命象之为,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春秋繁露·天容第四十五》之“天容”,意义略同。清末舒舆《春秋繁露义证》:“体天心,故天容遂。”)
案:《春秋繁露》所说“天容”,即天之容颜,指天之灾瑞、天之态度,体现天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表示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理人情,则天容舒展(出现祥瑞),亦即天承认政权具有合法性,其政权之历数可以长久。相反,统治者违悖天理人情,则为天所不容(出现天灾),其政权之历数不会长久。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认为,道高于君;政权有无合法性,取决于其政治有道无道;民心体现天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如《孟子·万章上》援引《尚书·周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汉代儒家政治哲学继承了先秦儒家上述理念,只是认为“天容”体现天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与先秦儒家有所不同。“天容”之说,带有汉代人的有意志的天的色彩,但是其内容则仍然是先秦儒家道高于君的理念。
《春秋繁露》是汉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对汉代以后影响深远。当陶渊明要表示对政权合法性的判断时,采用《春秋繁露》“天容”一语,自是恰当的词选。
“天容自永固”之“天容”,指判断政权有无合法性的天道天理。
“彭殇”一语,出自《庄子·齐物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在陶渊明的时代,“彭殇”一语最著名之近典,出自王羲之《兰亭诗序》。(在古典字面、今典实指的用典诗歌,古典字面包括原始古典,和后来使用原始古典的近典;近典由于时代接近此用典诗歌,及可能具有新增含义,因此往往比原始古典更为重要。)
《全晋文》卷二六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作于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353年):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案:在王羲之,“彭殇”是指人的寿命之长短;陶渊明借用王羲之“彭殇”之语,则是指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
何以证明陶渊明《述酒》诗“彭殇”之语,是用王羲之《兰亭诗序》“彭殇”之典?由以下三点,可以证明。
第一,王羲之《兰亭诗序》是东晋家喻户晓之文章,陶渊明自熟悉之,其使用“彭殇”一语,其心意中自然有《兰亭诗序》“彭殇”一语之近典。
第二,按陶渊明《神释》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及《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之句,皆是用王羲之《兰亭诗序》“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典(注:陶渊明《神释》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及《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是否用王羲之《兰亭诗序》“修短随化,终期于尽”,此实际关系到一部魏晋思想史。
“随化”,是指生死一事而言,指顺应自然、接受死亡。魏晋时期社会普遍流行的思潮是求长生不死,而不是“随化”。略述于下。
魏晋之际。嵇康(224-263年)《养生论》:“夫神仙虽不目见,……其有必矣。”《答难养生论》:“玩阴阳之变化,得长生之永久,任自然以托身,并天地而不朽。”
西晋。葛洪(283-363年)《抱朴子·内篇·论仙》:“或问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答曰:……不死之道,曷为无之。”又云:“夫求长生,修至道,诀在于志,不在于富贵也。”
东晋。《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
《晋书》卷一百《孙恩传》:“号其党曰长生人。”(孙恩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即399年起兵,是造反者亦以长生为号召。)
案:由以上文献可见,第一,自魏晋之际至西晋、东晋,社会上下各阶层普遍流行的思潮是求长生学神仙以不死。士人如嵇康、葛洪、采药服食的王羲之,社会下层如孙恩党人等,皆求长生。尤要者,士大夫谈自然者虽多,求长生不死、不随化、超越自然者,却是主流。
第二,王羲之《兰亭诗序》“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语,在魏晋以来求长生不死的思潮中,真是孤明先发。王羲之此语,实与《晋书》本传所载“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不远千里”之事不类,此语或许是觉悟语,或许是兴到语,但是不论如何,此语确实不同于其采药服食之行为,不同于求长生不“随化”的魏晋人之思想。
第三,王羲之《兰亭诗序》“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之语,既然是魏晋以来求长生不死思潮中的孤明先发,而时间又是在陶渊明之前,因此可以确定陶渊明《神释》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及《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是用王羲之此语。
王羲之此语,实际是陶渊明“随化”新自然观的先声。但无论是觉悟语,或兴到语,王羲之并没有大力伸张其意义,如陶渊明《形影神诗并序》之所为。
第四,陶渊明真正大力提倡“随化”的生死观,主张顺应自然,视死如归,以反对魏晋以来的求长生不死的旧自然观,故得称之为新自然观。
陶渊明创立新自然说,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观点。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云:“主张旧自然说者求长生学神仙(主旧自然说者大都学神仙)”,又云:“[陶渊明]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又云:“渊明思想……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页199,页202,页205。)
此自然观就是生死观。所谓新,是就魏晋以来这一特定时期而言。这并不是说魏晋以前无此“随化”的生死观(“随化”的生死观是先秦儒道二家的共同思想),而是说魏晋以来此思想失落已久,陶渊明是此思想的再发明者,也可说是此思想的重新创建者。)。则渊明诗用《兰亭诗序》之典,已非孤证。
第三,《兰亭诗序》“彭殇”一语之下文,即“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语,与刘裕开篡弑之恶例、会自食其恶果之事,若合符契。此正是陶渊明所要表达的意思。
《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所谓“天之历数”,实际是以政权寿命之长短,表示政权之有道无道、有无合法性。“彭殇非等伦”之“彭殇”,犹言“天之历数”之长短,指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彭殇”之“殇”,是指刘裕政权将寿命短暂。何以证明陶渊明诗“彭殇”一语,是指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这是由上下文所决定的解释。因为全诗内容是揭露刘裕篡弑,因此在全诗结尾判断刘裕政权无道、将寿命短暂,实是文从理顺之结尾。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二句,犹有今典。(时事)之实指。
《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皇帝位册:
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鉴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
案:由此可知,陶渊明“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二句诗,正是针锋相对地痛斥刘裕即皇帝位册文所谓“天命”降于有宋,及“天保永祚于有宋”两点。此二句诗,用《春秋繁露》“极理以尽情性之宜,则天容遂矣”之语意,和用《兰亭诗序》“彭殇”之语并借用其下文“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之语,乃是表示:天理自绝不会从无道者之意志为转移,有道政权、无道政权寿命之长短亦将绝不会相同。此是喻指:刘裕篡弑违悖天理人情,虽自称天命,但是天理自绝不会从刘裕之意志为转移;晋、宋政权寿命之长短亦将绝不会相同,宋将寿命短暂,宋开篡弑之恶例,将自食遭篡弑之恶果,后之视宋,犹宋之视晋。
陶渊明认为天理自绝不会从刘裕之意志为转移,是针对刘裕即皇帝位册文自称“天命”降于有宋,所作出的严厉批判。渊明预料刘宋政权将寿命短暂,无法与晋祚相比,刘宋必遭篡弑而亡,则是针对册文所谓“天保永祚于有宋”,所作出的严厉批判。
《述酒》一诗表明,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是是非分明,同情晋朝,痛恨刘裕。认为陶渊明超然物外的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渊明《述酒》当作于永初二年(421年)刘裕弑恭帝后不久。按《宋书》卷九《后废帝本纪》元徽五年(477年)七月,齐王萧道成弑宋帝刘昱,迫贬之为苍梧郡王;复按《宋书》卷十《顺帝本纪》升明三年(即齐建元元年,479年)四月,萧齐代宋,废宋顺帝为汝阴王,五月弑之。萧齐篡宋弑帝,正如刘裕篡晋弑帝;宋立国五十九年,亦远不及晋立国一百五十五年。历史,应验了陶渊明的预见。
《资冶通鉴》卷一一九《宋纪一》武帝永初二年“兵人以被掩杀之。帝帅百官临于朝堂三日”,胡三省注:
自是以后,禅让之君,罕得全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武帝·刘裕篡继以弑》条:
宋可以有天下者也,而其为神人所愤怒者,恶莫烈于弑君。篡之相仍,自曹氏而已然,宋因之耳。弑,则自宋倡之。其后相习,而受夺之主必死于兵与鴆。夫安帝之无能为也,恭帝则欣欣然授之宋而无异心,宋抑可以安之矣;而决于弑焉,何其忍也!
案:胡身之、王船山之议论,犹是后世史家对于过去历史教训之总结。陶渊明诗“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则是站在当时对于未来“历史”发展之预见。渊明、身之、船山,对于历史类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法则的看法,则是一致的。
“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论”二句之用典艺术,至为精深。中国五七言诗歌史上的微言政治抒情诗,从曹植《赠白马王彪》、阮籍《咏怀诗》、左思《咏史》,到陶渊明《述酒》,逐渐形成以用典为主的艺术手法,以含蓄曲折地揭示历史真相,表示对现实政治的抗议。(后来则有庾信《拟咏怀》等继承此一传统。)而陶渊明《述酒》,堪称魏晋时期微言政治抒情诗用典艺术之颠峰。
五
最后,当续说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政治态度。
梁萧统《陶渊明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11](p.15)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宋文帝无嘉三年条:
是岁五月,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本传称:“道济往候,……馈以粱肉,麾而去之。”然本传载此在为镇军参军之前,以[《宋书》]《道济传》考其岁月,知史误也。[6](pp.23~24)
《宋书》卷九十三《陶渊明传》:
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晋恭帝元熙二年条:
要之,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6](p.21)
案:入宋后,陶渊明拒绝檀道济劝仕,是拒绝与刘宋政权合作;又所著诗文只书甲子记年,而绝不书刘宋年号。此皆是以实际行为,表示不奉刘宋政权正朔,亦即不承认其政权具有合法性。
陶渊明的诗歌如《述酒》、《夷齐》,其行为如拒绝仕于宋、不书刘宋年号,表明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不忘故国,不奉刘宋政权正朔,固守了遗民品节。
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饮酒》第二首: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又第十六首: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又十九首:
是时向立年,立意多所耻。
案:由是可见,陶渊明固守作人品节,只是因为存有羞耻之心,是非之心。渊明固守遗民品节,亦只是因为存有羞耻之心,是非之心。不妨借用陈寅恪之语论之:“斯固心中尚存黑白之盲瞽应有事也。”[12](p.187)
《文选》卷五十八刘宋颜延之《陶徵士诔》序称渊明为“有晋徵士寻阳陶渊明”,诔词云:“道必怀邦。”又云:“深心追往,远情逐化。”颜延之不愧为陶渊明的知心朋友,能写出渊明一生的大关节目。“有晋徵士陶渊明”,乃是明白无误地表示陶渊明是晋遗民。“深心追往”,写出渊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爱护,亦是对现实社会价值失落的感愤。“远情逐化”,写出渊明对中国委运乘化的人生哲学的信仰,亦是对追求长生或往生西方的现实风气的批评。“道必怀邦”,则写出渊明对国家命运的关怀,是以道心关怀邦无道的现实,当然包括对普朝的怀念,对刘裕篡晋弑帝的痛恨。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述酒》一诗,表彰东晋历史功绩,批判刘裕代晋册文贬低东晋历史;揭露刘裕杀害恭帝的真相及其制造恭帝善终的骗局;表示自己是晋之遗民,绝不奉刘裕政权正朔;并判断刘宋政权将寿命短暂,是陶渊明在晋宋之际政治态度的鲜明体现。
第二,陶渊明在《述酒》、《夷齐》等待中反复表明,自己在晋朝与入宋后的隐居,具有不同的意义。事实上,陶渊明在晋、在宋的隐居,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人格,但是,陶渊明在晋朝的隐居,只是不愿意“心为形役”,并不具有不奉晋朝正朔的意思;入宋后的隐居,则是不奉刘宋正朔。
收稿日期:2001-06-20
标签:陶渊明论文; 宋书论文; 王羲之书法论文; 述酒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归去来兮辞论文; 晋书论文; 东晋论文; 春秋繁露论文; 刘裕论文; 魏晋论文; 王羲之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