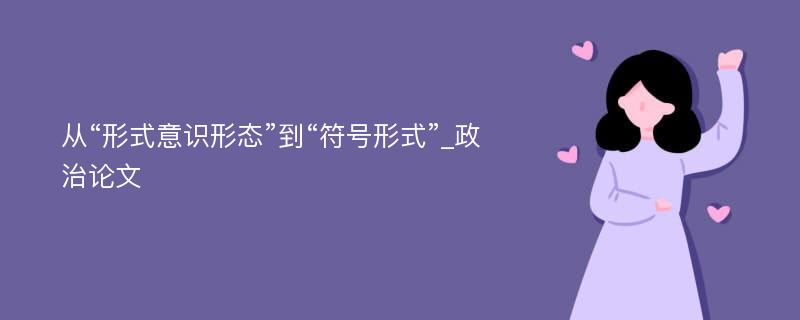
从“形式的意识形态”走向“象征的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式论文,意识形态论文,象征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作家究竟能不能被“培养”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确实建立了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中央文学研究所。这个机构的命运多舛,在“反右”和“文革”时期被停办;1980年恢复重办,更名为“文学讲习所”,培养出了王安忆等一批优秀作家;1984年定名为现称“鲁迅文学院”,连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都曾是该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研究生班学员。作为唯一的国家级作家培养机构,鲁迅文学院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冲击,也与时下的“网络文学”作家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互动。如何看待这一机构存在的意义及其传承态势?本文将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来分析这一机构不同时期之演变所呈现出的由“形式的意识形态”走向“象征的形式”的发展趋势。 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既往的“意识社会学”存在两种向度的局限性:要么将其化约为“知识社会学”;要么从经验性的传统角度,把它进一步化约为关于“组织起来的知识”的习俗机构(诸如教育机构、宗教机构等等)的社会学①。“知识社会学”是卢卡奇的学生曼海姆提出的一种研究方法。曼海姆对“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泛化的处理,将其视为“受社会环境所制约的、是人们(包括参与意识形态分析的人们)所共有的思想与经验模式的交织体系”②。这样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分析就过渡到了一般阐述,不再是一个党派的思想武器,而成为对社会与思想史的一种研究方法,被称为“知识社会学”。曼海姆试图分析影响思想(包括自己的思想)的一切社会因素,从而“为现代人们提供对整个历史进程的一项修正观”③。但是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将意识局限于知识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排除了明显归属于社会范围的“所有这些其他的现实文化过程”④,所以他提出“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文化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对这一复合体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作出分析。这种任务有别于那种只针对习俗机构、构形和传播关系的、已被化约了的社会学;同时作为社会学,它又完全不同于孤立的形式分析”⑤。文化社会学把各种影响因素认定为一个“整体的、相互关联的社会物质过程”⑥。 符号系统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它有“内在的”一面,即符号依赖于关系,又在关系中形成;它又有“外在的”一面,即这种系统依赖于那些使它活动的制度机构,并且在这些机构中形成(因而这些制度机构既是文化的,同时又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还有整体性,这也就是说,一个“符号系统”经过恰当的理解,那它就既是一项特定的文化技术,又是一种特定的实践意识的形式——这些迥然互异的因素在物质性的社会过程中实际上是统一的。⑦ 运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当代作家培养机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迁,能够很好地揭示其中各种复杂关系的冲突、交接;同时也呈现出它在不同时代涵盖的意识形态要素。 丁玲的中央文学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作家培养机构,它似乎从开办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早夭的命运。第一任所长丁玲身上所携带的不仅有她自己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向“左翼”作家转向的复杂性;更有以她为代表的“左翼”内部由“左联”时期经延安一路延续到新中国的各种矛盾冲突。这些冲突表面上体现为“宗派主义”的矛盾,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冲突,也非个人的矛盾化解能够平衡得了的,否则中央文学研究所缩编为文学讲习所之后,由周扬派过来的公木也不会同样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建立本身是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在具体办学过程中,却远远跨越了对苏联的模仿,即便在形式上,它也没能做到它的范本“高尔基文学院”那样的“正规化”。“正规化”问题一直是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的不少领导和学员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结,但是这个问题最终没能解决,也反映出我们还是要在中国具体环境当中探索自己培养社会主义作家的模式。 正如高华所分析的,中国共产党从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就进行了自己的教育实践。最初奉行的是“阶级论”的教育理念,用以对抗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思想。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国共产党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十年间,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⑧。但是对苏联的学习并不是一以贯之的,经过整风运动,根据地教育排除了另一种阶级论教育观——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烙有毛泽东印记的具有中国阶级论教育观。这两种教育观在本质上并无明显区别,但是,苏联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比较重视学校的正规化和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延安的阶级论教育观则更注重政治教育的通俗性和实用性,以及生产技能训练。根据地教育是抗战环境的产物。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动员,教育内容也是为战争和为生产服务,表现为教育内容的简单化和学制的灵活性。⑨ 这种教育理念和实践特征在1938年创办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的办学当中得到鲜明体现。为了培养更多的文艺干部为抗战服务,毛泽东亲自发起创办延安鲁艺,并且在鲁艺办学出现“关门主义”的倾向后,迅速通过“整风运动”来扼杀这一苗头。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按照列宁主张的文学“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思想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确立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标准。《讲话》的精神和延安鲁艺的办学传统随着新中国政权的确立从延安到达北京,成为中央文学研究所“幽灵”般的传统。 但正如“文化社会学”方法所揭示的,机构建立之后,影响它的将会是由各种因素综合而成的整体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分析的每一种因素都将是能动的:在许多不同层次上,每一个因素都将体现一些真实关系。在描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真正的文化过程将显现出来。”⑩中央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后,丁玲作为所长有自己的抱负,可是上级的领导、底下的工作人员,甚至学员,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抛开这些复杂的关系不算,丁玲按照《讲话》精神来办学,紧跟政治,不使中央文学研究所落下当时的任何一场文艺运动,还重点培养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可是仍旧摆脱不了“无产阶级作家”培养的悖论性困境。比如怎样对待传统,怎样选择“经典”,怎样教学,哪些教哪些不教,怎么教;在学员读书的时候如何使他们避免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侵蚀”;把工农兵学员纳入学校体制,进行“专门化”培养,如何能够保证他们原有的阶级属性不被“腐蚀”。这些从苏俄传统中就已携带来的悖论,似乎成为“无产阶级作家”培养无法抗争的“宿命”。正如大家之后看到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举办不到三年就被压缩规模,直到1957年干脆被撤销关闭。丁玲以及与她相关的“文研所”“文讲所”的一些领导干部、学员被打成“右派”或者“右派倾向”分子,宣告这一作家培养机构探索的失败。 但是“传统”总会在不同的时代经由后人有选择性的恢复。时隔二十二年之后,在“思想解放”和“文学热”的背景下,1980年作协恢复了文学讲习所的建制。“新时期”的文学讲习所当然不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鲜明地为政治服务,但是如果我们借用福柯分析“监狱”等机构的设置所使用的观察角度,同样会发现新时期文学讲习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正如德勒兹分析的,福柯的《监视与惩罚》探讨监狱这种“事物”:它既是一种环境建构(“监狱”环境),也是一种内容形式(内容就是囚犯)。但这种事物或形式并不指向意味着它们的“词汇”,也不指向以它们作为所指的能指。它们指向完全不同的词汇及概念,即犯行或犯行者,它们表达一种论述违法、刑罚及其主体的新方法。我们称这种陈述建构为表现形式(11)。形式以两种含义被使用:它形成或组织材料;它形成或目的化功能、赋予其目标。不止监狱,而且医院、学校军营、工厂作坊都是被定型材料。惩罚则是一种形式化功能,治疗、教育、训练与驱使劳动也都是(12)。学校这种机构的功能类似监狱,是“作为内容的形式,界定着一个可见性的区域(“屏视式监狱”就是说,是一个人们每时每刻可以观察一切而又不被发现的地方)”(13)。 文学讲习所这种机构体现的是一种“内容的形式”,也就是说它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即便是在被很多人称为“纯文学”的80年代,文讲所的存在也随时向我们提示着文学的“不纯”。它必然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它必然延续政治教育、承担对文学艺术进行规训的功能。我们从它恢复之后的第一期招收的学员构成就可以初步地感知到这一点,这一期学员基本来自承担了社会情绪抚慰,参与政治重建秩序的“伤痕文学”潮流当中的青年作家和重要的知青文学、改革文学作家。“我们自己时代的主导生产方式的改造也必然伴随着同样激进的对在结构上与之共存的所有古老生产方式的重建,这种改造也必然要由这种重建来完成。”(14)当然,重建肯定不是照搬,也不可能照搬。“象征形式由处于具体社会—历史背景中的人们所接收,这些背景的社会特点塑造了象征形式被他们接收、理解和评估的方式。接受过程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吸收过程;相反,它是一个创造性的解释和评价过程,一个象征形式的意义被主动地构建和再构建。”(15)新时期的文学讲习所从形式上接续了20世纪50年代的“家谱”,把恢复后的第一期排为总第五期;招生方式、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也基本延续50年代的传统,但也创造性地增加了新的政治教学内容和文学内容。 恐怕令很多一直主张“纯文学”观点的人们要失望的是,新时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们似乎并不抵制这种意识形态建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在为庆祝鲁迅文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文集里,我们看到很多有关文讲所的文字,也是充满深情地回忆了那段“苦中作乐”的学习时光,尤其是其中的“同窗情谊”。学员们带着正面的感情认同自己的母校,对这一段资历引以为傲。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 交换过程的社会有效性是这样一种现实,它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参与其中的个人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正确逻辑;就是说,它是这样一种现实,它的本体一致性暗示出参与者的某些非知。如果我们“知道得太多”,洞悉了社会现实的运作机制,这种现实就会自行消解。 这大概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维度: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意识”,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幻觉性再现,相反它就是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自身。“意识形态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正是它的存在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有效性,是意识形态有效性的再生产,它暗示单个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意识形态性的”并非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意识”,而是这种存在本身,虽然它为“虚假意识”所支撑。(16) 这段学习经历确实为不少学员积累了必要的“象征资本”,从他们当中出产了不少作协官员和获各种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他们也通过一种情感的记忆与抒发,将自己融合进了有关80年代文学热的整体“感觉结构”当中,想象性地弥合了意识形态和“纯文学”之间的缝隙。 相比起来,90年代那段受市场经济冲击的鲁迅文学院办学反而没有80年代在“文学热”时代背景掩护下的天时地利。看上去,“政治”松绑了,办学自由了,而实际上这段日子对于鲁迅文学院来说最难过,经费上失去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招生也需要收费,为了筹措资金,需要换着花样办班吸引学员。这一段时期,也是工作人员觉得对学员“最难管理”的时期。因为“收费”这样的经济行为改变了学员的认同结构。佛克马和蚁布思对“经典”构成的分析很适合这个时期“政治”和鲁迅文学院关系的描述,“只有当一政治或宗教机构决定对文学的社会作用较少表示担忧时,它才会在经典的构成方面允许某种自由。但如果这种自由将被给予了的话,那么结果有可能是文学(和作家)将会失去它们在政治和社会上的某些重要意义”(17)。“自由”有时候意味着“你已经不再重要”。 鲁迅文学院再次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是新世纪之后,中宣部拨款为鲁迅文学院改善办学环境,每年拨巨款支持他们开办“高研班”。“高研班”从形式上努力恢复延安鲁艺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办学传统,采取短训的形式,讲座式教学。由于师资力量强大,都是各级专家、领导,对学员的要求也高,而且直接与主旋律评奖制度等挂钩。“高研班”从此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金字招牌”,每年一个省(直辖市)的指标根本不够分配,各地都出现争抢名额的现象。在这种利好形势下,鲁迅文学院不仅加强了对传统作家的培训,对80后作家和网络文学作家也进行培训。尤其是网络文学班,目前还属于探索的阶段。 虽然表面形式接续传统,但新的辉煌恢复的其实不是政治和文学的蜜月关系。学员对新世纪鲁迅文学院的认同更多的是出于对“象征资本”的追求。约翰·B.汤普森区分了三种形式的资本:“经济资本”,包括财产、财富和各种金融资本;“文化资本”,包括知识、技能与各种教育资格;以及“象征资本”,包括积累的赞扬、威信以及与某人或某位置有关的认可(18)。进入“高研班”,从现实的考虑能够走进主流的文学“圈子”,利于获得各种国家级文学奖项,结识各类高级官员,成为他们的“学生”。这些资本日后还可以与经济等其他资本相互转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为何从中央文学研究所到文学讲习所到鲁迅文学院,很多人追求的“正规化”理想一直不能实现。因为这种机构的设立本身其实就是为了“使这个‘圈子’的扩展得到有效的控制,并且使这种扩展在文学规范的秩序中进行”(19)。它一开始的理想就不是设立成大学中文系,更不是一般的“普及”机构或在西方社会很常见的那种“小说创作速成班”之类的培训机构(20)。从培养效果来看,这种机构选择作家与其说是“培养”不如直接理解为“控制”。“压制性主体(不管是主人、殖民主义者或是统治阶级)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准客观性过程,这一过程似乎事实上已不可挽回地存在着。这一控制过程甚至进入到人体本身的体验。”(21)事实上,几十年来,很少有作家是依靠这种机构“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是已经有了创作成绩才有“资格”进入这个机构,然后这个机构又更明确地赋予他们一种更稳妥的“资格”。这个机构成功“培养”出来的大多数是文学工作者,比如官员、编辑等等,倒不是作家。对此机构来说,他们的培养“结果”不如“形式”的存在本身来得重要。 杰姆逊用“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指称“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22)。这些不同符号系统会包含限定性矛盾。对形式的意识形态的分析,就是要寻求解释文本内部一些断续的和异质的形式程序的能动存在。“如果得以适当完成,应该揭示这些古老的异化结构——及其特有的符号系统——在形式上的固持,在所有新近产生的和历史上原生的种种异化——如政治统治和商品物化——的重叠之下,已经成为所有文化革命中最复杂的文化革命即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因素,在这场文化革命中,所有先前的生产方式都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在结构上相共存。”(23)这也是我们试图通过对中央文学研究所-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这种机构的沿革史的分析试图呈现的复杂性所在。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一独特当代作家培养机构的存在无论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历经80年代发展到现在,它的形式一直作为内容而存在,它的形式本身就是意义,在这个形式身上,各种诸如文学、政治、社会或者经济等等关系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尤其到了新世纪,它越来越发展为一种“象征的形式”。从它这里,“各种有意义的行动、物体和表述——关系到历史上特定的和社会上结构性的背景和进程”(24)一一呈现出来。揭示它们,也是我们研究的意义所在。 ①④⑤⑥⑦[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147、148、148、149、149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③(15)(18)(2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译,54、54、168、163、150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⑧⑨高华:《革命年代》,170、17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⑩[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分析》,赵国新译,见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12)[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杨凯麟译,35、3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3)杜小真:《福柯集》,56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14)(22)(23)[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90、66、8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2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7)[荷兰]佛克马、蚁布斯:《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4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9)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比如芝加哥最成功的独立作家工作室“作家阁楼”等。英美国家很多大学普遍开设创意写作学位项目,美国当代作家几乎都获得了创意写作学位,绝大多数知名作家也都在大学任教于创意写作专业。参见杰里,克里弗:《小说写作教程》,王若定译,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2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标签:政治论文; 文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鲁迅文学院论文; 作家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